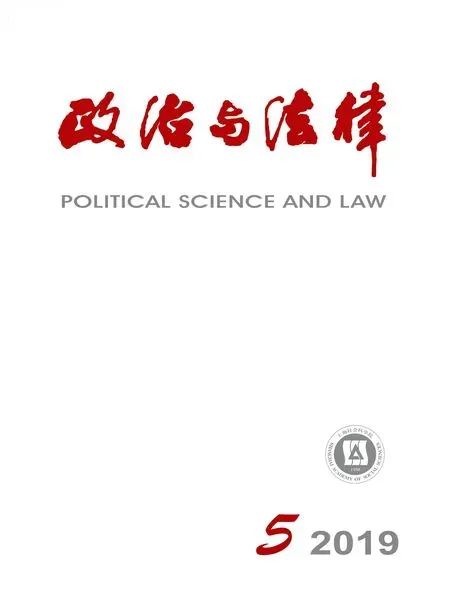論作為新興權利的代際權利*
——從人類基因編輯事件切入
錢繼磊
(濟南大學政法學院,山東濟南250022)
一、“基因編輯人”①:從理論到事實
①為了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因人類基因編輯技術而誕生的“基因嬰兒”之權益,筆者于本文中使用“基因編輯人”這一比“基因嬰兒”更為一般的概念來指涉這類自然人。
在2018年前,除專業人士外,絕大多數人對于人類基因編輯技術及相關問題尚不甚了解。人文社科界學者也未有對此給予太多關注和討論。自2018年11月26日始,這項技術因一則事件而廣為世人所知。這一天受關注不僅是因為將于次日召開的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編輯峰會,而且是因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對基因編輯嬰兒“健康出生”這一爆炸性新聞的宣布。據稱這對女性雙胞胎的一個基因經過了修改,由此使得她們出生后即獲得天然抵抗艾滋病的能力。這則新聞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全球科學群體,在當今自媒體時代可以說迅速席卷了整個人類社會。這意味著,當人們還在將主要目光集中于未來的“智能人”(或人工智能)時,基因編輯后的“基因人”卻突然來到現實世界,成了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這種將基因編輯技術用于人類胚胎并孕育出了生命的“壯舉”幾乎受到異口同聲的批評和譴責。這些批評和譴責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技術層面的,認為當前基因編輯技術用于人類胚胎尚不夠成熟,存在脫靶及未知的可能風險等;二是倫理層面的,認為這種基因技術用于人類胚胎違背科學倫理;②參見艾丹:《科學倫理的底線沒有試探的“自由”》,《湖北日報》2018年11月28日,第007版。三是安全層面的,認為這種行為將會對人類的基因庫造成永久且不可逆轉的污染和改變,威脅到人類整個基因庫的安全性;③參見方舟子:《人類胚胎研究容不得半點輕率》,《環球時報》2018年11月28日,第015版。四是個人權利層面的,認為目前還難以有效保護好這兩個嬰兒的個人隱私。④參見晁星:《“基因編輯”背后的倫理之門誰來守》,《北京日報》2018年11月28日,第003版。另外,也有人對于這種技術用于人體可能面臨的倫理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并提出了一些解決措施。⑤參見方秀丹:《人類基因編輯技術面臨的倫理問題及對策研究》,昆明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第22~32頁、第41~49頁。
如果說之前的相關研究還只是對于未來風險可能的理論準備與防范預測,那么隨著首例基因編輯人的出生,人類不得不面對無法改變的既定事實。對于此次事件,也有人從法教義學角度,試圖從民法、行政法乃至刑法角度對基因編輯行為的法律責任進行分析和探討,但問題是,暫且拋開現代法律自身的滯后性、刑法的謙抑性以及“罪刑法定”等不論,即便是依據現行法追究了當事人的責任,也無法解決現代法律面對涉及人類權利的高新科技所帶來的未知結果和風險。
由上可知,學界對于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的限度從倫理、道德、法律等方面進行了一些研究,并就立法模式、隱私權利保護等方面提出了建議。然而,從法哲學角度對此進行反思性研究尚顯不足。法學乃權利之學,這種權利本位其實是與權利自身的邊界密切相關的。不過,權利的邊界是止于自身的義務還是止于公共的善,或是止于最大的不傷害,人們對此存在著不同的論爭。若從這個的視角講,針對上述事例,既有研究并未充分涉及這樣一些問題:誰應當具有作為決定基因編輯人是否誕生于世間的權利,其未來的父母、相關專業人士或醫學倫理委員會之類的組織是否應當擁有此權利;是否父母基于生育權、專業人士基于科學探索自由權、醫學倫理委員會基于職業權力可以單獨或共同行使決定權。這些問題背后更為深層次和根本的問題是:作為父母之當代人的生育權與作為其子女及其后代的后代人免于處于不可知風險的自由與權利之間的張力問題。這不僅意味著在當下人工智能、互聯網、生物工程等新科技爆炸式發展所帶來的未知風險對傳統的個人權利形成的法理和法治層面的新挑戰,而且也使整個人類日益加速成為風險的命運共同體。由此,在當下人類風險命運共同體時代,對作為新興權利的代際權利理論進行梳理、反思和闡釋就顯得不僅必要而且迫切。
二、代際權利是“虛妄”的嗎
從既有文獻看,“代際權利”的概念目前多在社會學等領域被使用,并不是一個常用且具備共識的概念,⑥以中國知網為例,截止2018年11月底,以“代際權利”為關鍵詞搜索,可得到以下文獻。董海軍:《代際權利與話語:“80后”社會評價的變遷——基于長沙、杭州兩地的調查》,《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2年第3期;John Aron Grayzel等:《代際權利與責任語境下的青年展望——來自非洲的啟示》,朱國棟、楊桂萍譯,《中國青年研究》2008年第5期;田忠輝:《“80”后文學的代際權利與社會權力》,《文藝爭鳴》2009年第12期。遺憾的是,這些文獻并未對“代際權利”進行詳盡的闡釋和限定,由此,何為“代際權利”實質上是混亂而模糊的。而“后代人的權利”概念則更多地被使用。⑦多數學者則使用“后代人權利”,如劉雪斌、趙融:《論后代人權利的法律保護》,《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劉衛先:《后代人權利理論批判》,《法學研究》2010年第6期;劉衛先:《后代人權利論批判》,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李冰強:《虛幻的權利與現實的義務——對〈后代人權利論批判〉的本質解讀》,《政法論叢》2013年第5期;羅飛、馬永雙:《代際倫理視野下的后代人權利保護問題研究》,《產業與科技論壇》2014年第4期;梁增然:《保護環境是后代人權理論的立論目的——讀〈后代人權利論批判〉感言》,《公民與法(法學版)》2014年第4期;徐祥民:《環境保護走向何方——評〈后代人權利論〉批判》,《荊楚學刊》2014年第3期。然而,從邏輯上講,若“代際權利”得以證成,其前提應是“代”及“代際”命題的成立,然后才是不同代之間的權利關系問題,因為當代人享有權利應該不是理論問題,所以這其中應該又是以“后代人權利”成立為前提的。由此,是否存在不同的“代”以及不同代的不同權利是否成立,就構成了判斷代際權利這一概念是否“虛妄”的兩個核心要素。
(一)人類存在不同的“代”嗎
從生物學上意義講,“代”是一種自然界物種劃分、物種進化與更替的事實性存在。任何有生命的物種都是通過不同“代”而實現生命的延續的。可見,“代”是一種生物事實的存在。代際關系則意味著上下相鄰兩代之間的關聯,如生物學說的遺傳與變異等。換言之,生物學意義上的“代”意指物種的傳宗接代,新一代的誕生與發展伴隨著上一代的老化與衰亡。就作為高級動物的人而言,其本身就是生命自然的組成部分,其自身的延續也離不開這種代際傳遞,而這種代際關系發生在家庭中并成為家庭成員之間社會關系的前提與基礎,由此,對于代際關系較早給予系統關注的是社會學家。
早在1928年,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在其著作《代際問題》中就對代際關系與代際問題從社會學研究角度進行了專門研究。當然,對人類不同“代”(generations)給予提及并關注的歷史要久遠得多。在西方,古希臘的柏拉圖就提及了“每個家庭由現在世代、未來世代以及他們的祖先所組成”的主張。⑧高景柱:《正義的歷史維度——以羅爾斯的代際正義理論為中心的考察》,《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明確論及代際問題的則屬英國的埃德蒙·柏克,他曾從憲政共同體意義上說過,國家“乃是一切科學的一種合伙關系,一切藝術的一種合伙關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種合伙關系。由于這樣一種合伙關系的目的無法在許多代人中間達到,所有國家就變成了不僅僅是活著的人之間的合伙關系,而且也是在活著的人、已經死了的人和將會出世的人之間的一種合伙關系”。⑨[英]埃德蒙·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29頁。后來美國的托馬斯·杰斐遜和詹姆斯·麥迪遜等從憲政共同體角度對不同代之間的權力約束及權利保障進行了激烈的論爭。⑩參見高景柱:《論正義與代際關系》,《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就我國而言,傳統思想對于人類不同“代”際關系的關注與其說是基于生物學上的陳述,不如說是對社會倫理層面的強調。作為主流傳統思想的儒學,其實解決的就是代際倫理問題,在先秦儒家思想體系中,“仁”為其核心,“孝”與“愛”為其兩翼。“孝”并非父對子的單向度的道德要求,而是與“慈”作為父對子的道德責任共同雙向的代際契約倫理觀,因而才有《顏氏家訓·治家篇》的“父不慈,則子不孝”。
就我國法學界而言,對于代際問題往往給予忽視,而是將其隱含于對“后代人權利”主張的闡釋之中。然而,人類不同的“代”是否成立卻是討論“后代人權利”的前提性問題。因為如果人類不同的“代”本身就是無法成立的偽問題,何談后代人權利呢?國內較早討論后代人權利的“論未來世代權利的法哲學基礎”及“論后代人權利的法律保護”的文獻可以證明這一點。①劉雪斌最早使用的是“未來世代權利”概念,而后來一直使用的是“后代人權利”概念,可見在他那里,兩個概念是不做區分的。參見劉雪斌:《論未來世代權利的法哲學基礎》,《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7年第1期。劉雪斌認為,“當代人的行為引起了資源消耗、核廢料、環境污染以及基因改變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都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后代人利益,對后代人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威脅”,由此“對于作為一種新型權利的未來世代權利如何保護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法哲學問題”。②同上注,劉雪斌文。在之后的論文中,他又提出,“在20世紀中葉以后,隨著科技發展和經濟進步引起的資源消耗、核廢料、環境污染以及基因改造等問題,不僅影響同代人的利益,而且已經嚴重影響了后代人的利益,這種情況對于后代人乃至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威脅”,并對“后代人權利的內容”、“各國對后代人權利的法律保護”、“國際社會對后代人權利的法律保護”等方面進行了闡釋。③同前注⑦,劉雪斌、趙融文。可見,該學者實際上是將當代人與后代人之分作為一個不爭事實來看待并加以認可的。
對于人類不同“代”的問題化反思則是由學者指責當代人與后代人二分的荒誕性開始的。這種觀點認為,“代際理論的根本錯誤在于虛構了多個人類主體,即所謂過去世代的人類、現在世代的人類和將來世代的人類”。④徐祥民、劉衛先:《虛妄的代際公平——以對人類概念的辨析為基礎駁“代際公平說”》,《法學評論》2012年第2期。接著,該學者進一步論證了代際論者之所以會犯這種錯誤的原因在于其錯誤地把本為集合概念的人類偷換為類概念的人類。集合概念所反映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事物,即一個“個體”,類概念所反映的則是一類個體,即多個“一”。由此,“當他們說過去世代、當今世代和未來世代,并把它們放在辯說公平、簽訂契約的雙方或多方的位置上時,實際上便把集合概念的人類改變成了類概念的人類。這個類概念是對過去世代人類、現在世代人類和將來世代人類的一般稱呼,事實上,語境中,人類是唯一的集合體,它只是‘一’,沒有甲乙丙等同類項”。⑤同上注,徐祥民、劉衛先文。
對于上述對“后代人權利”以及后面將討論的代際權利看似連根拔起式的質疑與反思,有學者給予了回應,指出“判斷環境法上的‘代際公平說’是否‘虛妄’,既應建立在科學的邏輯論證基礎之上,又應建立在法律社會價值的判斷與選擇基礎之上”,以集合概念、類概念二分為基礎的預設路徑實質上忽略了邏輯的事實要素,因而其進一步展開必然也無法達到論證結論(價值的正確)。⑥參見郭武、郭少青:《并非虛妄的代際公平——對環境法上“代際公平說”的再思考》,《法學評論》2012年第4期。然而,該論者的這種回應盡管揭示了對后代人及其權利質疑者的唯邏輯論,但也存在著不足。在筆者看來,對當代人與后代人之分的質疑論者實質上對后代人本身有誤讀,而進行回應的論者依然僅是在其所預設的邏輯層面上展開。在質疑論者的另一篇長文中,作者借用其他學者的表述對“后代人”進行了界定——“和現在的世代沒有重疊的那些世代”,即“那些將社會在未來,但是直到現在最后一個活著的人死亡后還沒有出生的未來世代”。⑦See Lawrence B.Solum,To Our Children's Children's Children's:The Problem of Intergenerational Ethics,35 Loyolal of Los Angeles L,171(2001).轉引自前注⑦,劉衛先文。其實這種對后代人的理解是對以前諸多學者觀點的認可,如有學者就認為“未來人不在場,只是一個虛構的主體”。⑧魏波:《存在意義的傳承見證代際公平》,《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11期。
然而,需要反思的是,是否就如質疑論者所言,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截然二分,以及在何意義上二分。在筆者看來,之所以包括質疑論者在內的諸多學者認可不同代際之分,是因為其將研究問題的視角僅僅限定在了生態環境問題上。因為后代人權利理論的興起本身就是基于環境危機以及人們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并得到眾多學者支持,從環境法學領域逐步擴展到法哲學、政治哲學等領域。⑨參見前注⑦,劉衛先文。由此,不論是從較早在《動物及未來世代權利》中提出后代人享有權利的約爾·范伯格,⑩Joel Feinberg,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Future Generation,pp.4~5,13~14,http://site.voila.fr/bibliodroitsanimaux/pdf/FeinbergtheRightsof AnimalsandFutureGeneration.pdf,2019年1月訪問。到主張代際平等及代際信托論的愛蒂絲·布朗·魏伊絲(Edith Brown Weiss),①Edith Brown Weiss.The Planetary Trust:Conser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ality.Ecology Law Quarterly,1984,11(4),p.495~581.還是將環境問題、時間距離、非同一性和未來人偏好問題視為代際正義可能性論證的困難立場,②劉雪斌:《代際正義研究》,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頁。堅持“未來人與現代人物交涉”、③周謹平:《論代際道德責任的可能性基礎》,《江海學刊》2008年第3期。“‘在場’的當代人與‘不在場’的后代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其實質是當代人對后代人所承擔的單方面的義務”等觀點,④鄔曉曄:《代際倫理:可持續發展倫理的新維度》,《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8年第1期。大多都未擺脫在環境生態的視角上加以觀察的視域。
從更寬泛的角度看,生態環境只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外部因素和條件,盡管它非常必要。其實,除了作為外部條件的生態環境外,人類自身也是其得以延續和發展的必要前提和要素,甚至是更為根本的目的性要素。盡管生態環境情況會影響人類自身的生存、繁衍與發展,但作為人類生存外部條件的生態環境與人類自身的內部環境生態并非一回事。如果說人類之所以關注生態環境問題是因為科技的發展導致人類對外部自然資源環境的認識、改造、利用能力的不斷增強的結果,那么隨著人工基因編輯等生物新技術的不斷提高,人類已經具有了對人自身生物信息的認識、改造和利用的能力,從而使人自身的生物信息也成為一種內在的資源、環境生態,并使其被侵犯和破壞成為現實的可能。
由此,如果對于后代人的理解僅限于傳統的環境生態的保護與有效利用的視角,則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似乎是在場與不在場的關系。然而,如果將當代人與后代人關系置于人自身所帶的生物信息也是一種環境生態,也需要環境生態保護的視角,則兩者的關系就不可能是不在場的關系,而是通過人類共同的基因世代延續并傳遞下去,即便是在遙遠的未來世代,人類的基因編碼也具有無法割裂的連續性與共同性,不論人類自身主觀上是否意識到并承認它。
恩格斯的兩種生產理論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他指出:“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分為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頁。參見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5頁。傳統上對環境生態問題的關注是基于第一種生產,忽略了人類自身生產更為根本和目的性方面。即便是有個別學者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有的談到了通過人工方法改變人的一些基因強加給后代人,存在難以預料的長遠后果,⑥參見汪堂家:《代際倫理的兩個維度》,《中州學刊》2006年第3期。劉衛先:《自然體與后代人權利的虛構性》,《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年第6期。有的認為“即使不存在試圖通過基因技術控制全人類的野心家,基因技術也確實對后代人的生存和人類進化構成嚴重的威脅”,⑦劉雪斌:《論代際正義的原則》,《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4期。但他們并未對此進行系統討論,更未意識到兩種生產視角所導致的對后代人的不同乃至沖突的理解。
可見,“代”(或世代)不僅是個家庭意義上的,還是社會意義和時間順序意義上的概念。⑧See Joerg Chet Tremmel,A Theory of Integenerational Justice,Earthscan,2009,pp.19~21.人作為主體,并非是唯一樣態,而是作為類主體、群體主體以及個體主體的同時存在。⑨參見楊盛軍:《環境代際非正義之主體原因及其對策探析》,《濟南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作為未來世代的后代人與當今世代不僅有可能存在重疊,而且必然存在重疊關系。⑩參見高景柱:《論正義與代際關系》,《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由此,對后代人的理解不僅是未來的、遙遠的、不在場的后代,而還應該關注與我們重疊、交叉、共同生活的眼前的后代人。
(二)后代人應當有其權利嗎
即便是后代人作為獨立的存在得到認可,也不意味著后代人就可以成為權利的主體,因為作為權利主體需要具備一些必要條件。可以說,當今世界是個“權利世代”,①[美]路易斯·亨金:《權利的世代》,信春鷹等譯,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人們習慣用“權利”去應對和解決各種問題。然而,對于何為權利,“就像問一位邏輯學家一個眾所周知的問題‘什么是真理?’同樣使他感到為難。”,②[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59頁。J·范伯格則干脆將權利這一概念視為“簡單的、不可定義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③[美]J·范伯格:《自由、權利和社會正義——現代社會哲學》,王守昌、戴栩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2頁。國內學者曾對權利概念的起源及其成長歷史進行過詳細的考察和論述,④參見夏勇:《人權概念起源——權利的歷史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頁。也有學者對權利學說進行了較為全面而詳細的梳理歸納。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頁。參見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5頁。囿于論旨及篇幅,筆者于本文中并不打算對權利本身重點討論和闡釋,而是重點就國內目前對后代人權利質疑者關于權利的誤讀進行剖析。這些質疑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劉衛先教授。他在論證后代人權利虛構性時,專門對權利的虛構性進行了揭示。劉教授認為,權利以文化為存在的環境、以個體主義為權利的主體哲學、以自由為權利的主導價值,是利益有限度轉化的結果,總之既有權利主體,“無論是‘美國殖民者’、‘奴隸’、‘女人’,還是‘印第安人’、‘勞動者’和‘黑人’,都屬于‘現實中的人’。自然體權利和后代人權利只不過是一種理論的虛構”。⑥參見汪堂家:《代際倫理的兩個維度》,《中州學刊》2006年第3期。劉衛先:《自然體與后代人權利的虛構性》,《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年第6期。
然而,劉衛先教授對權利的這種梳理與闡釋卻存在著誤讀,最為要害的在于其僅僅是一種歷時性視角下對權利過去的回顧,這導致其忽略了權利在共時性視角下對現實乃至未來問題及風險的智慧性應對意義。首先,他指出,權利以文化為其存在的環境,“文化是人所創造的,文化的主體只能是人”。⑦同上注,劉衛先文。然而,權利還是人類在應對和解決各種困難和風險而形成的智慧性結晶,其自身也會隨著實踐問題及風險的變化而發生變化。也就是說,權利不僅僅面向過去和現在,還應當關照未來;它不是靜止的,而是隨著人類面臨的問題及風險而變動,不僅是作為文化意義上的“地方性知識”,而且是可以被普遍適用的實踐智慧。其次,他還指出,權利以個體主義為其主體哲學,權利主體的個體主義蘊涵著“權利主體的主動性和權利功能的向內性”。⑧同前注⑥,劉衛先文。然而,這種權利哲學只能是一種古典自然法傳統意義上的,是一種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即第一代權利意義上的理解,而后來的第二代、第三代權利理論所倡導的社會權、生存與發展權、環境權等都對這種原子式個人主義進行了修正,⑨對于人權劃代理論,學者有不同的分法。參見齊延平:《和諧人權:中國精神與人權文化的互濟》,《法學家》2007年第2期;徐祥民:《環境權論——人權發展歷史分期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徐顯明:《和諧權:第四代人權》,《人權》2006年第2期;邱本:《論人權的代際劃分》,《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由此個體主義在哈耶克的方法論意義上更具有意義。然后,對于他所主張的權利以自由為主導價值,同樣更多地是第一代權利理論意義上的,而并不適用于所有權利。因為除了自由外,還有安全、平等、正義、效率等價值,而其間的價值位次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因特定社會問題及風險所需而表現不一,并且視其在具體部門法中所要解決的特定問題而不同。最后,在其論證“利益轉化為權利的限度”中,將利益轉為權利限定為以下條件,即利益的客觀存在、對利益進行權利保護必須體現主體的獨立人格需求等。⑩參見前注⑥,劉衛先文。這樣,該論者的利益范圍僅僅限于既存的、確定的可見利益,而將避免不可知的未來風險的安全等利益排斥在外。同時,對于利益轉化為權利的保護主體的獨立人格需求也僅適用于現實中的完全權利行為能力主體,而對尚不具備完全權利行為能力卻處于未來可能風險的不安全中的主體卻被排斥在外。
總而言之,正是該論者的這種歷時性視角,將權利僅僅固定于過去既有的認識,從而使權利的主體僅被限定于現實的具有完全權利行為能力的獨立的個體,這才導致其所主張和闡釋的權利理論的不足。權利理論從來都是處于自我發展變化中的,都是其所處的特定時空下人類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的有效應對的智慧。在當下科技新時代,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等使得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新風險、新問題、新挑戰,權利理論也應當自我發展,使其不僅能夠為既定的現實問題進行有效應對和提供救濟,還應當能夠有效防范和避免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未知風險。由此,后代人權利應當是新科技時代下權利理論的新發展,是一種新興權利,代際權利則是對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權利的張力與有效安排進行的新思考。
三、代際權利的法理基礎: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代際正義
當然,即使上述后代人權利暫且得以確認,也只是概念層面上的,作為新興權利的代際權利以及作為其重要前提支撐的后代人權利依然缺乏背后的深層次法理基礎。由此,筆者將在法理層面對其進行更加深入的討論與闡釋。
(一)后代人權利的既有理論基礎反思
從既有研究看,學者將后代人權利的理論建立在代際正義下的代際契約論、代際平等下的代際信托論以及跨代共同體理論等基礎之上。
在環境法領域,代際契約論以克里斯汀·西沙德—弗萊切特(K.S.Shrader-Frechette)為代表。他認為,在我們和后代人之間存在著一種可稱為代際接力式的相互性——跨越時間的鏈式相互性。退一步講,即使不通過相互性,只通過人的理性、正義等要素也可達成社會契約,并且,“某些形式的契約之所以能夠形成,不是因為達成了預先安排好互惠利益的協議,而只是因為契約的一方主動選擇了接受義務”。①參見[美]維西林、岡恩:《工程、倫理與環境》,吳曉東、翁端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04頁、第206~207頁。這種代際契約理論是以西方傳統社會契約論為基礎的,尤其受約翰·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影響,甚至直接借用了羅爾斯的“原初狀態”假設和“無知之幕”理論。②韓立新:《環境價值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頁。羅爾斯認為,“將正義延伸到包括我們對未來各代人義務(包括正義儲存的問題)”,③[美]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頁。是其正義理論遇到的難題之一。不過他認為,由于無知之幕是徹底的,“在假設所有其他各代都要以相同的比率來儲存的基礎上,他們愿意在每個發展階段儲存多少。……[他們]必須選擇一個能分派給每一個發展水平以一種合適的積累率的正義的儲存原則”。④同上注,羅爾斯書,第278頁。然而,這種對各代人利益的考慮與其所假設無知之幕的原初狀態的兩個條件存在矛盾:一個是原初狀態當事方是理性的,其動機在于“努力為自己尋求一種盡可能高的絕對得分”,⑤同上注,羅爾斯書,第278頁。而此種情況下契約的達成實質上是一種作為互利的正義;另一個是原初狀態當事方身份,羅爾斯要求人們從現時的角度來解釋和對待不同時代的人,實質上是一種作為公平的正義。這樣,代際契約所要實現的作為公平的正義與代內契約所秉持的作為互利的正義同時出現在無知之幕的原初狀態下當事方那里。作為互利的正義建立在理性自利或互利互惠基礎之上,作為公平的正義則要求當代人為后代人做出讓步和犧牲,承擔義務和責任。可見,兩者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而“羅爾斯在探討其一般正義論和代際正義理論時,往往把這二者混為一談”。⑥參見楊通進:《羅爾斯代際正義理論與其一般正義論的矛盾與沖突》,《哲學動態》2006年第8期。也正因為如此,有學者“質疑‘后代人權利’的代際契約說基礎”,認為社會契約論中“契約的達成和實現的四個核心要素,即‘締約方力量平等、締約方參與和保持契約的原因一致、契約的維持受到社會控制功能的制約、締約雙方具有互惠性’”,在代際契約的情況下,“都是無法實現的”。⑦劉衛先:《質疑“后代人權利”的代際契約說基礎》,《中州學刊》2011年第1期。
如果說代際契約所依據的代際正義是作為公平的正義,那么這種能夠使得第三方(即后代人)受益的正義原則,因為原初狀態的正義環境要求大家相互間是冷漠的,所以不可能是基于“對于他們的直系后裔義務”。⑧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28.由此,有學者認為,即使客觀上承認在原初狀態下的人們選擇了這樣一個能夠使第三方受益的作為公平的正義原則,那也僅是一種偶然的結果,這就意味著人們也可以反對建立這樣的一個義務。這種缺乏嚴格服從義務的選擇之結果,也就“不可能在現在世代和作為第三方的未來世代建立任何具有約束的正義關系”。⑨劉雪斌:《論一種作為公平的正義》,《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年第5期。
這樣,代際正義下的代際契約論無法給后代人權利提供具有說服力的法理基礎,也就無法支撐起作為新興權利的代際權利理論。之所以如此,在筆者看來,其更為深層的原因是,不論是約翰·羅爾斯還是弗萊切特,他們所著力解決的只是作為人自身之外的世界,如資源、生態環境等利益,這種哲學認識論依然是一種主客體二分觀念。也正是如此,羅爾斯才會用正義儲存原則來試圖解決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分配正義問題。他們都忽視了作為人自身的生物信息等也是一種資源和生態環境,這種由人自身生物信息等構成的資源生態環境隨著人類的再生產得以不間斷的延續。對于這種人類自身共有的內在資源與生態環境,不論是過去世代,還是當今世代,或是后代人,人類自身都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共有者,人們不能用也無需用基于仁慈和道義的“代際契約論”及正義儲存原則來解決這一問題。
代際平等下的代際信托論以愛蒂絲·布朗·魏伊絲為代表。她認為,人類不同世代之間是一種針對地球環境資源的信托關系,每代人“既是受托人又是受益人”,作為受托人,他“不僅是為了相鄰近各代的利益,而且為了所有未來各代的利益”。⑩Edith Brown Weiss,The Planetary Trust:Conser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ality.Ecology Law Quarterly,1984,11(4),p.505~507.可以說,這種代際平等理論旨在解決全球環境生態危機,不愧為一種偉大設想。不過,有論者指出,這種理論構想在邏輯上存在著循環論證之悖論和謬誤,且實為虛構的結果。該論者所指出的這種理論的的困惑在于:環境問題是世代的公平問題還是整個人類的生存問題,地球環境是否為人類的財產,“地球權利”的主體到底應該是誰,代際信托何以可能,后代人的權利是否比當代人的義務更有利于保護“后代人的利益”,等等。①參見前注⑦,劉衛先文。對這些困惑是否虛妄,限于篇幅及論旨,筆者于本文中不再詳盡剖析,不過可以指出的是,其中前三個困惑之所以會出現,其背后依然是現代哲學上的主客體二分觀念。這種主客體二分觀念將人自身視為認識、利用、改造人之外一切的主體,人之外的一切則是作為人之主體被認識、被利用、被改造的對象而存在。主客體之間是截然的認識與被認識、利用與被利用、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由此,該論者才會提出,到底是地球環境是人類的財產還是人類自身屬于地球的疑問。對于代際信托何以可能的問題,該論者指出,作為代際信托的委托關系成立的前提是委托人即后代人對委托事務享有權利、代際信托理論的目的則是為了證成后代人享有環境權,這樣就出現了循環論證的邏輯悖論和謬誤。②參見前注⑦,劉衛先文。這或許正是揭示了代際平等下的代際信托論的軟肋之處。對于后代人的權利是否比當代人的義務更有利于保護“后代人的利益”問題的困惑,與其說是證成了代際信托論的虛妄,不如說是給人們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盡管對于誰能夠代表后代人行使這種權利,后代人權利不具備具體內容是什么等問題的解答至今尚未達成共識,但這并非意味著后代人權利不存在,更不意味著討論和闡釋后代人權利沒有重要價值,只是表明后代人權利依然是值得人們深入討論的重要論題。
跨代共同體理論的主張者往往將其理論淵源追溯至英國的柏克以及其代表人物是喬治·賴特等。柏克認為,國家“乃是一切科學的合伙關系,一切藝術的一種合伙關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種合伙關系。由于這樣一種合伙關系的目的無法在許多代人中間達到,所以國家就變成了不僅僅是活著的人間的合伙關系,而且也是在活著的人、已經死了的人和將要出世的人們之間的合伙關系”。③[英]埃德蒙·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29頁。賴特從柏克的這段表述中詮釋出支持后代人權利的跨代共同體論。顯然,柏克的這種跨代共同體論是以那個時代所思考的憲政共同體意義上而言的。后來托馬斯·潘恩對其將國家與社會完全等同起來以及薩拜因對其“對社會的崇拜代替了對個人的崇拜”,④劉玉安:《西方政治思想史》,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頁。就可證明這一點。此后跨代共同體理論更多受到社會學界的關注,如齊格蒙特·鮑曼的對共同體的討論,⑤歐陽景根:《〈共同體〉序曲·譯注》,載[英]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歐陽景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體論,⑥[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于散布》,吳睿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以及桑德爾、費迪南·滕尼斯等人的理論。這些都是基于當代人間共同體的本能、習慣或者思想的共同記憶等產生的某種共同關系的心理同感。這一點也可從阿夫納·德-沙利特(Avner Dr-Shalit)對共同體的三個特征的闡述中得到論證,即“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動、文化交流與道德相似性”。⑦Avner De-Shalit,Why Posterity Matter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22.然而,僅憑處于人心理上同感以及長輩與晚輩之間感情上的仁愛是不夠的,其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幾代后淡化而消失。由此,有學者認為,人類共同體即便存在,“也只能是所有當代人的集合體,對于永遠未出生的‘場外’后代人而言”,“不可能成為人們所說的人類共同體的現在的成員,因為尚未出生的后代人不能與當代人形成相互交流和聯系”。⑧同前注⑦,劉衛先文。戈爾丁(Golding)也發現,跨代共同體理論存在兩個困境,即當代人無法與后代人共享生活以及當代人與后代人缺乏道德上的相互作用。⑨Avner De-Shalit,Why Posterity Matter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19.由此,與代際契約論類似,通過跨代共同體論證成當代人對后代人的義務是不充分的。對此,有論者認為,即便是在主張當代人與后代人確實可以構成跨代共同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沙利特(Avner Dr-Shalit)那里,也只是推出“‘當代人負有義務’,而不是后代人的權利”。⑩劉衛先:《對跨代共同體學說的幾點質疑——以否定“后代人權利”為視角》,《太平洋學報》2010年第9期。
綜上所述,不論是在社會學領域,還是在其他學科如政治學等領域,不論對跨代共同體論持贊成還是反對態度,其共同預設依然是將后代人界定為與當代人沒有交際的永遠未出場的“未來”人,沒有看到人類自身再生產中由人自身生物信息而勾連在一起的不間斷的延續性和共有性。隨著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的日益成熟,對人自身生物信息的認識、改造等在技術上成為可能,使得人自身的生物信息成了區別于傳統的人之外在的資源、環境、生態的一種人的內在資源和生態環境。
(二)作為代際權利法理基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代際正義
如前所述,既有的作為后代人權利理論基礎的幾種觀點都存在著諸多問題且受到多方面質疑與挑戰,顯然已經無法為新科技時代所帶來的新問題提供充要的法理依據。伴隨著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等新科技的迅猛發展,人類不但在改造作為人類生存必要條件和基礎的資源、環境生態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而且也從技術上掌握了認識、利用和改造人自身的生物信息等方面的能力。由此,有學者斷言:“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人類的力量從未像現在這樣強大,以至于他的決定和行為所造成的影響可以超越時間的限制,影響到無法預測的未來。”①周光輝、趙闖:《跨越時間之維的正義追求——代際正義的可能性研究》,《政治學研究》2009年第3期。然而這種影響給人類帶來的不僅僅是美好的東西,還可能伴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風險,由此,人們應當對此有足夠的認識和理論準備,以盡可能地防范和避免這種未知風險。
如前所述,既有的對后代人及其權利問題的討論者顯然并未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僅僅出于對傳統的人之外部的世界視角且將其作為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和前提來展開的。在筆者看來,即便是承認范伯格的設想,即由一個權利的當代人與未來世代的正義共同體作為理論基礎,②喬爾·范伯格認為,我們為了我們的子女、我們的下一代的保護環境,是一種愛的行為;而我們為了我們遙遠的后代保護環境,則主要是一個訴諸未來世代權利的正義事件。See Joel Feinberg,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in E Partridge(ed)Responsibility to Future Generations,New York,Prometheus Books,p.139.然而面對人類編輯技術等新科技浪潮,后代人權利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代際權利應當有一種新的法理基礎。在筆者看來,這個法理基礎應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代際正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本來是個政治術語,由習近平主席于2017年1月18日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提出,旨在就解決全球性難題而提出中國方案,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③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7年1月20日,第1版。不過,人類共同體理念也已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目前學界主要關注以下方面:追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淵源和發展歷程;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及特征;分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原則;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價值觀基礎和倫理意義;從國際關系視角加以分析研究。④參見高景柱:《論代際正義視域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11期。可見,上述研究主要著眼于當代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忽略了人類中的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多從國與國之間關系視角展開而非人與人視角;多從作為人類生存的外部條件的資源與環境生態保護出發,忽略作為人自身內部生態環境的人的生物信息保護問題。不過,筆者認為,面對人類基因編輯技術所帶來的風險與挑戰,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可以通過詮釋其新內涵而為代際權利提供法理基礎。
如果說過去的共同體要么是“基于血緣、地域、情感或倫理”,要么是“基于共同利益抑或私人利益形成的一個聯合體”,⑤同上注,高景柱文。那么在人類基因編輯技術日益成熟的現狀下,整個人類由于共同的生物信息而成為一個聯合體。這種因人類共有基因等生物信息而形成的命運共同體不以社會學意義上的道德、風俗、倫理等方面的共同記憶和心理同感為要件,也無須基于作為人類生存之必備條件的外部資源和環境生態而構建,而是基于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即人類共有的生物信息。如果說人們之前還可以對其視而不見,那么隨著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人類自身生物信息所面臨的未知風險就使人們不得不對自身內部資源和生態環境安全進行問題化思考。這使得人類成為一種基于基因等生物信息安全的命運共同體。
由此,在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等新科技下,應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有如下理解。一是這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再是外在的、心理上的、文化上的認同,而是成為了一種無法否認的事實存在,不再以國別、民族、地域為區分,而是基于每個人固有且人類共有的生物信息資源和環境。二是這種將人類命運勾連起來形成的共同體不僅是由于作為人類生存之必需的外部資源、環境生態等,而且源于人類自身所共同固有的基因等生物信息。這種人類共有的這種生物信息將過去世代、當今世代以及未來世代的人們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三是此種意義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應關注的不再僅僅是人自身外部世界的資源及利益分配與儲存問題,而是更強調如何應對、預防和避免人類自身生物信息這種內在資源、環境生態面臨的風險乃至危機問題。四是這種人類命運共同體關注的與其說是利益,不如說是面對未知風險的安全。五是這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因人類基因編輯技術使得當代人與所謂不在場的后代人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人類基因編輯事件的發生使得當代人的行為帶給后代人的未知風險成為必然。
自十六世紀開始,法律已經成為社會控制的最主要手段和方式,⑥參見[美]羅斯科·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9~13頁。法律對社會控制則是通過權利義務的分配來實現的。就人類基因編輯而言,這種技術帶給當代人的可能是利益和權利的實現,對于后代人而言更多則是未知風險的安全利益問題。在此基礎上,從法理角度,如何有效應對和控制這種未知風險,也需要權利與義務的分配來實現。換言之,就人類基因編輯行為而言,如何在當代人生育權所體現的利益與后代人避免未知風險權利(或生物信息安全權)的安全利益之間進行協調,也需要一種權利義務分配的法理思維。這就涉及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代際正義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筆者于本文中并不是在羅爾斯所提出的代際正義意義上來使用代際正義概念的。羅爾斯所指的代際正義只是基于對人類外在的資源和環境生態等人生存必需條件意義上的,筆者于本文中說的這種代際正義則是基于由人類基因等共有的生物信息連接起來,將當代人與后代人緊密勾連起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代際正義。這種代際正義不是為了在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如何分配人自身之外的資源環境,而旨在如何在當代人利益與權利的實現與后代人應當有避免未知風險之權利之間的協調與分配。如果說羅爾斯的代際正義中,當代人對后代人負有的正義儲存原則所依據的作為公平的正義與當代人間分配正義所秉持的作為交換的正義之間存在著混亂和矛盾的話,那么這種基于人類共有的生物信息而形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代際正義則可以避免這一點。因為基于當代人與后代人共有共享人類基因等生物信息構成了人類得以生存和延續下去的最基礎和最根本的要素,當代人和后代人共同負有維護人類自身生物信息的內在生態環境之安全的義務。后代人還未成為現實,不可能存在對人之生物信息進行破壞或構成風險的可能,因此,這種義務就應當由當代人承擔和履行。也正是由于人自身的生物信息為整個人類所共有且構成人類得以延續的最根本的內在要素,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這種共同義務就無需再由代際契約論、跨代共同體理論提供法理基礎。當代人對后代人的這種維護人自身生物信息安全的義務其實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安全,也是為了維護整個人類自身的內在安全。
由此,如果說基于維護人自身生物信息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旨在解決“類概念”下的整個人類的自身的內在生態環境風險,那么其下的代際正義則旨在解決如何為了更好有效地實現前一目標在“集合概念”意義上的當代人與后代人權利與義務的權衡。⑦對于通過人類這一概念的“類概念”與“集合概念”二分來質疑人類“當代人”與“后代人”分割觀的討論,參見前注⑦,劉衛先文;前注④,徐祥民、劉衛先文。這樣,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代際正義理論不但可以有效解決“類概念”與“集合概念”意義上人類這一概念的邏輯矛盾,而且可以為代際權利提供更堅實且有解釋力的法理基礎。
四、作為新興權利的代際權利
如果人們承認代際權利,那么進一步需要明確的便是,它到底是一種什么權利,這種權利與以往的權利理論存在著什么關系。筆者認為,代際權利是建立在傳統權利理論基礎之上的新興權利,它不僅為人們如何解決新科技下人類面臨的新風險挑戰提供一種更有效的理論解釋,而且還可能是人們認識和分析當下問題的方法論,能為對人類的新風險的有效控制提供可能路徑和思路。
(一)作為新興權利的后代人的權利
如前所述,代際權利的成立需要以后代人權利存在為前提。從某種意義上講,之所以將代際權利視為新興權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后代人權利的新興性。由此,首先需要討論的是后代人應該享有權利,然后才能討論后代人享有的是一種新興權利。正如有學者所總結的那樣,權利意指資格、主張、自由、利益、選擇等觀點,⑧參見前注⑤,張文顯書,第300~305頁。但權利并非僅僅是對當代的現實人而言的,而是還需要對雖未來到世間但應該成為現實人的人的關注。詳言之,權利所蘊含的資格主要是指現實中的人的資格,但不應當剝奪后代人的資格;權利所蘊含的主張主要是指當代人的主張,但不應剝奪后代人的發表其主張的機會和可能性;權利所蘊含的自由主要是指當代人的自由,但不應當剝奪后代人的潛在自由;權利所蘊含利益主要當代人的既定的利益,但不應當剝奪后代人不應承擔未知風險之安全利益;權利所蘊含的選擇主要是指當代人的選擇,但不應當剝奪后代人選擇的機會和可能性。如果僅將權利理論限定在上述的當代人,則這種權利是不正義的,也與實定法不符。
之所以有學者將權利主體限定在具有權利行為能力的現實的當代人,是因為混淆了權利的享有和權利的行使之間的區別。其實,在當前的部門法中,類似法律也體現了權利享有主體并非僅限于完全權利行為能力范圍內。譬如,我國《民法總則》第16條就規定:“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的,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娩出時為死體的,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在。”這種立法也是對域外立法普遍經驗的借鑒,旨在規定非現實人權利的享有,避免使之失去可能的利益和權利的機會。其實,在我國目前已在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諸方面將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的權利主體,而且對于其在生命權、健康權等人身方面是否應成為權利主體,學界也已有很多討論。盡管這種規定是基于對胎兒作為準現實人的權利保護之必要且僅限于作為純受益人范圍,但胎兒同樣無法參與現實人的意思自決。另外,對于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的法律主體而言,即便是現實人,也因其無法憑自我理性之意志決定行使相應權利而需要監護、代理等制度來輔助解決這些問題。
由此,從理論上講,作為準現實人之具體個人的后代人享有最低限度的權利并非毫無正當性理據。如果說因為“后代人權利”理論因古典自然法之自然權利建立在基礎不牢固的“流沙”之上就完全排斥,那么當代人權利理論也面臨同樣困境。即便是早期對古典自然法基于批判和排斥的分析法學派成員,也日益意識到完全拒斥權利的不可能性和不可欲性,并提出了作為“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⑨哈特認為:“這些以有關人類、他們的自然環境和目的的基本事實為基礎的、普遍認可的行為原則,可以被認為是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內容。”[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張文顯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89頁。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為代際權利理論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與可行性。
一種權利之所以可稱為新興權利,是相對于傳統的既有權利而言的。對其“新”的標準“既可以從以時間和空間為核心的形式標準來判定,也可以從權利的主體、客體、內容和情景為核心的實質標準來判定”,其“產生在根本上乃是因應社會的發展而在法律制度需求上的‘自然’反應”。⑩姚建宗:《新興權利論綱》,《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年第2期。就后代人權利而言,其“新”之處至少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其一,后代人權利的主體是與當代人相對的后代人。如前所述,既有權利理論主要關注和解決的是現實當代人之間的法律問題和法律關系的,其權利主體是當代人或由當代人組成的組織等。其預設是所有參與法律關系的當事方都是具有完全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理性人。由此,意思自治、誠實信用、等價有償等才成為了作為現代法律基礎的民事法的基本原則,刑法中犯罪的構成才會強調犯罪動機、犯罪目的等;當然,法律對于限制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自然人的行為和權利也加以考慮,但其僅是例外性規定。后代人權利主體不可能是具有意思表示能力的客觀存在的客體,而是將傳統法中的非完全行為能力主體作為常態。由此,這就注定了后代人權利具有權利主體方面的新興性。
其二,后代人權利的客體是防范和避免可能給其帶來的未知風險。傳統法理中,法律關系中權利和義務的客體通常意指“主體的意志和行為所指向、影響、作用的客觀對象”,往往要求其具有“客觀性”、“有用性”、“可控性”等特征,主要包括物、人身、人格、智力成果、行為、信息等。①參見張文顯:《法理學》(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159頁。可見這種對權利客體的界定是建立在具有意思表示的現實當代人設定之上的。對于后代人權利,其客體不是因其自身的意志行為所指向、影響或作用的對象,而是指當代人的行為給后代人所造成的影響的對象,即給后代人帶來的未知風險。由此,后代人權利客體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物、人身、人格、智力成果、行為、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信息,而是自身生物信息的安全或風險防范。這對既有權利客體理論具有很大的挑戰性,也具有新興性。或許也正是出于這種考慮,張文顯教授在其最新修訂的《法理學》一書中頗有開放地將權利的“其他客體”列入其中,②同上注,張文顯書,第159頁。這為適應后代人權利客體的理論發展提供了可能。
其三,后代人權利所保障的是一種特殊的利益。在傳統權利理論中,權利所保護的通常是權利主體的利益,然而這種利益往往被界定為客觀、可控的有利的東西,是一種正面、積極的界定,適合于當代人之間關系的調整。后代人權利所保障的利益則是一種對后代人免于處于風險和危險的安全利益,雖然這種風險可能是未知的,但是風險一旦成為現實,其帶來的危害是無法估量和不可逆轉的。如果說傳統權利所保障的利益是一種既有利益的可得或不減損,那么后代人權利所保障的利益則是一種未來風險可能性的避免,由此可以視為一種負面清單式的消極性規定。這種權利所保障的利益與彩票購買人類似,只不過彩票購買者是通過對價獲得中獎的機會,而后代人權利所保護的利益是因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代際正義使得后代人免于處于未來風險的可能性,即前者是機會的獲得,后者是機會的避免。
其四,后代人權利實現的方式是享有。以當代人為權利主體的傳統權利的實現方式可能是享有,也可能是行使。享有但并不要求權利人具有完全權利或行為能力和明確的意思表示,以獲得利益而不需要承擔義務為限,可以視為一種消極的權利。通過行使方式實現的權利則需要通過明確的意思表示和行為來達致。這種權利需要以權利主體具有相應行為能力為要件,是典型的當代人權利的思維和實現模式。后代人權利只以享有為唯一實現方式,并不要求后代人在場,更不需要作出意思表示,也不需要后代人對當代人承擔同等的對價或義務,而是以純粹利益(即免予處于未知風險的這種特殊利益的獲得為目的),這在某種意義上類似于柏林所說的“免于……的自由”。③[美]以賽亞·伯林:《自由四論》,陳曉林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86年版,第243頁。
(二)作為一種未知風險控制方式的代際權利
如果說后代人權利是一種新興權利,那么代際權利則是建立在這種理論基礎上的一種新興權利思維方式和權利樣態。這種代際權利以當代人權利和后代人權利共同認可為前提,旨在如何尋求當代人權利與后代人權利之間的協調和均衡,以更好地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代際正義。
從權利發展史看,代際權利可以被看作是建立在過去類型化、進化式權利理論之上的修正和提升,也可視為我國權利本位理論的新發展。對于權利的發展歷程,有學者從人類人權發展歷程維度出發,認為西方人權史經歷了“自由權本位的人權、生存權本位的人權和發展權本位的人權三個歷史階段”;④同前注⑨,齊延平文。也有學者將人權史劃分為“初創期、發展期和升華期”,其“核心性人權分別是自由權、生存權和環境權”;⑤同前注⑨,徐祥民文。還有學者提出了作為第四代人權的和諧權。⑥參見前注⑨,徐顯明文。限于本文主旨,筆者不擬對這些權利理論本身進行過多闡釋。不過,從中可看出,這些都是類型化、單向度的權利理論,即關注和強調權利自身的正當性及其彰顯,甚至將不同權利之間的關系視為一種進化式的替代關系,卻對權利自身的合理邊界不甚關注,也未對不同權利之間的關系進行重點闡釋。過去幾十年來,權利本位理論在我國一直處于主導地位,也對中國法理、法治和法學的現代化理論與實踐起到了巨大的促進和支撐作用。不過,此理論同樣過多關注權利本身的證成和實踐以及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等,不同權利之間的關系及權利的合理限度等方面同樣不是其重點關注的對象。筆者于本文中論述的代際權利理論不同于上述既有權利理論,而是著重強調當代人與后代人權利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呼吁權利自身得到更為合理的安排和規制。
可見,這種代際權利看似是建立在前述“后代人權利”理論之上,實際上是與之存在顯著差異的權利理論。其核心不在于尋求、彰顯某種具體的類型式權能,而更多地是在揭示隱藏于權利背后的當代人與后代人權利之間的張力。這種權利張力關系不僅僅限于生態環境領域(甚至可以說,與生態環境維度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關聯),而是一種作為準現實人的后代人所應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權利,以及后代人與其上一代人之間的權利關系。如果說“后代人權利”理論是基于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之追求的類權利,那么筆者于本文中論述的代際權利則旨在強調構建人類安全命運共同體關系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的建構是建立在對不同代際權利的合理安排和尊重基礎之上的。這種新興權利與舊有傳統權利之間的沖突和協調不僅貫穿于法律權利實踐的始終,而且“彰顯著權利發展的真實樣態”。⑦姚建宗:《新興權利論綱》,《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年第2期。
對于筆者于本文中提出的作為新興權利的后代人權利及代際權利論,或許有人會提出質疑。因為依據法律思維,權利與義務作為雙向調整機制,共同構成法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特有方式,由此,一般認為權利義務具有結構上相關、數量上等值、功能上互補和價值上主次等關系,⑧參見張文顯:《法理學》(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138頁。因而在當代人與后代人、權利和義務之間應當有不同組合,即當代人權利與當代人義務、當代人權利與當代人權利、當代人義務與當代人義務、后代人權利與后代人權利、后代人義務與后代人義務、后代人權利與后代人義務、當代人權利與后代人權利、當代人權利與后代人義務、當代人義務與后代人權利及當代人義務與后代人義務等十對關系。這樣,當代人權利與后代人權利僅是其中一個組合而已。其實筆者對其他幾種組合并非視而不見。值得探討當代人權利與當代人義務、當代人權利與當代人權利、當代人義務與當代人義務這三對組合,系純當代人之間的代內權利義務關系,并非本文論旨,顯然超出了本文的討論范圍。后代人權利與后代人權利、后代人義務與后代人義務、后代人權利與后代人義務這三對組合屬于純后代人之間的代內權利義務關系,由于其權利義務關系主體都不在場且也屬于其代內關系,顯然也沒有討論的必要。剩下的四對組合即當代人權利與后代人義務、當代人權利與后代人權利、當代人義務與后代人權利、當代人義務與后代人義務值得探討。也就是說,除了筆者于本文中討論的作為代際權利的當代人權利與后代人權利這對組合外,另外三對最具挑戰性和討論的必要,因為其中揭示了這樣問題:后代人是否對當代人負有義務;通過當代人與后代人間的義務分配是否可以達到當代人與后代人間的權利分配。對于第一個問題,如果承認后代人對當代人也應負有義務,那么是什么義務,其限度在哪里呢?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則意味著當代人對后代人只能犧牲和承擔義務,這對當代人也不公平。對于第二個問題,其如果成立,則意味著代際權利可能被完全虛化和顛覆。
對于第一個問題,筆者認為,后代人的義務只是一種消極意義上的,只為當代人權利的享有和行使提供正義法理基礎,后代人的權利則可以為當代人權利的享有和行使進行適當限制提供正義法理基礎,兩者并非水火不容。對于第二個問題,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是義務關系的協調還是權利關系的協調,從邏輯上看,兩者似乎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然而,權利思維是一種尊重主體的目的思維,是認識和分析問題的法理思維,而義務思維只能是為了實現維續和擴大權利提供保障的手段思維。由此,通過協調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權利關系的代際權利思維才是符合現代社會人作為主體的思維,這種代際權利旨在為對人工基因編輯等新科技帶來的未知風險的有效控制提供一種視角和可能。在筆者看來,代際權利作為人類未知風險的控制方式,至少可以給人們提供以下啟示和要求。
其一,當代人和后代人不但負有維護人類生活之外部資源、環境生態的義務,而且負有維護人類共有的生物信息等內在資源、環境生態,使之免于承受未知風險的共同責任。面對人類基因編輯等新科技,人類已不可否認地成為另一種意義上命運共同體。如何維護人類自身生物信息等安全利益已對人們構成現實性的問題和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成為需要人們思考和解決的現實難題。
其二,當代人權利的享有和行使應當審慎和保守,以不使后代人被置于未知巨大風險之中為限。盡管當代人權利的享有和行使具有正當性依據,但也不應毫無限度和節制。如果說約翰·密爾將當代人之間的自由的限度確定為應遵循“不傷害(或不干涉)原則”,⑨對于權利的自由限度,約翰·密爾認為:“……這種自由,只要我們所作所為并無害于我們的同胞,就不應遭到他們的妨礙,即使他們認為我們的行為是愚蠢、背謬、或錯誤的。第三,著無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聯合,只要參加聯合的人們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騙。”此即“不傷害”或“不干涉”原則。[英]約翰·密爾:《論自由》,程崇化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13頁。那么當代人權利享有和行使的限度還應止于給后代人帶來未知巨大風險的可能性。這不僅是對后代人權利(如生物信息完整權)的尊重,對后代人的人格尊嚴的承認,⑩參見前注④,高景柱文。而且是為了維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安全利益。
其三,后代人權利的享有也同樣有其正義的限度。就人類基因編輯等新科技而言,對后代人權利的尊重以不對其構成未知巨大風險為限,而不應使當代人權利的行使和享有受到過多限制。如果說羅爾斯針對如何解決當代人與后代人間的資源、環境生態等人類生活必需的外部條件提出了正義儲存原則,那么針對人類基因編輯等技術對人自身生物信息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應當采用并遵循一種類似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