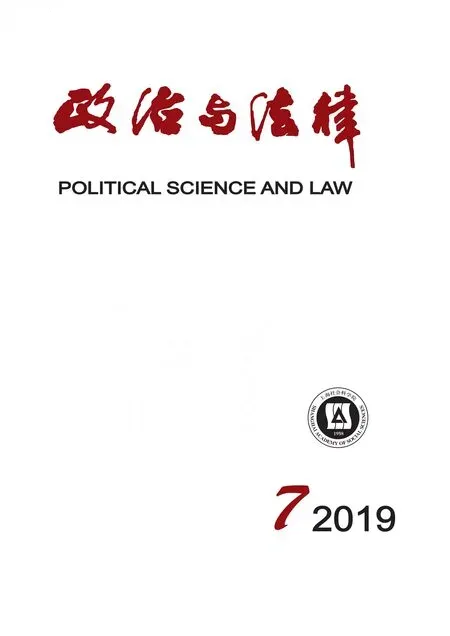人民意志視野下的法教義學
——法律方法的用途與誤用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2)
法教義學已經在我國法學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民法、刑法、憲法、商法、法理學等不同學科中,各領域的學者都開始有意識地借鑒和運用法律教義學的方法。同時,圍繞著法教義學的各種爭論也開始逐漸顯露。 例如,在社科法學的主張者看來,法教義學存在著各種問題,需要以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加以解決。
就學術發展來說,學術爭論無疑是一件值得鼓勵和慶幸的事, 學術爭論是學術真理得以凸顯的唯一方法。 然而,要實現理想的學術爭論,必須依賴于一個前提, 這就是要消除學術爭論各方的誤解和誤判。 只有消除雙方的誤解和誤判,學術爭論才不會出現“群體極化”的現象, 加劇各方原有的偏見。(1)D.J. Isenberg , “Group Polar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 50 (6): 1141~ 1151.或者說,只有在學術爭論中澄清爭論各方的基本立場,才能防止學術爭論演變為一般性的言論爭論。(2)關于言論與學術兩者之間的區別,參見[美]羅伯特·波斯特著:《民主、專業知識與學術自由——現代國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論》,左亦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版,第66頁。
在筆者看來,目前我國學界圍繞著法教義學的探討存在著不少誤讀和誤解。 在當前關于法教義學的分析中,對于法教義學到底是什么這樣一個基本問題仍然缺乏足夠的分析。 根據現有的材料,不少學者只是籠統地將法教義學視為一種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法律方法,而沒有詳細地指出這種方法有何特殊性,和已有的法律方法——例如法律推理、法律解釋——有何不同。 因此,如果說法教義學是一種特殊性的法律方法,那么比較恰當的學術討論方式應是將法教義學進行拆解,對法教義學中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釋等方法進行逐一的分析。 只有通過這種具體而細致的探討,人們才能清晰地認識到,法教義學在什么意義上成立,法教義學的正當性與弱點何在。
在本文中,筆者將結合德國法學背景下的法教義學,引進英美法學的知識來深化對法教義學的理解。 經分析可以發現,法教義學在知識或學術的層面上并沒有太多的特殊性,法教義學所包含的法學方法其實與一般的專業性思維并無太多區別,并不能減少法律分析中的價值判斷。 因此,在運用法教義學的時候,法律人應當保持智識上的自覺與價值判斷上的審慎,就價值判斷而言,法律人需要將法律價值判斷的終極正當性建立在人民根本意志或民主正當性的基礎上。 然而,筆者于本文中也將指出,法教義學也具有重要功能,如果運用恰當,法教義學可以成為一種經驗拓展與理性討論的載體,提升和規制并不穩定的人民意志,從而實現法治與民主、 法律人與大眾的良性互動。
一、法教義學是什么
很多中外學者都已經對法教義學進行過相似的定義和總結。 在《法學方法論》中,拉倫茨認為,法教義學是“以處理規范性角度下的法規范為主要任務的法學,質言之,其主要想探討規范的‘意義’。 它關切的是實證法的規范效力、規范的意義內容,以及法院判決中包含的裁判準則”。(3)[德]卡爾·拉倫茨著: 《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 2003 年版,第 77 頁。德國弗賴堡大學卜元石教授認為,法教義學指運用法律自身的原理,遵循邏輯與體系的要求,以原則、規則、概念等要素制定、 編纂與發展法律以及通過適當的解釋規則運用和闡釋法律的做法。(4)卜元石:《法教義學:建立司法、學術與法學教育良性互動的途徑》,載田士永、王洪亮、張雙根主編:《中德私法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許德風教授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并且指出,法教義學的“核心在于強調權威的法律規范和學理上的主流觀點”。(5)許德風:《法教義學的應用》,《中外法學》2013 第 6 期。從這些定義和總結來看,法教義學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征。
第一,法教義學關注的是實證法的規范性效力,在這一方面,它不僅區別于傳統的古典自然法學派,而且區別于現當代各種運用道德政治哲學和法律經濟學等理論來進行規范性分析的學派。 在法教義學看來,規范性的出發點應當是現行法所包含和體現出來的規范和價值,而不是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種道德或政策的判斷。
第二,與第一點相關的是,法教義學預設了現行法律系統內部存在著一種先驗性的規范價值或法秩序,并且以這種“自身已經確定而無須再作任何檢驗的信條為前提”,(6)[德]沃爾福岡·弗里希:《法教義學對刑法發展的意義》,趙書鴻譯,《比較法研究》2012 年第 1 期。它是以此為出發點開展體系化與解釋工作的規范科學。(7)白斌:《論法教義學: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環球法律評論》2010 年第 3 期。這樣,即使法教義學對于某個法律條文或法律判決展開批判,其批判也是在法律系統內部進行的,其依據的對象是法律系統內部的先驗性規范價值或法秩序。(8)參見[德]考夫曼:《法律哲學》,劉幸義等譯,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 頁;前注③,卡爾·拉倫茨書,第 76 頁。
第三,法教義學對于價值判斷具有獨特的處理方法。 一方面,法教義學并不排斥價值判斷。 正如同許德風教授所說,法律規制的適用很難和價值判斷徹底割裂,無論是三段論下的法律適用,還是區分簡單案件和疑難案件,都無可避免地會涉及價值判斷。(9)參見許德風:《論基于法教義學的案例解析規則——評卜元石:〈法教義學: 建立司法、學術與法學教育良性互動的途徑〉》,載同前注④,田士永、王洪亮、張雙根主編書。另一方面,法教義學認為價值判斷并不能簡單適用在法律適用中,價值判斷必須通過“價值判斷的論證規則”,轉化為法律體系的一部分,才能夠成為法律應用的依據。(10)許德風教授區分了價值判斷本身和“價值判斷的論證規則”,認為前者屬于哲學上的思辨,后者則是將價值判斷納入法律應用過程的規則,是法教義學的重要部分。 參見許德風:《論法教義學與價值判斷——以民法方法為重點》,《中外法學》2008 年第 2 期。
在某種程度上,法教義學非常類似于德國社會學家盧曼所提出的系統論中的系統。 在盧曼的系統論中,社會是一個大的復雜系統,在這個復雜系統之下,存在著很多相對自我封閉和自我創生(autopoiesis)的子系統。 在這些子系統內部,每個系統都有自己獨特的身份和規則。 因此,如果復雜系統要影響子系統,就必須將復雜系統中的信息轉化為子系統中的代碼,唯有如此,這些信息才能被子系統所接納,成為子系統的一部分。(11)See Niklas Luhmann,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Cardozo Law Review, Vol.13,No.5. (1992).借用盧曼的理論,人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理解法教義學的立場和特征。 法教義學正是法律系統內部的規則,它一方面向法律體系之外的其他價值開放,另一方面則將這些法律體系之外的其他價值轉化為法律代碼,保持法律領域的自治性。
除此之外,法教義學也類似于普通法中所說的技藝理性(artificial reason)。 在柯克法官與詹姆士國王的著名爭論中,柯克法官提出,“法律是一門需要長時間地學習和歷練的技藝,只有在此之后,一個人才能對它有所把握”;對于法律案件“不應當由自然的理性,而應當依據技藝性理性和法律的判斷來決定”。(12)[美]小詹姆斯·R·斯托納著:《普通法與自由主義理論》,姚中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8 頁。在一定意義上,法教義學可以說是大陸法系的技藝理性,它強調對于法律問題的判決必須在法律人內部尋求答案,正像對于普通法的判斷必須由普通法法律人來做出決定一樣。
以上分析大致展示了“法教義學是什么”。 不過,以上對于法教義學的定義與概括似乎仍然是在較為宏觀的層面上展開的,仍然缺乏較為微觀層面的分析。 例如,以上對法教義學的分析和定義沒有回答如下問題:法教義學和其他各種法學方法論,例如演繹推理、類比推理、歸納推理、遵循先例、技藝理性(artificial reason)、各種法律解釋規則(體系解釋、原旨解釋、字面解釋)之間有何關系? 法教義學是否是這些法學方法論的綜合化或體系化? 對這些更為細化和分析性(analytical)的追問將有助于人們理解,法教義學到底在什么意義上存在,法教義學是否存在多幅面貌。
二、法教義學與法律推理
思考法教義學在何種意義上存在,是否存在多幅面貌,可以首先分析法律推理這一最為常用的方法,以此來辨析法律分析中是否存在法教義學所謂的獨特的法律方法。 具體來說,可以將這一問題進行分解,探討法律分析中時常運用的一些邏輯推理方式。
(一)演繹推理
可以從三段論(syllogism)這一最為著名的演繹推理方式開始分析。 三段論認為,通過大前提和小前提,就可以推論出相應的結論。(13)See 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18~52.例如,某法律條文規定,某些類型的車輛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駛時速如果超過 70 公里,就將受到相應的處罰(可以將其視為大前提)。 一旦屬于這種車型的某輛車時速超過了70 公里(可以將其視為小前提),結合大前提和小前提即可得出結論,即這輛車需要接受相應的處罰。
初看起來,三段論的演繹推理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一般原則并不決定具體情形”,(14)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 69 (1905).仔細分析,會發現法律適用過程實際上是進行決斷或價值判斷,而不是在推理。 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需要作如下一些判斷。首先,需要對大前提中的各種規范進行判斷,例如某些類型的車輛是否包括警車和救護車, 高速公路的范圍是哪些, 行駛時速超過 70 公里是否包括短時間內的突然加速, 是否包括了因為逃避追殺而超速,等等。(15)See Cass R. Sunstein, 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25.其次,需要對小前提中的事實進行判斷,判斷車型是否屬于前者的規定,時速是否真正超過了70 公里,等等。 在整個過程中,對于大前提和小前提的判斷決定了某輛車是否應當受到處罰。 可以發現,三段論其實并沒有告訴人們哪些情況是例外,哪些情況位于規則之內,其本身并沒有任何增強確定性或減少價值判斷的功能。(16)See Gidon Gottlieb, The Logic of Choic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Rule and Rationality, chapter 1 and 2.
在一定意義上,三段論其實扮演了一種隱喻的功能。 大前提只不過是在說,有這么一個箱子,凡是這個箱子里的東西都應當受到處罰,小前提則告訴我們,某輛車屬于這個箱子里的東西,當人們把這輛車拿出這個箱子時,人們就知道它是應當受到處罰的。 在這一看似三段論的推理過程中,事實上我們首先確定了這個箱子里應當放什么東西,然后確定了某個東西是屬于這個箱子里的。 這樣,人們拿出來的不過是人們預先放進去的東西。(17)See Richard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8.
除了三段論,其他演繹推理的方式也同樣無法增加確定性和減少價值判斷。 以法律推理中經常采用的反證歸謬推理(inference of reduction to absurdity)為例,可以發現其推理過程同樣取決于價值判斷。 例如,美國憲法第 2 條第 2 款規定,“總統是合眾國陸軍、海軍和征調為合眾國服役的各州民兵的總司令”。如果按照嚴格的文義解釋,那將會得出總統不能領導空軍的結論,因此可以反推,對于美國憲法的解釋不能完全按照文義解釋的方式。 然而,這里之所以可以這樣反推,關鍵還在于人們普遍認為,美國總統應當也是空軍的領導者。 在其他的例子中,一旦人們對于結論無法形成共識,反證歸謬推理就無法有效地展開。
(二)類比推理與歸納推理
類比推理是另一種常用的法律推理方法。 一般認為,類比推理的重要功能在于,通過將當前案件與先前案件進行對照,可以實現同案同判的功能。(18)See Martin P. Golding, Legal Reasoning,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3, pp.44~49; 102~111.然而,這里的問題在于,類比推理本身無法提供確定性的類比規則,法律實踐中的個案類比仍然取決于具體情境。 例如,法律學說或法律判決一般都認為,個人在野外的合法狩獵所得應當屬于個人所有,(19)在普通法中,這被認為是“捕獲規則”(rule of capture)的適用結果。 See Ohio Oil Co. v. Indiana, 177 U.S. 190, 203 (1900).但對于被個人發現的烏木、文物甚至煤炭石油等,是否可以歸其所有呢? 類比推理可以將野生動物和烏木、文物、煤炭石油進行對比,得出它們同屬于無主物的結論,但這一類比最終是否會得出相同的法律適用結論,則取決于這些相似的物品是否具有其他不同的屬性,如果它們被認為具有其他完全不同的屬性,那么它們仍然將適用完全不同的法律規則。(20)對此,一個很重要的區別是,該物品是否屬于可再生資源或有限資源,是否屬于可再生資源或有限資源將決定捕獲規則是否能被適用。SeeRichard J. Pierce, Jr., State Regulation of Natural Gas in a Federally Deregulated Marke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Revisited, 73 CornellLaw Review 15, 20~23(1987).在這一過程中,真正確定類比是否能夠成立的決定性因素仍然是隱藏在類比推理過程中的價值判斷,而不是類比推理本身。
歸納推理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就歸納推理來說,其本質在于通過對先前案例或學說的總結來提取可以適用的法律或教義,例如,某種法律意見在先前的案例中被一再重申,某種法律學說被大多數的法官和法學家所認可,那么這種法律或教義就將被認為是權威意見。 在規范性層面上來說,這種歸納過程更多只是一種事實性的描述,而事實性的描述不可能推導出關于法律的規范性結論。 即使所有的先例都以“隔離且平等”(separate but equal)來理解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這也不能說明這種教義就代表了對法律的正確理解,(21)即使歸納推理“可以挑出之前案件的共同之處,也并不能確立這些共同之處就是不可缺少的”。 See Richard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88.也不能保證這些歸納所得出的結論不會在某一天被推翻。(22)See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 (1954).因此,歸納推理雖然在概率的層面上對于未來的法律判決或法律解釋具有一定的預測作用,但在得出規范性法律結論的意義上,歸納推理本身并不能減少價值判斷,對先例或學說的歸納必須在規范或價值意義上進行重新判斷。
(三)小結
上述分析可以表明,即使假定存在一個先驗的法律規范或法律秩序,要在具體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得出結論,法律人也要進行價值判斷。 法律推理并不能減少這一過程中的價值判斷,更無法幫助法律人回避這一點。
三、法教義學與法律解釋
除了法律推理,和法教義學相關的另一項重要法律方法是法律解釋。 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可以通過法律解釋的方法發現或接近發現對法律的正確理解,減少解釋者本身的價值判斷,這決定了法律解釋是否可以成為一種獨特的法律方法。
(一)字面解釋
字面解釋和形式主義的法律解釋具有很高的相似性,都強調按照法律的字面規定來進行嚴格解釋。然而,這里的問題是,字面解釋看似簡單確定,但一旦涉及爭議問題,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對字面背后各種價值問題的爭論。(23)See William N. Eskridge, Jr., and Philip P. Frickey, Cases and Materials on Legislation: Statutes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Policy, 1988, chapter 7.對此,最為著名的案例是美國最高法院曾經作出的西紅柿是否屬于水果的判決。 該案的爭議點在于,進口水果不用征稅,進口蔬菜則需要征稅,對于西紅柿是否需要征稅。(24)See Nix v. Hedden, 149 U.S. 304 (1893).法院在此案判決中認為西紅柿屬于蔬菜。初看起來,這取決于西紅柿到底屬于水果還是屬于蔬菜,只需要對此問題加以回答就可以下判。 然而,這個問題在科學常識和生活常識上存在不同的答案,植物學家們將番茄視為水果,普通民眾則更多地將其視為蔬菜,適用科學答案還是適用生活答案,這本身就需要在價值上進行取舍。 有的人可能傾向于認為,進口與關稅問題是一個涉及種子和農業的問題,因此應當以科學界的答案為準;另外的人可能認為,進口與關稅可能更多關乎國民經濟與國民消費問題,因此應當以一般民眾的理解為準。
除了不同人群可能產生不同的理解之外,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對語義產生不同的理解。 當分歧發生的時候,是應當以當時的字面含義為準,還是以解釋時發生的字面含義為準呢? 這其實也無可避免地又會涉及價值判斷。 以當時字面含義為準的觀點可能會認為,法律是一種約束未來的活動,當然應以立法時候的理解為準;以當下字面含義為準的觀點可能會認為,法律的解釋不能僵化,否則會出現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關于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規定不能保障現代網絡言論的觀點。 在法律解釋的實踐中,這種向前看和向后看的不同價值觀經常會影響對于法律的解釋。(25)最為典型的是麥克洛克訴馬里蘭州案中對于何謂“必要且恰當”(necessary and proper)的理解。See McCulloch v. Maryland, 17 U.S. 316(1819).
(二)原意解釋
法律解釋的另一個重要方法是原意解釋。 在堅持原意解釋的學者看來,堅持原意的最重要理由之一在于法律必須能夠約束未來,如果對于未來的法律解釋總是能夠以實用或其他理由來與現實進行妥協,那么法治就不可能實現。
原意常常被理解為法律制定者所理解的原意,原意解釋則意味著對立法者原意的探尋。 如同布萊克斯通在《英格蘭法釋義》中所指出的,法律解釋應當“探明立法者的意志”,“查明其立法時的意圖。”(26)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6th ed. ,J T Colerdge,London:Butterworth & Son,1825,vol,1,p.78.然而,一旦人們考慮現代立法機關的意圖,就會發現意圖是一個變動不定的概念。 在立法機關中,每個人的意圖是千差萬別的,有的人贊成某項法律可能是因為同意其中的一部分,有的人贊成可能僅僅是因為利益交換,(27)Albert Kocoure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Law,Boston:Little,Brown & Co. ,1930,p. 201.人們很難尋求到一個極為明確清晰的立法意圖。 “立法機關本身沒有思想。 因此,堅持意圖論必然要為如何將諸多個別意圖合并成集體的、虛幻的意圖而自尋煩惱。”(28)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 336~337.
即使人們將原意理解為立法者的原意,也仍然可以發現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立法者原意。 可以將原意理解為立法者對于某個具體問題的原意,也可以將原意理解為立法者可能會產生的原意。(29)See H. Jefferson Powell,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Original Intent,” 98 Harv. L. Rev. 885 (1985), pp.887~888.根據前者,人們可以得出結論,認為美國憲法的制定者的原意必定會反對用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來保護女性,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男女平等的觀念遠未被大多數憲法制定者所接受。 然而,根據后者,人們卻可能得出結論,認為當時的憲法制定者可能并不反對用第十四修正案來保護女性,因為立法者可能意識到自己當時的價值判斷未必是正確的,立法者可能更希望將這個問題交由未來的憲法解釋者來進行判斷。 后一種理論可能聽上去有些狡辯,但也并非缺乏論據,因為如果立法者非常明確地確定不能以第十四修正案來保護女性,他們就會在法律中進行明確的規定。 他們之所以在第十四修正案中采用了一般性的表述,或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為未來的平等保護預留空間。(30)See Jack M. Balkin, Living Originalism,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20~255.
除此之外,原意也完全可以理解為憲法或法律批準者的原意,而非立法者的原意。 在持這種理論者看來,立法者的原意并不重要,因為立法者只是很小一部分人,并不能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 如果要尋求立法原意,就應當去分析憲法或法律的批準者或接受者所理解的原意(original understanding)。(31)Antonin Scalia, “Address Before the Attorney General’s Conference on Economic Liberties (June 14, 1986),” in Original Meaning Jurisprudence: A Sourcebook, Office of Legal Polic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87, p.101; Office of Legal Polic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Guidelines on Constitutional Litigat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88, pp.3~6.然而,這里的問題同樣存在,當法律批準者或接受者存在理解分歧的時候,到底以誰的理解為準呢? 由此可見,盡管原旨主義力圖發現法律中的法律意志,但是這種法律解釋方法本身并不能帶來確定性,也不能減少法律解釋中的價值判斷。
(三)文本解釋
或許最接近法教義學的還是文本主義。 這種理論認為,當法律被制定之后,意圖就不應當被考慮,無論是立法者的意圖還是法律接受者的意圖, 因為“法治預設了文本(texts)的統治,而非創造文本的人的統治”,一旦“本文被確立,文本本身便構成了判決案件的權威”。(32)J.M. Balkin, Deconstructive Practice and Legal Theory, 96 Yale L.J. 743,783 (1987).
然而,文本主義也同樣面臨著如前所述的各種問題,文本主義也同樣存在各種版本。 文本主義可以指強調對某個條款進行特別嚴格解釋的條款主義,(33)例如布萊克法官就是如此認為的。 See“Justice Black and the Bill of Rights” ,9 Sw. L. Rev.937, 938 (1977).認為對法律文本的某些條款應當進行嚴格解釋。 當法律具有清晰條款的時候,就應當按照這些條款的清晰含義進行解釋。 另外,文本主義也可以指與整體文本密切聯系的語境文本主義,認為對于法律中的專業術語,必須結合整體的法律文本和句子加以體系性地閱讀,通過在具體案件中結合整體文本的理解來獲取對法律的最佳解釋。 除此之外,文本主義還可以指著名憲法學家阿吉爾·阿瑪(Akhil Amar)所說的文本互證主義(intratexualism),(34)A. Altman,Critical Legal. Studies:A Liberal Critiqu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pp. 95~ 96.即在解釋憲法中的某個具體條款時,必須與其他條款中的相近或相似詞語或表述進行文本上的對照,以求得對憲法的最佳解釋。(35)Akhil Reed Amar, Intratextualism, 112 Harvard Law Review 747 (1999); Akhil Reed Amar, Foreword, The Document and the Doctrine, 114Harv. L. Rev. 26(2000).采用不同版本的文本主義,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法律結論。
最為重要的問題是,文本主義的解釋方法雖然勾勒出一種區別于人治的法治理念,但其本身在爭議案件中卻無法提供確定性的答案。 各方雖然可以在宏觀層面上都贊同必須從法律文本中尋求答案,但一旦發生爭議,各方對于法律文本的爭論就必定會延伸到法律文本之外的政治道德, 用各種價值來證明自己所理解的文本含義才是正確的含義。 因此,如同德沃金所言,法律帝國不僅僅包括規則,法律帝國的邊疆要更為廣闊,其意味著政治道德或價值判斷也是法律的一部分。(36)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44.
(四)小結
法律解釋的方法遠遠不止前述三種,對于法律解釋確定性的批判也不僅僅限于當代英美法學理論,在德國法學理論中,也同樣存在著類似的批判。(37)例如,在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的著作中,他就指出,無論是訴諸立法原意,還是訴諸文本,都不可能獲得確定性的答案。 CarlSchmitt, Gesetz und Urteil. Eine Untersuchung zum Problem der Rechtspraxis (1912), München: C.H. Beck, 1969,pp.1~ 20. Carl Schmitt, On the Three Types of Juristic Thought (1934), trans. by J.W. Bendersky,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4,pp.47~ 57.然而,對于這三種具有代表性的法律解釋方法的分析已足以表明,即使假設存在一種法教義學所認為的先驗的法秩序,(38)很難說存在一種先驗的法秩序,因為對于法律是什么,即使從描述性的角度來分析,法律是什么也依賴于社會主流群體的承認規則對其進行認定。See H.L.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pp.113~114. 在此,人們也可以再次反思施密特對于凱爾森的批判。在施密特看來,凱爾森的純粹法學的問題在于他只關心想象的世界的確定性,而對于現實世界所出現的規則的不確定性,純粹法學所能做的只能是讓人再次去想象純粹法學的完美。 See Carl Schmitt, On the Three Types of Juristic Thought (1934), trans. by J.W. Bendersky,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4, p.52.法律解釋這種法律方法也無法幫助人們增強法律的確定性或者擺脫價值判斷。(39)See Kent Greenawalt, “Discretion and Judicial Decision: 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Fetters That Bind Judges,” 75 Columbia Law Review 359(1975).這里的原因在于,法律解釋方法本身是多元多樣的,不同的解釋方法會帶來不同的法律答案。(40)參見桑本謙:《法律解釋的困境》,《法學研究》2004 年第 5 期。法律文本所蘊含的法秩序也并不是完全確定的,它和法律文本之外的政治道德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旦人們對其進行解讀,就不可避免地會將這種“前見”帶入對法律的解讀。(41)德沃金的“理論爭論說”就是如此。 See 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p.1~90.
四、作為經驗拓展與說理載體的法教義學
筆者在前兩部分得出的初步結論,或許讓法律人頗為沮喪。 無論是法律推理,還是法律解釋,法律方法本身都不能減少法律實踐中的價值判斷。 在法律實踐中,不存在一種可以增加法律確定性的法律方法。既然每一種法律方法單獨都無法達成這一目的,那么作為法律方法之綜合的法教義學顯然也無法實現這一目標。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結論卻又似乎與人們的直覺直接抵觸。 如果說法律推理、法律解釋或法教義學都不具有獨特性地減少價值判斷或增強確定性的功能,那么法學的專業性何在? 難道在進行法律問題判斷的時候,法律人并沒有任何獨特性或專業性可言? 這顯然是一個讓人難以接受的結論。
在此,或許有必要區分兩種意義上的專業性。 第一種專業性認為,因為有了法教義學等諸種法律方法,法律人可以憑借這些法律方法而獲得身份上的權威性和專業性。 第二種專業性則認為,法教義學本身并沒有提供任何特殊的東西,但通過圍繞著法教義學等法律方法而展開的法律思辨中,法律人發展出了一種因為訓練和審慎而積累形成的專業性。 在知識的層面上,這種專業性強調法律人訓練和思辨的專業性,但不強調法律人身份的特殊性。 筆者認為,第一種專業性無法成立,第二種專業性則真切地存在。將法律的專業性定義為第二種專業性,上文提到的法律推理與法律解釋中的很多問題將能夠得到非常合理的解釋。 對于法律推理來說,法律推理的幾種推理方式雖然不能增強法律的確定性,減少對其的價值判斷,但圍繞著法律推理的過程卻能夠使人們拓展經驗思考的邊界,對法律問題進行更為周全的考慮。
以類比推理為例,類比推理可以迫使法律人對相關案例進行更全面和體系化的辨析。 在上文所提到的發現無主物和捕獲規則的例子中,可能一般人的直覺是,所有的無主物一旦被發現都應當歸個人所有,“捕獲規則”應當無條件地適用,因為在個人經驗的邊界中,采摘和狩獵自然界的水果與動物,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42)See Joseph Raz, Practical Reasons and Norm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9~62; Frederick Schauer, Playing by the Rules:A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 of Rule-Based Decision Making in Law and i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5.然而,大概沒有人會否認,這種直覺性的思維存在很多問題,它無力對現實社會中的復雜情況進行分析。 簡單以直覺來對法律問題進行判斷,必然會導致很多非理性的判斷結論。(43)這在刑事案件中可能更為明顯。 例如,對于若干嚴重的暴力犯罪,許多人的第一直覺就是應當進行嚴厲地處罰,但過于嚴厲的處罰可能會激勵犯罪人采取更為極端的措施。 如果對持槍搶劫都適用死刑,那么搶劫犯在搶劫時就更可能進行謀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發現類推推理的作用。 由于法律先例和類推推理的存在,法律人不可能直覺性地將捕獲規則應用在所有無主物上。 相反,法律人將會無可避免地需要對相似的不同類型做仔細地辯證和分析,(44)關于這種直覺思維和類比推理所帶來的反思性推理,參見Richard Brandt, A Theory of the Good and the R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1~23。以對該問題尋求一種羅爾斯所說的“反思性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45)Se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9~22, 46~51; Henry S. Richardson, PracticalReasoning About Final En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在這種“反思性平衡”的思維指引下,法律人將能夠區分一般無主物和石油、礦產等屬于國家資源的無主物,并且會對烏木、珍貴野生動物等處于邊界性的無主物進行較為謹慎的分析。(46)參見王旭:《論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的憲法規制功能》,《中國法學》2013 年第 6 期。歸納推理則是另一種使得法律人可以更為全面和體系化辨析法律問題的方法。(47)事實上,有的學者認為,類比推理在實質上是一種歸納推理,因為類比推理必然要涉及對很多案件的類比,而這個過程的實質是歸納。See Richard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89.在歸納推理中,法律人對以往存在的眾多先例或學說進行總結,這可以大大拓展法律人的信息邊界和經驗邊界,促使法律人總結和確定具有共識性的法律答案。(48)See Robert Axelrod,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 8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95, 1108~1109(1986).先例和學說反映了歷史上法律人對于相關問題處理的經驗,通過歸納方法所得出的法律答案盡管不可能百分之一百正確,但如果社會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那么這些以往的判例或學說中所總結的規則就能夠大體適用于當前的情況。(49)關于時間和法律先例權威性的關系,參見 Gerald J. Postema, “Some Roots of Our Notion of Precedent”, in Precedent in Law, Laurence Goldstein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pp.9, 18~20。在這一過程中,法律人雖然和普通人行使著同樣的價值判斷,但由于法律人對于先例或學說進行了更多的反思和總結,法律人所行使的價值判斷將更容易避免不合情理的錯誤。
法律解釋亦是如此。 法律解釋雖然具有多種不同模式,本身無可避免地隱含價值判斷,但多種法律解釋方法的對話和交流卻能夠拓展經驗邊界,使得法律解釋趨向于實踐上的合理性。 例如,對于上文提到的番茄是否屬于水果,從而是否應當征收關稅的判斷,不同的解釋方法雖然答案可能不同,未必能像德沃金所設想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那樣給出“唯一正確答案”,(50)See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p.151~ 224.但可以通過這種辨析來深化人們對于該對進口水果征收關稅條文的認識,從而避免得出荒謬的答案。 以字面解釋為例,當法律人開始爭論,到底是應當像植物學家那樣將番茄視為水果,還是應當像普通民眾那樣將番茄視為蔬菜時,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會對這個問題進行更為謹慎的分析,會權衡將番茄視為水果或蔬菜的不同后果。 同樣地,在對此問題的原意解釋和文本解釋中,法律人也會進行更審慎的判斷,做出至少比普通人更為全面和綜合的考慮。 在原意解釋和文本解釋的過程中,法律人將不可避免地思考,如果法律文本的含義并不明確,以立法原意來進行法律解釋,是否會涉及法律預期的不穩定性, 如果放棄立法原意解釋或法律的目的性解釋,這是否會造成食品安全的風險,等等。 總之,當法律人開始進行法律解釋時,無論是采取某一種解釋方法還是采取多種解釋方法,都可以通過法律解釋來提升法律判斷中的理性和綜合性判斷。(51)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法律更多應當被視為一種決斷。 See Gesetz und Urteil. Eine Untersuchung zum Problem der Rechtspraxis (1912),München: C.H. Beck, 1969.
據此,人們或許可以說,法教義學是一種經驗拓展和說理載體。 通過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釋,法律人可以將更多的經驗性事實納入討論的范圍,從而大大增強對法律問題的復雜性和體系性考慮,避免反射式的直覺思維。 在這個意義上,法律人共同體的正當性是存在的,通過專業性的思維和開放式的經驗拓展,法律人可以促使法律問題得到更好的思考和回答。
五、作為民主集中制的法教義學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本文第四部分所定義的第二種法教義學視為一種民主審議的法律方法,因為它通過法律推理、法律解釋等方法將更多的經驗和信息納入考慮的范圍,從而實現對于法律問題更為合理的判斷。
然而,這種民主審議的法律分析方法卻同樣面對集中的難題。 在法律共同體的內部,對于法律問題往往具有復雜的爭論:一旦深入到法律辯論的內部,就會發現一個案件往往可以找出截然相反的類似先例,或者可以發現存在得出不同答案的多種學說。 要獲取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法律共同體必須在內部確立起權威裁決的辦法。(52)費斯教授曾指出,法律解釋的確定性其實主要來源于解釋共同體的存在,而不是法律解釋在知識論上的確定性。 See Owen Fiss, On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34 Stan. L. Rev. 739 (1982).
對于權威裁決,其本質更多是一種強力,而不是一種理性或說服。(53)費斯教授曾指出,法律解釋的確定性其實主要來源于解釋共同體的存在,而不是法律解釋在知識論上的確定性。 See Carl Schmitt, Staat, Bewegung, Volk. Die Dreigliederung der politischen Einheit(1933),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3.法律實踐中的法院的等級設計自不必說,上級法院之所以能夠推翻下級法院的判決,最主要是因為上級法院的權威性使然,而并不一定是上級法院在知識或理性上更勝一籌而說服了下級法院。 對此,近代美國最高院最偉大的法官之一羅伯特·杰克遜(Robert H. Jackson )指出:“我們并不是因為不犯錯誤而成為終局仲裁者,相反,我們是因為終局仲裁者才不犯錯誤。”(54)Brown v. Allen, 344 U.S. 443 (1953).
法學研究群體內部也存在類似的現象。 在法學研究的內部,雖然并不存在類似法院等級設置這樣的權威裁決體系,但仍然有自己的決斷方式。 當出現對法律問題的分歧和爭論時,具有主導地位的“通說”就往往是由這個群體內部最有權威的學者所做出或認可的,盡管權威學者所提出的“通說”也總是面臨著挑戰的可能。 從說服的角度來看,這種決斷的過程也是一種行使強力的過程,因為在知識和理性方面,權威學者對某個具體問題所做出的分析并不一定就能勝過非權威學者,也不一定就能讓非權威學者心服口服。
在這個意義上,法教義學的知識架構和決策體系非常類似于人們所熟悉的民主集中制。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民主集中制,指的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即圍繞著共同的目標,使各方面的意見得以充分發表,然后對其中科學的符合實際要求的東西,通過集中形成統一的意志,作為共同的行動準則。 在法律教義學中,法學研究一方面允許各方面充分發表對于法律問題的見解,另一方面通過法院等級或學術權威來保證法律共同體能夠得出相對確定的法律答案。
六、“反多數難題”嗎:人民意志視野下的法教義學
民主與集中、開放與決斷的混合使法教義學具有生命力,也賦予法律人治國以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在現代社會,法律正當性的終極基礎卻必須奠基在人民民主和人民意志的基礎上。 根據這種觀念,法律必須是人民意志的體現,立法機關承擔制定法律的功能,而司法機關所做的僅僅是解釋和適用法律以幫助人民實現自己的意志——即使這種意志在某些人看來并不理性。(55)Frank Easterbrook, Method, Result and Authority: A Reply, 98 Harvard Law Review 622(1985):Frank Easterbrook, The Role of Original Intentin Statutory Construction, 11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59(1988).借用霍姆斯的極端表述就是,如果他的美國同胞們想下地獄,他也會幫助他,因為這是法官的工作。(56)Oliver W. Holmes-Laski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 Holmes and Harold J. Laski, 1916~1935, vol. 1, Mark De Wolfe Howeed., London: Geoffrey Cumbrlege at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248~249.
從這種人民意志的角度來看,法教義學所蘊含的專業與理性是否可以賦予法律人正當性,這值得重新思考。(57)這里的問題可以轉換為,法律應當是意志的體現,還是理性的代表。參見丁曉東:《自然法抑或實證法——理性與意志視野下的美國憲法》,《法制與社會發展》2012年第1期。在美國憲法學領域中,困擾美國法學精英幾十年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畢克爾教授所提出的“反多數難題”(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58)See Alexander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Bobbs-Merrill, 1962;See Barry Friedman, “TheHistory of the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Part One: The Road to Judicial Supremacy”, 73 N.Y.U.L. Rev. 333, 334 (1998).這個問題之所以困擾法律人,其中關鍵的問題就是:當法律人以憲法之名宣布體現人民當下意志的法律違憲時,其正當性何在? 對于這一問題,雖然各路法學精英學者都提出了有創建性的見解,例如宣稱司法審查其實可以促進代議制民主和人民意志,(59)John Hart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宣稱人民的意志只有在憲法時刻才能真正體現,(60)Bruce Ackerman, “The Storrs Lectures: Discovering the Constitution”, 93 Yale L. J. 1013 (1989).但沒有任何一人敢于以法律人的專業性來否定人民意志在整體上的正當性。(61)當然,這一現象和美國憲法文化中對于人民主權原則的信奉具有密切關系。 See Paul Kahn , Judging Judicial Review: Marbury in theModern Era: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a New Key, 101 Mich. L. Rev. 2677(2003).認同憲法最終的權威來源于人民,這基本上已經成為美國憲法學界的共識。(62)Hanna Fenichel Pitkin, The Idea of a Constitution, 37 J. Legal Educ. 167, 169 (1987).從人民意志的角度來看,這種“反多數難題”也同樣存在于憲法之外的其它法律領域。 在法律人和普通人對于法律判斷具有類似價值判斷的時候,法律人共同體的民主集中可能問題不大,但當兩者出現分歧的時候,法律人通過法教義學所形成的判斷的合法性何在? 既然法律人和普通人一樣必不可少地要進行價值判斷,那么這種價值判斷是否應當反映人民的意志呢?
這里的問題不僅僅是理論性的,在現實層面,問題同樣存在。 如果法律人所做出的判斷離人民的價值觀和意志觀距離太遠,那么人民對于法律人就會積累起越來越多的不信任。 對此,最為明顯的例子莫過于美國新政時期最高法院的“及時轉向”(switch in time)。 在新政期間,羅斯福總統和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大力推行新政,但遭到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百般阻撓。 然而,由于具有極高的民意支持度,羅斯福最終開始考慮法庭改造計劃(court-packing plan),準備從人事入手來改變聯邦最高法院的人員構成。 在這種背景下,聯邦最高法院不得不改變其法律解釋的原有立場,更加向民意靠攏。(63)See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ume 2,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與西方國家中法律人享有的權威與地位相比,中國法律人在社會上面臨著更加嚴峻的信任危機。一旦出現疑難案件,這種對法律人的不信任感往往就會迅速在公共話語層面爆發,直接挑戰法律人共同體的權威。
對于這種現象,有的觀點認為,普通民眾對法律人的懷疑與不信任是一種非理性的表現,同時,有的觀點還認為,人民的民主意志本身就是一個虛幻縹緲的東西。 如同立法機關的原意難以把握一樣,人民意志也不是一種客觀的存在。 例如,在共時性的層面上,哪些群體的看法可以視為人民的意志?在歷時性的層面上,經歷了多久沉淀的觀念可以視為人民的意志呢?(64)Paul Kahn, The Cultural Study of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18~ 41.據此,這些觀點認為,由于人民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意志表達途經的局限性,尋求真實代表人民的意志,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65)參見丁曉東:《宗教視野下的美國憲法解釋——評巴爾金的<活原旨主義>》,《政法論壇》2015 年第 5 期。
然而,這里的問題是,即使人們能夠在學術層面上消解人民意志的正當性,(66)在筆者看來,中國的法律文化與政治文化非常強調人民意志的正當性,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法律與政治文化要更接近美國而非歐洲。對于歐美法律文化與政治文化的不同,可參見Paul Kahn , Judging Judicial Review: Marbury in the Modern Era: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a New Key, 101 Mich. L. Rev. 2677(2003)。也不可能在現實政治的層面上消解人民意志的正當性。 在現代社會,人民主權和人民自治的原則已經成為一個基本性的共識。(67)See Edmund S. Morgan, 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1988; Bruce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ume 1, Found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John Dunn,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London: Atlantic, 2005; Margaret Canovan, The People, Cambridge: Polity, 2005.在這種正當性共識的背景下,如果過度排斥大眾的價值判斷,那么法律人就將無可避免地遭遇正當性危機, 同時,從法律人共同體權威的角度來看,這也不利于法律人共同體權威的樹立。 一旦法律人通過法教義學所形成的價值判斷離普通人的價值判斷過遠,法律人共同體內部的共識就會被質疑甚至拋棄。 對于脆弱的中國法律共同體來說,這顯然不是一個值得追求的選項。
事實上,在西方國家,雖然法治一般被認為是一種區別和獨立于政治活動的治理方式,但人民意志卻通過種種途經與法律人的價值判斷形成溝通。 在美國,在法律共同體的內部,就存在著所謂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其對應于美國社會整體上的意識形態分歧。(68)See Jack M. Balkin & Sanford Levinson, Understand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87 Va. L. Rev. 1045 (2001).首先,這就保證了法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整體價值觀不會相差太遠。 其次,法官一般為民選的總統或州議會提名,這使得反映民意的法官能夠及時被輸送到權威法律解釋機構,從而使得在任法官的價值觀更符合民主的意志,(69)當然,這種反應具有滯后性,并且,也有不少法官背離了其所在政黨的價值觀,最為著名的例子當屬沃倫法官。使得他們對憲法或法律的解釋更能反映民意的變遷。(70)對于政黨政治影響憲法解釋的分析,可參見Jack M. Balkin & Sanford Levinson, The Processes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Partisan Entrenchment to the National Surveillance State, 75 Fordham Law Review 489 (2006)。最后,社會運動所產生的民意也會影響法律解釋的變遷,通過影響憲法文化和法律文化,社會運動可以逐漸改變法律人對于相關法律問題的理解。(71)See Reva B. Siegel, Constitutional Culture, Social Movement Conflict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the de facto ERA, 94 CAL. L.REV. 1323 (2006).
雖然與美國相比,德國可能更加強調法律自治以及法律與政治的分野,但是在德國,法律人共同體恰巧和普通民眾共享了更多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這使得法律人的精英話語和大眾話語出現緊張或對立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回溯到《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前的薩維尼與蒂鮑之間的爭論,人們就會發現,這種人民意志和法律人價值之間的分野也是德國法學學者們最為關心的問題。 薩維尼之所以強烈批判蒂鮑的唯理性主義,強調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希望把德國人民的內在精神與意志內化為法律的一部分,使得德國的民法典成為德國精神的代表,(72)參見[德]馮·薩維尼著:《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許章潤譯,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第6~13頁。就像普通法代表了英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精神一樣。(73)參見李猛:《除魔的世界與禁欲者的守護神:韋伯社會理論中的“英國法”問題》,載李猛編:《韋伯:法律與價值》,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七、辯證法思維下的法教義學
一方是雖然變幻莫測但卻具有正當性和現實影響力的人民意志,一方是法律人共同體的自治和法律人內部的民主集中制,那么應當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緊張和矛盾呢? 在這種緊張和矛盾中,法教義學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
在筆者看來,無條件地選擇法律判斷中的民意或大眾話語,或者以法律共同體的民意來簡單地排斥民意,都存在不小的問題。 前者的問題在于忽視了民意中的非理性和人民意志的可塑性;后者的問題則在于夸大了法律方法或法律人共同體的科學性。 正如筆者于本文中的分析所表明的,法教義學只有在提供體系性和復雜性思維——而非科學——的意義上才能成立。
從辯證法的思維來看,這種法律人還是普通民眾、法治還是民主、精英還是大眾的二元矛盾應當以一種辯證和互動的方式來消解其緊張。 一方面,法律人應當將其最終的價值來源奠定在人民意志的基礎上,在法律推理與法律解釋中尊重和維護人民的根本價值判斷。 另一方面,法律人共同體也應當以自己的理性與復雜化思維來規訓民主,將人民意志提升為一種“經由理性思考的意志”(reasoned will),將那些反復無常或一時沖動的意志剔除在外。(74)參見[美]曼斯菲爾德:《社會科學與美國憲法》,汪慶華譯,載趙曉力編:《憲法與公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9 頁。這樣,法律人與普通民眾、法治與民主就有可能形成良好的互動。
辯證法的思維常常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75)最典型的當屬群眾路線的表述:“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 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9 頁。但用這一思維處理法治與民主、精英與大眾的關系的方式,也已經為西方不少著名法學家所采用。 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前院長安東尼·克羅曼(Anthony Kronman)教授就曾經在其名著《迷失的法律人》中提出,法學院的精英教育應當培養法律人對共同體的倫理價值采取一種既同情又保持距離的態度,從而影響和引領其所在共同體的價值。(76)See Anthony Kronman, The Lost Lawyer: Failing Ideal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p.62~ 87.耶魯大學法學院前任院長羅伯特·波斯特(Robert C. Post)教授在《哈佛法律評論》一年一度的最高法院觀察前言中則提出了一種法治與文化辯證的理論。 在他看來,憲法最終的價值來源于人民在憲法文化中所體現的價值判斷,但法律人卻能夠影響和規訓(regulate)這種憲法文化,從而使得兩者實現良性的互動。(77)See Robert C. Post, Foreword: Fashioning the Legal Constitution: Culture, Courts, and Law, 117 HARV. L. REV. 4 (2003).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人們也同樣應當用一種辯證的思維來看待法教義學。 一方面,如前所述,法教義學本身并不減少價值判斷,在應用法教義學進行法律分析的時候,法律人應當有充分的智識自覺和價值自覺,認識到自身也會無可避免地在進行價值判斷,并且不應當以法教義學的名義來拒斥大眾的民意或價值取向。 因為離開了人民意志作為法律的最終依托,法治最多成為一部分法律精英的智力游戲,而無法成為整個民族的共同追求和信仰。 另一方面,法教義學可以提升和引領人民意志。 在知識論的層面上,法教義學雖然和人們的其他思考方式相比沒有太多特別之處,但它卻可以將那些不具有法律思辨經驗、不具有復雜化思維的人群排除在外,從而構建一個相對理性的對話共同體。 在這個層面上,法教義學或許類似于“識字測驗”的篩選機制,通過“識字測驗”篩選的群體并不一定就比“文盲群體”更具有知識上的優勢,畢竟知識本身是多樣性的,但從整體上說,“識字測驗”無疑將大大促進討論者能夠具有更理性的思考和辯論方式,避免過于直覺性的簡單思維。
在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法教義學已經充當了這種溝通法律人與民眾、法治與民主的橋梁,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類似于法教義學的技藝理性也發揮了同樣的功能。 在中國,人們卻似乎面臨著雙重困境:一方面,法律體系整體移植自西方,法律體系中所蘊含的價值體系仍然與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價值觀具有不小的差距;(78)參見李強:《中國法教義學的“價值自覺”》,《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 年 11 月 16 日;張龑:《論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家與個體自由原則》,《中外法學》 2013 年第 4 期。另一方面,法律共同體也仍然遠未獲取普通民眾的高度信任,從而也無法發揮其規制和提升人民意志的作用。 在這種背景下,對法教義學進行充分反思,了解法教義學的用途與誤用,或許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