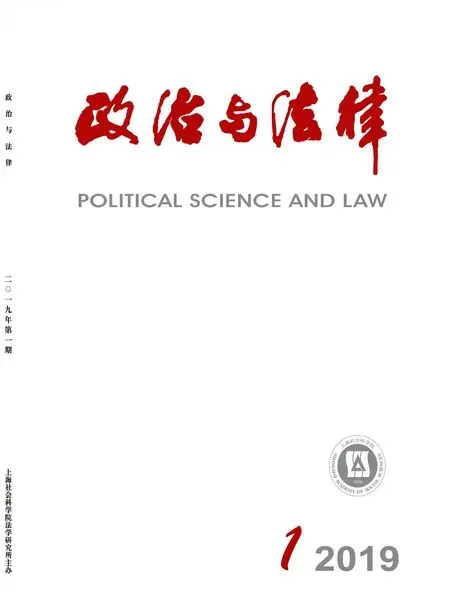擔保貸款雙重欺詐的犯罪認定
——以擔保的刑法評價為切入點
陳少青
(清華大學法學院,北京100084)
一、問題的提出
行為人騙取擔保人的信任,使其為貸款提供擔保,并偽造貸款所需的相關材料,形式上符合銀行的貸款要求,①《中國人民銀行貸款通則》(1996年)第10條規定:“除委托貸款以外,貸款人發放貸款,借款人應當提供擔保。貸款人應當對保證人的償還能力,抵押物、質物的權屬和價值以及實現抵押權、質權的可行性進行嚴格審查。經貸款審查、評估,確認借款人資信良好,確能償還貸款的,可以不提供擔保。現實中,絕大部分的貸款活動均需要借款人提供擔保。”從銀行取得貸款。這個過程存在雙重欺詐,行為人既向擔保人隱瞞騙貸事實,導致后者陷入認識錯誤為債務提供擔保,又偽造相關資質或虛構貸款用途,從銀行騙取貸款。
司法實踐中,以借款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為標準,可以將欺詐活動分為詐騙貸款和騙取貸款兩種。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主要取決于還款能力與款項實際用途兩點,如果借款人在借款前明顯無償還能力(如欠他人巨額高利借款不能歸還),②參見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遼刑二終字第00050號刑事裁定書。并且在借款后將款項的絕大部分甚至全部用于償還個人債務或揮霍,③參見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豫刑終298號刑事裁定書;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16)渝刑終93號刑事裁定書;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魯刑二終字第30號刑事裁定書。則為詐騙貸款;如果借款人在借款時公司經營狀況較好,或者雖然已經出現較大虧損但仍將大部分貸款用于合法的生產經營,④參見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川刑終字第617號刑事裁定書。或用于償還公司運營中產生的正常借款(非高利貸),⑤參見山東省濱州市濱城區人民法院(2014)濱刑初字第194號刑事裁定書。則為騙取貸款。對于上述兩種情形,刑法應如何認定,在理論界與實務界爭議較大,但整體處罰范圍過寬。當擔保人能夠償還銀行債務時,對于銀行是否為被害人,法院存在兩種處理意見。當擔保人最終未能全部償還,銀行出現損失時,法院均認定銀行為被害人,有如下兩個案例為證。
案例一,田野貸款詐騙、合同詐騙案(以下簡稱:田野案)。田野為騙取貸款,偽造土地承包合同和相關貸款證明文件,騙取長春吉聯擔保有限公司信任,由該公司為田野貸款提供擔保。田野從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騙取貸款80萬元后,將款項用于償還其他債務、購買車輛等,無力歸還并逃匿,擔保公司代為償還相關欠款。一審法院認為,田野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騙取擔保公司提供擔保,其主觀目的是騙取貸款,欺騙擔保公司的行為是手段,構成貸款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競合,以貸款詐騙罪論處。⑥參見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2014)前刑初字第323號刑事裁定書。二審法院認為,田野通過向建設銀行貸款欺騙擔保公司的行為,表面上看是騙取貸款,實際上侵害的是長春吉聯擔保公司的財產權益,在田野沒有償還貸款后,建設銀行通過行使擔保權,沒有受到損失,而擔保公司承擔擔保責任而遭受損失,故本案的被害人系擔保公司,而非建設銀行,田野構成合同詐騙罪。⑦參見吉林省松原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松刑終字第126號刑事裁定書。
案例二,陳猛騙取貸款案(以下簡稱:陳猛案)。山東怡豐艾海得化工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猛采取提供虛假財務報表、利潤資料及虛假的購銷合同等欺騙手段,騙取沾化縣富美康生物醫藥公司提供擔保,從原沾化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騙取貸款600萬元。案發前,農信社人員找擔保公司協商還款事宜時,沾化富美康醫藥公司負責人明確表示無能力履行擔保義務,致使沾化農信社600萬元的債權已無法實現,法院認為,陳猛構成騙取貸款罪。⑧參見山東省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魯16刑終123號刑事裁定書。
上述兩個案件的處理基本涵蓋了司法審判中的犯罪認定思路,其最顯著的特征是,特別重視擔保人是否實際清償債務。筆者認為這種思路主要存在三個問題。
第一,過于注重擔保人的實際清償狀況,導致受害人的認定不準確。田野案屬于較為典型的詐騙貸款案件,第一審和第二審法院的核心分歧點在于“誰是受害人”,如果銀行和擔保人均是受害人,則行為構成貸款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如果僅擔保人為受害人,則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該分歧同樣出現在騙取貸款案件中,如果銀行和擔保人均為受害人,則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⑨參見廣東省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東中法刑二初字第24號刑事裁定書。如果僅擔保人為受害人,則行為無罪(擔保人的財產損失只能通過民事途徑解決)。⑩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粵高法刑二終字第212號刑事裁定書。這兩種認定思路在實務中頗為常見。這不僅導致在相似案件中,判罰的罪輕罪重差異明顯,甚至是有罪無罪的天壤之別。產生分歧的緣由是,對擔保在刑法評價中的定位認識不清,進而導致分析的著眼點出現偏差。兩者都側重對擔保人的實際清償進行評價,一方將清償納入到犯罪構成要件的財產損失認定中,另一方則直接把其理解為事后救濟措施。雖然兩種觀點都能在某一側面正確認識擔保在犯罪認定中的意義,但未能把握其本質特征,導致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這恐怕也是爭議一直無法消弭的根源。
第二,過于注重擔保人的實際清償狀況,使得該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理論依據明顯不足。在詐騙貸款的情形中,多數法院都認為,行為人騙取擔保人提供擔保,構成合同詐騙罪,對此學界也不乏支持者。其中尚存疑問的是:騙取擔保保行為是否符合我國《刑法》第224條規定的“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擔保財產后逃匿”?案件中,實際收到擔保財產的是銀行,銀行不會逃匿,即便認為行為人收款逃匿,也發生在擔保人實際清償之前。所以有必要專門對合同詐騙罪的成立依據進行論證。
第三,過于注重擔保人的實際清償狀況,會大幅度提升企業的貸款風險。將擔保人實際清償狀況納入刑法評價中,是為了對銀行財產提供充分乃至過度的保護,只要案發前擔保人未全部清除債務,銀行遭受損失(擔保人無力清償或不想清償),企業就可能陷入構成騙取貸款罪或貸款詐騙罪的風險中。陳猛案中,法院認定其構成騙取貸款罪的根據之一,就是擔保公司事后無力還款。考慮到我國民營企業的籌集資金的困境,上述處理無疑增大企業運營的難度和風險。2018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召開會議專門指出:“合理和準確把握資金借貸的裁判尺度,立足司法職能促進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①《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召開會議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強調充分運用司法手段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務和保障》,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26971.html,2018年11月7日訪問。所以,因擔保人事后未能清償,擴大刑罰的打擊范圍,乃是刑法對經濟生活的過度干預。
筆者認為,擔保直接引起即時的財產價值轉移,將債權擔保的設立(而非擔保人的清償)作為刑法評價擔保的重心,才能正確認定雙重欺詐案中的財產損失。銀行在發放貸款時,已經通過設立擔保獲得相應的擔保權,沒有遭受損失,也就沒有成立貸款詐騙罪或騙取貸款罪的空間。即便在之后的清償過程中,因擔保人無力清償導致銀行受損,刑法也不能將其歸責于債務人。當擔保人向銀行交付擔保財產時,銀行受債務人欺騙,成為其收受擔保財產的工具,并將擔保權以貸款的形式兌現為實際利益,債務人將貸款隱匿,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犯罪認定的分析路徑
在擔保貸款雙重欺詐中,針對誰是受害人,主要存在兩種對立的解釋進路,即最終受害人與雙重受害人的分析路徑。兩種路徑成為法官處理詐騙貸款和騙取貸款的核心思路,考慮到論證便捷性,筆者以詐騙貸款為例對兩種路徑予以梳理和解析,并通過歸納兩者的分歧與共識,嘗試設立第三條路徑。
(一)路徑一:最終受害人
之所以在雙重欺詐的情況下,行為僅構成合同詐騙罪,不構成貸款詐騙罪,是因為整個詐騙活動的受害人是擔保人,并非作為債權人的銀行等金融機構。②參見李文燕主編:《金融詐騙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頁。銀行放貸時,已經從擔保人那里獲得擔保,在犯罪人不歸還貸款時,銀行通過行使擔保權(保證債權或擔保物權),由擔保人還本付息。真正利益受損的,是擔保人。因為擔保人才是債務的實際承擔人,并最終遭受損害,所以成立合同詐騙罪。③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3刑終字234號刑事裁定書;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6)滬刑終字67號刑事裁定書;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川刑終字第640號刑事裁定書;安徽省宿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宿中刑終字第00266號刑事裁定書。
當擔保人能夠足額清償時,銀行最終沒有損失,僅成立合同詐騙罪尚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如果未能足額清償,銀行同樣是“受害人”時,刑法應作何處理。對此,法院一般認為,如果擔保人無力清償全部的貸款債務,導致銀行遭受損失,或者擔保人雖代為償還,但償還發生在案發之后,則成立貸款詐騙罪(如果借款人無非法占有目的,則成立騙取貸款罪)。④參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2014)新兵刑終字第00013號刑事裁定書;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通刑初字第35號刑事裁定書。不過,如果銀行債權尚未通過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或對抵押人所提供的抵押物折價或者以拍賣、變賣該抵押物所得的價款受償等方式進行受償,⑤參見陜西省榆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陜08刑終180號刑事裁定書。或者在有關擔保的民事案件執行完畢之前,銀行是否能夠獲得足額受償(如抵押物變現)尚無結論,則不能確定銀行債權是否能完全實現,進而不能認定銀行是否存在直接經濟損失及損失數額,⑥參見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滁刑終字第00140號刑事裁定書。此時,欺詐行為造成銀行重大損失的證據不足,不能認定構成貸款詐騙罪。
路徑一的分析思路是,找尋整個欺詐活動中的最終受害人,重點考察銀行是否真的遭受實際損失,如果銀行通過擔保獲得足額清償,則雙重欺詐僅構成合同詐騙罪,如果銀行由于各種原因未能獲得足額清償,則依然能成立貸款詐騙罪。該思路具有兩個特征:(1)擔保權被視為銀行獲得清償的重要途徑,是判斷財產是否受損的必備要素;(2)認定是否成立貸款詐騙罪的時點,不是行為人取得貸款之時,而是銀行實現債權擔保之時,只有銀行通過保證債權或擔保物權的實現,尚不足以獲得清償,才會出現財產損失。
(二)路徑二:雙重受害人
雙重欺詐行為具有騙取貸款和騙取擔保的雙重故意,對兩者都實施了詐騙行為,因此銀行和擔保人均是受害人。具體而言,銀行因被騙而支付貸款,貸款被非法占有和國家金融管理秩序被侵犯的事實,在貸款支付后就已經客觀存在;擔保公司償還的行為,是第三方對被害人損失的彌補,屬于事后救濟,不能據此否定銀行貸款所有權已經遭受侵害。⑦參見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大刑二終字第182號刑事裁定書。“更何況,擔保人的代償行為是犯罪已經完成后由他人實施的、事后的行為,與行為人無關,擔保人是否有能力或愿意履行擔保責任償還銀行貸款,也是超出行為人預料范圍之外的,不能影響對行為人行為的刑事評價。”⑧李小文:《騙取他人擔保以獲取貸款無非法占有目的也構成犯罪》,《檢察日報》2015年7月8日。因此,擔保公司是否履行代償義務,銀行損失是否得到彌補,都不影響貸款詐騙罪的認定。
部分學者支持上述思路并認為,雙重欺詐行為應該成立貸款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競合,擔保人與銀行均是受害人。銀行財產損失的時點,是債務人完成騙取貸款行為之時,此時銀行雖然獲得了債權,但債務人不打算歸還債務,該債權自始不能實現;銀行雖然從擔保人那里獲得擔保權,但實現擔保權的事實本身,就是因為銀行遭受了未能收回貸款本息的財產損失;至于銀行最終通過實現抵押權彌補了損失,屬于事后救濟,與銀行之前受到的法益侵害不能混為一談。⑨參見武曉雯:《“雙重詐騙”案件的定性與處罰——以欺騙不動產擔保后騙取貸款為例》,《法學家》2017年第4期。所以,借款人不能因侵害結果的轉嫁而逃脫貸款詐騙罪的罪責。⑩參見錢葉六:《擔保貸款雙重詐騙案刑民交叉實體問題研究》,《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在具體處罰時,因騙取擔保人提供擔保的行為與騙取貸款的行為之間,具有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構成牽連犯,從一重罪論處。
路徑二主張,銀行財產損失的認定,不能以事后是否得到挽回為依據,擔保物權的行使只是針對損失的救濟措施,而侵害事實一定發生在救濟之前,所以侵害造成的財產損失與之后的擔保權行使之間,是兩個各自獨立的范疇。該思路的特征是:(1)債權擔保被視為銀行獲得清償的重要途徑,但這僅是事后救濟的手段,與判斷銀行財產是否受損無關;(2)認定是否成立貸款詐騙罪的時點,是行為人取得貸款之時,只要銀行放出貸款,信貸資金安全及金融信貸管理秩序就遭到現實侵害。
(三)兩種路徑的分歧與共識——路徑三的設定
不難看出,最終受害人與雙重受害人的分析路徑在銀行財產損失的判斷時點和判斷內容上存在直接對立。前者將擔保人清償作為認定銀行財產損失的必備要素,貸款詐騙的既遂點為清償之后銀行依然存在損失之時,后者將擔保人清償理解為銀行事后的救濟途徑,借款人取得貸款時犯罪既遂,銀行的財產損失就已經產生。兩者的分歧是如何理解擔保人清償在財產犯罪認定中的意義。路徑一將其作為犯罪阻卻事由,只要擔保人足額清償,銀行沒有財產損失,就否定貸款詐騙罪的成立;路徑二則主張擔保人清償與貸款詐騙罪的成立無關,僅為事后的救濟手段,如果清償后銀行沒有損失,最多只能被部分法院作為酌定的從輕處罰事由予以考慮。①參見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川刑終字第617號刑事判決書。
擔保人清償是關乎定罪還是僅可能影響量刑,對行為人而言有本質差異,這一點在騙取貸款情形中更為明顯。在最終受害人路徑下,擔保人足額清償因而銀行沒有受損,不成立貸款詐騙罪,同時刑法沒有為擔保人此時的財產損失提供保護,擔保人只能通過民事途徑尋求救濟,故行為人不構成犯罪。②參見遼寧省撫順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遼04刑終94號刑事判決書。在雙重受害人路徑下,擔保人足額清償是銀行財產受損后的救濟途徑,不影響騙取貸款罪的成立。③參見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4)安刑初字第344號刑事判決書;山東省濱州市濱城區人民法院(2014)濱刑初字第194號刑事判決書;江蘇省江陰市人民法院(2014)澄刑初字第0063號刑事判決書。
不過,在分歧背后,兩種路徑對擔保在刑法評價中的定位有著明確共識,均將分析重點放在擔保人清償對認定財產損失有何影響——路徑一是,因為有清償,所以無損失;路徑二是,因為有損失,所以才清償。然而,對于雙重欺詐,除了擔保人清償,擔保權的設立同樣重要,后者在絕大部分案件中,直接被忽視,僅有個別案件中的法官重視擔保權設立對財產變動產生的影響。
例如,在秦文虛報注冊資本、合同詐騙案(以下簡稱:秦文案)中,秦文虛假出資成立藝術品拍賣公司、中晟公司后,在沒有償還能力的情況下,采用虛構借款理由、隱瞞公司真實情況及虛假抵押等手段,騙取東航江蘇公司擔保,向7家銀行貸款共計3700萬元,之后歸還銀行貸款1995萬元,剩余1705萬元由擔保人東航江蘇公司償還。該案之所以認定秦文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且不構成貸款詐騙罪的理由是:“通過向銀行貸款的方式騙取擔保人財產的行為,表面上看是騙取貸款,實際上侵害的是擔保人的財產權益,犯罪對象并非銀行貸款而是擔保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財產……行為人虛構事實騙取銀行與擔保人的信任,非法占有錢款后,銀行可依據擔保合同從擔保人處獲取擔保,而擔保人則是銀行債務的實際承擔者,受侵害的往往是擔保人。即使擔保人因某種客觀原因如破產等情況導致無法償還擔保,銀行的債權無法實現從而權益受到實際侵害,但只要擔保人與銀行之間所訂立的擔保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銀行與擔保人之間就成立債權、債務關系,法律關系的最終落腳點和行為侵害對象就應認定是擔保人而非銀行。”④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審判參考》(總第45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該案的判罰思路看似屬于路徑一,但仔細研究不難發現,兩者之間有本質差異。銀行之所以沒有遭受財產損失,不是因為事后得到清償,而是在債權擔保設立和擔保合同生效時,銀行就獲得與貸款額等同的擔保權。即便擔保人不能足額還款,銀行最終遭受的損失也不屬于詐騙罪中的財產損失。筆者將秦文案形成的分析思路設定為路徑三。從形式上看,路徑三分別采納了路徑一和路徑二的部分內容:將擔保權作為認定銀行財產損失的要素,與路徑一相同;對銀行的財產損失認定,置于借款人取得貸款時,與路徑二一致。然而,本質上講,路徑三已經將刑法對擔保的評價從擔保人的清償轉移至擔保權的設立,財產損失的認定需圍繞設立擔保權引發的三方(債務人、擔保人和債權人)財產(權)變更進行分析。
三、擔保的刑法評價
比較三種路徑的處罰范圍,路徑三重視擔保設立時財產權的轉移狀況,處罰范圍最小;路徑二既忽視擔保權設立時當事人的財產變化,也排除擔保人清償對犯罪認定的影響,處罰范圍最大;路徑一只關注擔保人清償對財產損失的認定意義,處罰范圍居中。當然,選擇何種路徑,不能只依據處罰范圍的大小,而應基于正確把握擔保在財產犯罪中的定位,只要定位準確,三種路徑之間的主要爭點——擔保是否影響財產損失的認定,以及如何影響財產損失的認定——就迎刃而解。
在傳統的刑法理論中,債權擔保屬于財產性利益,這已經成為許多學者的共識。學者一般認為,財產性利益就是財物以外的一切財產性利益,例如取得債權或擔保物權、獲取勞務、免除債務等。⑤參見[日]松原芳博:《刑法各論》,日本評論社2016年版,第262頁。與此同時,“合同的擔保具有保障債權實現性”,⑥債權擔保既然圍繞著債權的實現而存在——確保更大可能地兌現債權利益,那么將其作為財產性利益,似乎具有邏輯自洽性,這一點也未被學者質疑。然而,在具體處理與騙貸相關的案件中,上述立場卻未被堅守。例如,“銀行等金融機構實現擔保權的行為,正是其在遭受財產損失的情況下基于另一個法律關系即擔保合同關系而采取的民事救濟手段”,⑦同前注⑩,錢葉六文。債權擔保從財產性利益轉化為事后的救濟措施,由債權、物權演化為救濟權,已經脫離財產本身的范疇,究其原因,是對債權擔保(尤其是擔保物權)在刑法中的性質的理解存在偏差。事實上,民法中的債權擔保既包括人的擔保的保證,也包括諸如抵押權、質押權等的擔保物權,當兩種屬性不同的權利納入刑法評價中時,將兩者簡單化處理為財產性利益是不恰當的,對此應分別進行討論。
(一)保證屬于財產性利益
保證屬于財產性利益,⑧參見黎宏:《刑法學各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89頁。保證屬于債的范疇,具有單務性與無償性,債權人對保證人不負給付對價的義務,但保證人需對債權人負保證債務,保證債權人在取得保證債務人的財產給付后,無需支付對待利益。⑨參見高圣平:《擔保法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頁。因此,相對于普通債權,保證完全不缺“利益”屬性。在連帶責任保證中,保證人不享有先訴抗辯權,當主合同的債務履行期屆滿,沒有履行債務的,債權人既可以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也可以要求保證人履行債務。法律將保證人與債務人置于同等地位,擔保債權與主債權的利益屬性沒有本質不同。即便是一般保證,若債務人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準備履行債務,那么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變得虛無,擔保債權自始就承載了主債權所有利益屬性。如果債務人沒有非法占有目的,但還款能力明顯欠缺,那么對于貸款中的部分(甚至是絕大部分)金額,同樣自始就由擔保人承擔清償義務。既然主債權作為財產性利益已被廣泛承認,那么在騙取貸款的過程中與主債權具有“同等”權利性質的保證也應該認定為財產性利益。
(二)擔保物權屬于財物的法益
與保證不同,擔保物權不屬于財產性利益,而屬于財物的范疇(該范疇包括財物的性質、種類、權能等,例如所有權屬于財物的范疇)。對此需要思考如何界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⑩對于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關系,學界存在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將財物分為廣義的財物和狹義的財物,后者與財產性利益共同構成前者,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33頁。另一種理解是將財物和財產性利益作為同級概念,均屬于財產的下位概念,參見前注⑧,黎宏書,第288頁以下。兩種觀點不存在本質不同,筆者采取第二種理解。
以往學者對財產性利益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特征或認定標準。例如張明楷教授主張,財產性利益作為詐騙罪的對象,必須同時符合四個標準:(1)利益內容是財產權本身;(2)利益需具有管理可能性和轉移可能性;(3)利益具有經濟價值:(4)取得利益的同時導致他人遭受財產損害。①參見張明楷:《財產性利益是詐騙罪的對象》,《法律科學》2005年第3期。李強博士認為,判斷財產性利益的一般標準是無體性、客觀的財產價值、確定性、具體性。②參見李強:《財產犯中財產性利益的界定》,《法學》2017年第12期。上述理論可以一定程度上劃定財產性利益的外延,但其更多指向財產性利益與看似具有一定利益特征但不屬于財產犯罪對象之間的劃分,并未討論在財產犯罪的對象內部,財產性利益與財物應如何界分,反而直接將財物作為定義財產性利益的要素,例如“所謂財產性利益,就是財物以外的、無形的、具有經濟價值的利益”;③同前注⑧,黎宏書,第289頁。財物以外,具有財產價值的,都是財產性利益。④參見[日]江家義男:《刑法各論》,青林書院新社1962年版,第268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論》,王昭武、劉明祥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頁。問題是,“財物以外”應作何理解,僅僅通過對財物和財產性利益進行概念設定是難以解決的。
無論是財物還是財產性利益,都是人最終獲取利益、價值滿足的手段。對于財物而言,權利人兌現利益只需要對該物予以處分,具有排他性,是“人對物”的關系形態,犯罪人實施的侵害直接指向物本身,導致財物價值出現減損;對于財產性利益而言,權利人兌現利益欠缺可供支配的具體財物,只能依賴于他人的行為(包括積極地給付和消極的不作為),⑥參見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頁。雙方相互配合與互動,是“人對人”的關系形態,犯罪人實施侵害,乃是不為權利人請求之行為。所以,導致特定物價值減損的行為,都屬于“人對物”的范疇,犯罪對象是財物;妨害不依托于特定物的權利實現行為,屬于“人對人”的范疇,犯罪對象是財產性利益。該區分映射到民法領域,即“財物價值”屬于物權保護范圍,保護權利人對物的支配權,“財產性利益”歸于債權保護領域,保護債權人對債務人的請求權。⑦參見王駿:《刑法中的“財物價值”與“財產性利益”》,《清華法學》2016年第3期。換言之,刑法中,對支配權的侵犯,是對財物的侵犯;對請求權的侵犯,是對財產性利益的侵犯。
以此為基礎,擔保物權屬于財物的范疇,而非財產性利益,有以下三個理由。
第一,擔保物權被物權法保護,是債權人對擔保物所享有的支配權。物權的實現具有排他性,屬于“人對物”的關系形態,不需要請求擔保人或債務人的允許。擔保物權包括抵押權、質押權和留置權三種,其中,質押權、留置權由權利人直接占有標的物,抵押權人雖然不直接占有標的物,但其在法律上支配標的物,在債權期限屆滿時,無需債務人的許可即可拍賣、變賣進而受償。擔保人對銀行提供物保,使銀行獲得對標的物(包括該標的物的變價形態)的價值支配權,所以其給付了“物的權能”,而不是“債的權能”。
第二,擔保物權直接導致擔保人(即所有權人)享有標的物的價值出現減損。財物作為財產犯罪的對象,其損失是指財物價值的減損。財物價值來源于物所具有的占有、使用、受益、處分等權能,這些權能共同決定了物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擔保物權的設立,必定減少所有人在該物上享有的部分權能,最明顯的是其處分權受到嚴重限制。⑧參見謝懷栻:《外國民商法精要》,程嘯增訂,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頁。作為一種定限物權,擔保物權雖然不能像所有人那樣依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行使所有權的全部權能,但可以就物的交換價值進行支配,⑨參見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下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0頁。其反射效果,是所有人享有的交換價值被嚴重削弱。此外,在為債務提供擔保后,擔保人通過抵押能夠獲得的經濟利益必然減少。例如擔保人向銀行提供抵押的房屋價值1000萬,其所擔保的債務數額為600萬,那么擔保人再次通過抵押該房屋最多獲得400萬的經濟價值。因此,擔保人以擔保物權的形式,將特定財物的部分價值和權能讓渡給債權人,使得財物價值分裂為兩部分,分別被擔保人和債權人享有。
第三,與擔保物權同屬物權的權能指向對象均是財物。在現有刑法理論中,所有權和不具有本權依據的占有狀態等支配權被刑法保護,而且所有權與占有權的對象均為特定財物而非財產性利益。那么與所有權、占有權同屬物權領域的擔保物權,理應在刑法中獲得與之一致的評價,權利對象為財物,即擔保物權屬于財物的范疇。
從式(13)中可知ΔV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用戶n自身滿意度函數值的改變量,第二部分為用戶n放棄an策略后干擾用戶集In滿意度函數值改變量,第三部分為用戶n選擇an′策略后干擾用戶集In′滿意度函數值改變量,第四部分為剩余用戶滿意度函數值改變量.由于集合V-In-In′-n中用戶或處于n的干擾范圍之外,或與n使用不同信道,故有
擔保物權是一種權利,雖然直接影響財物價值的變動,但不能直接視為財物,其在刑法中的定位,應該與所有權一致,即擔保物權是財物的法益,但是,作為同屬擔保的保證,卻是財產犯罪的對象,造成這種錯位的原因是,財物和財產性利益兩個概念的不對等性。刑法中,財物和財物權(即物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財物既是財物權的載體,也是財物權的來源。例如,財物是所有權的載體,所有權自生于財物本身,財物滅失,則所有權滅失,權利與載體的二分,分別與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與保護對象相對應。與之相對,財產性利益是權利人請求對方向自己進行或不進行一定支付的權利,即財產性利益是權利,該權利沒有載體(或者說,權利的載體就是權利本身),保護法益與保護對象相互融合。例如,租賃權既是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也是財產犯罪的對象。因此,民法中的物權(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在刑法中屬于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民法中的債權,在刑法中既是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也是財產犯罪的對象。保證和擔保物權分別作為債權和物權,在刑法評價中的定位自然不同。
(三)財產利益說(請求權說)的缺陷
筆者之所以強調擔保物權屬于財物的法益而非財產性利益,既是為擔保本身的刑法評價正本清源,也是由于在處理雙重欺詐的案件中,如果將擔保簡單概括為財產性利益,將之理解為一種請求權而非支配權,會得出不合理的結論。
首先,將擔保物權理解為財產性利益,是考慮到擔保物權是為實現債權而設立,依附于債權,這是“擔保物權債權說”在刑法中的延伸。該說認為,擔保物權僅是為擔保債權的實現,依據法律的規定或當事人的合意和公示,對一定的債權賦予優先清償權的權能。⑩參見[日]加賀山茂:《擔保物權法的定位》,于敏譯,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頁以下。擔保物權債權說一直被我國學者批判,而且擔保物權作為我國物權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然是對該說在法律層面予以的徹底否定。擔保物權雖然對債權實現起到保護作用,但其本身具有獨立的、不依附于債權的特定屬性,它以獲取標的物的交換價值為內容,其效力及于標的物的變價形態,是對標的物價值的支配權。①參見高圣平:《物權法擔保物權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頁。
其次,將擔保物權理解為財產性利益,視為附屬于債權的一項權利,容易進一步將擔保物權引申為事后救濟或保障措施。如果擔保物權是財產性利益,那么其權利本質是請求權,而非支配權。以請求權為基礎,擔保物權從債權進一步弱化為事后救濟權便有了連接點(債權與救濟權都屬于請求權)。這一點在路徑二中尤為突出,導致前后結論的不一致,即擔保人遭受侵害,是因為擔保物權屬于財產性利益,但在認定銀行財產損失時,又將擔保權視為追回財產損失的救濟措施。②參見前注⑩,錢葉六文。顯然,該觀點與刑法理論不符,救濟權與財產性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債權的派生權,不是財產犯罪的對象。③參見前注①,張明楷文。物權或債權與因該權利未被履行形成的救濟權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權利,只有前者屬于財產犯罪的對象,因為救濟權本身只是恢復權利的途徑,侵犯救濟權的本質依然是侵犯作為原權利的物權或債權。
再次,將擔保物權理解為財產性利益,進而引申為救濟措施,不符合權利的實現方式。債權人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可以通過對擔保物所享有的優先受償權確保其利益不受損害,客觀上確實達到“追回財產”的效果,但是,與救濟權和債權不同,物權屬于支配權,其優先受償權本身是支配權的體現,排除他人干涉。④參見程嘯:《擔保物權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7頁。在質押和留置的場合,債權人可以自行處分擔保物獲得相應清償,無需獲得債務人、擔保人以及公權力的許可;抵押權的實現雖然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請拍賣、變賣抵押財產,但向法院申請只是債權人自行實現對抵押物變價權的手段(因為債權人沒有占有抵押物,需要公權力為其提供幫助),無需取得擔保人的同意或認可,因而法院決定抵押權實現的程序屬于非訟程序,⑤參見程嘯:《論抵押權的實現程序》,《中外法學》2012年第6期。抵押權人向法院請求拍賣、變賣抵押物最多只能理解為物權實現過程中的必要流程,而非銀行享有的物權受到侵害后的事后救濟措施。因此,將支配權理解為財產性利益已經不妥,而進一步把支配權簡化為救濟性措施,無視其物權屬性更是本末倒置。
最后,將擔保物權理解為財產性利益,進而引申為救濟措施,難以準確判斷債權人的財產損失。例如,當借款人擅自處理抵押物,導致銀行的抵押權受到侵害時,有學者主張,此時借款人只是破壞了銀行債權的優先受償性,并非對銀行債權本身造成侵害,借款人與銀行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依然存在,銀行債權沒有受損意味著無法益侵害事實,也無構成犯罪的必要。⑥參見楊志瓊:《貸款詐騙罪擔保條款解釋適用研究》,《法學評論》2018年第1期。照此擔保物權被侵害欠缺具體利益的受損,不被刑法所保護,但是,銀行喪失對財物處分的支配權,失去對該物所享有的重要價值本身,已經導致其遭受了經濟損失,完全無視擔保物權的利益屬性的做法,勢必造成處罰上的漏洞。⑦對于擔保物的處置,刑法應如何評價是較為復雜的理論問題,對此筆者另行撰文探討。然而,無論如何,刑法對此不作處理是不合適的。
總之,將擔保物權理解為財產性利益,進而作為銀行挽回或轉嫁損失的途徑,無視權利本身的物權屬性與價值內核,錯把擔保物權從支配權降至請求權。無論是保證還是擔保物權,都直接引起即時的財產價值的轉移,擔保在刑法評價中的重心是擔保設立,而非事后清償。正確把握銀行對財物交換價值的支配性,能夠實現與詐騙罪認定的無縫對接。在詐騙罪中,財產是作為“交換手段、目的達到手段”而予以保護的,⑧參見[日]山口厚:《刑法各論》,王昭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頁。本罪中的財產損害,尤指對交易中的財產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侵害,⑨參見前注⑤,松原芳博書,第263頁。這些價值正是擔保物權的權能范圍所在。
四、雙重欺詐行為的刑法定性
無論是保證還是擔保物權,在設立擔保時,銀行就已經取得相應的債權或財物價值,此時在債務人、擔保人和債權人之間的財產權發生變動,財產數額有所增減。之后,擔保人的清償只是將設立擔保時銀行取得的債權或財物價值兌現為相應利益,并非損害發生后的救濟措施。因此,擔保的設立才是影響犯罪成立的核心要素。路徑一和路徑二將評價重心置于擔保人的清償,忽視了在擔保設立之時,財產在擔保人與債權人之間的轉移,路徑三符合擔保在刑法評價中的定位,具有合理性。根據路徑三的思路,擔保貸款雙重欺詐的犯罪認定如下。
(一)詐騙貸款的情形
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人實施雙重欺詐時,遭受財產損失的被害人是擔保人,銀行并未遭受損失,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即便銀行事后通過實現擔保仍不能獲得足額清償,也不成立貸款詐騙罪。
1.被害人的認定
判斷財產損失的時點,應是被害人進行財產處分的時點,關鍵在于財產處分行為完成時,被害人因財產處分所減少的財產是否直接獲得經濟上的等價補償,如獲得相應的民事權利。⑩參見王鋼:《德國判例刑法學(分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219頁。銀行在向借款人發放貸款時,基于借款合同擁有主債權,但由于債務人不會歸還貸款本息,所以該債權自始不能實現。即便如此,由于銀行在處分貸款時已獲得債權擔保,該擔保無論是作為財產性利益還是財物法益,都是對銀行提供的等價經濟補償。具體而言,如果擔保是保證,無論是一般保證還是連帶責任保證,保證人才是債務實際承擔人,這一點在銀行發放貸款時,就已經客觀存在,所以銀行與保證人簽訂的保證合同使其獲得了相應的民事權利,銀行在減少自己財產時獲得了等價的權利,不存在財產損失。①參見前注⑥,楊志瓊文。
如果擔保是擔保物權,則銀行失去貸款時,獲取了擔保物上相應的財物價值——財物交換價值的支配權,其承載或被兌現的經濟利益就是銀行的貸款額。擔保人讓渡財物的處分權可以獲得經濟利益,當為貸款設立擔保時,其在此方面的經濟損失(由銀行獲得的經濟利益)與擔保的債務相當。例如,前文提到擔保人向銀行提供抵押的房屋價值1000萬,其所擔保的債務數額(銀行貸款)為600萬,那么擔保人再次通過抵押該房屋最多獲得400萬的收益。換言之,擔保人以房屋的處分權為對價,能夠獲得1000萬的經濟利益,但由于已為貸款提供了擔保,再次抵押最多也只能獲得400萬,房屋總值中的另外600萬就是擔保人可能因擔保而遭受的損失,與之相對應,銀行獲得相應的擔保物權,也就獲得600萬的經濟利益。所以擔保人在擔保物上享有的價值減損部分由銀行取得,銀行沒有財產損失。②筆者在此沒有考慮利息的問題,因為銀行在發放貸款的時點犯罪既遂,此時尚未產生利息,刑法不對利息提供保護。即便考慮利息,根據我國擔保法的規定,銀行取得的擔保物權也涵蓋利息總額,所以其同樣沒有損失。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分析采取整體財產說的立場,詐騙罪的成立,以對全體財產的損害為必要,③參見[日]林干人:《刑法各論》,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年版,第145頁。如果被害人的“凈財富”沒有受損,就不構成本罪。④參見付立慶:《論刑法介入財產權保護時的考量要點》,《中國法學》2011年第6期。如果行為人向被騙人的給付對價高于后者交付財物的價值,被騙人在民事法上可以被認為沒有損害,刑法卻認定構成詐騙罪的做法是不合理的。⑤參見[日]瀧川幸辰:《刑法各論》,世界思想社1951年版,第152頁。與之相對,路徑二立足于實質的個別財產說。與形式的個別財產說不同,實質的個別財產說主張單純的交付財產不等于財產損失,還需要從實質上判斷是否存在法益侵害。⑥參見[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東京大學出版會2015年版,第244頁以下;前注④,西田典之書,第212頁。因為詐騙罪的本質是基于被害人的意思交付財物,如果交付意思存在瑕疵,則交付目的沒有達成,⑦參見[日]大塚裕史:《刑法各論の思考方法》,早稻田經營出版2010年版,第226-227頁。所以受騙者處分財產所欲實現的目的是否達成,是判斷有無財產損失的基本標準。⑧參見張明楷:《論詐騙罪中的財產損失》,《中國法學》2005年第5期。在擔保貸款雙重欺詐中,“銀行發放貸款的目的在于追求利潤,因此銀行一定是希望貸款人能夠按時還款付息,而不是為了拍賣擔保物并以其價款獲得優先受償……既然銀行發放貸款的目的沒有實現,就表明銀行存在財產損失”,⑨同前注⑨,武曉雯文。擔保人代為償還是目的未實現的事后救濟手段。筆者認為,即便基于實質的個別財產說,也應該認為銀行沒有損失。銀行發放貸款的目的是追求利潤,希望貸款到期時能夠收回本金和利息,至于交付本息的是債務人還是擔保人,都不影響其目的的實現。在保證擔保中,擔保人成為實際的債務履行人,是銀行實現盈利目的的唯一途徑。在擔保物權中,因為債務人自始不準備履行債務,擔保物成為銀行實現目的的基礎,銀行在該物上享有的物權使其能夠按照自己意愿排他性地支配擔保物,無需獲得擔保人或債務人的許可。
因此,在銀行發放貸款之時,其實現目的的手段從對債務人行使請求權,轉為向保證人或擔保物實現其權利。擔保的設立只是說明在目的實現過程中,債務實際履行人或履行方式發生變化,而非目的本身無法實現。借款人取得借款時,銀行的交付目的就已達成,即便基于實質的個別財產說,銀行也不存在財產損失。真正的受害人,只能是擔保人。
2.合同詐騙罪的成立依據
既然在雙重欺詐的案件中,真正的受害人僅為擔保人,按照現有的司法審判情況,行為人應當構成合同詐騙罪。誠然,行為人在整個詐騙過程中,通過設立貸款合同和擔保合同取得財物,既侵犯了擔保人的財產,又導致被害人對合同這種手段失去信心,從而侵犯市場秩序。⑩參見前注⑩,張明楷書,第833頁,然而,僅以行為侵犯了合同詐騙罪的保護法益,尚不足以認定其構成合同詐騙罪,行為只有符合我國《刑法》第224條的規定,即行為人必須采用該條所規定的行為方式,才構成合同詐騙罪,否則將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我國刑法對合同詐騙罪一共規定了五種方式,其中與詐騙擔保財產相關的,是“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遺憾的是,已有的司法判決中均未去論證為何借款人的雙重欺詐符合“收受對方當事人的擔保財產后逃匿的”,而是直接以擔保人財產受損為由成立合同詐騙罪。筆者認為,之所以如此,恐怕還是基于現有的路徑一和路徑二,存在無法解決的解釋困境。路徑一將擔保在刑法中的意義理解為擔保人的實際清償,交付行為是向銀行的還款行為,那么收受擔保人財產的是銀行,銀行不可能逃匿;若將逃匿人理解為借款人,借款人逃匿的時點是取得貸款之時,銀行獲得擔保人的實際清償的時點更為靠后,整個行為方式為“銀行收到擔保人實際清償前,借款人逃匿”,這與我國《刑法》第224條的規定明顯不符。
如果基于路徑二,銀行在發放貸款時就導致財產受損,那么對擔保人的交付對象和財產受損狀況又應當如何理解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當擔保人提供擔保時,即遭受財產損失。如果行為人導致被害人財產陷入緊迫的具體危險,則可認定被害人財產受到了損失;等同于損失的財產危險必須基于已經確定的事實產生,并且導致被害人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阻止這種危險最終轉化為現實的財產損失。①參見前注⑩,王鋼書,第215-216頁在雙重欺詐的案件中,擔保人提供擔保時,因為借款人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擔保人自始便要償還借款,其擔保財產陷入一種等同于損失的緊迫危險之中。②參見前注⑨,武曉雯文。該觀點難以解釋在提供擔保的時點,擔保人損失的財產由誰獲得。路徑二已經預設銀行發放貸款時財產受損,自然沒有獲得擔保人損失的財產,借款人獲得銀行發放的貸款,沒有另行取得額外的利益。當財產在三方之間轉移的過程中,如果兩方沒有獲得收益,第三方卻遭受損失,顯然不合邏輯。另一種觀點認為:“擔保的設定只是對擔保人的財產法益形成一定的威脅,唯有在借款人不履行還款責任,擔保人基于擔保合同履行了代償責任時,這種財產法益的被侵害的風險才會轉變為一種現實的法益侵害結果。”③同前注⑩,錢葉六文。該觀點將擔保人的交付理解為實際清償,其存在的問題與路徑一如出一轍。
路徑一與路徑二在解釋上的無力,仍然源于兩者對于擔保在刑法中的評價存在誤區。在提供擔保時,擔保人已經向銀行交付了財物(財產性利益或財物價值,以下同),銀行作為借款人的犯罪工具收到擔保財產,并以貸款的形式將擔保財產兌現為經濟利益。借款人取得貸款后將錢款隱匿,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整個流程不涉及擔保人的實際清償。該流程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借款人以騙取貸款為手段,欺騙擔保人簽訂擔保合同,實現騙取擔保財物的目的。現實中,行為人首先騙取擔保,之后騙取貸款,即通過第一個欺騙行為騙取財物后,又以此為工具,實施第二個欺騙行為,④參見陳興良:《合同詐騙罪的特殊類型之“兩頭騙”:定性與處理》,《政治與法律》2016年第4期。這是學界與實務界的通說。在客觀的形式層面,上述觀點似乎并無不妥,但在規范層面分析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時,必須對雙重欺詐中的手段與目的關系進行反思。
行為人在實施犯罪之前,一般以騙取貸款為目的,但是當銀行要求提供擔保時,借款人知曉自己欠款不還,債務由擔保人承擔,擔保人為真正的受害人,取財來源實際為擔保財產。換言之,當銀行為降低風險要求提供擔保時,行為人明知銀行不再是欺詐的財產損失方,侵害對象轉為擔保人,擔保人才是財物的交付人。所以騙取擔保財物是犯罪的真正目的,而騙取貸款從之前的目的降為騙取擔保的一種手段,即以取得貸款為名義,騙取擔保。
第二,行為人沒有親自取得財物,而是由銀行作為第三人收受擔保財物,此時行為人利用銀行作為詐騙的工具。⑤參見[日]高橋則夫:《刑法各論》,成文堂2014年版,第309頁。在詐騙罪中,被害人財產交付的相對方既可以是行為人也可以是第三人,我國《刑法》第224條規定的“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擔保財產”,涵蓋行為人收受與第三人收受兩種情形。銀行作為第三人,對行為人的犯罪計劃缺乏認識,不了解犯罪事實,沒有犯罪故意,受行為人欺騙,成為收受財產的工具。
第三,銀行以貸款的形式將擔保財物兌現為經濟利益,將贓物直接變現,成為行為人處置贓物的工具。銀行收到擔保財物之后,不能直接將其交給行為人,而是以貸款的形式將擔保財物兌現為價款,以貸款的形式支付給行為人,擔保財物歸于銀行。現實中,被害人處分財產交給第三人,后者將財產變現并將現金支付給行為人,自己留有財產的情況并不少見。例如甲向乙謊稱自己的手機報廢,借用乙的昂貴手機一個月,并以自己暫時外出為由,讓乙將手機寄給丙,再由丙代為轉交,同時甲以急需用錢為由,將丙收到的手機直接賣給丙,丙拿到手機后向甲支付4000元。本案中,丙既是手機的收受人,又將手機變現,并向甲支付一定價款,甲對乙構成詐騙罪。⑥丙的行為屬于善意取得,《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第2款規定:“他人善意取得詐騙財物的,不予追繳。”因此丙取得手機受法律保護,真正的被害人是乙,所以甲只對乙構成詐騙罪。實際上,無論是銀行向行為人發放貸款,還是丙向甲支付4000元,都可以視為贓物的處置。因此,擔保貸款中的雙重欺詐具有不同功能,欺騙擔保人是為了獲取擔保人財物,欺騙銀行是為了讓銀行成為收受財物和處置贓物的工具。
第四,行為人在將贓物變現,取得相應價款(即貸款)后逃匿。所謂逃匿,分為出逃和隱匿兩種情形。行為人取得貸款,將貸款隱匿的行為符合“逃匿”的內涵。
總之,行為人以銀行為工具,既利用銀行收受擔保財物,又利用銀行將贓物變現,之后逃匿,屬于我國《刑法》第224條規定的“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3.擔保人的清償不影響犯罪的成立
路徑一以擔保人清償債務后的損失狀況確定受害人,這種以事后損失倒推刑事責任的做法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擔保人清償全部貸款,則借款人成立合同詐騙罪,如果擔保人僅清償部分貸款,銀行與擔保人都遭受實際損失,則借款人構成貸款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如果擔保人破產或擔保財產滅失,最終受損的是銀行,則借款人成立貸款詐騙罪。⑦參見前注⑩,錢葉六文。這樣“罪與非罪的認定似乎取決于擔保方的賠償意愿與賠償能力,有損法的安定性”。⑧毛玲玲:《經濟犯罪與刑法發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95頁。
筆者認為,擔保人事后清償的狀況與犯罪的認定相互獨立。在設立擔保時,擔保人的財產損失就已確定,此時損失的表現形態是承擔主債務或者向債權人讓渡擔保物的價值和部分財產權。擔保人的事后清償是將債權人享有的債權或物權兌現為特定利益,擔保人的財產損失由權利的減損轉化為利益的減少,這僅是損失形態的變化,并沒有出現刑法需要保護的新的損失。因此,擔保人的清償屬于事后權利兌現為利益的過程,超出了刑法的評價范圍。即便擔保的實現并不足以清償債務,導致銀行最終遭受損失,也與合同詐騙罪的認定沒有直接關聯,更不能額外構成貸款詐騙罪,理由有以下三點。
第一,即便擔保人最終沒有完全履行債務,銀行遭受損失,也不影響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規定:“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詐騙數額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債務人借助銀行作為第三方,以騙取貸款之形,行詐騙擔保人財產之實,故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認定與銀行是否實際受損沒有直接關聯,債務人實際取得的數額源于擔保人的財產損失。
第二,即便銀行最終遭受損失,也不能認定成立貸款詐騙罪。無論是合同詐騙罪,還是貸款詐騙罪,犯罪既遂均是行為人取得財產時,財產損失的認定只能在此進行判斷。若之后擔保清償受限,銀行未能收回全部貸款,則需分情況進行討論。如果保證人因正常的金融風險導致其財產發生重大減損,甚至破產,或者擔保物因不可抗力導致不足以清償債款,都屬于因外在風險導致的經濟損失(銀行追求盈利,必然承擔一定的風險,此時風險現實化為實際損失),不能將損失歸責于借款人或擔保人。如果擔保人擅自處置擔保物,致使銀行遭受損失,可能構成其他犯罪。例如質押人竊取銀行保管或委托第三方保管的質押物,導致銀行基于質押權對財物享有的財產權受到侵犯,則質押人構成盜竊罪。
第三,即便放款后銀行撤銷借款合同,作為從合同的擔保合同因此而自始無效,擔保人不需要承擔擔保責任,也不成立貸款詐騙罪。因為在銀行行使撤銷權之前,合同自成立之日起就已生效,⑨參見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72頁。即在設立擔保和借款人取得貸款時,擔保是真實存在的,在這個階段,合同是有效的。此時擔保人因擔保的設立存在財產損失,同時銀行從擔保人那里獲得等額的財產性利益或財物價值,沒有遭受損失。所以行為只能構成合同詐騙罪,在此之后的一系列情狀(銀行行使撤銷權導致三方的權利義務發生變更、保證人破產導致銀行實際受損等)不屬于犯罪認定的評價范疇(或許可能影響量刑)。
在田野案中,長春吉聯擔保有限公司在銀行發放貸款時就成為債務的實際履行人,銀行在設立擔保時獲得的該公司的保證擔保填補了因發放貸款導致的資產“漏洞”,其整體財產未遭受損失,因此被害人為作為保證擔保人的該公司,銀行只是收受擔保財產和處置贓物的工具,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騙取貸款的情形
如果借款人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隱瞞公司經營狀況或貸款實際用途,騙取擔保。在偽造相關材料騙取貸款后,仍有歸還意圖,但因經營不善或經濟形勢變化等因素導致還款不能,最終由擔保人代為清償(部分或全部)債務。對此類騙取貸款情形的處理,有兩種觀點,即認為行為人無罪或認為行為人構成騙取貸款罪。
1.銀行資金未遭受重大風險
與上文對詐騙貸款的分析相一致,在騙取貸款的場合,銀行同樣沒有財產損失,不成立騙取貸款罪。具體而言,當擔保人為債務提供保證時,如果是一般保證,債務人不能履行的債務(不能償還部分的貸款)將由擔保人承擔,即擔保人成為該部分債務的實際履行人,銀行從擔保人處獲得與之對應的債權;如果是連帶責任保證,擔保人對全部貸款均有清償義務,銀行同樣可以從擔保人處獲得足額的債權。當擔保人為債務提供擔保物權時,銀行獲得財物的部分價值和權能(對財物處分的支配權),其具有的經濟利益用于清償債務人不能履行的部分債務。因此,銀行在發放貸款時,獲得了等價的財產權(包括債務人能夠履行部分的債權和擔保人提供的用以清償債務人不能履行部分的保證債權或擔保物權)。
可以說,只要承認在設立擔保時,擔保人為銀行提供了財產性利益(保證)或財物的部分價值(擔保物權),財產從擔保人轉移至銀行,銀行就不存在財產損失。并且,立法者設立騙取貸款罪的目的是保護銀行等金融機構信貸資金的安全,⑩參見郎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理解與適用》,中國民主與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頁。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是貸款安全,其最低入罪標準是債務人的借款行為形成貸款風險,危及貸款安全。①參見孫國祥:《騙取貸款罪司法認定的誤識與匡正》,《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顯然,銀行不存在財產損失,也就沒有貸款風險。②該風險是指犯罪成立所要求的不當風險,不包括銀行為獲利所必須承擔的正常風險。與此同時,由于債務人主觀上有清償銀行債務的意愿,同時債務人清償債務自然免除擔保人的擔保責任,擔保人為擔保提供的財產具有歸還的可能。所以債務人對雙重欺詐過程涉及的財產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為既不構成騙取貸款罪,也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只能以無罪論處。擔保人的財產損失通過民事途徑加以解決。
如果為貸款提供的擔保只針對全部貸款的一部分,則對有足額擔保部分的貸款不成立貸款詐騙罪,這一點獲得司法實務的認可。例如在著名的“劉漢、劉維等人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故意殺人案”中,二審法院認為,漢龍集團有足額擔保的貸款可從犯罪數額中予以核減,原審量刑偏重,予以改判,③參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鄂刑一終字第00076號刑事判決書。對此最高人民法院予以肯定。④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劉漢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故意殺人等死刑復核刑事裁定書(2015年1月27日)。
2.“重大損失”與“嚴重情節”的認定
在發放貸款時,銀行不存在財產損失,以此否定騙取貸款罪的成立的觀點恐怕會遭到一定的質疑,因為刑法中騙取貸款罪的成立,要求行為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難道銀行遭受損失,不應該就構成本罪?
筆者認為,銀行損失以及信貸風險的認定時點,只能是發放貸款時。只要銀行在該時點因足額擔保沒有產生資金風險,就應認定銀行沒有損失。即便之后銀行實現債權擔保,卻依然遭受損失(如保證人破產、擔保物的市場價值發生重大減損),也不成立騙取貸款罪,因為造成損失不能歸責于擔保人或債務人,而是由于外在其他風險所致(該風險是銀行為了獲利而必須承擔的),損失與行為之間缺乏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故銀行最終的實際損失不屬于騙取貸款罪中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失。
與“重大損失”相比,“嚴重情節”的認定更為復雜。司法實務中,不少判決中的定罪依據,就是騙貸行為符合司法解釋規定的嚴重情節。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以下簡稱:立案標準)第27條規定:“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一)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的;(二)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的;(三)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準,但多次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的;(四)其他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情形。”部分法院以立案標準為依據認為,即便存在擔保,但借款人偽造材料、虛構貸款用途,騙取銀行貸款,并且數額超過一百萬元,符合上述規定的情形一,也成立騙取貸款罪。⑤參見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4)安刑初字第344號刑事判決書;山東省濱州市濱城區人民法院(2014)濱刑初字第194號刑事判決書;江蘇省江陰市人民法院(2014)澄刑初字第0063號刑事判決書。問題是,該立案標準是否應該作為騙取貸款罪的裁判依據,以及如何理解立案標準中提到的情形,均需謹慎對待。
第一,立案標準執行主體是公安機關與檢察院,其內容規定符合立案偵查和審查起訴的情形,但并不涉及審判,不應直接作為法院的定罪依據。法院在認定事實和證據的基礎上,根據刑法規定和相關解釋方法,對是否構成犯罪需采取實質解釋。如果僅形式地適用立案標準,則法院獨立審判的職能將被大幅度弱化。
第二,騙取貸款罪中的“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分別對應立案標準的情形二和情形一、三,即將數額巨大(騙取貸款超過一百萬元)作為嚴重情節之一,但如果借款人提供足額擔保,甚至提前歸還借款,僅因為提供材料有虛假導致銀行被騙,就構成犯罪,無疑造成處罰范圍過大。因此不少法院認為,只有對銀行造成實際損害時,才構成本罪。⑥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6)滬01刑終579號刑事裁定書;廣東省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20刑再6號刑事判決書;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刑重字第5號刑事判決書。對于如何確定本罪的“嚴重情節”,可以采取體系解釋的方法。《刑法修正案(六)》之所以將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構成要件之一的“造成重大損失”改為“情節特別嚴重”,是因為實踐中對“損失”如何認定出現分歧。例如,該損失是否只包括對銀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還是也應該將對其他單位和個人的經濟損失、給金融機構造成的社會損失、聲譽和信譽損失計算在內等。正是因為對損失的認識出現不一致,《刑法修正案(六)》將損失改為情節,⑦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頁。但這里“情節嚴重”所解決的,是針對部分損失難以認定的問題,而非完全沒有損失的情形。⑧同為保護銀行金融安全的騙取貸款罪也面臨相似的困境,所以該罪的情節嚴重也應是指,造成銀行損失但損失的具體數額和程度不能精確認定的情況,有學者將其概括為銀行的巨額資金陷入巨大風險,并與巨大損失具有相當性,⑨筆者認為具有合理性。⑩
因此,形式地將立案標準作為騙取貸款罪的定罪依據,只要欺騙銀行的借款人貸款數額超過100萬元就構成該罪的做法不具有合理性。只有當借款人騙取貸款造成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重大損失或使銀行資金安全出現重大風險時,才符合本罪的構成要件。如果借款存在有效擔保,銀行的信貸資金安全并未陷入風險(至少未陷入可罰的風險),則不構成犯罪。考慮到司法實務中,法院經常將立案標準作為裁判依據,筆者認為,在適用該司法解釋時,必須做限制解釋。騙取詐騙罪的成立應遵循以下原則:(1)騙取貸款數額超過一百萬元,是指扣除存在擔保的相關貸款之后的數額;(2)造成銀行直接經濟損失超過二十萬元,不得包括由于保證人破產或擔保物市場價值減損等,導致擔保實現后仍不能足額清償所造成的損失;(3)多次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中的“多次”,不得包括提供足額擔保的貸款行為次數。
在陳猛案中,陳猛向銀行申請貸款600萬元,其數額雖然超過立案標準所規定的數額,但在發放貸款時,沒有證據證明沾化縣富美康生物醫藥公司提供的擔保是無效的(事后擔保公司無力還款不能證明提供擔保時就沒有還款能力),因此銀行的信貸資金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即便最終作為擔保保證人的醫藥公司未能清償債款,也不能將其歸責于陳猛,故不成立騙取貸款罪。至于陳猛與擔保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則交由民法解決,陳猛應以無罪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