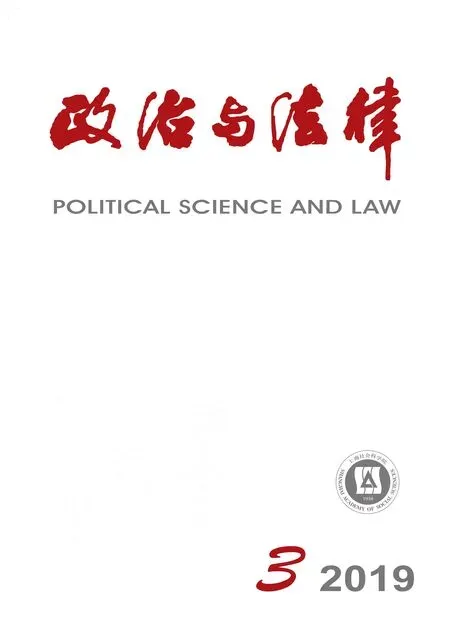敲詐勒索罪中“被害人處分必要說”之辨析
蔡桂生
(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被害人處分,又稱被害人交付,在我國刑法學中,經常被認為屬于敲詐勒索罪成立的必要要素。王作富教授認為:“采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目的是迫使他人交付財物。亦即行為人的上述行為與他人交付財物之間,必須存在著直接因果關系。如果交付財物不是受到威脅或要挾的結果,不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①王作富:《侵犯財產罪》,載高銘暄主編:《新編中國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04頁。贊同王作富教授觀點的有劉明詳、尹文建等,參見劉明祥:《財產罪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298頁;尹文健:《敲詐勒索罪》,載趙秉志主編:《侵犯財產罪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頁。張明楷教授認為:“敲詐勒索表現為使用……脅迫手段使對方……處分財產,使行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財產。處分財產的人必須是被脅迫者。”②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7頁。勞東燕教授指出,正是處分行為的存在,使得敲詐勒索罪區別于違反被害人的意思而取得財物占有的盜竊、搶劫等奪取型犯罪。③參見勞東燕:《敲詐勒索罪》,載陳興良主編:《刑法各論精釋》(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578頁。與勞東燕觀點類似的學者有車浩、鄒兵建、郭澤強等,參見車浩:《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之界分:基于被害人的處分自由》,《中國法學》2017年第6期;鄒兵建:《交通碰瓷行為之定性研究》,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判解》(第1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101頁;郭澤強:《敲詐勒索罪》,載馬克昌主編:《百罪通論》(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74頁。
這一要素是否真的必要呢?我國《刑法》第274條(敲詐勒索罪)規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該法條中并沒有“處分”或“交付”的明文表述。因此,“究竟需否以被害人處分作為敲詐勒索罪成立的必要要素”這一問題,仍需從理論上加以解答。以下,筆者將首先基于比較法的視角,在一般學理上對被害人處分是否必要進行研討并作出判斷,之后再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對此問題加以針對性的處理。
一、關于被害人處分是否必要的正反意見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刑法學界大量地引入了日本刑法的知識。在這種條件下,可以參考一下日本刑法學如何回答被害人處分是否必要這一問題。《日本刑法典》第249條(“恐嚇罪”)(對應于我國的敲詐勒索罪)規定“恐嚇他人使之交付財物的,處十年以下懲役”。該條中出現了“交付”的字眼,而此處的“交付”即為“處分”。由于法條中明確限定了以“處分”為必要,且恐嚇罪與詐騙罪同列于該法第37章,在日本刑法學說上均要求恐嚇罪的要件之一是被害人處分財物,沒有爭議。④參見[日]大塚仁:《刑法概說(各論)》,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09頁。不過,自21世紀以來,除了日本刑法的知識,德國刑法的文獻也逐步為我國學界所了解。與日本的情況不同,《德國刑法典》第253條規定的勒索罪則是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地獲利,違法地使用暴力或以帶有明顯的害惡的威脅,強制他人為一定行為、忍受或不為一定行為,因此使得被強制者或他人遭受財產損失(處五年以下的自由刑或罰金刑)”為其內容。這種表述和我國《刑法》一樣,都缺乏“交付”或者“處分”的字眼。這就使得德國(而非日本)的情況,成為我國研究者應當關注的對象。⑤車浩在相關論著中提到德國經驗,但未對德國經驗深入分析。參見前注③,車浩文。與德國類似,同樣不以“交付”或“處分”作為敲詐勒索罪之要素的,還有《奧地利刑法典》第144條(參見《奧地利聯邦共和國刑法典》,徐久生譯,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頁)、《丹麥刑法典》第281條(《丹麥刑法典與丹麥刑事執行法》,謝望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頁、第214-215頁)、《越南刑法典》第135條(《越南刑法典》,米良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頁)。
在法條沒有規定“交付”或者“處分”的字眼的德國刑法中,被害人的任何行為(作為、忍受、不作為)皆可以成為強制的結果和勒索罪中財產損失的中介。有鑒于此,成立勒索是否需要被害人的處分行為呢?在德國,判例和多數觀點認為,構成勒索不必以被害人處分為要;⑥Vgl.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3 ff.;LK-Vogel,2010,§253,Rn.13 ff.少數觀點則主張,勒索以被害人處分為要。⑦Vgl.Wessels/Hillenkamp,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10,Rn.712 f.
這兩種觀點在德國司法實務中的區別,體現在暴力搶開他人汽車的案件之中。按照前一種觀點,當被告人以暴力搶開被害人的汽車一陣子之后,又將車輛返還給他,直接成立搶劫性勒索(處罰較重)。⑧《德國刑法典》第255條(搶劫性勒索)規定:“如果勒索是用針對人的暴力或者在使用帶有對身體或生命的現時危險的威脅之下實施的,對行為人處與搶劫者同樣的刑罰(一年以上自由刑)。”Strafgesetzbuch,Beck-Texte im dtv,2009,S.127.根據后一種觀點,搶開他人汽車的,由于缺乏交付或者處分,不構成搶劫性勒索,同時,因為缺乏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構成搶劫,而只能構成強制罪和未經許可使用交通工具罪(處罰略輕)。⑨《德國刑法典》第240條(強制)規定:“非法用暴力或以明顯的惡行相威脅,強制他人為一定行為、忍受或不為一定行為的,處3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第248條b(未經許可使用交通工具)規定:“違背權利人的意愿,擅自使用其汽車或自行車的,若該行為未在其他條款規定更為嚴厲的刑罰的,處三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Strafgesetzbuch,Beck-Texte im dtv,2009,S.123,126.德國的自由刑最短為一個月,這使得成立強制罪和未經許可使用交通工具罪通常而言比成立搶劫性勒索處罰更輕。除了實務上的這一區別外,在德國刑法學中,這兩種觀點還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討論。
(一)“被害人處分不要說”的主張及其理由
在德國,主張被害人處分不是成立勒索罪的必要要素的,是判例和部分學說(多數觀點),其理由如下。
第一,在德國刑法史上,勒索罪是從搶劫罪中發展起來的,其擔負著填補搶劫罪的漏洞的任務,并且,在當今的《德國刑法典》中,勒索罪與搶劫罪被置于同一章,而不是與詐騙罪被歸為一類。《德國刑法典》第255條規定的搶劫性勒索的處罰,也是指向搶劫而非其他罪名。可以說,德國刑法發展史說明,勒索與搶劫之間是補充法與基本法的競合關系,而非互斥關系。⑩Vgl.SK-Sinn,2010,Vor§249,Rn.16.
第二,德國刑法不僅保護絕對權免受外界直接的侵害,而且也保護相對權免受外界直接的侵害,比如,《德國刑法典》第289條規定的抵押品的取回(“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以違法的意圖從用益權人、質權人、使用權人或留置權人處取回他自己的或他人的動產,處三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便是如此。?gl.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6.所以,那種認為“勒索罪由于保護的是(包括相對權在內的)整體財產,也就不能像絕對權所享受的免于自外向內之侵害的刑法保護那樣,而只能通過阻止自內向外的處分來實現刑法保護”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要求成立勒索以被害人處分為必要,是將勒索罪的犯罪結構理解成詐騙罪那種(類型化的)間接正犯結構。在詐騙罪的場合,被告人以間接正犯的形式對被騙者進行操縱,從而使得被騙者淪為被告人的行為媒介,基于此,操縱他人“自我損害”便應認定為“他人(即被告人)實施的損害”而受到詐騙罪條款規定的處罰。如果將勒索罪類比于間接正犯式的詐騙罪,那么被告人以輕微暴力的方式直接侵犯被害人財產,就會因為沒有借助被害人之手間接侵犯其財產,進而缺乏被害人處分這一必要要素,而無法成立勒索罪了。并且,將勒索罪類比于詐騙罪是有問題的,因為詐騙只能以間接正犯的方式展開,以直接正犯的形式來欺騙對方,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告訴對方要侵犯其財產的真相,就無法詐騙了。這種間接正犯結構是詐騙這一犯罪行為所獨有的,不是財產犯罪所共有的特性。強制罪既可以以間接正犯的方式(以暴力相威脅或者脅迫),也能以直接正犯的形式(“暴力”或“絕對的力量”,absolute Gewalt)實施,所以,沒有理由如詐騙罪那樣,將勒索罪限制在間接正犯式的行為之上。?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9 ff.
第四,《德國刑法典》勒索罪罪狀中的“忍受”應解釋為缺乏處分意思的情形。該法典第240條強制罪的結果,包括由暴力(即絕對的力量)所造成的“忍受”,而其第253條勒索罪由于使用了與第240條相一致的文字表述(“忍受”),也就應當采取前后一致的解釋。“暴力”造成單純的“忍受”是沒有處分意思的。?這是赫德根(Herdegen)在《萊比錫刑法典評注》中的觀點。Vgl.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4.“忍受”包括“忍受他人的拿走”之意,而“拿走”正意味著被害人沒有交付的動作。?Vgl.BGHSt 25,228;LK-Vogel,2010,Vor§§249 ff.,Rn.57.
第五,如果勒索須以被害人處分為必要,就會導致在暴力強開汽車這種憑借“絕對的力量”侵害財產的案件中,既不成立搶劫(因為缺乏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成立搶劫性勒索(由于缺乏財產處分),而如果被告人采取更緩和的手段,比如以暴力相威脅或者施加加重的脅迫,從而使得對方交付財物,那就可以依照《德國刑法典》第255條處以和搶劫罪一樣的刑罰,嚴重之情形下甚至可以適用“嚴重的搶劫”(第250條)乃至“帶有死亡結果的搶劫”(第251條)這些罪名的刑罰。?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8.這是對使用更為嚴重的暴力手段的行為判處輕刑,而對采用更為緩和的行為手段的情形判處重刑,屬于罪刑失衡。
第六,若要求以被害人處分為必要,就會使得以“絕對的力量”(即“暴力”)撕毀債務憑證或乘坐出租車下車時不買單直接暴力奪路而走這種以暴力逃避債務的行為無法成立(處罰更重的)勒索罪,而只能論以《德國刑法典》第240條強制罪。?持槍拒付出租車費的案例,見BGHSt 25,224(227 f.)。
(二)“被害人處分必要說”的主張及其理由
在德國,主張成立勒索罪需要被害人處分的,主要是部分學說(少數觀點),其理由如下。
第一,德國立法體例區分“針對物的犯罪”(Eigentumsdelikt)和“針對財產的犯罪”(Vermoegensdelikt)。前者如盜竊、搶劫,其對象只針對有體動產,這類有體動產可以呈現固態、液態和氣態,但電力這類能量則不包括在內。后者如詐騙,針對的是有經濟價值的財物及財產性利益。在“針對財產的犯罪”中,總是以進入到財產受損者的財產領域之內,從內部掏走其財產(即間接侵入財產)作為其表現形式的。被告人要么利用本屬于被害人財產領域的某個犯罪工具(如在詐騙案件中),要么是自己就身處于被害人的財產領域之內(如在背信案件中)。刑法只在面對絕對權(對世權)時,以特定方式提供保護以免受到他人從外界直接入侵受損失者財產領域,?這是薩姆森(Samson)在其著述中提到的。Vgl.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36.而勒索乃是針對整體財產的犯罪,其侵犯對象包括相對權(對人權),所以其構成要件像詐騙罪一樣,以財產處分這一形式的受害人加功為必要,并以從內部掏取受害人財產作為其構成要件的特征。
第二,要求勒索必須以財產處分為必要,并不意味著在《德國刑法典》第253條中采用與第240條強制罪中不同的“暴力”概念。要求勒索在構成要件上必須具備財產處分要素,不會影響到“暴力”的界定,不會(在理論上)導致產生一個限縮了的“暴力”概念,而只是會將施加暴力的特定情形,從勒索構成要件中排除出去,并且,在德國的普通法時代和德國以前多數的諸侯國法典中,“絕對的力量”(即“暴力”)并不是勒索的手段。?這是弗蘭克(Frank)在其著述中提到的。Vgl.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5.
第三,要求勒索必須以處分為必要,是在勒索罪的成立上增添了一個構成要件要素,從而限縮了勒索罪的入罪范圍,這在罪刑法定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雖然“被害人處分不要說”的方案在刑事政策上可能更有助于抗擊暴力犯罪,但“被害人處分必要說”的觀點在理論上更為合適。?Vgl.Wessels/Hillenkamp,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10,Rn.712 f.
第四,《德國刑法典》第240條和第253條中的“忍受”(dulden),在字義上乃是一種“有意的舉止”。如果要將它解釋為“無意的舉止”,那就逾越了文義的界限,因為在德文中,只有“任由”(erdulden)才是“無意的舉止”。通過改變法條表述的文義,去解決解釋上的難題,屬于立法者(而非司法者)的任務。?SK-Sinn,2010,Vor§§249,Rn.15.
第五,要求勒索必須以被害人處分為必要,不會導致罪刑失衡。在暴力搶開汽車的場合,“被害人處分不要說”認為,暴力搶開汽車也應成立搶劫性勒索,否則就是重行為輕處罰了。然而,“暴力”(絕對的力量)也包括把車主騙出車外并將車主關在車外,從而奪路而逃的情形。此時的“暴力”,并不比拿槍逼迫車主轉移汽車操縱權更為嚴重,所以,將暴力搶開他人汽車的行為,判定為符合未經許可使用交通工具罪和強制罪的構成要件,是合理的。?Wessels/Hillenkamp,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10,Rn.712.
(三)“被害人處分必要說”的芒刺與觀點的選擇
以上正反兩方面的意見見仁見智、各有理由,這就需要在理論上對這兩種意見作出適當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處分必要說”存在一處較嚴重的實務疑點:如果被告人采用普通的脅迫手段,例如以揭發犯罪相要挾,以阻止被害人對其采取反抗措施,從而自己將被害人的財物拿走(而不是由被害人交付)的情形,應當如何處理?
在德國刑法學中,該種情況稱作“小搶劫”(kleiner Raub),由于其主流學說和判例主張勒索不以被害人處分為要,將這種案件作為《德國刑法典》第253條普通勒索罪來處理,沒有疑義,而主張被害人處分為必要的觀點,卻認為此處應當成立強制罪和盜竊罪的想象競合。?LK-Vogel,2010,Vor§§249 ff.,Rn.58.福格爾教授則認為,此處處分不處分的問題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這時被告人迫使對方放松管理,尚不構成財產損失,而之后的拿走則是盜竊,認定盜竊在德國法上處刑較之于勒索更輕。LK-Vogel,2010,Vor§§249 ff.,Rn.61.《德國刑法典》第242條(盜竊)規定:“意圖盜竊他人動產,非法占為己有或使第三人占有的,處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trafgesetzbuch,Beck-Texte im dtv,2009,S.124.
“小搶劫”案件中,被害人讓被告人拿走財物時,被害人自己的行為狀態,應當如何認識呢?此處被害人并無交付行為,不具備處分的表象,若要將其也視為處分,那就要從別的角度加以解釋。有人提出,被害人的舉止只要是有意識的就可以,反對的意見則認為,這會導致改變財產處分概念的含義。?這也是赫德根在《萊比錫刑法典評注》中的觀點。Vgl.LK-Vogel,2010,Vor§§249 ff.,Rn.65.因此,更多人采取的是被害人還有無“選擇自由”或者“采取其他舉止的可能性”的方案來判定其有無處分:被脅迫者只要認為自己的加功,仍能造成財產損失結果或者使對方牟利,認為自己是這方面的關鍵環節(Schluesselstellung)(如知道財產藏匿處或保險箱密碼),或者他仍有其他能阻止財產損失或對方實現牟利的舉止,就是在處分。如果他認為他已經到了不管采取何種舉止都于事無補的地步,已經沒有選擇的自由或沒有采取其他舉止的可能,因為不管被害人是否加功,被告人無論如何都會實現造成對方損失和牟利的目標,這時,就算被害人有交付的形式,也不能認定有處分,這種交付應當認定為“拿走”。反之,如果他認為還可以有選擇或者采取其他舉止的可能,比如,可以向他人求援以阻止拿走,但他覺得這樣做會遭到對方傷害或者殺害,于是有意不選擇求援等其他舉止,則他忍受被告人拿走其財物,也應認定為“處分”。?Vgl.Lackner/Kuehl,2007,§255,Rn.2;S/S-Eser,2001,§249,Rn.2.
反對“選擇自由”的意見認為,若有選擇自由但忍受被告人拿走其財物,應認定為“處分”,會導致許多“搶劫”被認定為“搶劫性勒索”。在被害人認為損失無論怎樣都會發生的時候,不應認定他沒有采取其他可能舉止的“選擇自由”:他仍然可以出于自尊心的原因進行反抗,即使反抗在他眼里可能并無多大成功的希望。如果他放棄了這種反抗,以使得被告人在這方面省了力氣,那么這個被害人在逃避脅迫壓力這個問題上,與那些覺得有可能阻止損失的被害人,并無多大區別。所以,搶劫和搶劫性勒索的區分標準,還應該是行為的外觀究竟是拿走還是交付。具體而言,也就是“拿走”(不排除有被害人的加功)的為搶劫,“交付”(不排除有被告人的加功)的為勒索。這個標準非常淺顯,也是有操作意義的,它不僅合乎真實案件中常見的情形,而且符合法律文字的表述。?Vgl.LK-Vogel,2010,Vor§§249 ff.,Rn.66.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同樣存在“小搶劫”成立敲詐勒索的案件,如(“顧某等人敲詐勒索案”)2000年8月的一天,被告人顧某、張某、魯某等人在明知被告人崔力(已另案起訴)盜竊了摩托車的前提下,以送其至派出所相威脅,敲詐并奪走崔力盜竊得來的錢江125型摩托車1輛(價值人民幣4000元)及人民幣300元。法院認定顧某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張某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魯某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拘役6個月,緩刑6個月。?參見劉中發主編:《刑事案例訴辯審評——敲詐勒索罪》,中國檢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頁以下。然而,與德國立法體例不同,我國《刑法》中并未規定所謂“搶劫性勒索”的罪名,故需要區分的不是(處罰上無異的)搶劫與搶劫性勒索,而是(處罰上有異的)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就被害人處分而言,筆者以為,被害人是否有處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關于財產的意思自由是否完全被取消。為了自尊心而反抗,并不能代表他有自由處分的意思,因為在經濟社會中,“理性人”的標準并不會要求人為了單純的自尊心去殊死反抗。由于許多搶劫案件中也存在被害人交付的現象,在德國,采用外觀來區分搶劫與搶劫性勒索的辦法,將這類搶劫案件認定為處罰上相同的搶劫性勒索,并無不可。然而,在我國,若運用該種方法將它們認定為處罰偏輕的敲詐勒索罪,則在處罰上未免有重行為輕處罰之嫌。所以,不適宜以外觀方法作為我國刑法中區分搶劫和敲詐勒索的標準。由于意思自由乃是處分的前提,理論上關于“小搶劫”案件中是否存在被害人處分的爭論,便可引出另一問題:能否以受害人意思形成的不自由作為認定是敲詐勒索行為還是搶劫行為的標準?
在回答該問題前,應明確的是,以受害人真實的事后心理反應,特別是其在案件中事后表現出的膽量,來判斷被告人之前的行為是搶劫行為還是敲詐勒索行為,是不妥當的。因為究竟是搶劫行為還是勒索行為,需由司法者對其客觀地予以評價,只有被告人著手犯罪之前所把握到的受害人的情況,才可以作為判定被告人之行為性質的輔助資料。在這一前提之下,被害人在接收到被告人的搶劫或敲詐勒索信息之時,會出現的不能自由形成自己意思的情況,才可以作為判斷被告人行為性質的輔助材料。具體而言,在出現搶劫信息時,被害人的意思形成自由是被完全取消;在收到敲詐勒索信息時,被害人的意思形成自由只是受到限制。有鑒于此,在“小搶劫”的場合,只是限制了被害人的意思形成自由,即便缺乏被害人處分的動作(在前述“顧某等人敲詐勒索案”中,被告人奪走了摩托車),也應當認定為敲詐勒索罪而非搶劫罪。或許有人認為該種情形宜成立搶奪罪,但是,如果認定搶奪罪,就不適當地遺漏了對脅迫行為的評價。
二、我國法上的敲詐勒索罪應否以被害人處分為必要
在我國,任何國外的理論分析,都須結合我國實際的情況予以取舍。以下便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對敲詐勒索罪應否以被害人處分為必要作出研析。
(一)我國語境下采用“被害人處分不要說”的理由
在德國刑法學中,不管是主張不需要被害人處分作為必要要素的主流學說,還是主張被害人處分作為勒索罪要素的少數說,都給出了較細的論證,盡管結論可能未必符合我國的立法和司法路徑,但是其論證過程是有啟發性的。特別是其結合文義的方法論視角以及關于“小搶劫”案件的論述,對我國相關問題的討論有參考價值。筆者認為,在我國刑法學中,也不應堅持將被害人處分作為敲詐勒索罪的要素,而只需被告人敲詐勒索行為侵犯財產的風險,體現在對方的財產損失之中即可。這與德國刑法學中該問題上的判例意見是相似的。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理由如下。
第一,我國《刑法》中關于敲詐勒索罪的表述,既不同于《德國刑法典》,也不同于《日本刑法典》。我國《刑法》未像《日本刑法典》那樣明文規定“交付”的字眼。這使得日本刑法學中以被害人處分作為構成要件要素的做法,難以直接套用于我國敲詐勒索罪的討論。我國也沒有像《德國刑法典》那樣,規定“強制他人為一定行為、容忍或不為一定行為”,這使得“被害人處分必要說”的支持者所主張的“忍受”(dulden)不同于“任由”(erdulden),進而反對將“忍受”解釋為“忍受他人拿走”的論據,在我國缺乏相應的實定法前提。
第二,“交付”還是“拿走”作為被告人行為的外觀,只屬于表面要素,它不能夠決定犯罪的不法程度。在用“絕對的力量”(比如持槍搶劫)要求對方交出財物的場合,有交付的動作,但仍然無疑應當成立搶劫,而非敲詐勒索。“交付”或“處分”的動作,不是敲詐勒索罪特有的外在特征,在搶劫罪中同樣可以有。我國立法部門也未要求以“處分”作為區分搶劫和敲詐勒索的標志。?參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91-492頁。
第三,在“小搶劫”的場合,仍然應當成立敲詐勒索罪。如果堅持“被害人處分必要說”,就必須在此種場合中對“處分”作寬松化或者泛化的理解,即不再以被害人的實際交付為內容,而是主張被害人有“(被動)處分的意思”就足以認定“處分”:即使被告人親手拿走了財物,也應認為被害人本人存在“默許”的處分意思。?參見前注③,勞東燕文,載前注③,陳興良主編書,第579頁。勞東燕教授認為被害人“單純轉移占有的意思”即已足夠。可是,在筆者看來,這種“(刑法效力交談上)無意義”的轉移動作,只能算是案件中時而會有的表象,它無法充作需要犯罪含義的“構成要件要素”。勞東燕教授還反對將“小搶劫”認定為敲詐勒索既遂,而是主張定敲詐勒索未遂和搶奪(或盜竊)數罪。在筆者看來,這是將一個行為分成了兩個行為來處理,例如,被告人看見被害人手機放在桌上,便對站在一旁的被害人說:“你不要過來,不然揭發你的犯罪。”被害人便保持原地不動,于是手機被對方拿走。這時被告人的行為明明侵犯了財產,應該是敲詐勒索既遂,而不是敲詐勒索未遂加盜竊罪的數罪。然而,作出此種理解會改變交付、處分概念的含義,在罪刑法定原則上存在缺陷,同時,也使得被告人行為的不法性質,不再取決于自己的行為,而要取決于被害人的主觀意識,容易造成定罪量刑中的恣意。此外,在“小搶劫”的案件中,訴諸于被害人“處分意思”的做法,還會導致一處疑惑:“處分意思”是什么?在筆者看來,只有意思形成尚有自由的情況下,才有處分意思,意思形成不自由便沒有處分意思;被告人的行為尚未達到取消被害人意思自由的程度,就意味著其行為沒有壓制性,對方還可以反抗。?至于對方實際上有沒有加以反抗,則另當別論。該問題便由此進一步轉化為:被告人的行為有無壓制性?如此轉化使得規范交往的對話者從被害人轉換為被告人。刑事處罰以被告人而非被害人為談話對象,才是刑罰法的真義所在。?參見潘星丞:《兼有欺詐與勒索因素的刑事案件之司法認定》,《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6期。因此,在“小搶劫”的場合,借助“處分的寬松化”以貫徹“被害人處分必要說”是不合適的。
第四,采用“被害人處分不要說”并非德國法的特例,在東亞地區也存在相應的規定。《蒙古刑法典》第149.1條規定:“以暴力威脅被害人本人及其近親屬,或者以傳播可以詆毀被害人本人及其近親屬的信息,以及以毀損被害人本人及其近親屬所有的或保管看守的財物相威脅,并有可能實際造成損害,要求轉讓財物或物權或履行任何具有財產性質的行動的,處以最低工資額251倍以上300倍以下罰金,并處3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監禁或3年以下徒刑。”?參見《蒙古國刑法典》(英文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頁。我國臺灣地區有關規定中有所謂“恐嚇得利”罪。依該規定,在行為人恐嚇他人以免除債務的情形下,被害人并無處分行為,但這不妨礙恐嚇者成立犯罪。例如,甲雇傭出租車旅行,因無力支付用車費用乃于車行至荒僻之地時,命令司機乙停車,詭稱系逃犯,并將攜帶的小刀一把故意露出,聲言欲索用車費用隨同其上山取之,致乙心生畏懼,不敢索取用車費用,隱忍而歸。?參見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臺北)2006年版,第509頁。依照我國《刑法》,該行為(在不考慮數額的情形下)屬于“敲詐勒索財產性利益”的范疇,同樣不妨礙敲詐勒索罪的成立。
第五,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由于搶劫、盜竊罪的對象“財物”在實際適用中已經脫離其表面文義,明顯出現了將財產性利益等內容納入其范圍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下,不記名、不掛失的債權憑證等財產憑證已經成了搶劫、盜竊等罪的適格對象。?參見陳興良:《規范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36-837頁;前注②,張明楷書,第974-975頁。以絕對力量撕毀被害人的債權憑證,以及暴力迫使出租車司機放棄出租車車費,均可能處以搶劫罪。換言之,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以搶劫罪、盜竊罪的方式對絕對權與相對權均進行刑法上的保護,以免其受外界直接的侵害。所以,如果以敲詐勒索和詐騙阻止的是整體財產、相對權的損失而非絕對權的喪失為由,進而主張敲詐勒索具備區別于搶劫、盜竊等罪的間接正犯結構和肯定敲詐勒索成立以被害人處分為必要,就沒有注意到搶劫、盜竊等罪在我國同樣可以針對相對權乃至整體財產而成立。這樣,認為敲詐勒索由于可以針對相對權,就具有間接正犯結構和需要被害人處分的主張,便站不住腳了。
(二)采用“被害人處分不要說”的影響:搶劫與敲詐勒索之間成立競合關系
采用“被害人處分不要說”,也有助于明確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之間是屬于競合關系,還是互斥關系,從而合理地劃定兩罪的成立范圍。我國有學者認為,如果低程度的行為能夠成立甲罪(敲詐勒索罪),那么高程度的行為更能成立甲罪(敲詐勒索罪),所以,成立敲詐勒索罪只需要達到低程度即可,如果行為達到高程度,則另觸犯搶劫罪。?參見張明楷:《犯罪之間的界限與競合》,《中國法學》2008年第4期。按照這種觀點,可以認為,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之間存在法條競合關系,前者是基本法,后者是補充法。?基本法與補充法,意味著兩個法條的構成要件之間屬于交叉關系,符合了前者的構成要件,未必符合后者的構成要件;特別法與一般法,則表明兩法條的構成要件之間成立從屬關系,符合了前者的構成要件,必定也符合后者的構成要件。當然,反對的觀點認為,應當保持以被害人處分作為敲詐勒索罪的必要要素,搶劫與敲詐勒索罪之間并非競合關系,而是互斥的關系。?參見前注③,車浩文。
在筆者看來,借助被害人處分來區分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并認為有被害人處分的是敲詐勒索罪,沒有處分的是搶劫罪,兩者呈現互斥關系的主張,是比較片面的。從現象上講,在許多搶劫罪的案例中,被害人也存在交付財物的情形,這就使得它較難與敲詐勒索罪相區分。進一步而言,使用被害人處分作為區分標準,也有利用被害人的行為來決定被告人行為的犯罪性質的嫌疑:被害人事后有自主的處分,被告人的行為就成立敲詐勒索罪;被害人事后沒有自主處分,則成立搶劫罪。這會使得被告人的罪責依附于作為個別情形的被害人的習性,而不是取決于被告人在刑法規范上對于自己的行為所應當承擔的責任。搶劫與敲詐勒索之所以不同,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在于其采取的究竟是搶劫行為,還是敲詐勒索行為。如果其采取的行為能夠取消具體被害人為了保衛財物而加以反抗的意思自由,就是搶劫行為,自然,在這種場合,無論是被告人拿走還是讓被害人交出財物,都不存在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被害人處分。如果被告人采取的行為只是限制具體被害人為保衛財產而反抗的意思自由,則是敲詐勒索行為。這種場合下,被告人已經給被害人留出了自主處分的空間。所以,被害人處分與被害人意思自由是否被取消一樣,均只是判斷被告人行為之不法內容的輔助性材料,不能倒過來決定其行為本身的不法性質。
以被害人處分來作為互斥的標志,只是看到了犯罪結構這一方面,犯罪結構只是反映了犯罪行為的外觀,雖然借助犯罪行為的外觀在很多時候可以區分出不同犯罪的界限,但是,這仍然是一種不關心規范保護目的的本體論徑路,進而可能會錯失問題的關鍵點,導致耗費很多精力,卻得不到應有的成效。在筆者看來,還是應把關注點放在規范的保護目的上,換言之,也就是要注意財產法益在敲詐勒索罪和搶劫罪這兩個罪名上的體現。犯罪對象則是法益的現實載體,這樣就有必要考察這兩個罪犯罪對象的范圍寬窄問題。馬克昌教授從犯罪對象的角度提出敲詐勒索罪和搶劫罪之間存在對象上的區別:“……索取利益的性質不同。本罪(敲詐勒索罪——引者注)取得的可以是動產或不動產,也可以是財產性的利益;而搶劫罪獲取的一般只能是動產”。?馬克昌主編:《刑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9頁。張明楷教授在論證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之間是補充法與基本法的關系時,便針對該“對象上的區別”加以駁斥:“既然敲詐勒索取得的可以是動產,而搶劫罪獲取的一般只能是動產,那么,一方面,當行為人獲得的是動產時,上述……區別便沒有意義。另一方面,既然搶劫罪獲取的‘一般’只能是動產,那么,當特殊情況下行為人搶劫了動產以外的財產時,也可能成立搶劫罪,上述……區別也沒有意義。”?同前注?,張明楷文。
張明楷教授可能是在試圖將財產性利益也納入搶劫的對象以批駁互斥論,但是,這似乎在論證理由上未能切中肯綮。按照德國刑法立法體例,搶劫罪屬于“針對物的犯罪”,而非“針對財產的犯罪”。這使得搶劫了不值錢的親人紀念照在德國只成立搶劫(對象只需要是“物”,而不需要是有經濟價值的“財產”),而若勒索不值錢的紀念照卻根本無法成立勒索罪,因此,德國的搶劫與勒索之間屬于基本法和補充法的關系,而非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我國《刑法》中并不存在“針對物的犯罪”與“針對財產的犯罪”的二分法,故我國司法實踐不會將搶劫了他人不值錢的親人紀念照認定為搶劫罪,這也使得在我國不會由于被告人搶劫了無經濟價值的物,而出現德國刑法中那種成立了搶劫罪卻不成立勒索罪的現象,進而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之間似乎也無法呈現基本法和補充法的關系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與德國的情形不同,雖然我國司法實踐不會將搶劫了他人不值錢的親人紀念照認定為搶劫罪,卻會將搶劫毒品、假幣、淫穢物品認定為搶劫罪。?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指出:“以毒品、假幣、淫穢物品等違禁品為對象,實施搶劫的,以搶劫罪定罪;搶劫的違禁品數量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搶劫了違禁品,是依照司法解釋成立搶劫罪的,而敲詐勒索違禁品是否入罪,則似乎缺乏相應的司法解釋。倘若這無法成立敲詐勒索罪,那就意味著,實施了“高程度的搶劫行為”仍可以不符合“低程度的敲詐勒索行為”。由此可以推出的結論是:在我國,依照司法解釋,通過在違禁品問題上成立犯罪的肯定與否,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之間仍然可以呈現基本法與補充法的競合關系。然而,若敲詐勒索違禁品、贓物,也成立敲詐勒索罪(如前述“顧某等人敲詐勒索案”),?理論上的觀點,見前注③,勞東燕文,載前注③,陳興良主編書,第576-577頁、第581頁。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之間就成立特別法與一般法的競合關系了。
綜上所述,在實定法框架下,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可以成立基本法與補充法、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不過,實然法上這種競合關系的認識仍然存在說理弱點:第一,如果勒索了違禁品,意味著保護違禁品的占有免受勒索,這就與非法持有違禁品的犯罪在評價上產生了矛盾;第二,在我國司法解釋上,盡管違禁品屬于搶劫罪的對象,但是,在法律上還是沒有承認違禁品的價值(認定盜竊違禁品的具體數額時,原來只是“參考”而非“采納”違禁品非法交易的價格,現在是盜竊、搶劫“不計數額”)。?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毒品工作座談會紀要》(2013年后失效)指出:“盜竊、搶劫毒品的,應當分別以盜竊罪或者搶劫罪定罪。認定盜竊犯罪數額,可以參考當地毒品非法交易的價格。認定搶劫罪的數額,即是搶劫毒品的實際數量。”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盜竊、搶奪、搶劫毒品的,應當分別以盜竊罪、搶奪罪或者搶劫罪定罪,但不計犯罪數額。”故而,在應然法上,搶劫違禁品和敲詐勒索違禁品,皆應當只以非法持有違禁品的犯罪加以處罰。基于此種認識,搶劫和敲詐勒索的對象均只是合法的整體財產,存在區別的只是搶劫的對象范圍更為狹窄(比如不包括不動產),這樣,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之間,便不再是基本法與補充法關系,而只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競合關系。
三、結 語
敲詐勒索罪構成要件的滿足,是否以被害人處分為必要的問題,應當結合具體的立法體例展開討論。日本和德國的刑法中,日本法在恐嚇罪(相當于我國敲詐勒索罪)中規定了需以被害人處分作為犯罪成立的必要,德國法在勒索罪中沒有規定要有“交付”或“處分”的要素,因此,應當參考法律規定與我國相似的德國法來研討這一問題。在我國,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不宜堅持將被害人處分作為敲詐勒索罪的要素。敲詐勒索行為與被害人的財產損失之間,只需要被告人敲詐勒索行為侵犯財產的風險體現在對方的財產損失之中即可。敲詐勒索罪并不具有詐騙罪那樣的間接正犯結構,故而,也就不需要被害人處分這一要素。在所謂“小搶劫”和“敲詐勒索財產性利益”的場合,只要造成了相應的財產損失,無需被害人處分,就可能認定敲詐勒索罪既遂。在“被害人處分不要說”的條件下,司法解釋對搶劫違禁品成立搶劫罪進行了肯定,這使得搶劫罪可以憑借這一點在成立范圍上大于敲詐勒索罪,由此,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之間可以呈現基本法與補充法的關系。然而,敲詐勒索贓物也有成立敲詐勒索罪的,這使得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的犯罪對象重疊,它們之間又屬于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此外,從應然法上講,搶劫違禁品和敲詐勒索違禁品,均應只以非法持有違禁品論處,在這種條件下,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之間也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競合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