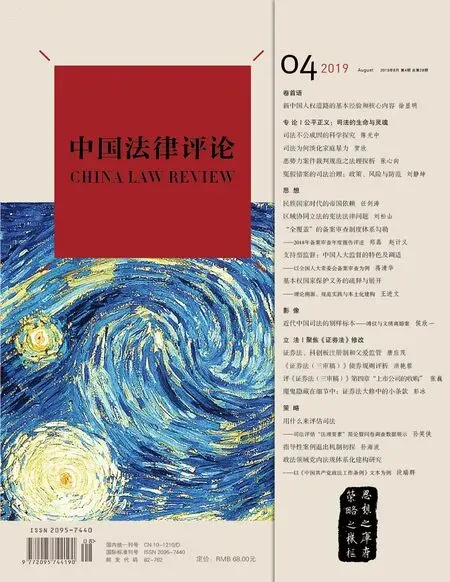指導性案例退出機制初探*
孫海波
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員
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副教授
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的出臺,具有中國特色的案例指導制度于2010年年末得以正式確立,這標志著中國司法界和理論界對于判例制度的摸索和研究又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在中國這樣一個以成文法為主導形式的大陸法系國家,實行判例制度也從理論構想變成了客觀現實,以至于有學者將這種實踐稱之為“中國式的普通法”。1See Mark Jia, "Chinese Common Law? Guiding Cases and Judicial Reform", Harvard Law Review, Vol.129, No.8 (2016),pp.2213-2234.在過去幾年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發布了21批共計112件指導性案例,案例數量越來越多、覆蓋面越來越廣,案例制度的發展重心已慢慢轉變到實踐適用的問題上來。在實踐中,當事人往往將指導性案例當作證據來提交,要求法官參照或拒絕參照從而來維護己方的權利訴求;而法院有時也會以明示的或默示的方式主動援引指導案例,這么做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統一適用和化解疑難案件的裁判僵局。盡管如此,我國指導性案例的司法適用局面也只是初步打開,使用的斷裂性(很大一部分還尚未被適用過)、啟動的混亂性(被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而提出)、參照的規范性(只提要求而不附加論證理由)、隱性適用盛行等不良現象普遍存在,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案例指導制度的健康發展。
為了克服實踐中存在的適用難點,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發布了《〈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就指導性案例的遴選標準、發布主體與程序、參照適用標準以及退出機制等內容作出了明確、細致的規定。就像法律必然面臨立、改、廢的命運一樣,在推進案例制度建設的過程中也會清理和廢止一些舊有過時的案例,同時選編和補充一些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通過推陳出新,形成一個不斷流動和變化的案例集群。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為了讓案例制度獲得新鮮的活力,相關主體在何種情形下、基于何種程序可以廢止指導性案例?是否允許法官在審判實踐中規避既存的指導性案例?法官規避指導性案例的可能理由有哪些?法官不當規避指導性案例應承擔何種責任?以上問題綜合在一起構成了指導性案例的退出機制,本文嘗試初步描繪這一制度的主要結構形式和內容。
一、對幾點常見誤解的澄清
在正式討論指導性案例的退出機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幾種誤解。當論及指導性案例時,應該認識到它已經不再是一種簡單司法判決的載體,而是由最高司法機關通過嚴格法定程序加以選編和發布的,具有一定的規范性拘束力的“判例”。2對指導性案例的效力學界素來存在爭議,主要有事實拘束力、規范拘束力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準規范拘束力三種觀點。參見張騏:《再論指導性案例效力的性質與保證》,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年第1期;以及雷磊:《指導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載《中國法學》2015年第1期。面對“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指導性案例”這一強行性規范,人們難免會產生這樣一種感覺,認為法官不能背離指導性案例,因此不存在“指導性案例的退出機制”。在一次法院系統的會議上,一位法院干部就曾對筆者所使用的這一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認為這一提法不符合案例指導制度的精神,指導性案例是拿來用的而非讓法官選擇規避適用。對此,筆者將對這些誤解加以說明和澄清,借此為指導性案例的退出機制正名。
第一,應認識到退出機制是整個案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退出機制的存在,可以讓案例制度獲得開放性和包容性,同時也讓法官在適用指導性案例時具有自主性和判斷權,避免在個案中機械性地照搬照抄裁判摘要所造成的實質不正義。顯然,提倡退出機制并不是要否定或破壞案例指導制度,它是案例制度發展所不可避免要涉及的內容。《實施細則》中已經初步為這一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正式的規范性依據,我們需要探索的是如何讓退出機制與選編機制、參照適用機制等內容之間,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
第二,“應當參照”并不意味著“毫無理由地必須參照”。
“應當參照”對實踐主體提出了比“可以參照”更強的規范性要求,這意味著法官在裁判過程中對“參照義務”是不能隨意放棄的。然而,不能隨意放棄并不意味著絕對不能放棄,正如法律在某些情況下由于自身的一些原因具有可廢止性(defeasibility),指導性案例也不總是能夠在所有案件中都要求法官適用自己。指導性案例生產機制的行政性和程式化,3參見鄭智航:《中國指導性案例生成的行政化邏輯》,載《當代法學》2015年第4期。會使某些案例先天就帶有缺陷,或者伴隨著政策改變或社會的發展而喪失存在基礎,因而必然面臨著廢止或在個案中被規避適用的命運。
第三,退出機制并不賦予法官自由背離乃至恣意漠視指導性案例的權力。
有人可能會擔心,退出機制會不會為法官提供了一個輕視指導性案例的機會或借口,只要他想規避就可以任意地作出規避決定。不得不承認,這種擔心是很必要的,如果法官可以自由地背離指導案例,那么案例制度勢必會被徹底架空。退出機制的內涵是豐富的,它會在程序步驟、實質理由以及責任負擔三個方面盡可能最大限度地限制法官的恣意行為,從而確保相關主體只有在極個別特定的情形下,嚴格遵照特定的程序才能廢止指導性案例的效力或背離不該參照的指導性案例。除此之外,任何缺乏充分理由或錯誤地漠視指導性案例的行為將要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第四,指導性案例的退出并不意味著案例指導制度的消滅。
指導性案例與案例指導制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是點與面的關系。指導性案例是案例指導制度的重要構成性要素,但是案例制度本身是個內容更豐富的概念,是一個包含指導性案例選編、發布、參照適用和退出于一體的動態體系。僅僅有指導性案例還尚不足以確立這一制度。同樣的道理,在實踐中清理或規避一定數量的指導性案例,也不足以從根本上撼動這一制度。因此,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指導性案例與案例指導制度之間的關系,案例指導制度的正常運轉離不開退出機制,而退出機制非但不會摧毀案例指導制度,而且還會為這一制度的發展不斷注入新鮮血液。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看到如果將案例指導制度看作一個綜合系統,那么退出機制應該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任何一個判例(案例)都有自己的生命,有的因為蘊含著一般性的法律原則、原理或精神而歷久彌新,而另外一些則隨著時代變遷而走到自己生命的盡頭。為了不斷給判例體系注入新鮮的活力,有必要弄清楚退出機制到底是怎樣的一套制度。在我國,狹義的退出機制主要是指專門主體對指導性案例的清理或廢止,有時也被人們歸入指導性案例的選編范疇,而廣義的退出機制還包括法官對指導性案例的規避適用,對此我們將分別予以介紹和討論。
二、指導性案例的清理或廢止
判例匯編(law report)是判例法得以運行的一個重要條件,通常只有被選中并刊載在判例匯編中的判例才具有正式性的拘束力。當然,由于判決本身的多樣性,加上判例編制主體既有官方的又有民間的,這就使事實上并非所有的判決都能得到匯編,而法官也時常可能會引用未經匯編的或來自判例匯編之外的其他叢書的判例。4參見[美]格倫頓、戈登、奧薩魁:《比較法律傳統》,米健、賀衛方、高鴻鈞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判例法的精妙就在于它是靈活與穩定的統一,遵循先例是一個兼具變與不變的過程。判例匯編會定期或不定期地將一些過時的或有重大內容缺陷的判例加以清理或廢止。當然除了這種有意的清理活動之外,某個判例由于與新的判例在內容上存在沖突而遭到長期漠視,或者其所蘊含的先例規則與新的成文規則相沖突,這種情形下判例也會失去其效力。
清理或廢止,在本質上是對判例效力的直接否定。在一些地方,比如我國臺灣地區,還存在一些變更判例內容的做法,這可以看作一種對相關判例之效力的間接否定。依照臺灣地區“法院組織法”第57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之裁判,其所持法律見解,認為編為判例之必要者,應分別經由院長、庭長、法官組成之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或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后,報請‘司法院’備查”,該法第2項又進一步規定,“‘最高法院’審理案件,關于‘法律’上之見解,認有變更判例之必要時,適用前項規定”。法院所作之判例也應像法律一樣具有一定的安定性,它能夠給人們以一定的信賴,因此不得隨意變更,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或符合相應的條件,方可為之。這里,比較有爭議的一個問題是,變更之判例應從何時發生效力,臺灣地區對此大致有三種不同觀點:其一,效力應追溯至判例所變更之判決公布當日以前要件事實已終結之案件;其二,只適用于該變更之判例公布后要件事實尚未終結之案件;其三,判例變更時除發生嗣后效力,同時也對要件事實已告終結之原因案件發生效力。5參見孫銘宗:《臺灣地區判例制度之評析與檢討》,載《江海學刊》2014年第6期;林合民:《論“司法院”解釋及判例變更之時的效力》,載《臺灣憲政時代》1987年第4期。以筆者之見,依照信賴保護原則,判例就像法律一樣,一般只對變更以后的法律事項產生約束力。故而所變更之判例原則上對其之前的案件并不具有約束力,如果新判例的適用更有助于保護爭訟當事人利益的,也可以有限地承認變更之判例的溯及力。
變更判例與廢止判例,從語義的角度來看也是不同的,變更意味著一定是改變了過去舊有的東西,同時又要以新的東西取而代之。換言之,變更判例是一種推陳出新,意味著要以新的觀點取代法院以前對于某個法律問題的舊有觀點,而廢止判例只是推翻或取消了法院之前對于某個法律問題所持有的見解或立場。6參見王澤鑒、楊日然、黃茂榮等:《判例之拘束力與判例之變更》,載《臺大法學論叢》1980年第1期。從這個意義上講,變更判例是先破后立,廢止判例是只破不立。
現在我們轉向判例的清理或廢止,由于這種活動觸及對判例效力的直接或根本否定,通常是由特定主體進行的,具體來說是由有權創制判例的主體來完成的。這也是清理和廢止判例與規避判例之間存在的一個根本性區別,后者在活動主體上并不加嚴格限定,只要是法律適用者,在實踐中通常都有權規避指導性案例。
(一)活動主體
在我國,對于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有權作出判例編撰活動。在檢察案例指導制度中,有一項制度叫“宣告失效”,這與清理或廢止在實質上是基本一樣的。對于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只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有權作出清理或宣告失效的決定。其法律依據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19條之規定,“宣告指導性案例失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決定。”鑒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內部分別成立了專門機關,集中統籌和執行指導性案例的清理和廢止工作。
通過上面的討論來看,在我國指導性案例的清理或廢止主體具有專門性或特定性。除此之外,它還具有單一性,分別只有一個單一的特定主體有權從事此類工作,作為個體的法官無權對指導性案例作出此類具有“準立法性質的”否定性評價。這一點上,普通法系的司法實踐是完全不同的。在普通法系國家中,除了集中的判例編撰工作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推翻判例”(overruling)制度。“對先例的推翻實質上是法院在相互沖突的諸多價值中進行選擇和判斷的過程,法律一方面必須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又必須適應時代進行自我變革,以在社會中發揮應有作用,推翻先例可以說就是在穩定與變革性之間所作出的價值選擇。”7何家弘:《外國司法判例制度》,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95—96頁。從推翻判例的主體來看,一般上級法院可以推翻下級法院的判例,本級法院可以推翻自己先前的判例,原則上下級法院無權推翻上級法院的判例。通過對比發現,普通法系國家在推翻先例方面,主體也仍然是相對特定的,只不過其范圍會更加廣泛一些,形式也會更為靈活一些。
(二)清理或廢止判例的條件
判例的作出與公布,本身代表著官方對于特定法律議題所持有的見解,按照平等對待的原則,人們有理由相信自己的類似爭議在未來會被以類似的方式而解決。如果允許相關主體任意地變更或廢止判例,就會對現行的法秩序的統一性帶來干擾,整體上降低法律體系的有效預期。因此,對于判例的清理或廢止要設定一定的條件限制,只有判例在出現以下情形的時候才能啟動清理或廢止的程序。大體上講,主要包括兩種情形:要么判例完成任務,已經過時,而與新的情況或局勢格格不入;要么判例本身在內容上存在缺陷,或與法律之間存在沖突。
《實施細則》第12條規定了兩種情形下指導性案例失去指導作用:第一種情形,指導性案例與新的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司法解釋相沖突。在我國,指導性案例具有一種接近法源或準法源的地位,但它仍然與作為正式法源的成文法存在本質性差異。如果指導性案例與新的成文法內容出現沖突,其效力自然無法壓倒成文法的規定。第二種情形,是為新的指導性案例所取代。指導性案例之間出現觀點沖突的情形難以避免,如果針對同一個法律問題,新的指導性案例改變了在先的指導性案例的觀點,那么舊有的指導性案例將會失去效力。在以上兩種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展開清理和廢止工作。
《規定》第19條明確列舉了宣告失效的幾種情形,分別是:(1)案例援引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釋廢止;(2)與新頒布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釋沖突;(3)被新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取代;(4)其他應當宣告失效的情形。具體來說,第一種情形是指導性案例做出的成文法依據喪失了,因此其繼續存在的正當理由也就不復存在了;第二種情形是與新的成文法相沖突,其所蘊含的裁判觀點已被新的權威性觀點所取代;第三種情形實質上是舊有的指導性案例所蘊含的裁判觀點被新案例中表達的觀點所取代,同樣也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此外還有一個兜底性條款,比如指導性案例疏漏了非常重要的事實,結果導致法律的適用出現嚴重的錯誤,在指導性案例出現或存在這種實質性缺陷的情況下,也可以成為宣告該案例失效的一個重要理由。
從普通法系的實踐經驗來看,推翻先例的理由也涉及很多方面。布萊恩·A.加納(Bryan A.Garner)詳細地提出了六種可能性理由,包括:第一,先例判決與明確的法律原則出現沖突;第二,先例裁決是單個的,做出來之后一直未被適用或參照過;第三,法院對于某個重要問題的判決現在遭到了嚴重的質疑(seriously doubted);第四,先例裁決作出時的客觀情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第五,被推翻的先例尚未建立起重要的信賴利益;第六,盡管推翻先例可能會影響到一些個體的或私人的權利,但是它首先出現了錯誤,它產生了普遍的不正義。8See Bryan A. Garner eds., Law of Judicial Precedent, Thomson West, 2016, pp.396-401.英國學者尼爾·達克斯伯里(Neil Duxbury)也介紹了推翻先例的兩點重要理由:首先,最明顯的一種是下級法院在創制先例時犯了錯誤,這是針對上級對下級法院發布的判例而言的。但是,如果是涉及推翻自己的判例,或者推翻同級法院的判例時,則會是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此時不僅要確認出現錯誤,而且要有十足的把握認為這是個“足夠清楚的錯誤”(clearly wrong)。其次,有的時候法院在推翻先例時,可能還需要有更強的理由。比如說,很確信推翻錯誤的先例將會給法律帶來一種整體的改進,哪怕有時候只是一丁點的改進。又比如說,所期待實現的改進是單靠立法干預所無法實現的。9See Neil Duxbury, The Nature and Authority of Preced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18-119.由于推翻先例在普通法中已經進入法官造法的范疇,所以實踐中往往會對這種行為施加非常嚴格的限制。
(三)清理或廢止判例的程序
清理或廢止判例不是任意進行的,除需要滿足以上諸種條件之外,還意味著這種活動應遵循一定的程序或步驟。就目前關于指導性案例的規范性文件來看,無論是針對法院還是檢察院的指導性案例的清理或廢止,都尚無明確、直接的規定。
此前學者們曾爭議過,對于指導性案例的廢止,是否應該經過一個特別確認的程序,還是將這個問題留待后案的法官根據具體情形自行定奪?對此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指導性案例的廢止應由發布機構根據下級法院、當事人的申請,或者依職權予以廢止,在廢止的程序上應當同確定指導性案例的過程一樣規范,并加以公布;第二種觀點認為,指導性案例的廢止應采自然死亡規則,無須經過專門的廢止程序,舊的指導性案例與新的指導性案例相沖突的自然失去效力。”10參見胡云騰、于同志:《案例指導制度若干重大疑難爭議問題研究》,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6期。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理由在于:第一,中國的法官、司法制度與普通法系存在很大差異,法官無權自行宣布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無效;第二,指導性案例的清理或廢止屬于廣義的指導性案例的編纂范疇,既然對于指導性案例的選編已經設定了一些嚴格、明確的程序,那么對指導性案例的廢止自然也要采取同等嚴格的程序;第三,如果采取自然廢止論,難題在于誰來判斷前后指導性案例是矛盾的或沖突的,何種矛盾或沖突能夠足以導致其中一個徹底失去效力,如果將這些問題完全交給后案中法官自行判斷和決定,難免會造成認識和判斷不統一的混亂局面。
鑒于此,筆者傾向于主張應為指導性案例的廢止設立一套程序規則。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為例,可以在借鑒指導性案例選編程序的基礎上提出一些基本的構想。根據《實施細則》第4—8條的規定,清理或廢止指導性案例的程序應大體上包含以下內容:第一,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統一行使清理或廢止指導性案例的權力;第二,各級法院、案例指導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陪審員、專家學者、律師、當事人,以及其他關心人民法院審判、執行工作的社會各界人士,認為指導性案例符合廢止條件的,均可以向案例指導辦公室提出廢止建議;第三,應該提出書面的廢止理由;第四,被提出廢止請求的指導性案例由案例指導辦公室按照程序報送審核。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的印發各高級人民法院,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人民法院報》和最高人民法院網站公布。
對于指導性案例的推翻活動,在普通法系國家并無明確的程序限制,而是采取由法官個人自主決定的模式。這種模式對法官個人的職業素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要求對遵循先例的原則有足夠深的認識和運用。此外,這種推翻還會受到整個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監督。即便如此,在推翻先例的問題上,實踐中還是形成了一些共識性的限制規則,這里我們只介紹一個比較具有代表性也很重要的規則,即推翻先例前的評估和權衡程序。法院需要評估推翻舊有先例、創制新的先例,是否能夠阻止造成更大的危險,這種評估將是一個略顯復雜的活動過程。11See Douglas E. Edlin, Common Law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9.同時這也是一個權衡利弊的過程,權衡維持舊先例與堅持適用新先例哪一種做法利大于弊,只有確證堅持適用新的先例能夠在整體上帶來更小危害時,推翻先例才具有了一種初始的正當性理由。用加納的話來說,即便是推翻了先例,其所帶來的傷害也必須要小于繼續維持先例所可能帶來的傷害。12See Bryan A. Garner eds., Law of Judicial Precedent. Thomson West, 2016, p.388.進行利益的評估和權衡,構成了法官在推翻先例前通常要履行的一個程序。由于兩大法系的司法制度、法官思維等的不同,中國案例制度中應設立一套嚴格的清理和廢止程序。
三、對指導性案例的規避適用
廣義的判例退出機制,除了判例清理和判例廢止這一專門化的行動之外,還包括審判實踐中法官對于判例的規避適用。它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法律適用活動,有智慧的法官會設法規避一個不恰當、不相關或有問題的判例,同時盡可能找到一個與眼前爭議案件真正相關、相似的案件,這也一直被認為是普通法之精妙或靈活性之所在。在構建我國特色案例指導制度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塊內容就是引導法官合理地規避對指導性案例的適用,從而確保在個案中真正地實現裁判正義。在大陸法系國家,下級法院一般不能推翻上級法院的判例,但是實踐中卻可以基于一些理由偏離上級法院的判例,比如說,為了更加嚴格地遵守法典或成文法文本,或者是為了在特定個案中實現正義或貫徹某項政策而不得已偏離某個先例中的解釋。據調查顯示,芬蘭、西班牙、瑞士的下級法院很少偏離上級法院的判決,但是一旦做了,他們往往傾向于以一種明示的方式進行。13See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 Summers eds, Interpreting Preced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7, p.523.我們這里的討論主要關注,法官在對指導性案例的規避適用過程中,是否需要借鑒德國建立一種特殊的判例偏離的報告制度?規避適用的實質條件(理由)有哪些?規避適用判例是否需要遵循某些程序性的規則(形式性要件)?
(一)不宜建立背離判例的“報告制度”
前文提及在推翻先例的問題上,普通法系采取了法官自主的模式,在規避適用判例的問題上將決定權交給作為裁判者的法官個人。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德國建立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判例偏離的報告制度。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例可以看作行使憲法解釋或違憲審查權的結果,因而具有正式的法律約束力,并能夠成為正式的法律淵源,各級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應像遵守法律一樣遵守這些判例。除此之外的其他法院的判例,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而只具有事實上的拘束力。盡管如此,由于各種原因,“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幾乎總是得到下級法院的遵循。類似地,州法院的判例也幾乎總是得到本州下級法院的遵循,并且也經常得到其他州的下級法院的遵循。而本州的其他法院或其他州的州法院至少也會參考這些判例。地區法院的判例幾乎總是得到本地區的基層法院的遵循”。14張騏等:《中國司法先例與案例指導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頁。由于判例所蘊含的重要價值,法律職業共同體對判例在實踐中的功能和作用達成了共識,因此實踐中法官對于判例的偏離或規避適用就不應當是隨意的。
這里應先予以澄清的是,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由于對所有法院都具有正式拘束力,因此即使其他法院認為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有誤仍無權隨意偏離之。對于其他法院的判例,比如聯邦法院的判例,如欲偏離則應履行報告義務。這一制度被規定在《德國法院組織法》以及其他程序法中。具體而言,包括這樣三種偏離情況:第一,在聯邦一級法院體系中,如果五個聯邦最高法院的某個法院想要偏離另一個最高法院的判決,則需將分歧提交至最高法院聯合大審判庭;第二,在聯邦最高法院內部,如果聯邦最高法院的某個審判庭想偏離另一個審判庭的判例,則需要將分歧提交至大審判庭;第三,如果一個州高等法院想要偏離另一個州高等法院或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則需要將案件提交至聯邦最高法院。15參見高尚:《論德國法中偏離判例的報告制度》,載《法律適用》2017年第2期。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并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都可以產生偏離判例的報告義務,有兩項條件特別值得重視或考慮:其一,發生偏離所涉及的問題必須是法律問題,對于事實問題所產生的分歧或爭議一般不會產生偏離報告義務;其二,僅就法律問題而言,一個判決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有時候是復數的,但并不是就其中每一個問題都可以產生偏離的報告義務,通常能夠產生偏離報告義務的僅僅是其中對判決而言具有根本重要性或決定性的難題。16參見陳興良主編:《中國案例指導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23—724頁。為對特定判例的偏離設定一項強制性的報告義務,目的是確保法院能夠尊重那些在審判實踐中所累積形成的“持續一致的見解”,促進法律的統一適用和實現類似案件類似審判。
除此之外,在相關主體漠視這一報告義務而任意背離判例時,法律也設立了一套救濟和監督機制。比如說,“如果聯邦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或者州高等法院在發生判決偏離的場合,違背了《德國法院組織法》的規定的報告義務,則可以針對該判決提起憲政抗告,原因在于此種條件下基本法所規定的當事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遭到了侵犯”。17同上注,第726頁。設立這樣一整套的程序,目的在于限制專斷的司法自由裁量權,維護法律體系的一致性和可預測性。如果容許法官任意背離已經存在的判例,或者說對于偏離判例作出一種不妥當的解釋或安排,那么法官將不會以“類規則推理的方式”(rule-like fashion)來解釋或適用判例,因此會犧牲掉作為合法性價值的實質法治,會喪失客觀性、確定性以及平等性等。同時允許任意偏離,會使整個法律體系變得效率低下,法官需要每一次都重新考慮、解釋、權衡案件的爭論點,即便是類似的案件也可能被以一種不類似的方式處理,這違背了遵循先例的基本要義,付出的成本會比較高,可能會產生更多的訴訟、需要更多的律師、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18See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 Summers eds., Interpreting Preced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7, pp.526, 520.德國獨具特色的判例偏離報告制度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發,就是要為偏離判例設立一套程序性規則。
至于這樣一套程序規則是什么,是不是一定要建構一套類似于德國的報告制度,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依據筆者的觀察,德國的判例偏離報告制度與德國復雜的法院體系、三審審級制以及違憲審查制度等聯系在一起,它的產生有著特定的司法傳統和法律背景。在我國,不宜采納一種類似于德國的判例偏離的報告制度。理由如下:
第一,我國指導性案例并非正式法源,不具有嚴格法律意義上的拘束力。其事實性拘束力源自于兩個層面:一個是形式層面的,它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經過特定程序加以遴選、討論和公布的,具有一定的外在權威形式;另一個是實質層面的,指導性案例本身判決觀點正確或提出了正確的實質性理由,而說服后案法官在審理類似案件時對自己加以參照。19參見張騏:《再論指導性案例效力的性質與保證》,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年第1期。對于指導性案例的背離,雖說不像對法律的背離那樣要求嚴格地加以限制,但這種背離行為也不應是隨意的。這體現為,法官在決定規避適用指導性案例時,應對自己的決定行為提供充分的理由加以論證。這種說理的義務或責任,所要服務的目的或起到的作用其實和德國偏離判例的報告制度是一致的,只不過后者有專門的法定程序加以保障和實施。
第二,德國設立專門的偏離報告制度,目的是為了確保三審法院內部的司法統一。根據《德國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審判庭提交至“聯合審判庭”或“大民事審判庭”的案件主要包括“基于觀點分歧的提交”與“基于原則性意義的提交”兩大類:前者主要針對具體的法律問題,并且產生強制性的提交義務;后者針對的主要是具有原則性意義的法律問題,并且審判庭可以自行斟酌是否將其進行提交,通常如果認為提交可以促進法律的發展或統一司法便會選擇提交。20參見盧佩:《司法如何統一——以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為實證分析對象》,載《當代法學》2014年第6期。這一套制度設立的目的,首先并不主要是為規范判例偏離行為本身,而是為了解決最高法院內部的意見分歧。21參見曹志勛:《論指導性案例的“參照”效力及其裁判技術》,載《比較法研究》2016年第6期。在我國,為了解決法院內部不同意見的做法有很多,典型的比如審委會集體討論、審判長聯席會議制度、個案請示與批復制度等。22參見孫海波:《疑難案件裁判的中國特點:經驗與實證》,載《東方法學》2017年第4期。故而,在這些制度之外并無專門再設立一種偏離判例報告制度的必要。
第三,這一制度的冗余性還在于,如果偏離判例的行為都要上報最高人民法院,這一方面隨著指導性案例數量的激增,會加大審理法官和最高法院的負擔;另一方面也會進一步加劇司法的行政化色彩。23參見曹志勛:《論指導性案例的“參照”效力及其裁判技術》,載《比較法研究》2016年第6期。對于法院如何將爭議問題或案件層層上報給最高人民法院,實踐中已經形成了獨特的做法,專門增設判例偏離報告制度也勢必會與三大訴訟法在某些規定方面出現不一致之處,增加協調成本。除此之外,在司法責任制改革的背景下,2018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進一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實施意見》,其中第9條規定:“各級人民法院應當在完善類案參考、裁判指引等工作機制基礎上,建立類案及關聯案件強制檢索機制,確保類案裁判標準統一、法律適用統一。存在法律適用爭議或者‘類案不同判’可能的案件,承辦法官應當制作關聯案件和類案檢索報告,并在合議庭評議或者專業法官會議討論時說明。”這一規定將類案的檢索與參照當作一種司法義務,也可以有力地對法官任意偏離判例的行為構成一種客觀的限制。
綜上,德國偏離判例的報告制度對思考指導性案例退出機制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是考慮到這一制度產生的制度和法律背景,以及其所承載的獨特目的和功能,在我國不宜直接建立一種類似的制度。
(二)規避適用指導性案例的實質理由
有學者認為司法裁判公正的品質,源自于法官如下的三個承諾:對正義目的的承諾、對司法職業主義的承諾以及對理性裁判方法的承諾。就最后一點而言,一種科學的裁判方法要求法官必須對其裁判結論提供理由加以證立。24See John W. McCormac, "Reason Comes Before Decision", Ohio State Law Journal, Vol. 55, No.1 (1994), pp.161-166.正如古老法諺所表達的,“無理由即無判決”,法官不僅應為其裁判提供理由,而且從邏輯上理由還應走在結論之前。如果法官在偏離決定作出之前,未提供理由或提供的理由不夠充分,那么這種對判例的規避行為就是一種不正當的規避。這里我們仍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為例,談談規避適用的主要理由可能有哪些,其中部分可能與清理或廢止指導性案例的情形存在交叉。
1.指導性案例已經過時
最高人民法院在遴選和編纂案例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案例本身的典型性與代表性,同時還要考慮判決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以及政治效果等。案例指導制度在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社會和諧方面能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尤其體現在指導性案例所具有的政策性功能方面,“指導性案例既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對于樣板案件裁決的認可,也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對樣板案件的選擇與‘修飾’,尤其是基于司法政策考量的選擇與‘修飾’。一個原生效判決之所以能夠作為樣板被選擇成為指導性案例,并且在成為指導性案例過程中之所以被如此非彼地加工,其中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傾向性”。25王紹喜:《指導性案例的政策引導功能》,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典型的如:指導性案例第4號“王志才故意殺人案”就旨在明確判處死緩并限制減刑的具體條件,從而貫徹少殺慎殺、寬嚴相濟的死刑政策;指導性案例第89號“‘北雁云依’訴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記案”,該案判決理由之一是公民任意創設姓名會增加社會管理成本、降低社會管理效率,可以說具有十分鮮明的政策性色彩。
普通法法系的學者在論及遵循先例原則時也提到,“遵循先例原則有一個很強的預設,即不應推翻先前的裁決,但是它并不禁止這樣的實踐。如果一個法院打算改變法律,它可以基于政策性的理由這么做”。26Kenneth J. Vandevelde, Thinking Like A Lawyer: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Reasoning, Second Edition, Westview Press,2011, p.131.伴隨著政策的改變,在過去特定時期特定政策背景下選編的指導性案例將會失去繼續存在的客觀依據,而變成一種過時的東西。比如說,假定在未來國家放開對公民選擇姓名權的限制,像“王者榮耀”“北雁云依”這種名字也很難說就真的在實質性意義上危害到公序良俗價值,那么伴隨著國家政策的變化,指導性案例第89號便會過時而退出歷史舞臺。對于過時的指導性案例,在尚未被相關機關清理之前,法官可以通過規避適用來偏離它。
2.內容存在實質性缺陷
在普通法系的司法實踐中,下級法院的法官不具有推翻上級法院判例的權力,因而在實踐中遇到內容上有缺陷的判例時,可以選擇區分(distinguishing)或規避適用。同樣的道理,當指導性案例在實質內容上存在缺陷時,法官沒有義務去重復或復制過去的不正義。大體說來,這些缺陷可能包括:
(1)指導性案例在事實認定方面,遺漏掉或錯誤地歸納了案件中的一個或多個關鍵性事實(material fact),也就意味著法官對于案件的基本認定存在嚴重失誤,這進一步導致法律適用出現錯誤。對于這種由事實認定錯誤導致后續法律適用出現錯誤的情形,顯然屬于內容方面的實質性缺陷。
(2)在法律適用以及裁判理由論證方面出現問題。單純的適用法律錯誤可能實踐中并不是非常常見,但是在判決證成方面可能經常會出現問題,而判決的證成與對法律的理解和適用往往又是聯系在一起的。仍以指導性案例第89號為例,為了證明“北雁云依”這個姓名不合法,法官機械地套用了相關立法解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99條第1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22條的解釋》)的規定,認為“北雁云依”這個姓名的選取不符合司法解釋所允許的兩種情況,即選取其他直系長輩血親的姓氏,或因由法定扶養人以外的人扶養而選取扶養人姓氏。而僅憑個人喜好愿望并創設姓氏不符合立法解釋第2款第3項(有不違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當理由。少數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從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的情形,因此不應獲得支持。仔細推敲這一論證顯得非常粗糙,法院似乎并未集中力量討論這種行為到底有沒有違背公序良俗,而只是簡單下了一個結論,并未提供實質性的充分理由。27這一點筆者受到了南京大學法學院陳坤教授的啟發,在此特別予以感謝。因此,單從這一點來看,這個判例在實質論證上便存在缺陷。
(3)指導性案例的內容或蘊含的裁判規則與法律相沖突。其中,可能會具體涉及這樣幾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指導性案例與基本的法律原則出現沖突;其二,指導性案例與新發布的法律、行政法規或司法解釋相互沖突。這兩種情況屬于兩種不同性質的法律淵源之間的沖突,指導性案例是一種非正式的、輔助性的法律淵源,而法律原則、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司法解釋均是正式性法律淵源,指導性案例的參照要求自然會被后一種更強的權威性理由所凌駕。或者借用一些學者的話說,原有指導性案例的裁判規則已經被制定法所直接吸收、推翻或替代了。28參見于同志:《論指導性案例的參照適用》,載《人民司法》2013年第7期。在以上這樣幾種情形下,由于指導性案例在內容上所出現的實質性缺陷,因而給法官規避適用它們創造了理由。
3.指導性案例之間相互沖突
針對同一個法律問題,在不同時期可能會形成數個不同的指導性案例,而這些案例之間在法律觀點上可能會出現不一致。法官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作出判斷,然后在它們之間擇一選擇適用。指導性案例出現沖突,一般的選擇規則是在后的指導性案例效力優先于在前的指導性案例,這是因為后來者往往代表最新的裁判觀點和立場,但也并非絕對如此。如果后來的指導性案例存在先天缺陷,比如存在前面所講的各種缺陷,那么法官仍然可以選擇在先的指導性案例進行參照裁判。因此,當數個指導性案例發生沖突時,法官究竟應選擇何者來參照,還是需要結合具體情況進行判斷。
4.實質不相似或不相干
最后一點理由,也構成了實踐中法官規避適用指導性案例的常見理由,即眼前待決案件與指導性案例在實質上并不相似或不相關。29參見何家弘:《外國司法判例制度》,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頁。待決案件與指導性案例具有實質相似性,才是參照指導性案例進行裁判的合理前提。在實踐中,可能會面臨這樣兩種情況:第一種,當事人主動提出了一個可能相關或相似的案件,法院經過審查、判斷,認為兩案之間在實質上并不相似,可以采取規避適用的決定;第二種,法院主動提出一個可能相似或相關的指導性案例,當事人一方提出充分的理由加以反駁,認為該指導性案例與待決案件之間并不實質相似,法院經過審查同意的,作出規避適用指導性案例的決定。普通法系中的“區分先例”的運作,也恰恰是以此為基礎和根據的。
(三)不當規避適用指導性案例的形式
自案例指導制度確立以來,中國法官在實踐中已經開始嘗試參照或援用指導案例。據相關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共發布的20批106例指導性案例中,已有78例在實踐中被參照,還有28例尚未被援引過,與2017年同期(60例)相比,被應用的指導性案例數量增加了18例。30參見《重磅!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司法應用報告(2018)》,載“北大法寶”微信公號,2019年4月1日。筆者曾將當下中國法官參照適用指導性案例的實踐格局歸納為六個方面的特征:使用的加速性、提出方式多樣化、斷裂性、不規范性、間接性以及當事人主導型。31參見孫海波:《論指導性案例使用的特點與難點》,載高鴻鈞主編:《中國比較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328頁。其中指導性案例使用的不規范性問題特別值得注意,這種不規范性又包括:對指導性案例的性質認識存在誤區、只關注指導性案例的形式而疏忽其實質內容、任意啟動對指導性案例的使用、漠視或參照指導性案例的隨意性等。32參見孫海波:《論指導性案例的使用與濫用——一種經驗主義視角的考察》,載舒國瀅主編:《法學方法論論叢》(第3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240頁。這里我們也來簡要討論一下,在規避使用指導性案例的實踐中存在哪些不規范的現象或形式。
1.對指導性案例效力性質的認識存在錯誤
指導性案例畢竟不同于一般的判決,它是經過特定的程序從判決中遴選出來的、具有較強代表性、能夠發揮一定指導性作用的案例。同時,不得不承認,指導性案例在效力性質上又不同于普通法系中的先例。因而,它更像是一種介于普通判決與作為正式法源之先例之間的一種過渡性存在,以至于某些學者稱其為“準法源”,“是中國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基于附屬的制度性權威并具有弱規范拘束力的裁判依據,因此既不同于判例在普通法系中的法源地位,也不同于判例在民法法系中被作為非法源來對待的境遇,而是走的中間道路”。33雷磊:《指導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載《中國法學》2015年第1期。由于指導性案例形成所具有的制度性權威和實質性權威,使法官在背離或規避指導性的時候不能是任意的。然而實踐中,我們注意到一些法官仍然以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成文法是唯一正式性法律淵源為由,拒絕在裁判實踐中參照或援用當事人一方所提供的指導性案例,這樣一種做法明顯就是誤解了指導性案例的效力性質。另外,筆者在基層法院調研中還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如果上級法院的指導性案例與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相沖突時,基層法院更傾向于參照上級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這主要是由于上訴審的存在,上級法院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自己的案件在上訴審中是否會被改判。
2.形式上規避而實質上隱性適用
指導性案例的適用,本質上屬于案例推理或判例推理,這依賴于一套復雜的歸納性思維,由于中國法官很少系統地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加上中國判決書格式的特定結構沒有為判例推理和說理創造出比較好的條件,使實踐中法官即便認為某個指導性案例具有可參考性仍選擇形式上規避,但暗中參照該指導性案例的裁判結果或裁判精神的方式。筆者將這種做法稱為“隱性適用”,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這種隱性適用,在形式上規避本該加以參照的指導性案例,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它僅僅將指導性案例當作達到某些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只注重案例的形式而不關心其內在的實質,因此本質上是一種工具化的案例適用觀;其次,它人為地遮蔽和扭曲了案例適用的過程和事實,指導性案例與待決案件事實之間的比對、相似性判斷、運用案例進行推理和說理等活動均被掩飾,使這種活動無法接受法律共同體的約束;最后,隱性適用還是一種司法虛飾的表現,違背了法官誠信裁判(judging in good faith)的基本要求。34參見孫海波:《指導性案例的隱性適用及其矯正》,載《環球法律評論》2018年第2期。與隱性適用這種做法相對的是,如果實踐中存在本該參照的指導性案例,尤其是當事人一方提出某個指導性案例要求法院加以參照時,法官負有強制性的回應義務,這一點在《實施細則》中有所規定,如果拒絕參照或援引該指導性案例,法官必須履行說理和論證的義務。
以上,便是規避適用指導案例實踐中的兩種較為常見的不規范做法。德國學者阿列克西(Robert Alexy)曾提出過判例適用的兩條規則:(1)當一項判例可以引證來支持或反對某一裁決時,則必須引證之;(2)誰想偏離某個判例,則承受論證負擔。35參見[德]阿列克西:《法律論證理論:作為法律證立理論的理性論辯理論》,舒國瀅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頁。歸結為一句話,無論法官是選擇參照還是拒絕援用判例,都必須對自己的決定提供理由加以論證。尤其是在規避適用指導性案例時,必須以明示的方式回應:究竟指導性案例出現了以上所討論的哪一種情形,不宜在判決中加以參照或援用。
四、初步的結論
卡多佐(Cardozo)曾提醒人們必須牢記:“法律的確定性并非追求的唯一價值,實現它可能會付出過高的代價。法律永遠靜止不動與永遠不斷變動一樣危險,妥協是法律成長原則中很重要的一條。”36Benjamin N. Cardozo, The Growth of the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4, p.17.指導性案例的退出機制,便是協調法律體系穩定性與靈活性的重要橋梁。離開了退出機制,案例指導制度將失去鮮活的生命力。同時,如果允許過時的或有缺陷的指導性案例繼續存在并發揮效力,勢必會在個案裁判中導致種種不正義。即便在判例作為正式法律淵源的普通法系國家,也不得強迫法官去遵循一個有問題或有實質性缺陷的判例,法官也沒有義務去復制過去的某種不正義。至此,對于指導性案例的退出機制問題,我們大致可以形成這樣幾點初步的結論:
第一,要正確對待指導案例的退出機制,它是案例指導綜合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這一制度的存在并不是要從根本上取消或摧毀案例指導制度,而是要通過不斷將過時的或有缺陷的指導性案例加以清理或廢止,或者賦予法官在案例參照實踐中靈活規避不相關或不相似案例的權力,為案例制度的健康發展和順利運行不斷注入新生的力量,也讓案例指導制度真正成為一個動態的、不斷向前循環和發展的制度。
第二,在我國不宜專門建立一種類似于德國的判例偏離報告的制度。在德國這一制度的重要價值在于統一最高法院內部的司法意見,而非規范偏離判例的行為本身。同時,該制度的產生是與德國復雜的法院體系、三審終審的復雜審級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在我國,已有類似制度能夠發揮判例偏離報告制度的功能。除此之外,如果允許實踐中法官在決定是否偏離或規避適用指導性案例時都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報告,這不僅會嚴重加劇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負擔、浪費司法資源,而且還會不可避免地造成與三大訴訟法之間在對接協調上的困難與沖突。
第三,法律適用者應負論證之義務,無論是專門主體對指導性案例進行清理或廢止,還是在裁判實踐中個體法官決定偏離或規避適用指導性案例,都必須對自己的決定提供充分的理由加以論證,其通常既包括形式層面(程序性)的,也包括實質層面的各種理由。否則在不加論證或說理的情況下,任意清理或規避適用指導性案例的做法,都將是恣意、專斷的,需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
第四,無論是對指導性案例的清理或廢止,還是在個案裁判中對指導性案例的規避適用,目的都是為了激活案例指導制度的生命力。到目前為止,由于指導性案例的數量仍相對有限,清理或廢止的活動還尚未真正實踐過。但是伴隨著人們“判例意識”的增強,相關主體在實踐中應用指導性案例的實踐活動會越來越成熟。如何正當地規避不相干或不合適的指導性案例,成為一個非常具有現實性的議題。這既有賴于整個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監督,也有賴于法官自身職業素養的提高,此外還依賴于一定的責任監督機制的確立,不當廢止或規避指導性案例的行為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