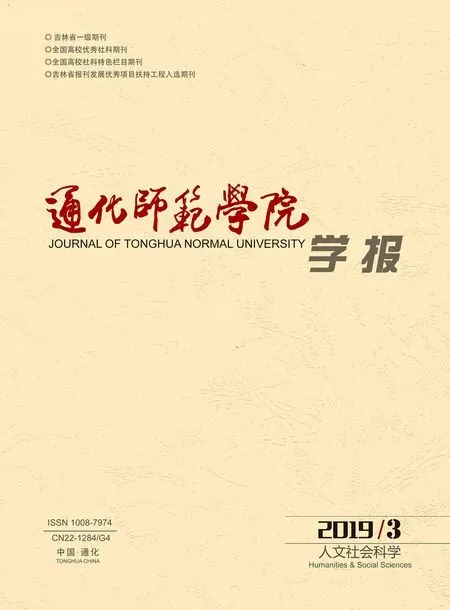運輸毒品罪的既未遂形態研究
吳沛澤
運輸毒品行為是指在國邊境范圍內,將毒品從一地移動到另一地的行為。[1]60而運輸毒品罪的犯罪形態歷來是學界爭議較多的問題,主要集中體現在運輸毒品罪的犯罪既遂、未遂的認定上。該問題之所以爭議較多,不僅因為在學界對該罪名所保護的法益、該罪名的行為性質有著不同的認識,還因為對運輸行為本身(手段、方式、距離)產生爭議。筆者擬對這些問題逐一予以分析。
一、運輸毒品罪的保護法益
刑法是一部“法益保護法”,因此,“無法益保護,就無刑法,換言之:倘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刑法的必要性。”[2]13在認定具體犯罪的犯罪形態上,法益也起著重要作用。脫離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去談犯罪的既未遂問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刑法規定毒品犯罪是為了實現對毒品的管制,即毒品犯罪的客體是國家對毒品的管制。[3]19但這種抽象的表述并沒有從實質上揭示毒品犯罪的本質是什么。國家不會為了管制毒品而去實施禁毒的措施。正如張明楷教授所說:“如果我們追問國家為什么要管制毒品,回答只能是為了保護公眾健康。”[4]1140由于毒品自身的一些特征,沾染上毒品的人極其容易形成癮癖,從而嚴重危害身體健康。而法益在根本上又是個體的權利,所以我們在討論運輸毒品罪的侵害法益上,也必須要從個體的利益或權利角度出發。[5]故筆者認為,運輸毒品罪的保護法益是不特定多數人的健康,即公眾健康。明確運輸毒品罪所保護的法益對認定犯罪既未遂問題上起著關鍵的作用。例如,被告人吳某受人委托將200克海洛因(后經鑒定200克白色粉末實際為普通面粉)從A地運往B地時,被公安機關查獲。按照傳統觀點吳某的行為應該構成運輸毒品的未遂,但吳某的行為(運輸普通面粉的行為)在客觀上無論如何都無法侵害或威脅到公眾的健康,因而吳某的行為不構成運輸毒品罪。一罪名的犯罪形態認定離不開對該罪法益的認識,將運輸毒品罪的保護法益確定為公眾的健康是至關重要的前提,這不僅為運輸毒品罪的既遂、未遂形態的區分提供了標準,也使刑法的處罰更具有合理性。
二、運輸毒品罪的犯罪既遂形態類型
我國刑法理論長時間認為運輸毒品罪是行為犯。而行為犯這個概念在我國刑法理論中本身就具有爭議。有的學者認為:“舉動犯是犯罪行為,行為都有其自身的發展過程,將其包含在行為犯中更為妥當……依此觀點,運輸毒品罪是行為犯,必須完成法定的運輸行為才能構成既遂。”[6]也有的學者直接指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為行為犯。[7]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犯罪是針對侵犯法益行為的類型,現實地由于加害行為而發生了“結果”的場合,則成立犯罪。我們應當認為結果是所有犯罪都必須具備的構成要件要素。“不存在沒有結果的犯罪。”[8]換句話說,刑法也不會單純處罰國民的行為。而運輸毒品罪的法益是不特定多數人的健康,所以刑法不僅處罰已經對公眾健康產生危害的行為,還會在某些特定場合對公眾健康進行提前的保護。所以筆者認為毒品犯罪是抽象危險犯。行為犯視角下的運輸毒品行為,往往一經實施了運輸毒品的行為即完成了犯罪既遂,但這并不符合刑法設立的初衷。但將毒品犯罪認定為抽象危險犯不會導致處罰范圍的擴大。因為行為人相應的行為,如果能反證確實不具有危害公眾健康的危險時,就不能認定為犯罪。這種分類不僅是與毒品犯罪保護法益一脈相承,還能從實質上掌握該罪的既未遂問題。
三、運輸毒品罪中“運輸”行為分析
《現代漢語辭海》關于“運輸”的釋義:“用交通工具把物資或人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9]但概括來講,刑法上的“運輸”和通常意義上的“運輸”是有明顯區別的。運輸毒品行為主要包含了兩個要素,即方式和距離。
(一)刑法意義上的“運輸”,通常被表述為“運載、輸送、攜帶、郵寄、交付托運”[10]15-18
從該表述可以看出,刑法上的運輸除了通常意義上的空運、水運、陸運等之外,還包括了通常不被認為“運輸”的方式(比如說郵寄運輸、將毒品放入體內進行運輸等)。故筆者認為在運輸毒品罪中運輸毒品的方式沒有任何的限制,即只要是能使毒品在空間上進行移動,都可以構成運輸毒品的方式。
(二)運輸毒品必須使毒品在空間上的位置發生變化
毒品的空間移動距離,是運輸毒品行為中的關鍵問題,需要進行進一步的說明。一般來說,運輸毒品應限制在我國的境內,這是為了與走私毒品罪相區分。有的學者指出:“運輸毒品是指采用攜帶、郵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在我國領域內轉移毒品”[11]1144。還有的學者指出:“運輸毒品應以國內領域為限,而不包括進出境”[12]292。筆者認為這些觀點是沒有爭議的。即運輸毒品行為必須要在我國國境內范圍內進行,換句話說,運輸毒品的距離存在一個上限,運輸行為不能越過國邊境線,否則構成走私毒品罪。但問題是運輸毒品的距離存不存在一個下限。比如行為人攜帶毒品欲乘坐汽車進行運輸活動,但在車站就被抓獲,從汽車運輸的角度來看,距離確實沒有任何的移動。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不需要考慮毒品實際的移動距離,而是應該結合該罪名的保護法益進行理解,哪怕交通工具尚未發生移動,也不影響運輸毒品罪(未遂)的成立。因為運輸毒品罪是抽象危險犯,行為人到達車站的那一刻就已經對公眾的健康產生了危險(威脅),所以沒有必要考慮毒品的實際移動距離。筆者認為關于運輸毒品行為的距離存在兩個限制,首先運輸行為不能越過國邊境線,換句話說,行為必須發生在我國的國境內。其次,該行為同樣存在一個下限。這里的下限是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精確的點。我們沒有辦法用一公里、十公里這樣的表述進行規定,這樣就會使不法分子鉆法律的空子,即只在規定的范圍內進行運輸,或者將長途運輸切割成小段運輸。所以下限的判斷必須要結合刑法的保護法益來確定。即只要運輸活動存在著一定的危險性、緊迫性,就應該承認行為人實施了運輸毒品的實行行為。
四、運輸毒品罪既遂、未遂問題的認定
(一)運輸毒品罪的既遂標準
關于運輸毒品罪的既遂標準在學界存在爭議。有的學者認為:“運輸毒品罪既然是行為犯,必須完成法定的運輸行為才能構成既遂。與之相對的是,行為人著手了毒品的運輸行為后,卻因為自己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即運輸行為未能完成,則構成未遂。[6]有的學者認為:“運輸毒品罪的既遂與否,應以毒品是否起運為準。毒品一經進入運輸途中,就構成本罪的既遂。”[13]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都值得商榷。首先,上述的觀點是將運輸毒品罪放置在行為犯的視角下進行展開的,而筆者贊同將運輸毒品罪劃分在抽象危險犯的犯罪分類里面。其次,第一種觀點認為運輸毒品罪的既遂標準是必須完成了法定的運輸行為。筆者認為這種并沒有明確指出法定運輸行為的行為模式類型,同時,刑法也不可能對所有運輸行為進行一個詳盡的描述與規定。這種觀點也并沒有從實質上指出運輸毒品罪的既遂標準的合理性。比如認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既遂標準是完成了法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一樣。這樣的表述沒有任何的實際意義。故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不妥當。第二種觀點認為運輸毒品罪的既遂標準應當采用起運說。即明知是毒品而予以運輸的,只要開始起運,不問距離的遠近,應以運輸毒品既遂論處。[13]因為到達目的地說會使運輸毒品的既遂范圍過窄,所以起運說相比于到達目的地說,確實更為合理。但該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筆者認為該觀點與罪刑均衡原則和法益保護原則相違背。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如下的現象:行為人為了運輸毒品而乘坐交通工具,但交通工具尚未處運行或出發,行為人就被司法機關查獲。按照起運說的既遂標準,行為人應該構成運輸毒品罪的既遂。但不管是危險犯還是實害犯,都應以是否發生了特定的法益侵害結果作為區分未遂與既遂的標志。進一步講,判斷危險犯既遂的標準只能是行為人所實行的危害行為是否達到了造成一定危害結果的客觀危險狀態。[14]88而該行為人在起運時所產生的客觀危險狀態相比于行為人達到目的地時所產生的危險狀態更低,對刑法所保護法益產生的威脅更小,所以將這種行為評價為運輸毒品罪的既遂并不合適。其次,如果刑法對兩種行為作出相同的評價,即對法益侵害程度不同的兩個行為作相同的處理,這種做法明顯違背了罪刑均衡的原則。還有學者指出:“將‘起運'作為運輸毒品罪的既遂的標志,依照字面解釋,是指貨物開始運出。時至今天,運輸方式日益多樣,不同的運輸方式具有不同的起運標準,而且就是一種運輸方式,依照不同的理解,何為起運,得出的結論也是不同的。”[15]所以筆者不認可將起運說作為運輸毒品罪的既遂標志。
筆者認為運輸毒品罪作為危害公眾健康的抽象危險犯,要從社會經驗上來判斷該罪名的既未遂標準。正如有的學者指出:“正因為毒品通過行為人的行為實現了空間位置的移動,在一般意義上是毒品處于流通狀態,更迫近于毒品使用者可獲取的狀態,產生了抽象的對于人民健康的危險。”[16]對于這種危險狀態就必須進行一個抽象的判斷。比如說,當行為人攜帶毒品乘坐火車,如果火車尚未行駛就被抓獲,此時我們認定行為人構成運輸毒品的未遂。但此時如果火車行駛了一段距離行為人才被抓獲,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下應當認定為運輸毒品的既遂。因為火車的運行使火車形成了一個內部的、封閉的空間,且這種封閉狀態是很難被外界打破的。行為人乘坐行駛中的交通工具有著極高的可能性把毒品順利送至目的地。進一步講,如果交通工具一旦把行為人送至目的后,毒品的流通就很難被阻斷。所以此時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我們可以認為行為人的此時行為已經對公眾的健康產生了抽象的危險。這種觀點既與運輸毒品罪的犯罪本質相符,同時也可以合理區分該罪名的既遂與未遂。只要行為人使毒品進入了運輸的狀態,我們就可以認為該行為在客觀上造成了一種危險的狀態。在通過郵寄運輸毒品的場合中,筆者認為也需要通過相同的方法進行認定。正如有的學者指出:“行為人以郵寄方式運輸毒品時,在郵件包裝過程中被查獲的,屬于未遂;如果已將裝有毒品的郵件交付給郵局,則為既遂。”[11]1157
(二)運輸毒品罪中共犯的既遂、未遂的認定
毒品犯罪的犯罪主體日益復雜,常常呈現出多人分工、配合作案的特點。在司法實踐當中運輸毒品罪以共同犯罪形態出現的情形也屢見不鮮。在共同正犯當中(即甲與乙都實施了運輸行為)應該如何認定既遂與未遂。筆者認為“整體既遂說”就可以合理解決這個問題。整體既遂說認為:“在共同者開始了實行行為,但是客觀上沒有造成結果的發生。我們可以承認結果犯的共同正犯的未遂。在個別地考察時,即使共同者中的一部分人沒有使結果發生,但是由于他人的行為使結果發生時,共同正犯就成立既遂。”[17]換句話說,在運輸毒品罪的共同正犯中一人既遂即全體既遂。例如,甲和乙約定將一包毒品分成兩小包,由甲和乙各自攜帶一包從A地運往B地。結果甲剛到車站就被民警抓獲,而乙按約定到達B地。按照整體既遂說進行認定,甲和乙成立運輸毒品罪的既遂。其中既遂的毒品數量為乙負責運輸部分的毒品數量。
在教唆、幫助下實施了運輸毒品行為的場合,主要有共犯獨立說、共犯從屬說與二重性說等不同主張。其中共犯獨立說認為狹義共犯的成立不要求存在正犯者的實行行為。這種觀點具有明顯的缺陷。而支持二重性說的學者則指出:“甲教唆、幫助乙后,乙未著手實施運輸行為,則乙不構成犯罪,甲構成運輸毒品罪(未遂);若甲教唆、幫助乙后,乙著手運輸且在運輸途中被抓獲,根據運抵目的地構成既遂的觀點,乙的實行行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沒有完成,則乙構成運輸毒品罪(未遂)。”[6]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首先二重性說認為甲教唆、幫助乙后,乙未著手實施運輸的行為,則乙不構成犯罪,而甲構成運輸毒品罪(未遂),這體現了共犯的獨立性。但是甲單純的教唆行為并未在客觀上造成任何刑法上所禁止的危害,故甲的行為不應該成立犯罪。從德日刑法關于共犯的處罰依據學說發展來看,修正引起說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正如有的學者指出;“與正犯一樣,共犯的處罰依據在于引起了法益侵害的危險性。”[18]這種觀點不僅與結果無價值相吻合,而且更好地貫徹了法益保護原則。刑法不會處罰行為人單純的教唆行為,而是因為教唆犯通過正犯實施實行行為,參與引起了法益侵害的結果。換句話說,在共同犯罪里,應該承認“沒有正犯的共犯”是不存在的。同時,共犯的獨立說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理論缺陷,而二重性說對于這種缺陷又無法克服。故筆者認為毒品的共同犯罪運輸,也必須要遵循共犯從屬說和因果共犯論,正如有的學者指出:“教唆犯的成立必須具備正犯著手實施犯罪的實行行為這一條件。”[19]229因此,甲教唆、幫助乙后,乙未著手實施運輸行為,則乙不構成犯罪,由于并不存在正犯實施實行行為,教唆者或幫助者甲當然不構成犯罪。
五、運輸毒品罪與非法持有毒品行為之區分
在司法實踐當中,出現了大量如下的情形:行為人運輸毒品被查獲后,向司法機關交代這些毒品是為了自己吸食而運輸。在無法查明其確切犯罪目的時,認定案件性質就成為了疑難的問題。司法機關在面對這種情況時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該案屬于刑事案件,應以非法運輸毒品罪立案追訴。另一種意見認為該行為為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20]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的補漏之罪。立法者設置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攜帶大量毒品參與走私、販賣、運輸毒品的行為人因證據不足而不能定罪處罰的情形。[21]120非法持有毒品行為人的目的大多都是供自己吸食的,所以此時攜帶毒品的數量的認定就格外重要。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對于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在認定犯罪事實和確定罪名上一定要慎重,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儲存毒品過程中被抓獲的,如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為的,一般不應定罪處罰,但查獲的毒品數量較大的,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毒品數量未超過刑法第348條規定數量最低標準的,不定罪處罰。”如果行為人攜帶的毒品未超過刑法第348款規定的最低標準,,對行為人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2條第1項予以處罰即可。但是行為人攜帶的毒品明顯超過刑法第348條規定的最低標準又該如何認定呢?筆者認為主要分兩種情況進行判斷。
(1)行為人持有毒品的數量超過刊法第348條規定的最低標準但尚未超過吸毒者的吸食量時,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2)行為人持有毒品的數量明顯超過吸毒者的吸食量時,構成運輸毒品罪。但此時必須要給被告人足夠的反證的空間。
這樣的認定既可以發揮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堵截性功能,以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不斷擴散的態勢,減輕公訴機關證明責任的功能[22],同時給被告人反證的機會也可以體現刑法本身的謙抑性,既堅持了依法辦案,又保證了不縱不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