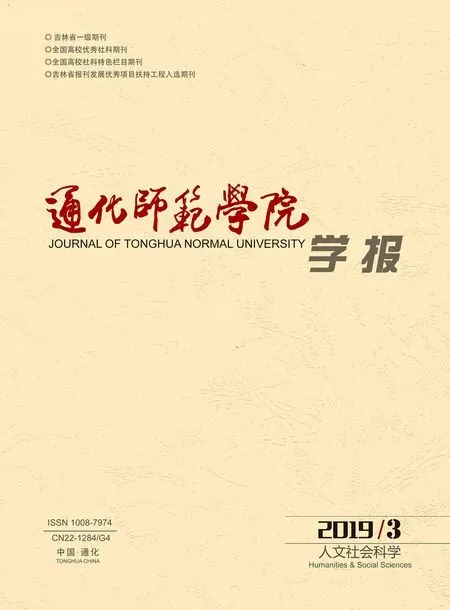《三國史記》人物類型探析
秦升陽,李春祥
《三國史記》[1]是朝鮮古籍中的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1145年(高麗仁宗23年),金富軾奉高麗仁宗之命,撰修《三國史記》。本書采錄了《尚書》《春秋》《左傳》《孟子》《史記》《漢書》《后漢書》《晉書》《南齊書》《梁書》《魏書》《南史》《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冊府元龜》《通典》《古今郡國志》《風俗通》《括地志》等中國古代典籍及一些朝鮮古籍中的相關史料。《三國史記》全書共50卷,分別為:本紀28卷(包括新羅本紀12卷、高句麗本紀10卷、百濟本紀6卷),年表3卷,志9卷,列傳10卷,敘述了新羅(前57—935年)、高句麗(前37年—668年)、百濟(前18年—660年)三個政權的歷史。作為紀傳體斷代史,《三國史記》的史學價值不言而喻,但從文學角度看,其本紀所記載56個新羅王、28個高句麗王、31個百濟王和列傳所記載的52個人物(不包括附傳人物),又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目前學界已有許多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問世[2]。金富軾所塑造的這些生動鮮活的不同人物形象,呈現出不同的人物類型特征。以人物類型理論為指導,探討《三國史記》的人物類型特征,對于深入探究《三國史記》的文學價值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人物類型理論概述
中國古代已經產生了人物類型理論的萌芽。如墨子的“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圣王”“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3]的理論,可視為中國古代人物類型理論的發端。[4]中國古代人物類型理論一直處在發展過程當中,如中國古代藝術理論中的“意境理論”對詩、詞的境界創造也作了不同類型的劃分。從魏晉志怪小說開始,中國敘事文學逐漸發展,此后的唐傳奇、宋代話本、元代雜劇、明清小說,人物類型化的特點越來越明顯,人物類型理論也得到相應的發展。如清代戲劇理論家李漁認為:“欲勸人為孝,則舉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紀,則不必盡有其事,凡屬孝親所應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5]這反映了我國古代小說家、戲劇家將人物類型理論當作塑造各類人物類型的重要創作原則,這一創作原則對于我國古代豐富的小說、戲劇等文學成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并產生了許多典型的人物類型,如《三國演義》中智慧的藝術典型諸葛亮、陰險奸詐的藝術典型曹操、忠義的藝術典型關云長便是突出的代表。
古希臘人物類型理論的產生當首推亞里士多德,他將悲劇中人物的類型分為“高尚的人”和“鄙劣的人”,認為“較為嚴肅的詩人摹仿高尚的行為或高尚的人的行為,而較為平庸粗俗之輩則摹仿那些鄙劣的人的行為”[6],這是西方最早的關于人物類型的闡述。也有學者認為亞里士多德“是人物類型理論的創始人,也是18世紀以后的理論家完善類型理論,強調類型中的個性特征的起源”[7],在典型理論中,亞里士多德認為典型就是類型,同時又主張類型的人物應該有自己獨特的性格。古羅馬的賀拉斯提出了人物性格創造的“定型論”,他將亞里士多德人物性格的類型定型化,賀拉斯的這一理論對西方文論界影響很大。17世紀法國的文學理論家布瓦洛贊同賀拉斯的人物理論觀點,他在《詩的藝術》里主張模仿古典,表現“自然人性”,認為“寫阿加門農應把他寫成驕橫自私,寫伊尼阿斯要顯出他敬畏神祉,寫每個人都要抱著他的本性不移。”[8]這種新古典主義類型論在18世紀受到一些理論家的批評。法國文學理論家狄德羅強調表現人物類型中的個性特征,對新古典主義類型論中只重視類型的普遍性、把類型定型化的傾向持否定態度。歌德受到狄德羅的影響,提出要在特殊中表現一般,通過創造一個顯出特征的生命力的整體來反映世界。黑格爾強調類型中的典型,人物典型被稱作“理想性格”或“理想人物”(ideal character),主要從理念出發來闡明典型。19世紀的別林斯基更多地從形象出發去闡明典型,強調人物典型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個性的統一,他認為“每一個典型對于讀者都是似曾相識的不相識者。”[9]巴爾扎克提出“典型是類型的樣本,因此,在這種或者那種典型和他的許許多多同時代人之間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點”,“為了塑造一個人物,往往必須掌握幾個相似的人物。”[10]他側重在人物類型中表現個別人物的個性。
到了20世紀,文學角度的人物類型理論以1927年英國小說家福斯特的“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觀點最具代表性,福斯特“將人物分成扁平的和圓形的兩種”,扁平人物是“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個句子描述殆盡”[11],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是咸亨酒店中“站著喝酒的唯一的人”,孔乙己便是一個典型的扁平人物;圓形人物“可以適合任何情節的要求”,如《包法利夫人》中的愛瑪,是一個集單純、美麗、聰明、輕浮、孱弱、大膽于一身的“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給人以新奇之感”“絕不刻板枯燥”“在字里行間流露出活潑的生命”[11]的圓形人物。福斯特可謂現代人物類型理論的奠基人,對這一理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中國學者對人物類型理論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如北京大學申丹教授提出了“功能性人物”和“心理性人物”的二分法,她認為“功能性”人物是“從屬于情節或行動的‘行動者'或‘行動素'”,“心理性”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實質的(逼真的)‘人'”[12],這種觀點已經注意到了人物在情節中的功能,是對福斯特人物類型理論的完善和補充。更有學者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將人物劃分為“功能性人物”和“審美性人物”[13]兩種類型。“功能性人物”是指在文本的敘述中起著一定調節或控制作用的人物,如《裝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布留金,他講出了別里科夫的故事,在故事情節中起到了調節敘事情節發展的功能。“心理性人物”是指在文本中的敘述中充分展示其心理活動,甚至潛意識本能的人物,如《墻上的斑點》中的“我”就是一個典型的“心理性人物”,一個墻上的斑點使他展開了一系列聯想,這些心理活動構成了故事的主線。“審美性人物”是指文本在敘述中突現其審美形態和審美價值的人物,包括描述人物外在行為的“扁平人物”“圓形人物”和描述人物心理活動的“心理性人物”。
上述人物類型理論是從文論角度所作的簡要敘述,這一理論不僅適用于研究純粹的文學作品,對于探討史學著作中的人物類型同樣適用,下面將借助人物類型理論,并在借鑒他人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文學的角度對《三國史記》本紀和列傳人物類型進行初步探索。
二、《三國史記》本紀人物類型分析
《三國史記》本紀記載了56個新羅王、28個高句麗王和31個百濟王,共計115個國王。這些國王是以本紀的形式從歷史的角度進行記載,但從國王的行事中又能體現出其文學上人物類型的某些特點,其中既有所謂的“扁平人物”“圓形人物”,同時也有描述人物心理活動的“心理性人物”。
這些國王中大多數屬于“可以用一個句子描述殆盡”的“扁平人物”類型,如新羅始祖赫居世“娶妃以德”,倭人欲犯邊,因“聞始祖有神德,乃還;樂浪人將兵來侵,見邊人夜戶不扃,露積被野,相謂曰:‘此方民不相盜,可謂有道之國。吾儕潛師而襲之,無異于盜,得不愧乎?'乃引還。”另外赫居世不趁他國有喪征之,曰:“幸人之災,不仁也。”乃遣使吊慰;新羅南解次次雄,“民饑,發倉廩救之。”由于國君有德,上天都會相助,“倭人來侵,流星夜墜敵營”,嚇退敵兵;新羅儒理尼師今“存問,鰥寡、孤獨、老病不能自活者,給養之。于是,鄰國百姓聞而來者,眾矣。”高句麗東川王,“王性寬仁,王后欲試王心,候王出游,使人截王路馬鬣。王還曰:‘馬無鬣可憐。'又令侍者進食時,陽覆羹于王衣,亦不怒。”新羅味鄒尼師今“七年(268),春夏不雨。會群臣於南堂,親問政刑得失。又遣使五人,巡問百姓苦患……十五年(276),春二月,臣寮請改作宮室,上重勞人,不從。”新羅婆娑尼師今“省用而愛民,國人嘉之。”從這些國王的行事中可以看出,他們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有德之君。因為有德,不僅百姓受益,甚至上天也暗中相助,保護國家不被敵人侵犯。
除了有德之君外,還有一些國君也屬于這“扁平”類型的人物,如新羅脫解尼師“望楊山下瓠公宅,以為吉地,設詭計,以取而居之。”是一個聰明而狡詐的國君;新羅訖解尼師今“狀貌俊異,心膽明敏,為事異於常流。”新羅智證麻立干“三年(502)春三月,下令禁殉葬。前國王薨,則殉以男女各五人,至是禁焉。”這是一個尊重生命的開明的國王。還有心地善良的新羅真興王,他信奉佛教,在位期間“許人出家為僧尼奉佛。”尤其是“三十七年(576)春,始奉源花。初,君臣病無以知人,欲使類聚群游,以觀其行義,然后舉而用之。遂簡美女二人,一曰南毛,一曰俊貞。聚徒三百余人,二女爭娟相妒。俊貞引南毛於私第,強勸酒至醉,曳而投河水以殺之。俊貞伏誅,徒人失和罷散。其后,更取美貌男子妝飾之,名花郎以奉之。”真興王的這一從善良角度進行的改革,將原本充滿仇恨和殺戮“源花”組織變成了為新羅培養賢能之人并略帶浪漫色彩的花郎徒組織。而高句麗烽上王則是一個不聽勸諫的剛愎自用,最后落得個自經的下場的國王,“九年(300)八月,王發國內男女年十五已上,修理宮室,民乏于食,困于役,因之以流亡。倉助利諫曰:‘天災薦至,年谷不登,黎民失所,壯者流離四方,老幼轉乎溝壑……大王曾是不思,驅饑餓之人,困木石之役,甚乖為民父母之意。'王慍曰:‘君者,百姓之所瞻望也。宮室不壯麗,無以示威重。今國相蓋欲謗寡人,以干百姓之譽也。'助利曰:‘君不恤民,非仁也;臣不諫君,非忠也。臣既承乏國相,不敢不言,豈敢干譽乎!'王笑曰:‘國相欲為百姓死耶?冀無復言。'助利知王之不悛,且畏及害,退與群臣同謀廢之,迎乙弗為王。王知不免,自經。”高句麗慕本王是一個殘暴的國王,“為人暴戾不仁,不恤國事,百姓怨之……王日增暴虐,居常坐人,臥則枕人。人或動搖殺無赦。臣有諫者,彎弓射之。”最后的下場是被大臣杜魯刺殺。
新羅圣德王性格寬和仁厚,是一個一心與唐結好甘愿做唐屬國的國王類型,他在位36年,共計39次遣使入唐賀正或獻方物,與唐保持良好的附屬國關系。除了敬獻方物外,其給唐帝的上表也極為謙恭:“臣鄉居海曲,地處遐陬,元無泉客之珍,本乏寶人之貨。敢將方產之物,塵瀆天官,駑蹇之才,滓穢龍廄。竊方燕豕,敢類楚雞。深覺靦顏,彌增戰汗。”頻繁的賀正、獻方物、上表令唐玄宗非常感動。玄宗降書曰:“卿每承正朔,朝貢闕庭,言念所懷,深可嘉尚。又得所進雜物等。并逾越滄波,跋涉草莽,物既精麗,深表卿心。今賜卿錦袍、金帶及彩素共二千匹,以答誠獻,至宜領也。”圣德王的這種執著單一的性格也影響了后來的新羅國王,此后的新羅景德王、恵恭王都成為一心與唐結好朝貢的新羅王。
相當于“圓形人物”的國王類型要少一些,但有三位頗具特點,一是新羅照知麻立干,二是新羅文武王,三是高句麗琉璃明王。新羅照知麻立干“幼有孝行,謙恭自守,人咸服之。”但在“王二十二年(500)秋九月,王幸捺巳郡。郡人波路有女子,名曰碧花,年十六歲,真國色也。其父衣之以錦繡,置以色絹獻王。王以為饋食,開見之,然幼女,而不納。及還宮,思念不已,再三微行,往其家幸之。路經古郡,宿於老嫗之家,因問曰:‘今之人以國王為何如主乎?'嫗對曰:‘眾以為圣人,妾獨疑之。何者?竊聞王幸捺巳之女,屢微服而來。夫龍為魚服,為漁者所制。今王以萬乘之位,不自慎重,此而為圣,孰非圣乎?'王聞之大慚,則潛逆其女,置於別室,至生一子。”照知麻立干當王之前“謙恭自守”,頗有美名,但當王后,在美色的誘惑與圣王的美名之間,他選擇了前者,放棄了擁有已久的圣王美名。這種品行的變化表現了照知麻立干具有一點“圓形人物”的特色。新羅文武王是一個性格怪癖的王,他是《三國史記》所記115個國王中唯一一個有愛戀男童之癖的國王,“八年(668)冬十月二十五日,王還國,次褥突驛,國原仕臣龍長大阿餐私設筵,饗王及諸侍從。及樂作,奈麻緊周子能晏,年十五歲,呈加耶之舞。”文武王見能晏長得“容儀端麗”,便將能晏召到自己近前,以手撫摸能晏之背,然后“以金盞勸酒,賜幣帛頗厚。”在對大唐的態度上,則陽奉陰違,表面恭敬,實則我行我素。“九年(669)春正月,唐僧法安來,傳天子命,求磁石。夏五月,遣祗珍山級餐等入唐,獻磁石二箱。又遣欽純角干、良圖波珍餐入唐謝罪。”一方面文武王對唐有求必應,另一方面則暗中“擅取百濟土地遺民”,同時封高句麗大臣淵靜土之子安勝為高句麗王,其冊曰:“謹遣使一吉餐金須彌山等,就披策、命公為高句麗王。公宜撫集遺民,紹興舊緒,永為鄰國,事同昆弟,敬哉敬哉。兼送粳米二千石,甲具馬一匹,綾五匹,絹細布各十匹,綿十五稱,王其領之。”結果唐高宗大怒,“詔削王官爵。”當時唐滅高句麗勢頭正盛,為避免與高句麗有同樣的下場,文武王對唐表面上十分謙卑,以麻痹唐高宗,暗中卻網羅高句麗余部,以壯大自己的勢力,與唐朝抗衡。
高句麗琉璃明王的“圓形人物”特點要比文武王顯著一些,他幼時頑皮,當王以后多情、殘忍、兇狠。幼年頑皮,“出游陌上彈雀,誤破汲水婦人瓦器。婦人罵曰:‘此兒無父,故頑如此。'”當王后,又很多情,“三年(前17)冬十月,王妃松氏薨。王更娶二女以繼室,一曰禾姬,鶻川人之女也;一曰雉姬,漢人之女也,二女爭寵不相和,雉姬慚恨亡歸。王聞之,策馬追之,雉姬怒不還。王嘗息樹下,見黃鳥飛集,乃感而歌曰:‘翩翩黃鳥,雌雄相依。念我之獨,誰其與歸?'”琉璃明王還殘忍、兇狠,“十九年(前1)秋八月,郊豕逸。王使托利、斯卑追之,至長屋澤中得之,以刀斷其腳筋。王聞之怒曰:‘祭天之牲,豈可傷也?'遂投二人坑中殺之。”同時對太子也痛下殺手,“王遣人謂(太子)解明曰:‘吾遷都,欲安民以固邦業。汝不我隨,而恃剛力,結怨于鄰國,為子之道,其若是乎?'乃賜劍使自裁。太子乃往礪津東原,以槍插地,走馬觸之而死,時年二十一歲。”如此殺害太子,令金富軾都慨然論曰:“今王始未嘗教之,及其惡成,疾之已甚,殺之而后已。可謂父不父,子不子矣。”
小說中的“心理性人物”可以充分展現其心理活動,像《墻上的斑點》中的“我”那樣以心理活動展開故事情節。《三國史記》中關于國王心理活動的描寫并不充分,但在具體行事過程中體現了其心理活動,可以看作是“心理性人物”。如高句麗山上王和新羅敬順王便是如此。山上王是一個借助王嫂于氏當上高句麗王的人,“初,故國川王之薨也,王后于氏秘不發喪,便往延優(故國川王之弟)之宅。延優起衣冠,迎門入座宴飲。王后曰:‘大王薨,無子,發歧作長當嗣,而謂妾有異心,暴慢無禮,是以見叔。'于是,延優加禮。”對于王嫂于氏的突然到來和故國川王的突然去世,山上王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他似乎看到了平日里心中仰慕的王嫂于氏和高高在上的王位離自己越來越近了,這種激動而復雜的心理活動通過下面的行動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宴飲過程中,延優“親自操刀割肉,誤傷其指”,于氏“將歸,謂延優曰:‘夜深恐有不虞,子其送我至宮。'延優從之”,并與“王后執手入宮。”延優取得王位以后00000,立于氏為后,但其心中是不甘心“不復更娶”的,于是借夜夢給自己“更娶”尋找借口。“七年(203)春三月,王以無子,禱于山川。是月十五夜,夢天謂曰:‘吾令汝少后生男勿憂。'王覺語群臣曰:‘夢天語我諄諄如此,而無少后奈何?'巴素對曰:‘天命不可測,王其待之。'”在“十二年(208)冬十一月,郊豕逸,掌者追之,至酒桶村,躑躅不能捉。有一女子,年二十許,色美而艷,笑而前執之,然后追者得之。王聞而異之,欲見其女。微行,夜至女家。使侍人說之,其家知王來,不敢拒。王入室,召其女,欲御之。女告曰:‘大王之命,不敢避。若幸而有子,愿不見遺。'王諾之。至丙夜,王起還宮。”這段記載說明山上王既顧及王后于氏又要暗中臨幸民女,這一舉動將山上王即位前后在這件事上的心理活動充分展現出來。
新羅敬順王是一個明大義的亡國之君。當新羅行將滅亡,國土日蹙,甄萱與高麗大軍不斷吞滅新羅國土的時候,敬順王感到亡國的腳步迫近,在國家之名、王位與人民的生命安危之間,敬順王經過多次的心理斗爭,最后做出了痛苦的抉擇,歸順王建。931年,敬順王與王建見面,商討新羅歸順之事,敬順王置宴于臨海殿,“酒酣王言曰:‘吾以不天,寢致禍亂。甄萱恣行不義,喪我國家,何痛如之。'因泫然涕泣。左右無不嗚咽,太祖亦流涕慰藉。”935年,敬順王“乃與群下謀舉土降太祖。群臣之議,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王子曰:‘國之存亡,必有天命,只合與忠臣義士,收合民心自固,力盡而后已。豈宜以一千年社稷,一旦輕以與人。'王曰:‘孤危若此,勢不能全。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至使無辜之民,肝腦涂地,吾所不能忍也。'乃使侍郎金封休赍書,請降于太祖。王子哭泣辭王,徑歸皆骨山。倚巖為屋,麻衣草食,以終其身。”在歸順那天,“王率百寮,發自王都,歸于太祖。香車、寶馬連亙三十余里,道路填咽,觀者如堵。”這里雖然沒有描寫敬順王心理怎么想的,但通過這些描寫,生動地再現了沿途新羅百姓親視昨日的國王,如今落得亡國之君的境地,金富軾以“道路填咽,觀者如堵”反襯了此時新羅王悲涼的心情。
三、《三國史記》列傳人物類型分析
《三國史記》中共記載了52個列傳人物(不包括附傳人物),其中有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的政治、軍事、平民人物,既有在戰場上為國效死的英雄,也有為了保全自己把妻子獻給國王的懦夫,還有弒君、反叛的國之逆臣,許多人物的描寫十分精彩,人物類型特點突出,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這52個列傳人物中屬于“扁平人物”類型的最多,這類人物中,在戰場上勇于效死的英雄比較多,他們都是秉承為國獻身的宗旨,壯烈殉國,如新羅將領奚論,是一個秉承父志為國效死的勇士。“至建福三十五年(618),奚論為金山幢主,與漢山州都督邊品興師,襲岑城,取之。百濟聞之,舉兵來,奚論等逆之。兵既相交,奚論謂諸將曰:‘昔吾父殞身于此,我今亦與百濟人戰于此,是我死日也。'遂以短兵赴敵,殺數人而死。”新羅僧徒驟徒,在百濟來攻的時候,脫去僧衣,“乃詣兵部,請屬三千幢,遂隨軍赴敵場。及旗鼓相當,持槍劍突陣力斗,殺賊數人而死。”新羅將軍品日之子官昌,“儀表都雅,少而為花郎,善與人交。唐顯慶五年(660),王出師與唐將軍侵百濟,以官昌為副將。至黃山之野,兩兵相對。父品日謂曰:‘爾雖幼年有志氣,今日是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其可無勇乎!'官昌曰:‘唯。'即上馬橫槍,直搗敵陣。馳殺數人,而彼眾我寡,為賊所虜。生致百濟元帥階伯前。階伯俾脫胄,愛其少且勇,不忍加害,乃嘆曰:‘新羅多奇士,少年尚如此,況壯士乎!'乃許生還,官昌曰:‘向吾入賊中,不能斬將搴旗,深所恨也。再入必能成功。'以手掬井水,飲訖,再突賊陣疾斗。階伯擒斬首,系馬鞍送之。品日執其首,袖拭血曰:‘吾兒面目如生,能死于王事,無所悔矣。'”新羅將領金歆運,“永徽六年(655),太宗大王憤百濟與高句麗梗邊,謀伐之。及出師,以歆運為郎幢大監。”戰斗中,“歆運拔劍揮之。與賊斗,殺數人而死。”新羅將領竹竹,善德王“王十一年(642),百濟將軍允忠領兵來攻其城。竹竹收殘卒,閉城門自拒。舍知龍石謂竹竹曰:‘今兵勢如此,必不得全,不若生降以圖后效。'答曰:‘君言當矣。而吾父名我以竹竹者,使我歲寒不凋,可折而不可屈。豈可畏死而生降乎!'遂力戰至城陷,與龍石同死。”新羅將領匹夫,為七重城下縣令。高句麗發兵來圍七重城。“匹夫守且戰二十余日,賊將見我士卒盡誠斗不內顧,謂不可猝拔,便欲引還。逆臣大奈麻比歃密遣人告賊以城內食盡力窮,若攻之必降。賊遂復戰。匹夫知之,拔劍斬比歃首,投之城外。乃告軍士曰:‘忠臣義士,死且不屈。勉哉努力,城之存亡,在此一戰。'乃奮拳一呼,病者皆起,爭先登。而士氣疲乏,死傷過半。賊乘風縱火,攻城突入。匹夫與上干本宿、謀支、美齊等向賊對射,飛矢如雨支體穿破,血流至踵,乃仆而死。”百濟將軍階伯,“唐顯慶五年(660)庚申,高宗以蘇定方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師濟海,與新羅伐百濟。階伯簡死士五千人拒之曰:‘以一國之人,當唐羅之大兵,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吾妻孥沒為奴婢,與其生辱,不如死快。'遂盡殺之。至黃山之野,設三營,遇新羅兵,將戰,誓眾曰:‘昔句踐以五千人破吳七十萬眾,今之日宜各奮勵決勝,以報國恩。'遂鏖戰,無不以一當千,羅兵乃卻。如是進退至四合,力屈以死。”這些戰死沙場的英雄,其壯烈的事跡無不令人動容。
《三國史記》中文字最多的人物列傳是金庾信傳,他是一位重要的新羅將領,也屬于“扁平人物”類型,金庾信“年十七歲,見高句麗、百濟、靺鞨侵軼國疆,”就“慷慨有平寇賊之志。”成為將領后,作戰不懼生死,在“建福四十六年(629),率兵攻高句麗娘臂城……庾信……乃跨馬拔劍,跳坑出入賊陣,斬將軍,提其首而來。”表現了作戰不懼生死的性格。為了國家的戰事,三過家門而不入,645年,“信從外地歸家,但因戰事緊急,三過家門而不入。”又善于用計謀,在唐蘇定方率領20萬大軍前來滅百濟的時候,信為押梁州軍主,為了試探民心是否可用,信“若無意于軍事,飲酒作樂,屢經旬月。州人以庾信為庸將,譏謗之曰:‘眾人安居日久,力有余,可以一戰,而將軍慵惰,如之何!‘庾信聞之,知民可用,告大王曰:‘今觀民心,可以有事。請伐百濟以報大梁之役。'”金富軾在《三國史記》中將金庾信塑造成一個一心為國、善于計謀、作戰勇敢的正面人物形象。
此外,“扁平人物”類型的人物還有許多,如勇敢而有智謀,臨危不亂,集勇敢、智慧、富有軍事才能于一身的英雄人物形象高句麗大臣乙支文德;言而有信、知恩圖報的新羅將領居柒夫;少年便有報國之志、有一顆仁慈之心又極重友情的新羅將領斯多含;一心為國、苦心勸諫的新羅良臣金后稷;類似于荊軻的高句麗英雄人物紐由;天資溫良,以孝順為時所稱熊川州板積鄉人向德、菁州人圣覺、韓歧部百姓連權女子孝女知恩;自知必死而不避之,“死非其所,可謂輕泰山于鴻毛者也”的近乎呆板愚蠢的沙梁宮舍人劍君等等,都是人物性格單一執著,并極具自己的特點的類型。
《三國史記》列傳中屬于“圓形人物”的類型人物主要有三個:弓裔、甄萱、丕寧子。新羅景文王膺廉之子弓裔,后高句麗的建立者,少年時孝順、懂事,因為“生而有齒,且光焰異常,恐將來不利于國家……王敕中使抵其家殺之,使者取于襁褓中,投之樓下。乳婢竊捧之,誤以手觸眇其一目,抱而逃竄,劬勞養育。年十余歲,游戲不止。其婢告之曰:‘子之生也,見棄于國。予不忍,竊養以至今日。而子之狂如此,必為人所知。則予與子俱不免。為之奈何?'弓裔泣曰:‘若然,則吾逝矣。無為母憂。'便去世達寺……祝發為僧,自號善宗。”但當他稱王后,卻變成一個窮奢極欲、殘忍的人,“善宗自稱彌勒佛,頭戴金幘,身被方袍,又自述經二十余卷,其言妖妄,皆不經之事。時或正坐講說,僧釋聰謂曰:‘皆邪說怪談,不可以訓。'善宗聞之怒,鐵椎打殺之。”后來甚至將夫人康氏殘害致死。“貞明元年(915),夫人康氏以王多行非法,正色諫之。王惡之曰:‘汝與他人奸,何耶?'康氏曰:‘安有此事?'王曰:‘我以神通觀之。'以烈火熱鐵杵,撞其陰,殺之,及其兩兒。爾后多疑急怒,諸寮佐將吏,下至平民,無辜受戮者,頻頻有之。斧壤,鐵圓之人,不勝其毒焉。”
后百濟的建立者甄萱,年輕時“體貌雄奇,志氣倜儻不凡”“喜得人心”,但對戰敗的新羅國王卻殘忍加害,暴露他性格中陰暗殘忍的一面,天成二年(927)秋九月,“萱猝入新羅王都。時王與夫人嬪御出游鮑石亭,置酒娛樂。賊至,狼狽不知所為,與夫人歸城南離宮。諸侍從臣寮及宮女伶官皆陷沒于亂兵。萱縱兵大掠,使人捉王,至前戕之。便入居宮中,強引夫人亂之。”
丕寧子是一位新羅勇士,最后也英勇戰死疆場,與其他勇士不同的是,丕寧子既有為國而死之心,又有為家庭考慮的一點私心,表現了一個平常人的平凡思維,真德王元年(654),百濟以大兵來攻茂山等城,丕寧子隨金庾信率軍迎敵,出戰前,丕寧子“謂奴合節曰:‘吾今日上為國家,下為知己死之。吾子舉真雖幼年,有壯志,必欲與之俱死,若父子并命,則家人其將疇依?汝其與舉真好收吾骸骨歸,以慰母心。'言畢,即鞭馬橫槊,突賊陣,格殺數人而死。舉真望之欲去,合節請曰:‘大人有言,令合節與阿郎還家,安慰夫人。今子負父命,棄母慈,可謂孝乎!'執馬轡不放。舉真曰:‘見父死而茍存,豈所謂孝子乎!'即以劍擊折合節臂,奔入敵中戰死。合節曰:‘私天崩矣,不死何為!'亦交鋒而死。”一幕何其悲壯的父、子、仆三勇士慨然赴死的英雄畫面,表現了作為一個有著妻子兒女的平凡人的丕寧子,在殘酷的戰爭面前,既要為國而死,又在這生死關頭流露出掛念妻兒的令人不禁淚落的感人親情。
《三國史記》列傳中屬于“心理性人物”的主要有蓋蘇文和都彌。蓋蘇文是高句麗大臣,他“自云生水中以惑眾。”儀表雄偉,意氣豪逸,但同時又善于偽裝、兇狠和殘暴。“其父東部或云西部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而國人以性忍暴惡之,不得立。”在這種情況下,“蘇文頓首謝眾,請攝職,如有不可,雖廢無悔。”眾臣被蓋蘇文的虛偽所欺騙,“眾哀之,遂許嗣位。”但后來眾臣認為蓋蘇文兇殘不道,“諸大人與王密議欲誅,事泄。”結果“蘇文悉集部兵,若將校閱者,并盛陳酒饌于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余人。馳入宮,弒王,斷為數段,棄之溝中。立王弟之子臧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唐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職也。”此后蓋蘇文徹底撕去了自己“意氣豪逸”的偽裝,“于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甚有威嚴,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當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出行必布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坑谷。國人甚苦之。”
都彌是一個百濟蓋婁王時的編戶小民,“其妻美麗,亦有節行,為時人所稱。”荒淫的蓋婁王聞聽之后,召都彌與語曰:“凡婦人之德,雖以貞潔為先,若在幽昏無人之處,誘之以巧言,則能不動心者,鮮矣乎!”都彌“對曰:‘人之情不可測也。而若臣之妻者,雖死無貳者也。'王欲試之,留都彌以事。”都彌娶了一個美麗的妻子,而且遠近聞名,蓋婁王問他這些話,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面對這種情況,都彌進行著復雜的思想斗爭,一面是蓋婁王的淫威,一面是美麗的妻子,一面是自己的一己私利,思考的結果是面對強大的國王,都彌將自己的妻子扔到了一邊,去迎合蓋婁王的心意,將自己的妻子拿來比喻,主動給蓋婁王一個可乘之機,將美麗的妻子奉獻給國王。在危險到來之際,都彌可恥地選擇了屈服。也許都彌想以此保全自身,因為他知道違背君意的后果,希望以此保全自己,把全部的危險和恥辱無情地留給妻子一個人獨自面對和承擔,反映了都彌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人,將美麗的妻子當作換取自己安全的籌碼。結果是都彌的妻子以智慧和勇敢獨自應對蓋婁王的淫威和脅迫,最終得以全身而逃,蓋婁王終于未能得逞,都彌自己也被蓋婁王矐去雙眸,未能保全自己。妻子后來在泉城島上遇到都彌,不僅沒有因都彌雙目失明而拋棄他,還“掘草根以吃,遂與同舟,至高句麗山之下。麗人哀之,丐以衣食。遂茍活,終于羈旅。”和美麗、智慧、勇敢、善良的妻子相比,都彌顯得那么丑陋、愚蠢、自私和猥瑣,這顯著的對比雖然通過都彌與蓋婁王的對話表現出來,但這種表現卻是都彌復雜心理活動帶來的結果。而金富軾卻評價都彌:“雖編戶小民,而頗知義理。”不知金富軾所說的這個“義理”是什么“義理”,難道是將自己的妻子無償獻給國王就是“知義理”?真是令人費解。
四、結語
綜上所述,以人物類型的相關理論研究《三國史記》中的人物類型,雖然不免有生搬硬套和以偏概全之嫌,同時《三國史記》中所謂的“扁平人物”“圓形人物”“心理性人物”的人物類型特征亦不像純粹的文學作品那樣鮮明和豐滿,至于像“功能性人物”和“審美性人物”這種更為復雜的文學人物類型在《三國史記》中更是難以找到,盡管如此,如上文所述,許多《三國史記》人物類型還是頗具特色的,如丕寧子的平民性格本色、都彌妻子的堅貞勇敢的性格、蓋婁王的好色性格等等,都是很有人物類型特點的。性格決定類型,每一種人物類型都有自己的性格特點,許多《三國史記》本紀、列傳中的人物基本能達到黑格爾所說的人物“要有一個豐富充實的心胸,而這心胸中要有一種本身得到定性的有關本質的情致,完全滲透到整個內心世界”[14]這一性格特征。《三國史記》中大多數本紀和列傳的字數都比較少,而這比較少的文字又能體現出多種人物的類型特征,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人物本身具有各自的特點,另一方面也和金富軾較高的文學修養密切相關。金富軾在《進三國史記表》中說道:“是以君后之善惡,臣子之忠邪,邦業之安危,人民之理亂,皆不得發露,以垂勸戒。宜得三長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貽之萬世,炳若日星。”[15]史家“三長”是劉知幾提出的一個優秀史家所具備的三個條件,其中的“史才”便是指寫史的表達能力,金富軾以史家“三長”作為自己的最高追求,認真效法學習《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中國史書的著史方法,在本紀、列傳的記述中最大程度地展現了自己的史學和文學才能,為后人呈現了一部人物類型相對豐富的紀傳體史書《三國史記》,從而使《三國史記》在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的同時,也具備一定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