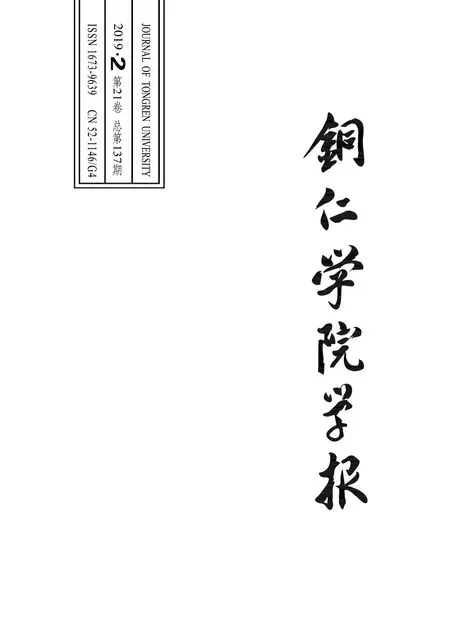元代閩學家熊禾詩學觀念與詩歌批評探析
邱光華
( 三明市閩學文化研究中心 三明學院文化傳播學院,福建 三明 365004 )
熊禾(1247-1312),字位辛、去非,號勿軒、退齋,福建建陽人,宋咸淳十年(1274)進士,宋元易代之后,隱居鄉里,著書立說、授徒講學,以尊崇、闡發和踐行朱子之學為職志,是元代福建著名的理學家。熊禾的傳世詩文作品,現存《熊勿軒先生文集》8卷,是今人研究其文學活動的主要文本依據。
學界現有的熊禾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生平履歷,以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傳記問題》一文所作的考辨最為詳切。[1]24-29二是學術思想,高令印、陳其芳《福建朱子學》一書所設“熊禾”一節,[2]以及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學術思想問題及其從祀孔廟議案》一文,[1]37-50先后進行了詳切的論述和闡發;此外,謝靜芳《熊禾〈易經訓解〉易學思想評析》一文對熊禾該著作的易學思想進行了探討[3]。三是著述情況,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學術思想問 題及其從祀孔廟議案》[1]50-58、王次澄《宋遺民福建大儒熊禾及其詩歌作品析論——兼述詩歌內容之區域文化觀照》[4]75-79二文均有專門的梳理和論述。相對而言,作為熊禾學術活動一項重要內容的詩學,較少被研究者關注。目前,僅有上文提及的王次澄先生的文章曾對熊禾詩歌創作的體式特征、題材內容及修辭特色進行論析。[4]79-110至于熊禾的詩學觀念與詩歌批評實踐,尚無專門的探討。有鑒于此,本文將經由對熊禾傳世詩文集中各類話語文本的解讀,發掘他所著力思考、論說的詩學理論問題,從中歸納蘊含于其間的詩學觀念,并對其詩歌批評的基本趨向、話語構造及言說重心略作論析。
一、詩歌之學的性質界定與詩歌“體用”觀
以義理之道作為“文”的根本內核,將“文”視為“道”的呈現載體與表現形態,宋代以來受理 學文化熏染沾溉的詩人文士,大抵都具備這一觀念性認識。如,宋末元初,尊崇朱子之學的著名詩論家方回,即認為“詩文亦道之一”(《跋汪君若楫詩文》)、“凡言語文字不畔于理者,皆以道為體”(《應子翱經傳蒙求序》)。甚至,在《吳云龍詩集序》一文中他還直截了當地將“詩歌之學”定位于儒學范疇之內,視之為“義理之學”的一個特殊分支。按照他的理解,詩歌之學原本就歸屬于義理之學,“《詩》以吟詠情性言義理”,樹立了垂范后昆的楷式,后世的詩歌創作也應以“義理”的闡揚或彰示作為依歸。[5]
熊禾有關詩學的思考與論說,從屬于他以理學為中心的學術建構活動,較為零散,但若能并置而觀,即可發現他對詩歌之學的性質界定與方回所持觀念并無不同。茲臚列三則材料:
文者道之用也,天地間惟道可以立國,惟文可以經世。儒者一身,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而可以徒文哉?[6]2266(《佩韋齋文集序》)
重惟文公之學,圣人全體大用之學也。……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詩》《書》……[7]30(卷3《考亭書院記》)
文之體,莫善于《詩》《書》。……若后世詩、詞一類,則自虞夏庚歌而下,備見于《三百篇》之風、雅、頌。[7]6(卷1《翰墨全書序》)
其一言“文”為“道”的發用,載“道”之“文”,可以經世;從整篇序文來看,此處所謂“文”指的是包括了“詩”在內的各類文體。其二言《詩》《書》為“圣人全體大用之學”的表述形式與經典文本,而其自身亦以“體用之學”為根柢,即“體”“用”兼備。其三言《詩》《書》確立了“文”之諸種體式的創作典范,后世的詩文應以此為本原和準的。合而言之,熊禾對詩歌之學的定位與要求,乃以他所崇奉并躬行的“有體有用之學”為觀念依憑,主要是圍繞“文”之本體與發用而展開的,他所認可和提倡的詩歌之學,由源及流,以經學理學闡揚的“道”為其本體,以立教經世為其功用追求。這其實是將詩歌之學作為儒者的一項學問素養,并從“體用之學”的維度對其進行考量。
相應地,熊禾對“體用之學”的論說,也就成為把握其詩歌體用觀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在熊禾的學術視域下,“湖學”“關學”“洛學”以及朱子之學,皆為“有體有用之學”。他曾在不同場合對此予以標舉:
湖學有明經治事齋,使人通一經,治一事,邊防水利之類,靡所不講。關、洛大儒,為往圣繼絕學,而孫吳、韓信兵法,亦未嘗不通,此有體有用之學也。[7]24(卷2《跋謝春堂詩義后》)
昔安定胡公,以經術德行教人,至農田、禮樂、刑政、兵防之類,欲使之人治一事,世稱為明體適用之學。[7]35(卷3《晉江縣學記》》)
重惟文公之學,圣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為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7]30(卷3《考亭書院記》)
胡瑗創立的“湖學”,明經與治事并重,既強調通乎經術以涵養德器,又要求達于事務以有用于世;張載創立的“關學”,以及二程為首的“洛學”,皆以接續和傳承孔、孟的心性義理之學為指歸,又因應于當世之需,重視實務;朱熹繼承并發展了“體用之學”的學術傳統,由一己之身心而及于國家天下,從德行涵養,到事業作為,其“體”臻于全備,其“用”涵容廣大,最為楷式。基于上述認識,熊禾在《送胡庭芳后序》一文中還將朱子締造的全體大用之學視為“集正學大成”,認為儒道正傳即在于此。[7]9再結合其《商有三仁兩義士傳》《敬齋銘箴跋》《史纂通要序》等文本的相關論說,可知他所謂“正學”,亦即“正心之學”,以正人心為首要之義,尤為強調以經學義理塑造人心;同時,也是經世致用之實學,學者躬行踐履,施之于政事或世務,以天下之治為價值向度。二者因果關聯、互為體用。其本在“立德”,其用在“立功”。
在熊禾的思想觀念里,作為載道之具與儒者立言之一端的詩歌,其“體”“用”自然要以“明體適 用”或“全體大用”之學為準的。就“體”而言,即《題童竹澗詩集序》所表明:詩歌是“蘊抱”的表達,是“情性”的抒發,是“肺肝”的流露。[7]7而其依歸乃是道心之所在、人心之所為主的“六經大義”(《跋謝春堂詩義后》),故要求合乎禮義、造于理境。就“用”而言,乃藉之陶冶性情、端正人心、移易風俗,乃至于介入國政民生。因此,如《佩韋齋文集序》所示,“不悖名教、有補倫紀”者,“起人悠然深長思”者,“閑雅沖澹中,發揚蹈厲之意存焉”者,熊禾都著意予以標舉。[6]2266-2267如《題童竹澗詩集序》所示,屈原、陶淵明、杜甫諸人之作,“痛憤憂切”于世事;童敬仲,矚目于“風教”“世情”,其詩蘊含“忠愛懇惻之情”,亦皆為他所推重。[7]7反之,文學史上的諸多詩人詩作,如他在《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所概括,或溺情于物,或高蹈虛曠,捐棄世事,無補于世道人心,已然背離了“正學”的要義和宗旨,故為他所指斥、否棄。[7]21
朱熹的再傳弟子,著名理學家真德秀嘗編選《文章正宗》,試圖藉以確立合乎其理學觀念的詩文典范。《文章正宗綱目》明確其選錄標準,即“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后取焉”;又述及“詩賦”一門主要是參照朱熹《答鞏仲至第四書》所言選詩方案進行輯纂,宣稱其宗旨是助益于“性情心術”。[8]熊禾對真德秀頗為推崇,他以朱子“私淑”之實而主張“全體大用之學”,主要的幾位近取之師當中即包括真氏。[1]41-42由此來看,真氏的經典著作及其撰述用意,熊禾應當不會陌生。如《謝鄉舉論學》一文即曾說過:“欲仿文忠公真西山先生《衍義》,只就學者分內事,輯為后傳,以見明體適用之學。”[7]68熊禾還編有《詩選正宗》一書,不傳于世,詳情無從查考;但據題名可推測此書的編纂或許受到《文章正宗》的啟發,大概也是致意于性情心術和世教民彝,以“明義理切世用”作為其選錄的指導思想。綜觀熊禾在《題童竹澗詩集序》《佩韋齋文集序》《跋謝春堂詩義后序》《謝貢舉啟》《翰墨全書序》等文所標舉的詩、賦、論、策、紀志、碑記諸體之作,知其所持批評標準與《文章正宗》一致,此可作為上述推論的一個旁證。
熊禾的存世詩歌作品,據《全元詩》的編錄,共73題,115首。其中,酬贈詩56首,內容主要涉及“時事與民生”“閩學道統與儒者職志”“官吏涵養與家國治理”;游覽題詠詩約28首,或托物言志,或寓理于景,往往蘊含著理學價值取向;儒學教化詩約15首,主要涉及儒學義理、地方教化、書院建設等內容;羈旅行役詩約9首,不僅抒發羈旅情懷,也表達儒者志趣,還敘寫世態民情。此外,感興、懷人詩4首,大多涉及儒者的出處情志;聯句詩1首,蘊含易代之感和興復之愿;擬體詠古詩1首,敘寫個體生存與生命情感;論詩詩1首,闡發基于理學本位的詩歌審美觀。由此可見,熊禾對詩歌之學的性質的界定,以及對詩歌的“體”與“用”的觀念性認識,不僅體現在他的詩歌閱讀與批評上,也體現在他的詩歌創作實踐上,可以說相當程度地塑造了其詩學活動的整體格局與風貌特征。
二、詩人之“心”與詩歌之“境”的關系建構
詩歌之學歸屬于儒者學問的范疇,要求詩歌的“體”與“用”皆應契合于“體用之學”的要義和宗旨。作為詩歌創作主體的詩人,相應地也應具備經學義理涵養、經世宰物情志。以此為準的,熊禾將詩人區分為兩類,一是儒者型詩人,二是尋常詩人。前者如《適堂說》《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所論周敦頤、程顥、朱熹等理學詩派詩人,以及《題童竹澗詩集序》《佩韋齋文集序》所論屈原、陶淵明、杜甫、韓愈、歐陽修、俞德鄰、童敬仲等具備儒者心胸品格的詩家。后者如《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閑樂堂記》《送夏思學歸江東序》等所泛論的留連光景或遺棄事物或貴詞華、尚雕飾的諸多騷人墨客。
在熊禾看來,創作主體胸中之所存,從根本上決定了作品的格調境界。因此,對于具備經學義理涵養或儒者情志品節的詩人及其詩作,他甚為推重。如,《佩韋齋文集序》有云:
唐宋以來,文章大家數不為少矣,其立言之卓然不可冺者,惟韓、柳、歐、蘇最著。柳固不敢望 韓,蘇之于歐,亦未易同日語。過江,少失真粹矣。同甫、正則,一時擅名江左,取節焉可也。……而其表表者,讀四書,通經博史,多自洛、建門庭中來。風聲氣習,漸涵演迤,百余年間,詩人文士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一言一詠,猶足起人悠然深長思,蓋《豐芑》《菁莪》之澤遠矣。[6]2266
文中所述詩人作家,大抵以儒學安身立命,深受經學義理或理學文化風習的濡染沾溉,其詩歌作品往往也因此寓倫理綱常之道,助益性情,扶植世教,卓然可傳。這里,熊禾在柳宗元與韓愈之間以及蘇軾與歐陽修之間,皆有所抑揚。據其《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一文披露,大概是因為,柳、蘇二氏胸次所存,除了儒學之外還有佛禪、莊老之學。南宋的陳亮、葉適,分別是宋代理學中永康學派和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皆倡“事功之學”,于“性理之學”則有所輕忽。這與熊禾所主張的“明體適用”或“全體大用之學”有一定距離;不過在他看來,二人的義理涵養雖稍欠真粹,但情志品節仍頗為可取,故也予以表出。又如,《題東坡詩集后》指出,蘇軾的詩歌創作有過三次演變,從“雄騁”到“清永”,再到“習氣脫略盡”,漸趨于正;而個中緣由,據熊禾觀察,除了生存遭遇之磨礪和江山風月之助推,還在于其義理涵養漸臻于真粹。[9]232-233在《又和》詩中,熊禾還從“斯文”傳承的層面,對儒學之士的詩學活動進行觀照,他認為:在世道衰微、禮義存廢之際,堅守儒者職志而以人倫教化為歸宿的詩學活動(包含寫作、閱讀、教學等)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9]236
相反,對于后一類詩人作家,熊禾大不以為然。《題童竹澗詩集序》在肯定《詩三百》中諸詩篇創作者的情性、節行以及屈原、陶淵明、杜甫諸人的憂世情懷之后,接著又對“近代詩人”進行評論,曰:“格力微弱,骎骎晚唐五季之風,雖謂之無詩可也”。[7]7這里所謂“近代詩人”,指宋末元初風行于詩壇的以“四靈”晚唐體為詩學宗尚的江湖詩人。由宋入元的一些詩學人士,與熊禾大概同時或稍相先后,曾對江湖詩人及其詩歌創作予以嚴厲批評。如,方回《送胡植蕓北行序》(《桐江集》卷1)云:
近世詩學許渾、姚合,雖不讀書之人皆能為五七言。……而務諛大官,互稱道號,以詩為干謁乞覓之資。敗軍之將,亡國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陽,刊梓流行,丑狀莫掩。[10]
方回《唐長孺藝圃小集序》曾從創作主體志趣品格的角度,將江湖詩人歸為“格卑者”。這里他認為,江湖詩人不具備學問涵養,缺乏雅正志趣,將詩歌作為干謁謀私的工具,背離了“詩道”。趙文也持有近似之論,其《蕭漢杰青原樵唱序》云:
江湖者,富貴利達之求而饑寒之務去,役役而不休者也,其形而不全而神傷矣。而又拘拘于聲韻,規規于體格,雕鎪以為工,幻怪以為奇,詩未成而詩之天失矣。[11]64
趙氏論詩主“性情”之真,強調詩歌創作主體應具備超拔于俗流的胸襟意趣。在他看來,江湖詩人汲汲于“富貴利達”,志趣品格自然難以擺脫低俗卑陋之境;以詩為干謁之具,專務格律聲韻、詞采藻繪,創作也無從見其性情之真。又如,何夢桂主張以詩歌“載民風,系世變”(《文勿齋詩序》),并認為“詩以感而賦,不感則無詩”(《分陽諸公感寓詩集序》);據他的觀察,江湖詩人“不事時世”(《琳溪張兄詩序》),雖遭遇世變,詩歌創作仍專意于詠物,無所感寓。[12]何氏的這樣一種批評視角和價值基準,亦為方鳳所秉持。在《仇仁父詩序》一文中,方鳳將“人心”(即基于個體遭際體驗且關乎人倫風紀的知、情、意的活動狀態)視為詩歌之根本,認為詩歌乃“人心”的感發與呈現。以此為準據,他肯定“寄興深、裁語婉”的唐詩以及“氣渾雄、事精實”的宋詩,而對江湖詩人則多有不滿,認為他們處人倫事會之際,“人心”幽晦不明,以摹寫煙云月露為能事,盡失詩之根本要義。[11]655-656熊禾對江湖詩人詩作的看法,與上述諸人的批評意見大抵一致。通觀《題童竹澗詩集序》全文,結合前文所述的詩歌“體用”觀,可知其所謂“格力微弱”,指江湖詩人氣格卑微、骨力靡弱,亦即方回所說的“格卑”,而根源就在于未具備經學義理涵養、儒者志趣 品節。所謂“骎骎晚唐五季之風”,也就是趙文、何夢桂、方鳳諸人所指斥者,即雕鏤刻削、專事于外從而背離發于情性、止乎禮義、切于世事、關乎風教這一詩史正脈傳統的創作風習。
即使是為他所推重的韓愈、蘇軾,因二人曾流露隱居避世以遂志、放情林壑以自適的思想意趣,熊禾也不無指摘,有云:
昌黎送李愿曰“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東坡和淵明曰“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他日賦赤壁,不過以“江上清風”“山間明月”便可為適之具,而胸次所存者,皆虛曠之余習,凡我所當有事者,皆視之以為無栱,而付之幻妄。……若是者,雖足以少愧世之貪名逐利、終日馳騖不得息者,然秦漢以下,牽補架漏,人無宰物之情,其獨不以此哉?[7]73(卷5《適堂說》)
韓愈在《送李愿歸盤古序》一文中,借隱士李愿之口,表達他對超塵絕世、獨善其身的隱逸生活的向往。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一),蘊含忘懷世事、擺脫物累之情愫;《前赤壁賦》也蘊含遺世獨立、縱浪大化之意趣。熊禾基于“全體大用之學”的思想觀念,批評其流于“虛曠”“幻妄”,認為這是導致士人喪失宰物經世之情志的重要原因。其《閑樂堂記》也明確張揚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品格,批評捐棄世事、留連光景、逍遙自適的觀念與行為,強調儒學之士對國家和社會現實事務的擔當。[7]36基于此觀照視角,熊禾對上引韓、蘇二氏的作品頗致不滿之意。同樣,在《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一文中,他認為:自陶淵明、謝靈運、王維、柳宗元以來,詩歌史上眾多詩人所作的山水游覽詩,或拘拘于物色,或高蹈玄虛,世道之念往往闕如,皆不及朱子的“廬山紀行”“南岳唱和”“云谷武夷雜詠”諸作。要之,按照熊禾的詩學觀念,詩人所具備的經學義理之涵養和成己成物之志趣,正是合乎“體”“用”準則之詩歌創作能有效展開的基本前提,也是詩歌審美價值能得以實現的根據所在。
三、詩歌批評的基本趨向、話語構造及言說重心
作為文學研究的主要部類之一,文學批評有廣義和狹義的不同界定。就廣義言,它包括關于文學一切問題的“理論探討”以及對于文學作品的“實際批評”;而就狹義言,它主要指稱的是對于具體文學作品的“詮釋”與“評價”,即所謂的“實際批評”,當然也包含與之相應的理論依據。[13]按照這一區分,我們這里擬探討的是狹義層面上的詩歌批評。熊禾對具體詩歌作品的詮釋與評價,傳世文獻可考者,主要是其《題童竹澗詩集序》《佩韋齋文集序》以及蔡正孫《詩林廣記》一書中稱引的5則詩評。
在《題童竹澗詩集序》一文中,熊禾以摘句批評方式評點童敬仲詩:“君詩曰:‘閑從理亂覘風教,每到急難知世情。’君之心事蓋如此。又曰:‘故國有喬木,好山多子規。’忠愛懇惻之情至矣。”乃著眼于詩句所蘊含的詩人情志。這一詮釋,實則建立在他對童氏其人之了解的基礎上。序文上引評語之前有云:
童君敬仲,氣誼節概人也……。壯年有經倫志,知時不可為,則退而居鄉善俗。……平居瀟然閑適,筑室萬竹間,哦詩讀書,無復一毫羨慕其外之意。[7]7(卷1《題童竹澗詩集序》)
這里著重敘述了童氏的出處志行和襟懷意趣。顯然,在熊禾的批評話語構造中,此與其詩歌作品的情感內涵相為表里,二者之間構成一種“互文”的關系。
與上述情志論批評趨向有所不同,《佩韋齋文集序》顯現了熊禾詩歌批評的另一趨向。該文論及俞德鄰的詩作,有云:
《飲酒》諸篇,酷似陶;《遣懷》等作,大類子美,則其時實使之然。公之詩閑雅沖澹中,發揚蹈厲之意存焉。……近律駢儷,亦皆典則精致。原其所尚體要,則綜渉綱常,造次理道,又不可與尋常詩人文士例論矣。[6]2267
這里提及的“《飲酒》諸篇”“《遣懷》等作”,蓋指文集中以卷3所錄《暇日飲酒輒用靖節先生韻積二十首》和卷2所錄《京口遣懷呈張彥明劉伯宣郎中并諸友一百韻》為代表的古體詩作,熊禾著眼 于題材類型、寫作體式,揭示其與陶詩、杜詩的淵源關系;接著,他又分別歸納了其古體詩、近體詩的審美風貌,并循此推原其創作體要。這主要是文體論意義上的解讀與評析。此一批評趨向,也體現于《翰墨全書序》和《題東坡詩集后》,相關文字前文已引述,茲不復贅。不過,就批評話語構造而言,《佩韋齋文集序》與《題童竹澗詩集序》其實并無二致。因二人系同年進士,俞德鄰在易代之際的出處行跡及節義品格,熊禾宣稱其“親歷而知之”。上文所引評語之前還有如下敘述:
方其劫質軍中,爵祿在前,刀鑊在后,公獨不撓不攝,從容懇款,以全其身,一難也。身愈退,望愈高,諸公貴人交剡無虛歲。公于此時卑則易流,髙則易抗,乃獨處之有道,得以優游余年,終遂其志,二難也。[6]2267
按前文所引詩評,俞氏的若干詩作之所以和陶詩、杜詩類似,乃時世境遇使然。熊禾的這一詮釋,以及對其古體詩的審美風貌的解讀,皆依憑于他對俞氏出處行跡、情志品節的觀照和體認。除此之外,熊禾所知者還有其人之學問旨趣,即序文所述“以六經、《語》《孟》為本,雖史傳百氏之書,靡不該洽,而必以此道為之指歸”。前引詩評中熊禾對俞氏詩文創作所尚體要的論定,蓋有據于此。可見,這篇序文也是以互文見義的話語構造方式展開其批評論述的。
從以上所作梳理還可看出:詩人的胸次品節、情志趣尚、出處進退以及詩歌作品的時世蘊含,乃熊禾詩歌批評的言說重心。這同樣反映在蔡正孫《詩林廣記》所稱引的熊禾5則詩評當中。
《詩林廣記》前集卷7選入孟郊《贈別崔純亮》詩,并附錄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詩,蔡正孫稱引熊禾評語:“東野之詩,不如高蟾《下第》一絕,為知時守分,無所怨慕,斯可貴也。”[14]124二詩皆以科考下第作為書寫主題,屬同一題材類型的作品,但前詩多嗟嘆之詞,怨憤之情溢于言表,后詩則達者之詞,自持自足之意了然可見。熊禾此處的批評意向即在于詩人的情志格調、襟懷氣度。又如,后集卷2王安石《君難托》詩后,蔡正孫稱引熊禾閱讀此詩時所下按語:
按神宗即位,召公參大政。公每以仁宗末年事多萎靡舒緩,勸上變風俗、立法度。上方銳于求治,得之,不啻千載之遇,公亦感激,知無不為。后公罷相,呂惠卿欲破壞其法,張諤、鄧綰之徒更相傾撼。上雖再召公秉政,逐惠卿等,而公求退之意已切,遂以使相判江寧,此詩疑此時作也。[14]224
這一解讀,意在經由對王安石作詩之“時”“地”的考索,揭示詩篇文義(或寓意),而其論說內容主要是詩人的歷史際遇與進退之跡、經世情懷與政治作為。又如,后集卷9選入晏殊《詠上竿伎題中書廳壁》詩,其后附錄王安石《和晏元獻題中書壁》詩,蔡氏征引熊禾評語:“元獻之詩意,謂露巧不如守拙;荊公之詩,謂經濟有術,固不必拘泥也”。[14]408兩首詩都用了《莊子·天地篇》“抱甕灌圃”這一典故,但表達的情志趣尚卻迥然不同,前者沿襲了《莊子》貴樸尚拙的情感態度和思想觀念,而后者則基于經世致用的價值理念,認為不必拘泥于此,主張因事制宜。熊禾的詮釋即聚焦于此。再如,后集卷5黃庭堅《秋思寄子由》詩后,蔡氏征引熊禾評語:“此詩言世道將變,人才老死山林,無人推挽出而用世也。”[14]308按熊禾的觀察,不少具有經世之才的士人,隱逸山林以終,但并非捐棄事業、逍遙遁世,而是為世所遺、不得其用的歷史境遇使然,《漢王不拜嗇夫論》即有云:“巖穴之士,懷才抱德者多矣,往往以不知見棄”。[7]48在閱讀此詩時,他的這一認知無疑會成為其接受視域的構成因素,并有可能對其具體的詮析、評議產生一定的影響。從詩的內容本身來看,黃庭堅或許只不過是在表達其堅定的隱逸之志。熊禾的詮釋未必就一定切合詩作本義,但可以明確的是其論說重心,乃在于經由對詩篇述及的士人出處行藏及其社會歷史原因的觀照,辨識詩人寄寓于其中的情志趣尚。
關于詩歌作品的時世蘊含,上述《詩林廣記》稱引的4則詩評其實都已有所涉及;但論說較為集中的則是后集卷2王安石《兼并》詩后所稱引的評 語。王安石此詩敘述了“兼并”之弊,表達了其抑兼并的思想觀念和情感態度。蘇轍對此頗不以為然,他認為:世間萬物皆有差異,富人的出現,是理勢之必然,亦有益于國家的穩固和強盛,“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乃天下安定的根本;王安石“不忍貧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當政后即設“青苗法”,呂惠卿又繼之以“手實法”,違情悖理,弊病叢生、禍患深遠,而其本原則在《兼并》一詩所言之“志”。[14]214熊禾對王、蘇二氏的思想主張有所折衷、辨正:
按此詩未盡如蘇氏所譏,抑強扶弱,必如明道、橫渠之議而后可,行之以青苗、手實,則非也。究蘇氏之說,則富者跨州連縣,安得而不橫?貧者將無立錐,安得而不匱?上不為限制,何有紀極?斯民又何日蒙先王至治之澤也![14]214
一方面,熊禾也對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以及呂惠卿推行的“手實法”持否定意見;但另一方面,他又積極肯定此詩所表達的抑強扶弱的社會政治理想,在他看來,若任憑兼并而不加限制,其結果只會是“富者橫”“貧者匱”,蘇轍所謂的貧富相安根本就無從實現。顯然,熊禾的批評論說,乃圍繞詩篇內容所關涉的歷史時世和國政民生而展開。
四、結語
以上,我們以《熊勿軒先生文集》和《詩林廣記》為主要依據,將各類話語文本并置互觀,對熊禾的詩學觀念及其批評實踐展開了梳理與論述。從中可以獲知,熊禾對詩歌之學的性質與詩歌之“體”“用”的闡釋,以及他對詩人所具之“心”與詩作所造之“境”的辨析,皆以其崇奉的“明體適用之學”或“全體大用之學”為觀念依憑和價值準繩,表現出強烈的理學本位意識;熊禾的詩歌批評,無論是其情志論的批評趨向,還是考時論事、辨言析義的“互文”式話語構造,抑或是將詩人節行和詩作的時世蘊意作為言說的重心,無不受其理學觀念及相應的認知模式的規范和制約,也因應于他在特定歷史境遇下的文化政治訴求。
參考文獻:
[1] 朱鴻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 高令印,陳其芳.福建朱子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179-193.
[3] 謝靜芳.熊禾《易經訓解》易學思想評析[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3.
[4] 王次澄.宋遺民詩與詩學[M].北京:中華書局,2011.
[5] 方回.桐江續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9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67.
[6] 祝尚書.宋集序跋匯編:第5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0.
[7] 熊禾.熊勿軒先生文集[M]//叢書集成初編本:2407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8] 陶秋英.宋金元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278-281.
[9] 楊鐮.全元詩:第16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3.
[10] 方回.桐江集[M]//續修四庫全書本:13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79.
[11] 李修生.全元文:第10冊[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12] 李修生.全元文:第8冊[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93,125,132.
[13] 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M].杜國清,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1-2.
[14] 蔡正孫.詩林廣記[M].常振國,降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