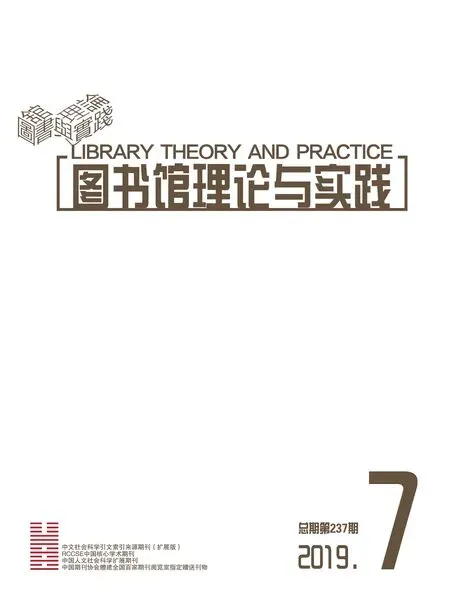歷史記憶視角的文獻辨偽學研究
關思雨(黑龍江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1 歷史記憶與文獻辨偽學
1925年,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特(Halbwachs)提出“集體記憶”的概念,為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經歷了幾十年鮮少被問津的時代,20世紀80年代之后,社會學和人類學界開始廣泛應用“集體記憶”這一概念探討社會與人類的歷史文化問題。自此,寬泛而粗糙的“集體記憶”概念逐步分化為個人記憶、歷史記憶、文化記憶、社會記憶等具有內涵交叉性、但又各有所指的子概念。
歷史記憶這一概念,指人對過去事物信息的保存、編碼和提取的過程。因而,歷史記憶的核心價值在于它的真實性指向。而文獻辨偽也正是以辨正歷史文獻的真偽為旨歸的,所辨之內容囊括文獻與作者的真偽。明王世貞曾言:“天地之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1]諸如此類六經皆史的論調,代而有之,說明古書文獻所載大都與歷史相關,偽書的存在也意味著歷史真實被人為破壞,代代訛傳逐漸面目全非,而文獻辨偽的過程則是對歷史記憶重新建構的過程。
此外,我們將研究范圍劃定為中國古代文獻辨偽學,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文獻辨偽學孕育于中國古典哲學,區別于現代西方理性世界觀統治下的二元對立話語體系。中國古代文獻辨偽學是融合于社會文化系統的學問,源于中國古典哲學中“天人合一”的辯證式思維,而不是客觀性的“是”與“否”的判分歷程。因此,我們需要在多元文化因素的整合中揭示古代文獻辨偽的本質,它不是具有共時性的唯一真理,而是歷時性的,表達著不同時間維度的主體對文獻和現實世界的政治或價值取向。中國古代圖書所包含的知識論意義上的客體維度與歷史信息中的“物理層面”相對應,而價值論意義上的主體維度則與歷史信息中的思想層面相對應,這就讓中國古代辨偽學最大程度上與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交相融合、互相解讀。
文獻辨偽學包括文獻辨偽實踐與文獻辨偽理論研究兩個方面,具體研究對象有存在真偽問題的文獻、文獻辨偽學史和文獻辨偽學理論三個方面。無論是辨偽學家甄定“偽”與“非偽”的辨偽實踐過程,還是數千年來辨偽理論的總結,都包蘊著知識性的歷史事實厘定與價值倫理層次上歷史記憶的廓清。因此,本文從文獻致偽與文獻辨偽兩個方面,探討文獻辨偽學是如何重構歷史記憶的。
2 文獻致偽
2.1 偽文獻的類型
在文獻辨偽學史中,明宋濂在其所著的《諸子辨》中第一次對文獻作偽類型有所總結。《言子》篇中所言:“大抵古書之存于今者,多出于后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為孔安國所錄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詞耳,善讀者固不敢與之。……此有所附麗而然。《三墳》書亡以久,宋毛漸特出之。……皆鑿空虛扇以惑世,尤使人驚愕不止。”[2]可以看出宋濂將偽文獻分為兩類。一類是“有所附麗”,如《孔子家語》等,以抄取《左傳》、《禮記》中個別篇次,并且稍作改動,以為己作。他認為這一類的偽文獻無論從取材、作偽態度和所托名的著者來講,都仍有可稱信之處。另外則是“鑿空虛扇”,如唐朝李笙偽作《陰符》而將其托名黃帝,該書沒有藍本,憑空捏造,其中所寫的只是一些七拼八湊的荒誕不經之語。他認為這類偽書次于前者,不僅沒有絲毫的可取之處,而且會霍亂人心。
宋濂之后,胡應麟所著《四部正訛》對文獻作偽的種類進行了全面的分析。他作此書的本意是輕論道而重辨偽,所以比起宋濂做的粗略分類,他能夠對偽書的性質做出客觀綜合的分析。他在緒論中將偽書分為二十個種類:“凡贗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數十種。有偽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有掇古人之事而偽者,有挾古人之事而偽者,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有憚于自名而偽者,有恥于自名而偽者。”[3]胡氏依從證據、心理和歷史等方面歸納出作偽的公例。《四部正訛》劃分偽文獻類型這一學術成果已經達到辨偽學界的巔峰,后人雖仍有不同說法,然皆未跳脫胡氏之公例。但因明代的學風務博而荒,學者多廣泛涉獵而淺嘗輒止,所以胡氏列此條目之后并未進行深入的研究。
古人以篡改文獻內容或著者的方式,導致歷史真實面目全非,使后人被偽文獻混淆視聽,對前人所經歷的史實、思想甚至社會文化背景有所誤解。有學者認為,偽書對治道和學統都有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應該對其盡心考辨,極力打擊。回歸“物理層面”上的歷史真實固然是正確的,但文獻造偽所給予我們的歷史信息也不完全是混淆與錯誤的,對造偽之人真實目的的發掘更能夠使我們真正了解到當代道術學統。
2.2 文獻致偽的原因
中國古代造偽之人的目的無非可以歸結為三種。
(1)為功名利祿。西漢時期張霸偽造“百二篇”《尚書》,是希望可以被成帝委以重任。張霸獻書成帝,成帝果真大喜過望并對張霸青眼有加。但張霸造偽書之事不久之后便敗露,這種大不敬的欺君之罪在當時理應處以極刑,但因為種種原因得以幸免。與張霸類似,劉炫為了取得賞賜而偽造《連山》《魯史記》,史書中對劉炫的評判“懷抱不曠,又吝于財”是十分切合的。
(2)為稱信于人。《漢書·藝文志》也曾分析古人造偽的原因。關于《神農》的造偽之事,書中有言:“六國時諸子疾時怠于農業,道更農事,托之神農。”因此,有學者認為造偽原因是經世濟民,這確實不假,但這僅僅是《神農》一書造偽的具體原因。究其根本,這類文獻的造偽是將有價值的文獻托于古人,稱信于大眾,才能更廣泛地流布于世。正如《淮南子·修務篇》中所言:“世俗之人,多貴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后能人說。”《畫書賦》本來是杜道士所作,但他本人才疏學淺,恐以自名則書難行世,所以偽托自己的老師陶弘景的名字,才使《畫書賦》得以流傳。
(3)為鏟除異己,或是動搖政權。古人的文獻辨偽與造偽,向來就不是單純的文獻整理問題。唐代后期著名的牛李黨爭中,就存在文獻造偽以打擊對方勢力的事情,托名劉柯所撰的《牛羊日歷》就是李派為詆毀牛派所造的偽文獻。偽書《御侮錄》紀宋南渡后與金人構兵及議和之事,作偽于南宋風雨飄搖、戰亂頻仍的時期,是戰亂時期交戰國的文官之間口誅筆伐相互詬病而偽造的文獻。《四庫全書總目》辯正其偽時言:“知為鄰國傳聞,不盡實錄也。”清朝的“偽孫嘉淦奏稿”一案更是為人所熟知的造偽事件,目的在于鏟除直言敢諫的孫嘉淦。這三例究其根本:一是以作偽的方式,將政敵陷于水火之中,最終目標在于鏟除異己;二是戰亂時期不同勢力相互動搖政治根基;三是企圖激化君民之間的關系,在清后期皇權空前強大的的情勢下,矛盾焦點越發明朗也是情理之中的。
2.3 文獻致偽對歷史記憶的“破”與“立”
2.3.1 “破”:混淆后人視聽
王國強認為,文獻的真偽決定著結論的客觀與否。[4]這是毋庸置疑的。無論出于何種原因而杜撰的偽文獻,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后人對前代曾發生過的真實歷史有誤解,而后人的學術境界與思想境界又傳承于前人構建的學統,偽文獻會造成學術的錯位或崩塌。如程朱理學一派“十六字心傳”的立論,來源于《尚書》中《大禹謨》篇,這一理論也成為理學一派修身齊家治國的基本原則。雖后來的學者通過多方舉證,證實《古文尚書》中《大禹謨》等篇為偽書,但程朱理學“以理殺人”早已經釀成定局,無法挽回的事實只能讓后人扼腕嘆息而已。
在科技不發達的古代社會,文獻的代代相傳是先賢記錄歷史、文化、思想的主要憑借,是我們了解前人的渠道之一,這也是我們至今仍有許多學者還在考辨古典文獻的重要原因。對文獻真偽的不同認識,指向了對歷史格局的不同認知。因此,偽文獻所造成的知識錯位確實對史實、學統與道統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壞,這是對歷史記憶知識性的破壞。
2.3.2 “立”:感知思想機理
文獻造偽只是表面上的歷史現象,經過古今學者的分析,我們漸漸了解了古人作偽的思想動機。淺層次上,時人為名利作偽、為爭勝作偽,謀財者如張霸與劉炫,爭勝者如黨爭中的牛李兩派;深層次上,則為動搖學術或政權的根基作偽,如清代孫嘉淦案。
中國古代學術活動與政教人倫是無法分別對待的。從邏輯上我們可以由文獻造偽活動推論古人的思想流派與政治分野。如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派對文獻造偽與辨偽即有不同的觀點,但心學一脈的基本理論是:“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5]這與文獻辨偽的考據務實精神背道而馳,因此在文獻辨偽活動中無法與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學分庭抗禮。《四庫全書總目》在分析宋明時期偽書產生數量增多的原因時也曾言:“考私家記載,惟宋明二代為多。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于朝廷,不得志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顛倒,頗亦螢聽。”[6]又如清代漢學與宋學兩派對文獻造偽與辨偽持有不同觀點,因乾隆皇帝更崇尚乾嘉漢學,所以《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文獻辨偽成果中大都是深藏漢學意味的。
綜上,從偽文獻產生的不同原因與類型,以及古代學者的學術視野,使我們能夠勘破當時學者的思想機理與目的旨歸,這就是文獻造偽的過程中對歷史記憶的“立”,在價值論層面上彌合了歷史真實。
3 文獻辨偽
3.1 文獻辨偽的成果
文獻辨偽學始于先秦,成于兩漢,直至唐宋元明,辨偽方法與辨偽學理論甄于成熟。歐陽修是宋代文獻辨偽發凡起例的代表人物,辨偽成果對后世影響十分深遠。他在研究《子夏詩序》時認為《詩序》非子夏所作,是后人偽托子夏的偽文獻,知識性層面上否認了《子夏詩序》的真實性,客觀上重新建構了歷史記憶。但他并未對《詩序》全盤否定,歐陽修言:“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于《詩》常以《序》為證也。”[7]這說明他在主觀維度上承認了《詩序》與圣人之志相合,并非是全不可取的。可以看出宋代諸儒尊六經而師孔孟的學術依歸。
歐陽修在對文獻考辨的過程中,既重視客觀性的歷史真實,也有主觀的價值性論斷。而朱熹則更注重文獻超現實的價值意義。在考辨《古文尚書》時,他以義理第一、考據第二的辨偽學思想,一方面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因《古文尚書》與理學脈絡頗為相合,朱熹便從義理的角度為其翻案。在朱子的辨偽成果中,雖然并不是都如《古文尚書》一案,但所考辨文獻真偽的出發點,都體現了程朱理學的哲學觀念與學術風格。
最為典型的政治意味濃厚的文獻考辨成果,應是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目前很多學者已經不將《新學偽經考》作為辨偽學的著作來考慮,它擁有極強的政治指向性和社會教化意義。康有為以辨偽一事遮蔽自己“托古改制”的真實目的。康氏的辨偽具有極強的主觀性,他認為《十翼》《漢書》等文獻都為劉歆偽作,得出“劉歆偽造群經”的結論。但他對于一部分偽書,例如《詩序》等的懷疑,也是有所根據而指向歷史真實的。基于清末的社會背景,康氏的《新學偽經考》使得思想界經歷了地動山搖的震顫,是維新變法的思想先導。
中國古代的文獻辨偽,表面上都是以重建“物理層面”的歷史真實為目的。但是實際上潛藏于中的,還有大量的“思想層面”的歷史信息沒有引起學界的注意。這兩者的融合,才能夠真正重構歷史記憶。
3.2 文獻辨偽的方法
在古人辨偽的過程中,產生了很多文獻辨偽的方法。但中國古代沒有形成西方學科化的知識體系,學問講究“融匯貫通”,指向“經世致用”,實用性大于理論性,所以辨偽學者也鮮少形成邏輯森嚴的理論總結。但在實際的文獻辨偽過程中,我們依舊能夠總結出古代辨偽學家應用的辨偽方法。
柳宗元在考辨偽書時,曾使用多種不同的辨偽方法。他在《辨列子》中曾言:“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8]柳宗元以比較作者所處年代是否與史實相符的方法辨《列子》之偽。而《辨文子》中,其言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意緒文詞,叉牙相抵而不合”,[7]則是依照書中文辭與思想是否與作者相合來考辨文獻。此外,柳宗元也使用過校對與比讀的方法考辨文獻真偽。
劉知幾在辨《孝經》鄭注并非是鄭玄所作時,根據鄭玄的門生是否引用過該書中的理論或言辭來考辨真偽。朱熹則通過義理來辨偽,認為首先要規整思想,其次才有文獻真偽。胡應麟的《四部正訛》不僅列出了二十種偽文獻的類型,也全面的列舉了辨偽的方法,史稱“辨偽八法”:“核之《七略》以辨其源,核之群志以觀其緒,核之并世之言以觀其稱,核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核之文以觀其體,核之事以觀其時,核之撰者以觀其讬,核之傳者以觀其人。”
綜上,后世學者總結古代文獻辨偽學中的理論方法,大概分為兩類。① 知識性的辨偽,如校勘、輯佚、史實、典章制度等。② 價值性的辨偽,如言辭是否雅馴、思想體系是否相承。這兩類辨偽方法依舊可以指向歷史真實的正反兩面,一方面為我們解決了文獻內容與作者的客觀真實性,另一方面為我們梳理了古人主體維度層面的價值立場。
3.3 文獻辨偽學者的“客觀”與“私心”
中國古代的文化思維與西方迥然不同。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說過:“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窮盡真理是西方文化的思維方式。西方學者秉持著主客二分的二元論觀點,將人抽離于客觀世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去掌握自然法則。而中國古代的文化思維則是“天人合一”的,如《道德經》中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中國古代學者將“天道”的法則與“人道”的原則融合為一體,因而主體與客體是渾然一體無法割裂的。反映在古代文獻辨偽學中,這種整體性的思維使得辨偽學家們潛藏在考辨文獻真實背后的真實目的形成了一個鮮明的邏輯序列:考辨真偽——考鏡源流——申明大道。但這個邏輯序列并非完全客觀的,而是偏重于超現實的主觀維度,學術立場是考辨學術源流的前提性問題,申明大道之“道”也是儒家之道,不是百花齊放的多元之“道”,這就是文獻辨偽學者的“私心”所在。因此,探討文獻辨偽學建構歷史真實的問題時,不能僅僅考慮客觀真實的建構,更重要的是古人思想機理的建構與把握。
3.3.1 還原歷史真實,考辨學術流別
文獻辨偽學的邏輯始點即是去文獻之“偽”存歷史之“真”,使偽造的文獻還原本來面目。這一點是古代辨偽學家共同致力的具體目標,所舉證的論點論據或出于考據、或出與義理,必定有所依憑。很多史上辨偽學之公案,最后由歷代學者們多方舉證,能夠得到一個相對統一的關乎是非真偽的答案。張霸“百二篇”《尚書》的真偽問題,漢儒王充、宋儒朱熹、清儒顧棟高、惠棟等都對此進行過不同角度的考辨,皆得出其作為偽的結論。而且,乾嘉樸學繼承了漢學重考據之風,漢學與乾嘉樸學的學者多用考據學家的視角去審視和闡述文獻的真偽問題,這也為客觀歷史最大程度的還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四庫全書總目》不僅是傳統目錄的巔峰之作,也蘊含著豐富的辨偽學思想,它在“凡例”中所提出的辨偽目的和方法,包蘊著辨偽一事如何還原歷史真實,偽文獻又為何是學術源流中的重要一環。“《七略》所著古書,即多依托。班固《漢書·藝文志》注可覆按也。遷流洎于明季,偽妄彌增,魚目混珠,猝難究詰。今一一詳核,并斥存目,兼辯證其是非。其有本屬偽書,流傳已久,或掇拾殘剩,真贗相摻,歷代詞人已引為故實,未可既為捐棄,則姑錄存而辨別之,大抵灼為原帙者,則題曰某代某人撰,灼為贗俈者,則題曰舊本某代某人撰,其踵誤傳偽,如呂本如《春秋傳》,舊本稱呂祖謙之類,其例亦同。至于其書雖歷代著錄而實一無可取,如《燕丹子》陶潛、《圣賢群輔錄》之類,經圣鑒洞燭其妄者,則亦斥其存目,不使濫登。”[6]《凡例》中雖然謂偽文獻“魚目混珠”“猝難究詰”,但仍因為歷代學者不知其書為偽,已經將偽書中的論斷納入正統的學術源流之中,而不武斷的將其“捐棄”。它也認為偽文獻并不是全無可取,只有經鑒定完全沒有可取之處的偽文獻才會“不使濫登”,這說明《四庫全書總目》的辨偽思想中就已經存有偽文獻對考辨學術流別存在一定價值的觀點,而且在價值論層面上統攝于學統與道統的偽文獻,也是有存留價值的文獻類型。
綜上,透過考辨文獻真偽這一具體目的,在文獻辨偽學的深層學理中,可以讀出考辨學術流別的意味,并且是以申明大道為旨歸的。大量的偽文獻橫行于世,必將霍亂人心引起負面影響,破壞學統的純正根基與發展脈絡,我國古代以儒家思想文化的政治根基也可能面臨地動山搖的局面,以至于君統與道統崩壞的結果。因此,建立血統純正的文化傳承是必要且合法的,這個過程也順勢彌合了被破壞的歷史真實。同時,一部分偽文獻的存在也是古代學統不可磨滅的一環,辨偽學家們辯正其真偽,但并不能將其焚毀于世,辨偽只求真相而無關偽書取舍,它們在學統與道統的層面上是合法存在的,在繁復的學術體系中有其自身的位置與價值。這就是文獻辨偽將重構歷史記憶中“物理層面”與“思想層面”全盤考慮的體現。
3.3.2 支持思想正統,維護學派立場
“天道”反映在學術領域是逐本究源,以申明大道為旨歸。而反映在社會人倫的領域則包括是君臣之道和師生之道。《論語·顏淵》篇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宋代詩人蘇軾也曾說過:“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9]因此,支持思想正統,是中國古代臣子做為人臣的題中應有之義,辨偽學家也不外如是。此外,尊師重道也是中國古代社會人倫重要的一環。呂不韋曾言:“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師者。”[10]中國古代尊師與維護學派的立場幾乎是等同的概念。
在后人總結的古代文獻辨偽學的方法中,我們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辨偽方法的界定都是含混不清的。如,以文辭辨真偽時端看文辭雅馴與否,而文獻內容是否雅馴并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不同的主體在對同一篇文獻進行判分時,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又如思想是否一脈相承,這也是一個解釋學(hermeneutik)層面上的問題,這種判定充其量可以作為一門藝術,其結果也是“一千個人眼里的一千個哈姆雷特”。
正因如此,辨偽學家們才擁有足夠的空間,擠壓客觀性知識的存在空間,給主觀的價值論維度提供更寬闊的發揮余地。康有為的辨偽學家的名號要以政治家為前提;顧頡剛的地理沿革研究應用于古史辨,也要囊括在他“新漢學”學派學者的身份之中,傳承了中國傳統學術的衣缽;最為典型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文獻辨偽成就,它的主旨就是發揚儒家正統思想,批駁異端,維護封建皇權。在考辨文獻過程中,無論文獻真偽,只要能夠彰顯儒家學派風貌,或是贊頌封建專制的治國之道,既“可為寶貴也”。
4 結語
目前文獻辨偽學的研究,往往注重具體文獻的考辨、文獻辨偽學史的梳理和文獻辨偽學思想的總結。將其囊括在歷史記憶重構視角下的文獻辨偽學研究,僅僅在蔣永福、高晶的《歷史記憶的重構:校讎學的宗旨》一文中,作為一個部分所提及,并指出辨偽的目的是辯正歷史之偽。本文在這一概念的基礎之上,從歷史記憶的“物理層面”和“思想層面”兩個角度分析文獻辨偽學在辯正歷史之偽時以怎樣的方式彌合歷史真實的。指出文獻作偽并非完全給予歷史真實以致命的打擊,實質上在思想層面能夠讀出學術派別的分野與傳承,政治派系的整合與分野。而文獻辨偽活動也并不完全是彌合歷史真實的武器,在辨偽的過程中,文獻辨偽學家的主觀性“創造”也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修復歷史記憶的原本目的,而以自身的價值取向定論文獻的是非真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