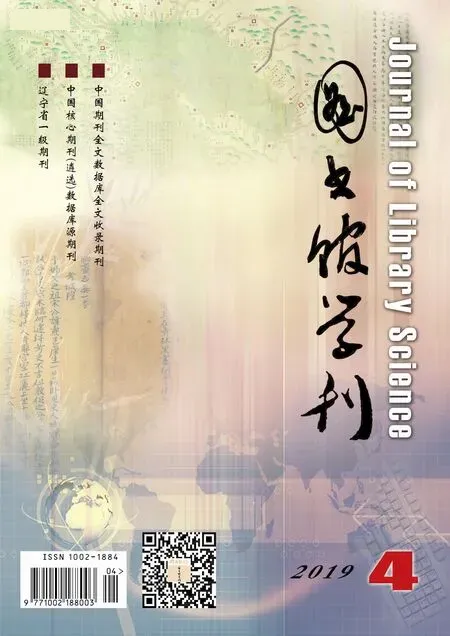葉昌熾的目錄學思想探究
劉惠蘭
(平頂山市圖書館,河南 平頂山 467000)
1 葉昌熾其人
葉昌熾(1849—1917),近代學者,藏書家,金石學家。字頌魯,號緣袈,又號鞠裳,自題緣督廬主人。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少聰慧好學。早年就讀正誼書院,幫助馮桂芬編修《蘇州府志》一書。光緒己丑(1889年)會試以魁選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張文襄公密疏薦,當事沮之。循資平進,賞侍讀銜,充會典館幫總纂、國史館提調,遷國子監司業、翰林院撰文。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賞戴花翎,升授侍講。辛丑,奉命督學甘肅,清介勤慎。校士之暇,訪求古跡,最早重視敦煌藏經洞所藏文獻。尋清廷廢科舉,引疾歸里。后充禮學館顧問官。辛亥之后,悲天憫人,艱貞自矢。舉目山河,注心魏闕,忠憤沉郁,至痛在心,震而發為詩歌[1]。葉昌熾一生讀書勤奮,每年抄書、校書達十數部以至數十部,校書尤為認真仔細。葉昌熾精于版本、目錄、校勘及金石學。家富藏書,積至一千余部,三萬余卷,多有明清文集及宋元佳本,其中吳中鄉邦先哲遺書占三分之一。藏書處名治鷹室、雙云閣。所藏書在晚年售于嘉業堂與聚學軒。“買書難遇盲書賈,管教仍然老教官。蕓香濃處多吾輩,廣覓同心敘古觀。”[2]生平著述豐富,編有《治唐室書目》《伍百經幢館藏書目錄》等,撰有《庚子紀事詩》《滂熹齋讀書記》《語石》《緣督廬日記》等。其代表作為《藏書紀事詩》。
2 葉昌熾的目錄學思想
根據葉昌熾自己回憶:“昌熾弱冠,即喜為流略之學,顧家貧不能得宋元槧,視藏家書目,輒有望洋之嘆”。[3]“流略之學”即目錄學。清人重視目錄學,認其為作學問的第一緊要事,“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人,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4]葉昌熾的目錄學思想主要體現在《藏書紀事詩》一書。《藏書紀事詩》七卷,專搜中古以來藏書家史實,起于五代,迄于清末,凡739 人。“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簿錄、古今文集,見有藏家故實,即哀而錄之。”(《藏書紀事詩》前記)開創了“領以絕句,綴以事跡,必要時殿以按語”的紀事詩體藏書家傳體式,為后世學者所效法。并有“藏家之詩史,書林之掌故”之譽。
《藏書紀事詩》是一部七卷的味述藏書家事跡的絕句集[5]。收入“書目書話”叢書。本書是我國第一部以紀事詩體為古代藏書家立傳的著作,收錄豐富,廣征博引,為后人研究中國古代藏書家及藏書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線索。對于集中所收錄的每一位藏書家,他都寫了四句詩來敘述其人的藏書事述,然而,這部書的最具價值之處,是在于葉昌熾博征群書而得的引文。作者也在這些引文之后表述一下自己的見解,長者竟可達八頁之多。這部書事實上成為了古代藏書家的傳記辭典。由于作者在書中只提供資料概略,而未直接提供完整的原文,所以是一種資料的參考指南。
《藏書紀事詩》注文后,還有葉昌熾的多則案語,案語前標“昌熾案”三字。一般而言,案語放在注文后面,也有穿插在注文中間的。葉氏對于案語的撰寫十分留心,有引用典籍的,而更多的則為自己見聞,案語史料價值之高自不待言。一般來說,《藏書紀事詩》的案語作用主要表現補充資料、匡正資料、存疑待考《藏書紀事詩》注文中所引資料有誤、點評之語方面。
案語有解釋注文中出現的名詞的。如卷四《錢謙貞履之子孫保求赤》注文引用《愛日精廬藏書志》:“李群玉《唐風集》,皆有錢履之讀書記。板心有‘竹深堂’三字。”對于“竹深堂”三字的來歷,案語曰:“竹深,謙貞七世祖洪自號也。錢陸燦《常熟縣志》:“洪字理平,與兄寬字理容世家奚浦。能詩好客,洪愛種竹,堂曰‘竹深處’。”案語有補充介紹傳主生平事跡的。如卷四《胡介祉循齋》注文所引《鐵琴銅劍樓書目》《楹書隅錄》《經籍訪古志》皆無胡介祉生平,案語曰:“茨村名介祉,字循齋,山陰人,宛平籍,少保兆龍子。由蔭生歷官河南按察使。著《隨園詩集》,詳見《兩浙鞲軒錄》。《毛西河詩話》載其《趵突泉》詩一首,稱其詩盛為當時所推。竹圪嘗屬其刻宋本《十家宮詞》,有序,見集中。其藏書印冠以‘燕越’二字者,以南人隸北籍故耳。蕘翁皆未能知也。”案語有補充介紹藏書家藏書下落的。如卷七《丁丙嘉魚》,對于丁丙藏書下落,案語曰:“歸安陸氏麗宋樓精本與守先閣所藏明以后刻本,日本以六萬金并金石拓本捆載而去。是時陶齋制府督兩江,聞丁氏書亦將散,懼其為平原之續,亟屬繆筱珊前輩至武林訪之,盡輦之白下,開圖書館以惠學者。兩家之書,同一不能守,而松存身后,不至流入海舶,視存齋為幸矣,亦陶公之力也。”通過案語,補充大量注文中不能得見之史料,對于理解傳主生平、藏書等幫助甚大。
《藏書紀事詩》注文所引資料在給出藏書家生平事跡方面,有時存在與史實不符的情況,這就需要葉昌熾在案語中給予匡正。
文獻記載傳主藏書流傳有誤,案語及時匡正。如卷一《呂正愍大防·張玢》注文引《邵氏聞見后錄》曰:“神宗欲更修《后漢書》,求《東觀漢紀》,久之不得。后高麗以其本付醫官某來上,神宗已厭代矣。元祜中,高麗使人言狀,訪醫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予嘗寫本于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提到《東觀漢紀》一書毀于宋金戰火,葉氏案語曰:“今《四庫》本二十四卷,輯自《永樂大典》。然則其書明初尚存,不亡于南渡也。”文獻有記載人名訛誤者,案語一并改之。如卷二《光澤榮端王寵》注文引《天祿琳瑯(書目)》曰:“史記,明興宗第四子衡王允煌藏本,有‘衡王圖書’印。”葉氏案語曰:“興宗子封衡王者,名允燥,非允煌。允煅,靖難時改封懷恩王。此衡王為憲宗第七子衡恭王裙揮。”注文所引資料記載中有不加考證者,案語給以匡正。如卷四《錢裔肅嗣美子曾遵王孫沅楚殷》,葉氏的案語考證“述古”一詞的來歷說:遵王藏書處曰“也是園”,曰“述古堂”。考陳繼儒《妮古錄》:“繆貞得宋紹興丁巳邵諤所講述古圖研,因以‘述古’名堂,黃晉卿為記。是‘述古’之名,不始于遵王也。”此外,案語中還有匡正地名、書名等之誤者。
存疑待考《藏書紀事詩》注文中所引資料有誤,但是葉氏難以根據資料給予改正者,則提出疑問,留以待考,體現了嚴謹的治學精神。面對不同文獻對統一問題記載的歧義,葉氏在無確鑿證據情況下,常常以“未詳”存疑。如卷一《朱遵度》,注文引用《直齋書錄解題》記載五代人“崔遵度”曾編《群書麗藻》,而《焦氏筆乘》《金陵舊事》卻記載為“朱遵度”著,因無其他資料佐證,葉氏案語云:“《焦氏(筆乘)》‘崔’作‘朱’,未詳。”根據今人盧燕新考證可知,《群書麗藻》的作者應為五代時人“朱遵度”,而非“崔遵度”,《直齋書錄解題》記載有誤。資料對于兩代人的關系記載不明者,葉氏亦存疑待考。如卷二《邢量用理邢參麗文》注文引用《列朝詩傳》謂邢量和邢參是祖孫關系,而乾隆《蘇州府志》卻稱“麗文,量之族孫”,因而葉氏案語云:“未知孰是。”資料對于傳主名、字記載往往不一,葉氏一時難以確考,常存疑。如卷三《孫江岷自》注文引《讀書敏求記》云:“唐僧《宏秀集》十六卷,元人鈔本。予獲之于孫岷自。岷自購一古圖記,刻鏤‘孫江’,字絕佳,苦愛之,即改名江,亦吾鄉俊民也。”葉氏根據這段記載推斷說:據此,則“江”非原名也。《瞿氏書目》有《沈下賢集》,馮氏藏本,葉奕傳錄,孫明志再錄之。又《古文苑》,有岷自跋云:“趙凡夫藏宋刻。紙墨鮮明,字畫端楷。靈均鉤摹一本,友人葉林宗見而異之,亦錄一冊。辛巳夏,假歸,分諸童子,三日夜鈔畢。”江與林宗為友,《沈集》亦錄自林宗。頗疑“明志”即其原名,但無可考耳。只是提出疑問,不輕易下斷語,葉氏做法十分審慎。
對注文所引資料給以適當的點評,為葉氏案語主要內容,可以從中了解作者對問題的態度。[6]
此后,他的宗人葉德輝指出了其局限,批評它“不及刻書源流與夫校勘家掌故”,因而決心另寫一部書來補其不足。葉德輝決心的結果是寫成了一部奠基性的書史著作《書林清話》。
3 結語
葉昌熾是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金石學家。他在收錄藏書家的事跡時,會記載收藏家的跋語、印記,或解題,或考究其優劣,或援引文獻中書目題跋。《藏書紀事詩》的征引文獻、目錄索引的價值還在于為后學者從此書直接查詢到一些不常見珍稀書籍或某版本的善本信息線索[7]。《藏書紀事詩》記述藏書家時往往引文列舉其著作,而這些作品中有許多為目錄學著作,具有目錄索引的作用[8]。《藏書紀事詩》具有編撰指導思想明確、編排體例得當、人物取材廣泛和注文簡煉、案語中肯等特點,特別是《藏書紀事詩》內容涉及歷代藏書、刻書、校書、訪書、焚書等,尤其是包含了大量有關中國古代讀書史實的原始資料線索,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名著之一[9]。該書以詩歌的形式記錄了自五代到清末藏書家的事跡,其中還介紹歷代刻書、抄書、校書等方面的情況,打破了目錄學著作原有體例的禁框,開創了一種新的體栽結構,開拓了一門專門學科——藏書家史的研究,集中反映了葉昌熾先生的目錄學成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