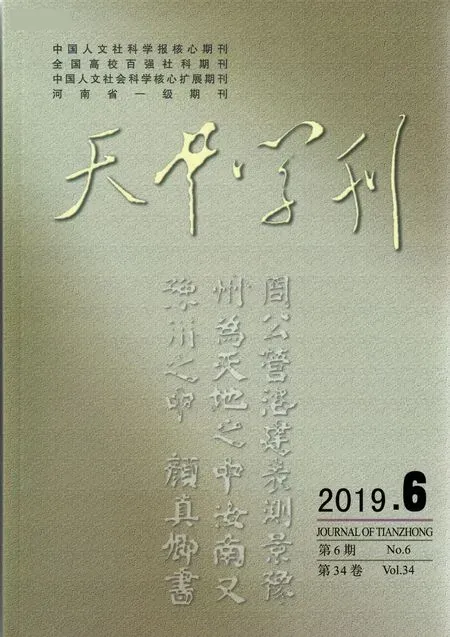李本固《汝南志·列女》探析
王 會 斌
(黃淮學院 天中歷史文化研究所,河南 駐馬店 463000)
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貢獻與價值,表現在文獻方面則不僅是對女性人物記述的篇幅逐漸增加,更主要的是開始將女性人物作為獨立類別進行撰述。劉向《列女傳》即為女性類傳的開山之作。其后,范曄《后漢書》更是在正史中為女性獨辟一章。繼而,《魏書》《晉書》《北史》等十多部正史,甚至一些地方史志,雖然在取材標準上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也均設置有此部分。李本固《汝南志》設有《列女》一篇,旨在反映他對女性價值認知情況下的當時社會的諸多現實問題,而這無不與發展變動的歷史進程密切相關。
一
李本固,字叔茂,明汝寧固始人,萬歷八年(1580年)舉進士,后歷任蒲城知縣、御史、巡按御史等職。其《汝南志· 列女》收錄了涉及6 個時期的94 名女性人物,其中春秋時期1 人,漢代3 人,晉代3 人,唐代2 人,元代6 人,明代79 人。從宏觀角度分析,入傳之女性人物按是否節烈①可分為兩大類。
(一)非以節烈入傳
這類女性共有11 人,約占“列女”總人數的11.7%,其中漢代3 人,晉代2 人,唐代2 人,明代4 人。她們入傳的原因比較多樣,如漢代馬融之女馬倫少因在婚禮之時以才辯迫使其夫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慚……有名于世”[1]1115而入傳;晉代梁州刺史朱序之母韓氏,則是因苻堅派其將領苻丕圍攻其子所鎮守的襄陽時,“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余婢于其角斜筑一城。賊果攻破西北角,眾守筑以御,丕遂引退”[1]1116的勇謀表現而入傳;明代的劉氏二女則是因其父感嘆“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宜”[1]1128之后,誓不嫁人送養父母終老,及無力營葬時“即屋為丘,亦庶幾不離親側”[1]1128的至孝行為而入傳。再如漢代之張劭母、范滂母[1]787,唐代的周氏、楊氏,明代的王氏、張氏等[1]866-869,或以子貴入傳,或以深明大義入傳,或以重誓守信入傳,原因不一。
(二)因節烈入傳
因節烈入傳的女性共有83 人,約占“列女”總人數的88.3%,其中春秋時期1 人,晉代1 人,元代6 人,明代75 人。若按是否付出生命守節為標準節烈入傳,則這些女性又可分為節女和烈女兩類。
1.節女
節女共有32 人,其中春秋時期1 人,元代1 人,明代30 人。除春秋時期的“宋人之女也,蔡人之妻者”,因“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醮之”[1]1113,她以芣苢為比,不肯棄夫而去的事跡而入傳外,其他31 人均因在夫君(含許聘未娶)死后表現出的忠貞不二、奉姑養子的節義形象而入傳。像“矢死守節,終養舅姑,居貧教子”[1]1123的胡冕之妻趙氏(尚書趙好德之曾孫女),“截發自誓,紡績以養舅姑,恪守婦道”[1]1124的平民莊十一之妻范氏,“誓不他適,紡績自給,奉舅姑各以壽終”[1]1125的邑人桂蘭之妻張氏等,莫不如此。
2.烈女
烈女共有51 人,其中晉代1 人,元代5人,明代45 人。按死亡原因的不同,烈女又可以分為三類:(1) 自殺殉夫(含許聘未娶)。此類女性共有25 人,其中晉代有1 人,元代有4 人,明代有20 人。她們多是在夫君因某些原因死去之后,自殺殉節,如藺氏是在其夫君邑庠生周基因病之后,“長號不食,志甘同穴……越二十日,竟縊死柩側”[1]1130;程英姐在其丈夫李長春死后,“日夜號呼……乘間縊于柩側”[1]1132;吳氏在其未婚夫徐蘭自殺之后,“欲往哭臨,母不聽,亦縊死”[1]1150等。(2) 為賊所殺(含被迫自殺)。這類女性共有25 人,其中元代有1 人,明代有24 人。她們在賊人以利誘或威逼手段迫使其順從己意時,為守貞節誓死不從,被賊人所殺。如面對想要侵犯自己的流賊,大罵曰“吾名家女,已許為雷黃門兒婦矣。肯從爾狗彘耶”[1]1131而被剖腹所殺的田臘梅;面對流寇逼迫時,“大罵,舉刃傷賊”[1]1147,最后被肢解的民家女孔秋香;面對流賊逼迫使其從行時,厲聲曰“我良家婦,肯從賊乎”,以刀自刺其面,而后被殺的張九方之妻董妙聰等。(3) 殉道自殺。此類女性人物僅有1 人,為明代彭養性之妻彭氏。在彭養性死后,彭氏念及尚有幼子,并未以死殉夫,等其子14 歲時,度其可立,恰逢其婆婆去世,公公再娶一個改嫁的婦人,強迫她參拜,她掩面號哭曰:“失節之婦,吾何忍見之?”[1]1153自縊而死。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彭氏的自殺雖與其夫君之死有關,但主要原因是其強烈的貞節觀念,即不僅自己不失節,而且不能忍受與失節的人共處。
從上述女性的構成比例可以明顯看出,李本固《汝南志· 列女》與劉向《列女傳》和范曄《后漢書· 列女傳》的多元標準已經大不相同,它對女性其他方面的品行如品德、節義、才智等已不再關注,貞烈幾乎成為能否入傳的唯一準繩。這也與《北史· 列女傳》以降,諸正史撰寫《列女傳》由重視貞烈到唯尚節烈選材標準的變化趨勢是一致的[2],是正史撰寫觀念在地方史志編寫中的體現。
二
選材標準只是作者挑選寫作素材主觀層面的因素,它只會決定作者要什么不要什么,但卻不能決定素材本身的存在與否。這也就是說,李本固撰寫《汝南志· 列女》采取了崇尚節烈女性的入傳標準,從而盡量收錄此類女性,但卻不能決定現實中是否確實存在此類女性。因此,我們并不認為“列女”篇中女性言行事跡的具體細節全部為真,但從李本固為女性創立史傳的目的來看,這些人物的基本事跡應當是真實存在的,至少在李本固看來應是如此②。可這些女性,尤其是以節烈入傳的女性,為什么會做出那些異于常人甚至匪夷所思的行為呢?
其一,有些女性人物的節烈行為明顯缺乏足夠的情感基礎,特別是那些只是許聘而未經婚嫁,缺乏共同生活經歷的。在李本固《汝南志· 列女》中這樣的女子共有4 位,且均出現在明代。比如:西平人張妙秀“聘陜西參政尹聰之孫琳,未娶而琳卒”[1]1137,但她卻“至葬所,躍身壙中以頭觸棺,欲同穴。其母強扶之出,挽之歸,曰:‘此吾家也!’遂留不去。”[1]1137-1138光山人李氏女,本許聘羅生, 未嫁而羅生“ 為繼母凌虐以死”[1]1147-1148,但她卻“聞訃酸楚,縞素自居。有富室欲娶之,乃剪發垢面,以死自誓。禮佛通經,不出戶庭者三年”[1]1148。固始人吳氏,本許聘徐蘭,“蘭以他事縊死”,“吳聞欲往哭,臨母不聽,亦縊死”[1]1150。羅山庠生麻袍之女麻氏,本許聘光山錢寧,“未嫁而寧舉家病疫,死者半”[1]1155,她請求母親允許她去看望,但“至則寧已死矣”,她不僅“跪奉藥餌于姑”[1]1155,待其姑病稍愈之后,自縊于夫旁。通過這些事件的描述,我們看不出這些女子與其未婚夫之間有多深的感情基礎,而且從明代社會對男女交往的種種限制考慮,他們在婚前也不太可能有較多的往來,所以她們能夠做出如此行為顯然不是因為深厚的自然情感。
其二,絕大多數節烈女性的行為常常是在夫妻非對等付出的情況下進行的,其付出的艱苦與辛勞遠遠大于其夫君所為,且不論以生命為代價的殉葬及“割肉事姑”③的極端行為,就拿守節孀居、奉姑養子來說即是如此。例如:汝陽人余氏,嫁給劉漢,生有一子,一年左右其夫即死,她不僅要撫育遺孤,還要“守節刺繡以養舅姑”[1]1125,在翁姑相繼去世后,又要“竭力營葬”[1]1125。詹氏,嫁給李尚德幾年之后,尚德即死,她不僅要面臨彼時“饑饉兼有流寇之變,米珠草桂,驚恐流離”[1]1126的社會環境,還要“上事孀姑,下撫孤兒”[1]1126。上蔡諸生劉用良之妻馬氏,其夫去世時她尚未及壯年,在饑荒年,不僅要為人傭“刺繡以養舅姑”[1]1134,甚至要“剪發鬻錢佐之撫二孤”[1]1134。因此,從現實利益考慮,她們的節烈行為對自身而言并沒有好處。
其三,節烈女,特別是烈女誓死守節或以死殉夫的行為明顯違背了人的求生本能。比如:西平女子賈慧恣因年少有色而被賊所執“欲以其獻其渠魁”[1]1137,她不僅沒有媚賊以求生,反而“踴躍赴火不得,遂臥地求死”[1]1137,終被賊所殺。遂平民家女王九斤,面臨霸寇的金帛之誘、刀刃之逼,不為所動,最終被剜目肢解而死。遂平王仲和之妻張菊花,面臨賊人“先奪其所抱女,貫之于槍如搖鼗皷然”的恐嚇,不僅沒有屈從,反而“恨哭罵愈勵(厲),賊怒磔之”[1]1140。此中或有被賊逼迫的成分在內,而自殺殉夫的像邑諸生張堯心妻劉氏、諸生田一方之妻王氏、諸生王民仁之妻趙氏等[1]1138-1141,則多半是自愿的。人是自然人與社會人的結合體,雖然說社會性是人在人類社會生存的根本保障,但自然人的存在才是社會人存在的前提,所以人自然屬性的第一要義即是保持個體生命的存在。顯然,烈女這種自我舍棄生命的行為方式,完全違背了這一點。
然而,種種因素并未能阻礙節烈女性采取如此的行為,這說明在其心中遠遠有比個人情感、利益、幸福甚至生命更寶貴的東西需要去堅守與維護——節烈女性觀念中的“貞節”。
三
那么節烈女們這一扭曲的貞節觀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背離人性的儒家倫理宣傳
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成為歷代王朝的正統思想。但儒家思想并非一成不變,其內涵及外延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這不僅表現在它對釋、道兩家思想的內化和融合,也表現為其自身原有思想內容的豐富和延展,以及向社會生活各個細部滲透的趨向。女性的貞節標準和觀念,就是儒家在發展其自身原有綱常倫理思想過程中形成的。
儒家思想講求的“三綱”即有“夫為妻綱”[3]一條,認為在家庭中丈夫相對于妻子起領導作用。但起初,這還只是儒家對《周易》所含陰陽觀念認知在家庭倫理秩序中的對應判斷,但到了宋代出現了將其極端化解讀的現象。程頤首倡女性“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4],朱熹不僅積極推行此說,而且進一步進行了細化[5]。在宋代,這一思想還只停留在部分理論家的頭腦層面,進入元明時期,特別是明代,由于統治者將朱熹所作《四書集注》作為科舉的參考書,且以八股取士,不準任意發揮經義,使得朱熹的思想在知識分子階層中傳播開來。當時的知識分子作為知識權威,擁有評判社會價值是非的絕對權威,他們直接推動了整體社會對女性貞節的道德要求。同時,由于貞節觀念符合了長期以來在社會中占有優勢地位的男性利益,也必然會得到大多數男子的支持和宣揚,這種社會氛圍的出現模糊了女性對自我權利的認知,而逐漸將背離人性的貞節要求視為天經地義之事,并付諸實踐。
(二)忠君愛國理念在女性中的生成
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忠君愛國主要是對男子的要求,這既是男權社會中男子的權利,也是其義務,而對女性卻較少有這樣的要求,忽視了女性在穩固政權方面的價值。隨著社會的發展,男性逐漸認識到女性在忠君報國方面的作用。特別是在戰亂動蕩時期,雖然女性少有直接在戰場上沖陣殺敵的機會,但她們當中的很多人在面臨“大是大非”時的表現甚至會超過一般的男性。同時,統治者也逐漸認可女性反抗賊寇的節烈行為,其直接表現就是在史書《列女傳》記述當中不斷擴大此種女性所占比例,這從前文所述《汝南志· 列女》收錄的貞烈女性人物的數量即可看出。這種官方認可的“精神獎勵”反過來又推動了少有出頭機會的中國古代女性不斷地投身于此,故李本固感嘆此類女子“何其盛也”[1]1156。
當然,并非所有的女子都“有幸”碰到戰亂并通過自殺式的“罵賊”④慷慨就義以入史傳,那么她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呢?統治者設計了這樣的一個途徑——守節。守節行為越極端,越容易被統治者注意到,其進入史傳的可能性就越大。在一定意義上講,這和男性的科舉有一定的類似之處,都是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通道而已。因此,很多節烈女性的行為都帶有一種表演性質,從“長號不食”[1]1130到“截發自誓”[1]1124再到“毀形容”[1]1122,從表面上看是其哀痛不已、守節決心的表現,但如果細細思索這些行為,無不是“演”給別人看的。不過,這并不是說所有節烈女的行為都是有意識的“表演”,而是說她們的這種行為在客觀上促使了其“脫穎而出”,從而會給其他女性樹立一個守節行為的基本標桿。標桿一旦樹立,許多女性就不得不朝著這個標準努力,否則便會被“淘汰”,被認為不夠貞節。
(三)律法規定的官方獎勵
理念的宣揚固然能夠激勵很多女性,但官方的現實獎勵更具有吸引力。《明史· 列女傳序》載:“明興,著為條規,巡方督學歲上其事。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井閭,乃至僻壤下戶之女,亦能以貞白自砥。”[6]這在李本固《汝南志· 列女》中有突出表現,其記錄的受官府表彰的節烈女性共有70 人,其中元代有6 人,明代有64 人。建祠祀之的如被“有詔旌表仍行,縣建烈女祠祀之”[1]1132的田臘梅,被“有詔褒旌,俱祀于‘貞節祠’”[1]1137的賈慧恣、周氏女、李明良、劉氏、左氏,被“立祠通海”[1]1147的盧氏等。獲旌表表彰的如被“詔表其門曰:‘節婦’”[1]1123的趙氏,被“旌為‘貞節’”[1]1124的范氏,被“豎坊表之,題曰:‘星月同孤’”[1]1156的麻氏等。
除了旌表之外,守節之婦女還可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明令· 戶令》載:“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后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⑤在李本固《汝南志》“列女”篇中雖未見此一具體記載,但根據古代史書編撰“常事不書”的一般原則,可以推知此種獎勵必然存在。當然,除了某些父母會因憐愛自己的女兒或貪戀財產的其夫家叔伯兄弟⑥等真心不希望其守節之外,對家族的其他人而言,犧牲其個人利益,換取整個家族的利益顯然更加合適,因此他們也成為規勸或逼迫婦女守節的重要力量。
(四)守節禁欲的女性家庭教育
在古代,女性幾乎沒有到學堂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她們所受教育的地點多局限于家庭內部,主要由其母親負責,學習一些技藝性的女工,在文化知識方面則相對缺乏。而且自漢代始,包括女性在內的中國古代早期教育主題已經出現了由禮儀向道德的轉變,并出現了偏重文化、偏重理論的傾向[7]68。到了明代,統治者對女性貞節觀的教育更為重視,其直接表現就是以官府名義編撰和頒布了一系列女教讀物。據《萬歷野獲編》載“洪武元年三月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8]71,“本朝仁孝皇后著《內訓》,又有《女誡》,至章圣皇太后又有《女訓》,今俱刻之內府,頒在宇內。今上圣母慈圣皇太后所撰述《女鑒》一書,尤為詳明典要”[8]71。加之在社會上早已流行的漢代班昭《女誡》、唐代宋若莘《女論語》及歷代《列女傳》等,以及官方對節烈觀念的提倡,使得這一價值觀念逐漸在社會上傳播開來,尤其是在家世⑦中上的家庭之中。這是因為她們有更多接受此類教育的資源和機會,所以蒙受“毒害”的可能性也更大。而這直接導致了中上層家庭出身的節烈女性在李本固《汝南志· 列女》中所占的比例很大。
單以明代來論,在李本固《汝南志· 列女》中,家世中上的節烈女性有26 位,如汝寧府知府申達之女申氏、吏部郎趙敏之女孫趙氏[1]1121等;而家世相對偏下的只有5 位,如民莊十一之妻范氏、民程秀之女程蘭香、民王尚德之妻丘氏等[1]1122;另外,還有44位沒有明確交代其家世,如夏家婦單氏、孫守貞妻申氏、胡登仕妻胡氏等[1]1123,從一些細節描寫來看,她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也絕非經濟匱乏的普通平民,如“日課子尚德讀家藏書,夜則篝燈相伴”[1]1126的蔡氏、“延師訓子”[1]1152的黃家樓妻楊氏、“撫其三歲孤,加緒向學”[1]1155的黃雍妻胡氏。由上可知,能夠做出節烈行為的必然是以中上層家世出身的女子居多,盡管李本固感嘆“我朝諸媛紅粉白刃、視死如歸、華發青燈、抱節無二,豈盡士大夫妻女哉?!即遐陬窮巷、裙布釵荊,亦有然者”[1]1156,但下層家世出身的女子投身于節烈的并不太多。
(五)易于走極端的個人因素
節烈女貞節觀的形成應該還跟個人缺乏社會經驗有關。由前文可知明代律法規定,可以獲得旌表的節烈女,是在三十歲之前亡夫,五十以后不改節的,但縱觀李書“列女”篇收錄女性,除去未經許聘即被賊所殺的,在接近三十歲亡夫的守節并不多,僅有民莊十一之妻范氏(27 歲)、李暹妻蔡氏(28 歲)、李暹之子尚德之妻詹氏(27 歲)、尚德之子麒之妻朱氏(26 歲)、諸生吾志學妻張氏(27歲)等;大部分都是在20 歲左右守寡或殉夫,如郭維藩妻祝氏(20 歲)、郝昂妻沈氏(19歲)、史嘉法之妻王氏(20 歲)等。她們雖已成年,但在古代女性較少接觸外部社會的大環境下,她們很難獲得足夠的社會經驗,以對自己的守節行為有一個比較明智的判斷。她們很容易被社會道德綁架和被女性貞節觀念哄騙,從而選擇極端手段維護自己的貞節,所以在明代以死殉節的甚至比守節孀居的人數還略多。而一旦選擇守節孀居,就會更加與社會脫離,又憚于社會道德的批判,想要放棄守節恐怕已是不能和不敢。
除上述因素之外,女性貞節觀的形成應該還有一定的地域原因。這從李本固《汝南志· 列女》收錄明代汝南13 地的節烈女性數量分布上的差異即可看出⑧,其中汝陽(含汝寧府)、遂平、固始數量最多,分別為13人、11 人、11 人;上蔡、西平、光州數量居中,分別為7 人、6 人、8 人;新蔡、確山、息縣、羅山數量較少,分別為4 人、3 人、3人、4 人;真陽、商城、信陽數量最少,只有1 人、2 人、2 人。這可能主要與各地的女性教育發展水平差異有關。
注釋:
①節烈,蓋指守節或殉節的女性,本文按其是否以生命為代價,又將其分為節女和烈女。
②我們不排除一些地方官員為了政績,虛造烈女人物的現象,但李本固收錄進傳的女性人物多已獲得官方認可,也就是說在官方層面他們是承認這些人物事跡的真實性的,所以若說其全為造假,恐亦缺乏足夠可信的證據。
③張妙秀“一日,姑病思鹿羹,秀密割左臂以進,姑食而甘之,疾果愈”。參見李本固撰《汝南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8 頁。
④如史秀妻袁氏、韓拱妻李氏、桂客妻喻氏等,參見李本固撰《汝南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5、1135、1152 頁。
⑤按:當頁龍山先生校訂曰“‘者’《箋釋》作‘至’”,應從《箋釋》。見龍山先生校訂《明令》(江都書肆,文刻堂青竹樓刻本影印本)。
⑥《明令· 戶令》載:“凡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并聽前夫之家為主。”龍山先生校訂《明令》(江都書肆,文刻堂青竹樓刻本,影印本)。
⑦稱“家世”而不稱“家庭”則是考慮到一些落魄的中上層社會成員,因為雖然其可能遭受了一時的經濟貧困,但其整個家庭的文化氛圍仍未失去。
⑧李書收錄的明代以前節烈女性數量較少,缺少可參照性,故此處暫且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