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音樂創(chuàng)作中“和而不同”音樂美學(xué)思想探析
韓霖,肖桂彬
“五四”時(shí)期之后,多種音樂思潮并駕齊驅(qū),中國(guó)新音樂的創(chuàng)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jī)遇和挑戰(zhàn)。面對(duì)國(guó)樂日漸蕭條的現(xiàn)狀,以劉天華為代表的一批作曲家認(rèn)識(shí)到國(guó)樂改進(jìn)之重要性,認(rèn)為必須要從東西方的調(diào)和與合作中探索一條新路,由此掀起國(guó)樂改進(jìn)思潮。作為國(guó)樂改進(jìn)社成員之一,趙元任在其“中國(guó)派”音樂創(chuàng)作的試驗(yàn)中,將京劇元素、中國(guó)語言聲調(diào)以及五聲化旋律等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曲調(diào),與西洋大小調(diào)體系中的功能性和聲、轉(zhuǎn)調(diào)等技法相融合,并嘗試五聲化和聲和對(duì)位,體現(xiàn)了“和而不同”的音樂美學(xué)思想。
一、“和而不同”之美學(xué)涵義
和而不同是一種具有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審美觀念,對(duì)中國(guó)文化體系的建立起著指導(dǎo)作用。“和”而不“同”思想產(chǎn)生于春秋時(shí)期,史伯首次通過對(duì)比“同”以提出“和”,用以揭示世間萬物的普遍發(fā)展規(guī)律。史伯認(rèn)為“以他平他謂之和”,只有異類相雜才能產(chǎn)生新的事物,“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同類相加只能產(chǎn)生量變而無法達(dá)到質(zhì)變,因此“和實(shí)生物,同則不繼”; 晏嬰認(rèn)為,相異事物只有經(jīng)過矛盾斗爭(zhēng)才能達(dá)到高度統(tǒng)一的“和同”,即“無過無不及”的平和狀態(tài);伶州鳩認(rèn)為“聲不平和,非宗官之所思也”,亦強(qiáng)調(diào)“平和”。綜上,“和”有兩種含義,第一是“和諧”,如史伯的“和實(shí)生物”“和六律以聰耳”中的“和”強(qiáng)調(diào)矛盾雙方的對(duì)立、統(tǒng)一,與之對(duì)應(yīng)的“同”為“一”; 第二是無過無不及的“平和”,如史伯“以他平他謂之和”、伶州鳩“和從平”中的“和”強(qiáng)調(diào)保守的平衡、統(tǒng)一,與之對(duì)應(yīng)的“平”即為“度”。1蔡仲德:《中國(guó)音樂美學(xué)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 年版,第55—57 頁。因此,和而不同既要“和諧”,又要“平和”。孔子繼承春秋時(shí)期“和”的美學(xué)思想,進(jìn)一步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認(rèn)為君子能夠與他人和睦相處,而不隨意茍同他人觀點(diǎn),揭示了孔子的為人之道,此“和而不同”的“和”與史伯“和實(shí)生物”的“和”涵義并不相同,前者講人際關(guān)系的和諧,后者講世間萬物的混雜,2邊家珍:《孔子“和而不同”考釋》,《北京日?qǐng)?bào)》2012 年11 月26 日,第019 版。然而兩者都反映了對(duì)立、統(tǒng)一的一般矛盾概念。因此,“和”的精神就是要協(xié)調(diào)“不同”,達(dá)到新的統(tǒng)一。
“五四”時(shí)期,隨著學(xué)習(xí)西樂思潮的興起,“和而不同”使我們進(jìn)一步認(rèn)識(shí)到中西音樂的對(duì)話、交流和相互補(bǔ)充的重要性。趙元任作為國(guó)樂改進(jìn)社成員之一,他認(rèn)識(shí)到中西樂之差異,并在音樂創(chuàng)作中將中西音樂元素相互融合。有人認(rèn)為,趙元任在音樂創(chuàng)作中“有意淡化西洋和聲功能”,3吳艷、戴雄:《趙元任歌曲創(chuàng)作新論》,《中國(guó)音樂學(xué)》2008 年第2 期,第122 頁。或有人說他的作品“歐化”,4趙元任:《新詩(shī)歌集·序》,《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122 頁。這些評(píng)論具有一定片面性和主觀性,筆者認(rèn)為,趙元任將中西音樂之異同進(jìn)行分析,指出中國(guó)音樂“不及”西樂之處,這本身是站在十分客觀的角度,若今天加之主觀內(nèi)容評(píng)論其音樂作品,顯然有失偏頗;另外,《趙元任歌曲創(chuàng)作新論》一文中還提到,《勞動(dòng)歌》中采用“類似大齊奏的鋼琴與人聲寫法,流露出作者有意淡化西洋和聲功能……”,“大齊奏”本是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中常有的演奏形式,與“西洋和聲功能”似乎不可相提并論。總之,從客觀角度講,趙元任既不是有意模仿也不是有意淡化西洋音樂,而是本著“和而不同”的音樂美學(xué)思想,在諸多國(guó)樂與西樂的“普遍成分”中求“中國(guó)音樂的特性”。正如在《新詩(shī)歌集·序》中所言,“無論是什么藝術(shù),都用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原則。”5趙元任:《新詩(shī)歌集·序》,《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109 頁。
二、對(duì)“不同”的闡釋
趙元任所理解的“不同”有二,一是“不同的不同”,二是“不及的不同”。6趙元任:《新詩(shī)歌集·序》,《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114 頁。“不同的不同”為“國(guó)性”,例如,七聲音階和十二律理論是國(guó)樂和西樂共有的,但論起風(fēng)格和用法來卻相差甚遠(yuǎn),“根據(jù)五度相生法所得的中國(guó)古典音階C-D-E -#F -G -A -B”實(shí)為中國(guó)的雅樂音階或稱“正聲音階”“古音階”,是因?yàn)榧尤胱儚张c變宮,而放到西方則為利底亞調(diào)式,因?yàn)樗鼜?qiáng)調(diào)增四度音程。他曾以《湘江浪》為例談到中西調(diào)式體系之間的矛盾: 第一點(diǎn),按照西方的音樂分析法,由于本位B 的存在,此旋律應(yīng)為G“米索利地安調(diào)式”,但是以首調(diào)唱名唱旋律,反復(fù)出現(xiàn)的是re 而不是sol;第二點(diǎn),“目前普遍使用的這個(gè)‘西方體系’—合、四、乙、上、尺、子、工、凡,總要產(chǎn)生一般的大調(diào)式”,但是,“聽上去像do,re,mi 的音是‘上、尺、工’而不是‘合、四、乙’,因此隨后的就是凡音fi”。7趙元任:《關(guān)于中國(guó)音階和調(diào)式的札記》,《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48—50 頁。這是中西調(diào)式體系之“不同”;國(guó)樂強(qiáng)調(diào)“正聲”即五聲,多用作旋律主干音,其它“變聲”多用作裝飾音,而西樂七聲音階中的每個(gè)音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當(dāng)然,趙元任并不排斥使用七聲音階做調(diào),這在其作品中隨處可見,這是對(duì)七聲音階用法的“不同”。其他“不同的不同”如花音、滑音以及中國(guó)的樂器七弦琴等,這些都是值得保存與發(fā)展的。
“不及的不同”算不上是國(guó)性,如曲式結(jié)構(gòu)、和聲、復(fù)調(diào)以及管弦樂隊(duì)等,這是國(guó)樂“不及”西樂之處。面對(duì)“不及的不同”,趙認(rèn)為,“咱們得在音樂的世界上學(xué)到了及格的程度,然后再加個(gè)人或是中國(guó)的特別的風(fēng)味在上,作為有個(gè)性的供獻(xiàn)。”8趙元任:《新詩(shī)歌集·序》,《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116 頁。趙所提出的“不同的不同”和“不及的不同”實(shí)為兩層矛盾,一是音樂內(nèi)部各要素所存在的中西之“異”; 二是國(guó)樂對(duì)西樂體系借鑒與否或如何借鑒的矛盾。這就要求首先辨別異同,其次在“同”中求“不同”,又在“不同”中求得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從而促進(jìn)國(guó)樂的發(fā)展,這也是“和”之本意。
三、曲調(diào)、和聲之“和”
“和實(shí)生物”“和樂如一”,“和”是合規(guī)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tǒng)一,是對(duì)“不同”的超越。通過比較異同認(rèn)識(shí)到“不同”之處,這是“和”的必經(jīng)之路,因此,“和”是“不同”的最終目的,音樂正是按照“和”的規(guī)律而構(gòu)成矛盾統(tǒng)一體,音樂之美就在于此。
(一)詞曲之“和”
趙元任作為一位語言學(xué)家,他深知中國(guó)語言規(guī)律,并將中國(guó)語言中的字音和聲調(diào)融入曲調(diào)當(dāng)中,形成其獨(dú)具特色的旋律創(chuàng)作手法。在其與青主討論“《金縷衣》中‘取少’兩字聽起來像一個(gè)詞”的問題中,趙元任以詞曲結(jié)合的角度認(rèn)為,曲調(diào)不但要合乎字的輕重音,還應(yīng)合乎語氣和聲調(diào),而青主則認(rèn)為樂歌“如果受了字音的限制”,就沒有“樂的獨(dú)立的生命”,因此“寧可以曲害文,決不宜以文害曲”。9趙元任:《討論作歌的兩封公開的信》,《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60 頁。表面來看,兩者的看法是相悖的,一個(gè)寧可以文害曲,另一個(gè)寧可以曲害文,但趙在其后又提到,“說話與唱歌的關(guān)系……是很難分清楚的……假如能更加注意到這幾種成分是怎樣以種種辦法配合在一起的,就可以欣賞它……是如何產(chǎn)生中國(guó)的語言、文學(xué)、音樂作品出來”。10趙元任:《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12 頁。他依然承認(rèn)詞曲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只是在詞曲矛盾之中追求內(nèi)在的統(tǒng)一,就像他在論述節(jié)奏與音調(diào)時(shí)所說的,“熟為主要?jiǎng)t視其所表樂意而定”,凸顯其追求“和”之美的精神。
趙元任認(rèn)為在音調(diào)方面存在著兩層矛盾,第一是中西語言中聲調(diào)的差異:中西都須講究“字的輕重音”,這是“同”;外國(guó)更加注重輕重音卻沒有中國(guó)語言中的平上去入,這是“不同”。憑這點(diǎn),外國(guó)“什么字都可以怎么唱”,而中國(guó)音樂“平上去入要是配的不得法,在唱時(shí)不免被歌調(diào)兒蓋沒了”,這應(yīng)該可以說是國(guó)樂與西樂之間“不同的不同”了,但是“中國(guó)現(xiàn)代的作曲家,多半是不受任何歌詞聲調(diào)的限制”,11趙元任:《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12 頁。直至今天看來,還是不免覺得可惜! 第二是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過程中字音與樂調(diào)之間存在的矛盾。在趙的旋律創(chuàng)作中,“凡是文一些兒或是正經(jīng)一點(diǎn)兒的歌詞,大致是平聲低或者是往下來,仄聲高或者是往上走”,12趙元任:《關(guān)于我的歌曲集和配曲問題——答李抱忱來信》,《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53 頁。如《聽雨》中,“北地”采用上行的旋律,“半年”采用先上行后下行的旋律; 又如《相見歡》中,“古人長(zhǎng)想長(zhǎng)想長(zhǎng)想長(zhǎng)想無窮”,幾個(gè)“長(zhǎng)想”均采用平低仄高的寫法。但也并不完全是平低仄高,有時(shí)也會(huì)脫離聲調(diào)的限制依曲逆字,如《春風(fēng)輕輕吹》中,“花園里”三字為平平仄,“里”字卻低下來,這大概是為了與前句“輕輕吹”的曲調(diào)相呼應(yīng); 又如《老天爺你年紀(jì)大》中第一句“老天爺”三字,“天爺”二字的音調(diào)卻高于“老”字,這是為了加強(qiáng)語氣,抒發(fā)不滿之情。無論是依字作曲還是以曲逆字,實(shí)際都是對(duì)詞曲矛盾的協(xié)調(diào),也正是“詩(shī)樂分離”的存在,才能達(dá)到“詩(shī)樂共融”的高度統(tǒng)一。13江江:《中國(guó)吟詩(shī)調(diào)與西洋和聲——趙元任<小詩(shī)>詞曲及和聲配置》,《音樂藝術(shù)》1999 年第1 期,第58 頁。
(二)中西曲調(diào)之“和”
趙元任認(rèn)為,中國(guó)的宮、商、角、徴、羽五聲音階,有點(diǎn)像“中國(guó)的diatonic 音階”,不同于西方的七聲diatonic,比如在使用?到5 的經(jīng)過音時(shí),西方往往采用“?765”或“”,而在中國(guó)五聲音階里,盡可以用“”; 在裝飾音的使用方面,西方要用“676”,而按中國(guó)的diatonic 音階,則為“”,這可算作中西曲調(diào)方面的“不同的不同”了。
既然國(guó)樂與西樂都有十二律和七聲音階的情況,那么使用五聲音階作調(diào)兒就可以算作是中國(guó)風(fēng)味。趙元任在旋律創(chuàng)作中將西洋曲調(diào)與中國(guó)風(fēng)味的曲調(diào)相互融合,形成中西曲調(diào)并置。《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旋律大半是“中國(guó)派”的,而“枯樹在冷風(fēng)里搖,野火在暮色中燒”一句采用e 和聲小調(diào)作旋律,形成調(diào)式上的強(qiáng)烈對(duì)比;《湘江浪》《勞動(dòng)歌》中,將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宮調(diào)式( 趙元任稱利底亞調(diào)式) 與西方大小調(diào)式相融合,五聲音階作骨干音,升高的四度音作外音處理;“中國(guó)用‘’這個(gè)動(dòng)機(jī)的很多”,《賣布謠》中“嫂嫂織布”一句,以“”三音組成并貫穿全曲,其變形分別為“563”“”“235”等,且在結(jié)尾處采用“”結(jié)束,完全不同于西方“diatonic”中的主音傾向,但旋律中也并不都是“中國(guó)派”的,在講“洋貨”時(shí),他加入西方的小調(diào)旋律“3#4#56”“23#45”形成五聲化的旋律與西洋大小調(diào)的旋律并置,使中西曲調(diào)在碰撞與對(duì)比中相互融合。
(三)中西和聲之“和”
“中國(guó)的音樂程度不及外國(guó)的地方……關(guān)鍵就在個(gè)和聲方面”,趙元任曾將和聲比作“山水橫披”,認(rèn)為單音音樂缺了和聲便沒有多少發(fā)展的余地了,以此強(qiáng)調(diào)和聲在音樂中的地位,但由于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沒有和聲、和弦的概念,所以缺乏一套完整的和聲體系,“當(dāng)然是只有用西樂的和聲法”。14趙元任:《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117—118 頁。趙元任對(duì)西方和聲法的借鑒,為“中國(guó)派”和聲創(chuàng)作尋了一條新路。
趙元任認(rèn)為“五聲和聲的范圍比七聲和聲至少要小幾百倍……還是得取用全部十二律的音作為和聲的原料,偶爾用五聲派的和聲算是中國(guó)的色彩”,15趙元任:《中國(guó)派和聲的幾個(gè)小試驗(yàn)》,《趙元任音樂論文集》,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4 年版,第72 頁。形成了七聲音階的五聲化;他還在調(diào)式和聲中加入調(diào)性表情,“突破了民族音樂很少轉(zhuǎn)調(diào)的常規(guī)”,16賀綠汀:《趙元任音樂作品全集·序》,《趙元任音樂作品全集》,上海音樂出版社1987 年版,第1—2 頁。其調(diào)性布局手法以平行調(diào)式交替、近關(guān)系轉(zhuǎn)調(diào)和三度關(guān)系轉(zhuǎn)調(diào)為主。《上山》調(diào)性布局為bB -G -B,轉(zhuǎn)調(diào)手法主要為調(diào)性并置,強(qiáng)調(diào)調(diào)性色彩對(duì)比,并多次采用平行調(diào)式交替手法; 《嗚呼! 三月一十八》為bD 大調(diào)與#c 小調(diào)的并置; 《瓶花》中多次采用下屬和屬方向的離調(diào); 《海韻》中主要采用平行調(diào)交替和三度關(guān)系轉(zhuǎn)調(diào)手法;《教我如何不想他》以近關(guān)系轉(zhuǎn)調(diào)為主等等,對(duì)西方轉(zhuǎn)調(diào)手法的借鑒,為中國(guó)風(fēng)味旋律的發(fā)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并加強(qiáng)音樂的表情性和對(duì)比性。
在對(duì)西方和聲體系的借鑒過程中,趙元任將三度疊置結(jié)構(gòu)和弦與五聲縱合性結(jié)構(gòu)和弦相結(jié)合,將調(diào)式化和聲進(jìn)行與功能和聲進(jìn)行相結(jié)合,形成中西和聲并置。《湘江浪》中多處采用五聲化對(duì)位,以及“四度三音列式、四五度式”17參見桑桐:《五聲縱合性和聲結(jié)構(gòu)的探討》,《音樂藝術(shù)》1980 年第4 期,第20—44 頁。等五聲縱合結(jié)構(gòu)和弦,但在和聲終止處采用G 商調(diào)式的主—屬—主和弦進(jìn)行,低音為d -g 的四度強(qiáng)進(jìn)行,功能性明顯;《望郎歸》中,和弦以三度疊置為基礎(chǔ),和聲進(jìn)行以主屬交替為主,而在第九小節(jié)插入五度四音列式和弦。這種并置手法,使中西和聲在碰撞與沖突中得到融合。
(四)中國(guó)曲調(diào)與西洋和聲之“和”
趙元任將中國(guó)派的旋律與大小調(diào)體系和聲相融合。江蘇蘇州民歌《孟姜女》旋律為D徴雅樂調(diào)式,和聲配置以三度疊置和弦為基礎(chǔ),“別人家”和聲進(jìn)行為三級(jí)到六級(jí)和弦,具有民族風(fēng)味,緊接“夫妻”二字,采用屬到主的進(jìn)行強(qiáng)調(diào)功能性;曲調(diào)與和聲的對(duì)位也十分講究,“點(diǎn)紅燈”的“紅”字字頭為下方屬和弦的外音,但緊接又成為字尾和聲的和弦音,“別人家”的“人”字、“夫妻”的“夫”字尾音及“團(tuán)圓”的“圓”字尾音亦是如此,形成五聲化的中國(guó)民間曲調(diào)與西洋三度疊置和聲的“對(duì)話”。鋼琴曲《偶成》第一部分的主題旋律采用G 宮五聲調(diào)式,和聲配置為G 大調(diào)主和弦與下屬和弦交替進(jìn)行;《教我如何不想他》中,頭三句“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曲調(diào)為京劇唱腔,最后一句的和聲配置采用-D7-T 的終止式,這形成了中國(guó)民間曲調(diào)與功能和聲進(jìn)行的融合。在融合過程中,還形成了對(duì)傳統(tǒng)西洋和聲的突破,如平四平五度進(jìn)行: “2321”對(duì)“6561”,“565”對(duì)“123”等,以及小小七和弦的使用,“似乎西洋味少一點(diǎn)”。
結(jié) 語
趙元任采用辯證的眼光看待國(guó)樂與西樂之間的矛盾,面對(duì)國(guó)樂與西樂之“不同的不同”,他保留中國(guó)音樂的特性; 而面對(duì)國(guó)樂與西樂之“不及的不同”,則大膽借鑒西洋音樂體系。在詞曲矛盾方面,趙元任將中國(guó)語言聲調(diào)、吟詩(shī)調(diào)與歌曲旋律相融; 在音階與調(diào)式方面,將七聲音階五聲化,使中西風(fēng)格的曲調(diào)相融;在和聲方面,將三度疊置結(jié)構(gòu)和弦與五聲縱合性結(jié)構(gòu)和弦相結(jié)合、調(diào)式化和聲進(jìn)行與功能和聲進(jìn)行相結(jié)合,使中西和聲相融;此外,還將中國(guó)民間歌曲曲調(diào)配置西洋大小調(diào)和聲,形成中國(guó)民間曲調(diào)與西洋三度疊置和聲的“對(duì)話”。其“中國(guó)派”音樂的創(chuàng)新之處,正是“和而不同”之必然結(jié)果。
音樂的“時(shí)代性”要求音樂必須要發(fā)展,這也正是“五四”時(shí)期愛國(guó)人士力圖振興逐漸衰落的國(guó)樂之根本原因。然而,究竟如何發(fā)展中國(guó)音樂,仍是當(dāng)今我們需要面臨的現(xiàn)實(shí)問題。現(xiàn)如今,西方音樂體系對(duì)中國(guó)音樂的影響已根深蒂固,西方的作曲技法以及音樂分析方法早已“教科書式”地印在腦海之中,然國(guó)人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以及自己本民族音樂的認(rèn)知卻日趨局限,這是急需國(guó)人反思的。在當(dāng)前文化背景下,只有堅(jiān)持文化自信,才能在世界舞臺(tái)中展現(xiàn)中華民族精神,同樣,賦予音樂以“民族性”內(nèi)容也正是中國(guó)音樂發(fā)展的重中之重。音樂作為一種文化載體,承載著強(qiáng)大的精神力量,我們是否應(yīng)善于借助這種力量,讓中國(guó)音樂面向世界,傳遞中國(guó)聲音,講好中國(guó)故事,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中國(guó)的音樂。筆者認(rèn)為,這或許才是趙元任先生“和而不同”思想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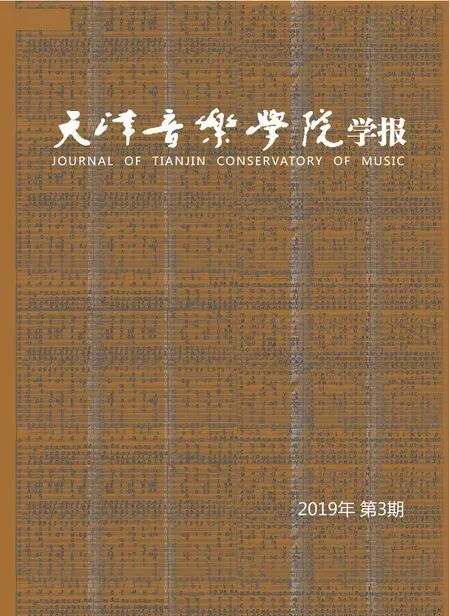 天津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9年3期
天津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9年3期
- 天津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學(xué)術(shù)交流活動(dòng)
- 弘揚(yáng)傳統(tǒng)音樂文化 培養(yǎng)民樂指揮人才
——香港中樂團(tuán)2019第十一屆國(guó)際中樂指揮大師班側(cè)記 - 南島印象
——古箏協(xié)奏曲《黎之引》演奏與創(chuàng)作探析 - 中小學(xué)開展移動(dòng)音樂學(xué)習(xí)的可行性研究
——基于學(xué)生、教師、家長(zhǎng)的態(tài)度與需求 - 《電腦制譜》課程教學(xué)中音樂形態(tài)的視覺美感表達(dá)及創(chuàng)意性研究
- 點(diǎn)、線、面“三重奏”:由“單音”技術(shù)引發(fā)的幾何結(jié)構(gòu)風(fēng)格
——以古拜杜麗娜神圣簡(jiǎn)約主義音樂《三重奏》第一樂章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