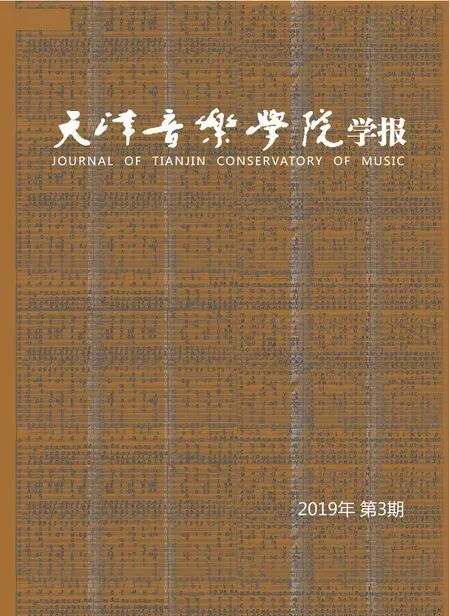先秦古琴弦數考
張艷輝,曾芳
關于古琴的起源,古籍文獻中說法不盡相同,如蔡邕認為古琴為伏羲所造,而桓譚則認為是神農所造,也有唐堯、虞舜,要之不出圣人制琴之說,這就有點撲朔迷離的意味了,對此,歷代并無不刊之論。然而,古人未必盡然說謊,如同史家之述歷代圣王,總要加上一些神秘因素才能凸顯其與眾不同的天命與功績。以此類比,古琴在中國傳統樂器中的尊崇地位亦可想見。在先秦時期各種文獻中,“琴”之意象屢次出現,如《詩經》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1程俊英:《詩經注析》,中華書局1991 年,第5 頁。( 《周南·關雎》)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鄭風·女曰雞鳴》) 《尚書·益稷》:“搏拊琴瑟以詠。”2李民:《尚書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49 頁。《左傳·昭公元年》:“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5 年,第1222 頁。多統稱為“琴”,而根據文獻資料,除此之外,還有大琴、中琴、小琴以及頌琴等稱謂,不同稱謂弦數又有不同。
關于古琴的弦數問題,目前學術界僅有黎國韜、周佩文的《“琴棋書畫雜考”之二——古琴弦數考略》指出: “歷史上至少出現過‘無弦、一弦、兩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十弦、十二弦、十三弦、十五弦、二十弦、二十五弦、二十七弦’等十四種弦數。”4黎國韜、周佩文:《“琴棋書畫雜考”之二——古琴弦數考略》,《文化遺產》2017 年第1 期,第135 頁。綜論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古琴弦數。就先秦時期的古琴弦數來說,這篇文章的論說不夠詳細,有些問題亦有待商榷,如二十七弦琴等問題。本文運用地下材料與文獻記載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來研究先秦時期古琴不同名稱及弦數的淵源,厘清先秦時期五弦琴、七弦琴、十弦琴、十三弦琴乃至二十弦琴、二十五弦琴之間的關系。
一、大琴、中琴、小琴
關于大琴與中琴的概念較早出現于《禮記·明堂位》,其云: “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也。”5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397 頁。四代即指虞、夏、殷、周。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樂考》卷一百三十七注曰: “古人之作樂,聲應相保而為和,細大不逾而為平。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后大者不陵,細者不抑,五聲和矣。”6( 元) 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1986 年,第1211 頁。指出大琴必以大瑟配之,而中琴需以小瑟配之。這也正好契合先秦時期文獻記載中琴瑟常常同時出現的現象。對此,陳旸《樂書》云: “《書》曰: ‘琴瑟以詠’,《大傳》亦曰: ‘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爾雅》曰: ‘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7( 宋) 陳旸:《樂書》卷一百十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說: “《鄉飲·酒禮》: 《禮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詩》曰‘并坐鼓瑟’,‘何日不鼓瑟’。《傳》言趙王為秦鼓瑟。皆不及琴者,以瑟見琴也。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不及瑟者,以琴見瑟也。”8同上注。指出二者的共存關系,古書中琴、瑟二字往往相亂也是這種原因。這里的重點是大琴、中琴概念的提出。
關于大琴的功用,《尚書·益稷》云: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大傳》云:“古者,圣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9( 清)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1986 年,第122 頁。由此可見,升歌即在祭祀、宴會登堂演奏樂歌時用大琴、大瑟。
關于大琴的弦數,文獻記載基本一致。《爾雅·釋樂》云: “大琴謂之離。”郭璞注云:“琴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10( 晉) 郭璞:《爾雅注》,四部備要漢魏古注十三經本,中華書局1998 年,第53 頁。清人郝懿行《爾雅義疏》云: “郭注作二十七弦,疑與大瑟相涉而誤也。汪中據《宋書·樂志》校,‘七’字衍,去之是矣。然《通典》已引作‘二十七弦’,則自唐本已然。”11( 清) 郝懿行:《爾雅義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718 頁。根據汪中對《宋書·樂志》的校對,郝氏以郭注“七”字為衍文,當是。由此,大琴二十七弦之說應當是錯誤的。另外,唐代徐堅《初學記》引《樂錄》: “大琴二十弦,今無此器。”12( 唐) 徐堅:《初學記》,中華書局2004 年,第385 頁。宋代《太平御覽》引《爾雅注》云:“大琴曰離,二十弦。”13( 宋) 李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 年,第2602 頁。均以大琴為二十弦。此外,關于大琴的長度,也是沒有異議的,《史記·樂書》: “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14( 漢)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 年,第1236 頁。唐李賀《聽穎師彈琴歌》: “古琴大軫長八尺。”15( 唐) 李賀著,( 清) 王琦等評注:《三家評注李長吉詩歌》,中華書局1998 年,第185 頁。宋代聶崇義《三禮圖》: “大琴長八尺一寸。”16( 宋) 聶崇義:《三禮圖》,宋淳熙二年刻本。宋陳旸《樂書》云:“其長八尺一寸,正度也。或以七尺二寸言之。”17( 宋) 陳旸:《樂書》卷一百二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由此可見,古人關于大琴的概念是比較明晰的18關于琴長,清代黃以周認為《禮書通故·名物通故》: “琴體之長短相較,必微有參差,而其聲則無弗同。”同時,他指出,古琴的長度是與琴隱( 即所謂岳山) 的高低相關的,此不贅述。。
厘清大琴的概念,則中琴和小琴也就順理成章了。宋代陳旸《樂書》言: “蓋五弦之琴,小琴之制也; 兩倍之而為十弦,中琴之制也。四倍之而為二十弦,大琴制也。”19( 宋) 陳旸:《樂書》卷一百十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指出小琴為五弦,中琴十弦,大琴二十弦,而弦數雖多少不同,要之本于五聲。又云: “小者五弦,法五行之數也;中者十弦,大者二十弦,法十日之數也。”這一論述后人也未有疑義并且多引此論。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先秦時期的大琴二十弦,中琴十弦,小琴五弦。
就出土文物來說,廣泛為人注意的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除此之外,還有湖北棗陽九連墩出土的戰國初期的十弦琴,學術界的焦點是半箱琴與全箱琴,而對于十弦琴與七弦琴的淵源判定則頗為一致。如日本的岸邊成雄認為十弦琴是七弦琴的祖型20轉引自王清雷:《曾侯乙墓音樂考古綜述》,《中國音樂考古八十年》,上海音樂出版社2012 年。; 丁承運則認為十弦琴是五弦發展為七弦的過渡琴制;21丁承運:《曾侯乙墓十弦琴調弦與演奏法探索》,《鐘鳴寰宇——紀念曾侯乙編鐘出土30 周年文集》,武漢出版社2008 年。王清雷在評價曾侯乙墓十弦琴時說: “對十弦琴作為七弦琴的先祖的認同,使古琴史有了提前千年的實物證據。”22王清雷:《曾侯乙墓音樂考古綜述》,《中國音樂考古八十年》,上海音樂出版社2012 年。當然,無可否認的是,十弦琴確實是七弦琴的先祖之一,而十弦琴與七弦琴亦同時并存于先秦時期。
那么,文獻中記載的中琴,能恰好對應曾侯乙墓或九連墩的十弦琴,李純一認為曾侯乙墓十弦琴為實用器23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448 頁。,由此可見,二者可以互相佐證。關于中琴的長度,王邦直《律呂正聲校注》云:“四尺五寸,三尺九寸為中琴。”24( 明) 王邦直:《律呂正聲校注》卷三十八,中華書局2012 年,第353 頁。其長度也明顯與后世的七弦琴不同。
關于小琴即五弦琴,以舜鼓五弦之琴的典實最為著名。《淮南子·泰族訓》即云:“舜為天子,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25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 年,第1399 頁。《韓非子》《禮記·樂記》《史記》等均有相關記載。據文獻記載,五弦琴長三尺六寸六分,這與后來的七弦琴長度基本一致。在出土文物方面,1978 年湖北隨州出土了戰國時期的五弦琴,有人認為這就是典籍中所謂“五弦琴”,黃翔鵬則認為其為“均鐘”,功用是為編鐘調律的音高標準器26黃翔鵬:《均鐘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的研究》,《黃鐘》1989 年第1、2 期。。除此之外,五弦琴尚無出土實物佐證。然而,五弦琴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頻繁出現,足夠說明其確實存在。
二、頌琴
在大琴、中琴與小琴的系統之外,還有頌琴。關于頌琴的記載,于《左傳》可得兩條。第一,《左傳·襄公二年》: “初,穆姜使擇美,以自為櫬與頌琴。”27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5 年,第920 頁。第二,《左傳·襄公十八年》:“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2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5 年,第1039 頁。清人惠棟曰:“公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29( 清) 惠棟:《惠氏春秋左傳補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惠氏認為此處的公琴即頌琴。對于頌琴的功用,晉杜預注: “頌琴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30( 晉) 杜預注,( 唐) 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 年,第227 頁。杜預的注來看,頌琴的功用是殉葬。清人徐乾學在其《讀禮通考》云: “頌琴,明器之屬。”31( 清) 徐乾學:《讀禮通考》,清錢塘飛鴻堂刻本。界定其明器的屬性。這一殉葬屬性無論是杜預還是徐乾學,其觀點是一致的。
關于頌琴的弦數與形制,《左傳》中并未提及,直到宋代陳旸《樂書·雅部》在“七弦琴”條目下云:“至于弦數,先儒謂伏犧蔡邕以九,孫登以一,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三。”34( 宋) 陳旸:《樂書》卷一百二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里的頌琴,即屬于古琴系統,有十三弦。
但需要提出的是,在陳旸的《樂書》中還有一條關于頌琴的似是而非的記載,并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樂書·俗部》“頌琴”條目說:
古之善琴者八十余家,各因其器而名之,頌琴居其一焉。其弦十有三,其形象箏,移柱應律,宮縣用之,合頌聲也。齊桓公以號鐘名之; 李汧公以韻磬名之,是不知鐘磬各自有器,非所以名琴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鐘磬名琴,豈孔子正名之意乎?35( 宋) 陳旸:《樂書》卷一百四十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很顯然,陳旸與杜預相同,將頌琴歸入七弦琴的系統之內。從整段話的描述來看,陳旸以為頌琴是以“頌”為琴名,這一點與杜預是一致的,并以齊桓公的“號鐘”、李勉的“韻磬”的以鐘、磬為琴名為例。同時,“其形象箏”,僅就形制與箏對比,并未言明其形即箏,這一點是尤其要注意的,這也是導致后世誤認為頌琴即箏的根源。元代馬端臨收錄了陳旸的說法,也認為頌琴十三弦。由于馬端臨《文獻通考》在學術界的巨大影響力,后人大多延續了陳旸和馬端臨的說法,以頌琴為十三弦。
這里還需要考辨的一點是,楊伯峻注《左傳》中所謂的頌琴二十五弦是錯誤的。楊伯峻注《左傳》云: “據宋聶崇義《三禮圖》,頌琴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穆姜制此以殉葬。”36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5 年,第920 頁。然而,無論是清康熙十二年通志堂刻本,還是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的聶崇義《三禮圖》,這段話都說的是“頌瑟”,而非“頌琴”,顯然,楊伯峻將琴瑟二字混淆了,由此,頌琴二十五弦之說亦誤。
也正是由陳旸開始,關于頌琴,歷代都維持了十三弦的說法,如宋代段昌武的《毛詩集解》,認為頌琴當屬于七弦琴系統,并且說:“檿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昆山之玉,聲不過五。五弦之琴,小琴也;兩倍之為十弦;四倍之為二十弦,大琴也。孫登以一弦,則聲或不備; 蔡邕以九弦,則聲或太多; 至于全之,為郭璞之二十七; 半之為頌琴之十三,皆出于七弦,倍差溺于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也。”37( 宋) 段昌武:《毛詩集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代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清代俞樾《茶香室四鈔》、秦蕙田《五禮通考》等皆襲用陳旸的說法。那么,頌琴十三弦是無爭議的。
三、七弦琴及其他
漢代揚雄《琴清英》:“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38( 清)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 年,第421 頁。認為七弦是堯帝在五弦的基礎上增加二弦而成。而桓譚《新論·琴道》則認為: “五弦,第一弦為宮,其次商、角、徴、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為少宮、少商。下徵七弦,總會樞要,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39( 漢) 桓譚:《新論·琴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63 頁。認為是周文王、周武王各加一弦。應劭《風俗通義·聲音》卷六:“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為君,小弦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40( 漢) 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 年,第193—194 頁。蔡邕《琴操》亦認為是文王、武王各加一弦。無論如何,上述皆以為七弦琴是在五弦的基礎上增加二弦而成,指出五弦琴與七弦琴的關系。關于七弦琴,文獻多有記載,所記形制大體相同,此不贅述。同時,1993 年湖北荊門郭店一號墓戰國中期七弦琴的出土也證實了先秦時期七弦琴的存在。另外,長沙袁家嶺燕子山亦發掘出土了一件戰國晚期的七弦琴,其形制與長沙馬王堆七弦琴相似41丁承運:《漢代琴制革故鼎新考——出土樂俑鑒證的滄桑巨變》,《紫禁城》2013 年第10 期,第48 頁。。
除了十弦琴與七弦琴之外,1980 年湖南長沙五里牌戰國晚期楚墓出土了一張彩繪琴。章華英將其暫定名“九弦琴”42章華英:《古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90 頁。。李純一先生則以為:從龍齦上九道不明顯的弦痕來看,有可能為九弦,也有可能略多或略少于九弦43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448 頁。。故此,五里牌楚墓出土古琴的弦數目前不能確定。此外,尚不能確定弦數的還有湖北棗陽郭家廟出土的春秋早期的古琴,為半箱琴,弦孔若干,應當是年代最早的出土實物44劉修兵:《湖北棗陽郭家廟墓地考古新進展——發現中國最早的琴和瑟》,《中國文化報》2016 年5 月9 日,第8 版。。
總之,就現有考古資料以及文獻資料來說,先秦時期的“琴”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其實遠遠大于漢代以后的“琴”的概念。大琴、中琴、小琴與頌琴弦數不等,功用也不相同,演奏場合亦不盡相同。除了頌琴之外,琴瑟幾乎如影隨行,是樂隊中的合奏樂器,即所謂“堂上之琴瑟,堂下之鐘磬”。戰國以降,琴瑟合奏除用于廟堂之外逐漸消亡,琴也隨之獨立,進而成為“進御君子”之器。在這種演進過程中,古琴漸至定型,雖然也有宋代的九弦、十三弦的改革嘗試,但卻以失敗告終,七弦成為古琴的固定形制。正如明代王邦直所說:“《韓詩外傳》曰:‘伏羲琴長七尺二寸,應七十二候。’即二十弦琴也,然今之所用者七弦足矣,其余俱廢可也。”45( 明) 王邦直:《律呂正聲校注》卷三十九,中華書局2012 年,第363 頁。可聊備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