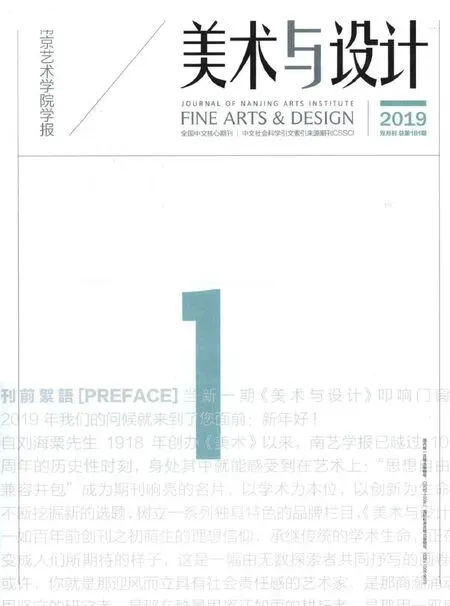留日書畫家與印象派在中國的初期傳播(1905-1912年)
方 茜(上海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上海 200072)
本文所關注的印象派繪畫,涵蓋法國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以及法國印象派的日本變體“外光派”油畫等多種繪畫形態。它們在中國的初期傳播由少數留日書畫家通過期刊美術譯述予以開啟,從1905年初現,到1912年左右獲得相對集中的呈現。此后相關傳播陷于沉寂,直至1917年復蘇①民初中國文化教育界經歷了蔡元培推出“美育”政策(1912),以及袁世凱取消“美育”(1915)等一系列重大起伏,其波動狀態對印象派繪畫在中國的跨文化傳播也造成一定影響。參見蘇云峰.中國新教育的萌芽與成長(1860-1928)[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19-39頁。,并加強了與中國藝術界的交流互動。
印象派繪畫在近現代中國的跨文化傳播,關乎近現代中外藝術交流、中國現代藝術發展等重大問題,近年來中國美史學界已就此給予一定關注,并積累了重要的研究基礎。整體而言,現有相關研究往往對20世紀20-30年代印象派在中國傳播推進問題,即,相關傳播與中國美術教育相交織,并逐步推進至藝術創作、展覽等領域的情形著墨較多,[1][2]但是對于清末民初印象派在中國的初期傳播狀況則缺乏深入的探究。現有研究大多僅述及美術留學生對印象派傳播的開啟之功,或者將初期傳播狀況概述為“由支離破碎到逐漸清晰的過程”。[3]不僅如此,現有相關研究的歷史觀也頗受“沖擊-反應”模式限制,誤以“中國繪學衰敗論”②1917、1918年,康有為、陳獨秀先后闡發“中國繪學衰敗論”“美術革命論”,相關言論曾被不少研究者視為近現代中國藝術史研究的重要前提。但是近年來,已不斷有藝術史研究者指出,康、陳言論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20世紀中后期的近現代中國美術史寫作。參見李偉銘.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一樁“公案”及其相關問題[J].美術研究,1997(3).為前提預設,偏重于強調印象派傳播對中國現代油畫發展的引領作用,忽略了相關傳播與中國傳統書畫界交流互動的具體情景,以及傳統畫界為推進中外藝術交流、中國藝術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這也導致現有研究就印象派傳播對中國現代藝術發展的實際影響,尚未形成客觀評價。
鑒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國中心歷史觀,聯系清末民初中國社會文化語境,深入考察印象派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問題(1905-1912年),通過爬梳涉及相關傳播的期刊文本,揭示那些兼具留學生、傳統畫人、現代報人等多元身份的傳播者,如何依據各自的習藝經歷、學識背景,就印象派繪畫形成不同的價值判斷、傳播策略,如何借助對外交流經驗,形塑自身的中西藝術比較觀、中國藝術發展觀,如何探索傳統繪畫發展創新道路,同時嘗試于世界藝術場域中確立中國藝術的獨特定位,由此,本文力圖澄清“中國藝術現代轉型不僅受到印象派等外來藝術傳播的積極影響,更由中國藝術傳統內生的現代發展趨向所主導”這一重要歷史實相,并為近現代中國美術史研究貢獻新的史料與有價值的思考路徑。
一、李叔同:點到即止與中西藝術觀變異
書畫家李叔同較早留日習藝,不僅是最早運用期刊媒介傳播印象派信息的先行者,而且不乏相關繪畫創作經驗,但他卻一再以“點到即止”的方式簡略帶過印象派油畫信息,轉而將期刊美術傳播重點留給了水彩畫。事實上,正是出于對中西藝術理想、現實等諸多方面的理性思考,李叔同才采用了上述傳播策略,而在經歷了一系列對外交流活動后,他的中西藝術比較觀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傾慕西方繪畫轉變為盛贊中國傳統書畫的藝術價值。
1905年秋,李叔同從上海前往日本準備留學事宜,抵日后不久便在《醒獅》①《醒獅》月刊于1905年9月在東京創刊,其目標受眾為中國國內的讀者。《醒獅》第3期出版于1905年11-12月。李金龍.清末留日學生創辦《醒獅》月刊釋疑[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26 卷(1).雜志第3期發表《美術界雜俎》,部分內容涉及對法國印象派變體、日本“外光派”油畫的介紹,由此開啟印象派在中國的跨文化傳播。
早于李叔同留日十年,留法歸國的日本洋畫家黑田清輝,已憑借從法國傳回印象派與學院派油畫的綜合產物“外光派”、創立相關繪畫社團白馬會等舉措,在日本洋畫界確立了領軍者地位。[4]由他主持的東京藝術學校西洋畫科,既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西畫教育機構,也是日后中國畫人留日學習西畫的首選目標。[5]盡管李叔同實際要待到1906年才正式進入東京藝術學校西洋畫科學習,但懷揣對目標學校、科系及相關教師的向往之情,甫一抵日,他已迫不及待地向國內讀者介紹與之相關的雜志、展覽信息。例如,《美術界雜俎》介紹《光風》②《光風》雜志創刊于1905年5月,即李叔同抵日當年,這也是白馬會成立的第10周年。《スケッチ》③意即sketch,寫生。等雜志,皆為白馬會重要刊物,以介紹會員畫家的作品為主要內容。而該文在介紹展覽信息時所涉及到的和田英作、岡田三郎助等油畫家,更是黑田清輝的藝術盟友、外光派名家、東京藝術學校西洋畫科骨干教師及白馬會成員。[5]10-11[6][7]不過,盡管李叔同汲汲于分享上述信息,卻未在文中道明它們與“外光派”繪畫的實際關聯,這與李叔同此時尚未全面開展西畫研究不無關聯。
留學期間到歸國后,李叔同又不止一次地在期刊文論中簡略提及印象派等西方現代繪畫,但均未就此展開論述。例如1910年,李叔同受邀在上海城東女學④城東女學由李叔同至交好友楊白民創辦于1904年。李叔同亦自同年始,受邀在城東女學任教,直至1905年出國留學。1911年留學歸國后也曾繼續在該校任教。陳星.游藝:楊白民、城東女學及李叔同[M].三聯出版社,2013.《女學生雜志》⑤1909、1910年,城東女學社先后創辦《女學生》月刊、《女學生雜志》(不定期),李叔同也曾受邀在兩刊發表多篇文章。第1期上發表短文《油畫》⑥原文未署名,經筆者考證為李叔同所作。介紹:“油畫分二種,一寫意法,二工致法,學者當從工致法入手,及純熟之后,然后畫寫意法(油漆,日本小川町熊野屋發賣。每小匣二元。上海外國書坊亦有之,惟其價目甚貴,不易購買)”。李叔同以國人較為熟悉的“寫意法”稱謂指代印象派等意態抽象的西方現代繪畫,以“工致法”指稱西方傳統寫實油畫。他建議習畫者先行掌握“工致法”,再著手研習“寫意法”,同時也提到國內油畫顏料昂貴且不易購買等現象,此外則無意于進一步展開論述。
1912年,已經歸國的李叔同在上海《太平洋報》⑦《太平洋報》是民初同盟會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家大型日報,于1912年4月1日創刊,由宋教仁、姚雨平主辦,葉楚傖任總編輯,柳亞子、李叔同任副刊主編,后因經費困難于同年10月18日停刊。擔任美術編輯。其間,他于該報發表源自日本的美術譯述《西洋畫法》,⑧1912年,李叔同任《太平洋報》廣告部主管,以及該報《廣告叢譚》欄目撰稿人。《西洋畫法》一文署名凡民,經王中秀考證,凡民即李叔同。李叔同在文章開篇云:“是編為余在某校時所編輯者,以橋本邦助氏之《洋畫一斑》為藍本,但多以己意增刪顛倒,又采取他書補人者,約十之二”。王中秀.《西洋畫法》:李叔同的譯述著作[J].美術研究,2007(3).在系統講授西畫繪畫方法的同時,正式提及印象派這一重要的西方現代繪畫流派:
“西洋畫以空氣與日光為主,無空氣即無遠近。完全自然之美,決不能表出。如近草雖綠,遠草則藍,空氣有薄有厚之故也。現日光最困難,日光映射處,不能僅以黃色了之。最近之印象派,以畫日光著名。此外,又有反射亦宜研究。如晴天時,人顏受木葉之反射,則呈綠色。又,雨天反射最多”。
盡管這是李叔同首次在期刊文論中為印象派“正名”,但他仍然沒有將其作為傳播重點。相反,《西洋畫法》以主要篇幅重點介紹同為西洋畫的水彩畫,不僅詳細交代其繪畫工具及技法,還就與之相關的光色原理予以詳解,而這一現象也曾反復出現在李叔同其他一些較為重要的期刊美術傳播活動中。⑨1906年,李叔同在《醒獅》雜志第4期發表《美術:水彩畫法說略》;1907年,他又以 “LK生”之署名在上海《學報》月刊第2-4期發表連載文章《美術:西洋畫科》等,均以水彩畫法講授為主要內容。參見方茜.印象派繪畫在近現代中國傳播研究(1905-1937) [D].2018.
從1905年《美術界雜俎》未及言明日本美術見聞的“外光派”屬性,到1910年《油畫》以國人易于理解的“寫意”“工致”等語匯,概述西方現代繪畫、傳統寫實油畫的特征及區別,再到1912年《西洋畫法》為印象派“正名”,可以說,隨著李叔同因留學而逐步加深對印象派等西方現代繪畫的認識,他在期刊文論中涉及相關討論的程度也有所推進。但是與同一階段李叔同運用期刊媒介著重介紹水彩畫的情形相對照則不難發現,他無意于將印象派繪畫作為期刊美術傳播的重點。
另一方面,從個人創作實踐角度觀之,李叔同對印象派繪畫的興趣不可謂不濃:他不僅在東京藝術學校西洋畫科接受了“外光派”油畫系統訓練,而且至遲于畢業展覽之際,即已運用法國新印象派手法創作自畫像,并因此而獲致好評,[8][6][7]歸國后直至出家前也堅持從事相關藝術實踐。[9][10][11]然而,對印象派繪畫感覺敏銳、勤于探究的李叔同,為何僅以“點到即止”的方式在期刊文論中簡略帶過相關信息,轉而將期刊傳播的重點分配給同樣源自西方的水彩畫?在不無矛盾的傳播現象背后,實際蘊藏著李叔同對中西藝術理想、現實等諸多方面的理性思考。
首先,在李叔同看來,固然國人西畫常識匱乏、亟待補充,但鑒于西畫、尤其是油畫研習專業性強、難度較大,相關學習過程必須由易至難,循序漸進:
“西洋畫為一種專門技術,非有畫才者不能學。即學之,亦非有三五年之學力,不能窺其門徑。無畫才者學之,終身為門外漢也(美術學校——一年生之優者,其程度每在尋常卒業生之上)……西洋畫以油畫為主……是以西洋畫研究之次序,先習木炭畫,并習鉛筆、水彩等。研究木炭畫二三年,略知寫形、寫調子之大義,然后再作油畫,乃為正格”。[12]
第二,李叔同認為,西方水彩畫與中國畫畫法相近,比較適合西畫新手入門。[13]但即便如此,仍須結合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調整學習方法。如,鑒于國人對西畫“寫生”方法多感陌生,因而較宜從中國畫傳統臨摹方法入手開啟相關學習。[14]
第三,不僅從東西繪畫藝術屬性、研習方法等角度觀之,水彩畫比油畫更適合國內的初學者,即使從畫材工具是否易得的角度觀之,油畫學習也面臨更多障礙。這一點,李叔同在《女學生雜志》上以“寫意法”概稱印象派等西方現代油畫時,即已用帶括號的文字予以交代:
“油畫分二種,一寫意法,二工致法,學者當從工致法入手,及純熟之后,然后畫寫意法(油漆,日本小川町熊野屋發賣。每小匣二元。上海外國書坊亦有之,惟其價目甚貴,不易購買)”。[15]
可見,油畫學習不僅專業性強、難度大,甚至連最基本的顏料工具也十分昂貴、不易購買,這使得李叔同無意通過期刊媒介向國內的西畫初學者廣為推薦,更無需贅言需以熟練掌握“工致法”為基礎的印象派油畫。
第四,李叔同在《太平洋報》擔任美術編輯期間,也負責該報廣告事務,[12]對于這一時期滬上商業美術市場風行美人月份牌、照相布景的現實情景必定了然于心。鑒于上述商業美術制品多以水彩畫法繪制,對于后者李叔同既不缺乏繪畫體驗,[16]還積累了相當成熟的文字資料,于是便順應商業市場、大眾審美需求,提煉成《西洋畫法》一文發表于《太平洋報》。由此,水彩畫便憑借畫法易于掌握、工具獲取便利、實用且富于商業價值等諸多“優勢”,一再超越印象派油畫而構成李叔同期刊美術傳播的重點。
值得注意的是,李叔同一方面理性地回避了以期刊媒介大舉介紹意態抽象、意涵前衛的印象派繪畫,另一方面仍以飽滿的熱情堅持從事中國書法、西方繪畫創作研究。正是基于持續的交流、實踐與深入反思,他對傳統書畫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如前文所述,1905年,李叔同初抵日本,便在《醒獅》雜志發表《圖畫修得法》,開篇即表達了對中國繪畫及其教學方法的不滿:
“我國圖畫,發達蓋早。黃帝時史皇作繪,圖畫之術,實肇乎是。有周聿興,司繪置專職,茲事寢盛。漢唐而還,流派灼著,道乃烈矣。顧秩序雜邇,教授鮮良法,淺學之士,靡自窺測。又其涉想所及,狃于故常,新理眇法,匪所加意,言之可于邑”。[13]
上述意見既受到國內貶抑傳統書畫的主流輿論影響,也構成諸如李叔同等中國畫人留日學習西畫的主要動因。1910年,李叔同又在《女學生》雜志《中西畫法之比較》文中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中西藝術比較觀,其態度相較于5年前可謂差別迥異,從原本傾慕西方繪畫轉變為盛贊中國傳統書畫的藝術價值:
“西人之畫以照相片為藍本,專求形似。中國畫藝作字為先河,但取神似而兼言筆法。嘗見宋畫真蹟,無不精妙絕倫,置之西人美術館亦上乘之列。中畫入手既難,而成就更非易易……使中國大家而改習西畫,吾決其不三五年必可蹤彼國之名手。西國名手倘改習中國畫,吾決其必不能遽臻絕詣……余嘗戲謂看手卷畫猶之走馬看山。此中畫法為吾國所獨具之長,不得以不合畫理斥之。”[17]
《中西畫法之比較》指出,中國書畫以“神似”為追求目標,藝術境界遠在“專求形似”的西畫之上;不僅如此,中國繪畫強調書法用筆,在方法層面也具有獨樹一幟的價值。這些言論表明,至遲于留學后期,李叔同對本民族藝術傳統已形成強烈認同,從而憑借自主意識沖破了國內主流輿論的限制。①李叔同留學期間,日本藝術界已經歷了明治前期崇尚西洋、明治中期保存國粹等一系列動蕩起伏,逐步形成“東西互補”發展共識,既努力與西方現代藝術潮流保持同步,更強調在弘揚民族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日本藝術現代發展方向。這種語境氛圍也對諸如李叔同等中國留學生造成影響,促使他們深入反思本民族藝術傳統及其發展方向。
1912年到1918年,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擔任美術教職。其間,他一方面積極采納日本、西方美術院校先進教學方法,在課堂上推行石膏像、人體模特寫生等西畫基礎訓練,另一方面又在課余組織以研習西畫為要務的“桐蔭畫會”,并與李鴻梁、豐子愷等弟子就西方現代繪畫進行交流。[18]20、30年代,李鴻梁、豐子愷等人曾先后出版關于印象派、后印象派繪畫的美術文論,②1920年,《美育》雜志第3期刊載李鴻梁文章《西洋最新的畫派》,涉及印象派傳播。30年代,豐子愷也曾多次憑借出版媒介傳播印象派信息。參見方茜.印象派繪畫在近現代中國傳播研究(1905-1937) [D].2018.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李氏師生的相關交流,這為印象派在中國的后續傳播埋下了重要伏筆。
二、陳樹人:持有異議與形而上思考
區別于李叔同對印象派繪畫“點到即止”式的傳播,另一位留日書畫家陳樹人則通過其美術譯述《新畫法》簡要介紹了印象派及其代表畫家畫作的藝術特質,甚至明確就此表達其否定意見。究其原因在于,陳樹人早年所受書畫訓練與留日習藝經歷,都將其導向精細寫實藝術觀,從而使其較為排斥意態抽象的印象派繪畫。此外,連載《新畫法》的《真相畫報》也以實用美術為關注,而較難認同意涵前衛的印象派繪畫。另一方面,基于留學、譯述等一系列對外交流活動,陳樹人對中國藝術發展問題的思考角度獲得了重大調整,從強調美術的實用價值轉變為關注藝術的形而上意涵。
1912年,由日本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畢業歸國的廣東畫人陳樹人,在上海《真相畫報》①《真相畫報》,旬刊,1912年創刊于上海,由高奇峰編輯,真相畫報社出版,1913年3月出版第17期后停刊。1912年6月至1913年2月,《真相畫報》第1-16期連載《新畫法》。發表美術譯述《新畫法》,部分內容涉及西方印象派繪畫傳播。《新畫法》由陳樹人參照日文原著《繪畫獨習書》節選、譯述而成,主要保留原書的第一編《繪畫大意》、第二編《水彩畫描法》呈現給中國讀者。[19]其中,關于印象派及其代表畫家莫奈的介紹首先出現在第一編第五章《繪畫之變遷(下)》,即西方近代繪畫簡史部分:
“更有奉極端主義之一派,即印象派是也……克羅特摩涅等此派之先河也。摩涅普法戰爭之際,率其同道渡英,見他拿之作,而有所感,爾后畫法為之一變……蓋摩涅一派,注重光線空氣,專思所以表出之。聯絡近世科學,因原色點線之配,列而表物,此原色并列法,世謂之印象派……摩涅則張畫架于戶外,全畫告成,攜入室內,不加一點。畫之章法極大膽極奇僻,蔑視古法。唯不好大景色,而耽小部分。無大幀巨制,故時人大攻擊之,謂其非完備之畫,不過練習之畫耳,至今仍有以此誚之。摩涅等則固以完全畫自居也。[20]
《新畫法》不僅將印象派定性為“奉極端主義之一派”,同時還指出由于莫奈的藝術創作標新立異、蔑視傳統,且畫幅偏小,而被同時代畫評嘲諷為“非完備之畫,不過練習之畫耳”。接下來,在第一編第九章《分解與綜合》,即自然風景畫法講授部分,譯述者進一步表達了他對印象派繪畫的否定態度:
“描寫自然,厥道有二,一分解一綜合。分解客觀的也,綜合主觀的也,而畫必不越乎此兩方面。印象派主綜合。例如窗嵌玻璃上,懸透花帷,常法寫之必須細辯,印象派則不然,瞬間感想,玻璃與花帷合一色以寫之而已。故印象派之畫往往流于形色不確之弊。其時己所感想或如是,惟囿于一人心目,而謂人人盡興我合節,有是理邪”。[21]
《新畫法》在指出印象派繪畫存在過于主觀、“形色不確”等問題的同時,也相應地對那些注重客觀寫照、畫風嚴謹的畫家給予了充分肯定。如評價先于印象派而成名的法國外光派畫家巴斯蒂安·勒帕熱:“巴士之畫,寫實極嚴密,一草一木,悉照之以繪不加人意。其對于自然,意態殊懇摯,毫無浮薄處,可謂穩健之自然派也”。[20]可見,所謂“悉照自然”“意態懇摯”“寫實嚴密”,才更接近陳樹人自身的藝術價值標準。
身為嶺南花鳥畫衣缽傳承者,陳樹人自青年時代拜師居廉門下,②居廉,廣東著名畫師,善作花卉、草蟲,畫風工整,意態生動,不僅強調對景寫生,還創造性地運用“撞粉”“撞水”等方法,令所繪花卉富于明暗光感、立體意味。李偉銘.陳樹人[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便開始接受風格近似西式寫真的書畫訓練,并逐步建立起注重細致觀察、強調師法自然的繪畫觀念。這一點,從《新畫法》字里行間亦可見:
“故于己眼所感覺之自然,摹之擬之而寫于適宜之平面上,此即繪畫矣……我輩描畫觀畫之眼,所感之自然異乎于與畫無關之人所感之自然……學畫之要義眼之教育而已”。[22]
在此基礎上,京都留學的經歷又進一步強化了陳樹人的寫實藝術觀,尤其是日本畫家竹內棲鳳、山元春舉,憑借寫實繪畫手法及西式透視構圖[23]給陳樹人留下深刻印象,日后,陳樹人在書畫創作中亦不時借鑒上述風格與技法,說明其受影響之深。[24]可以說,居門習藝經歷與日本留學經歷共同鑄就了陳樹人的寫實藝術觀,因而使其較難接納意態抽象的印象派繪畫。
不僅陳樹人自身的藝術知識背景影響了他對印象派繪畫的價值判斷,連載《新畫法》的《真相畫報》也頗為關注實用美術,而較難認同“惟囿于一人心目”的印象派繪畫。事實上,《真相畫報》之所以刊布《新畫法》,主要看中的是其第二編《水彩畫描法》所蘊藏的“實用價值”。對比而言,意涵前衛的印象派繪畫只能作為近代西方畫史的組成部分而被予以必要交待。這一點,與李叔同在《太平洋報》《水彩畫法》文中簡略帶過印象派信息、同時又將水彩畫法作為傳播重點的情形頗為相似。
連載《新畫法》的《真相畫報》并非一份孤立的報刊,而是自20世紀初以來,廣東革命畫人“二高一陳”等人③即以高劍父、高劍父、陳樹人為核心,同時包括何劍士、潘達微等廣東籍革命畫人。通過辦報鼓吹革命之系列活動中的最后一環。[25]1912年前后,陳樹人、高劍父、高奇峰等人輾轉至上海,憑借出版《真相畫報》、創辦審美書館等舉措謀求新發展。鑒于此時革命剛剛成功,舉國上下政治熱情有所消退,《真相畫報》也相應減弱了政治議程,轉而加強文藝與實業經營導向,不僅連載陳樹人的美術譯述《新畫法》,還頻頻刊登由高劍父等人撰寫的美術陶瓷制造等實用美術主題文章,表達了編撰團隊對實業救國、美術救國問題的強烈關注。[26][27]從出版《真相畫報》轉向經營審美書館后,高氏兄弟又與月份牌畫家鄭曼陀①鄭曼陀,安徽歙縣人,民國時期著名的美人月份牌畫家、廣告畫革新者。合作,通過大量印發以后者首創之“擦筆水彩畫法”繪制的美人月份牌,淘汰了先前流行的擦炭法美人畫,由此不僅開啟了商業美術時尚新篇,還收獲了良好的業界聲譽與經濟效益。[28]聯系陳樹人在譯述《新畫法》時僅保留了原著中的水彩畫內容,而刪略了木炭畫、油畫等內容,[19]不久審美書館又將該部連載集結成單行本予以出版、再版,②審美書館于1914年10月出版《新畫法》單行本,后又于1916年2月予以再版。種種跡象表明,即使《新畫法》所講授的水彩畫法與美人月份牌畫法不盡相同,但在傳播經營者眼里,這種象征商業美術發展趨勢的“新畫法”蘊藏著豐厚商機,必須給予重要關注。對比之下,意涵前衛的印象派繪畫僅僅作為西方美術史常識被順帶提及,而不可能獲得更多關注。
無可否認,《真相畫報》編撰團隊對實用美術的關注與晚清中國社會彌漫著的“自我認同危機”[29]存在千絲萬縷的關聯。在此氛圍下,無數像李叔同、陳樹人一樣感時憂國的書畫家,都在哀嘆中國傳統繪畫的“衰落”境遇,并力圖通過留學、辦報、譯書等途徑引進西畫新知,復興中國美術,更主張借鑒歐美、日本先進經驗,大力發展實用美術,以實現國富民強之期望。聯系1908年陳樹人留學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之初,曾首選進入圖案科就讀,一年后方才轉入繪畫科,[24]216-225這意味著陳樹人也曾追隨主流輿論,對富于實用價值的工藝美術給予重要關注。不過,在經歷了留學、譯述等對外交流活動后,陳樹人思考中國美術發展問題的深度獲得實質性推進。1913年,他在《新畫法》連載完結后的譯述者短跋中寫道:
“記者述是書畢,回顧神州美術界現狀,不禁擲筆太息曰:誰意我有四千年美術史媲美希臘之中國,至今日而凋落至于斯極,此淺稚繪畫法,求之出版界而不可得;即有矣,過問者寥寥,豈黃裔審美思想獨缺乎?西哲曰:欲覘一國文化,先覘其美術。今也我國徒具共和美名,文物典章,掃地以盡;有為之士,非殉利名,則死權勢;稍尚者,亦唯傾注于物質的事業,幾曾見于形而上之文藝美術一顧及哉。是則可唏也已!”[30]
盡管此時陳樹人仍然認為中國美術發展狀況堪憂,但令他唏噓的已不再是實用美術匱乏等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環境并未因民國初建而有所改善,國人唯重物質、趨名逐利的狀況反而愈演愈烈等現象。失望之余,陳樹人清醒地意識到,片面地關注物質文明實際有害無益,中國文藝復興的宏愿若要得以實現,還須從形而上層面激發藝術潛能,使之有益于構筑機能健全的現代文明。
三、陳師曾:理論升華與文人畫藝術觀
留日書畫家陳師曾通過美術譯述《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表達了他對印象派等西方現代繪畫的強烈認同,同時也以較為宏觀的理論研究視角區別于陳樹人等人對實用美術的關注。陳師曾不僅在初涉印象派繪畫傳播時既已闡發了卓爾不群的中西藝術見解,日后更致力于通過傳統書畫研究、對外藝術交流,推進中國藝術現代轉型,同時也策略性地將印象派傳播經驗轉化為捍衛文人畫進步價值的理論依據。
1912年,正在南通師范學校任教的陳師曾,在該校《南通師范校友會雜志》③《南通師范校友會雜志》創刊于1911年,共出8期,于1919年9月停刊。第2期發表由他翻譯、由日本洋畫家久米桂一郎④久米桂一郎是與黑田清輝同時代的洋畫家,也是黑田重要的藝術盟友之一。原著之《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一文。該文立足于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洲畫壇整體發展狀況,對印象派、后印象派等現代繪畫的藝術特質、價值與地位展開分析論述。文章指出,18、19世紀的歐洲畫壇,見證了從古典主義到自然主義等一系列畫派的上下求索,但始終未曾收獲真正意義上的突破與創新,原因在于,這些畫派都執著于對“形似”的追求,然而,“夫藝術一出于模仿,即非絕詣……凡繪畫惟表現物體之外形,非其究竟之目的,故停滯而不前,不足進于道也”。直至19世紀中后期,上述情形終獲改觀:印象派繪畫應“科學時代”感召而誕生,通過發揮光色科學理論影響,將歐洲繪畫對真實再現的追求從外形層面延伸至光色層面,更憑借富于個性的審美發現為歐洲畫壇帶來突破性變化,從而打破了后者自近代以來發展趨緩的局面:
“所謂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者出焉,依然科學精神之一發現也。要之,科學之觀察漸及精細,由自然確實之觀察,遂進而分解其構成之要素。印象派以為聲音沖擊鼓膜,悟其為音波;而色彩亦由原色之光線配合而映于網膜,乃成印象……由19世紀之始,以迄于今之畫界,以自然之真相為目的……如印象派者,不得謂尋常之寫實超乎寫實,而進于解剖者也;無所謂形,惟覺其畫光色燦爛,涌現目前。蓋形也者,乃光與色所結合,故得光與色而形亦在其中。此即作者能得光與色之真相而別創一種之寫實派也。且不僅形與色而已也,而其中所含之美尤為重要。此真繪事范圍內之事矣。
文章進而比對印象派、后印象派繪畫的聯系與區別,指出后者在前者的基礎上進一步沖破“形似”之束縛,將情感抒發、個性表達作為藝術的終極關懷:
“印象派重色而輕形,分析光線,因而遺其形;新印象派①《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原文中指后印象派繪畫。以遺形為前提焉。印象派分析光線以還原其各構成之要素;而新印象派則于其所分析要素之中,擇其適于發表自己之感情者。而構成我之自然。故印象派為解剖家,而新印象派乃綜合家也。印象派以自然為主,其態度乃受動者也;而新印象派以畫家之情志為基本,其態度乃獨立而不羈。印象派發見自然美者也,而新印象派則自然美于個人之感情中求之。且此派以簡單化物之形,實受以前馬內之影響”。
不難看出,《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高度認同印象派、后印象派繪畫注重個性表達的藝術特質,以此對立于陳樹人《新畫法》對印象派主觀特征的質疑。此外,《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也以富于理論色彩的觀點表述區別于前述李文、陳文對實用美術技能的關注。而且《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一文的理論性不只體現在分析論述印象派、后印象派藝術特質方面,還體現在探索思考更具普遍性的藝術發展規律方面。例如文章談到,藝術發展與社會環境變化存在密切關聯;藝術發展態勢以循序漸進為主,而少有突然性變革;不重形似而注重主體意識表達的后印象派繪畫之所以能代表歐洲藝術發展趨向,與攝影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不無關聯,正是后者觸發了歐洲藝術界對“真與美”這對矛盾統一體的深刻反思:
“19世紀之畫界,亦科學精神之所發露者也。雖然,其變革非突然變革者也,循序而漸變者也……至1900年之時,尚古派于美術家中,頗以為陳腐矣;印象派如摩內諸人,于當時人之眼中,不以為怪。此時新印象派,②在原文中指誕生于20世紀的表現主義繪畫。正其發奮之秋也……最近歐洲畫界之傾向,此派之勢力為著云……挽近照相術之進步,頗與繪畫無異。以照相為基礎之畫,其價值薄弱,故必求照相術所不可能之繪畫。約言之,對于真之美感反抗也。然徒然真,則褊狹。徒然美,則亦不完全。故此反抗,焉知不有與之反抗者?甚難于解決也”。
在這一系列藝術觀點表述當中,《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對印象派價值精髓的概括,也構成陳師曾個人的核心藝術觀:
“所謂美術者,奇妙不可思議,決非僅以寫實可以盡之……不僅形與色而已也,而其中所含之美尤為重要。此真繪事范圍內之事矣”。
《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所具備的理論研究視角,不僅與其日文原著存在一定關聯,更與陳師曾自身的學術修養密切相關。這一點,從《南通師范校友會雜志》1912年第2期在《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文后刊出的譯者短跋,及其所表達的卓爾不群的中西藝術見解亦可見一斑:
“按西洋畫界,以法蘭西為中心;東洋畫界,以吾國為巨擘。歐亞識者,類有是言。東西畫界,遙遙對峙,未可軒輊。系統殊異,取法不同,要其喚起美感、涵養高尚之精神則一也。西洋畫輸入吾國者甚少,坊間所售,多屬俗筆,美術真相,鮮得而睹焉。日人久米氏有《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一篇,今譯之以紹介于吾學界,藉以知其風尚之變遷:且彼土藝術日新月異,而吾國則沉滯不前,于此亦可以借鑒矣。衡恪附識。”
對立于清末民初中國藝術界普遍以西方為先進、以中國為沉滯的偏頗輿論,陳師曾憑借自身的對外交流經歷,體會到海外藝術界對中國書畫的強烈認同,由此增強了對傳統藝術的自尊、自強意識。他認為,盡管中西繪畫表現手法各異其趣,但它們的精神追求卻頗為一致。鑒于近代中國繪畫發展趨緩,中國藝術界對西方繪畫的認知也極其匱乏,因此有必要通過譯述等活動向國人介紹西方“美術真相”,進而主張理性借鑒西方現代藝術發展機制,以助推中國藝術發展與創新。
陳師曾的中西藝術觀不僅源自其家學淵源的出身、自幼習畫的經歷,更離不開他對中外藝術的濃厚興趣與持續探究。盡管陳師曾留日所學為博物學,但在留學期間他亦廣泛涉獵東西繪畫信息,不僅為日后的西畫譯述活動收集資料、奠定基礎,還積極嘗試日本漫畫式的書畫實驗,[31]回國后又與吳昌碩過從甚密,跟隨后者研究金石書畫。[32]
陳師曾發表《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后不久,移居北京,他一邊在教育部從事圖書編輯、在高校擔任教職,一邊堅持從事書畫創作研究,并與金城合作籌辦了一系列中日書畫展覽,積極推進中外藝術交流。[33]20年代前后,陳師曾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以及《繪學雜志》《東方雜志》等教育、出版平臺闡發了一系列書畫藝術見解,[34][35][36][37][38]憑借其在歷史研究、對外交流過程中所積累的豐厚學養、寬廣識見,回應新文化運動反傳統主義的偏激輿論。在這些書畫研究著述中,陳師曾一方面從繪畫題材、流派樣式、發展脈絡等角度詳論傳統書畫藝術屬性,另一方面又從文化背景、藝術志趣、源流趨向等層面比較中西繪畫之異同,由此闡明中國書畫杰作不僅凝結了傳統文化精髓,而且顯示出與世界現代藝術共通的發展方向。這些論述的字里行間也不時透射出早年譯述、傳播印象派的經歷,為陳師曾拓展中西藝術視野、堅定傳統文化信念所奠定的重要基礎。
例如在《文人畫之價值》文中,陳師曾為闡明“文人畫不求形似,正是畫之進步”這一重要觀點,不僅就文人畫的意趣、追求等內在特質展開分析論述,還援引西方現代繪畫發展演變軌跡作為外部旁證,指出:“西洋畫可謂形似極矣。自19世紀以來,以科學之理研究光與色,其于物象,體驗入微。而近來之后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體,專任主觀。立體派、未來派、表現派聯翩演出,其思想之轉變,亦足見形似之不足盡藝術之長,而不能不別有所求矣”,以此說明文人畫與西方現代繪畫相近,不受形似之束縛,以表現超越再現,具有顯著的進步價值。事實上,該文不僅論述過程如聞《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余音繞梁,其觀點“文人畫不求形似,正是畫之進步”,也與《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在闡述印象派繪畫特質時所言“所謂美術者,奇妙不可思議,決非僅以寫實可以盡之”如出一轍。無獨有偶,1922年,陳師曾又在《論南畫》文中談到:“東西方藝術終究是各自獨立的;它們有著各自的體系、歷史、習俗和智識基礎……將來,當世界大同時,當知識和思想能以多種方式交流時,藝術的融合或許可能實現。但是,那個時候是否會來到,仍然是未知數”[39]——此處他對文化多樣性,以及藝術獨立發展原則的強調,亦與其在《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譯述者跋中所言:“東西畫界,遙遙對峙,未可軒輊”[40]①陳師曾. 歐洲畫界最近之狀況[J]. 南通師范校友會雜志,1912(2).遙相呼應。可以說,譯述、傳播印象派繪畫的經歷為陳師曾完善西畫知識儲備奠定了重要基礎,持續的書畫創作實踐、理論研究為其洞察中西藝術價值精髓提供了學養支持,與他人合作舉辦中日藝術展覽等經驗則在拓寬其中外藝術視野的同時,也幫助其增強了傳統文化信念。基于上述積淀,他自覺地擔負起維護中國藝術傳統的職責,進而提煉形成“文人畫藝術觀”以迎擊貶抑傳統的新文化浪潮。
結 語
清末民初,印象派繪畫在中國傳播初啟,部分傳統書畫精英兼而運用自身的留學經歷、傳統書畫學養,表達了其對西方現代繪畫的藝術見解、價值判斷。亦有相關傳播者基于豐富的期刊傳播經驗,有所取舍地刊布相關藝術信息,其傳播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末民初崇尚實利的社會文化語境對外來藝術傳播、中國藝術發展的深刻影響。
更重要的是,在印象派傳播等對外交流經驗與傳統書畫研究的共同作用下,上述留日書畫家的中西藝術比較觀、傳統藝術發展觀逐漸調整定型,既有李叔同從追隨貶抑傳統的主流輿論,轉為強烈認同傳統書畫的藝術價值,同時積極推行歐美、日本先進藝術教育方法,也有陳樹人從原本關注美術的實用價值,轉變為從形而上層面思考藝術救國等問題,更有陳師曾憑借廣博的東西藝術見聞、豐厚的傳統書畫學養,支撐其對中西藝術共通發展趨向的深刻洞察,進而捍衛傳統文人畫的進步價值。這些現象生動地再現了外來藝術知識與中國本土藝術知識體系交流、碰撞的歷史情境,說明清末民初中國傳統藝術界并非如主流輿論所言“陳陳相因”“停滯不前”,相反,不乏傳統藝術精英一直致力于探尋各種路徑,推進傳統藝術的現代轉型。他們積極地與外來藝術對話,同時深刻反思中國藝術傳統,不乏相關人士由此增強了民族文化自尊、自強信念,也就“中國藝術發展的恒久動能潛藏于藝術傳統內部”這一洞見產生強烈共鳴,進而不約而同地訴諸“返本開新”策略,推進中國藝術現代發展。②雖然“返本開新”藝術發展策略由山水畫一代宗師黃賓虹明確提出,但李叔同、陳師曾等人在20世紀10、20年代先后闡發的傳統藝術價值觀,實與“返本開新”策略形成精神共鳴,而且陳師曾與黃賓虹也確為藝術同道關系。關于印象派在中國的傳播推進,及其與“返本開新”策略的關聯,筆者將另行專文予以討論。另一方面,盡管驅動中國藝術現代轉型的核心動能,源自藝術傳統內生的現代發展趨向,而非外來藝術影響,但印象派傳播仍然在與中國藝術界交流互動的過程中,對中國藝術現代轉型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