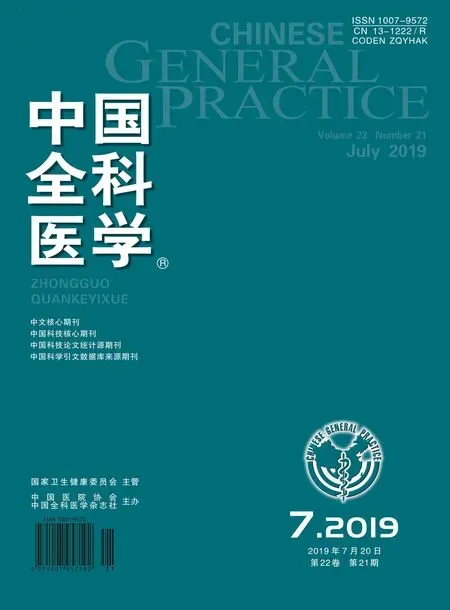晚期腫瘤患者預立醫(yī)療照護計劃干預模式的研究進展
邱業(yè)銀,張江輝,繆佳芮,陳柳柳,鄧仁麗
惡性腫瘤已成為人類發(fā)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2016中國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統(tǒng)計年鑒》[2]顯示,中國死于惡性腫瘤人數約為220萬。醫(yī)療水平不斷提高在延長晚期腫瘤患者生命的同時,也造成了過度醫(yī)療現象日益嚴峻[3-6]。65%~85%晚期腫瘤患者將會在沒有生前預囑的情況下死亡,甚至連臨終治療意愿討論也沒有[7-8]。預立醫(yī)療照護計劃(ACP)可了解患者將來的治療意愿,保障患者的自主權,ACP干預措施可增加患者和家屬的滿意度[9-11],提升干預者的自我效能,減少照顧者的抑郁和焦慮[12],并減少患者臨終時過度使用醫(yī)療服務的情況[9,12]。目前國內晚期腫瘤患者ACP僅局限于患者、家屬及醫(yī)護人員認知、態(tài)度及影響因素的調查[13-19],而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相關研究開展較少。為此,本文綜述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模式研究現狀及進展,以期為開展本土化ACP干預工作提供參考,現綜述如下。
1 ACP概念與內涵
ACP又稱預前照護計劃,指個人在失去決策能力前,闡明符合個人價值觀的未來醫(yī)療治療意愿,與家屬和/或醫(yī)護人員溝通并記錄其首選治療意愿和臨終場所意愿的過程[20-21]。ACP旨在保障個人實際接受的醫(yī)療照護服務與其臨終治療意愿一致[7,22]。起初,ACP側重意識清楚時的溝通過程,干預人群主要局限于疾病終末期或慢性進行性疾病患者,討論內容為臨終治療意愿[23-24]。隨著研究的深入及社會實踐的推廣,ACP的概念及內涵也發(fā)生較大變化。至今,ACP溝通時機演變?yōu)槭Q策能力前,不僅局限于溝通過程,也包括記錄過程,干預人群逐漸由疾病終末期或慢性進行性疾病患者過渡到現在的任何年齡或健康階段的人群[25]。
2 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模式現狀及構成要素
2.1 國內外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模式現狀 在國外,ACP起步較早,其在發(fā)達國家廣泛應用,甚至在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被納入了衛(wèi)生保健系統(tǒng),并被作為醫(yī)療常規(guī)的一部分[26-31]。國外ACP的運作主要是在醫(yī)院由具有豐富腫瘤護理工作經驗及經過ACP培訓、能獨立開展ACP討論的腫瘤科護士或一些具有腫瘤臨床工作背景的專業(yè)人員如腫瘤學專家或腫瘤科醫(yī)生等,針對未來1年內可能會去世或者需要接受ICU治療的腫瘤晚期患者開展[26-28]。國內相關研究主要局限于腫瘤晚期患者、家屬及醫(yī)護人員對ACP的認知、態(tài)度及影響因素的調查[13-19]。多項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醫(yī)護人員、患者、家屬對ACP的認知率普遍較低,而贊同ACP實施的比例則較高[13-16,32]。此外,部分國內學者運用質性訪談的方法探索了晚期腫瘤患者的照護需求及其對生命意義的理解,結果顯示,很多晚期腫瘤患者有ACP需要,但卻存在不愿接受治療又不忍心傷害家屬的矛盾心理[33]。明星[34]探索了晚期腫瘤患者生命意義的干預方案,通過干預減輕了患者心理痛苦,提升了其生命意義感,這和ACP干預過程中與患者溝通生命意義是一致的。我國香港、臺灣地區(qū)關于ACP的研究亦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群如衰弱老年人、疾病終末期老年人等,重在探索基于本土文化和醫(yī)療體系下的ACP干預機制和實施方法[35-37],盡管其對晚期腫瘤患者ACP的研究尚無干預性研究,但是其文化背景與大陸很接近,其研究結果對大陸構建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模式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2.2 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模式構成要素
2.2.1 干預類型 國外ACP干預模式主要有結構化干預模式[12,29]、決策輔助模式[10-11,38-40]、以家庭為中心干預模式[41-42]及以患者為中心干預模式[29]等。表現形式靈活多樣,如有電話訪談干預[43-44]、網絡模型干預[9]、健康教育師干預[12]、情景假設(Vigitta技術)干預[45]及自傳式記憶(ABM)干預[46]等。
結構化干預模式和決策輔助模式中的視頻教育干預是腫瘤晚期患者ACP干預中最常見形式。結構化干預模式即與患者及其家屬進行面對面、循序漸進的溝通交流,一般包括疾病相關信息、患病體驗、生命價值觀、臨終治療意愿等內容[12,29],其已然形成體系,逐步被研究者接受并在臨床實踐中開展研究。決策輔助模式的目的在于幫助患者明確各種醫(yī)療干預的利弊并做出明智的決定,有利于激發(fā)患者表達未來醫(yī)療照護目標,是一種ACP干預的創(chuàng)新解決方案,主要通過決策輔助工具來實現[10-11]。視頻教育干預是決策輔助模式形式之一,其ACP干預內容主要包括延長生命照護、基本醫(yī)療照護及舒緩照護,主要通過視覺信息幫助患者臨終決策,有助于增加信息傳播,展開敏感話題的對話,提高患者理解能力,更好地讓患者參與臨終治療討論[10-11,39-40]。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醫(yī)學模式及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影響,國內尚未開展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許多晚期腫瘤患者尚無表達臨終治療意愿的機會。家屬、醫(yī)護人員與患者缺乏有效溝通,造成家屬及醫(yī)務人員并不了解患者的治療意愿,因此亟待開展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而結構化訪談干預及視頻教育干預值得國內借鑒。
2.2.2 干預者 ACP干預者主要為腫瘤科醫(yī)生、腫瘤科護士及經過培訓的相關人員,如研究助理、社會工作者及健康教育師等。腫瘤科醫(yī)生在ACP討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大多數癌癥患者希望由醫(yī)生親自告知病情[9]。然而,ACP討論較為耗時,在現有的醫(yī)療資源和條件下,時間成了腫瘤科醫(yī)生與患者討論ACP的重要障礙,故腫瘤科護士及經過培訓的相關人員作為干預者越來越普遍[47]。腫瘤科護士在晚期腫瘤患者醫(yī)療照護過程中身份地位特殊,與患者互動最多,有助于建立持久照護關系,同時也是醫(yī)療照護倡導者,被認為是受信任的一員,處于一個理想的干預者地位[46]。國內責任制整體護理模式也為腫瘤科護士在晚期腫瘤患者中開展ACP干預提供了有利條件。目前在國內,ACP干預尚處于探索階段,培訓體系暫未建立,經過培訓的相關人員作為干預者暫不可行。因此,腫瘤科護士是國內晚期腫瘤患者開展ACP干預較為理想的干預者人群。
2.2.3 干預時間、頻次及隨訪時間 各種干預模式中,因視頻教育干預信息可視化的優(yōu)點,干預時間最短,為 3~6 min[10-11,40],而結構化訪談干預時間均在 20 min 以上[29,39,48],網絡模型干預時間最長,為60 d[9]。因網絡模型干預的便利性
,干預頻次為2~3次/d[9],其他干預模式干預頻次為1次[10-12,29,39-40,46,48-49]。部分研究未開展隨訪[10,39,45-46,49],研究的主要隨訪時間節(jié)點為1個月[11]、6 個月[9,11,29,46]、8 個月[40]、12 個月[46]及 18 個月[12],如患者死亡則終止隨訪。鑒于隨訪時間節(jié)點出現頻次和晚期腫瘤患者預期壽命,隨訪時間推薦為 6 個月內[9,11,29,46]。
2.2.4 評價指標 ACP干預能有效提高晚期腫瘤患者生命意愿表達率,促進醫(yī)患溝通和臨床決策,從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以及患者和家屬的滿意度[27,31]。因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模式的表現形式較多,加上各項研究評價指標不統(tǒng)一,不少為自行設計的測量量表,其干預后評價指標也較多,但主要評價指標為以下幾個。
2.2.4.1 臨終治療意愿 臨終治療意愿主要通過測量患者生命支持治療意愿,如心肺復蘇(CPR)、機械通氣(MV)、ICU治療、置入鼻飼管、靜脈營養(yǎng)、血液透析、輸血及手術等的意愿。視頻教育干預后,患者CPR意愿顯著下降,不同研究中MV意愿不同[10-11,40]。VOGEL 等[9]測試了網絡模型干預對卵巢癌患者姑息治療決策的影響,結果顯示兩組之間無統(tǒng)計學差異(P=0.440),但干預組表現出計劃或考慮姑息治療的傾向,這種趨勢為干預組提供了更高的決策確定性。BROHARD[46]采用ABM干預測量了11個生命支持治療項目,每個項目分別測量“決策”及“溝通”,共測量22個變量,結果顯示,干預后患者更愿意溝通院外復蘇、置入鼻飼管及抗生素3種治療方式,患者靜脈滴注治療的決策確定性更高。以上研究僅測量了患者的臨終治療意愿,并未測量患者與家屬意愿的一致性。我國臺灣在2005年已經對晚期腫瘤患者及其家庭照護人員對臨終治療意愿一致性進行了測量[50]。周雯等[51]調查并分析了晚期腫瘤患者及其家屬對預先指示及生命支持治療(LSTs)態(tài)度的一致性,提示患者與家屬意愿一致性可作為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研究的通用評價指標。
2.2.4.2 生前預囑簽署率 生前預囑簽署表達方式可以是書面或口頭的,書面表達形式承接的載體有住院病歷、門診病歷及醫(yī)療保健文書等[10-11]。ACP討論可提升生前預囑簽署率,但并不具有統(tǒng)計學差異[9-11]。DURBIN等[52]納入的8篇關于不同教育干預方式與生前預囑簽署率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顯示,組合教育干預較單一教育干預具有更高的生前預囑簽署率(P<0.05)。部分患者雖做了關于生前預囑和醫(yī)療委托書的決定,但并不愿意簽署書面文書[46]。ACP強調的是溝通過程,溝通的結果需要有個承載的形式,而生前預囑簽署率可作為溝通的結局指標,但部分患者并不愿意簽署書面文書,所以書面文書及訪談過程中患者口頭表達的錄音均可作為生前預囑簽署率的表達方式。
2.2.4.3 患者及家屬滿意度 視頻教育干預及網絡模型干預均測試了患者及家屬的滿意度,其測量采用李克特量表。其中視頻教育干預主要通過視頻舒適度、有用性及是否會向他人推薦3個維度進行測量,患者表示視頻教育干預有較高的舒適度及有用性,愿意向他人推薦視頻內容[10-11,40];網絡模型干預主要通過總體感覺、使用簡易程度、內容質量、信息量及電腦技能操作水平要求5個維度進行測量,乳腺癌患者對網絡模型干預總體及內容質量感覺較好,90%以上的患者愿意向他人推薦網絡模型[9]。網絡模型具有便利性及可視化效果的優(yōu)點,可成為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模式之一,但其也有不少缺點,如設計困難、需要豐富的內容資源、經費高及使用率低等,這些缺點成為網絡模型干預推廣的障礙。
2.2.4.4 其他 其他評價指標有:健康知識水平、患者生活質量、培訓者的自我效能及經濟學指標,如死亡地點、生命最后30 d住院率、ICU住院率等。
3 對我國的啟示
晚期腫瘤患者過度醫(yī)療現象嚴重,許多患者臨終前甚至無機會表達治療意愿。國內前期調查結果顯示,醫(yī)護人員、患者及家屬ACP認知率低,晚期腫瘤患者臨終治療意愿表達率低,而贊同開展ACP干預率高[13-19]。但由于傳統(tǒng)文化根深蒂固,國內對ACP認識起步較晚,ACP推廣的法律依據暫不健全,目前尚無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性研究。ACP干預有望成為提高國內晚期腫瘤患者表達臨終治療意愿的重要方式,但實施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要尊重中國文化,而不是一味照搬國外干預模式,應鼓勵ACP干預模式的創(chuàng)新及本土化研究,同時獲得社會重視及法律支持。
4 小結及展望
腫瘤晚期患者ACP干預模式構成要素主要包括干預類型、干預者、干預時間、頻次、隨訪時間及結局指標。結構化干預模式和決策輔助模式中的視頻教育干預是晚期腫瘤患者ACP干預中最常見形式;腫瘤科護士為理想的干預者;干預時間隨著干預形式不同差異較大;干預頻次均為1次;隨訪時間以6個月內為宜;結局指標主要有臨終治療意愿、生前預囑簽署率、患者及家屬滿意度等[9-12,29,39-40,45-46,48-49]。因此,國內可嘗試借鑒國外干預模式的主要研究成果,構建一套本土化腫瘤晚期患者ACP干預模式并開展實證研究,提高患者臨終治療意愿表達率。
作者貢獻:邱業(yè)銀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文章的可行性分析,撰寫論文;邱業(yè)銀、張江輝進行文獻資料收集、整理;鄧仁麗進行論文的修訂,對文章整體負責、監(jiān)督管理;張江輝、鄧仁麗進行英文的修訂;張江輝、繆佳芮、陳柳柳負責論文的修訂、質量控制及審校。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