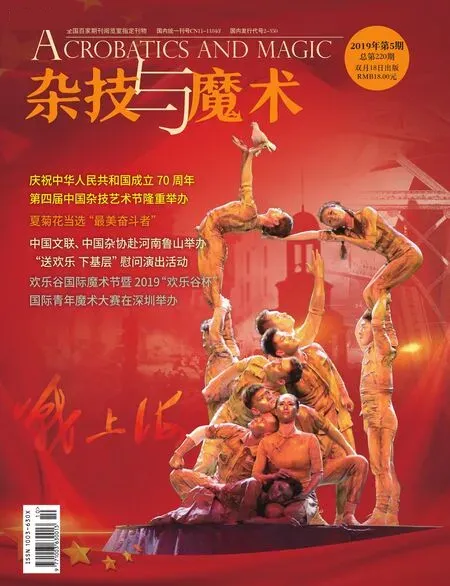“新馬戲”創作與“后戲劇劇場”勘探(續)——以中國首部“新雜藝”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為例(第13 屆中國武漢國際雜技藝術節國際馬戲論壇提交論文
文︱董迎春(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
西方“新馬戲”的表演具有“街頭劇”或“玩物劇場”的即興性、隨意性及“物我合一”性。“‘玩物劇場’中的‘玩物’,雖是‘玩耍物件’,展露‘雜耍把戲’的技術;但若細究‘物件’,在表演舞臺上,其本質實是一種‘符碼’,簡意即指‘物形之外’的另層或多層意涵。”[1]顯然,對“新馬戲”而言,其戲劇性和劇場性的藝術效果是通過“人”(表演者)、“技巧”(雜技或舞蹈)及“物件”(道具)三者之間的“物我合一”進行演戲與表現的。如在《TOUCH——奇遇之旅》第4場(雜技節目:拋球,一男三女組成)中,一個如公園街頭藝人般的拋球者,在三個女孩將從一個到兩個再到七個球陸續拋給拋球者的時候,拋球者沉迷于球和自我的世界。在一個到七個球慢慢在拋球者的雙手來回穿梭,或是由拋球者的頭頂滑落到肩上,從左腳彈到右腳,再轉身接住,亦或是一球或多球拋至空間后落在地上,滑向舞臺四周后靜止。這種“球”在拋球者身上和劇場空間的快慢、緩急地來回變動,象征著拋球者人生的起落和世界若即若離的命運關系,以顯示第4場“迷”的主題。
可以說,“后戲劇劇場”顯著的特征是不再以排練與上演虛構性的戲劇為中心任務,而是“一種狀態劇場,一種場景的、動勢的造型劇場。”[2]“新雜藝”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作為“新馬戲”(當代馬戲)藝術的中國探索,同樣是以“后戲劇劇場”和“后現代”戲劇的舞臺特征進行場景布置的。該劇整個舞臺的左右墻和上空的燈光與吊桿被設置成一個可見的(沒有大幕、橫幕、側幕)“主場景”;全臺地面鋪了黑色地膠,舞臺中央有一塊方形的灰色地毯;舞臺的后方有一個鐵架(軟鋼絲),后面是一道黑幕,再后面是一道斑駁的天幕(用燈光變換顏色);舞臺的右下有一張長椅(蹬傘),左下有一條紅絲帶(單人綢吊)懸掉著,整體上以一種灰冷色調和破舊場景顯示著“后戲劇劇場”和“后現代”戲劇如何演繹未來100年公園(可能曾經的雜技舞臺)的劇場空間與時間質感。
在“后戲劇劇場”不再以排演虛構性世界為中心任務時,“它也把異質空間、日常空間、一種處于帶框的劇場和‘未加框’的日常現實之間的廣闊范疇囊括進來。”[3]“后戲劇劇場”這種把異質空間、日常空間共置于舞臺的即時空間的表現形式,展現了“后現代”戲劇藝術(新馬戲)敘事文本莊嚴性、純粹性的消解,及所極力追求與表現的戲劇藝術突出虛無、強調怪誕和玩世不恭的“折中主義”的藝術效果。“新雜藝”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中設置了飛機板男、智者、男孩、蹬傘女、柔術女(雙胞胎2人)、拋球男、綢吊女、車技女(2人)、雙人綢吊(男女各1人)、飛竿男、無名氏共11個表演角色(共17人)。在每個場次雜技節目人員固定不變的情況下,以未在場上即時演出的演員(8人)和其他人員(6人)有序組合成一個“無名氏”陣容,以兩人4人一組或5人一組的形式,來回穿過每個場次的表演中(部分無名氏為表演人員傳遞或撤走道具),創造出“后現代”戲劇所具有的日常空間(100年后的公園演出、行人走動)、異質空間(戲劇演出的突兀、怪誕或玩世不恭特征),以突出“新馬戲”藝術的“后現代”戲劇特征。
《TOUCH——奇遇之旅》作為一部在劇場內演出的“新馬戲”(當代馬戲)實驗劇,其戲劇主題的藝術性表現與感知,劇場舞臺的場景布置、空間感,展現了在“后戲劇劇場”和“后現代”戲劇的發展趨勢下,中國當代雜技藝術主題化、劇目化發展之后表現出的新可能與新方向。可以說,《TOUCH——奇遇之旅》在緊跟世界“新馬戲”(當代馬戲)藝術發展的大潮中,不僅彰顯中國雜技藝術特色的努力與探索,也顯示了中國雜技與世界雜技本質的發展與追求。
三、“新雜藝”的探索價值與可能
從對西方“新馬戲”制作理念和編創方式的理解與執行,到對“新馬戲”的“后戲劇劇場”與“后現代”戲劇發展特征的把握,中國雜技團這部“新雜藝”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不僅展現了中國當代雜技與西方當代馬戲的融合可能,使中國當代雜技藝術煥發出主題化、劇目化發展之后的新特征與新趨勢;而且從該劇編創、演出及營銷的整個過程看,也承載著中國雜技團探索如何實現中國當代雜技藝術邊界的新突破和深入融合世界馬戲(雜技)營銷市場及發展格局問題。可以說,“新雜藝”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表現了中國雜技團和從業者一種國際性的眼光與視野。
第一,從“雜技主題晚會”“雜技劇”到“新馬戲”(當代馬戲),“新雜藝”建構中國當代雜技的邊界突破。
中國當代雜技的巨變與轉型,始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雜技主題晚會”和“雜技劇”。中國當代雜技的這一主題化、劇目化轉型一方面改變了傳統雜技重“技”而不重“藝”的“炫技”和新時期以來雜技觀眾銳減及演出市場不景氣問題;另一方面則是以戲劇和劇場的表現與創意思維,賦予當代雜技藝術以審美特征,進而實現當代雜技藝術的劇場與市場轉型。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雜技藝術的主題化、劇目化轉型,有關人士以“‘類型雜技節目’→‘標題雜技節目’→‘主題雜技晚會’→‘雜技劇’”的發展圖式加以概觀。而中國各省市的雜技團體和從業者亦是繼續思考當代雜技新的發展形式。2018年,中國雜技團上演的“新雜藝”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積極借鑒西方國家“新馬戲”制作經驗與演出形式,創編具有中國特色的,對中國當代雜技藝術主題化、劇目化轉型后的邊界突破(新馬戲),無疑具有深遠肇始與導引意義。
第二,“后戲劇劇場”的積極探索,創造中國當代雜技藝術的戲劇性、詩意性表達與審美。
近年,法國Camille Boitel劇團,加拿大炫光馬戲工場和七指劇團帶入中國市場的《此時此刻》(2014)、《大都會》(2016)、《Réversible》(2017)等“新馬戲”劇目,為中國當代雜技藝術和從業者形象而具體地展示了在“后戲劇劇場”和“后現代”戲劇語境下,馬戲(雜技)中具有的多維演繹空間與可能。所以,中國當代雜技藝術的“新馬戲”探索與實踐,需要我們用奇思妙想將東方技藝的精華通過“新馬戲”路徑的探索充分釋放。中國雜技團“新雜藝”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即是在“新馬戲”的“后戲劇劇場”和“后現代”戲劇的思維與趨勢下,結合中國雜技自身的主題化、劇目化及高難度技巧等特色講述人的故事,創造中國當代雜技藝術的戲劇性、詩意性表達與審美。
第三,積極探尋中國當代雜技藝術的跨國聯合創編、演出及合作的經驗。
國際一流藝術家的聯合創編與演出早已是西方馬戲行業營銷的主要方式。中國雜技團“新雜藝”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的創編,體現了西方馬戲行業跨國聯合創編的特征。為了打造這部劇,中國雜技團聘請了多名國際一流的藝術家進行聯合創編。而該劇在演出時展現的良好戲劇效果、舞臺效果、視覺效果、音樂效果,也證明了這種聯合創編的價值與意義。可以說,該劇的聯合創編為中國當代雜技藝術積累了開展跨國聯合創編、演出及合作的經驗。
第四,“新雜藝”實驗,引導中國當代雜技藝術與世界馬戲(雜技)市場對接和前景開拓。
相對于西方國家的傳統馬戲和“新馬戲”,以高難度技藝著稱的中國雜技在世界馬戲(雜技)市場和觀眾面前,表現出節目編排及創意方向的薄弱和不足。所以,雖然“中國雜技以它高超的技巧、獨特的風格在國際上獨領風騷,備受青睞,成為我們對外商演創匯的大戶”[4],但依然不能改變中國雜技藝術在世界馬戲(雜技)市場相對被動和喜憂參半的境地。雜技藝術作為每年占據中國對外商業性演出80%的藝術門類,理應在世界馬戲(雜技)市場中有更多的營銷空間。中國雜技團“新雜藝”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體現出中國當代雜技藝術與世界馬戲(雜技)市場對接和開拓意愿與追求。“該劇在創排時就得到了國際演出商的關注,目前已經成功簽約國際演出訂單,且仍有數個邀約在洽商過程中,首演后該劇將赴世界各地展示中國雜技藝術的當代風采。”[5]
綜上而論,“新雜藝”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為中國當代雜技藝術帶來從“雜技主題晚會”“雜技劇”到“新雜藝”的變化,顯示了該劇所具有的超前性與引導性的探索價值。同時,在“后戲劇劇場”、“后現代”戲劇發展趨勢下,《TOUCH——奇遇之旅》以世界“新馬戲”的藝術理念、節目的跨國聯合創編、演出及世界市場的節目定位與營銷經驗為劇目本身的制作理念,也將為中國當代雜技藝術在世界馬戲(雜技)市場開拓更多的合作與營銷空間,這將提升中國當代雜技在世界馬戲(雜技)中的形象與地位,它對推進中國當代雜技藝術發展表現出有益價值與可能。
結語
“新雜藝”是中國雜技團“新馬戲”(當代馬戲)實驗劇《TOUCH——奇遇之旅》的“命名”,它顯示了中國雜技團和從業者為推動中國當代雜技藝術發展與轉型所作的新探索與抱負。以西方國家流行的“新馬戲”風潮的創編和演出經驗及世界營銷模式為自身的參照,相對于中國現今已有的主題雜技晚會和雜技劇,《TOUCH——奇遇之旅》的確在劇目的戲劇特征、節目的難度思考及舞臺審美方面表現出新的特點和變化。在“后戲劇劇場”和“后現代”戲劇發展趨勢下,顯然“新馬戲的界限有待于解釋”(田潤民語),但《TOUCH——奇遇之旅》作為中國首部“新馬戲”(當代馬戲)邊界突破的劇目,其引發的中國雜技與西方馬戲的融合與探索之旅程已經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