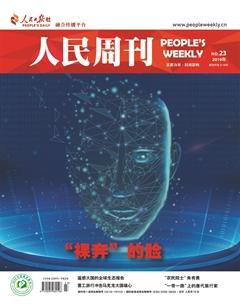那時(shí)雪濃
楊占廠
那時(shí)候,季節(jié)一入冬,天色就開始醞釀雪意了。望著一天比一天弱的日光、一天比一天厚的彤云,舅舅們把屋頂加固嚴(yán)實(shí),舅爹給牛棚里備足草料,舅奶用筷子敲擊腌菜壇子聽聲辨味,而孩子們呢,把用當(dāng)季棉花新做的冬衣冬鞋,都排在了床頭。
就等著雪,紛紛揚(yáng)揚(yáng)地來(lái)了。
比人急的,是大地。從深秋到初冬,收割完莊稼的土地遼闊而寂寞,鳴蟲們一個(gè)個(gè)都遁了,除了略帶綠意的麥苗,整體呈現(xiàn)出蒼黃的暗色調(diào)。那些樹木,成天都在風(fēng)里呼嘯著,夜晚尤其如此;河水也都瘦了,懶得流淌,不如干脆待到冰封就此冬眠。
就等著雪,不遮不掩地來(lái)了。
在連著幾個(gè)密云不飛的陰天之后,雪,來(lái)了。因?yàn)橛羞^(guò)足夠的醞釀和足夠的等待,這場(chǎng)雪,通常都不會(huì)讓天、地、人失望。大人們都待在屋里,這時(shí)候沒有農(nóng)活,雪來(lái)了,意味著可以坦然地冬歇了,爐火更旺了,粥也更燙了。孩子們沖出屋外,跑到野地,仰頭看著大雪或疾或徐地跌落下來(lái),一片雪覆蓋另一片雪,溫柔,決絕。嘶喊著打雪仗,不一會(huì)兒,頭發(fā)、衣服,以及遠(yuǎn)近的田野、村莊,都白了。
這雪從白天下到了深夜,興之所起,一發(fā)難收。雪落并非無(wú)聲,枯枝被壓斷的“咔咔”聲等到醒來(lái),仿佛俗世被按下了暫停鍵,美好的,不美好的,都被封存。雪光經(jīng)太陽(yáng)反射,灼人眼目。雪后巨寒,野外,只剩下嶙峋的樹木站著,看到它們,想起我們,同在人世間把身軀骨骼喂到風(fēng)雪冰凍里煉。而在沃雪之下,麥苗和蟲子們正孕育著又一個(gè)輪回的生機(jī)。
那時(shí)候,放眼曠野,連電線桿都很少,也聽不到機(jī)動(dòng)車的聲音。所以,那樣的雪,和魏晉的雪,唐宋的雪,明清的雪,應(yīng)該是一樣的雪。
這些雪,首先是詩(shī)意的。每一冬,瞇著眼望簾外飄飛不盡的雪,舅爹舅奶的臉上,泛出和他們千年來(lái)的祖先一樣的光芒來(lái),且禁不住地說(shuō):“這么大的雪,開春是個(gè)好年景哩。”
有些大一點(diǎn)的女孩子們,還會(huì)把雪鏟到壇子里,密封,埋入地下,等來(lái)年盛夏取出使用。每逢雪后,三舅總會(huì)去叮當(dāng)河里鑿開一個(gè)冰洞釣刀魚,當(dāng)時(shí)我就覺得那么木訥粗笨的他,其實(shí)內(nèi)心也是有樸素美感的,“獨(dú)釣寒江雪”的剎那雅致,并非文人獨(dú)有。
談到雪中雅致,大概沒有人可以比得上魏晉風(fēng)流吧。那些人活得真叫率性不羈。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四望皎然,忽憶戴安道,時(shí)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經(jīng)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wèn)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lái),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山陰,就是今天浙江的紹興;王子猷,就是王羲之的第五子。那場(chǎng)雪下過(guò)1000多年之后,另一位山陰人張岱,也遭遇了一場(chǎng)雪。彼時(shí)已是明末崇禎五年間了,杭州西湖邊,一場(chǎng)肥雪漫天覆下,人鳥聲絕,張岱去湖心亭看雪,“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長(zhǎng)堤一痕、湖心亭一點(diǎn)、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一痕,一點(diǎn),一芥,兩三粒,這哪里是寫文呢,分明是中國(guó)風(fēng)濃烈的山水畫呀。張岱耐不住好奇心,乘舟去看湖心那舟,舟中兩人,童子以雪煮茶,以爐燙酒。張岱不啰唆,入席浮三大白,返回途中,擺渡人喃喃自語(yǔ),“莫說(shuō)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還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古時(shí)候的雪,是從冬閑里的說(shuō)書人口中聽到的,譬如林教頭風(fēng)雪山神廟,賈寶玉踏雪出家路,那兩場(chǎng)雪,一定特別濃,特別冷,冷到現(xiàn)在讀到這兩個(gè)章節(jié)都能有刺骨的寒意傳來(lái),尤其是寶玉那一段,也是《紅樓夢(mèng)》的終結(jié),“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