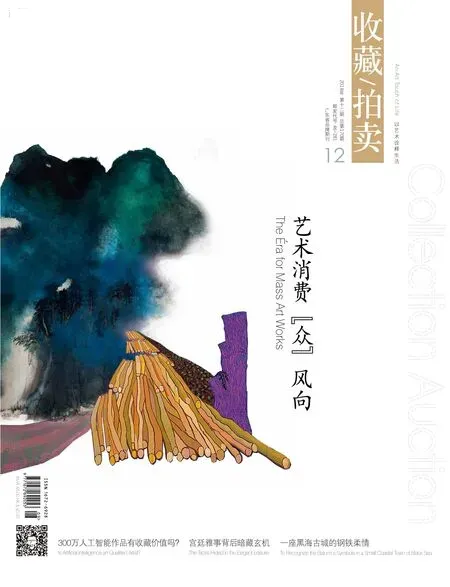宮廷雅事背后暗藏玄機
文/圖:谷卿
雅集是中國文化藝術史上的一道獨特景觀,正是這種隨意性與藝術的本性相契合,使得在歷代文人雅集中產生了大量名垂千古的文藝佳作。往日鑒賞“雅集”主題圖畫,大多是考究古代文士的文化情結與藝術狀態。然而,在對畫中人物和相關事件的歷史背景進行系統梳理的基礎上,發現這些表面上看似日常聚會的圖像背后卻另有隱情。繪制者似乎努力地在用一個雅集的場景承載、蘊含甚或掩蓋那些過于沉重的話題和意義。
“屏中之屏”掀出的謎團
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原本不存,今藏故宮博物院者是后世摹本,一般認為其近于宋人風格,可作宋畫看待。該畫最早著錄于《宣和畫譜》,記為《重屏圖》,其得名之由來,自然是畫中那座“屏中有屏”的奇妙屏風。
北宋名臣王安石曾在友人家見過此圖,他在詩中寫道:“不知名姓貌人物,二公對奕旁觀俱。黃金錯鏤為投壺,粉幛復畫一病夫。后有女子執巾裾,床前紅毯平火爐。床上二姝展氍毹,繞床屏風山有無。堂上列畫三重鋪,此幅巧甚意思殊。孰真孰假丹青摹,世事若此還可吁。”1可以看出,初見《重屏圖》的王安石認為此圖很見巧思,但因無法確知畫中人物身份而微感疑惑,直覺告訴他圖像背后“意思殊”。
《重屏會棋圖》畫的是四名文士模樣的男子,圍坐在室內一張四足低座小榻上所設棋枰的三面,兩人手談,兩人觀看,一旁小童叉手侍立。榻上正中主席一人雍容高貴,峨冠長須,腰間系朱色革帶,應是四人中年齡最長、地位最高者,他的右手持一打開的書冊,或正有所醞釀。并坐于其身旁的男子年紀與之相仿,手搭右側青年左肩,目視棋局,似在催促落子。位于東西二側的兩名對弈男子,皆舉一手,較年輕者持子待落,頗有猶疑之態,稍年長者眼觀對方,意態悠然自若。
畫家花費了不少筆墨用以表現四人所居屋內華貴的陳設,他們身后那座四足有著如意云紋裝飾的矮榻上,放置了一尊古樸的投壺,壺中插有六支無鏃之矢,壺外尚有兩支,打開的棋盒亦極精美。畫面右邊和屏風上所畫的床榻皆有壸門造型,屏外真實的床榻深處,放著一只體型不小的帶座衣匣,其頂部四角有花形貼片,正面箱蓋和箱體之間有金屬飾片,極為雅致;至于畫中榻上,則是一位半躺準備就寢的老翁,足前火盆正熱,左手書案上置書冊、杯盞,身后有婦人傍立,另三名女仆正為之整理氈褥,生活氣息十分濃郁。
然而正是畫中那座奇妙的“屏中之屏”,引來有關故宮所藏此圖繪制時間的異議。巫鴻將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一件明人摹本《重屏圖》與故宮本加以比對,認為后者不會是明代以前的作品,且并不忠實于周文矩原作,他的理由是:弗利爾本畫中單扇大屏上所畫的三折小屏,其旁兩折具有不同的寬度,它們顯示的在三維空間的這一角度由觀者在觀看時所處的位置決定,如此處理的用意在于為觀者造成一種錯視效果,使他們誤以為畫中的三折小屏本是實物,而這頗具機巧的創意一定來自周文矩本人。至于故宮本中單面大屏上所繪的三折小屏,其旁兩折寬度等長,“雖然這種糾正完全合理,但是聰明的摹仿者卻因此而失去原作中‘不合邏輯’的要旨所在。一旦作了這種糾正,這架三折屏風就變成靜態和不透明的了,觀賞者的目光受到了阻礙,周文矩原作中的錯視不再存在”,故而在巫鴻看來,故宮本是一份因“誤讀”“誤改”而產生的晚期摹本。



《重屏會棋圖》,絹本設色,本幅縱40.3cm,橫70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重屏圖》,紙本設色,本幅縱31.3cm,橫50cm,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巫鴻以細致的觀察發現了弗利爾本相對于故宮本的區別和“優勝”之處,即其可以更巧妙地給觀者帶來錯覺,引誘人們相信畫中屏風里的家居景象是真實世界的一部分,并稱這才是畫家周文矩的用心所在。文以誠(Richard Vinograd)也覺得這樣一種對于再現與錯覺的探索應該發生于群像的語境中,暗示了這個時代在肖像畫上制造錯覺的能力以及表征歧義的意識正在增長。可惜的是,周文矩的原作今天已經無法看到,我們當然也很難確知他的繪圖思路,只能根據這兩幅摹本的比較得出一個審慎的暫時性的結論:弗利爾本更具創意。至于故宮本的繪制年代,仍當以其畫風和技藝為判定基礎。
《重屏會棋圖》暗蘊政治隱情
《重屏會棋圖》的構圖確實相當特別,它展示了三重空間,即四人對弈所處的室內場景、對弈者身后屏上的家居場景以及待寢者身后屏上的山水風景,其畫面內容雅致、閑適,足令觀者感到放松。不過,倘若沒有幾位宋元鑒藏家的筆記和題跋的提示,后世當僅單純以“宮中行樂”或“雅集”主題圖畫目之。
最早指認《重屏會棋圖》中對弈和觀棋人物身份并指明屏風畫意者,是南宋的王明清,他在《揮麈三錄》卷三中記道:
樓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榘所畫《重屏圖》,祐陵親題白樂天詩于上,有衣帽中央而坐者,指以相問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頃歲大父牧九江,于廬山圓通寺撫橅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此繪容即其人。文榘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畫一時之景也。”亟走介往會稽,取舊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服,無豪發之少異。因為跋其后。樓深以賞激。2
王明清在此披露了有關《重屏會棋圖》的兩個重要信息:一是圖中所繪的核心人物為南唐中主李璟;二是大屏上的場景為據白居易詩意所繪。這一看法得到后來一些學者的證明和補充,比如元人袁桷在《題模本重屏圖》中不但重申了王明清的意見,而且具體說出宋徽宗在畫前所題白詩究竟是哪一首3,《硯北雜志》也將這首詩抄錄出來“: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有趣的是,白居易有意引導人們將一個生活場景視為圖畫,而上引王安石的詩顯然由觀圖而生對于“世事”的思考,他們描述的無不是有關“孰真孰假”的造設、迷惑與恍然。
《重屏會棋圖》中最重要人物的身份得以確認后,圍坐在他身邊的三名文士也被一一指認出來:“圖中一人南面挾冊正坐者,即南唐李中主像。一人并榻坐,稍偏左向者,太弟晉王景遂。二人別榻隅坐對弈者,齊王景達、江王景逿兄弟。” 記述者莊虎孫沒有詳細介紹這一說法的根據,但并不妨礙當代學者據之考索《重屏會棋圖》背后的政治隱情。比如余輝根據畫中四人座位順序以及棋盤上棋子的奇異狀態,認為該畫實際體現了李璟本人的意志,暗契當時他有關皇位應當依循“兄終弟及”之例的表態,至于景逿以一枚黑子占樁,用另外七枚黑子擺成勺狀北斗的樣子正對著手持譜冊的李璟,是為了說明弟弟們對于兄長地位及他所擬定秩序的服從和遵守。4李凇則嘗試解讀出畫中的另一些意涵,他發現李璟、景逷均著素色布衣且前者衣衫不整,景遂著紅衣,景達著黃衣且衣紋經過精心勾染,身份等級當為最高,李璟的目光投向景達,可證景達才是畫中核心人物,而與其余幾位兄弟非同母所生、地位最低的景遂被擋住半邊臉,表明其只是一個過渡式的人物,手執黑子是表明順從之心,至于畫中屏風上的樂天詩意圖,實非隨意繪成,它蘊含了李璟欲讓位給景達、自己則以白居易為榜樣退位隱居的深意。基于這些觀察和分析,李凇聯想到李璟兄弟盟誓和宋太宗在帝位繼承上的相似性,推測《重屏會棋圖》或為周文矩入宋后為太宗所畫,用以迎合、比附太祖太宗兄弟之間的傳位。

《聽琴圖》,絹本設色,縱81.5cm,橫51.3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其實,以雅事暗蘊禮制是古畫中常見的做法,就像上述《重屏會棋圖》,畫家不僅利用畫中人下棋布子透露他想傳達的意圖和消息,同時還借助榻上的投壺給予觀者隱微的暗示。在古代早期飲宴活動中,投壺的身影頻見,它既是有關射禮的“禮器”,承載著禮儀和秩序,又是一項富含娛樂意味的游戲,這也是《重屏會棋圖》兼具“雅集行樂”和“遵儀定序”兩重主題的象征。
《聽琴圖》用雅事承載雙重主題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典型例子是《聽琴圖》。這幅畫之所以聞名遐邇,多半因為在常見的美術史敘述中,它都被當作是宋徽宗的自畫像。這個說法的來源實是清人胡敬,他經過比對南薰殿所藏三幅徽宗畫像,在筆記中指認《聽琴圖》中彈琴者為徽宗,并順道批評了在畫上題詩的蔡京太過肆無忌憚。5
胡敬對蔡京的批評提示并引發了一種反對意見,如謝稚柳根據蔡京題詩的位置和語氣認為,《聽琴圖》根本不可能出自徽宗之手,也非代筆,而是畫院中人所作。 倘若這一看法符合事實,《聽琴圖》自然就與所謂“自畫像”無涉。雖然《聽琴圖》可能并非出于徽宗真筆,但其上題識不像是偽造,因此研究者仍愿相信它還是體現了徽宗本人的意志,特別是畫中彈琴者的打扮如同一位得道的羽士,這也完全符合徽宗崇信道教的史實和人們對于這位“教主道君皇帝”形象的想象。
曾有學者公開表示,《聽琴圖》的內容雖然為琴事,但不能視為有關“雅集”的圖像,原因是“聽琴”這一活動的主導者是皇帝,其間所含政治意味過于濃重。不過,《聽琴圖》的情況實際比較復雜,畫中徽宗的形象并非完全寫實的帝王尊容,而是他理想狀態的呈現——假如彈琴者真如胡敬所確信的那樣是徽宗本人的話,那么他將是宋代唯一一位在畫中身著“休閑服”的皇帝。
應當留意的是,優雅畫面的背后仍然隱藏著有關政治的表達。王正華的研究認為,畫中兩位身穿不同顏色官服的聽琴者,是全體文人官僚的代表,他們在畫中所處的位置和凝神靜氣恭敬聆聽的神態,顯示出一種森嚴而不容置疑的階級性和秩序感;而徽宗所彈的音樂當然不是為了娛賓遣興,那是一種能正是非的道德之音,因此畫上題名“聽琴”而非“彈琴”,即在強調所演奏的音樂有其感化的對象,帝王的德音能夠被臣子接受而遵奉。由此視之,《聽琴圖》之“雅”,可謂是“言王政之所廢興”之“大雅”。
某種程度上來說,《聽琴圖》的場景是徽宗虛構的一場雅集,《重屏會棋圖》可能也是如此:沒有文獻證明徽宗曾在禁中為臣下彈琴,也很難查到有關李璟召集三位兄弟一起下棋或進行投壺比賽的記錄。但假如我們據此否定上述兩圖的畫面真實的話,顯然也不合適,更何況繪制者已然十分努力地在用一個雅集的場景承載、蘊含甚或掩蓋那些過于沉重的話題和意義。
注解:
1.此詩亦見載梅堯臣詩集,題作《二十四日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錄其所見》。
2.(宋)王明清撰:《揮麈錄》,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264頁。
3.(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欽定四庫全書本,第15頁。
4.詳參余輝:《古畫深意——試析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特展中的三件名作》,《榮寶齋》,2016年第4期;又見《宋代宮廷繪畫里的政治秘辛》,載《“宋代的視覺景象與歷史情境”會議實錄》,第197—199頁。
5.(清)胡敬:《西清劄記》卷二“宣和聽琴圖”條案語:“此徽廟自寫小像也,旁坐衣緋者當是蔡京,題御容乃敢以行押大書幅端,亦無忌憚之甚矣。”見《胡氏書畫考三種》,清嘉慶二十一年刻本,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