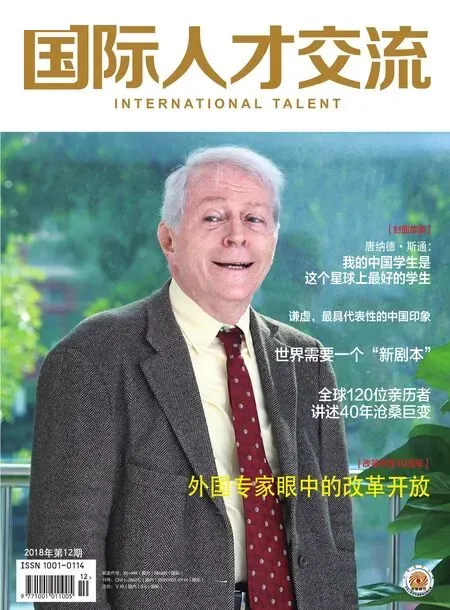我參與中國國有企業的重組
文/龍安志(美) 譯/諶融
1994年,作為一名走南闖北參與合資企業談判的年輕律師,每天我都生活在一場重組中國國有企業的大規模試驗中。每當有外國企業與中國國企開啟合資經營,便意味著針對后者的重組工作拉開帷幕。我在工廠里待了好幾年,調整管理架構、清點企業資產,想方設法將債務轉化為股權。
“活力28”的試驗
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活力28”,這是一家坐落于湖北省荊沙市(后更名為荊州市)的國有洗滌劑工廠。它是一家典型的國有企業,老板是本地人,名叫滕吉新(音譯),心思活絡。除了生產肥皂和洗滌劑之外,滕吉新還開辦了不少副業,比如生產衛生巾、瓶裝水,以及開卡拉OK舞廳和餐館等。由于大量應收款項無法收回,這家企業負債累累、不堪重負。但是,與大多數國有企業一樣,“活力28”的管理層無心扭虧為盈,工人們也是得過且過。這扼殺了企業的創造力和競爭力,而這兩大要素對于中國改革開放、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至關重要。中國需要國際營銷、分銷和零售方面的技術、管理技能和知識。
合資經營談判經常會在如何裁員這個問題上談崩。由于外企進行了技術升級,往往使得中方企業2/3的勞動力成為多余。對于中國領導層而言,這可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大難題。在中國,“鐵飯碗”的觀念根深蒂固。當然,這也是造成中國國企效率低下的部分原因所在。如何才能夠在不打破“鐵飯碗”的同時釋放中國人民的創業精神?
外國投資者在中國裁員,政府必須要找到恰當的應對方法。德國利潔時集團亞洲區總裁桑杰·班達里到訪“活力28”總部時,問題的答案出現了。當時,中德雙方的合資經營談判已經拖了好幾個月,班達里此行希望能夠給談判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班達里抵達荊沙市后,滕吉新沒有安排他入住酒店,而是用一輛警車把他和我拉到一個人潮聚集的十字路口,那里新建了一座人行天橋,正在舉行落成剪彩儀式。滕吉新邀請我們跟他一起走上人行天橋,他滿面笑容地向橋下的民眾揮手。這座天橋被命名為“活力28”,因為造橋的錢是“活力28”出的。
班達里問我這是怎么回事,我嘗試“翻譯”了滕吉新想要表達的信息,“滕吉新是在想辦法打破我們的談判僵局。‘活力28’為荊沙人民建了一座天橋。現在,利潔時必須為工廠的工人們向‘活力28’提供資金。”班達里吃了一驚:“是這么回事嗎?”“是的,”我解釋道,“一切都是旁敲側擊。你必須要抓住要點,因為他在談判桌上不會告訴你。所以,要靠你自己來弄清楚他的意思。這就是中國的方式。”
因此,利潔時沒有進行大規模的裁員,而是又建了一個合資企業以提高“活力28”其他副業的產能,比如衛生巾和瓶裝水,這些與利潔時的主業洗滌劑毫不相關。事實上,這成為中國第一個合資股權投資基金。該基金由利潔時出資設立,但交給中方合作伙伴管理。在滕吉新的領導之下,基金投資新的產業以重新雇用多余的勞動力。
我們在“活力28”進行的這場試驗,被當作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典范。“活力28”股權投資基金成為全國性的下崗工人再就業計劃的一部分。
一方面,身為大型跨國公司的內部法律顧問,顯而易見,公司管理層將生產制造外包給中國,不僅希望從中國出口,還想要接管中國的品牌和市場。另一方面,我站在一場又一場先鋒試驗的最前沿,推動中國的商業和社會結構轉型。但當時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正身處一場重組中國國企的大規模試驗的前沿。與此同時,中國的國企改革不斷深入,隨即迎來了朱镕基總理1998年開啟的新一輪改革。
從安徽到全國
1997年,一場全國性的改革從安徽省開始,這里是20年前自由市場改革開始的地方。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紅手印,拉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基于這種歷史沿革,安徽省被選為四大行業工業企業改革的試驗場。如若重組理念取得成功,這可能成為一場全國性的國企改革的試點甚至藍圖。我受邀擔任小組負責人,也可以說是試驗的協調人,小組成員包括來自國家層面和安徽省政府不同部門的代表,以及東歐專家,他們將分享后蘇聯時代推行類似改革的經驗。在另一個由中國經濟學家和官員組成的小組的協助下,我們考察了鋼鐵、水泥、化工和化肥這四大行業的大型工業企業。

本文作者龍安志
每一家企業都背負著巨額債務,由于過去數十年間企業接受來自不同部門的政府資金,譬如工業部、地方政府、省政府和國家層面,債務情況錯綜復雜。40年后,這些資本線相互交織、亂成一團。它們究竟是撥款還是貸款?它們是否被記入賬本?又是如何記入的?這些問題看起來似乎難以解答。
當生鐵從生產線上滾下來的時候,我能聞到生鐵燜燒的味道,氣味四散開來。“我們所有的設備都是六七十年代購入的,”王廠長介紹設備情況時不自覺地搖了搖頭,“所以我們的產品無法與韓國進口的產品競爭,除非我們可以購買必需的技術。但是,這需要巨額資金注入。怎么樣才能拿到這筆錢呢?沒有投資者愿意接手我們企業背負的社會重擔。”工人們轉過頭來好奇地打量著我們,他們單調重復的工廠生活里,鮮少有機會見到外國人。
離開生產車間后我們開車經過了工廠附屬的學校、幼兒園、食堂、診所、康樂中心和退休人員活動中心。這家工廠就像是一個五臟俱全的小型城市,工人在這里出生、上學、結婚、工作、生活、死亡。
“我們有5萬人口居住在這里,包括退休職工和工人家屬,我們必須保證這些人的生計。”王廠長說,“工人的數量大約有兩萬。為了實現效能最大化,我們需要約2000臺現有設備。如果可以進行設備升級,我們完全可以與韓國鋼鐵競爭,甚至還可以減少一部分人力。”
這似乎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間,必須面對的、難以克服的挑戰。
國有企業負責工廠職工和干部的住房、醫療和退休,基本涉及生活、社會、物質福利等方方面面。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內亂、內戰、外國入侵和半殖民化之后,這種國有企業模式實際上解決了新中國成立時面臨的核心問題。
可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競爭中,中國的企業必須要擺脫其背負的社會重擔。這要求從醫療到教育、從住房到保險的全面商業化。
所有這些都需要法規規范,但當時幾乎沒有。最終,所有成本都將轉移至資本市場。舉個例子,企業甩掉住房負擔需要進行銀行改革,讓老百姓可以貸款購買自己的住房,讓開發商可以貸款蓋樓。同時,這也需要法律上的擔保,保障土地權和所有權,這又需要法律層面的改革。
因此,1998年中國開始對國有企業和整個社會構架進行重大調整。醫療服務的商業化和養老基金的引入意味著改組保險業,而這又要求進行全面金融改革。這件事情太復雜了,只有按順序調整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才能解決。
甩掉這諸多負擔,國有企業才能輕裝上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