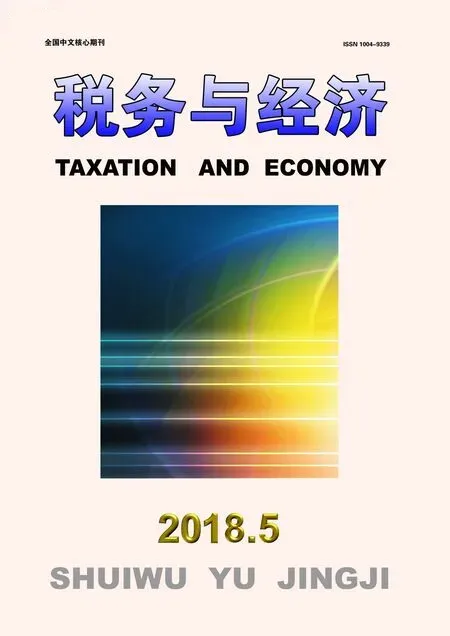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的舉證責(zé)任:現(xiàn)行法的厘清與建構(gòu)
湯潔茵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大學(xué) 政法學(xué)院,北京 102488)
由于避稅安排對國家稅基的侵蝕,近年來各國的反避稅之戰(zhàn)可謂愈演愈烈。避稅與反避稅有如征納雙方之間一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較量。一項以減輕稅負(fù)為目標(biāo)的交易,在征納雙方之間難免形成節(jié)稅抑或避稅的分歧。受到反避稅調(diào)整的納稅人往往面臨稅額的巨額調(diào)增,對納稅人利益影響甚巨。不僅如此,反避稅規(guī)則本身包含了大量的不確定概念和巨大的自由裁量權(quán),有如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從事經(jīng)濟生活安排的納稅人為免遭反避稅調(diào)整,不得不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盡管各國立法設(shè)定了諸多的程序規(guī)則,拘束稅務(wù)機關(guān)從事實調(diào)查到法律適用乃至決定做出的全過程,卻依然無法消解交易從依“形式”到“實質(zhì)”課稅調(diào)整的不確定性。否定真實、合法、有效且已為誠實申報的法律形式,發(fā)掘被隱藏的經(jīng)濟實質(zhì)并據(jù)以課稅,稅務(wù)機關(guān)應(yīng)為事實之查明程度如何、或雖為事實之調(diào)查卻難為形與實之辨又當(dāng)如何,當(dāng)前規(guī)則或者語焉不詳,或者言語含糊,稅務(wù)機關(guān)這一應(yīng)稅事實認(rèn)定的裁量權(quán)限亦因此越發(fā)不受拘束。在實踐中對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有關(guān)舉證責(zé)任存否的爭議頗多,又與納稅人提供證據(jù)資料的協(xié)助義務(wù)糾葛不清,實有進一步闡明之必要。
一、“形似”的反避稅調(diào)查舉證責(zé)任規(guī)則:現(xiàn)行法的誤讀
在稅收行政程序中有關(guān)應(yīng)稅事實的舉證責(zé)任,現(xiàn)行立法——包括《稅收征管法》和各個單行稅種法,未見明確的規(guī)定。*在稅收行政復(fù)議和訴訟程序中,應(yīng)稅事實的查明適用行政復(fù)議與行政訴訟的一般舉證責(zé)任規(guī)則。在反避稅的眾多規(guī)范性文件中卻有不少條文包含“提供資料”、“證明”等用語。如《特別納稅調(diào)整實施辦法(試行)》第84條規(guī)定:“中國居民企業(yè)股東能夠提供資料證明其控制的外國企業(yè)滿足如下條件之一的,可免于將外國企業(yè)不作分配或少分配的利潤視同股息分配額,計入中國居民企業(yè)股東的當(dāng)期所得……”。此類規(guī)則因此被冠以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之名。如有學(xué)者認(rèn)為《特別納稅調(diào)整實施辦法(試行)》第95條即屬納稅人應(yīng)對經(jīng)濟安排具有合理商業(yè)目的這一事實要件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的規(guī)定。
從外形上看,舉證責(zé)任固然包含了“提供資料”、“證明”的要求,但是否設(shè)定了“提供資料”、“證明”義務(wù)的規(guī)范均屬于舉證責(zé)任的范疇,則不無疑問。那么,不妨對現(xiàn)行立法中疑似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的條文做逐一的梳理,以考察其是否真正涉及舉證責(zé)任分配的問題。
在現(xiàn)有反避稅規(guī)則中,多個條文均規(guī)定了納稅人負(fù)有就特定事項向稅務(wù)機關(guān)提供法定類型的資料的義務(wù)。除上文提及的條文外,《企業(yè)所得稅法》第43條、《特別納稅調(diào)整實施辦法(試行)》第89條、《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第11條、《特別納稅調(diào)查調(diào)整及相互協(xié)商程序管理辦法》第7條亦有所規(guī)定。從外形上看,納稅人提供資料以證明特定事項,與“就爭執(zhí)之事實,竭盡所能地提出所主張的證據(jù)”[1]的主觀舉證責(zé)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不少學(xué)者正是基于納稅人根據(jù)上述規(guī)則有義務(wù)實施證據(jù)提出的活動而認(rèn)定上述規(guī)則構(gòu)成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2]
然而,將一項證據(jù)提出義務(wù)等同于主觀舉證責(zé)任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原則上舉證責(zé)任與主張責(zé)任是一致的,在收集和提出證據(jù)之前應(yīng)當(dāng)有確實、具體的事實主張的提出,提出證據(jù)資料的目的在于說服裁決者承認(rèn)將產(chǎn)生當(dāng)事人所期望的法律后果的小前提(要件事實)。[3]66兩者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4]51因此,一方當(dāng)事人所承擔(dān)的主觀舉證責(zé)任,應(yīng)當(dāng)是針對能夠使其請求正當(dāng)化的事實進行證據(jù)的提出,亦即當(dāng)事人提出的事實主張,而這些主張含有或表明有利于該方當(dāng)事人的法律規(guī)范的(抽象性)前提條件。[4]46主觀證明責(zé)任與主張責(zé)任是完全相適應(yīng)的概念,其對象和范圍基本上是相同的。
納稅人依照現(xiàn)行反避稅規(guī)則提供相關(guān)資料,卻不以其提出任何確切、具體的事實主張為前提。如根據(jù)《企業(yè)所得稅法》第43條第2款規(guī)定,納稅人提供相關(guān)的資料,并不以其提出具體的“事實主張”為前提,亦不以證明其主張為目的,僅須根據(jù)稅法的規(guī)定或稅務(wù)機關(guān)的指定提供賬簿、憑證等課稅資料或提交納稅申報表,以陳述說明其從事的與納稅義務(wù)發(fā)生有關(guān)的經(jīng)濟活動和事實的真實狀態(tài)。[5]其提供的證據(jù)資料可能對自己有利,也可能有利于稅務(wù)機關(guān)。但只要納稅人提供其控制的、足以證明其經(jīng)濟活動發(fā)生狀態(tài)的資料或向稅務(wù)機關(guān)提供可據(jù)以實施進一步調(diào)查的方法,即使?fàn)幾h事實未能因此獲得全面闡明,亦應(yīng)認(rèn)定其已履行了這一資料提供義務(wù)。因此,單純由納稅人提供相關(guān)資料的義務(wù)并不構(gòu)成舉證責(zé)任的承擔(dān)。
但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納稅人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僅是針對特定事項提供資料,因而此項義務(wù)構(gòu)成主觀舉證責(zé)任。[2]這顯然是將基于主張的舉證責(zé)任與限定事項的解明義務(wù)混為一談。任何進入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的經(jīng)濟交易,在一般稅款確定程序中已全面、充分地履行了課稅資料的提供義務(wù)[注]如在這一程序中納稅人未按規(guī)定提供稅法要求的課稅資料,稅務(wù)機關(guān)可以根據(jù)《稅收征管法》第35條進行稅收核定,確定其應(yīng)納稅額,并無進入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的必要。,所提供的資料包括與應(yīng)稅事實的發(fā)生及其金額相關(guān)的合同、財務(wù)會計報表、協(xié)議書、憑證等,是為“一般事案解明義務(wù)”。在進入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后,為免資料的重復(fù)提供,納稅人承擔(dān)的資料提供義務(wù)宜有所限定,不僅局限于特定交易,也僅限于該交易安排是否存在法律形式的濫用及其真實的經(jīng)濟實質(zhì)等爭議事項。就此限定提供資料說明的特定事項適用于同一類型的案件,并非在具體個案中為適用對其有利規(guī)范而主張的事實。因此,限定事項的解明義務(wù)依然不能等同于主觀舉證責(zé)任。現(xiàn)行反避稅規(guī)則在規(guī)定納稅人資料提供義務(wù)的同時規(guī)定了該義務(wù)未履行所應(yīng)承擔(dān)的法律后果,這是不少學(xué)者認(rèn)為這些規(guī)定完成了客觀舉證責(zé)任分配的原因之所在。如納稅人未在規(guī)定期限內(nèi)提供資料,可以由稅務(wù)機關(guān)在證據(jù)缺失、尚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證據(jù)鏈條做出避稅安排認(rèn)定的情況下,“核定應(yīng)納稅所得額”[注]《企業(yè)所得稅法》第44條。或“根據(jù)已有信息實施納稅調(diào)整”[注]《特別納稅調(diào)整實施辦法(試行)》第95條。。由于是在證據(jù)缺失的情況下所做的事實判斷,最終納稅調(diào)整的結(jié)果便可能與真實的經(jīng)濟實質(zhì)及其發(fā)生額有所偏差,作為納稅人因其不提供或未提供完整的合格資料所承擔(dān)的不利后果。
將此種與實際發(fā)生情況可能存有偏差的調(diào)整結(jié)果視為基于客觀舉證責(zé)任的“敗訴風(fēng)險”,同樣是值得懷疑的。所謂客觀舉證責(zé)任是指在經(jīng)過各方的舉證,在程序結(jié)束時相關(guān)事實仍然真?zhèn)尾幻鞯那闆r下,應(yīng)當(dāng)由哪一方主體承擔(dān)不利的后果。而“真?zhèn)尾幻鳌币辉~指的是在程序結(jié)束時,當(dāng)所有能夠釋明事實真相的措施都已經(jīng)采用,但爭議事實仍不清楚的狀態(tài)。[3]21無論是稅收核定還是在已有資料的基礎(chǔ)上進行事實經(jīng)驗性推斷,都是幫助稅務(wù)機關(guān)最終確認(rèn)稅額的手段,由此稅務(wù)機關(guān)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開始時那種心證模糊的狀態(tài)可以在事實調(diào)查過程中被克服。這種模糊不清是進行稅收核定或事實經(jīng)驗性推斷的前提條件,并在事實調(diào)查過程中存在,與作為證明責(zé)任判決基礎(chǔ)的“真?zhèn)尾幻鳌庇兄鴩?yán)格的區(qū)別。[3]23
因此,盡管不少反避稅規(guī)則均規(guī)定在特別納稅調(diào)整程序中證據(jù)資料的提供以及未提供的法律后果,卻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可以說,在窮盡一切調(diào)查手段而交易的經(jīng)濟實質(zhì)仍然真?zhèn)尾幻鞯那闆r下,稅務(wù)機關(guān)如何做出最終的決定依然并無明確的規(guī)定。此種立法上的空白究竟是立法者的疏忽,還是在這一行政程序中并無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介入的必要,筆者認(rèn)為有必要予以考察。
二、反避稅調(diào)查舉證責(zé)任存否之爭及其射程范圍的限定
證明責(zé)任一向被視為訴訟的脊梁。在涉稅爭訟案件中,如有疑問的事實情況不能得到確認(rèn),舉證責(zé)任規(guī)則同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稅法并未對涉稅爭訟案件規(guī)定特殊的舉證責(zé)任規(guī)則,而是適用《行政復(fù)議法》和《行政訴訟法》的一般規(guī)定。[注]《<稅收征管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見稿)第130條對稅務(wù)行政復(fù)議中的舉證責(zé)任做出了規(guī)定。稅務(wù)行政程序中是否也有舉證責(zé)任作用的余地,由于當(dāng)前行政程序法的缺失,《稅收征管法》中亦無明文規(guī)定,致使其在實踐中每每有所爭議。這一問題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之下同樣存在。
(一)基于稅務(wù)機關(guān)的職權(quán)調(diào)查的舉證責(zé)任存否之爭
證明責(zé)任對一項訴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否僅對“訴訟”具有重要意義,學(xué)界存在頗多的爭議。訴訟是一項解決爭議的活動。在這一活動之下,除發(fā)生爭議的兩方當(dāng)事人外,與糾紛雙方不存在任何利害關(guān)系的司法機關(guān)通過各種方法查明爭議事實的發(fā)生,以確定規(guī)范中抽象表述的要件是否已成事實。但稅收征管顯然并非一種“訴訟”活動,而是稅務(wù)機關(guān)在實施稅收征管行為時所應(yīng)當(dāng)遵循的方式、步驟、時限等連續(xù)的過程。[6]在這一過程中并不存在獨立的爭議裁決者,而只有征納雙方當(dāng)事人。稅務(wù)機關(guān)既是一方當(dāng)事人,又是最終的決定者和法律適用者。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并不必然存在征納雙方對事實認(rèn)定的認(rèn)識分歧。征納雙方的目標(biāo)僅在于在查明應(yīng)稅事實的基礎(chǔ)上進行稅法的適用,以實現(xiàn)征管權(quán)。那么,在既無訴訟又無爭議的稅收征管程序中是否有必要引入舉證責(zé)任規(guī)則,則十分有必要予以討論。
當(dāng)前主張稅務(wù)行政程序中同樣存在舉證問題的學(xué)者對此大多語焉不詳。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回到最初的原點,即證明責(zé)任規(guī)范的價值何在。法律抽象表述的要件為規(guī)則調(diào)整的出發(fā)點,當(dāng)這一抽象要件變成具體的事實,將產(chǎn)生相應(yīng)的法律后果。因此,一項法律后果的產(chǎn)生,必須根據(jù)被法律規(guī)定為前提條件的事實情況是否發(fā)生來決定。然而,受限于認(rèn)識手段和能力,事實的查明并非總能盡如人意。作為法律適用小前提的事實不可能在每一個細(xì)節(jié)上均得到澄清。即使如此,法官卻不能因為此種事實問題存有疑問而拒絕做出相應(yīng)的裁決。只要判決的訴訟條件基本具備,法官必須做出有利于一方當(dāng)事人的判決。證明責(zé)任規(guī)范的本質(zhì)和價值在于,在重要的事實主張的真實性不能被認(rèn)定的情況下,引導(dǎo)法官如何做出判決。[4]2證明責(zé)任規(guī)范的任務(wù)恰恰是避免因事實主張的不確定性而使判決成為不可能,其核心不是對當(dāng)事人訴訟活動形成壓力,而是指示法官在重要的事實主張沒有得到證明的情況下,如何決定其判決的內(nèi)容。
實際上,這一問題在任何一個將抽象的法律規(guī)范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事實的過程中均要求得到回答,不僅是在適用言辭辯論原則的程序中。[4]83稅務(wù)機關(guān)行使征稅權(quán)的過程同樣是法律適用的過程。基于稅收法定主義的要求,稅收債務(wù)在稅法規(guī)定的抽象構(gòu)成要件實現(xiàn)時才告發(fā)生。因此,稅收債務(wù)以課稅事實的發(fā)生為前提,因此有必要調(diào)查完全正確的應(yīng)稅事實,才能實現(xiàn)稅法的適用。[7]但在稅務(wù)機關(guān)進行課稅事實調(diào)查的過程中同樣可能面臨作為稅法適用前提的課稅事實既不能確定已經(jīng)發(fā)生,也不能確定沒有發(fā)生的情形。由于稅收乃是國家最重要的財源收入,直接關(guān)系國家機關(guān)的運作與公共服務(wù)的及時、有效的提供。因征稅權(quán)的行使本身固有效率的要求,稅務(wù)機關(guān)不僅應(yīng)當(dāng)能夠基于稅法行使征稅權(quán),而且應(yīng)當(dāng)能夠以迅捷的方式予以實現(xiàn)。如在此情況下,稅務(wù)機關(guān)因課稅事實的發(fā)生與否存有懷疑而無法做出決定,征稅權(quán)的行使便可能有所延宕甚至無法行使。因此,同樣必須設(shè)定一定的規(guī)范,以指引稅務(wù)機關(guān)在此種情況下如何做出征或不征的決定,“適當(dāng)?shù)摹⒚髦堑淖C明責(zé)任分配屬于法律制度最為必要或最值得追求的內(nèi)容”[4]97。
就證明責(zé)任而言,包含了兩個層次,即主觀證明責(zé)任和客觀證明責(zé)任。所謂主觀證明責(zé)任是針對當(dāng)事人的證明活動,決定何方當(dāng)事人就事實主張應(yīng)當(dāng)提出證據(jù),又稱為行為責(zé)任。客觀證明責(zé)任則是決定何方當(dāng)事人在主要事實真?zhèn)尾幻鞯那闆r下承擔(dān)敗訴的風(fēng)險,即結(jié)果風(fēng)險。[8]證明責(zé)任理論一般認(rèn)為,當(dāng)事人的主觀證明責(zé)任,只有在以辯論原則為基礎(chǔ)的訴訟中,如民事訴訟,才發(fā)揮作用。[4]97那么,在稅收征管活動中的證明責(zé)任的分配是否同時包括這兩個層次,同樣值得關(guān)注。
基于稅收的課征及人民基本權(quán)利保障的公共利益,稅務(wù)機關(guān)在稅收征管程序中居于主導(dǎo)地位,應(yīng)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運用一切手段獲取必要且可取得的事實材料,主動調(diào)查并完整闡明與所有課稅要件相關(guān)的一切事實。此即職權(quán)調(diào)查主義。[注]由于我國并無“行政程序法”,作為基本稅收程序法的《稅收征管法》亦未規(guī)定采用職權(quán)調(diào)查主義。但從現(xiàn)有行政法律來看,如《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等均遵循這一原則,要求行政機關(guān)應(yīng)當(dāng)“全面、客觀、公正地調(diào)查、收集有關(guān)證據(jù);必要時,依照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可以進行檢查”。[7]47稅務(wù)機關(guān)為此負(fù)有“概括的調(diào)查義務(wù)”,即凡與稅款征收相關(guān)而有查明的必要與可能的事實,無論對納稅人有利或不利,均應(yīng)當(dāng)予以調(diào)查。[9]無論納稅人是否提供形式上的證據(jù)材料,稅務(wù)機關(guān)都應(yīng)當(dāng)就應(yīng)稅事實的發(fā)生及其具體狀況展開調(diào)查,不可能如同在以辯論原則為基礎(chǔ)的訴訟中,使提供證據(jù)的義務(wù)隨著稅收征管程序的進展、因應(yīng)需證明的待證事實的改變而在稅務(wù)機關(guān)與納稅人之間發(fā)生轉(zhuǎn)移。正因為如此,德國學(xué)者也大多認(rèn)為在稅收征管程序中納稅人并不負(fù)有證據(jù)提出的主觀舉證責(zé)任。[7]457實際上,主觀證明責(zé)任是典型的“責(zé)任”概念,是當(dāng)事人為了避免敗訴的不利后果而積極舉證的必要或負(fù)擔(dān),與不利后果有必然的聯(lián)系。[8]但在稅收征管活動之中,納稅人提供證據(jù)卻往往并非意在避免納稅義務(wù)的發(fā)生或稅額的增加,反而恰恰在于促使稅務(wù)機關(guān)準(zhǔn)確地查明應(yīng)稅事實的真實樣態(tài),進而準(zhǔn)確地認(rèn)定其稅收負(fù)擔(dān)。因此,納稅人提供證據(jù)或就應(yīng)稅事實所做的陳述僅為稅務(wù)機關(guān)職權(quán)調(diào)查的方式之一,乃作為稅務(wù)機關(guān)查明應(yīng)稅事實的輔助手段的協(xié)力義務(wù),而非主觀證明責(zé)任的承擔(dān)。
與此不同的是,客觀舉證責(zé)任盡管同樣名為“責(zé)任”,卻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責(zé)任”概念,而是一種法律風(fēng)險的預(yù)先分擔(dān)。應(yīng)稅事實同樣是以證據(jù)材料的形式呈現(xiàn)在稅務(wù)機關(guān)面前的。受到調(diào)查方式、認(rèn)知水平和征管技術(shù)等限制,稅務(wù)機關(guān)同樣可能在窮盡證明評價的各種手段后仍無法形成應(yīng)稅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確定心證。然而,稅務(wù)機關(guān)仍有必要做出征稅或不征稅的最終決定。“僅是不確定性這一事實本身就使得所謂的客觀證明責(zé)任規(guī)范的干預(yù)成為必要,而與訴訟的方式無關(guān)”。[4]因此,客觀舉證責(zé)任是作為輔助稅務(wù)機關(guān)進行稅法適用的操作規(guī)范,目的是對應(yīng)稅事實真?zhèn)尾幻鞯娘L(fēng)險進行預(yù)先分擔(dān)。但與訴訟程序下的客觀舉證責(zé)任由法院負(fù)擔(dān)不同的是,稅收征管程序下的客觀舉證責(zé)任只能在征納雙方之間進行分配,指引的是稅務(wù)機關(guān)在爭議事實真?zhèn)尾幻鞯那闆r下如何做出最終的征稅決定。
因此,基于職權(quán)調(diào)查,稅務(wù)機關(guān)對于應(yīng)稅事實的查明負(fù)有證據(jù)的收集和提供的義務(wù),這一義務(wù)并不隨著征管進程而發(fā)生轉(zhuǎn)移。在稅收征管程序中固然有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介入的必要,但需要在征納雙方之間進行分配的僅為客觀舉證責(zé)任,并不包括主觀舉證責(zé)任。
(二)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的爭議屬性與舉證責(zé)任的射程范圍
作為特殊的稅收行政程序,以職權(quán)調(diào)查為主導(dǎo)的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在事實真?zhèn)尾幻鞯那闆r下稅務(wù)機關(guān)同樣必須做出是否施以特別納稅調(diào)整的決定,因此,應(yīng)當(dāng)有證明責(zé)任及其分配的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一過程中發(fā)生的任何爭議問題都可以借助于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做出最終的裁決。就稅法適用的三段論中,抽象的稅法規(guī)范構(gòu)成大前提,而被認(rèn)定為真實的具體應(yīng)稅事實則構(gòu)成小前提。證明責(zé)任的問題僅存在于稅法演繹推理的小前提之中,且只有對擬裁決案件事實的真實性審核,屬于證明責(zé)任規(guī)范的適用范圍。[4]相反,如果是對稅法的內(nèi)容或是具體的法律評價等法律問題存有疑義,稅務(wù)機關(guān)則不得借助于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做出對任何一方不利的最終裁決。
因此,既然證明責(zé)任規(guī)范的使命只在于消除事實方面的疑問,那么,確定反避稅調(diào)查中征納雙方爭議問題的性質(zhì)便尤為重要,即為實施反避稅調(diào)整所需查明的問題是事實問題抑或法律問題。理論上對于反避稅的法律性質(zhì)的爭議使得這一問題更加撲朔迷離。事實擬制說以德國《稅收通則法》第42條第1款的規(guī)定為依據(jù)[注]德國《稅收通則法》第42條第1款規(guī)定:“如有濫用情事,依與經(jīng)濟事件相當(dāng)之法律形成,成立稅收請求權(quán)”。,認(rèn)為避稅交易的認(rèn)定爭議乃在于課稅基礎(chǔ)事實為依民事法成立的法律事實還是被該形式所掩蓋的經(jīng)濟事實關(guān)系,應(yīng)屬事實認(rèn)定上的問題。那么,如作為課稅基礎(chǔ)的法律關(guān)系如何存在或?qū)τ幸蓡柕姆筛拍畹倪m用十分重要的事實情況有爭議且仍有疑問的情況下,應(yīng)當(dāng)有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作用的余地。類推適用說則認(rèn)為,此時征納雙方對于交易之事實并無爭議,只是如依稅法條文的字面解釋進行稅收構(gòu)成要件的涵攝將產(chǎn)生與量能課稅不符的結(jié)果,對此交易則應(yīng)當(dāng)類推適用符合稅法規(guī)范目的的課稅要件。[10]因此,避稅的認(rèn)定應(yīng)當(dāng)為稅法的解釋適用之法,所發(fā)生的爭議為法律問題。如若其是,稅務(wù)機關(guān)在對稅法規(guī)范的解釋或稅法概念的內(nèi)涵和外延存有懷疑時,將不得借助于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做出最終的裁決。
事實上,任何案件的法律與事實問題很難找到一個清晰而明確的標(biāo)準(zhǔn)予以準(zhǔn)確地區(qū)分。作為形成裁判結(jié)論前提的案件事實問題,絕非完全脫離法律的事實,而是高度法律化的事實,具有明顯的法律屬性。[11]這一點在反避稅調(diào)查案件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
《特別納稅調(diào)整實施辦法(試行)》第94條、《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試行)》第5條均規(guī)定了稅務(wù)機關(guān)在認(rèn)定交易構(gòu)成避稅安排的前提下對其重新定性后進行稅法規(guī)則的適用。就此而言,我國反避稅立法似采事實擬制說。[12]那么,既然反避稅調(diào)查的爭議在于與法律形式背離的經(jīng)濟實質(zhì)的存否及其具體狀態(tài)如何應(yīng)屬于事實問題,在無法查明時可以有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的介入。然而,反避稅案件并不僅涉及到單一層面的爭議。稅務(wù)機關(guān)對交易的經(jīng)濟實質(zhì)重新予以定性,必須以交易構(gòu)成避稅安排這一事實作為前提。根據(jù)《企業(yè)所得稅法》第47條的規(guī)定,一項不具有合理商業(yè)目的的交易構(gòu)成避稅安排。國家稅務(wù)總局2014年12月頒布的《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試行)》第4條復(fù)又增加了“以形式符合稅法規(guī)定、但與其經(jīng)濟實質(zhì)不符的方式獲取稅收利益”作為認(rèn)定避稅安排的事實要件。無論交易的商業(yè)目的還是交易形式是否存在濫用情形,應(yīng)當(dāng)都屬于事實問題的范疇。但基于“交易安排與基礎(chǔ)經(jīng)濟事實之間缺乏邏輯和連貫的對應(yīng)性”這一事實的存在,即認(rèn)定一項交易構(gòu)成稅收的規(guī)避顯然是不恰當(dāng)?shù)模吘挂宰陨矶愗?fù)最小化的方式安排其經(jīng)濟活動乃屬納稅人的經(jīng)濟自由。只有當(dāng)此項形式上合法的交易所獲取的稅收利益并不符合稅法規(guī)則的立法目的和意圖時,亦即一項交易所取得的稅收后果盡管形式上符合稅法文義,實質(zhì)上卻是該條文禁止或未有期待的,才能將其認(rèn)定為一項避稅的安排。[13]在認(rèn)定法律形式與經(jīng)濟實質(zhì)的脫節(jié)這一事實的基礎(chǔ)上,還必須判斷交易安排的適用是否符合稅收規(guī)則的立法意圖。因此,對于交易是否構(gòu)成避稅安排的認(rèn)定,確定稅收規(guī)則的規(guī)范目的便至關(guān)重要,尤其應(yīng)當(dāng)考慮稅收規(guī)則對交易是否提供了激勵以及此項激勵的政策考量如何。[14]正因為如此,避稅安排的認(rèn)定往往被認(rèn)為涉及稅法的解釋問題。[15,16]
因此,盡管當(dāng)前立法明確規(guī)定反避稅調(diào)查的目標(biāo)是對被法律形式掩蓋的真正體現(xiàn)納稅人稅收負(fù)擔(dān)能力的經(jīng)濟事件的查明與認(rèn)定,但征納雙方之間的爭議并非純粹的事實問題。交易是否構(gòu)成避稅安排是高度法律化的事實。稅務(wù)機關(guān)除須查明交易的商業(yè)目的以及是否存在獨立于法律形式的經(jīng)濟實質(zhì)等事實要件,還必須審查這一交易安排是否符合立法機關(guān)制定該條文的立法意旨[17,18],亦即此種安排的采用是否與規(guī)則漏洞相關(guān)。此種審查顯然已經(jīng)脫離了事實查明的范疇,而是基于交易的各項安排、當(dāng)事人的意圖等因素來判斷是否存在法律欺詐的意思表示,稅務(wù)機關(guān)不能將此純粹的法律問題按事實問題進行處理,用證明責(zé)任規(guī)避來回避對這一純法律問題的解決。
三、反避稅調(diào)查的舉證責(zé)任分配:基于法律要件分類說
(一)稅收征管程序中舉證責(zé)任分配的一般規(guī)則
盡管稅法學(xué)界力圖尋找一種抽象的、固定的規(guī)則明確客觀舉證責(zé)任在稅收征管程序中的分配,卻收效甚微。從當(dāng)前有限的研究成果來看,一種類似于民事訴訟中的“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zé)任分配原則的觀點逐漸占據(jù)上風(fēng)。如德國學(xué)者Tipke Lang認(rèn)為稅務(wù)機關(guān)應(yīng)就課稅要件、稅收增加和偷逃漏稅的事實要件的滿足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臺灣學(xué)者陳清秀教授所持觀點大體相同,認(rèn)為稅務(wù)機關(guān)對于主張稅捐債權(quán)的事實、撤回稅收優(yōu)惠的前提要件事實、更正補稅規(guī)定的要件事實等,應(yīng)負(fù)擔(dān)客觀舉證責(zé)任,而被請求的納稅人則對于成立稅收減免、優(yōu)惠的事實,廢棄或限縮稅收債權(quán)的事實,負(fù)擔(dān)客觀舉證責(zé)任。[7]大陸地區(qū)學(xué)者大多持相同的觀點。[19]但也有不少學(xué)者僅籠統(tǒng)地論及稅務(wù)機關(guān)對要件事實的證明責(zé)任。[20]
“誰主張,誰舉證”是建立在法律要件分類學(xué)說基礎(chǔ)上的客觀舉證責(zé)任的基本規(guī)則。上述主張客觀舉證責(zé)任在稅務(wù)機關(guān)和納稅人之間進行分配的學(xué)者,正是基于稅收構(gòu)成要件事實的不同類別而進行證明責(zé)任的分配。然而,羅森貝克所倡導(dǎo)的法律要件分類說本是歐陸各國民事訴訟中分配客觀證明責(zé)任的主流學(xué)說,緣何可以在以職權(quán)調(diào)查主義為基礎(chǔ)的稅收征管程序中作為舉證責(zé)任分配的原則,卻鮮少有更深入的探討。法律要件分類說的基本內(nèi)涵是不適用特定的法規(guī)范其訴訟請求就不可能有結(jié)果的當(dāng)事人,必須對法規(guī)范要素在真實的事件中得到實現(xiàn)這一事實承擔(dān)主張責(zé)任和證明責(zé)任,即每一方當(dāng)事人必須主張和證明對自己有利的法規(guī)范適用的前提條件。[4]羅森貝克進一步將民事實體法規(guī)范按照對立關(guān)系分為兩大類,即權(quán)利發(fā)生規(guī)范和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和權(quán)利受制規(guī)范等對立規(guī)范。主張權(quán)利存在的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對權(quán)利發(fā)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實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否認(rèn)權(quán)利存在的當(dāng)事人應(yīng)對權(quán)利妨礙、消滅或限制的法律要件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4]
羅森貝克的法律要件分類說實現(xiàn)了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舉證負(fù)擔(dān)的最大平衡,這正契合了民事訴訟之下當(dāng)事人平等所要求的“武器平等”原則。那么,如果說這一客觀證明責(zé)任在當(dāng)事人之間平均分配的方法可以在稅收征管程序中適用的話,追根溯源,無疑是建立在基于稅收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說構(gòu)建的稅務(wù)機關(guān)與納稅人之間平等地位的基礎(chǔ)之上的。然而,稅收既為國民權(quán)利實現(xiàn)的成本,國家與納稅人在稅收征納關(guān)系的平等地位與民事法主體之間依然有著根本的不同。由于稅收的征收關(guān)系國家機構(gòu)的運作和國民基本權(quán)利的實現(xiàn),稅收債權(quán)的行使具有權(quán)力屬性,是一種“事關(guān)毀滅”的“圈錢”的權(quán)力。納稅人與稅務(wù)機關(guān)之間無論在實體上還是在程序上均處于不相當(dāng)?shù)牡匚弧21]稅務(wù)機關(guān)更可以采用眾多調(diào)查課稅事實和防止稅收逃避的方法。因此,單純就稅收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說推導(dǎo)出稅務(wù)機關(guān)與納稅人之間亦應(yīng)當(dāng)進行客觀舉證責(zé)任的平等分配,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羅森貝克的規(guī)范說僅僅是基于法律要件分類說對民事實體要件的舉證責(zé)任在當(dāng)事人之間進行分配的分類方法之一,卻非唯一的方法。基于法律要件分類說分配刑事證明責(zé)任的分類方法便與此迥然不同。[注]在羅森貝克看來,只有當(dāng)能夠確定具備了全部主客觀要件,且不存在阻卻責(zé)任或阻卻刑罰要素,或者不存在排除責(zé)任或者排除刑罰要素時,國家的刑罰權(quán)才可行使。[4]根據(jù)法律要件分類說分配稅收構(gòu)成要件的舉證責(zé)任的具體方法亦應(yīng)當(dāng)因應(yīng)稅收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價值追求予以確立。
就私權(quán)剝奪的結(jié)果而言,稅收債權(quán)與刑事請求權(quán)有著更大的相似性,前者意在私人財產(chǎn)權(quán)的剝奪與讓渡,后者則事關(guān)生命與自由的剝奪。因此,上述兩種權(quán)力均不可在要件事實尚且存疑的情況下行使,并無疑義。換言之,當(dāng)事實無法確實證明時,不能適用將使人民受到不利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規(guī)范。此事實的證明責(zé)任應(yīng)當(dāng)由權(quán)力的行使主體承擔(dān)。在稅收法定主義之下,經(jīng)濟活動的合要件性為舉證責(zé)任的核心問題。如果合于抽象稅收構(gòu)成要件的事實是否存在尚且真?zhèn)尾幻鳎悇?wù)機關(guān)如即做出征稅與否的決定,將難以確保其行為的合法性。因此,在稅收征管程序中應(yīng)當(dāng)采取一種將絕大部分法律要件事實的證明責(zé)任分配給稅務(wù)機關(guān)承擔(dān)的具體分類方法。
在法學(xué)上將一定的法律效果的發(fā)生而在法律上所須具備的事實要件的總體稱之為“法律構(gòu)成要件”。根據(jù)羅森貝克的法律要件分類說理論,“不適用特定的法規(guī)范其訴訟請求就不可能有結(jié)果的當(dāng)事人,必須對法規(guī)范要素在真實的事件中得到實現(xiàn)承擔(dān)主張責(zé)任和證明責(zé)任”,“每一方當(dāng)事人均必須主張和證明對自己有利的法規(guī)范的條件”。基于稅收法定主義,稅收債權(quán)在稅法規(guī)定的抽象構(gòu)成要件實現(xiàn)時才告發(fā)生。稅務(wù)機關(guān)欲主張基于特定稅法規(guī)范成立的征稅權(quán),即有必要證明符合這一稅收構(gòu)成要件的事實已經(jīng)發(fā)生。稅收債權(quán)的發(fā)生及其最終金額的確定往往是數(shù)個要件事實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那么,無論特定的要件事實適用的稅法規(guī)范的結(jié)果對哪一方當(dāng)事人有利,只要關(guān)系最終應(yīng)稅金額的確定,均應(yīng)當(dāng)由稅務(wù)機關(guān)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如雖然商品的銷售或勞務(wù)的提供決定了納稅義務(wù)的發(fā)生,但納稅人最終的應(yīng)納稅額實際上還取決于其為生產(chǎn)商品或提供勞務(wù)購進商品或勞務(wù)并負(fù)擔(dān)增值稅稅款的事實。盡管這一事實為最終的納稅金額的減項,稅務(wù)機關(guān)同樣負(fù)有查明的義務(wù),并在事實真?zhèn)尾幻鞯那闆r下負(fù)擔(dān)不利的結(jié)果。
(二)特別納稅調(diào)整程序下是否真的需要“特殊”的舉證責(zé)任規(guī)范
特別納稅調(diào)整程序下,稅務(wù)機關(guān)為保證其行為的合法性同樣負(fù)有職權(quán)調(diào)查之責(zé),這與一般稅收征管程序并無不同。然而,仍有不少學(xué)者認(rèn)為,在這一特殊程序之下,舉證責(zé)任應(yīng)有必要發(fā)生倒置,即由納稅人承擔(dān)特定要件事實的客觀舉證責(zé)任。如有學(xué)者認(rèn)為,納稅人應(yīng)當(dāng)對其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商業(yè)目的這一事實承擔(dān)客觀舉證責(zé)任。[2]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由納稅人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乃是國際經(jīng)驗,應(yīng)有必要予以借鑒。[22,23]那么,為探求被法律形式所掩藏的經(jīng)濟實質(zhì),以真正實現(xiàn)量能課稅為目標(biāo)的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是否有必要在稅務(wù)機關(guān)與納稅人之間確立特殊的舉證責(zé)任分配方法則值得探究。
盡管多有學(xué)者論及反避稅調(diào)查中納稅人應(yīng)承擔(dān)一定的舉證責(zé)任,卻鮮少對其具體的理由加以深入分析。但從有限的論點觀之,納稅人刻意隱藏交易實質(zhì)所造成的證據(jù)偏在與稅法欺詐意圖的證明困難,是秉持這一論斷的學(xué)者們較為共通的邏輯起點。但證據(jù)偏在并非反避稅案件所獨有。在當(dāng)前立法之下,被施以反避稅調(diào)查的納稅人不僅在一般稅收征管程序中已盡提供課稅資料的協(xié)力義務(wù),還須就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商業(yè)目的、是否構(gòu)成避稅安排負(fù)擔(dān)“限定事案解明義務(wù)”。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此類案件中可能產(chǎn)生的證據(jù)進一步偏在于納稅人的困境。交易意圖的證明困難在任何類型的案件中并無不同,這即使在民事訴訟中也從未被作為一項要件事實的舉證責(zé)任有必要發(fā)生倒置的理由。相反,將反避稅調(diào)整的全部或部分法律要件的舉證責(zé)任倒置由納稅人承擔(dān)則極有可能對納稅人產(chǎn)生實體上不公平的結(jié)果。
在一般稅收確定程序中,基于誠實推定權(quán),如無據(jù)以懷疑其內(nèi)容真實性的證據(jù),納稅人向稅務(wù)機關(guān)提供的課稅資料將被推定為真實和完整。[24]交易的法律形式既已有充分、合法且被推定為真實、有效的證據(jù)的支撐,稅務(wù)機關(guān)也只有在掌握的證據(jù)足以否定上述事實的情況下,才能使其改以交易的經(jīng)濟實質(zhì)重新確定應(yīng)納稅額的主張得以成立,以確保征稅行為的合法性。
然而,與司法程序中法院作為中立的裁判者認(rèn)定案件事實不同的是,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只存在稅務(wù)機關(guān)和納稅人兩方當(dāng)事人。稅務(wù)機關(guān)乃是對交易的事實屬性存疑而啟動調(diào)查程序者,同時又為證據(jù)的認(rèn)定者和最終裁判者,是納稅人說服的對象。[9]這意味著稅務(wù)機關(guān)實際上同時為當(dāng)事人和裁決者,作為國家行使征稅權(quán)的代表機關(guān),本已有做出對國庫有利的征稅決策的先天傾向,改變稅務(wù)機關(guān)已形成的偏見對納稅人而言難度顯而易見。即使納稅人已竭力提供其控制范圍內(nèi)、與交易發(fā)生相關(guān)的證據(jù)資料,交易事實是否存在真?zhèn)尾幻鞯臓顟B(tài)、是否有必要實施反避稅調(diào)整,最終仍由稅務(wù)機關(guān)自行判定。如果由納稅人對全部或部分要件承擔(dān)客觀舉證責(zé)任,由稅務(wù)機關(guān)承擔(dān)證據(jù)提出的主觀舉證責(zé)任將是毫無意義的。由于交易是否構(gòu)成避稅安排這一事實最終未能獲得闡明的不利后果無須由其承擔(dān),稅務(wù)機關(guān)是否收集證據(jù)、收集何種證據(jù)、收集證據(jù)達到何種程度將缺乏必要的約束,反避稅調(diào)查的實施將可能流于隨意甚至怠于調(diào)查。而納稅人為免事實陷于真?zhèn)尾幻鞯木车兀词共回?fù)擔(dān)證據(jù)提出責(zé)任,仍不得不多方收集證據(jù),而不僅僅提供其控制范圍內(nèi)的證據(jù)資料。作為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的主導(dǎo)者和證據(jù)的最終采信者,稅務(wù)機關(guān)是納稅人提供證據(jù)“說服”的對象,卻也恰恰是對交易的形式與實質(zhì)存疑的反避稅調(diào)查的啟動者,對應(yīng)稅交易的屬性一般已有先入為主的主觀判斷。納稅人即使疲于舉證,也未必可以避免納稅調(diào)整的厄運。加上稅法的繁復(fù)和技術(shù)性,一般納稅人根本無從與具有稅法專業(yè)知識的稅務(wù)機關(guān)相抗衡。[21]可以說,由納稅人承擔(dān)客觀舉證責(zé)任的結(jié)果,必然是稅務(wù)機關(guān)可以在證據(jù)尚有不足的情況下以事實真?zhèn)尾幻鳛橛膳卸ㄆ涮岢龅慕灰讟?gòu)成一項避稅安排的主張成立,反避稅調(diào)整將徹底淪為一項不受拘束的權(quán)力。納稅人將因此不得不面臨稅額的隨意調(diào)增,不公平的結(jié)果顯而易見。這與誠實推定權(quán)也是根本相悖的。
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稅務(wù)機關(guān)提出交易的屬性依其經(jīng)濟實質(zhì)而非法律形式認(rèn)定的事實主張,以否定對納稅人有利(稅收利益)的稅法規(guī)則的適用,轉(zhuǎn)而適用對其有利(國庫保護)的稅法規(guī)范。稅務(wù)機關(guān)同樣有必要證明這一規(guī)范適用的前提要件事實的存在,即其一交易構(gòu)成避稅安排,其二被隱藏的交易的經(jīng)濟實質(zhì)。這兩個層面的事實均有充分證據(jù)證明的情況下,稅務(wù)機關(guān)才可以做出交易的法律形式被忽視、改為以經(jīng)濟實質(zhì)適用稅法規(guī)則從而確定應(yīng)稅數(shù)額的決定。就此而言,稅務(wù)機關(guān)主張適用的為關(guān)系征稅權(quán)成立的稅法規(guī)則,這與一般稅款確定程序下并無不同。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和一般稅款確定程序中,稅務(wù)機關(guān)的目標(biāo)均在于以特定稅法規(guī)范的適用主張征稅權(quán)的成立,只在將交易與客觀稅法規(guī)范相聯(lián)系以確定發(fā)生哪一法律后果時,是以交易的法律形式還是經(jīng)濟實質(zhì)作為事實基礎(chǔ)這一問題上有所區(qū)別。這一法規(guī)范適用的結(jié)果,同樣是使稅務(wù)機關(guān)享有要求納稅人為一定金錢給付的請求權(quán),取回本為納稅人套取的稅收利益。就征稅合法性和稅收構(gòu)成要件合致性而言,舉證責(zé)任并無必要在稅務(wù)機關(guān)與納稅人之間重做分配。也只有由稅務(wù)機關(guān)對此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才能防止其在特別納稅調(diào)整程序中怠于調(diào)查或在證據(jù)不夠充分的情況下做出隨意調(diào)增應(yīng)納稅額的決定。
因此,在稅收征管活動中,無論是一般稅款確定程序還是特別納稅調(diào)整程序,基于法律要件分類說,稅務(wù)機關(guān)應(yīng)當(dāng)就征稅權(quán)成立的法規(guī)范適用的事實前提承擔(dān)客觀舉證責(zé)任。盡管經(jīng)濟實質(zhì)是否被刻意隱藏與交易的合理商業(yè)目的存在與否等事實存在一定程度的證明困難,但這并不足以成為反避稅案件的全部或部分事實要件的舉證責(zé)任倒置由納稅人承擔(dān)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相反,唯有反避稅案件中稅務(wù)機關(guān)承擔(dān)客觀舉證責(zé)任,才能真正有效地約束其特別納稅調(diào)整權(quán)的行使。
四、稅務(wù)機關(guān)證明“避稅安排”之程度
稅務(wù)機關(guān)既然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那么與之相關(guān)的問題是,稅務(wù)機關(guān)應(yīng)當(dāng)提供證據(jù)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要達到何種程度,此即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問題。證明標(biāo)準(zhǔn)是指“履行證明責(zé)任必須達到的范圍或者程度。……證據(jù)必須在事實裁判者頭腦中形成的確定性或蓋然性程度,是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的當(dāng)事人在有權(quán)贏得訴訟之前使事實裁判者形成確信的標(biāo)準(zhǔn)”。[25]也就是說,稅務(wù)機關(guān)在最終做出是否實施納稅調(diào)整決定時應(yīng)提供達到質(zhì)和量的要求的證據(jù)。證明標(biāo)準(zhǔn)越低,稅務(wù)機關(guān)提供證據(jù)對交易構(gòu)成避稅安排這一事實加以證明的責(zé)任越容易完成,越容易做出納稅調(diào)整的決定。反之,證明標(biāo)準(zhǔn)越高,因為事實不明而適用舉證責(zé)任分配規(guī)則做出決定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稅務(wù)機關(guān)調(diào)查、收集證據(jù)應(yīng)當(dāng)達到何種程度和要求,才可以通過心證做出判斷,當(dāng)前立法中并未予以規(guī)定。《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第16條僅規(guī)定,“主管稅務(wù)機關(guān)根據(jù)調(diào)查過程中獲得的相關(guān)資料,……形成案件不予調(diào)整或初步調(diào)整方案的意見和理由……”。但對于“獲得的相關(guān)資料”的“質(zhì)”與“量”如何,卻未做任何要求。這導(dǎo)致在反避稅調(diào)查實踐中,無論稅務(wù)機關(guān)實施調(diào)查的程度如何,只要取得了一定的證據(jù),都可以做出合法的納稅調(diào)整的決定。在兒童投資主基金間接股權(quán)轉(zhuǎn)讓一案中即是如此。[注]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兒童投資主基金訴杭州市西湖區(qū)國家稅務(wù)局一審行政判決書》(〔2015〕浙杭行初字第4號)。在該案中,稅務(wù)機關(guān)共收集了七項證據(jù)證明兒童投資主基金間接轉(zhuǎn)讓杭州國益路橋公司的股權(quán),“屬于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yè)目的的安排而減少其應(yīng)納稅的收入或所得額”。然而在七項證據(jù)中,2份原告購買CFC公司的股權(quán)認(rèn)購協(xié)議僅足以認(rèn)定投資主基金購入股權(quán)的成本,與認(rèn)定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商業(yè)目的”這一事實之間不具有相關(guān)性。而證據(jù)(七)僅證明該主體知悉稅法規(guī)定的情況,卻不足以認(rèn)定其規(guī)避的意圖。同樣,證據(jù)(二)證明的事實為投資主基金交易架構(gòu)的安排,且設(shè)立CFC的目的是“為了在中國境外籌集資金為杭州國益路橋公司成立和經(jīng)營提供資金”,稅務(wù)機關(guān)對此并未予以否定。證據(jù)(四)CFC公司發(fā)債說明書恰恰證明了CFC公司公開發(fā)行債券因此承擔(dān)了到期還本付息的實質(zhì)性風(fēng)險。證據(jù)(一)、(三)則均為證明香港國匯公司收入來源的證據(jù)。可以說,稅務(wù)機關(guān)提供的用以證明投資主基金的間接股權(quán)轉(zhuǎn)讓不具有合理商業(yè)目的這一事實的七項證據(jù)中,僅有(一)、(三)項證據(jù)與這一事實存在間接的相關(guān)性。但這是否已達到做出避稅安排認(rèn)定所要求的證據(jù)的質(zhì)與量,卻是值得懷疑的。相反,投資主基金提供的證據(jù)在交易是否具有合理的商業(yè)目的這一事實方面卻形成了如下的疑點:(1)在當(dāng)時的法律和投資環(huán)境下,TCI公司無法直接投資于杭州國益公司的杭州繞城高速公路的經(jīng)營權(quán)益項目,只能通過香港國匯公司來完成。根據(jù)2005年10月10日國家發(fā)改委(發(fā)改交運〔2006〕1948、1949號)對杭州繞城高速公路經(jīng)營權(quán)益轉(zhuǎn)讓項目的批復(fù),香港國匯和浙江國益合資注冊的項目公司為杭州繞城高速公路的經(jīng)營權(quán)益的受讓方。TCI公司無法直接取代香港國匯公司直接投資于杭州國益公司,否則,將導(dǎo)致《杭州繞城高速公路北東南線收費權(quán)益轉(zhuǎn)讓合同》、《杭州繞城高速公路西線收費權(quán)益轉(zhuǎn)讓合同》無效,杭州國益公司的投資項目可能因此作廢。(2)CFC公司的設(shè)立,目的在于通過發(fā)行債券為香港國匯公司投資于杭州國益公司提供必要的資金。根據(jù)《證券法》第16條的規(guī)定,2004年杭州國益公司設(shè)立時并不具備在大陸境內(nèi)公開發(fā)行公司債券的資格,加上公開發(fā)行債券籌集的資金不得用于非生產(chǎn)性支出,這就使得香港國匯公司只能通過境外融資滿足項目投資的資金要求。由于香港公司無法進行境外債券的公開發(fā)行,這也迫使TCI通過設(shè)立CFC公司并由該公司以其凈資產(chǎn)為基礎(chǔ)對外公開發(fā)行債券為香港國匯公司籌集資金。因此,TCI設(shè)立并持有CFC公司的股權(quán)是為了解決杭州國益和香港國匯公司在境內(nèi)外的融資困難。上述事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足以動搖稅務(wù)機關(guān)認(rèn)定的該股權(quán)結(jié)構(gòu)安排以“減少、推遲或免除企業(yè)所得稅為主要目的”這一結(jié)論的。而稅務(wù)機關(guān)卻未能提供任何證據(jù)足以否認(rèn)或推翻上述事實。可以說,在這一案件中,稅務(wù)機關(guān)做出避稅安排的認(rèn)定并施以納稅調(diào)整的證據(jù)基礎(chǔ)是極為薄弱的,難以保證其結(jié)論的唯一性。而最高院在該案的再審判決中卻僅僅簡單地認(rèn)定,“從行政訴訟證據(jù)的客觀性、關(guān)聯(lián)性、合法性的角度看,稅務(wù)機關(guān)在原審中所提供的證據(jù)的證明力更強,具有相對優(yōu)勢”,進而認(rèn)定稅務(wù)機關(guān)的納稅調(diào)整決定合法。[注]最高人民法院《兒童投資主基金訴杭州市西湖區(qū)國家稅務(wù)局行政裁定書》(〔2016〕最高法行申1867號)。
因此,單純要求稅務(wù)機關(guān)提出證據(jù)并在事實真?zhèn)尾幻鲿r承擔(dān)不利后果,而不設(shè)定其提供證據(jù)應(yīng)達到的質(zhì)和量的要求,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稅務(wù)機關(guān)本身同時為決定者和證據(jù)提供者,在不存在證明標(biāo)準(zhǔn)約束的情況下,稅務(wù)機關(guān)可以提供任何證據(jù)而做出決定,卻不至于遭到否定性的評價,職權(quán)調(diào)查主義將形同虛設(shè)。
在稅收征管活動中,稅務(wù)機關(guān)對有關(guān)稅收要件事實的證明應(yīng)達到何種程度,在當(dāng)前立法中并無明確的規(guī)定。根據(jù)《行政訴訟法》第69條規(guī)定,“行政行為證據(jù)確鑿”是認(rèn)定行政行為合法的重要條件之一。但何謂“證據(jù)確鑿”卻并不明晰。如依最高院對兒童投資主基金一案的判決,似乎認(rèn)為,只要形成證據(jù)上的“相對優(yōu)勢”即可滿足“證據(jù)確鑿”。從行為發(fā)生的順序來看,先有行政程序,后有行政訴訟程序;從源與流來看,行政訴訟中的證據(jù)來自于行政程序,因而可以說行政訴訟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也來自于行政程序,只是在作為司法救濟的訴訟階段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更加嚴(yán)格而已。[26]德國多數(shù)學(xué)說認(rèn)為,稅收征管活動中有關(guān)稅收要件事實的證明程度應(yīng)與行政訴訟程序采取相同的標(biāo)準(zhǔn)。[7]如果說在行政訴訟程序中對反避稅案件的證據(jù)要求達到“相對優(yōu)勢”,那么,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稅務(wù)機關(guān)提供證據(jù)應(yīng)當(dāng)達到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是“相對優(yōu)勢”或者是更低的標(biāo)準(zhǔn)?如前所述,特別納稅調(diào)整將直接導(dǎo)致納稅人負(fù)擔(dān)更高的稅收負(fù)擔(dān),對其財產(chǎn)權(quán)和經(jīng)營權(quán)將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在這一類型的案件中,“相對優(yōu)勢”或更低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是否恰當(dāng),值得關(guān)注。[注]多數(shù)學(xué)者均認(rèn)為,行政程序適用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高低應(yīng)當(dāng)與行政行為的具體性質(zhì)和嚴(yán)重程度相關(guān)。[27]
與其他法領(lǐng)域相同,反避稅案件中的待證事實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存在兩種可能的極端狀態(tài):一是稅務(wù)機關(guān)未提出任何證據(jù),無法證明任何案件事實,該事實不具有任何可信性;二是稅務(wù)機關(guān)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證據(jù),證據(jù)之間彼此印證,排除了任何合理的矛盾和疑問,有關(guān)待證事實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對該事實的真實性達到了“確信無疑”的程度。然而,在實踐中爭議交易的證明往往只能達到某種中間狀態(tài)。也就是說,稅務(wù)機關(guān)提供的證據(jù)盡管達到了一定的真實程度,但又不是達到了百分百的確信。待證事實是否存在,既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確信,又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懷疑。受制于人的認(rèn)識能力的有限性,要求所有的案件都在審查了全部證據(jù)之后達到100%確信的程度,在實踐中基本上難以實現(xiàn)。因此,必須設(shè)定“一種量的規(guī)定”,在促使裁決者形成確信的證據(jù)達到一定的質(zhì)量以上時,即可判定事實的存在。這種確信標(biāo)準(zhǔn)往往根據(jù)證明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區(qū)別。因此,形成了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各自不同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即刑事訴訟中的排除合理懷疑標(biāo)準(zhǔn)和民事訴訟的明顯優(yōu)勢證據(jù)標(biāo)準(zhǔn)。
盡管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設(shè)定證明標(biāo)準(zhǔn)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都是以蓋然性為尺度的法律真實的標(biāo)準(zhǔn)。也就是說,只要證明達到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性(蓋然性),即可認(rèn)為此項事實構(gòu)成法律意義上的真實。[28]同時,依據(jù)訴訟的性質(zhì)、所涉及的訴訟利益和案件處理程序的不同設(shè)定了不同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29]在刑事案件中,由于涉及到人的生命、重大的財產(chǎn)利益及名譽等,案件性質(zhì)最為嚴(yán)重,所以證明標(biāo)準(zhǔn)最高,要求達到高度的蓋然性,即排除合理懷疑。而在民事案件中,只要一方當(dāng)事人的證據(jù)證明力強于對方,即占優(yōu)勢的蓋然性,便可贏得訴訟。最高院在兒童投資主基金一案中即是遵循了這一標(biāo)準(zhǔn)。
然而,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采用與民事訴訟程序相同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設(shè)定與案件的性質(zhì)以及沖突的利益直接相關(guān)。而民事訴訟是當(dāng)事人由于私權(quán)的爭執(zhí)引起的,多指向財產(chǎn)性權(quán)益。即使涉及人身糾紛,也不至于產(chǎn)生自由或生命的剝奪。民事訴訟主要在于保證權(quán)利人正當(dāng)?shù)慕?jīng)濟或身份利益獲得滿足,如果設(shè)定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過高,收集、取得證據(jù)的投入超過或等于權(quán)利人可能獲得的利益,權(quán)利人的訴訟便毫無意義可言。因此,民事訴訟要求在保障一定程度的公正性的前提下盡快結(jié)束程序。加上訴訟中雙方當(dāng)事人的訴訟能力大體相當(dāng),這也決定了民事訴訟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不能太高,達到占優(yōu)勢的蓋然性即可。
然而,作為行政程序之一的稅收征管程序顯然與此有所不同。征稅權(quán)是一種事關(guān)“圈錢”的權(quán)力,行使的結(jié)果是納稅人實際可支配的財產(chǎn)的減少。稅法為保障國庫需要的實現(xiàn),更賦予稅務(wù)機關(guān)諸多的強制權(quán)力。為防止征稅權(quán)的濫用,稅收法定主義所要求的依法征稅必然要求征稅行為必須存在法律和事實依據(jù),以免對私人財產(chǎn)權(quán)利的侵害。尤其在當(dāng)前稅務(wù)機關(guān)對納稅人幾乎具有壓倒性優(yōu)勢的情況下,設(shè)定過低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極易造成對納稅人權(quán)利的侵害。
不僅如此,在稅收征管程序中稅務(wù)機關(guān)也居于舉證的優(yōu)勢地位。這種優(yōu)勢地位不僅源于其多種獲取證據(jù)資料的法定方式和渠道,更源于其“形式上的說服責(zé)任”。[30]在稅務(wù)機關(guān)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的情況下,稅務(wù)機關(guān)身兼證據(jù)提供者和被說服者的雙重身份,說服責(zé)任往往表現(xiàn)為自我說服。加之稅務(wù)機關(guān)就避稅安排的認(rèn)定及相應(yīng)的納稅調(diào)整為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公定力,納稅人并無直接對抗稅務(wù)機關(guān)的權(quán)利。稅務(wù)機關(guān)的說服責(zé)任僅限于形式內(nèi)容,即只要能夠滿足證據(jù)的形式要件,即可形成有關(guān)應(yīng)稅交易發(fā)生的確信。如所設(shè)定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過低,稅務(wù)機關(guān)將極易使“形式上的說服責(zé)任”獲得滿足,從而做出反避稅調(diào)整的決定,稅務(wù)機關(guān)征稅權(quán)的行使未免過于隨意,必將大大降低納稅人對稅法的信賴。因此,不僅應(yīng)當(dāng)規(guī)定稅收征管活動中稅務(wù)機關(guān)認(rèn)定應(yīng)稅事實應(yīng)當(dāng)達到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且這一確認(rèn)征稅權(quán)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高于解決民事糾紛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
那么,是否有必要要求稅務(wù)機關(guān)在征管程序中對案件事實的證明達到刑事訴訟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有臺灣地區(qū)學(xué)者認(rèn)為,在德國稅收征管活動中,對于稅收要件事實的存在,稅務(wù)機關(guān)確信某一特定的事實關(guān)系為真實,應(yīng)當(dāng)達到相當(dāng)高度的蓋然性,使任何有理性的、熟悉生活事實關(guān)系之人并不產(chǎn)生任何懷疑的程度。[7]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德國行政程序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是“達到一定程度的高度蓋然性真實”,“且應(yīng)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31]在刑事訴訟中有必要設(shè)置“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較高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原因在于通過刑事審判,國家要實現(xiàn)以嚴(yán)厲的手段對犯罪行為的懲戒,其后果往往是對個人的人身自由、財產(chǎn)甚至生命的剝奪。因此,刑事訴訟必須設(shè)定較高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以防止發(fā)生誤判而產(chǎn)生權(quán)利侵害的嚴(yán)重后果。盡管稅收征管程序最終導(dǎo)致納稅人財產(chǎn)權(quán)的剝奪,其嚴(yán)重程度仍不足以與刑事處罰的后果相比。加上稅收的征收必須及時支應(yīng)當(dāng)年度政府機關(guān)的財政開支,而稅務(wù)案件具有大量、反復(fù)的特性,征稅權(quán)的行使固有迅捷性的要求。如果設(shè)置過高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稅務(wù)機關(guān)必須進行詳盡的事實查明,將可能導(dǎo)致稅務(wù)機關(guān)過于謹(jǐn)慎地行使征稅權(quán),導(dǎo)致稅收收入無法及時征收入庫。征稅權(quán)及時、有效地獲得行使,事關(guān)政府公共服務(wù)的提供和納稅人基本權(quán)利的實現(xiàn)。基于稅收行政效率的考量,稅收征管程序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無須達到刑事訴訟的高度。
因此,包括稅收征管在內(nèi)的行政程序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原則上應(yīng)當(dāng)?shù)陀谛淌略V訟而高于民事訴訟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但多數(shù)學(xué)者也認(rèn)為,行政程序具有一定的復(fù)雜性和多樣性,不能完全適用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盡管《德國聯(lián)邦財政法院法》同樣肯定了稅務(wù)機關(guān)所確信的事實,應(yīng)當(dāng)是一定程度的高度蓋然性,但此“高度蓋然性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達到的程度,無論是司法實踐還是理論研究都存在不同的見解:(1)高度蓋然性。這一標(biāo)準(zhǔn)存在多種描述,如“沒有一個理性的、清楚通曉生活事實的人會懷疑的高度蓋然性”、“根據(jù)生活經(jīng)驗,實際上相當(dāng)于確實的高度蓋然性”、“在理性思考下,不會有不同看法的高度蓋然性”。(2)實際生活可使用的確信度,此確信度可使懷疑保持沉默,但并非毫無懷疑。(3)雖然無法完全排除懷疑,但在理性、客觀評價事實的觀察法下可以推翻、去除這種懷疑的確實程度。可以說,德國行政程序中所采用的并非單一的“排除合理懷疑”的標(biāo)準(zhǔn)。
具體就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而言,盡管與一般稅收征收程序一樣,該程序的目的同樣在于確認(rèn)征稅權(quán),但反避稅調(diào)查更意在以被法律形式所掩蓋的經(jīng)濟實質(zhì)判定納稅人真實的稅收負(fù)擔(dān)能力。這意味著本已被推定為真實的課稅資料所確立的交易事實將被推翻,而重新基于經(jīng)濟實質(zhì)確認(rèn)交易及由此發(fā)生的納稅義務(wù)。因此,反避稅調(diào)查的目標(biāo)在于發(fā)現(xiàn)最符合實際狀況的經(jīng)濟后果。一旦認(rèn)定,納稅人將面臨應(yīng)納稅額的調(diào)增,對其權(quán)利影響甚巨。如發(fā)生錯誤的判斷,納稅人可能不得不承受遠超過、甚至是數(shù)倍于本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的應(yīng)納稅額。面臨反避稅調(diào)查的交易往往已依其法律形式確定并繳納了稅款,因此,該程序的實施并不受制于財政支出的壓力,而是意在以被套取的稅收利益的取回實現(xiàn)稅法的公平。特別納稅調(diào)整決定的做出并無迅捷性的要求。相反,這一決定的做出將推翻納稅人已在一般稅款確定程序中提供的形式合法、申報內(nèi)容被推定為真實的課稅資料中記載的本應(yīng)受尊重的私法形式,對稅務(wù)機關(guān)對于相應(yīng)事實的證明程度的要求應(yīng)當(dāng)高于一般征收程序。
因此,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應(yīng)當(dāng)確立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shù)陀谛淌略V訟的“排除合理懷疑標(biāo)準(zhǔn)”而高于民事訴訟的“占優(yōu)勢蓋然性標(biāo)準(zhǔn)”,即比較嚴(yán)格的占優(yōu)勢的蓋然性標(biāo)準(zhǔn),又稱為清楚、明確和令人信服的標(biāo)準(zhǔn)。也就是說,稅務(wù)機關(guān)對交易構(gòu)成避稅安排的事實的認(rèn)定應(yīng)當(dāng)達到大致“80%~90%”的程度。具體而言,該標(biāo)準(zhǔn)包括如下的內(nèi)容:(1)稅務(wù)機關(guān)用來定案的證據(jù)必須確實,證據(jù)之間不存在任何矛盾,相關(guān)證據(jù)必須能夠證明相關(guān)案件事實。這是對證據(jù)本身個體“質(zhì)”的要求;(2)稅務(wù)機關(guān)認(rèn)定案件事實的要點是明確清楚的;(3)證據(jù)和認(rèn)定結(jié)論之間的證明關(guān)系是清楚的;(4)認(rèn)定結(jié)論是可信的。盡管從相同的證據(jù)不止可以得出稅務(wù)機關(guān)認(rèn)定的結(jié)論,但從現(xiàn)有的證據(jù)中能夠令人信服地得出稅務(wù)機關(guān)認(rèn)定的結(jié)論。與排除合理懷疑相比,該標(biāo)準(zhǔn)的特點是不排除其他合理的可能性;與占優(yōu)勢的蓋然性相比,該標(biāo)準(zhǔn)的特點是稅務(wù)機關(guān)認(rèn)定的結(jié)論的可能性與其他可能性相比,必須具有明顯的“差別”或“優(yōu)勢”。[28]
五、結(jié) 語
由于避稅交易對國家稅基的侵蝕,反避稅在當(dāng)前稅收征管實踐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在反避稅調(diào)查過程中,發(fā)生事實真?zhèn)尾幻鞯那闆r下如何做出決定,也日漸受到重視。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眾說紛紜,卻多是對現(xiàn)行立法中涉及證據(jù)提供的規(guī)則的牽強附會,至今仍是莫衷一是。
舉證責(zé)任是對事實真?zhèn)尾幻鞯娘L(fēng)險的事先分配。這種事實上的不確定性必須由主張適用特定法律規(guī)范對其有利的當(dāng)事人負(fù)擔(dān)。這種分配原則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同樣有必要予以遵守。由于稅務(wù)機關(guān)不僅是規(guī)則適用的主張者,更是最終的決定者,加上可以不受形式上確立的真實、有效的法律關(guān)系的拘束、綜合考量“環(huán)境與事實因素”,對應(yīng)稅事實的屬性做出判斷,如果任由稅務(wù)機關(guān)在經(jīng)濟事實尚未查明的情況下主張對其有利的規(guī)范的適用,所做決定必然是主觀而隨意的。
納稅人為套取稅收利益而以真實、有效的法律形式刻意隱藏交易的經(jīng)濟實質(zhì),稅務(wù)機關(guān)欲查明真正反映稅收負(fù)擔(dān)能力的經(jīng)濟事實,便存在更多的調(diào)查困難。這也是諸多學(xué)者主張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應(yīng)當(dāng)采取不同于一般稅收征管程序的舉證責(zé)任分配規(guī)則的立論基礎(chǔ)。然而,降低證明難度并非舉證責(zé)任分配規(guī)范的價值訴求,單純提供證據(jù)的困難也不足以決定舉證責(zé)任的分配方式,因此,在一般稅收征管程序中基于法律要件分配說確立的稅務(wù)機關(guān)對于稅收債權(quán)成立的要件事實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的分配規(guī)則,在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中并無予以修正的必要。
被真實、有效的法律形式所掩蓋的經(jīng)濟實質(zhì)本身缺乏更多的直接證據(jù)的證明,而不得不求助于諸多間接證據(jù)予以推定。這一事實的認(rèn)定過程本身包含了諸多的裁量。而一項交易的經(jīng)濟實質(zhì)如何予以認(rèn)定,當(dāng)前的規(guī)定更是言之了了。反避稅調(diào)整結(jié)果的不確定性正在不斷增加。因此,維持一種程序上的確定性,即反避稅調(diào)查程序?qū)⒁苑弦?guī)范性預(yù)期的方式直至結(jié)束,便具有更加深刻的意義。[15]在稅收法定主義之下,稅務(wù)機關(guān)既應(yīng)保證其依法征稅,在交易的法律形式或經(jīng)濟實質(zhì)的認(rèn)定尚且存疑的情況下,由其承擔(dān)不得實施特別納稅調(diào)整權(quán)的風(fēng)險,便屬應(yīng)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