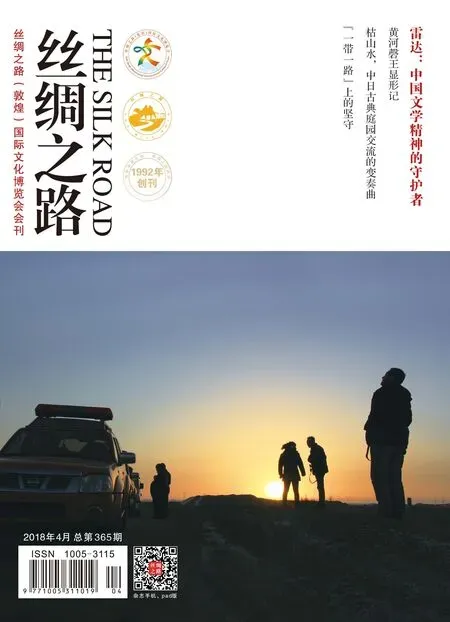雷達在新世紀的散文創作
文/陳 霖 齊 紅
(作者皆系蘇州大學教授)
雷達在文學評論之余,一直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散文的寫作中。在一定意義上,散文創作也是他的文學評論的延續、補充和闡釋。進入新世紀之后,雷達的散文創作依然保持著旺盛的活力,出版有散文集《皋蘭夜語》 (東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其中許多篇什是2000年以后的新作。從2014年起,雷達在《作家》開辟“西北往事”專欄,不定期地推出他關于甘肅以及大西北的回憶或記游的散文。
西部的歷史文化、地理風貌和人生故事是雷達散文中集中而鮮明的構成部分。黃河上游及其最大的支流渭河,作為文化地理的突出標識,貫穿著、聯系著、滋養著雷達的散文創作:“黃河的聲音,至今還會在夢中響起,它成了我解讀蘭州歷史文化的一把鑰匙”(《費家營》),而“渭河如弓弦劃出一道弧線,好似我臂彎上鼓突的血管”(《還鄉》)。在《費家營》 《黃河·遠上》 《新陽鎮》 《多年以前》等散文中,雷達都情深意切地回憶了自己在西北的生活經歷。這些回憶疊映著西部社會變遷的背景,勾勒出作者心靈成長的軌跡。一個個歷史事件的書寫,不僅再現了戰爭、饑荒、貧窮、地理風貌、極左政治,而且表現了個體、家庭乃至族群的心性與性格,展示出人在與自然、與社會的互動和沖突中,文化的傳承與裂變,生命的不屈與精神的強健。
在這些散文中,雷達以敏銳的感性落筆日常生活,關注點滴細節,引入宏闊背景,興之所至地娓娓道來。有時候,他就是一個健談的長者,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傳遞人生的經驗。我們看到那個兒童時的雷達:“背著快掉到屁股蛋下的書包,忽然躥上臺,面對麥克風,先擤了一把鼻子,把鼻涕抹到鞋幫上,在哄笑聲中唱開了。”(《黃河遠上》)我們聽到接受了新式教育而又才華出眾的母親的故事,她在丈夫病故之后,面對生活的各種困境,犧牲了自己的幸福,獨自一人含辛茹苦地將兒女培養成人(《多年以前》)。嫂子身上表現出的頑強的生命力,同樣給我們留下難忘的印象。這個最窮苦的貧農女兒、童養媳,卻在那個荒誕的年代頂起了“富農婆”的帽子,經常被扭去游街,干苦活、累活,“每次游街后,嫂子扔掉繩索木牌,抹去傷痕污漬,趕緊升火做飯,還說說笑笑,像沒事人一樣”(《新陽鎮》)。
有時候,我們則被他帶入審美活動的情境之中,譬如,“被巖畫之謎吸引著,不由遙想上古游牧人,頂風冒雪,輾轉深山荒灘,日夜與牛羊為伴,好不孤單,那種欲與天、地、人、萬物生靈對話的強烈沖動難以抑制,卻又苦無對象,于是以鑿刻為語言,把原始的思維和郁積于胸的怒吼注入了這萬古不滅的巖畫。”(《走寧夏》) 又如,他讓我們在《涼州曲》里領略了一首首民歌。這些民歌與山川形勝、尋常人家、文化古跡、歷史人物相得益彰,點染出濃濃的詩情。而在《費家營》里則讓我們“艷遇”了一夜盛開的桃花,看到“最鮮艷、最奔放的花兒與最蒼涼、最沉默的禿山構成了強烈的色彩對比,桃林像紅霞,像紅海,像火焰,在山腳下流淌著,在萬古蒼涼中寂寞地浮游著,燃燒著”。這不啻為西部精神的生動意象,蒼涼貧瘠中崛現的燦爛光華,是不可阻遏的生命力的奮然勃發。
有時候,我們被作者峻急的思考刺激著。回顧少年時代在費家營蘭州工農速成中學的經歷時,雷達寫道:“文革并不是從天而降的,也不是突然爆發的,文革的形形色色斗爭方式早已有之。”(《費家營》)這呼應著作者更早的時候發出的叩問:“一場大噩夢隨著那個時代的結束而結束了,但那時代的精神因子也永遠地消失嗎?”(《王府大街64號》)連接過去和將來的是此刻的現實,如此警醒人們對“文革”的反思,須推向人性的深處和精神的黑暗。我們也被作者驅策著面對現代消費社會與大山深處原生樣態之間的緊張關系,體會作者內心的糾結:“我的心是多么矛盾:我寫文章,希望人們知道扎尕那的美,但我深知,一旦知道的人一多,蜂擁而至,它立刻就會變色變味。”(《天上的扎尕那》)
神秘而貧窮、傳統而富有文化多樣性的西部,伴隨著雷達對現代文明的反思,每每作為一種精神原鄉的存在而被珍視和呵護。他在新陽鎮鄉親的臉上,“看到了對祖先、對傳統的無比虔誠和敬畏”(《新陽鎮》),在固原發出慨嘆:“切莫用施舍者的眼光看西部,西部不是可憐巴巴的施舍對象。‘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我深信,不管人類文明發達到了何等程度,我們永遠需要不斷回歸精神的故鄉。”(《走寧夏》)所有這些關于西部的散文,都突出體現了雷達心靈深處與西部割舍不斷的聯系,當傾訴的語流、動人的故事、鮮活的人物、欣悅與悲情、歡樂與憂愁從他的筆端流出的時候,他獨具個性的散文書寫空間也得以展示。
這樣的個性同樣體現于雷達其他題材的散文寫作。無論是狀寫人物如《達成先生二三事》 《秋實凝香》 《忠實兄永在我心》,還是發表隨感時評如《劉翔退賽是一種解脫》《開幕式能讓我們記住什么》,甚至是學術隨筆如《李白“故里”在甘肅秦安》,雷達都踐行了他自己的散文主張,即如他闡述胡適“有什么話,說什么話”時指出的,其精義“全在于自由、本真、誠摯、無畏”(《我心目中的好散文》),也因此,敏感又隨性、坦蕩而率真、博聞而善思的寫作者形象從他的文字中站立起來,與讀者進行親切而真誠地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