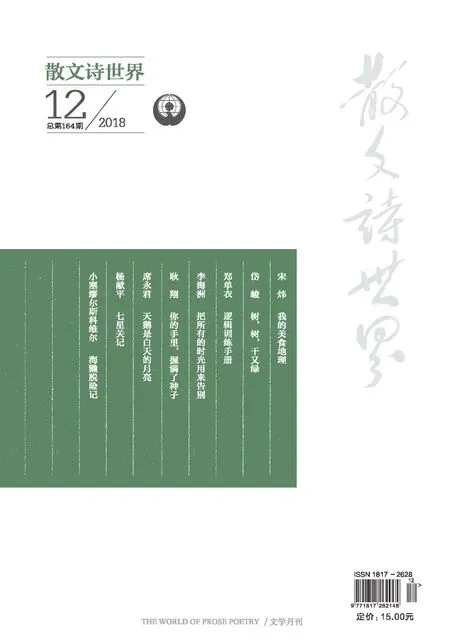塵埃落在暮雪之前 組章
蒲素平
落在樹上的柿子
灰色的天空,山坳處一棵柿子樹顯得灰頭土臉。
注定有些柿子要落在高處,鮮艷的身體,等待陽光或者一只鳥的啄。
一直這么掛著,紅色的皮膚上落滿了風(fēng),以成熟之軀,對抗注定的孤獨。如同中年的我,朝來風(fēng),晚來雨,一生終究被命運遺忘。
沒有人會無故想起山坳處的一棵柿子樹和它上面遺留的一個柿子,影子不過是憑空生出的妄念。
春天出走的人,秋天趕不回內(nèi)心。一塊石頭的天空,四季雷同。
塵埃將在暮雪之前,收回這遺留人間的最后一個柿子。
生在后宮的王,面對日薄西山的江山,除了飲下一杯酒,又能奈之若何?
一朵棉花
趁著天氣好,無雨水,我急急忙忙地開了,摘棉花的女人,彎下腰,摘走了我的心。
我剛剛開放的身體啊,少了一顆心。
我原本不會計較我的心去了哪里,比如一件新棉衣,一床被子,一個城市,一個偏僻的鄉(xiāng)村。那只是命運的一次安排。
冷暖,我已不知。或者說,有一個人知道,更好。
像一個孩子,被人捧起,“像永生者死一般活著”,一朵棉花,不會給秋天留下過多的注解。
保持君子最后的尊嚴,不管被多少灰塵覆蓋,不管看起來多么灰暗。如果,有一只期待的手,用力一拍,我就會復(fù)活,就會沖破歲月的塵埃。
我就會用余生把你,再愛一遍。
躺在黑夜的場地上
天黑下來,人們漸漸散去,曠野空曠起來。
躺在場地的麥子堆上,星星越來越多,越來越低,和不遠處機井旁的一盞電燈呼應(yīng)著。
剛剛收割下來的麥子,攜帶著自己的口糧,在身邊睡著了,發(fā)出暖烘烘的伴著香氣的呼吸聲。一根麥芒,順勢扎進了我十歲的皮膚里,今天,依然成為我生活中的一根刺。
風(fēng)越過我小小的幻想,越過新鮮的麥茬,一次次直接抵達了夜空。
行走的飛蟲,有的休息了,有的飛動著,衣兜里一個熟透了的小沙果蠢蠢欲動,我摸摸又放下,放下,又摸摸。
曠野越來越空曠,星星開始走動,我認不出哪一顆是我。
一個人,在夜風(fēng)里漸漸睡去。
一條河
不可以無緣無故地接近一條河的斷面,不可騎在一條河的身上行走,不可以對一條河使用人為的隱喻,不可以讓一條明亮的河暗無天日。
如果不是這樣,那么我將經(jīng)歷你所犯下的所有錯誤,盲目,自以為是。
大雨下了七天七夜,所能想象到的記憶都被雨水淹沒,那么就是這條河,一條渺小得被你屈辱地遮蔽于暗處的河,一下子掀開了蓋子。
一個水的世界大白于天下。
道路中斷,語言暴亂,如果你沒有翅膀,那么,你就返回吧。
時間洶涌向前,你卻返身折回。
一邊是弱智者的悲歡,一邊是弱勢者的悲歡。
對于一條河,我們奈之若何?
對于生活,我們奈之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