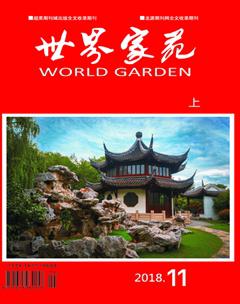反叛路上的口語詩人“他們”
李艷
摘 要: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詩人們藐視日常生活,藐視事物本身。當他們津津樂道于各種復雜的詩歌理論,并將自己淹沒在深奧的詩句里的時候。有這樣一些不斷探索的先鋒詩人,“他們”對于詩歌本質、形式及美感的探索和實踐,可謂獨辟蹊徑。
關鍵詞:“他們”;口語詩
上個世紀末的中國詩壇上,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擂臺賽上演得沸沸揚揚,并被后來者稱為盤峰論劍。實際上這兩種詩歌路向的爭斗是由來已久的。自新詩誕生之日始,詩壇就有貴族化與平民化之爭。說到文學平民化之路的不斷探索,不能不提到“他們”。
一、“他們”的定義
“他們”既不是詩歌流派也不是文學團體,“他們”匯聚了文學藝術的各方面,包括詩歌、小說、評論、甚至美術作品等,其“成員”散布全國各地,可以把《他們》僅僅看作是一本刊物,它只是提供了一塊園地,給于富有才能和創造精神的詩人、作家等以自由發揮的空間。它既沒有統一的宣言,也沒有公認的指導原則。它的獨特風格并非預先設計,而是水到渠成最終形成的結果。“它不是一種傾向,而是一種狀態。” [3]
二、“他們”詩人反叛之路
(一)“他們”詩人特殊的生存背景。
“他們”詩人大都出生于20世紀50或60年代,并在中年以前至少經歷了四個不同的時期:較為平靜的五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時代,思想解放的時代和市場經濟時代。時代的迅速更迭,使傳統上一切恒定的價值都受到質疑,他們不得不重新尋求一種價值觀以對人生做出合理的解釋,這為開拓詩歌領域的新局面提供了可能。就其代表詩人于堅來講,由于身處地域的邊緣(昆明)和內地文化的邊緣,加之他的青春期很幸運地避開了文革,時代的變化在他的生活中影響不大,日子依舊遵循著正常的軌跡,他像古往今來的蕓蕓眾生一樣,出生,長大,勞動,掙錢,戀愛,結婚,生子,所以他沒有機會熱血沸騰,也沒有學會振臂高呼,他的眼睛里裝滿的是民間,是日常生活,他們遭遇了一種局外人的處境,不得不習慣被時代和有經歷的人所忽視。這是與生俱來的,沒有任何辦法。但是,對于文學,局外人的處境也許是造就真正詩人的重要因素,因為一個真正的詩人需要對人生有某種距離感,以用一種相對客觀的目光關照這個世界。作為一個“后來者”,他們的身份決定了其無法融入到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只能作為一個個渺小的個體,置身于被遺忘的角落,這在給他們帶來開拓性機遇的同時也最終造成了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困境。
(二)“他們”隊朦朧詩的繼承和反叛。
“朦朧詩”最初也是在對以往意識形態中心話語的反思中、在醒悟到詩歌被利用被愚弄的真相后開始的,因而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與以往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絕決的姿態,要求打破陳腐老化的套語連篇,拒絕直抒胸臆的淺白,追求隱喻,突出象征與暗示,從而使詩歌由明晰變得朦朧,由確定變得不確定。所以,繼承和延續朦朧詩的開拓創新精神是“他們”反叛的前提和基礎。但是,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特色,沒有永遠流行的詩歌潮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正值青壯年的“他們”,面前呈現的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新時代:改革開放、商品化大潮、西方文化的鋪天蓋地和人們思想意識的深刻變化等。面對這一切,朦朧詩那種背負民族興亡的使命感在“他們”身上已經衰退,個體的種種生存欲望成了義正辭嚴的要求。當“北島們”開始遠離生活的真相的時候,“他們”毫不猶豫地采取了反叛“朦朧詩”的姿態。“他們”認為在清除強加于詩人身上的“非詩”的社會義務,讓詩歌回到個人的生命本體之后,詩才會與詩人的生命產生關聯。
(三)“他們”致力于打破種種遮蔽,還詩歌以自由本真。
以于堅為代表的“他們”意識到,詩歌在其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受到了層層遮蔽,以致被異化被扭曲。由此詩歌的王國也漸漸升至空中,變成天上的街市,從而遠離了自己的家。
首先,是意識形態的遮蔽。長期以來,傳統詩論一直傳承延續著“詩言志”一說,綜觀中國歷代的主流文化,都是更重視詩歌 “文以載道”的功能。尤其是20世紀以來,“革命”不僅成為整個時代的主題和中心,而且也滲透到中國文學的方方面面,意識形態的標準空前的統一。現代人從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做有意義的事情,詩歌當然也不例外。可是,“有意義”的界定標準往往是被意識形態批準的部分。這樣詩歌也就無可避免地被意識形態所遮蔽。我們關于意義的記憶結構就是“集體記憶”,而“私人記憶”喪失了它的存在空間,這“使人們往往喪失了對無意義的、私人生活的記憶,即使人們要尋找這些失去的時間,現成的話語系統也不為他們提供能指”日常生活在詩歌中被掩埋,人們對它麻木不仁、視而不見,因為人只有拋開自身完全依附于國家的意識形態,才會獲得安全感,或者就站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對立面并與之相對抗,只有這樣,他才會有存在感。長久以來,詩歌越來越形而上,不僅如此,我們的生活、文化,我們的話語方式、教育方式、寫作界限都表現出明顯的對日常生活的藐視。這樣,詩歌就被降低為意識形態的工具。
其次是知識的遮蔽,也可以把范圍夸大一些,稱之為文化的遮蔽。以知識為代表的正統文化秩序是導致詩歌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最可怕的是鼓吹詩歌應從西方獲得語言資源,應該處處以西方詩歌為標準,于堅認為這無疑是“通向死亡的知識,這是我們時代最可恥的殖民地知識……它毀掉了很多人的寫作,把他們的寫作變成了可怕的世界圖畫的寫作,變成了知識的詩。”很多詩人熱衷于對外來的復雜詩歌理論津津樂道,似乎詩歌與個體生命沒有多大關系,詩歌完全成了一種知識、一種技術,完全成了西方知識體系的附庸。這里的詩歌不再是第一性的,不再是最直接的智慧,它處處依賴知識、主義的闡釋,它只是知識、主義的復述而已。
作為逆潮流而動的一支先鋒力量,為了剝掉詩歌身上的重重負累,“他們”不再歌頌英雄,玫瑰和愛情,“他們”不是英雄,但致力于捍衛詩歌的本真,為日常生活尋找尊嚴。
參考文獻
[1]于堅.于堅的詩[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2]于堅.于堅集:人間筆記,拒絕隱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
(作者單位: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