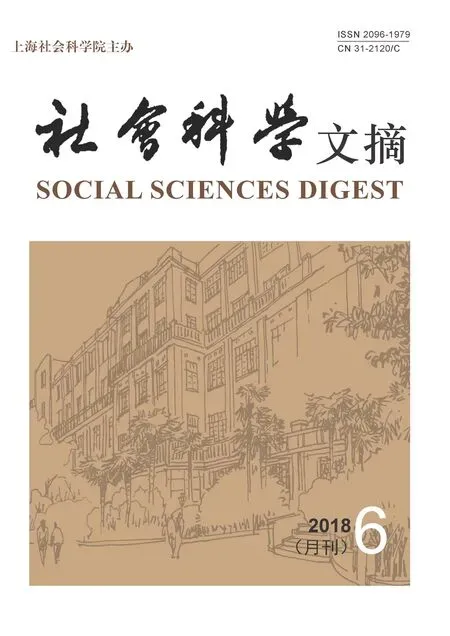中國的正義體系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文/黃宗智
筆者采用的是總體性的正義體系視野,兼及民事、刑事法律,“政”與“法”,正式和非正式正義體系,以及來自兩者的互動而形成的半正式體系(“第三領域”)。本文所論述的和引用的實例跨越古今、中西,并兼顧實踐和理論。前后一貫的是,由實踐歷史出發來突出其所展示的理論含義,特別是“實用道德主義”的二元合一(互動、互補)的思維與邏輯。據此,提出新型中華法系的前瞻性設想。
正義體系、全球視野以及新型中華法系
最近幾年,筆者在對法學和法律的探索上更明確地使用“正義體系”的概念來認識其整體的框架——包括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正義,強調唯有從如此的整體視野,才能充分認識到中國的正義體系只可能是一個同時來自三大主要傳統的體系,即古代的“中華法系”(尤其是其非正式民間調解和正式法庭斷案以及兩者之間的第三領域),近現代和改革時期從西方移植的法律,以及從中國革命傳統所承繼的政治體制與司法制度。筆者從這個角度分別對不同正義領域,如調解、婚姻法、侵權賠償法、產權法、繼承與贍養法、取證法、刑事調解以及黨國體制等所展示的三大傳統進行了梳理和論證。
筆者聚焦于民事與刑事間的關聯,說明即便是在今天,中國正義體系仍然傾向長期以來不截然劃分兩者的傳統。同時,兼用非正式正義(民間調解)和正式正義,以及由兩者的互動而在革命根據地所廣泛形成的半正式正義,如行政調解和法院調解。這里,筆者有意識地與新近的、影響極大的“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直接對話。WJP設定了八個主要要素來衡量全球主要國家的正義體系,并且比較重視其實際運作。但是,由于西方大多缺乏像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農村緊密人際關系的社區和在其中生成的調解體系,一直沒有正確認識到中國的非正式調解制度。西方近半個世紀以來所試圖建立的“非正式糾紛解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制度,無論在主導思想和運作機制方面其實都和中國的調解制度十分不同,而在實際效用方面,更和中國相去很遠。由于WJP傾向于把中國的非正式正義等同于西方自身的ADR,所以一直沒有能夠正確理解中國的調解體系。何況,其調查一直都限于每個國家的三大城市,完全無顧農村。雖然WJP如今已經認識到其在這些方面的欠缺,已經決定今后將把農村納入其調查范圍,并把“非正式正義”(informal justice)作為第九個估量要素,但尚未做到把其真正納入對全球正義體系的評估數據中,亟須進一步改正。只有正確納入農村的非正式正義指標,才有可能理解中國所代表的中華法系,包括曾經大規模引進中華法系的其他東亞國家(日、韓等)的正義體系。
關于中國正義體系中“政”與“法”之間的關聯。中國長期以來都沒有完全納入從西方引進的三權分立制度,其正義體系中的“政”與“法”一直緊密交織、纏結。此點可見于中國黨國體制中,根據“黨領導一切”的政治原則,中國共產黨所占的領導國家的“超級政黨”位置和西方的政黨一般被視作處于國家和法律之下的體制十分不同。文章追溯此體制的形成過程以及其在黨章和國家憲法文本中的體現。同時,“政”與“法”的交織更可見于廣泛的“行政施法”實際之中,如公安部門所大規模執行的“公安調解”司法功能,以及其所設置和管理的感化教養等機構(包括未成年人管教),也可以見于基層法律事務所的調解和司法功能等。“行政施法”更可以見于黨組織本身的“雙規” 制度,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下設置作為勞動糾紛訴訟前置條件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仲裁制度,以及國家直接通過《工傷保險條例》(2004年起實施)而介入工傷事件的裁定等諸多實例。此外,還有由行政部門以及地方政府分別發布的半正式、半法律的行政“條例”“規定”“補充規定”“通知”“意見”等。如此行政與法律交織的體制固然帶有韋伯所批判的行政權力介入司法的問題,但在轉型中的中國,應該可以說也不失為一種能夠更靈活地在法律之外采取多渠道的行政和半法律措施來處理社會問題的體制。雖然,未來肯定需要進一步規范。
此外,筆者特別聚焦于2006年頒布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失敗實例,其基本出發點是試圖模仿高度企業化的美國農業,完全無視中國農村社區以及其仍然主要是小農經濟(而不是企業化農業)的基本實際。它是一個意圖憑立法手段來進行行政管理的實例。這是一個由錯誤的立法意識形態所主導的實例,導致了大量的“偽”“空”和“虛”合作社的興起,對中國農業的發展、農民的權益和農村的重建都沒有起到該有的作用。如此的經驗應該成為我們的教訓,既是主導(模仿美國關乎農業的)立法思想上的錯誤,也是脫離實際的意識形態和過分依賴行政權力的錯誤。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美國的高度形式主義化法律如今所顯示的諸多弱點。舉其要者,首先是律師和法庭費用高得離譜,已經遠遠超出一般人民所能肩負的程度——這是韋伯早已經觀察到的問題。其導因歸根到底乃是(韋伯所倡議的)法律體制的高度封閉化和專業化。再則是過度形式化而無顧實質的問題。譬如,如今大跨國公司廣泛雇用眾多專業律師和會計師來為其鉆形式化法規中的漏洞和空隙,慣常并公開地從事實質上違法但形式上合法的行為。再則是過度法條主義化的問題。譬如,美國法律近年來廣泛過度形式化地使用“三振出局”的條文,不合理地嚴重懲罰下層社會的輕罪者,尤其是少數民族和貧窮群體。那樣的現象與跨國公司的行為形成鮮明的對照,直接影響到法律體系整體的威信和效率。固然,中國的實質主義傾向也有眾多的弱點,但可以適當采用一定程度的程序化和規范化來遏制。這不是一個形式與實質非此即彼的問題,應該是一個在兩者之中“取長補短”的問題。
相應當前的“民法典”編纂,欲探討更為系統的突出融合中西的理論與實例,可以聚焦于三個主要領域:
一是結合實證性調節(包括民間、行政與法院調解)與形式化法院制度的具體方案,建議從具體情況出發,在無明確過錯的爭執中采用實質性調節,有明確對錯的糾紛則采用形式化的法院裁判。
二是在道德理念層面上,倡議結合中國的“家庭主義”道德理念和西方的“個人主義”法理,考慮到現今社會的實際需要與具體問題,可以在不同的實際情況下,適用或結合不同法理的方案。
最后是“政”與“法”交織的黨國體制,以及如何長期結合的可能方案,倡議把黨章確立為中國的非正式“實質憲法”,借此以進一步明確共產黨自我設定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歷史使命。同時,以引進的形式主義憲法為國家機構的正式“形式憲法”。兩者可以逐步形成一個相互補充和制度的體系,取長補短。這其中的一個要點應該是,在革命勝利已經70年之后的今天,可以把黨組織進一步透明化、民主化,更完全地脫離其列寧主義式的地下革命歷史背景遺留下來的一些不再符合歷史需要的制度和操作方式。如今,中國正處于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需要設想、創建可以長期持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萬世之法”的正義體系。
新型的中華法系
首先把法律和正義理解為活生生的使用和轉變中的體系;從歷史、現實及其前瞻的視角來設想中國應建立的正義體系,試圖根據已經具有一定成功經驗的具體實例來初步勾勒一個未來的圖景;同時,也檢視一些反面的實例,來進一步闡明正面實例的含義以及其對立法方向的啟示。
作者的視野和如今分別占據法學兩大主流的“移植主義”和“本土主義”都十分不同,也與簡單的、描述性的“多元主義”不同。所突出的是一個融合和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路;說明長期以來實用道德主義在中國古今正義體系中所起的主導作用;闡釋其與來自西方的形式主義主流的不同,由此來勾勒一個“實質理性”的正義體系傳統。而后,借助西方挑戰主流的理論,如美國的實用主義、現實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傳統,以及歐洲的“歷史法學”“法社會學”“程序主義”法學等非主流法學傳統,來對形式主義法律進行優劣的梳理,再由此探討中國的實質主義法律傳統應該如何與西方偏重形式主義的法律共存、拉鋸和融合。
筆者不僅從立法的角度,也從學術研究和認識論的角度來對比“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兩大法律思維方式,并建議同時借用兩者,由其相互作用、融合以及創新來超越單一方的局限和偏頗,借此來形成未來的新型中華法學。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考慮,形式和實質、抽象和具體、普適和特殊都是真實世界所必然具有的雙維,不可簡單偏重任何單一方。兼顧雙方,追求其最優配合乃至超越兩者,既是學術認知也是正義體系制定的明智選擇。未來的道路需要從兩者的實際并存出發,不僅要追求其逐步磨合,更要探索其融合與超越的道路。那樣,才可能真正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束縛,建立中國式的、真正現代的、可長期持續的新型中華法系。
一個新型的“萬世之法”
中國今天面對的問題使我們聯想到秦漢一統之后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簡單繼受春秋戰國百家中任何一國或一家的理論,而是在新時代中,如何建立新的、長期可持續的“萬世之法”的問題,尤其不是在法家或儒家的二元對立之中簡單選一的問題,而是要探尋超越兩者的綜合;不是繼受任何單一元,而是如何綜合多元的各元而超越之,如何開啟綜合與整合的、長遠的正義體系。
回顧漢代前期的歷史,對我們今天的問題具有特別啟發的思想是當時的儒家思想,特別是董仲舒(約公元前179—前104年)思想中的洞見。他在嚴峻的法家的治理體系和法律之上,納入、貫穿儒家的道德理念,特別是“仁政”與“德治”,借以補法家之不足,要求在嚴厲的制度之中,添加和貫穿仁慈、溫和的道德理念。其卓越之處在于不簡單依賴法、儒任何單一方,而是憑借兩者的并用與結合來創建一個更寬闊、更包容、更可持續的正義體系。
如此的思路和其從陰陽學納入的宇宙觀是一致的,認識到陰與陽的有機結合,好比法家與儒家的結合,要比任何單一方更全面、更可持續,盡可能使偏重刑罰的(正式正義的)法家法律體系為輔,儒家的德治、仁政為主。同時,借助儒家的和諧人際關系理念,開啟家族和村社中的(非正式)民間調解機制之逐步形成,其后成為非正式正義(民間調解)與正式正義(法庭判決)結合的正義體系,比其任何單一方具有更為長期的可持續性。在我看來,正是這些基本點,而不僅是瞿同祖先生所強調的把法家法律等級化(即在其適用中加上儒家的尊卑之分),才是“法律的儒家化”的至為重要的內容。其實,瞿同祖在其論證法律的儒家化的過程中,雖然特別突出了源自儒家的尊卑等級之分,但在其著作的最后部分,也提到了董仲舒的“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的思路”,“陽儒陰法”的構想。當然,瞿之特別強調“禮”和“三綱五常”,以及其中的等級尊卑劃分,把其當作儒家的核心制度,是沒有錯的,但在筆者看來,儒家的思想中至為關鍵的,不是其等級制度,而是具有普遍價值的“仁”的崇高道德理念。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
董仲舒承繼的是儒家一貫的“仁政”理念,譬如,聲稱“天,仁也”,提出“以仁安人,以義正我”的設想。特別是對“德”與“利”的鑒別,即《論語》之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由此來反思劇變時代中的社會現實。對我們今天的現實來說,這樣的理念有極其重要的啟示。“利”是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核心。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最主要的潮流“新制度經濟學”提倡的是,憑借人人自我逐利來推動經濟發展,并因此而特別強調穩定的私有產權,認為那樣才有可能激勵人們的創業而推動經濟發展,并美其言曰,如此才能造福全社會。在那樣的價值觀的影響下,如今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逐利“小人”的天下,幾乎人人都在忙著盤算怎樣去賺更多錢。儒家的“義”與“利”劃分則自始便已對此做出了深刻的批評,可以說一言點到其中的致命問題。今天讀來,特別適切。
固然,董仲舒非常有意識地要為漢代皇朝建立一統天下的統治意識形態。西方19世紀的漢學大家理雅各,在其影響深遠的大作中把其稱作“帝國儒家主義”。其中,董仲舒借助“陰陽五行”的宇宙觀將皇帝置于“天人之際”,為的既是鞏固皇帝的威權,也是借“天”來限制皇帝的權。他特別強調“災異”,以為其表達了“天”對處于天人之際的皇帝的“譴告”。那樣的學說,雖然鞏固了歷代的帝國政治體制,但是并不符合當今的需要。它有意識地把儒家學說構成一家獨尊的統治意識形態,乃至于將其宗教化,當然也不符現實需要。
這里還要說明,在儒學之中,董仲舒的帝國儒家主義思想和經學中的今文學派有一定的關聯。在今文學(亦可稱公羊學)的“家法”中,一貫把孔子建構為“有其德而無其位“的“素王”;讀《春秋》以《公羊傳》(而不是《左傳》)為主導,突出其所包含的“微言大義”,特別是對統治者的“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宇宙觀則取自《易經》。如此的思想帶有強烈的應時而變的歷史感與“改革”傾向,故其“家法”包括把孔子認作“圣之時者也”。到了近現代,今文經學派的這些思路在康有為的思想中得到至為系統的表達。筆者青年時曾在臺灣師從經學家愛新覺羅·毓鎏(“俗姓”劉,康有為的第三代“天游輩”弟子,后來在臺灣的經學界中影響頗大),對劉毓鎏老師講授的這些(公羊)“家法”至今記憶猶新。今天回顧,其核心在其崇高的、帶有永恒價值的道德理念“仁”與“德”——也是中華文明以及中華法系的核心。
筆者正是出于對儒家和其所代表的中華文明如此的理解,來設想中國正義體系今后的走向。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復古設想,當然也不是簡單的全盤西化設想。我們需要的是:一方面借助儒家思想中至能適應現代需要的傳統,來對中華文明的實質理性正義傳統進行溯本求源的梳理;另一方面同樣借助西方一些至具洞察力的非主流傳統,如法律實用主義、后現代主義以及實質主義來對其主流形式理性法律傳統進行去劣存優的梳理。在兩者的并存和拉鋸的大框架之下,來設想一個新型的中國正義體系。具體的研究和所倡導的立法進路則是,從實踐歷史中區別優良的融合和惡劣的失誤,梳理其中所包含的法理,借此來探尋綜合兩者的方向和道路。這是一個要求綜合中西的設想,也是一個要求適用于中國變遷中的實際的設想。筆者深信,來自那樣的探索而形成的正義體系,才可能成為一個可供“萬世”之用的新型中華法系。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