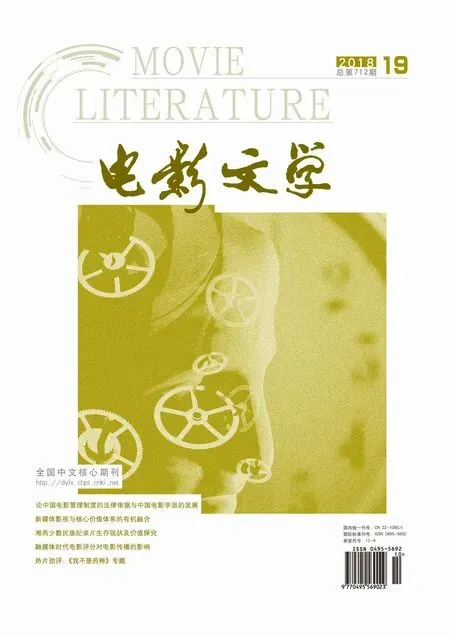《我不是藥神》與國產現實主義電影走向
朱雪梅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上海 200061)
現實主義已經被公認為我國電影藝術創作中的一種較為穩健,但又一直有所創新和突破的“超穩定結構”。近年來涌現的能適應時代發展,能滿足當代觀眾文化藝術需求的優秀現實主義電影,如《戰狼2》《紅海行動》等便是明證。而新銳導演文牧野的《我不是藥神》(2018)也是一部根植于當前藝術土壤,實現口碑與票房雙豐收的現實主義佳作。從這部電影中,我們可以一窺我國現實主義電影的創作走向。
一、傳統現實主義美學尺度的延續
我國電影創作與批評理論中的現實主義,沿襲的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而馬克思、恩格斯從對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等作品的分析中所提出的美學尺度也存在于包括《我不是藥神》在內的諸多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
根據韋勒克在《文學研究中的現實主義概念》中的總結,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的現實主義必須有如下三個特征,即客觀性、典型性和批判性。客觀性,即作品描摹的應該是客觀的生活,包括客觀事物和人際關系。《我不是藥神》根據真實存在,并引起社會轟動的“陸勇案”改編而成。主人公,因為為白血病患者代購印度仿制藥“格列寧”而招致牢獄之災的程勇,其原型正是陸勇。同時,電影又未拘泥于陸勇案,而是在藝術形象層面上,改變了程勇的身份性情,剝離了他的白血病患者身份,以使其更接近大部分觀眾的現實境遇和旁觀者視角。典型性,電影虛構出了呂受益、思慧、“黃毛”和劉牧師等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形象。幾個男病患角色代表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齡段和經濟條件的白血病患者,而思慧則是在經濟困窘的典型環境中,不愿意放棄親人的典型家屬形象;而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帶有“反面人物”色彩的張長林和瑞士醫藥代表等,也是代表了各方利益的典型人物。
而批判性則指的是作品要敢于大膽暴露社會弊端,這也正是《我不是藥神》引發觀影熱潮和一致好評的原因之一。在研發藥物的時候投入了巨額資金,需要從市場討回成本的藥廠保護版權的合理訴求,以及白血病等重疾患者面臨有藥而無法支付巨額藥費,只能含恨逝世的慘狀在電影中形成了尖銳沖突。有著求生欲的患者成為“天價藥”面前砧板上的魚肉、待宰的羔羊,激發著觀眾的同情,這無疑隱含了某種主創的變革訴求。而電影結尾時的字幕宣布了進口藥的零關稅及格列寧的入醫保政策,標示了問題得到了部分程度上的解決,也是這種批判性的體現。
二、與商業的接駁
王一川就曾指出:“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完整的藝術思潮和流派,早已退出世界藝術的主流舞臺了。”盡管現實主義的力量被邊緣化、隱性化,它依然是當代社會現實所不可或缺的特定角色。《我不是藥神》就體現著國產現實主義的新變。
首先是和商業接駁。在“大片時代”來臨后,國產現實主義電影實現了和商業的接駁,除前述的《戰狼2》等外,如馮小剛的《集結號》《唐山大地震》,以及參與到《我不是藥神》創作的寧浩、徐崢的《瘋狂的石頭》《泰囧》等,都是走現實主義路線,并能成功推向市場的商業電影典范。《我不是藥神》也有著商業電影屬性,電影選取的醫療醫藥問題本身就是觀眾所關切的現實話題,而一再與喜劇掛鉤的徐崢、王傳君等演員的遴選,也無疑能激發觀眾走進電影院的興趣。
值得一提的是,當現實主義和商業電影進行接駁時,如何在現實主義洞察現實、思考問題的嚴肅性,和商業電影的娛樂性與功利性之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就成為電影人所必須思考的問題。一般來說,國產商業電影在現實主義敘事這方面暴露出三種傾向,即游戲化(如《泰囧》)、浪漫化(如“小妞電影”)和奇觀化(如《瘋狂的石頭》等),這也就導致了現實生活在電影中經過了某種美化,而人們在現實中遭受的種種痛苦、掙扎等也都被淡化了,觀眾從電影中獲得的更多是愉悅和滿足。而《我不是藥神》恰恰規避了這一缺憾,電影關注、悲憫底層民眾的立場和態度是相當鮮明的。如呂受益在停藥一年后就痛苦去世,即使妻子不惜代價挽留丈夫的生命依然只能落得孤兒寡母的結局;思慧的丈夫拋棄妻女,思慧為了撫養女兒而一再被迫出賣肉體;張長林道出:“我賣藥這么多年,發現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這些都使得觀眾備感壓抑沉重,電影沒有為了向娛樂性妥協而將程勇等人在法律夾縫中販藥求生的過程游戲化、輕松化,而是將看似遙遠的白血病人生活拉近到觀眾面前,既不過分渲染其慘切,又傳達給觀眾一種心酸的滋味。
三、與其他藝術的融合
如前所述,國產現實主義電影同樣要面對市場的商業要求,同時,現實主義的創作理念,電影具體的表現手法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被揚棄的,正如布萊希特所指出的,現實在變,現實主義自然也在變。在電影創作日趨多元化的今天,國產現實主義電影出現了“轉益多師”的傾向,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藝術表現形式也開始進入到電影中,這可以視作現實主義的一種自我壯大和發展。
在《我不是藥神》中,現代主義中打破時空秩序,重視人的意識活動的一面就有所體現。在程勇被押解去監獄的路上,病人們紛紛前來送行,而就在人群之中,程勇看到了“黃毛”和呂受益,而這是違背現實的,因為兩人此時早已去世,但是他們是程勇最為重要的朋友,此時程勇看到二人,這實際上是他的幻覺和遐想。而在表現程勇拉攏各路“人馬”時,為了表現健康人與病人之間的互動和碰撞,電影運用了后現代主義中常見的多元化、荒誕化敘事,夸張人物的毛病,將人物“小丑”化,如呂受益、程勇和牧師的幽默對話等,甚至是對老電影進行“戲仿”,如思慧拿起折凳打架的場景,就是對周星馳電影的一種戲仿。電影在表現人物、調侃人物時,讓觀眾意識到人物行為兼具崇高、偉大和狹隘、自私的荒誕雜糅,使得人物更容易為觀眾接受。可以說,這些都給予了觀眾一種耳目為之一新的審美感受。可以預料到的是,國產現實主義電影還將繼續這種“有主元的多元”走向,汲取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中的藝術養分。
現實主義創作觀是包容性極強,且不是一成不變的。從《我不是藥神》中,我們不難發現,一方面,傳統的現實主義美學尺度依然歷久彌新,而另一方面,現實主義電影又有著與商業進行接駁,與其他藝術融合的“再出發”態勢,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