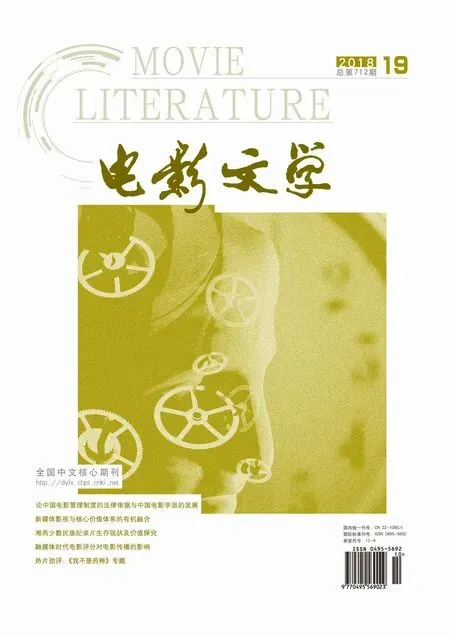《贖罪》的U型敘事解讀
郭宇飛
(河南城建學(xué)院,河南 平頂山 467000)
一、引 言
影片《贖罪》由英國著名導(dǎo)演喬·懷特執(zhí)導(dǎo),詹姆斯·麥卡沃伊、凱拉·奈特莉、西爾莎·羅南等人主演。曾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改編劇本提名,影片所涵蓋的愛情、人性、戰(zhàn)爭等多重主題使其展現(xiàn)出了耐人尋味的豐富內(nèi)涵,同時復(fù)雜多變的敘事結(jié)構(gòu)也體現(xiàn)出了英國本土影片的藝術(shù)魅力。該片改編自英國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的同名小說,將故事置于20世紀(jì)30年代的英國,圍繞英國處在上流社會的泰麗思家兩姐妹的故事展開敘事,展現(xiàn)了一幕由謊言引發(fā)的愛情悲劇和救贖之旅。許多評論家認(rèn)為,影片《贖罪》采用了較為繁復(fù)的敘事結(jié)構(gòu),通過多種敘事結(jié)構(gòu)的融合增加了影片的觀影難度,為觀眾帶來了陌生化的審美體驗。事實上,在這種繁復(fù)的敘事結(jié)構(gòu)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U型敘事”這一主線,即圍繞泰麗思家姐妹展現(xiàn)的“美好與寧靜—謊言與災(zāi)難—悔恨與救贖”的敘事,正是在這樣一種跌宕起伏、復(fù)雜多變的敘事中,影片的“罪”與“贖”及其背后的豐富內(nèi)涵才得以深化。本文將從影片的劇情設(shè)計、人物心理分析等角度入手,以影片故事中的謊言、災(zāi)難、救贖為焦點,解讀影片的U型敘事結(jié)構(gòu),展現(xiàn)影片在敘事主題和敘事方式層面的審美價值。
“U型敘事”最初由著名文藝批評家弗萊提出,在《偉大的代碼——圣經(jīng)與文學(xué)》中,弗萊從《圣經(jīng)》里的《士師記》入手,探討了一種經(jīng)歷下降、上升并上升至原有高度的敘事結(jié)構(gòu),并由此提出整部《圣經(jīng)》的故事發(fā)展軌跡和敘事脈絡(luò)都包含在這種“U型敘事”之中。從《圣經(jīng)》來看,創(chuàng)世紀(jì)之初,人類始祖亞當(dāng)和夏娃無憂無慮地生活在伊甸園中,在蛇的誘惑和人的背叛中,人類被逐出伊甸園,失去了生命之水和生命之樹,陷入到了逃亡、災(zāi)難、痛苦之中,在耶穌贖罪后,人類重新獲得了曾經(jīng)失去的美好。可以說,“U型”的敘事脈絡(luò)和“贖罪”的核心情節(jié)就是弗萊所提出的U型敘事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鍵,將“U型”和“贖罪”置于影片《贖罪》中,不難發(fā)現(xiàn)該片在多線交織的敘事中呈現(xiàn)出了四個敘事段落。第一個敘事段落發(fā)生在1935年的泰麗思家中,臆想和誤解凝造的謊言改變了泰麗思家姐妹塞西莉亞和布里奧妮及泰麗思家族的管家之子羅比這三個年輕人的命運,羅比背負(fù)著強奸罪鋃鐺入獄,青梅竹馬的塞西莉亞悲痛萬分,而謊言的制造者布里奧妮則陷入了終其一生的悔恨之中,第一部分也成為整部影片“U型”和“救贖”的起點。第二個敘事段落和第三個敘事段落分別發(fā)生在1939年的二戰(zhàn)戰(zhàn)場和戰(zhàn)地醫(yī)院,主人公通過參戰(zhàn)來追尋現(xiàn)實層面和精神層面的救贖。第四個敘事段落則發(fā)生在跨越了半個世紀(jì)后的1999年,年邁的布里奧妮通過撰寫小說的方式為其一生的贖罪之旅畫上了悲傷的句點。四個敘事段落以塞西莉亞和羅比的愛情故事與布里奧妮的贖罪之旅為主線,展現(xiàn)了包括階級的差異、殘酷的戰(zhàn)爭、復(fù)雜的人性等現(xiàn)實問題,這些在不同敘事段落中凸顯出的現(xiàn)實問題與貫穿始終的愛情、贖罪兩大主線交織呈現(xiàn),共同構(gòu)成了影片《贖罪》紛繁復(fù)雜又頗具深度的敘事影像。
二、美好中的謊言
影片《贖罪》的故事開始于1935年,處在上流社會的泰麗思家族來到鄉(xiāng)村中的莊園避暑,長女塞西莉亞與管家之子羅比一起長大,共同進(jìn)入劍橋大學(xué)學(xué)習(xí),雖然并未成為戀人但卻暗藏情愫。在一個炎熱的下午,塞西莉亞在花園中脫掉衣服跳入噴泉中乘涼,而恰巧路過的羅比被心愛之人曼妙的身姿所吸引并駐足觀看,這一場景被泰麗思的小女兒布里奧妮盡收眼底,成為改變?nèi)齻€年輕人命運的開端。隨著劇情的發(fā)展,布里奧妮對羅比的誤會越來越深,出于混合著好奇、嫉妒的復(fù)雜心理,布里奧妮偷看了羅比寫給姐姐塞西莉亞的信件,進(jìn)一步確定羅比對塞西莉亞存在著異常的情感,年幼的布里奧妮并沒有真正理解這份熾熱情感中的真愛,反而認(rèn)為羅比是一個色情狂。就在布里奧妮專注于羅比的不軌之行時,莊園的寧靜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強奸案所打破,泰麗思家的表親勞拉在莊園里慘遭強奸,就在泰麗思家族查找線索時,布里奧妮的謊言將羅比送進(jìn)了監(jiān)獄,而事實上布里奧妮并沒有真正看到羅比犯案的過程,只是憑借一個熟悉的背影和主觀的臆想將羅比認(rèn)定為強奸犯。正是布里奧妮的謊言徹底改變了羅比的命運,不僅羅比以強奸犯的身份鋃鐺入獄,羅比與塞西莉亞青梅竹馬的情誼也被斷送了。
在羅比蒙冤入獄后,塞西莉亞堅信羅比的清白,憤然與泰麗思家族斷絕關(guān)系,而塞西莉亞和布里奧妮的表姐勞拉卻順勢從受害者變成了豪門貴婦,嫁給了真正的強奸犯保羅,一系列變故使13歲的布里奧妮陷入了深深的自責(zé)和悔恨之中,自幼迷戀文學(xué)、富有想象力的布里奧妮盡管沒有害人之心,但卻實施了害人之行,用一個謊言背叛了親人、朋友,使羅比和塞西莉亞的愛情走向悲劇,同時也將泰麗思莊園中的三個年輕人的命運引向了黑暗的邊緣。在這個關(guān)于強奸的謊言背后,影片《贖罪》所體現(xiàn)的不僅僅是少女的無知和人性的復(fù)雜,還呈現(xiàn)了20世紀(jì)上半葉英國社會的等級制度和階級差異。影片男主人公羅比是一個外貌英俊、性情溫和的少年,在泰麗思家族的資助下成為劍橋大學(xué)的高才生。盡管如此,普通家庭出身的羅比在英國社會尤其是富有的泰麗思家族中并沒有獲得足夠的尊重,管家之子的身份也使羅比和塞西莉亞的戀情無法公之于眾。與羅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影片中真正的強奸犯保羅,身家不菲的保羅是一個典型的偽紳士,身處上流社會的他道貌岸然,肆意犯下強奸惡行,更為諷刺的是,保羅憑借上流社會的地位和雄厚的家產(chǎn)成為受害人勞拉的追求對象。階級的差異在這次意外事件和少女的謊言中得到了鮮明的對比,對歷史的批判也使得影片《贖罪》的U型敘事更具深度。
三、戰(zhàn)爭中的災(zāi)難
布里奧妮的謊言所導(dǎo)致的災(zāi)難并沒有止于羅比的入獄,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場上,泰麗思莊園中的三個年輕人懷著不同的心情,以不同的身份參加了戰(zhàn)爭。身為囚徒的羅比為了洗刷強奸犯的惡名成為一名征戰(zhàn)前方的士兵,而泰麗思姐妹則成為戰(zhàn)時救護(hù)隊的成員。與家族斷絕往來的塞西莉亞渴望在戰(zhàn)場上與昔日的戀人再續(xù)前緣,而布里奧妮則希望能夠當(dāng)面向羅比和塞西莉亞道歉,為昔日的謊言贖罪。喬·懷特在影片中通過戰(zhàn)爭這一大災(zāi)難展現(xiàn)了三個年輕人所面臨的命運之災(zāi),在1939年的故事講述中,導(dǎo)演構(gòu)建起了兩線并行的敘事結(jié)構(gòu),即羅比在戰(zhàn)場前線的廝殺和泰麗思家姐妹在戰(zhàn)后醫(yī)院的救護(hù)工作,通過戰(zhàn)爭的殘酷來展現(xiàn)三個年輕人的災(zāi)難命運和精神困境,同時又通過以小見大的方式圍繞敦刻爾克戰(zhàn)役呈現(xiàn)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殘酷。
在戰(zhàn)場中,喬·懷特從男主人公羅比的眼睛特寫為起點,通過劇中人的視角來呈現(xiàn)戰(zhàn)場影像,當(dāng)羅比所處的小隊在叢林中行進(jìn)時,羅比獨自走到了一片林間空地中,空地上一排少女的尸體使羅比停下了腳步,此時的鏡頭再次轉(zhuǎn)換到羅比的眼睛上,透過這雙湛藍(lán)色的眼睛,憤怒、恐懼、厭惡、震驚以特寫的方式呈現(xiàn)在銀幕之上。在通過羅比的視角特寫呈現(xiàn)戰(zhàn)爭中的死亡的同時,喬·懷特還采用全景式的拍攝方式展現(xiàn)敦刻爾克海灘撤退時的場面,在長達(dá)5分鐘的長鏡頭中,轟炸后的殘樓、廢棄的炮臺、受傷的士兵和哀號的平民均被收入到鏡頭之中,配合灰暗的色調(diào)凸顯了戰(zhàn)爭的殘酷,同時也襯托出了男主人公羅比在災(zāi)難命運中的無奈和悲涼。行軍途中,羅比在敵軍的轟炸中負(fù)傷,嵌入體內(nèi)的彈片最終使羅比患敗血癥身亡,而塞西莉亞也死在了被轟炸摧毀的防空洞中。伴隨著羅比和塞西莉亞的死亡,影片《贖罪》的故事已到達(dá)了U型敘事的“最低點”。同時,羅比和塞西莉亞悲劇愛情的結(jié)束也代表著布里奧妮現(xiàn)實層面的贖罪和自我救贖的失敗。影片將發(fā)生在泰麗思莊園的謊言和災(zāi)難終止于戰(zhàn)場之上,賦予個體所面臨的災(zāi)難以更宏大的歷史背景,在個體災(zāi)難與群體災(zāi)難的相互映襯下,凸顯了影片在愛情、人性之外的反戰(zhàn)主題。
四、幻境中的救贖
正如上文所述,布里奧妮在充滿想象與天真的13歲釀造了一個背叛真實、背叛親情的謊言,在謊言成真、羅比被帶上警車時,布里奧妮從臆想的世界中驚醒并開始了終其一生的贖罪之旅。面對羅比蒙冤入獄,布里奧妮一度無法面對自己的謊言,放棄了為羅比洗清冤屈和向塞西莉亞說明真相的機會,致使羅比在獄中參軍、塞西莉亞與家族決裂走向戰(zhàn)場。隨著年齡的增加,布里奧妮內(nèi)心的愧疚與日俱增,尤其是在她意識到昔日強奸案中熟悉的男人背影就是迎娶勞拉的保羅時,愧疚和悔恨徹底占據(jù)了布里奧妮的內(nèi)心,為了通過向羅比贖罪來實現(xiàn)自己內(nèi)心的救贖,她放棄了繼續(xù)求學(xué)的機會,像姐姐一樣奔赴戰(zhàn)場。在戰(zhàn)場后方,布里奧妮并沒有獲得贖罪的機會,反而在殘酷的戰(zhàn)爭中陷入了更深的愧疚和悔恨之中,一位名為路科的士兵在負(fù)傷后轉(zhuǎn)移到醫(yī)院,殘損的頭骨和紅色的腦髓使布里奧妮在震驚之下手足無措,直面戰(zhàn)爭殘酷后的布里奧妮自我救贖的渴望也更加強烈。布里奧妮所救治的士兵路科因腦部受傷呈現(xiàn)出了解離性狀態(tài)病癥,思維混亂的他所呢喃的只有與愛人美好生活的回憶,這種美好的回憶也成為路科在病痛之時唯一的“止痛藥”。這一情節(jié)的設(shè)置表面上看無關(guān)故事主線,但卻映射了布里奧妮現(xiàn)實層面贖罪和自我救贖的失敗,幻想中的美好與現(xiàn)實里的殘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弗萊通過對《圣經(jīng)》的研讀所提出的U型敘事是由美好下降為災(zāi)難,再由災(zāi)難上升至原有的美好的一個過程,嚴(yán)格來說影片《贖罪》所采用的并非典型的“U型敘事”,而是通過現(xiàn)實與臆想的交織來完成的這一“U型”敘事,在打亂時間順序的敘事中,影片外的觀眾直到最后一刻才看到了羅比和塞西莉亞的死亡,而影片內(nèi)的布里奧妮則是在長時間的愧疚心理的影響下再次進(jìn)入了臆想狀態(tài),幻想著羅比和塞西莉亞的重逢,進(jìn)而將這段愛情故事的美好結(jié)局寫入了小說中,在精神失常的狀態(tài)下模糊了現(xiàn)實與臆想的界限,從而獲得了內(nèi)心的釋然和心靈的救贖。在影片第四個敘事段落中,時間飛逝至1999年,垂垂老矣的布里奧妮已完成了關(guān)于羅比和塞西莉亞的贖罪之作,在小說世界中澄清了昔日的謊言,同時她也被醫(yī)生確診患有精神疾病,此時布里奧妮口中和筆下的美好結(jié)局不僅是虛幻的,更是具有強烈的諷刺性和宿命論色彩的,諷刺的焦點在于包括欺騙、懦弱、自私在內(nèi)的人性的弱點,而宿命色彩則與影片所呈現(xiàn)的階級問題、戰(zhàn)爭主題相呼應(yīng)。如果說布里奧妮少年時的謊言是羅比與塞西莉亞災(zāi)難命運和愛情悲劇的始作俑者,那么階級觀念和戰(zhàn)爭則成為個體悲劇的重要推手,如果沒有謊言,羅比和塞西莉亞的美好愛情是否也會成為一個不可能的夢呢?這是影片留給觀眾的思考。
影片《贖罪》是喬·懷特所執(zhí)導(dǎo)的第二部電影,憑借這部電影,喬·懷特入圍第65屆美國金球獎最佳導(dǎo)演獎和第61屆英國電影學(xué)院獎最佳導(dǎo)演獎,確立了其在美國好萊塢和英國影壇的地位,影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喬·懷特在敘事結(jié)構(gòu)上的大膽嘗試。這種大膽嘗試集中體現(xiàn)在非典型U型敘事之上,在采用U型敘事主線的過程中,喬·懷特打破了英國傳統(tǒng)改編電影的線性敘事,通過時間空間、現(xiàn)實幻象的雙重交錯營造了充滿懸疑和陌生感的氛圍,同時通過愛情、戰(zhàn)爭、人性等多主題的呈現(xiàn),深化了影片的歷史感和現(xiàn)實批判性,使影片中的U型敘事煥發(fā)出了更加新奇、更為深刻的審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