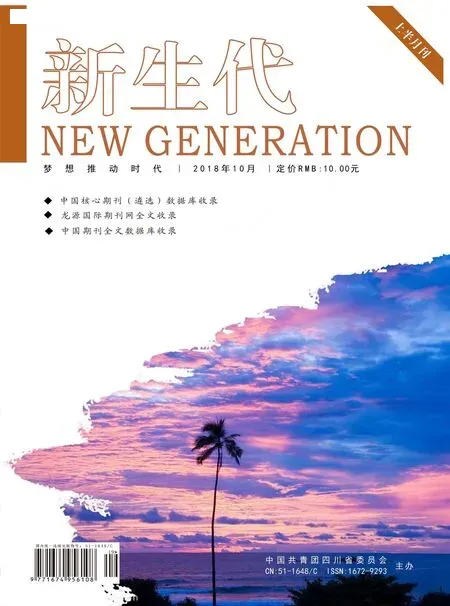一致而百慮之群己之辨淺析
韓春海 上海師范大學
馮契(1915~1995),原名馮寶麟,20世紀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他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底蘊與造詣極深,創造性地建構了中、西、馬融合的“智慧說”哲學思想體系,深刻揭示了中國哲學精神的特點。其代表作“智慧說三篇”(《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哲學史兩種”(《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反映了其理研究的高水平,至今仍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與價值。在其近半個多世紀的思想跋涉中,馮契既經歷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浸于中國的智慧長河。而對人類認識史的沉思與反省,又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及時代問題的關注。從早年到晚年,馮契以始于智慧又終于智慧的長期沉思,為中國當代哲學留下了一個創造性的體系。以智慧的探索為中心,馮契的哲學思考涉及中國哲學史,認識論,價值論,倫理學,美學,邏輯學等,各個領域。馮契對認識論作了廣義的理解,認為它包括以下四個問題:第一,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在?第二,理論思維能否達到科學真理?第三,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第四,人能否獲得自由?或者說,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養?認為,它不應限于知識論,而且還應是研究智慧的學說。按照馮契的理解,廣義的認識過程,包括兩個飛躍,即從無知到知的飛躍和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由無知到知的過程,發端于實踐中獲得的感覺,這種感覺能夠給予客觀實在。馮契認為知識經驗領域無非是以“得自經驗者,還自經驗,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由此形成了知識經驗。經驗知識,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馮契看來,認識并不限于經驗領域,他同時指向性與天道。如果說認識論的前兩個問題主要關聯著經驗知識,那么智慧,則更多地涉及認識論的后兩個問題,及關于性與天道的認識。而關于道的真理性認識又內在的關聯的人的發展,后者便展開為自由的人格。馮契肯定,邏輯思維能夠把握具體真理,人能夠在有限中認識無限,在相對中揭示絕對,而這一過程,即表現為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
對知識和智慧關系問題的探索所得的結果,就是《智慧說三篇》。三篇著作各具相對的獨立性,又相互聯系成為一個整體。《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是其主干,而《邏輯思維的辯證法》與《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其兩翼。第一篇的主旨在講基于實踐的認識過程的辯證法,特別是如何通過“轉識成智”的飛躍,獲得關于性與天道的認識。第二篇主旨是講“化理論為方法”,第三篇的主旨是講“化理論為德性”。馮先生在《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中對認識論作廣義的理解,不僅把認識論看成是關于知識而且是關于智慧的理論。文章是著重談關于智慧的學說。從智慧這個角度來考察認識論,講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兩者之間的關系,并在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交互作用中“轉識成智”和培養自由人格。馮契先生,在反對獨斷論和相對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一致而百慮”的思維矛盾運動。并通過群己之辨、群體意識和個別精神等章節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論證。在反對獨斷論中,列舉了孔子“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孟子“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說他們都很自負,以為自己所把握的“道”,就是治國平天下的唯一正確道路。并引用戴震批評的話“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進行批判。馮契先生認為這種獨斷思想是要不得的。而另一種觀點《莊子·齊物論》中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為是非無法辨明,各種意見的分歧是沒有辦法明辨清楚的,這種論調就倒向了相對主義。對此,墨家從形式邏輯做了批駁,就是《墨辯》所說的:“謂辯無勝,必不當。”而荀子進一步從辯證法的角度闡明了“辯”的本質。“不異實名”即辯論中不能偷換概念,要遵守同一律。辯說要有正確的態度:“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就是說,論辯中一要出于仁心,與人為善,幫助別人;二要虛心學習,聽取別人的意見;三是要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不參雜一點私心。荀子說:“君子必辯”(《荀子·非相》),對辯論抱著樂觀的積極的態度,富于辯證法的精神。和荀子相比《易傳》比較有寬容精神,說:“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就是說思慮的展開表現為“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矛盾運動。人們在認識過程中通過意見的爭論,達到了一致的結論,通過不同途徑達到了共同的目標,而“一致”又產生“百慮”,同時又引起不同的意見分歧,于是又有新的爭論……由于這樣的“一致”和“百慮”的循環往復運動,認識就表現為不斷的產生問題,又不斷的解決問題的過程,而人類的整個認識過程就是由無數的“一致”和“百慮”往復,錯綜交織成的前進上升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也自然而然涉及群己之辨。群己之辨古已有之而且包含涉及好多領域:楊朱“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墨家“兼愛”,“愛無差等”;孔子講“推己及人”。這些都涉及群和己的關系問題。哲學家也早已注意到人們在社會中生活,用語言、文字交流思想,展開不同意見,觀點的爭論,這也涉及我與他,己與群的關系。因為進行論辯時,認識的主題不僅是我還有對手,而我與對手又都在群體之中,這樣我們的論辯能否達到一致呢?莊子以為不可能也不必求一致。因為百家“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易傳》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肯定了通過爭辯,能夠達到一致的結論。同時馮先生強調,達到一致,被公認也不一定是真理,因為“時移世易”,時間,空間都是在不斷的變化中。馮先生為更詳細的闡明群己之辨,著重論述了“群體意識與個別精神”。群體意識是指社會心理,國民精神,階級意識的。而個別精神指各有個性特點的精神主體。這些精神主體總是一個一個的個體,這些獨特的個體,又不能離開群體而存在,只有通過群體的活動和交流,這些精神個體才能自在而自為的得到發展。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說:“歷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的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于一個人之個性?”馮先生指出這里討論的“共性”與“個性”就是指群體意識和個人心理(個體精神)。梁啟超強調共性離不開個性,個體離不開群體。就像我們每個人因生長環境,受教育不同等而千差萬別但是作為共同的中國人,大家又都具有中國人的國民共性。總之就是“個別精神與群體意識是不能分割的,精神主體有其獨特個性,同時又表現了群體意識。群體意識與個別精神兩者相互聯系,又常是矛盾著的”1馮先生在此鼓勵有個性的精神主體有勇氣和魄力打破舊有的條條框框能提出引領社會的新觀點、新理論,同時強調群體意識形成以后存在積極和消極的雙重作用,可能促進社會的進步也可能在社會變革的時期,阻礙社會的發展。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精神主體要同時代精神相一致,才是真正自由的,要通過個人的自由思考、通過群眾之間的自由討論,使先進的群體意識為更多人掌握,認同,這就需要在討論中自尊同時也尊重別人,這樣夫獲得一致的結論,先進的群體意識就能成為群眾的共同的指導思想。
馮先生在文章中大聲呼吁思想家、理論家要有一種生生不息的活力,要立足現實,面向未來,敢于沖破固定的框框,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要求首先掌握前人的體系化的基本理論,同時需要培養一種自由討論的學風,互相批評,互相切磋,使人們敢于懷疑,敢于創新,敢于自由思考。把以上兩者結合起來,理論才富有生命力。而中國數千年來的民族文化傳統之所以能持續地發展,就在于它體現了一致而百慮的規律,在群己之辨中既能兼容并包,又能自我批判,于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斷的自我完善,持續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