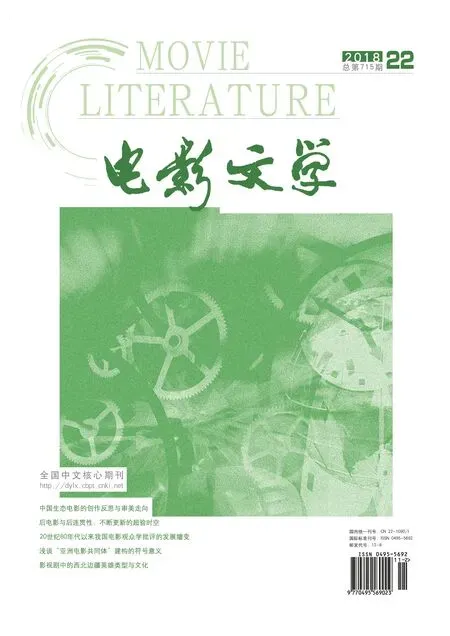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異形》:卡梅隆的憂患意識及影像呈現
嵇麗娜
(信陽農林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要想為已成功的、深入人心的科幻電影拍攝同樣成功,甚至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續集,普遍被認為是一項難以完成的任務,而詹姆斯·卡梅隆執導的《異形2》卻被評論界認為是最偉大的續集電影之一,這應該說是與卡梅隆在電影中表現出來的深刻憂患意識,以及其具體的影像呈現方式緊密相關的。
一、卡梅隆的憂患意識
雷德利·斯科特執導的《異形》(1979)一經問世就引起了轟動,電影被認為是一部教科書級別的驚悚電影,而只要與《銀翼殺手》(1982)、《普羅米修斯》(2012)稍作對比就不難發現,電影有著濃郁的斯科特風格。相比起科幻,斯科特更注重的是一種驚悚、壓抑與陰暗觀感。也正是為了保持這種氛圍,斯科特有意在電影中隱藏了大量信息以營造神秘感,人類為異形攻擊只能解釋為異形有繁殖的本能,以及人類為自己的好奇心所害。而卡梅隆則不然,只要對其《終結者》(1984)和《阿凡達》(2009)等電影有一定的了解,就可知其科幻電影中往往都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人類在其科幻電影中遭遇的苦難,往往與人類對科技的濫用有關。對于西方的物質文明進程,卡梅隆有著更為復雜的立場和更強烈的表達欲望。
這也就導致了《異形2》的風格與前作截然不同,但是其立意更上一層樓。卡梅隆在《異形2》中迅速建立起一個世界觀,干凈利落地交代斯科特所有意回避的問題,如女主人公蕾普莉的經歷、小行星的名字、“公司”的名字等,以便讓觀眾的注意力從異形這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恐怖獵殺者身上,轉移到如人與異形關系、人與人的關系等諸多問題中來。
(一)科技反思
對科技這把雙刃劍的警覺一直是卡梅隆要表達的話語。卡梅隆的科幻電影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多以強勢女性、弱勢形象為主角,思想較為偏向保守主義,對現代科技持戒備態度”,科技往往助長人性中惡的一面,人類發展科技的本意是從中獲益,但最終有可能被科技反噬。在《異形2》中,人類之所以會與異形展開激戰,根本原因就在于人類對LV-426號行星的殖民,也正是太空旅行所必需的休眠,讓蕾普莉在太空中飄蕩了長達五十七年,如果不是被搜救隊發現,蕾普莉就有可能飄向世界盡頭。也正是這五十七年的時間,切斷了蕾普莉與自己原有人生的一切聯系,她最介意的就是親生女兒阿曼達已經去世并且沒有留下子嗣,蕾普莉完全沒能享受到天倫之樂。因此,在醫務人員問蕾普莉是否要幫助入眠時,蕾普莉回答:“不,我已經睡夠了。”但在電影的結尾,蕾普莉還是被放入冬眠艙中,她的人生繼續被科技割裂。
(二)戰爭反思
《異形2》被認為有著強烈的反戰情緒,甚至被指為披著科幻和怪獸外衣的越戰電影。在《異形2》中,跟蕾普莉一起去解救同胞的陸戰隊員開始一直有著輕佻的態度,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敵人有多么厲害,對于異性攻擊下的幸存者小女孩紐特,他們也不屑一顧。而當異形如潮水般涌來,并且利用美軍士兵的身體很快繁育出下一代時他們才驚慌失措,還要憑借蕾普莉駕駛裝甲車前去拯救他們,甚至有的士兵想到了用化學毒氣來殺死異形,并且,在長官指揮不力,士兵精神壓力極大的情況下,美軍一方還出現了卡特·波克的背叛事件。這些都可在越戰中找到對應。正是因為人類屬于侵略的一方,因此士兵們的戰斗意志并不強烈,他們并不愿意陷入充滿敵意的、陌生的小行星上。盡管出于商業利益的考量,最終,人類取得了勝利,但是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卡梅隆無疑是借此來批判人類出于貪欲而發起殖民、戰爭,表示對人類在未來爭奪資源時,有可能又引發戰爭的擔憂。卡梅隆類似的科幻電影還有如明顯指涉了美國和蘇聯“冷戰”的《深淵》(1989)。
(三)人性反思
卡梅隆一向注重揭露人性的陰暗面,這在其非科幻的《泰坦尼克號》等電影中也可見一斑。卡梅隆擔憂,人性的道德層面上的低劣,如虛偽、貪婪、殘忍等,將有可能在科技的助力、戰爭情況的寬容下被放大,置人類于更為危急的境地。例如在《異形2》中,波克可以說是災難的罪魁禍首,正是波克故意誘導行星上的居民去調查異形,他則想將異形的標本帶回公司研究,好開發出能夠獲利的生化武器,而蕾普莉和紐特則被波克選擇作為異形卵的寄生體。可以說,波克其人完全利令智昏,喪心病狂。此外,作為正面人物的蕾普莉同樣有人性上的弱點,她因為曾在仿生人艾許那里遭到襲擊而一直對作為仿生人的主教抱有敵意,她當著主教的面質疑戈爾曼:“你從沒說過船上會有仿生人!為什么不告訴我?”當他人以性別來歧視蕾普莉,以年齡來歧視紐特時,蕾普莉其實也在歧視著他人。仿生人在這里無疑就是弱勢群體的代表。
二、憂患的具象
要在短暫的電影中,傳播出自己的人文意識,尤其是在有前作限制的情況下,卡梅隆無法另起爐灶地設計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讓電影演繹人生百態,在“戴著鐐銬跳舞”的情況下,卡梅隆還是完成了其憂患意識的具象化。
首先,極大地深化了異形的危害,以讓人類命運幾乎陷入絕境。在延續了前作令人發指的異形繁殖方式之外,在異形的種類上,電影中出現了抱臉異形和破胸異形,在分工上,異形除了有類似工蟻式的普通異形,還有類似蟻后的碩大無比的異形女王,在數量上,《異形2》出現的異形成百上千,人類在異形的海洋面前幾乎無法控制局勢,以至于蕾普莉說:“我提議我們離開,從軌道直接核爆整個基地。只有這一個辦法。”如果不是蕾普莉最終操縱起重機將異形女王踢入太空,她也有可能葬身于異形之手。
其次,卡梅隆賦予了幾乎每一個人類角色以鮮明的任務,使具體的角色設置都有清晰的指向,以實現敘事的高效。如反派波克,他代表的就是貪得無厭的資本,以及唯恐天下不亂的好戰者。這一個角色就猶如冰山的海面部分,一旦觀眾注意到冰山在海水下的部分,對全片矛盾沖突的理解就能更上一個臺階。而除波克之外,卡梅隆不再設計人類反派,讓矛盾集中。又如小女孩紐特,她在電影中就象征著人類的愛和希望,她既保留了小女孩的天真,同時又對于艱險的現實有清醒的認識,如既隨身攜帶玩偶,但又在蕾普莉哄她的時候說這不過是一塊塑料。這本身是矛盾的,然而這也正是卡梅隆對上述種種憂患的解決之道,即人類知世故而不世故,以兼具智慧與善良的態度來對待科技、對待他人,世界才有可能更好。
一言以蔽之,《異形2》中,人類與異形之間的較量從頭貫穿至尾,而卡梅隆的批判在整部電影的敘事中也沒有止歇。大量令人或恐懼,或震撼的影像,隱含的是卡梅隆的憂患意識,《異形2》的思想價值也在于此,它所提供的并不僅是一次感官娛樂,更是一次心靈訓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