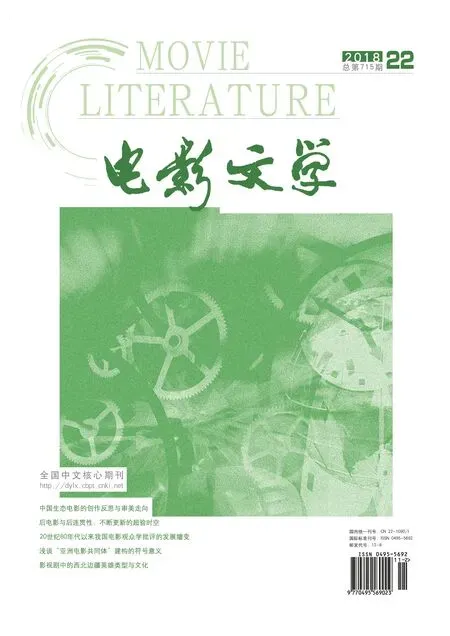卡梅隆電影的科學幻想烏托邦建構
郁舒雯
(江蘇省連云港中醫藥高等職業技術學校,江蘇 連云港 222006)
在世界范圍內的商業電影類型中,科幻電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分支,從早期商業電影工業形成時,不論是市場份額還是創作數量,科幻電影一直都是許多電影創作者開掘的重要領域之一。但是在開掘這個內容豐富的科幻類型電影的領域時,也常常伴隨著許多問題。科幻類型的電影通過商業電影的經濟大潮,依托于大量的科幻文本,雖然逐漸形成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商業電影潮流,但與之相對應的是,由于對票房利益和市場份額的過度追求,科幻電影逐漸消弭了自身獨特的藝術特性和奇絕的創造特性,成了制造噱頭的代名詞。
當然在這種商品化大潮下也有少數的導演和編劇創作了一大批具有藝術性和獨創性的優秀科幻電影作品,這些優秀科幻電影的著作之所以稱為具有典型的藝術特色,從創作方式上來看,也都具有共同的原因。那就是,這些科幻電影文本,都具有相對完整的科學烏托邦建構的敘事空間,這些敘事空間不僅有多元的敘事者參與其中,而且就空間本身而言也具有突出的科學幻想色彩,在這個空間本身的建構過程中就能夠體現出電影導演所獨具的文本空間的建構視角,也是文本敘事所發生的主要話語場域,因此科學幻想烏托邦的空間建構,并不僅是一種虛幻的未來想象,更多地包含著一種結構層面的意義。這種結構關系,更深層次地表現著創作者試圖處理的電影中人物、故事與環境之間的糾結狀態與關系,并且以此來表達自身對于這種狀態的理解與想象。
卡梅隆電影的表達,即使是在市場回報與藝術價值兩個側面都屬于優秀的科幻電影中,也顯得非常特殊。他不僅將目光放置在奇特卻又宏大的烏托邦空間中,而且敏銳地捕捉到了宏闊的歷史空間與狹窄的私人空間之間的復雜聯系,因此在他的表達中,每一種意識存在,包括人、外星人甚至是機器人,都處在這種復雜空間的籠罩之下,并且成為試圖掙脫這種空間,從而與這些空間產生互動的意識存在物。卡梅隆從網絡化的人與社會的相處形態與時間、空間倒錯產生的技術恐慌與人性對于科學的內涵重新建構兩種不同的角度切入電影文本對于空間的建構中,進而使電影文本中的烏托邦世界既能夠從內容上成為電影敘事的場景,也能夠從結構上成為卡梅隆對現實社會的觀照與想象。
一、意識網絡化空間的初步建立
科學幻想烏托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文本創作者在一定條件下所構建起的一個獨特的幻想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有屬于幻想的社會規則和世界特性。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特殊的規則與特性中,有關人的社會層面的構建在內容上要遠遠多于自然屬性。當然與此同時,不論這種幻想何其瑰麗和動人,它都是源于創作者對于現實社會的參照和思考所得出的具有一定規律屬性的社會形態。也就是說,在這種社會樣態的建構過程中實際上包含著創作者本身對于社會關系的思考,而這種幻想社會更加傾向于由當下意識形態環境所衍生出的烏托邦社會,并且在這個烏托邦社會,當下意識形態所形成的矛盾會被進一步激化,從而以一種具有豐富象征意味的手段得到解決。
在卡梅隆的電影文本中,他曾經塑造了一個具有優美而且神秘的自然環境的星球,在這個即將成為他系列電影,并且成為當年沖擊奧斯卡電影多項獎項的電影文本中,卡梅隆構造了一個奇特的幻想空間,這個空間中,類似人類的外星意識存在物與本土的其他生物可以進行互動,這種互動不僅停留在對于其他生物進行馴養,而是可以更進一步地通過某種媒介與進化出語言和社會行為的其他生物進行意識層面的互動,這種互動實際上就是一種對于烏托邦世界的理想化想象。如果說對于創作者而言,烏托邦的建構是一種理想化世界的重新崛起,那么對于卡梅隆而言,這種理想化的世界就更進一步成了一種現實世界的投影,與這種投影內部概念的置換。通過他對于潘多拉星球的初步設置,不難發現,這種生物之間的意識層面互動實際上是一種意識網絡,這種網絡將一個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互相聯結,呈現出了一種多元中心的社會形態,每一種生命都擁有溝通與表達的權利和能力,不同生命個體之間達成了一致,并且在此基礎上平等地互相尊重。如果從生態觀點的角度來理解的話,卡梅隆實際上建立起了一個多元并且平等的生命空間。但是從更深層次的角度上看,卡梅隆同時還從人與社會關系的角度出發,發掘了一個更為富有深意的空間意象。在這個空間意象中,社會的構成主體跨越了生命的個體特征,在平等地尊重個體生命的前提下,與星球和社會本身構成了一個互動性的整體,并且在這個整體內部實現了基本無障礙的意識傳遞,這實際上才是卡梅隆對于網絡化社會的最終構想,在這個網絡化社會中,每一個結點由星球的個體生命構成,而網絡的連接則是這些個體生命的互動。
二、時空關系對于網絡化空間的進一步塑造
卡梅隆所構建的網絡化空間,實際上是以網絡連接這一科技進步的成果作為基調的。而他所構建起來的網絡化世界實際上是一個逐漸前進的過程。從他早期的作品《終結者》的敘事邏輯上來看,卡梅隆所營造起來的未來世界也是通過網絡將人類連接起來的,所不同的是在這個未來的科幻世界當中,網絡并沒有對人本身產生社會層面的建構作用,不僅如此,在這個系列的電影文本中,網絡還扮演著科學技術進化的最終形態,而這一最終形態實際上展現出來的是一個科技烏托邦的未來社會樣態。如果我們對卡梅隆早期的《終結者》系列與《阿凡達》分類來看的話,那么兩種電影文本所構建起來的網絡化社會在內里上有著非常明顯的沖突。首先,《終結者》試圖表現的是人類在發明強大的科技武器之后,最終被科技反噬的烏托邦世界。其次,《終結者》所建構的網絡化烏托邦世界是科技高度發達之后的產物,而《阿凡達》則是外星球上的原始文明以某種神秘的方式達成的物種與生命之間的意識互動。這也是兩者最大的區別,在電影的不同時空視域之下,卡梅隆對科幻的烏托邦想象也大有不同,由特殊的時空條件所影響的烏托邦世界構成了卡梅隆電影最重要的核心。
從電影文本展示出來的時空關系上來看,這兩部電影的時間基點都是處于未來的烏托邦世界,也就是說這兩者空間都是作用于時間之后,形成的網絡化世界,但是兩者建構起來的空間有所不同,《終結者》中的網絡化空間并沒有真正地將人和社會聯結在一起,而是由機器之間形成了排斥人類社會的網絡機制,與其說這種情況是在表現科學的理性對于人類的感性無法適應,最終導致機器的反叛,不如說是創作者所希冀出現的包含著社會層面的意識互動,進而呈現出來更為深刻的平等關系。如果說卡梅隆對于人類社會的未來形態最終處于一種悲觀的理解,那么對于時間與空間雙重隱喻后的烏托邦建構,則是寄予著對于人類社會理想社會樣態的一種希望。從內在邏輯上來看,《阿凡達》是一種最為原始和神秘的網絡聯結形態,在社會層面上實現了真正的平等,從時空角度上來說,時間對于這個網絡具有長久持續的意義,空間則是一個有機的互動整體,這是這個網絡社會的最重要形式;而相比較而言,《終結者》則是時間的波動非常明顯,時間對于這個網絡社會更加脆弱和模糊,而空間上則是冰冷且無序的,這是在表明這個網絡社會拒絕了自發的社會關系,也就注定成了需要被人類反對的社會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