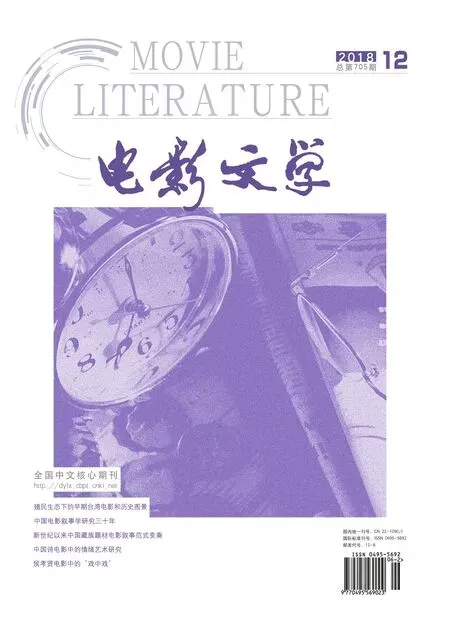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生活秀》:從文字到光影的嬗變
張亦元
(西安外國語大學 藝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8)
文學到電影的轉變,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再創作,它滲透著導演在個人思想和藝術趣味上的強烈主觀性,以及體現著客觀的時代影響。自稱是“第五代半”導演的霍建起的《生活秀》,改編自新寫實主義作家池莉的同名小說。而無論是霍建起抑或池莉,都是在各自領域中具有獨特美學特征、個人風格強烈的創作者。《生活秀》從文字轉換為光影的過程中,是否秉承了兩位主創的創作理念,又體現了霍建起對小說怎樣的藝術化處理方式,都是值得探討的。
一、性別凝視機制下的《生活秀》
正如讓-納波尼等人在《電影手冊》中指出的,所有電影都是被意識形態加工后的產物。盡管這種加工有時是不自覺的。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解讀《生活秀》的改編,不難發現從文字到光影的嬗變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從女性視角(池莉)到男性視角(霍建起)的嬗變過程。
學者勞拉·穆爾維認為:“在一個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為主動的/男性和被動的/女性。起決定作用的男性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風格化的女性的形體上。”霍建起本人盡管并非一個男性秩序的擁護者,也無意于將來雙揚的外貌編碼為某種具有強烈色情感染力的被展示對象。但他依然是以一個男性導演的身份來對來雙揚這個角色進行觀看和重塑的。在霍建起的男性視角下,來雙揚成為另一個和池莉女性視角下略有不同的角色。
在原著小說的開頭、中間和結尾,都是來雙揚對男性的觀看,并且有著自己的貶抑態度:開頭嘲笑前來占便宜的兄長來雙元,中間則是發現了卓雄洲西裝革履后不堪的一面,最終則是嘲笑給自己畫像的畫家。而在電影中,男性觀看來雙揚的視角則無處不在。以來金多爾為例,電影始于來金多爾獨自投奔來雙揚,以多爾默默注視大姑給爸爸打電話開始了對來雙揚的觀看。隨后電影又加入了兩個情節:一是多爾看到了來雙揚被自己的母親砸店以后的委屈哭泣;二是因為給多爾的炒面做得不好,來雙揚準備去罵廚師,結果發現老周在看自己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從這種改編我們不難看出,來雙揚這個角色相對于原著而言顯得更為無助,更為困境重重,更顧忌男性對她的眼光,她這種困境一方面來自電影敘事矛盾沖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她被霍建起寄予了更多的同情,當池莉幾乎是以一種零度敘事的態度陳述故事時,霍建起卻從男性的角度為來雙揚編織起了一個更為惡劣的生存環境,讓來雙揚顯得更加弱勢和無奈。相對于原著中女性主體強烈的情感表達而言,電影在主觀(導演本人的男性視角)和客觀(影像敘事的特征)因素的限制下,淡化了來雙揚的心理表現,弱化了來雙揚的形象,來雙揚成為一個雜糅了男性情欲、同情等心態的“景觀”。
二、主題的弱化
池莉小說擅長在簡單中體現豐富,在卑下中體現崇高。在《生活秀》中,池莉想表達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除了在來雙揚、來雙瑗和九妹等人身上體現的作者的女性主義思考之外,還有來崇德夫婦、來雙元夫婦等家庭體現出來的愛情婚姻問題,社會精英和平民之間的矛盾,乃至武漢的“漢味”書寫等。而電影的篇幅是有限的,且在改編之際,還要考慮到影像的表達方式以及電影的受眾和小說讀者之間的差異問題。因此,霍建起選擇了集中表現女性的堅強以及圍繞女性的親情愛情主題,而對于池莉糅入字里行間的種種煩惱和無奈則選擇了舍棄和淡化。
這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來雙瑗這個角色在電影中被完全刪去了,而隨著來雙瑗的缺席,導致來雙瑗主導的“整頓吉慶街”以及來雙瑗和來雙揚的爭吵這一重要內容在電影中缺位。而姐妹倆的矛盾對立其實代表了池莉安排的一個重要主題,即社會精英和底層小市民這兩個階層之間,乃至這兩種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來雙揚靠著成為在吉慶街上第一個“無證占道經營”者而撫養長大了來雙瑗和來雙久,在弟妹成年以后,來雙揚還依靠自己在吉慶街的鴨頸生意照顧著他們的人生:為來雙瑗交單位的管理費,為吸毒的來雙久開了一家“九九飯店”。而吉慶街也正是在來雙揚的帶頭下成為現在的小吃一條街。但是知識分子來雙瑗卻在躋身進精英階層后對養育她的底層市民文化進行了反噬:她以電視臺記者的身份曝光了吉慶街的各種隱患、噪聲問題,推動政府取締吉慶街,也不切實際地希望來雙揚改變自己這種晝伏夜出做生意的生活狀態。
無論是在外表,抑或是思想上,姐妹二人是以一種互相映襯的方式出現的。最終來雙瑗取締吉慶街失敗的結局代表了池莉對市民文化的肯定和對精英文化的嘲弄。而電影則將這種此消彼長的文化對立弱化為來雙揚女性奮斗史中的一部分,讓老周(卓雄洲)代表了精英文化,賦予了老周一個欲拆掉吉慶街的開發商的身份。這樣一來,來雙揚和老周之間的關系比小說中更富戲劇性,但是二人的矛盾更多的只代表了來雙揚個人奮斗史上的一次挫敗,而與文化沖突并無關系。相對于原著中,來雙瑗也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不應該被完全否定的對象,并且和妹妹關系的惡劣也給來雙揚帶來痛苦,電影中的老周則無法得到觀眾的移情,他和來雙揚最終沒能攜手對來雙揚的傷害也是短暫的、偶然的,電影的結尾暗示了來雙揚終將在她的小酒館繼續等待屬于她的真情。
三、人物形象的美化
如果對霍建起的其他電影,如《贏家》《那山那人那狗》等稍作了解就不難發現,霍建起是一位熱衷在電影中講述平淡故事,并在平淡故事里藏入一顆仁愛之心的導演。因此霍建起的影片敘事往往最終落腳于平凡、樸實而又不失美好的生活這一點。相對于池莉在《生活秀》乃至《不談愛情》等小說中對愛情、人生的悲觀看法,霍建起則盡可能地展現給觀眾生活中具有亮色的一面。在整部《生活秀》中,觀眾看到的是來雙揚的多情、美麗和在煩惱人生前的堅強,來雙揚作為一道“風景線”般的閃亮,讓觀眾有可能將其作為個例而忽視她遭遇的普遍性。
在描畫這道“風景線”時,對人物形象的美化也就成為必然。除了保留了原著中來雙揚的風姿綽約等女性魅力外,原著中來雙揚的錯誤也在電影中被削弱。例如,來雙揚為在戒毒所的來雙久偷偷運送毒品的犯罪行為,在電影中被削減。又如在原著中,來雙揚“出賣”九妹給房管所張所長做兒媳換取了房產轉移到自己名下,九妹的命運在她拍婚紗照,來雙揚掛斷了她的電話后就結束了,池莉并不戳破九妹婚后的痛苦,反而留給讀者極大的想象空間。而在電影中,來雙揚還在阿妹(九妹)結婚以后去看望阿妹,在發現阿妹手腕上的傷痕以后,來雙揚對自己的決定表現出了后悔。這種后悔是不可能存在于原著中早已放棄精神層面上的愛情,自私且冷血的來雙揚身上的,但又是電影中這個不失人情味的,依然對老周有著“喜歡誰就拼命要把自己嫁給誰”的桃花源幻想的來雙揚身上必然存在的。
從《生活秀》的改編中我們不難發現,霍建起從男性視角出發,對原著進行了主觀創造,在歌頌女性強勁生命力的同時,也出于對女性的情感而淡化了其生活中的矛盾沖突,并美化了人物形象,敘事主題也更為集中、緊湊。可以說,《生活秀》從文字到光影的嬗變盡管有得有失,但它代表了一種更獨立、自由和開放的電影創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