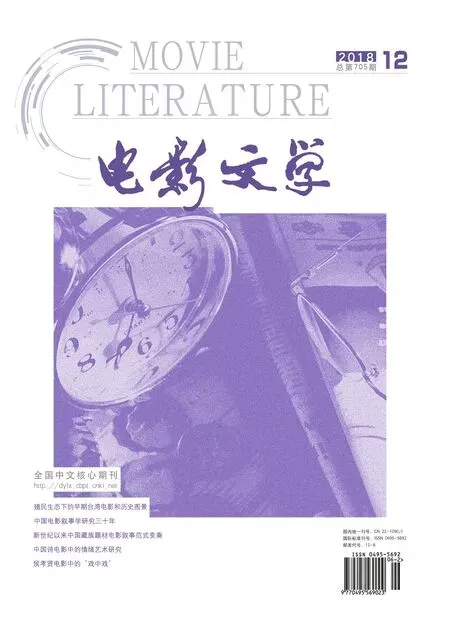埃德加·賴特與英式幽默
賈鴻麗
(內(nèi)蒙古民族大學(xué) 大學(xué)外語(yǔ)教學(xué)部,內(nèi)蒙古 通遼 028000)
英式幽默被認(rèn)為是對(duì)某種語(yǔ)言和行動(dòng)的概括,這種語(yǔ)言和行動(dòng)往往具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劇效果,且誕生于英國(guó)或深受其文化影響的前殖民地。在好萊塢在喜劇領(lǐng)域具有強(qiáng)大的統(tǒng)治力的當(dāng)下,英式幽默往往被人們用以對(duì)標(biāo)好萊塢的美式幽默,同出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二者被認(rèn)為代表了西方幽默文化中的兩種風(fēng)格。
英國(guó)新銳導(dǎo)演埃德加·賴特一貫以幽默著稱,其最初以《屋事生非》等連續(xù)劇在英國(guó)贏得了家喻戶曉的地位,在踏入影壇后,他在《荒野大指客》(1995)等電影中繼續(xù)用英式幽默來俘獲世界萬(wàn)千影迷。即使是在其進(jìn)入好萊塢發(fā)展,與漫威影業(yè)合作后,賴特也沒有放棄個(gè)人獨(dú)特的幽默思路與實(shí)踐,并沒有如人們所擔(dān)心的,在美式審美趣味或美式幽默之前失去自我。尤其是其“鮮血與冰淇淋三部曲”,更是成為在“憨豆先生”和蓋·里奇之外,人們討論英式幽默時(shí)必然提及的范例。一言以蔽之,英式幽默幾乎成為賴特的重要標(biāo)簽之一。
一、情景與語(yǔ)言的錯(cuò)位
英式幽默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制造情景或語(yǔ)言的錯(cuò)位,如將簡(jiǎn)單的問題復(fù)雜化,或?qū)?fù)雜的問題簡(jiǎn)單化,越是嚴(yán)肅、重要的東西,越是以不嚴(yán)肅的態(tài)度來談?wù)撍脖环Q之為“板著臉說笑話”,或是事與愿違、歪打正著等。
以賴特的《極盜車神》(2017)為例,在賴特的電影中,《極盜車神》是為數(shù)不多的一部非喜劇電影,賴特在其中張揚(yáng)的是自己運(yùn)用刺激勁爆的配樂,以及營(yíng)造令人熱血沸騰的搶劫飆車槍戰(zhàn)場(chǎng)面的一面。但賴特的英式幽默依然在其中俯拾皆是,也正是種種英式幽默,讓電影顯得劍走偏鋒,不至于被混淆于美國(guó)海量的狂野炫酷動(dòng)作片之中。在電影中,男主人公寶寶為亞特蘭大黑幫老大道格開車,道格每次找到不同的人來進(jìn)行搶劫,事成之后所有人坐寶寶的車撤離。寶寶以此來還他欠道格的債。在債務(wù)還清之后,本來以為可以浪子回頭的寶寶又被道格以打斷腿和家人性命威脅,不得不繼續(xù)跟著道格做搶劫的勾當(dāng)。這一次道格選擇了郵局為打劫的目標(biāo),讓寶寶以排隊(duì)買郵票為由先去察看攝像頭數(shù)目,柜臺(tái)數(shù)目,員工與顧客的數(shù)目,以及有沒有守衛(wèi),守衛(wèi)有沒有槍等。為了減輕嫌疑,道格還讓寶寶帶上自己只有幾歲的兒子一起進(jìn)郵局。然而郵局十分冷清,這讓進(jìn)去以后默默抬頭看環(huán)境的寶寶顯得十分突兀。此時(shí)道格一直在打游戲機(jī)的兒子悄悄告訴寶寶:沒有防彈玻璃,一個(gè)武裝守衛(wèi),十個(gè)攝像頭,八個(gè)柜臺(tái),兩個(gè)柜臺(tái)有操作,十一位客人和四位員工,說完繼續(xù)低頭打游戲。已經(jīng)有過多次犯罪經(jīng)歷的寶寶此時(shí)還不如一個(gè)看起來純真可愛的男童,偵察話語(yǔ)從孩童口中輕描淡寫、輕車熟路地說出,這就是一種情景和語(yǔ)言的錯(cuò)位,幽默效果也自然顯現(xiàn)出來。
而值得一提的是,通常情況下,英式幽默中演員的肢體語(yǔ)言并不夸張,甚至一板一眼,具有紳士風(fēng)度,卻在一板一眼中又意外頻出、跌跌撞撞,這反而能讓觀眾會(huì)心一笑,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溫文爾雅的“憨豆先生”。但賴特則在這方面進(jìn)行著突破。最為典型的例子便是根據(jù)漫畫《斯科特》改編而成的,極具游戲意味的《歪小子斯科特對(duì)抗全世界》(2010)。在電影中,斯科特為了追求到小花,需要擊敗小花之前的七個(gè)邪惡前男友。于是斯科特就如同打闖關(guān)格斗游戲一般莫名其妙地陷入各種打斗之中,并且擊敗每個(gè)人后還可以拾取金幣。人物的打斗動(dòng)作幾乎全部來自紅白機(jī)任天堂小霸王中的游戲,具有強(qiáng)烈的超現(xiàn)實(shí)感,而人物行為和畫面則極為夸張,如馬修突如其來的印度寶萊塢舞蹈,斯科特和洛克希打斗時(shí)的火焰掌和煙霧彈等,讓整部電影輕松歡快,讓人眼花繚亂。賴特在繼承了英式幽默不以低俗、惡心作為笑料的傳統(tǒng)時(shí),又陷入借鑒了昆汀·塔倫蒂諾等美國(guó)導(dǎo)演的互文、解構(gòu)等后現(xiàn)代主義手法來直擊觀眾的笑穴。
二、“傻子干傻事”的小人物
“英國(guó)式幽默似乎就是自我貶低,以自負(fù)為大敵,其最終目的就是自嘲,嘲笑自己的缺點(diǎn)、失敗、窘境乃至自己的理想。用英國(guó)喜劇演員查理·西格森的話來說,英式幽默與美式幽默的區(qū)別之處在于:‘英國(guó)人喜歡看傻子干傻事,而美國(guó)人則喜歡看聰明人干聰明事。’”可以確定的是,幽默的形成與具體的國(guó)情、特定時(shí)代下人們的審美心理等息息相關(guān)。人們基于英美的種種差異來命名和區(qū)分兩類幽默并非是毫無道理的,英美人不同的制造笑料的方式,其實(shí)反映了兩國(guó)人在潛在心理、愿望和關(guān)注點(diǎn),以及對(duì)本民族自我定位等方面的區(qū)別。早期來到北美的移民面臨九死一生的艱苦的開拓生活,夸張、直白、外放型的美式幽默代表了美國(guó)人在這種惡劣條件中生存下來,并迅速崛起的樂觀心理。而英式幽默則不然。英國(guó)的歷史和地理因素造就了其國(guó)民給他人的古老、刻板、保守內(nèi)斂、沉默寡言的刻板印象。這也使得其幽默是內(nèi)斂的、點(diǎn)到為止的,相對(duì)于給予受眾單純的喜悅,英式幽默更五味雜陳,甚至被認(rèn)為有哭笑不得式的意味。
在英式幽默中,“傻子干傻事”的往往便是小人物,人微言輕,或有著種種無傷大雅缺陷的小人物的自嘲,實(shí)際上也是為觀眾代言的一種自嘲。觀眾極能體會(huì)到小人物所面對(duì)的缺點(diǎn)、失敗、窘境以及理想遙不可及時(shí)的復(fù)雜心態(tài),人對(duì)自己備感無奈而又無法全盤否定,于是索性承認(rèn)(或?qū)а荽涑姓J(rèn))其“傻”,呆板或怪異、與他人格格不入以贏得觀眾的共情。例如,在《熱血警探》(2007)中,主人公尼古拉斯·安琪原本是倫敦的巡警,結(jié)果因?yàn)樽约汗ぷ魈^出色和認(rèn)真而遭到了同僚的排擠,被調(diào)動(dòng)到一個(gè)偏僻的小鎮(zhèn)當(dāng)警察。小鎮(zhèn)與世隔絕,據(jù)說已經(jīng)幾十年沒有犯罪記錄。然而就在尼古拉斯去到小鎮(zhèn)的第一天,就發(fā)現(xiàn)有未成年人飲酒,有人酒后駕駛,還有人當(dāng)街撒尿等。尼古拉斯于是“小題大做”地將他們都抓了起來。結(jié)果尼古拉斯帶去警察局關(guān)押的那位酒后駕駛之人正是小鎮(zhèn)警察局局長(zhǎng)的兒子——同為警察的丹尼·巴特曼。在尼古拉斯和丹尼不打不相識(shí)之后,一件件看似意外,卻讓尼古拉斯懷疑是謀殺的死亡事件接二連三地發(fā)生,然而小鎮(zhèn)所有人都眾口一詞地表示這些就是意外,除了丹尼沒一個(gè)人搭理要查案的尼古拉斯,讓尼古拉斯陷入被動(dòng)中。然而敬業(yè)的他越挫越勇,索性一個(gè)人去直面罪惡。
尼古拉斯作為一個(gè)平凡而較真的警察,在倫敦和小鎮(zhèn)都不斷碰壁和吃虧,被別人惡搞,被女友嫌棄,這是賴特對(duì)他的一種貶抑,也是賴特對(duì)觀眾有可能遇到的困境的夸大。但這些困難不影響尼古拉斯一根筋地將案查到底,為了不孤軍奮戰(zhàn),他甚至在超市買了許多噴霧分給青少年讓他們幫忙,而他之前一直幫鎮(zhèn)民抓的走失的天鵝也加入阻止罪犯的隊(duì)伍中來,這些“戰(zhàn)友”達(dá)到了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尼古拉斯的遭遇,正是一種英式幽默中的自嘲,是對(duì)自我和世界的不完美進(jìn)行承認(rèn)和真誠(chéng)面對(duì)的體現(xiàn)。
三、英式幽默與黑色幽默的調(diào)和
如前所述,自嘲是英式幽默的關(guān)鍵。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意識(shí)到,英國(guó)在當(dāng)代的衰落也使得這種不旨在讓人開懷大笑,而是讓人搖頭苦笑的英式幽默繼續(xù)風(fēng)行。《金融時(shí)報(bào)》曾經(jīng)就英式幽默進(jìn)行研究,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的大量英式幽默劇都為作者納入研究的范圍內(nèi),最終得出了英式幽默見證英國(guó)衰落的結(jié)論。文章認(rèn)為英式幽默很大程度上是國(guó)家走向衰落的產(chǎn)物,面對(duì)曾經(jīng)日不落帝國(guó)的沒落,英國(guó)人選擇了自嘲。
而也正是這種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聯(lián),讓英式幽默與本來誕生于美國(guó)本土的黑色幽默有了結(jié)合的可能。黑色幽默出現(xiàn)于20世紀(jì)60年代的美國(guó)文壇,約瑟夫·海勒等作家用黑色幽默實(shí)現(xiàn)了用喜劇表達(dá)悲劇內(nèi)容的目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荒謬、畸形和變態(tài),被以一種滑稽的方式凸顯出來,受眾在笑聲過后,收獲的是恐懼和絕望。這也是黑色幽默又被戲稱為“絞刑架下的幽默”的原因。而在當(dāng)代,荒誕的、與個(gè)體不相協(xié)調(diào)的現(xiàn)實(shí)生活顯然并不僅僅存在于美國(guó)。英國(guó)同樣有著環(huán)境與自我之間的矛盾,于是如蓋·里奇等英國(guó)電影人就曾試圖塑造乖僻的人物,如《兩桿大煙槍》(1998)中的艾德和他的朋友們等,在這些人物的經(jīng)歷中,社會(huì)的殘酷、無序、壓抑的一面被折射出來。
而自稱為蓋·離奇影迷的賴特也是一位將英式幽默與黑色幽默進(jìn)行嫁接的高手,在“鮮血與冰淇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世界盡頭》(2013)中,一事無成、酒精成癮甚至還罹患了精神病的蓋瑞·金約上20年前的舊友奧利弗等一干人,回到家鄉(xiāng)紐頓哈芬完成一個(gè)頗為荒唐的“啤酒馬拉松”,就在觀眾誤以為這是一個(gè)“老男孩”尋找青春和友情的故事時(shí),賴特讓情節(jié)急轉(zhuǎn)直下,觀眾猝不及防地看到了外星人和機(jī)器人的出現(xiàn)。原來大量的人都已經(jīng)被外星人進(jìn)行了置換,他們擁有更完美的外殼,但失去了個(gè)體的自由而被外星人以秩序的名義統(tǒng)治,原來的肉身變成了肥料。蓋瑞這才意識(shí)到為何一路上的酒吧都跟星巴克似的變得幾乎一模一樣。在被機(jī)器人包圍的情況下,只有始終追隨自己內(nèi)心,沒心沒肺揮霍人生的蓋瑞堅(jiān)決拒絕被統(tǒng)治,用自己膽大妄為的胡言亂語(yǔ)氣跑了外星人,而人類也重返農(nóng)耕社會(huì),為擁抱自由付出了代價(jià)。蓋瑞的態(tài)度實(shí)質(zhì)上也是賴特對(duì)于社會(huì)壓抑個(gè)性、扼殺個(gè)體自由的反抗情緒的體現(xiàn)。
而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由于時(shí)代環(huán)境的變化以及個(gè)人藝術(shù)取向等的區(qū)別,在這種嫁接中,賴特大大地淡化了“黑色”,而保留了“幽默”的底色,盡管觀眾可以明確地感覺到賴特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挖苦,但是觀眾并不因此而感到絕望痛苦,主人公的命運(yùn)雖然有一定的波折,但并不陷于無望的絕境,這與海勒時(shí)代黑色幽默中無處不滲透著令人揪心的苦澀大不相同。例如,在《僵尸肖恩》(2004)中,賴特的幽默體現(xiàn)在行尸走肉一樣麻木生活的活人實(shí)際上和僵尸沒有什么區(qū)別,肖恩等人日復(fù)一日生活得渾渾噩噩,以至于一開始都沒發(fā)現(xiàn)身邊爆發(fā)了僵尸之災(zāi)。這是賴特對(duì)于資本主義社會(huì)異化人的諷刺和嘲弄。但賴特?zé)o意于讓觀眾感到壓抑和不安。在電影的結(jié)尾,僵尸和人類實(shí)現(xiàn)了和平相處,僵尸可以去做某些重復(fù)的工作而毫不厭煩,可以上娛樂節(jié)目,而肖恩變成了僵尸的摯友艾德則還和肖恩住在一起,還是每天宅在房間里打游戲。麻木的生活本身是值得批判的,但既然突如其來的災(zāi)難也無力改變這一切,不如就繼續(xù)這樣生活。電影中固然有荒誕和警醒的一面,但觀眾自始至終都得以保持休閑、歡快的心態(tài)。
當(dāng)我們探討埃德加·賴特時(shí),無法回避英式幽默,而反過來,當(dāng)我們總結(jié)英國(guó)電影中的英式幽默時(shí),賴特也成為一個(gè)繞不過去的名字。可以說,英式幽默在賴特的電影中無處不在,成為賴特作品,甚至是賴特對(duì)世界進(jìn)行重新闡釋的一部分,而非賴特用以單純吸引觀眾的噱頭,而賴特在蓋·里奇之后也豐富了英式幽默,使英式幽默不曾因淺顯易懂、受眾更廣的美式幽默大行其道而遠(yuǎn)離人們的視野。二者是一種互相成就的關(guān)系。人們已經(jīng)承認(rèn),幽默是人類對(duì)抗世間疾苦的重要武器,在處處存在對(duì)立的后現(xiàn)代時(shí)代,人們更是需要幽默的眼光來審視社會(huì)問題。賴特在英式幽默上的藝術(shù)嘗試無疑是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