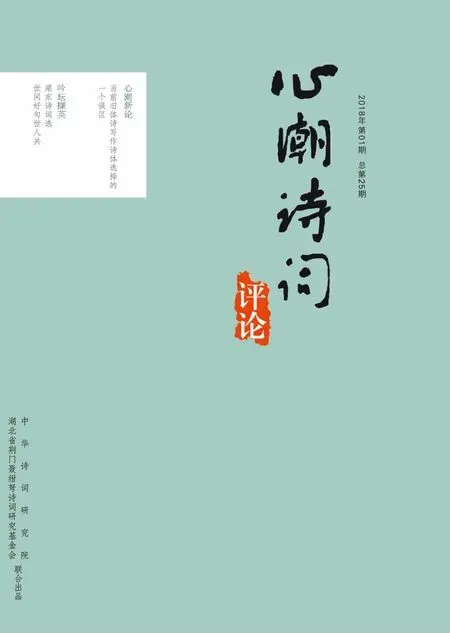當前舊體詩寫作詩體選擇的一個誤區
陳友康
21世紀以來,舊體詩寫作呈現全面復興態勢,作者隊伍龐大,文本數量巨大,學術性研討活躍,理論話語建構加強,社會影響力提升,取得可喜成績,為雅化社會風氣、推動現代漢詩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舊體詩逐漸從文學邊緣重返詩歌中心。新文學觀文學史表述中的“舊文學要么在五四的高歌猛進中潰不成軍,要么將它在現代文學的存在視作是舊文學的負隅頑抗”的局面已經根本改變,舊體詩與新詩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局面已然不可逆轉。隨著中國文化自覺和自信的強化,舊體詩將伴隨中國崛起走向進一步繁榮。
當代舊體詩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妥善解決這些問題,才能健康前行,創造出真正的詩歌新時代。本文要討論的是詩體選擇問題。舊體詩本來有古、近二體,各有所長。近體詩成立以后,古體詩和近體詩并行發展,均有名篇佳作。而當前的舊體詩寫作,在詩體選擇上卻出現偏誤:重近體詩,輕古體詩。許多人以為舊體詩就是近體詩,熱衷寫五七言律絕;報刊發表、網絡傳播的舊體詩大量是格律詩,近體詩難覓蹤跡;一些詩詞賽及征詩活動或明確要求詩體為格律詩,完全把古體詩排斥在外,或獲獎作品只有近體詩。這會導致舊體詩寫作路徑的“窄化”,不利于舊體詩繁榮。故撰此文略陳己見。
一、格律雙刃劍下的近體詩之優勢和劣勢
近體詩即格律詩,簡稱律詩或律體,有狹義律詩和絕句兩類,主要包括五律、五絕、七律、七絕和排律。排律是五律、七律的延展。以五言排律為多,杜甫詩中屢見佳作,元稹白居易唱和,動輒百韻,其后代有作者,終成滔滔大河。“若七言,則作者絕少矣”。歷史上有詩人作六言絕句,但數量更少,“不過詩人賦詠之馀耳”,一般讀者知之不多。
近體詩成立是中國詩史上的大事件。近體詩肇端于齊梁之永明體,在唐代成熟。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等為近體詩之定型發揮關鍵作用,因此稱“沈宋體”。近體詩之誕生,是中國詩歌演變一大關鍵。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序》指出:“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后,文體之變極焉。”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說:“五言律體,兆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拗澀,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于前;王孟高岑,并馳于后。新制迭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革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他們對近體詩成立的意義作了高度評價。自此以后,近體詩與古體詩就成為舊體詩的兩大體式,分鑣競騁,共同創造古詩之輝煌。
近體詩是古典詩歌中最精美的詩體,即陳寅恪《四聲三問》所謂“中國之美化文”者。其優長,一是具有強烈的形式美。它通過特定的句式、音節、對仗、平仄、黏連、用韻等藝術手段創造出韻律、節奏、均衡、變化、和諧等美感因素,釀造詩的氛圍,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一點決定了近體詩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藝術魅力,有獨立于內容之外的形式美,只要嚴格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即使是十分平常的內容裝入舊體的形式便獲得了詩的意味,就會像一首詩。這就為作詩提供了一個方便法門。二是寓變化于統一,固定的格式可以因應無限的對象。三是凝練精悍,便于記誦。是以廣受公眾歡迎,公眾瑯瑯成誦的詩大量是近體詩。因此,近體詩一旦成立,“百世攸宗”(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古體上)“世之文士,無人不作詩,無詩不七律”(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四),滔滔不絕,蔚為大觀。
但格律是雙刃劍,它帶來優勢的同時隱含劣勢。近體詩的劣勢主要是篇幅短小,騰挪空間有限,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的張力均受制約。一是模式化,容易造成詩歌內容單調,形式單一,結構雷同。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說:“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詩,前起后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他說的是五律的結構,“通例”實際上就是模式化;二是敘事性差,過程性、現場感、細節感被削弱,容易流于空洞;三是易于造成語言老化、意象固化和典故堆砌。由于受字數、句數、音律限制,近體詩書寫一個對象很難具體而微,只能大而化之,眾人趨向一致,于是意涵、意境、意象、詞匯、用韻、典故的趨同就難以避免。特別是同一個書寫對象,一些被反復歌詠的主題或事相,問題尤為突出。前者如山水名勝、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詠史詩)等;后者如詠物詩、節日詩等。排律句數不受限,但要滿足對仗,常常出現典故的堆垛。因此,近體詩把握不好,很容易陷入詩歌寫作的“套板反應”。
朱光潛《咬文嚼字》討論語言使用的套板反應說:“習慣老是喜歡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誘性最大,一人走過人人就都跟著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濫。”“這就是近代文藝心理學家所說的‘套板反應’(stock response)。一個人的心理習慣如果老是傾向于套板反應,他就根本與文藝無緣。因為就作者說,‘套板反應’和創造的動機是仇敵;就讀者說,它引不起新鮮而真切的情趣。一個作者在用字用詞上離不掉‘套板反應’,在運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個人生態度方面也就難免如此。不過習慣力量的深度常非我們的意料所及。沿著習慣去做總比新創更省力,人生來有惰性,常使我們不知不覺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應’里去。”詩詞寫作也是如此。
杜甫是最偉大的近體詩人,也許正是鑒于近體詩篇幅短小、格式固定造成的窘迫,他創為七律、七絕聯章,既保持七言律絕形式之精美,又拓展表現能力。所作《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夔州歌十絕句》《詠懷古跡五首》《秋興八首》等,均為近體聯章佳制。這是近體詩揚長避短的有效途徑。
由于近體詩確實存在窘迫之處,有些論家認為近體不如古體之高遠。唐代日僧遍照金剛《文境秘府論》引皎然《詩議》云:“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明人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律詩》謂:“大抵律詩拘于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此為持平之論。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近體律詩”條亦有類似的意見。
雖然杰出的詩人總能“戴著鐐銬跳舞”,以不變應萬變,用近體寫出佳作,但大量雷同之作的存在也是不爭的事實。
二、古體詩之自由度、包容量和表達張力
古體詩簡稱古詩,包含近體詩以外的所有詩體,有四言詩、騷體詩(楚辭體)、樂府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樂府歌行、近體歌行、雜言詩、雜體詩等。
相較近體詩而言,古體詩的最大特點是自由。篇幅可長可短,句式伸縮自如,結構靈活,用韻可以變換,不受平仄拘束。它可視為古代的自由詩,只是不像新詩那樣自由得漫無邊際。自由帶來表現力的伸張,它的自由度、包容量優于近體詩。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古體中論七古云:“七言古茍天才雄贍,而能刻意前規,則縱橫排蕩,滔滔莽莽,千言不窮,點筆力就,無不可者。”內編卷三古體下論歌行云:“古詩窘于格調,近體束于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辟,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于古詩而盡于歌行。”長篇五古亦有這些特點,如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等都是“縱橫排蕩,滔滔莽莽”。
古體詩因為可以自由揮灑,敘事、描寫、抒情、議論都有優裕的空間,而讓詩獲得更強的過程性、現場感和細節感,內容更為具體、充實,提供的信息更準確,所寫的往往是“這一個”,個性鮮明,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格式化書寫。李白詩中五七言律詩很少,大量是古體詩,縱橫飄逸。他這樣做,就是不愿受格律羈絆,而太白詩,以自由豪放、汪洋浩瀚形成鮮明個性,彪炳詩歌史。
長篇五古、樂府歌行、近體歌行固不待言,即使篇幅不長的古體詩和歌行,也能具備上述特征。如高適《燕歌行》、韓愈《山石》、王安石《明妃曲》、蘇軾《游金山寺》等。《山石》是唐人七古名篇:
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靰?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此詩歷來受到高度評價,“此盡人所稱道者也”。明人馮時可《雨航雜錄》卷上說:“此詩敘游如畫如說,悠然澹然。余嘗以雨夜入山寺,良久月出,深憶公詩之妙。”清人顧嗣立說:“中間偏有極鮮麗處,不事雕鑿,更見精采,有聲有色,自是大家。”方東樹說:“不事雕琢,自見精彩,真大家手筆。……雖是順序,卻一句一樣境界,如展畫圖,觸目通層在眼,何等筆力!……從昨日追敘,夾敘夾寫,情景如見,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記,而敘寫簡妙,猶是古文手筆。”它把敘事、描寫、議論融為一體,提供的信息是具體的、豐富的,過程性、細節感都很強。有些句子兩句一意,敘寫翔實,避免了律體的刻板。
古體詩長于寫人、敘事,能更好地展示時空背景,表現重要題材和人物命運。如屈原《離騷》、《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木蘭辭》、杜甫“三吏三別”、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吳偉業《圓圓曲》、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孔凡章《芳華曲》《涉江曲》等。這些詩對時代背景、人物遭遇、人物性格、音容笑貌等作相對詳細的敘寫,而呈示出人的命運,包含豐富的社會歷史信息和人生感悟。藝術上亦搖曳多姿。重要事件的書寫,近體詩受篇幅和句式拘牽,往往只能作抽象的議論和感慨,古近體詩卻可以放開手腳,縱橫鋪排,盡情渲染,寫出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事情面相、歷史教訓等,“興觀群怨”之效表現得更充分一些。
因此,近體詩產生之后,古體詩寫作并沒有消退,而依然作為詩歌寫作的強勁一翼,生機勃勃。唐以后的歷代詩人詩集中,古體詩的比重往往比近體詩還大,質量更不在近體詩之下。綜觀從先秦到民國的舊體詩,古體詩的數量遠大于近體,名篇佳作亦層見疊出。
認知古典詩歌,一定要清楚古體和近體是源和流的關系。古體詩是詩的源頭,近體詩是從古體詩中派生出來的,是古體之“波”。“沿波以討源”,方為學詩正軌。嚴滄浪所謂“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滄浪詩話·詩辨》)正是指此。故古人編詩集,都要把古體排在近體之前,以顯示詩歌發展之來龍去脈,尊重詩史本來面目。近體在前,古體置后是淺人的無知妄為。因此,在二者的關系上,絕不能本末倒置,讓近體凌駕于古體之上。否則,就會陷入認識誤區,使舊體詩寫作走上狹隘之路。
三、詩體選擇“窄化”是當前舊體詩寫作創造力萎縮之癥候
古人作詩讀詩,都是古近體并重。只是到了當代,一般人讀的都是“課本詩”,而課本詩選的大量是短小的近體,于是給人們造成好詩都是近體的錯覺。一般寫作者也不像古人那樣有廣闊的閱讀面和專精的理解力,以為寫古詩就是寫近體,寫近體才“正宗”,才體現“水平”。這是“識量不足”,“見詩不廣,參詩不熟”導致的偏弊,遺漏詩之大美,是詩歌鑒賞和寫作的誤區。
當前的舊體詩寫作,眾人咸趨近體一途,五七言律絕連篇累牘。其中固不乏佳章,但大量是率意之作、應景之作、凡近之作、俗濫之作,乃至有名無實(不合律)之作,模式化十分嚴重。“句句同區,篇篇共轍,名為貫魚之手,非變之才也。”詩體選擇不會“變”,近體詩寫作亦不善“變”。于是,“在浩如煙海的當代舊體詩中,能夠稱得上具備‘當代性’的、可以保證它作為一種文體的活力和合法性的篇什,在總體上是不多的,傳統經驗的大規模重復性書寫、陳腐的觀念、狹小的格局、爛熟的意象(境)乃至表達上的不成熟,充斥在舊體詩詞的寫作中,既考驗讀者脆弱的耐心,也使這一古老文體面臨日甚一日的質疑”。詩體選擇的“窄化”,是舊體詩寫作創造力萎縮的癥候。
最近讀到一些寫重陽節的詩,全為近體,不同詩人的筆下屢屢出現“雁陣”“雁字 ”“ 鴻 影 ”“ 黃 花 ”“ 紅 葉 ”“ 霜 林 ”等 意 象 。如果重陽登高,真的看見大雁、菊花、紅葉,如此寫亦無不可,但就文本看,多是節日應景之作,而且呼朋引類,此唱彼和,“為文而造情”,既無登高之實際行動,如今“雁陣”又不易見,現代都市“雁陣”“黃花”“紅葉”很難組成實際的場景,因此可以斷定“雁陣”“黃花”“紅葉”之類,均為“套板反應”,是即詞匯、意象之“固化”“老化”,缺乏真實性、現場感和個性化,并非“修辭立其誠”。詩之意涵,多為老生常談,是“傳統經驗的大規模重復性書寫”,“在古人勝境中作優孟衣冠”,同樣“固化”“老化”,“引不起新鮮而真切的情趣”。而這不是個案,在各種同類題材、主題的書寫中,相當普遍。這當然不是僅僅由詩體選擇造成的,但與詩體特性也脫不了干系。
潤色鴻業是詩歌社會使命之一,乃詩中之大雅正聲。當代中國取得歷史性成就,邁入嶄新時代,“澹然四海清”,呈現欣欣向榮景象。詩家“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李白《古風》其一),應該放聲歌唱,用詩記錄歷史進程和時代自豪,以恢張民族精神,鼓舞民氣,固結民心民力,致力民族復興和國家現代化,并讓詩成為中國崛起的見證而在詩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方面的詩歌書寫不少,但多是近體詩。一是“碎小”;二是詩意之概念化,寫法之公式化,詞匯、意象老化現象突出,缺乏“精深盤郁、雄偉博麗之氣”,未能反映時代之恢弘,不足以翊贊休明,感染力亦有限。
四、當前舊體詩寫作詩體選擇應兼顧古近體,拓寬發展路徑
中國古典詩歌能夠登峰造極,擁有舉世莫勍的輝煌,從體裁角度看,跟詩體多樣有關。中國是詩歌大國,也是詩體大國。在古體詩和近體詩兩大類型之下,包含著數十種詩體,構成詩體的洋洋大觀。加上詞曲,詩體數量之多,恐怕堪稱世界第一。這種局面是經過兩千多年的累積形成的。詩體的增加為中國詩歌發展拓寬了路徑,提供了多樣化選擇,從而使古典詩歌繼長增高,不斷開拓出新境界,不斷積淀豐富,最后形成罕與倫比的詩歌大國。
詩體的多樣化最大限度地滿足了詩歌寫作和欣賞的多元化需求,善莫大焉。詩人可以根據書寫對象、自身心境和功力在豐富的詩體當中選擇合適的體裁,從而使思想情感得到最佳表達。眾多詩體構成的作品各競其美,則使詩歌文本呈現出豐富性。鑒賞者亦可從豐富的文本中各取所需,各享所好。
選擇何種詩體,是作者的自由。但詩歌寫作,有其規律在,詩人又不是完全能夠隨心所欲的。善于采用多種詩體,以因應不同的對象,使詩作豐富多彩,是古今大詩人成功的經驗。其中蘊含規律性的東西。只盯住近體詩,會導致“心理習慣”“詩歌態度”的狹隘和淺陋,會形成寫作惰性,滑入套板反應。當代舊體詩寫作,應繼承和弘揚古典詩歌傳統,發揮古體、近體各自的優勢,古近體并重,體現詩體的多樣性,進而提高詩歌表現能力,達成文本的多樣化和豐富性。
這樣做,有顯著的好處。一是有利于表現復雜的現代社會、現代生活、現代人的心理和情感。復雜的社會生活及個人體驗,不是一種詩體所能窮盡,需要各種詩體共同發力。古體詩自由度高,包容量大,在處理重要書寫對象方面確實有優勢。即使書寫個人經驗,也容易寫出過程性、現場感、細節感而抑制“套板反應”,體現時代特點和個性化內容。近體詩韻律優美,短小精悍,易于成篇,自不妨盡情采用。各種詩體各展所長,各盡其用,從不同側面呈現現代社會和個人遭際,合之則成眾美。
二是有助于構建健康的詩歌生態。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各種生態元素各得其所,美不勝收,才是最佳狀態。這樣的生態系統孕育無限生機,不斷產生新的美麗與收獲。精神生態系統亦然。我曾在《構建更富包容性詩歌生態》一文中提出“構建包容性詩歌生態”的理念,“‘包容性的詩歌生態’主要是指詩歌界秉持‘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則,改變新舊詩對立對抗的局面,讓新舊詩不再‘亂吵架’,實現新舊詩體的‘存異求同,彼此競賽’,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分道發展。”在舊體詩內部,這一理念同樣適用,古體詩和近體詩都能茁壯成長,詩歌生態系統才會保持平衡并煥發生機,千芳競秀,呈現欣欣榮景。如果只有近體詩一枝獨秀,就像自然生態系統只有一種植物生長,不免單調,并潛伏危機。一個作者的詩集中,唯有近體詩,是乏味的,乃至讓人失笑的。如果一個時代沒有厚重的古體詩,必然使詩史單薄輕巧,絕非正常。
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是,走出重近體、輕古體的誤區,在古體詩寫作方面多用心,追求詩體多樣化,拓寬舊體詩寫作路徑,增強舊體詩表現時代的能力。宏觀言之,全球化及中國崛起時代,歷史變遷波瀾壯闊,社會生活備極燦爛,為詩歌寫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斑斕多彩的詩材,需有鴻篇巨制加以反映、容攝。詩家應發揮古體之長,作嚴肅的精神創造,就重大主題和題材,精心構思,寫出鴻篇巨制,以為國家之光、詩歌之光、世界之光。微觀言之,詩人采用古體,一能更好地展示才情,二能顯示風格多樣化,三能更具體、真切寫出個人經驗,從單一走向豐富,從輕巧走向博大,進而凸顯自己的價值和地位。報刊和網絡平臺要注意發表優秀的古體詩作。詩詞競賽也要以思想藝術為評判標準,而不能以詩體為標準,歧視古體詩。
不言而喻,不管寫古體還是近體,都要追求獨創,寫出新意,提高思想和藝術水平。而要創新,一條重要的路徑就是關注當下,寫出時代感、個性化。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是新文學運動的綱領性文獻之一,他倡導的“三大主義”影響巨大。其文曰:“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陳獨秀是文化激進論者,他對古典文學的評判有極端之處,但他指出的舊文學之弊端:雕鑿、陳腐、迂晦、艱澀,在近體詩中體現得最為典型。而建設平易、抒情、新鮮、立誠的新文學的祈向至今不過時。我在《當代詩詞向新詩學習什么》(《貴州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中說:“新文學家曾對舊體詩發起猛烈抨擊,他們抨擊的地方就是新詩試圖突破的地方,也就是舊體詩應該反省的地方。新詩突破創新之處,也就是值得舊體詩學習之處。”這一點,近體詩寫作尤需注意。
五、附論自標詩體問題
當代舊體詩寫作中還有一個誤區,附帶一論。就是有些人喜歡自標詩體。他們生怕人家不知道他寫的是律詩,在題目前冠以“七律”“七絕”之類名目。如果其詩合律,尚無大礙,但有些詩并不合律,于是弄巧反拙。不標詩體,讀者可以把它視為古體,姑且算詩,而一旦標明,畫蛇添足,就貽笑大方。有些“詩”本來就是幾句拙劣的順口溜,而自標律絕,以為可以抬高詩價,樂此不疲,令人噴飯。此不可不戒。
古人作詩,從來不自標詩體,因為古人浸淫于詩中,熟悉各種詩體的特點,一看便知。只是在編詩集的時候,有的按詩體分類,才會出現七律、五律、七絕之類字眼,但都是在大類中申明,絕不會在哪一首詩前自我宣揚。而且按詩體分類編排的詩集,也不是學者提倡的,最受推崇的編排方式是編年體,這樣的編排便于知人論世。
考自標詩體之起因,可能是受了毛澤東詩的影響。公開發表的毛詩,都標明詩體。而毛詩的經典化程度高,當代許多人學詩、寫詩都以毛詩為樣板,于是就形成寫近體詩要標明詩體的印象,紛紛效仿。但實際上,毛公博極群書,他們那一代人又自小受到古典詩歌訓練,他深諳作詩之道,所以寫詩并沒有自標詩體的習慣。觀毛公書自作詩手跡,都沒有交代詩體。毛詩每首詩都冠以詩體,應是報刊和毛澤東詩詞集編輯為了便于讀者把握加上的。手頭有一本文物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是公開出版的毛詩詞的最早版本之一,扉頁有說明:“本書收入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以前發表過的二十七首,這次出版時經作者作了校訂,另外十首是沒有發表過的。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這段文字用的是手寫體,雖然沒有交代書寫者,但一看就知道是郭沫若手書的,所以才會按手跡印制。是集按寫作時間排序,詩詞混編,由于詞都有詞牌,所以詩也就加了詩體。這是臧克家等編好后交毛公“校訂”的,毛公認可這種做法,是出于對讀者的關心。好心但未必符合詩歌傳統的行為被不明就里者奉若神明,自標詩體的現象就成為當代舊體詩寫作風氣。
今人寫近體詩,要遵循傳統,回到只寫詩題不標詩體的正途,保持詩之莊重,并避免不合格律而貽笑大方之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