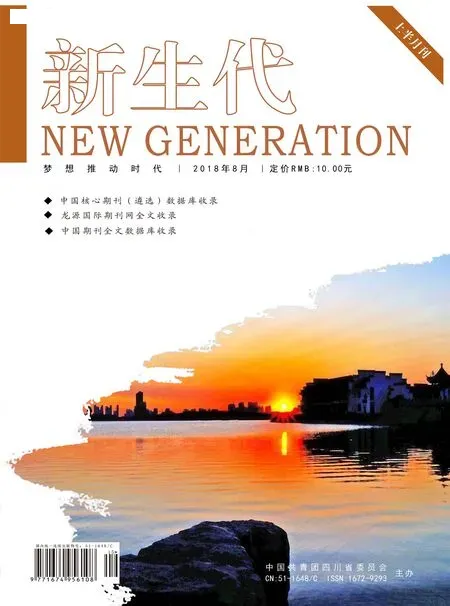中國明代文人畫與文藝復興時期繪畫色彩觀對比研究
武潔 河南大學藝術學院 475000
一、中國明代文人畫的發展
中國明代與意大利文藝復興發展時期,在時間上是幾乎同時存在的,但在這同一時間里,就藝術作品比較而言,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意大利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繪畫色彩觀。藝術都是以有限表現無限、言說無限,或者說就是超越有限。中國的文人畫,強調的是“無色”,所謂的無色其實是以畫面的白和墨汁的黑來作畫。畫面中只有黑白兩色,再沒有其他別的顏色來表達主張抒寫胸中之意的寫意之路。
在明代的畫壇,其實并不只是黑白兩色。明成祖朱棣對美術十分重視,試圖效仿宋代簡歷翰林書畫院,推動宮廷繪畫的發展。明代文人畫色彩觀為何多為黑白呢?這和當時的政治高度集權也有一定的關系,高度集權的政治需要在各個領域建立嚴密森嚴的等級制度。若說前面這點是客觀因素略微有些牽強的話,其實文人畫家從主觀上也并不想在畫面上使用更多的顏色。當時的顏色并不像現在的顏色一樣獲得的方式很多,人造的合成顏色價格低且與天然顏色差別不大,明代時的顏色多需要畫家自己研制,這既需要熟悉顏料的特性又需要耗費額外的時間和精力,而筆墨紙硯則是每個讀書人都具備的文房四寶,隨處可取,不需費心,如此中國文人畫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色彩觀,即僅存于黑白的色彩觀,以墨色為主,彩色只為“補筆墨之不足。從視覺心理上講,“任何視覺刺激圖式,最終都傾向于被看成是在給定條件下最簡單的圖形。”人的眼睛相對于較復雜的形狀和色彩更容易接受簡單的,就這樣文人們為了無色的山水畫發展出了許許多多自圓其說的理論“墨分五色”“水墨最為上”等等。
二、文藝復興時期色彩觀發展
在中國的西方,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新興的富商們需要顯示自己的身份,爭奪話語權。觀念的轉變是循序漸進的,中國人接受文人水墨畫也是自魏晉以來慢慢養成的視覺習慣,因此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題材以及色彩觀大部分還延續著中世紀的宗教色彩。
比如說文藝復興三杰都創作了許多與基督教有關的畫作,達芬奇創作了《最后的晚餐》,米開朗基羅創作了圣經故事穹頂畫《創世紀》,拉斐爾也創作了許多以圣母子為主題的畫作。即使都是表示宗教題材的畫作,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用色比較中世紀的更為大膽。如中世紀時,圣母子只能穿著紅黃藍三原色的服裝來表示人物純潔高貴的身份。而在拉斐爾的《坐在椅子上的圣母》中,圣母居然披上了綠色的披肩,這在中世紀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而出現這種現象,便是當時人們思想解放,開始關注身邊的人的意識表達。畫家畫中的圣母子不再是冷冰冰的天神形象,而成為了出門就能見到的和諧美的農婦與嬰兒。文藝復興時期宗教畫的背景不再是中世紀時的神明的金色,而變成了更有空間感的風景或者暗黑。赫拉克利特認為和諧來自自然:“自然是聯合對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諧。”簡化的背景,更順暢的使觀者把目光聚集在畫面的主體人物身上。意大利文藝復興時的畫家雖然已經開始表現物體的轉折、穿插的體積感。在肖像畫的用色上也更貼近實際,宗教畫的用色更接近于人的本身固有色。但當時的畫家并沒有深入描繪過環境色及反光,所畫的畫作中的顏色往往是一種固有色的身材變化,畫出的畫更像是一幅結實的素描的上色完成稿。
三、文人畫與文藝復興時期色彩觀差異
反觀中國明代文人畫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色彩觀,可以看出,中國文人畫比起真實地反映自然,更多是為了滿足自己內心的精神需求,他們在開始思考、理解世界的時候,就按照自己心中的形象去理解。而意大利文藝復興則開始注重科學性,繪畫在各種科學理論的支持下,發展的更為璀璨。
不同的色彩觀的產生都是由各種條件互相影響形成的,中國美學思想所講的“意象”,都與“意境”以至“境界”有密不可分的聯系,“詩之至處”,它的哲學本體論基礎是“萬物一體”即顯隱之綜合為一。這種能引人進入此種境界的藝術,比起模仿性藝術和現實典型之藝術來,我以為應居藝術之最高峰。我們今天的美學應繼承中國的這一思想傳統,以提高境界為旨歸,最高目標也應是使人高尚起來。因此畫面中一切是要合乎自己心境便好,作為初期是文人墨客的信手隨筆所以并不會很注重畫中色彩的探究,追求自己最簡單的顏色來完成整幅畫面。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資本主義慢慢興盛,畫家多為職業畫家,人們相信術業有專攻,畫家們也會窮其一生研究探索繪畫的更深含義,因此更容易產生更豐富的繪畫色彩觀。不管是莊子還是當代的的簡化美,看似兩種毫無交集的思想或者說審美方式,細細道來是有相通之處。
結語
萬物一體的境界是超越有限的意識所無窮追求的目標,在文化全球化和全球地域化的背景下,對美學的研究就不能一味地限定在某種傳統之下,要擴展美學研究范圍,加深中西方不同的美學思想、甚至藝術文化交流,“因此,在當代美學研究過程中,開放的態度與多維的視角是不可或缺的。”審美意識中“不在場者”在“在場者”中的顯現實際上就是通過想象力把在場與不在場結合為一體,人能在審美意識中體悟到與萬物一體,這就是一種崇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