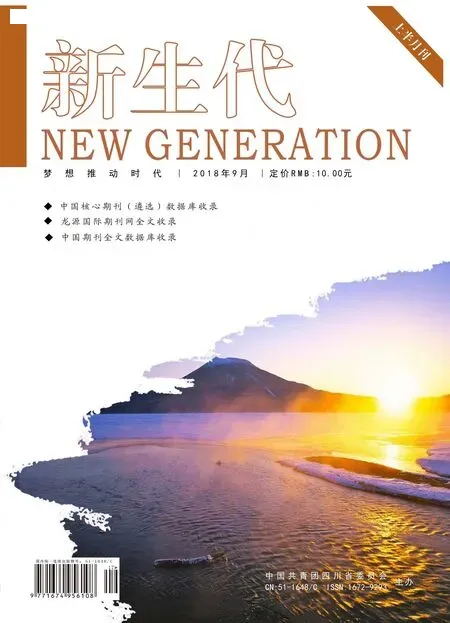《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復調特征解讀
曹曉彤
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
復調原是歐洲十八世紀以前廣泛運用的音樂體裁,指在同一部音樂作品中,不同演奏者用不同方式所演奏出的不同旋律一起構成和諧的樂章。巴赫金創造性地借用此術語來概括陀氏小說的詩學特征,以區別于“那種基本上屬于獨白型(單旋律)的已經定型的歐洲小說模式”。張賢亮的長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就顯現著巴赫金的復調理論的光芒。因此,筆者想通過巴赫金的復調理論來解讀《男》的對話性、未完成性和詩性語言的復調特征。
一、對話性
“對話”是被作為復調的理論基礎提出來的。正如巴赫金所說:“兩個聲音才是生活的基礎,生存的基礎。”我們的生活,是在交往和對話中進行的,這里所說的對話,是建立在人本主義思想的基礎之上的,它強調人的獨立和平等。在《男》中,這種對話性,主要體現在主人公自身的對話和主人公與與作者的平等對話兩個方面。
《男》的對話性,首先表現在主人公章永璘身上。章永璘內心獨白中出現的對白、辯論,正是他內心極度壓抑痛苦,精神失衡的產物。就像陀氏小說中的主人公一樣,《男》的主人公章永璘“在思想上自稱權威并具有獨特性”。小說以章永璘的視角和口吻進行,而且存在大段大段的主人公心理描寫,例如章永璘看到赤裸的黃香久之后,對于教育與文明的一系列思考,很具有哲理性,也很符合知識分子的身份,而且是獨特的“章永璘式”的思考。
小說中有很多涉及章永璘的多種意識間的對話。就其個人意識而言,作者通過對章永璘內心矛盾的沖突與自我思想的碰撞顯示其內心的不安與緊張,這是一種內在意識的對話,展示給我們的是一種獨白形式的對白。在小說中,章永璘會不時地處在一種“靈與肉”的對話狀態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這種理性與非理性的對話在第一部中表現最明顯,面對赤裸的黃香久,身體內部的力量和身體外面的力量相互斗爭,使得章永璘“既不能撲上去也不能往回跑”,“這是一塊肉,還是一個陷阱?是實實在在的,還是一個幻覺?如果我撲上去,那么是理所當然,還是一次墮落?”最終,精神上的憂傷戰勝了生理上的需求,章永璘“踉蹌地跑出葦蕩”。
此外,章永璘先后與大青馬、宋江、孟子、莊子、馬克思進行了“對話”,這是章永璘在內心壓抑卻又找不到交流的對象時,自我多個人格之間的對話。
《男》的對話性,也體現在作者與章永璘的平等對話上。這也是主人公自主意識的體現。《男》是張賢亮的自傳性小說,因此,章永璘這一形象既是作者形象的一種投影又是作者藝術構思的創造物,然而這一形象在小說中卻又有著他作為藝術形象的生命。這就使得主人公具備了主體性,這樣的主人公既是作家創作的客體也是自身擁有自主意識的主體。于是作者與章永璘之間就形成了平等的對話。這種平等對話,并不是在作者與主人公之間劃等號,而是作者賦予了主人公以自我意識,使其從作者的意識中獨立出來,擁有自己的個性與聲音。“這個時代,凡是能夠大聲唱出來或喊出來的聲音,全是沒有內容,沒有意義的。”像這樣的思索,既是章永璘的,也是作者的。它來自于章永璘內心深處,又是作者在文革時期遭受身心折磨后對那個時代的控訴。
這種主人公與多種意識,主人公與作者之間的對話,共同構成了《男》的對話性特征。
二、未完成性
“生活是無限的”,在這種意義上來說,對話也是沒有終止的,這就使得小說具有“未完成性”,這種未完成性,表現在小說故事的發展上,也表現在人物身上。
在《男》中,故事發展的未完成性是以一種相對隱晦的方式呈現的。表面上,小說以章與黃離婚作結,但在小說最后,“有一個小蟲子在墻角沙沙地爬。啊,春天來了!再有一個月便是清明。我是不是要回到她身邊來領受祭奠呢?好大好圓的月亮啊!”這讓我們不禁思考,兩人離婚了,故事就結束了嗎?章永璘還會不會回到黃香久身邊“領受祭奠”?這就是作者留給我們的小說故事上的未完成性,這顯然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和思考余地。
人物的未完成性,并非說人物塑造的不完整不豐滿,而是指“主人公們在對話中,用不給對方留下一個最終的、完成了的評語”,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開放的,個人的發展也是沒有終止的,既是生命停止,個人與社會與他人的聯系也會使他任然存在。在《男》中,無論是章永璘、黃香久還是其他人物,他們的生命都沒有停止,個體的發展也沒有停止,時代、社會的發展也沒有停止。
這樣,小說故事的未完成性和人物的未完成性,使得作品具有了開放性,作品留給讀者的空間更多了,作品的生命力在讀者那里得到了延續。
三、詩性語言
“詩性語言是隱含多層寓意的復調話語”。《男》便運用詩化的語言,表現了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也描繪了充滿詩意外部世界。
作者對章永璘內心世界的展現運用了詩性語言。當章永璘面對田埂上的蓖麻,內心大聲呼喊:“你好,我的蓖麻!你好,我的白楊!你好,我永遠流浪的白云!你好,我金黃色的小麥!我從你那里得到生命,而這個生命卻沒有價值。”時,情節的描寫淡化了,作者更關注主人公的內心,這心理活動,用詩歌一般的語言展現出來,使得讀者更生動地體驗到了主人公內心的活動,聽到了主人公內心深處對生命價值的思索與對生命的拷問。
環境描寫方面,作者所運用的語言是詩性的。這在每一部分都有有大量體現。比如當勞改隊女隊經過男隊時,“晨霧已經完全消散。橙黃色的陽光移到渠壩上,塵土上雜亂的足跡仿佛是無數奇異的花紋。”這種有沒而充滿詩意的環境描寫,為作者內心對女性的渴望做了映襯。
《男》所體現的這些復調特征,不僅是巴赫金復調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也賦予了這部作品更加含蓄而深沉的悲劇色彩,展示了主人公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艱難的生存狀況以及內心的苦悶與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