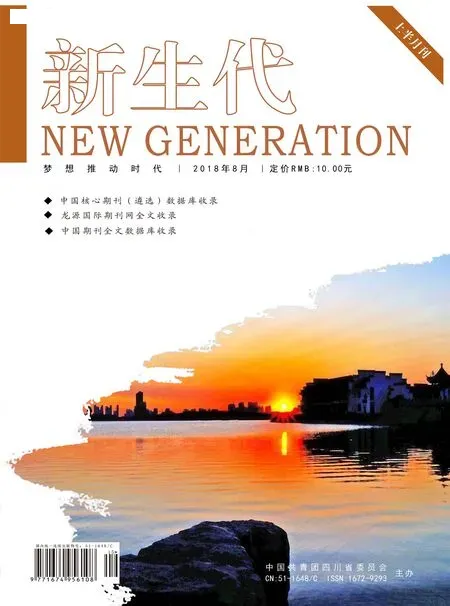試析翻譯與寫作的關系
——基于漢斯·弗米爾目的論的視角
陳添樂 湖南師范大學 湖南長沙 410000
1.漢斯·弗米爾目的論
20世紀70年代,德國出現的以文本目的為翻譯過程中最高準則的功能目的論對當代翻譯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功能目的論又叫做翻譯目的論(skopostheory),其中“skopos”是希臘語“目的”的意思。翻譯目的論認為整體翻譯行為的目的是整個翻譯過程中最主要的因素。
1.1 目的論的緣起
功能目的論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重要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1971年,德國的凱瑟琳娜·賴斯在他發行的著作《翻譯批評的可能性》中首次將功能范疇引入翻譯批評,把語言功能、語篇類型和翻譯對策聯系起來,主張把翻譯行為要達到的特殊目的作為翻譯批評的新范式,形成了功能目的論的雛形。萊斯認為綜合性交際翻譯也即理想的翻譯就應該使其概念性的內容、語言形式以及交際功能實現與原文的對等。但是在實踐中完全對等可能難以實現,因此譯本的功能性特征應給予優先考慮。第二階段:萊斯的學生弗米爾在1978年后提出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必須由譯文的預期目的和功能決定,將翻譯研究從以原文為中心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創立了目的論。該理論認為翻譯是以原文為基礎的,在特定語境下的有目的、有動機、有結果的行為活動。而這一行為必須要建立在協商的基礎上,除此之外,翻譯還要遵循一系列的原則如“語內連貫原則”和“語際連貫原則”前者指譯文要做到內部連貫,對于譯文讀者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后者指得是譯文與原文要有連貫性,譯文的內容要忠實于原文。同時弗米爾認為目的原則是翻譯過程應遵循的最高原則,翻譯的目的不同,自然方法和策略也不同也就是說翻譯的目的決定了翻譯的策略和方法。弗米爾目的論的提出對中西翻譯史上持續二三十年的異化和歸化之爭作出了很好的解釋。第三個階段:賈斯塔·霍茨·曼特瑞繼承和發展了費米爾目的論,她提出由“譯者行動”或“翻譯行動”來描述創造目標文本的聯合行動過程,在曼特瑞的理論建構體系中,她認為翻譯是一種“為實現某種特定目的而設計的復雜行為”。第四個階段:諾德在《翻譯中的文本分析》一書中提出了“功能加忠誠”的概念,修正了弗米爾提出的目的原則,克服了翻譯的隨意性。
1.2 目的論的原則和標準
翻譯目的論包括目的原則、連貫原則、忠實原則和忠誠原則。德國功能翻譯學派把“目的原則”和“忠誠原則”視為翻譯過程中的關鍵原則。“目的原則”是指翻譯的目的決定著翻譯的行為,一切翻譯活動都尤其目的性。“忠誠原則”是諾德在發現目的論的缺陷后提出的,它指譯者在翻譯過程既要尊重原作者又要對譯文讀者負責,協調譯文目的和作者意圖的同時使譯文讀者和譯者的關系在譯文中的關系保持一致。“連貫性原則”則是指譯文的語序要連貫,句式要通順,要使譯文讀者理解和接受。“忠實原則”與“忠誠原則”不同的是“忠實原則”著重于強調譯文要忠實于原文而不能偏離原文。
2.翻譯與寫作的本質
李長栓的兩部著作《非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2004)和《非文學翻譯》(2009)提出:“寫作是翻譯的基礎”(李長栓,2004:13)、“翻譯就是寫作,只是參照物不同。因此,寫作時應該遵循的原則,翻譯也應遵循”(李長栓,2004:158),那么事實上翻譯是否等同于寫作呢?這個問題的解釋應該從翻譯和寫作的定義入手,如果翻譯和寫作只是有交叉的范疇,那么把翻譯等同于寫作的說法可能存在缺陷。
2.1 翻譯的定義
翻譯是跨語言、跨文化、跨社會的交際活動。翻譯的過程不僅是兩種語言轉換的過程,而且是反應不同社會特征的文化轉換過程。翻譯涉及的內容有語言、文字、圖形、符號和視頻翻譯。有關翻譯的定義,許多翻譯名家各抒己見。古今明在其編著的《英漢翻譯基礎》一書中指出;“翻譯是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維內容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的語言活動,它包含著一個對原文含義的理解的逐步深入,對原文含義表達逐步完善的過程。”古今明似乎認為翻譯更加注重的是原語中思維內容的表達。而劉龍根在《大學英語翻譯教程》一書中把翻譯定義為是一種融藝術性和科學性為一體的創造性語言活動。
2.2 寫作的定義
夏德勇和楊鋒主編的《當代大學寫作》中把寫作定義為:“寫作是一項高級的腦力勞動,是寫作主體用有組織的文字反應客觀世界、表達思想感情和見解的活動。”寫作是一種創造性的思維活動,是人們運用語言或文字符號,對客觀事物的信息進行加工處理表達作者思想的活動。
3.寫作與翻譯的共性
通過上述對翻譯和寫作定義的闡述,我們不難發現翻譯和寫作都是一種語言和思想輸出的活動,任何與寫作和翻譯有關的實踐活動都有目的。若不是作者故意為之,以佶屈聱牙的方式填充文本來表達某種意圖或是譯者為保持源語語言的異國特色保持“信”而舍棄“達”的情況,寫作與翻譯一定是講究“達”的。
3.1 翻譯與寫作遵循連貫性原則
傅雷在提出“神似”的觀點時明確表示:“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傅雷,引自羅新璋,2009:624)。但是用“中文寫作”只可能是譯者,而不可能是原作者。譯文要達到使譯入語讀者看來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那么譯者就必須遵循譯入語國家的語言習慣,注重語內連貫和語際連貫,句子要講究通順達意。這也就要求譯者在處理譯文上要盡量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再優秀的翻譯家若是在翻譯一些帶有陌生化色彩的文學作品如意識流小說或是翻譯譯者未曾體驗過的生活經驗時,難免會受到自身知識結構建構、不同語言思維差異、文化層面上引起的詞匯空缺的影響而導致難以做到通順。而通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作品的銷量。在大多數情況下,譯文文本是否通順直接影響譯文讀者認為譯者是否做到了忠于原文。而對于寫作也是同樣的道理。每一篇文章都有一個中心思想,而中心思想是建立在文章段落的精煉概括上。因此文章中的固定要素若是游離,整個句式結構就會松散,語義不連貫,讀者也就無法捕捉到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內容。因此寫作也得遵循連貫原則。
3.2 翻譯與寫作遵循目的原則
無論是翻譯還是寫作都是有意識、有目的的腦力活動。譯者在接受翻譯任務時首先會對文本進行分析,對文本的難易程度、文本類型、文本風格都會有所了解。在此基礎上,譯者還會詢問文本的來源、文本的用途、以及譯文要達到的效果。這些信息其實都是譯者目的的體現。作者只有掌握了這些基本信息后才知道在翻譯中要采取何種翻譯策略。翻譯目的決定了譯者選擇什么樣的文本進行翻譯。比如林紓所生活的晚清時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飽受列強的欺凌。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的林紓翻譯目的很明確即喚起中國人民的革命意識推翻清政府統治。其翻譯的文本中政治因素占主導地位。而一本書或一篇文章的作者同樣是帶著某種目的寫作的,可能是為了完成交代的某項任務或是為了生計。即使有作者宣稱自己寫作沒有任何目的,只是興趣愛好使然,但事實上文本其實也是作者思想情緒的載體,情感的抒發也是作者獲得滿足的目的需要。
4.翻譯與寫作的異性
翻譯與寫作是兩個不同的術語,屬于不同的“工種”,因此它們之間的區別也是不言而喻的。
4.1 寫作更自由,翻譯受限制
對于譯者來說,翻譯時有一個現成的參考文本。譯者在翻譯文本時要參考原文的內容和結構,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對另一種語言“照抄”。譯者只能傳達原作者所思所想。若譯者偏離原文自我創造注定被認為是背叛了原作者,欺騙了新讀者。譯者就像是帶著鐐銬跳舞的奴隸,再怎么發揮能動性也跳不出原作者設定的圈。翻譯作品時還要遵循各種翻譯標準,經歷一系列的評判標準。但對于寫作而言,作者沒有必須要參考的物體,作者在思想的表達上擁有絕對的自主權,不會在形式上、措辭上受到嚴格限制。作者可以盡情地表達心中所想。沒有人會說一篇寫作背叛了什么,偏離了什么。因此翻譯要忠實于原文,遵循目的論的忠實原則。而寫作就像是自由的舞者,可以隨意創造舞步,無所謂忠不忠實。
4.2 翻譯更被動,寫作更主動
由于同語讀者與遭遇語言和文化隔閡的譯文讀者對于原文的體會是不一樣的。同語讀者和同語作者有著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因此他們更能意會原文的妙處。而譯文的讀者與原作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沒有直接關聯,譯入語讀者與原文作者中間隔了譯者這個環節。譯入語讀者想要獲取原文信息只能經過譯者。這時因為原作者沒有與譯入語讀者沒有進行語言文字上的直接接觸,所以譯入語讀者可能會懷疑譯者傳遞的信息內容是否失真或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是否帶有某種政治立場,從而故意在譯文中凸顯某種意識形態。所以譯者必須對譯文讀者富有道義上的責任,向他們解釋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這樣做的目的,對譯入語讀者忠誠。這就讓譯者陷入了被動的局面。而寫作恰恰相反,作者無需向讀者解釋為什么寫這篇文章的目的,關于文章內容的闡釋對讀者來說是開放的。作者在內容的自我創造方面擁有更大的主動權。
從目的論的四個原則出發,我們會發現翻譯與寫作有交叉的范疇,也有各自獨立的一面。無條件地把翻譯完全等同于寫作是不合適的,寫作的所有原則也不一定適用于所有類型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