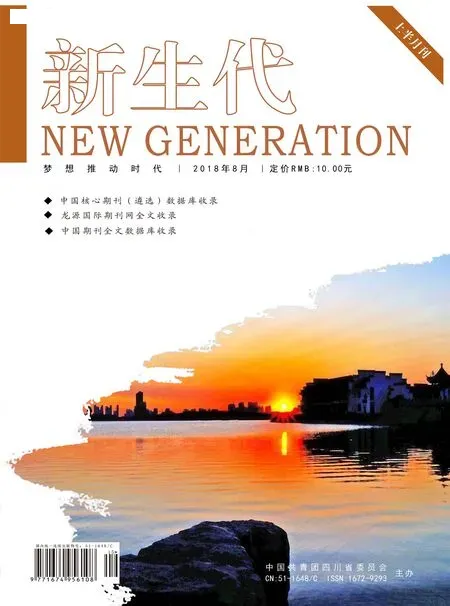論民主觀的兩種對立形式
——《路易十四時代》的思想基礎
廉鵬 遼寧大學
整個西方完全可以文藝復興為中心,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文明階段。民主意識的發展伴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形態,即自然制與意志一體制的對立,和形而上的信仰觀與人本身性質的對立。前者可簡述為民主與專制,后者則是宗教與人性。
文藝復興結束了中世紀的神秘主義傾向,但宗教改革又帶回了這種抽象的主觀理智。圣巴托羅繆的屠殺使胡格諾教受到重創,三十年戰爭改變了世界格局,法蘭西帝王路易十四為穩定法蘭西在歐洲取得的地位,開始了類似中國早期古代政治的體制。中國最先也認為君權神授,《尚書·康誥》載: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宅王命。”路易十四推行這種極權政治,正如麥克高希在《世界文明史》指出的那樣:“君主成為已組織起來的社會的一個正義的保護者及和平的維持者。”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強權專制需要有能力的君主才能體現其進步性。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指出,作為人的每個個體,都可能體現有個人意志,而這一意志對立或有別于他作為公民所具有的公意。韓非子極力壓制這一自由主義思想,主張“奉法者強,則國強”,面對群臣貪佞,則提出“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路易十四充分運用了這一思想,在一種已不適宜強權的環境下運用強力,經歷了一段輝煌的時期。“民主”二字在西方近代和中國古代史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民”字在中國古義是盲人奴隸,可以認為在經短暫的經驗崇拜后,王權已由一種非自然的力量轉化為一種由個體高級欲望產生的驅使力,大部分已被統治者剝奪了基本的肉身權利。而對于中西方共有的精神信仰即宗教,人又被剝奪了最重要的信由權但是實現民主觀后,專制性的優秀又體現出來,因為一個沒有基本約束力的社會是無法行使眾意和公意的,騷亂和再專制是無法避免的,正如辜鴻銘在其《中國人的精神》中說的那樣:“當歐洲各國的人民把他們的統治者,軍人和外交官趕下臺,正要親手處理與其他國家的戰爭與和平問題之時,在這些問題處理之前,恐怕是每個國家都處于戰亂紛爭的處境中了。”所以我們可以認為盧梭的契約主義是一種空想的矛盾體系,因為它將整個人類群體的意志假定不同化,然后再虛構一個有特殊意志的強權人物開始協調,但這一假定人物既要有足夠的強力使其他人民順從,又不能具有君主的性質,因此這種契約力是不存在的。
之所以將西方史分為兩個階段,以文藝復興為中心,是因為文藝復興使人類的本質得到認同。宗教的產生要遠早于政治性群體的組建,同時我們認為宗教信仰力要遠遠大于王權,路易十四將歐洲各國變為波旁王朝的附庸,但當他大力推行天主教,實行統一的教會時,歐洲各國便共同反抗,可見人民寧可在政治上被奴役,也不愿被剝奪思想上的自由。朋霍費爾將恩典分為廉價的恩典和高貴的恩典。他主張基督徒應該超越世俗,不應卷入塵世的生活。但這一思想正是基督教虛偽性體現,耶穌的呼喚使我們在順從時得到高貴的恩典,我們不能忽視這種中保作用,但如愛默生所言,為什么上帝不直接啟示人呢?我們可以發現,宗教在西方曾兩度被利用過,一次是在古希臘時期,阿那哥薩克,戴阿哥拉斯的受迫害使我們認識到君主專制可以保護社會成員,而宗教專制的這種偽共和制帶來的危害更加嚴重。另外一次則是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對全球的侵略,如史蒂芬孫的《化身博士》一樣,西方基督已帶有雙重人格,使我們認識到了基督教義的虛偽性。在這種非理性的存在下,宗教開始偏離自身的性質,它由一種人類的信仰成為一種強制手段,路易十四的政治壓制了這種現象,路易十四侮辱了教皇,使教權受到了大的沖擊。中世紀鑲嵌壁畫興起,人民對宗教的 狂熱達到了高潮,隨著加洛林王朝的文藝復興,人文在藝術上得到充分體現,人文主義的興起使人類逐漸意識到自我存在性,這時出現了新的藝術形式,如布魯內萊斯基的透視藝術和魯本斯這一超自然主義藝術。
拉納提出:“宗教哲學似乎本質上的超時間,超歷史的,因為它理應就是形而上學。”我們可以接受這種宗教觀,我們無法像普羅透斯那樣預知未來。斯賓格勒所持的歷史循環論將人類歷史看作是一個靜態的規則發展體,從表象含義上看他揭示了歷史發展的幾類基本規律,但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主觀意識的發展進程從初始形態(人類起源)與社會物質形態相符,但由于其不受客觀事件的影響,從而使兩種存在方式發生分離,但在某一階段開始作用于一特定時期時,便發生了與基本規律相悖的特殊存在,從而解釋了為什么路易十四的專制統治能在特定的背景下與新生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觀相協調。路易十四晚年財力枯竭,開始轉化為以義和德作為核心統治力,將權力分散。整個人類歷史的民主觀是基于一種文明上的,假定人類文明停滯,則我們始終要過穴居生活,民主觀便不可能存在,像斯塔夫利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所說:“文明的到來對人類平等來說是一種倒退。”自然科學的進步必將促進宗教哲學的完善和發展,基要主義不符合人類發展的基本規律。基要主義試圖將宗教完全獨立化,甚至不考慮民主觀的內在本質而將其視為一種后于宗教思想的心理欲求,但我們要理解民主概念是起始于社會群體出現的 ,只是作為客觀實在體在早期階段并被認識。阿諾德·湯因比認為宗教被科學技術取代,這是另一種極端的觀點。民主的相對獨立性必然會隨社會形態的變化而變化,自然科學的發展滿足了近代以前物質的需求從而使民主觀得到一部分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自然權利的需求停止,民主的對象會不斷發生變化,說明了民主觀的不可實現性。如果其全部實現,那么整個社會便會陷入絕對自由主義的混亂中。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生產力越發達,宗教便越發展,宗教在人類群居范圍內不可能消失,民主觀也不可能得到完全實現。伏爾泰撰寫這本書的初衷是要尋找一種精神,這位自然神論者將路易十四作為假想意志的依靠。路易十四在經過鼎盛時期帶著遺憾而死,如叔本華說的那樣:“環顧皆是敵人,爭斗永無止息,他至死劍不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