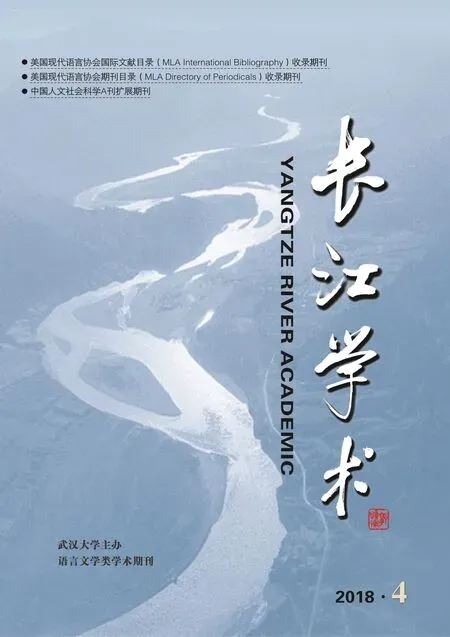從“新浪漫主義轉(zhuǎn)向”到“后啟蒙”時(shí)代
——改革開(kāi)放40年中國(guó)文藝觀(guān)的嬗變
金永兵 王佳明
(北京大學(xué)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新時(shí)期以來(lái),當(dāng)代中國(guó)文藝觀(guān)的幻變和文藝核心問(wèn)題及其理論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換,如果以1992年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正式確立為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經(jīng)歷了兩個(gè)主要階段,其一是強(qiáng)調(diào)審美自由的“新浪漫主義轉(zhuǎn)向”,其二是“后啟蒙”時(shí)代對(duì)自律化的現(xiàn)代性批判。
“新浪漫主義轉(zhuǎn)向”指的是那種通過(guò)強(qiáng)調(diào)“審美自由”來(lái)恢復(fù)“人”的感性維度,并借此打破以“階級(jí)論”為核心的政治理性壓抑的理論嘗試。“審美的”并不必然是“浪漫主義的”,在18至19世紀(jì)的歐洲,“審美”實(shí)際上就同時(shí)在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思潮中均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啟蒙主義中它指涉一種“人性”的客觀(guān)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即是“啟蒙”的基礎(chǔ),“如果沒(méi)有共同的判斷和情感標(biāo)準(zhǔn),人類(lèi)的推理和感情就沒(méi)有足以維持各自平凡而與之相符的生活的共同支撐”,它是一種“所有人因其天性與諸認(rèn)識(shí)能力的自由游戲而體驗(yàn)道德心靈狀態(tài)的普遍可傳達(dá)性”。而當(dāng)啟蒙主義的審美理論日趨抽象化時(shí),在當(dāng)時(shí)新興的浪漫主義之中,“審美”又開(kāi)始指涉一種根植于感性之中的無(wú)限性,正如以賽亞·伯林指出的那樣,此時(shí)“人們的思想意識(shí)開(kāi)始轉(zhuǎn)變。這種轉(zhuǎn)變足以使他們不再相信世上存在著普適性的真理……我們得知人們轉(zhuǎn)向情感主義……人們轉(zhuǎn)向無(wú)限,對(duì)無(wú)限的渴望噴涌而出”。
在我國(guó)1980年代的語(yǔ)境下,“審美”更接近于后者而非前者,它誕生于對(duì)“階級(jí)論”中所預(yù)設(shè)的客觀(guān)普遍性的反抗之中,主要強(qiáng)調(diào)人性中包含的無(wú)限豐富性,而并不想要建立一套客觀(guān)的“審美理性”。這種“浪漫主義”從反抗理性專(zhuān)制的意義上來(lái)講,與西方經(jīng)典的浪漫主義思潮是一致的,但從反抗的具體內(nèi)容上來(lái)看,其中又包含著新質(zhì)。它實(shí)際上是一次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內(nèi)部的自我調(diào)整,它試圖以具體的“審美自由”來(lái)反撥抽象的“政治自由”,而這種“具體性”在特定語(yǔ)境下則是通過(guò)對(duì)世俗物質(zhì)需求和欲望的恢復(fù)、肯定和激發(fā)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文藝上的“審美自由”既呼應(yīng)同時(shí)也批判著政治上以“去政治化”的形式對(duì)“物質(zhì)欲望”的肯定,這種肯定在文藝上表現(xiàn)為一種“新浪漫主義”,在政治上則表現(xiàn)為一種“新啟蒙”。政治上那種對(duì)物質(zhì)欲望的肯定并非強(qiáng)調(diào)人類(lèi)感性的全面性,而是以對(duì)馬克思主義的“物質(zhì)實(shí)踐”理論進(jìn)行再闡釋的方式,來(lái)肯定世俗物質(zhì)利益積累的合法性,這里的“物質(zhì)”并不指涉感性的人性,而是指涉物質(zhì)生產(chǎn),它更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的理性建設(shè),而非感性意義上的人性解放,這與“浪漫主義”的“審美自由”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從這個(gè)意義上講,此時(shí)政治上的變革是一種相對(duì)“階級(jí)理性”而言的“新啟蒙”。
“后啟蒙”時(shí)代則以抽象的“商品理性”取代具體的“物質(zhì)欲望”為核心特征,如果說(shuō)在“新啟蒙”時(shí)代中,“物質(zhì)”還在滿(mǎn)足人的需要的意義上保留著一定程度的使用價(jià)值,因而也同時(shí)具有一定程度的具體性的話(huà),那么在1992年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建立后,這種殘留的物的使用價(jià)值則通過(guò)高度發(fā)達(dá)的貨幣貿(mào)易被徹底抽象為物的交換價(jià)值、象征價(jià)值。在這一時(shí)期,文藝觀(guān)中出現(xiàn)了兩種新變,其一是出現(xiàn)了一種在意圖在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內(nèi)部通過(guò)強(qiáng)調(diào)“傳統(tǒng)性”“中國(guó)性”等新核心價(jià)值來(lái)重塑價(jià)值觀(guān)的嘗試;其二是針對(duì)“后啟蒙”時(shí)代產(chǎn)生的兩種自律化傾向——文學(xué)試圖通過(guò)市場(chǎng)化,遠(yuǎn)離政治干預(yù),在商品理性中形成的自律;出于批判商品理性的目的,作家和文藝?yán)碚摷覍?duì)“文學(xué)性”的自律性堅(jiān)守——所做的批判,這兩種自律性話(huà)語(yǔ)模式都是現(xiàn)代性發(fā)展到極端的表現(xiàn),而西方“新左派”的譯介、文化研究和后現(xiàn)代話(huà)語(yǔ)等新興話(huà)語(yǔ)模式,通過(guò)對(duì)話(huà)語(yǔ)自律化和價(jià)值自律化的反撥,試圖為“后啟蒙”時(shí)期的現(xiàn)代性困境尋找對(duì)策與出路。
一、現(xiàn)代性辯證法:“啟蒙”與“浪漫”
在“現(xiàn)代性”這一范疇紛繁復(fù)雜的內(nèi)涵之中,最核心的便是對(duì)主體性的確認(rèn)。正如哈貝馬斯所說(shuō):“現(xiàn)代性……只能在自身內(nèi)部尋求規(guī)范。主體性原則是規(guī)范的唯一來(lái)源。主體性原則也是現(xiàn)代時(shí)代意識(shí)的源頭。”現(xiàn)代性的主體訴求存在兩種意味:一方面,“主體性”范疇意味著存在一種普遍的人性;另一方面,“主體”的存在預(yù)設(shè)了“客體”,相對(duì)于客體的被動(dòng)而言,“主體性”就意味著一種能動(dòng)性,這種能動(dòng)性要求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必須以“自由”“自為”等范疇為依托承認(rèn)人類(lèi)行為具有一定限度內(nèi)的可能性,而且這種限度又必須是自律的而非他律的,否則,這種限制性就是外在于人的,必將是“非人的”。
從主體性確立的角度上講,啟蒙主義并未占據(jù)“現(xiàn)代性”這一范疇的全部外延,“現(xiàn)代性”的外延同樣涵蓋了浪漫主義。啟蒙主義代表了現(xiàn)代性中理性的一脈,但現(xiàn)代性?xún)?nèi)部早已產(chǎn)生對(duì)啟蒙理性的批判之聲,德國(guó)學(xué)者維爾默把其中的一支稱(chēng)作是“反對(duì)‘理性主義’的‘浪漫主義’力量”,他說(shuō):“針對(duì)啟蒙作為一種理性化的進(jìn)程,現(xiàn)代世界從很早,而且自始至終動(dòng)員了強(qiáng)大的力量。在這里,德國(guó)的浪漫派人物或許可以被視為其中的代表,他們包括早期的黑格爾、尼采,早期的馬克思、阿多諾以及眾多無(wú)政府主義者,此外現(xiàn)代藝術(shù)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納入這一股反對(duì)力量之中。”
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同時(shí)都是對(duì)現(xiàn)代主體性訴求的回應(yīng)。在主體性問(wèn)題上啟蒙主義尋求的理性主體,以理性秩序來(lái)消除外在性,通過(guò)理性主體對(duì)必然世界規(guī)律的把握實(shí)現(xiàn)對(duì)偶然世界的征服以消除主體的外在桎梏;而浪漫主義對(duì)此問(wèn)題的回答則是以對(duì)主觀(guān)無(wú)限性的塑造來(lái)應(yīng)對(duì)外在性,此時(shí)外在性并沒(méi)有消失,但是它已不再是一種對(duì)主體的束縛。二者以不同的方式規(guī)定了人性的普遍性,又都確定了主體自由的可能性,在“人只服務(wù)于人的目的”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講,二者都帶有人道主義的色彩。因此,“進(jìn)步性”“人道主義”“主體性”,這些范疇都不是判斷一種思想從屬于啟蒙主義或浪漫主義的充分條件,浪漫與啟蒙之間真正的這種區(qū)別在于,它們?cè)诿鎸?duì)外在性時(shí),浪漫主義以主觀(guān)無(wú)限性吸納并保留了外在性,而啟蒙理性則不允許無(wú)法轉(zhuǎn)化為內(nèi)在性的外在性存在。
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我國(guó)“新時(shí)期”是以“新啟蒙”思想為主導(dǎo),在一定意義上忽略了“現(xiàn)代性”的外延包含“啟蒙”并大于“啟蒙”這一問(wèn)題。學(xué)者們判斷“新時(shí)期”屬于啟蒙主義,往往出自一種對(duì)“五四”的懷念與接續(xù),以及對(duì)毛澤東時(shí)代新中國(guó)建設(shè)模式的批判,正如賀桂梅所準(zhǔn)確描述的那樣,“‘新時(shí)期’作為一個(gè)告別50—70年代的‘前現(xiàn)代’‘革命’的‘現(xiàn)代化’時(shí)期,作為一個(gè)重新接續(xù)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而打碎傳統(tǒng)文化‘鐵屋子’的新的文化啟蒙時(shí)期,同時(shí)也作為一個(gè)掙脫了傳統(tǒng)中國(guó)‘閉關(guān)鎖國(guó)’謬見(jiàn)而‘走向世界’的開(kāi)放時(shí)期,這種歷史意識(shí)和時(shí)代認(rèn)知在80年代贏得了普遍認(rèn)同。”這種在1980年代開(kāi)始獲得普遍認(rèn)同的判斷中,包含了兩種對(duì)“啟蒙”的指認(rèn)方式:其一是將“新時(shí)期”之前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時(shí)期視為一段“前現(xiàn)代”的彎路;其二是將“改革開(kāi)放”視為啟蒙主義所追求的那種“自由”的同義反復(fù)。這兩種指認(rèn)方式都不包含對(duì)啟蒙主義最必要的指認(rèn),即一種具有核心價(jià)值指向的理性對(duì)外在性進(jìn)行體系化征服,并同時(shí)將不能被納入此體系的偶然性排除在外,也就是說(shuō),不承認(rèn)其現(xiàn)實(shí)性與合法性。
事實(shí)上,相對(duì)于“新時(shí)期”而言,毛澤東時(shí)代的建設(shè)具有更為激烈的啟蒙現(xiàn)代性,那種政治至上的邏輯正是一種以階級(jí)斗爭(zhēng)為核心的理性模式,這種理性模式以無(wú)產(chǎn)階級(jí)斗爭(zhēng)的最終勝利,即共產(chǎn)主義作為自己的核心價(jià)值,并嘗試將其他一切偶然的個(gè)人性因素排除在外,這正是啟蒙主義的特征。對(duì)主體性的束縛實(shí)則就是啟蒙理性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正如以賽亞·伯林所言,理性主義的各種模式是想以理性為工具將人從實(shí)踐的錯(cuò)誤中解放出來(lái),是想通過(guò)確立理性的自覺(jué)使人從自發(fā)性意識(sh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lái),啟蒙主義就是多種理性主義中的一種,但是“毫無(wú)例外,這些模式的結(jié)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過(guò)的人類(lèi)。這些模式不能解釋人類(lèi)全部經(jīng)驗(yàn)。于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終成為另一種意義的獨(dú)裁者”。這一“理性的辯證法”正是在于它將自身定義為真理,而將所有異在于此的存在方式都定義為偶然和謬誤,這樣一來(lái),“人性”之中不能與之相符的成分便被排除在外,理性體系成了唯一擁有完整現(xiàn)實(shí)性的存在。這正是我國(guó)“新時(shí)期”之前政治理性的表征方式。彼時(shí)只承認(rèn)階級(jí)性、政治性,并不意味著對(duì)主體性的取消,而是為主體性中政治性的成分賦予了過(guò)度的主導(dǎo)權(quán)重,這種已呈現(xiàn)桎梏特征的政治性又正是從前革命年代的解放性力量。并不是所有自由都是啟蒙,所有束縛都是非現(xiàn)代,“新時(shí)期”要處置的是一個(gè)主體極度政治理性化的啟蒙性時(shí)代。
既然并不存在所謂的“前現(xiàn)代”時(shí)期,那么如果我們將新時(shí)期主導(dǎo)思想稱(chēng)作“新啟蒙”的話(huà),這里的指涉便是有待厘清的。學(xué)界常見(jiàn)的“新啟蒙”這一范疇中的“新”,主要被人們理解為是相對(duì)于“五四”現(xiàn)代性啟蒙傳統(tǒng)的中斷而言。但是,如果這種現(xiàn)代性從未間斷,“新啟蒙”之說(shuō)內(nèi)涵就成了可疑而模糊的,需要細(xì)致辨析。實(shí)際上,如果以“現(xiàn)代性”為總體視角,中國(guó)1980年代的思想實(shí)踐在文藝界主要是一種“新浪漫主義”,而可以被稱(chēng)作“新啟蒙”的種種現(xiàn)象恰恰是在此時(shí)的政治領(lǐng)域中發(fā)生的。指稱(chēng)政治上新變?yōu)椤靶聠⒚伞保饕蛟谟诖藭r(shí)在政治上以“去政治化”來(lái)強(qiáng)調(diào)“物質(zhì)實(shí)踐”的方式對(duì)馬克思主義進(jìn)行的再闡釋?zhuān)^之于那種以“階級(jí)論”來(lái)闡釋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是一種新變。對(duì)于文藝領(lǐng)域的“新浪漫主義”來(lái)說(shuō),這種補(bǔ)充主要以強(qiáng)調(diào)“審美”的方式出現(xiàn)。“審美”雖然是一個(gè)理性與感性并重的范疇,但是在“新時(shí)期”的具體語(yǔ)境下,它更強(qiáng)調(diào)一種用以反抗教條式政治理性的感性維度。審美自由和主體自由在這一時(shí)期被畫(huà)上了等號(hào),在批判政治理性,以審美的主觀(guān)方式呼喚那些不能被政治理性體系化、秩序化的人性?xún)r(jià)值的意義上來(lái)講,這主要是一次以“新浪漫主義”來(lái)補(bǔ)充啟蒙理性的文學(xué)嘗試。可見(jiàn),“新啟蒙”和“新浪漫主義”二者之“新”并非在于它們的現(xiàn)代性訴求,而在于它們?cè)诂F(xiàn)代性思想內(nèi)部進(jìn)行調(diào)整,開(kāi)啟了一種以感性形式來(lái)補(bǔ)充抽象政治性的“新現(xiàn)代性”模式。
“新啟蒙”對(duì)物質(zhì)欲望和物質(zhì)實(shí)踐的肯定與強(qiáng)調(diào),離不開(kāi)當(dāng)時(shí)對(duì)馬克思的“物質(zhì)實(shí)踐”的具有還原性質(zhì)的再闡釋。“物質(zhì)實(shí)踐”是馬克思在面對(duì)啟蒙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中那種理性的抽象性和浪漫理想的虛幻性時(shí)提出的一條在現(xiàn)代性?xún)?nèi)部進(jìn)行自我批判的新道路。在馬克思的“物質(zhì)實(shí)踐”理論中,“勞動(dòng)”及在其基礎(chǔ)上歷史地形成的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guān)系,一方面集中體現(xiàn)了人類(lèi)感性創(chuàng)造力,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社會(huì)關(guān)系是在物質(zhì)實(shí)踐過(guò)程中歷史地生成的,它并不具有理性主義認(rèn)為的那種必然性。馬克思看到,啟蒙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把私有財(cái)產(chǎn)在現(xiàn)實(shí)中所經(jīng)歷的物質(zhì)過(guò)程,放進(jìn)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這些公式當(dāng)作規(guī)律”,于是,“既然我們只想把這些范疇看作是觀(guān)念、不依賴(lài)現(xiàn)實(shí)關(guān)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們就只能到純粹理性的運(yùn)動(dòng)中去尋找這些思想的來(lái)歷了”。對(duì)于浪漫主義來(lái)說(shuō),馬克思認(rèn)為它是“宿命論”的一個(gè)分支,“浪漫派屬于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這時(shí)資產(chǎn)階級(jí)同無(wú)產(chǎn)階級(jí)處于直接對(duì)立狀態(tài),貧困像財(cái)富那樣大量產(chǎn)生”,如果我們?cè)噲D以某種屬于人的主觀(guān)無(wú)限性來(lái)對(duì)其進(jìn)行超越,“勞動(dòng)”就被他們視為一種被命運(yùn)賦予的必然局限,于是浪漫主義者“蔑視那些用勞動(dòng)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活人機(jī)器”。如果說(shuō)古典主義者對(duì)勞動(dòng)者的苦難缺乏重視是由于歷史發(fā)展所處的特定階段的局限,學(xué)者們尚無(wú)法洞察剝削的實(shí)質(zhì)的話(huà),那么在馬克思看來(lái),對(duì)于19世紀(jì)的浪漫主義者來(lái)說(shuō),“他們的漠不關(guān)心卻已變成賣(mài)弄風(fēng)情了”。馬克思以“物質(zhì)實(shí)踐”的形式及其歷史來(lái)同時(shí)批判啟蒙與浪漫,他認(rèn)為“在人們的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huì)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ce]和消費(fèi)形式。在生產(chǎn)、交換和消費(fèi)發(fā)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huì)有相應(yīng)的市民社會(huì)。有一定的市民社會(huì),就會(huì)有不過(guò)是市民社會(huì)的正式表現(xiàn)的相應(yīng)的政治國(guó)家”。這樣一來(lái),啟蒙主義中理性的法和國(guó)家的核心地位便被生成于物質(zhì)實(shí)踐中的市民社會(huì)取代了,而浪漫主義中的感性維度則被“勞動(dòng)”所補(bǔ)充。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階級(jí)”本身就根植于“物質(zhì)實(shí)踐”這一范疇之中。正是社會(huì)物質(zhì)實(shí)踐的方式?jīng)Q定了人具體的生活方式,而“階級(jí)性”正形成于生產(chǎn)與交換環(huán)節(jié)中人所處地位的不平等關(guān)系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說(shuō):“社會(huì)階級(jí)在任何時(shí)候都是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交換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一句話(huà),都是自己時(shí)代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那種對(duì)“階級(jí)性”的片面強(qiáng)調(diào)可以說(shuō)正是通過(guò)對(duì)“物質(zhì)實(shí)踐”的理性化抽象來(lái)完成的,將現(xiàn)實(shí)生活等同于“階級(jí)生活”,實(shí)際上就是將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決定性因素錯(cuò)誤地理解為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全部因素。“新時(shí)期”以來(lái)我國(guó)對(duì)物質(zhì)的強(qiáng)調(diào)在1990年代自我抽象為一種“商品理性”,這意味著“物質(zhì)實(shí)踐”這一范疇的內(nèi)涵已經(jīng)被大大改變了:1980年代之前那種最終被抽象為“階級(jí)”的“物質(zhì)實(shí)踐”最初意在說(shuō)明的是,在社會(huì)生產(chǎn)過(guò)程中具有普遍性的“勞動(dòng)”和“感性”最終在剝削制度下顯現(xiàn)為一種差別,因而我們必須通過(guò)政治斗爭(zhēng)來(lái)消滅這種剝削制度,其中暗含的邏輯是,“矛盾是人類(lèi)的狀態(tài);人類(lèi)的烏托邦追求的不是減少矛盾,而是根除物質(zhì)不平等所產(chǎn)生的卑劣的、殘酷的、不必要的結(jié)果”;而1990年代及其之后那種最終被抽象為“商品理性”的“物質(zhì)實(shí)踐”主要強(qiáng)調(diào)的則是,物質(zhì)匱乏和物質(zhì)不平等一樣都是產(chǎn)生“卑劣的、殘酷的、不必要的結(jié)果”的原因,“貧窮不是社會(huì)主義”,解決物質(zhì)匱乏問(wèn)題同樣是共產(chǎn)主義的一個(gè)目標(biāo),于是對(duì)物質(zhì)的經(jīng)濟(jì)積累取代了對(duì)其制度層面的斗爭(zhēng),“商品理性”正是這種物質(zhì)積累方式的極端理性化形式。
可以說(shuō),自“五四”以來(lái),中國(guó)實(shí)際上大致經(jīng)歷了四種意義上的啟蒙:1930年代以前的“反封建啟蒙”是一種面向封建制度與思想的理性啟蒙,這種啟蒙之所以在當(dāng)時(shí)與“救亡”結(jié)合在一起,是由于思想家們將中國(guó)的危機(jī)歸結(jié)為封建主義的腐朽,將人性問(wèn)題歸結(jié)為封建綱常倫理對(duì)主體性的壓制;1930—1970年代末,我國(guó)則經(jīng)歷了一次“階級(jí)論”的啟蒙,雖然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物質(zhì)實(shí)踐”的論述對(duì)啟蒙具有鮮明的批判性,但是我國(guó)出于政治革命與斗爭(zhēng)的需要對(duì)物質(zhì)實(shí)踐所蘊(yùn)含的“階級(jí)性”更為強(qiáng)調(diào),在中國(guó)最后形成了一種以“階級(jí)理性”為核心的啟蒙主義;1980年代開(kāi)始我國(guó)則通過(guò)對(duì)“物質(zhì)實(shí)踐”中“階級(jí)斗爭(zhēng)”的淡化和對(duì)“物質(zhì)積累”的肯定走向了“新啟蒙”道路;從1990年代初期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確立開(kāi)始,中國(guó)社會(huì)則進(jìn)入了一種以“商品理性”為主導(dǎo)的“后啟蒙”時(shí)期。
在我國(guó)“啟蒙”與“浪漫”不能被截然區(qū)分,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圍繞“現(xiàn)代性”展開(kāi)的辯證關(guān)系。首先,這是因?yàn)樽鳛閮煞N現(xiàn)代性的路徑,“啟蒙”與“浪漫”之間形成的批判關(guān)系正是現(xiàn)代性進(jìn)程的內(nèi)部動(dòng)力;其次,在我國(guó)革命性“啟蒙”總是要借助一種由浪漫主義提供的激情,而浪漫的激情則有賴(lài)于啟蒙的理想來(lái)為之樹(shù)立一個(gè)共謀和批判的對(duì)象;最后,極端“啟蒙”實(shí)際上由于就是一種“浪漫”,而極端的“浪漫”實(shí)際上就是一種“啟蒙”,因?yàn)槿绻鎻?qiáng)調(diào)某種理性?xún)r(jià)值的有效性,那么理性的客觀(guān)性就將徹底變成一種絕對(duì)的主觀(guān)性,而對(duì)某種主觀(guān)性的極度發(fā)揚(yáng)則又必將導(dǎo)致這種主觀(guān)性喪失了任何具體性而變成一種絕對(duì)抽象的理性?xún)r(jià)值。
這種“現(xiàn)代性辯證法”早已存在于我國(guó)1930—1970年代的文藝建設(shè)之中。首先,當(dāng)一種現(xiàn)代性模式走向極端,另一種現(xiàn)代性模式將會(huì)站出來(lái)對(duì)之進(jìn)行反撥。“左翼文藝”對(duì)革命秩序的服務(wù),實(shí)際上反對(duì)的就是當(dāng)時(shí)文藝界中廣泛存在的那種只以主觀(guān)創(chuàng)造來(lái)對(duì)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超越”的浪漫主義傾向,例如在電影《英雄兒女》中主人公的革命動(dòng)因無(wú)非是源于友人之死和那一曲《鐵蹄下的歌女》,這種將革命情感化、藝術(shù)化的創(chuàng)作方式無(wú)疑只能是一種浪漫主義的幻想。對(duì)浪漫化的反撥成熟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huà)》那種將文藝納入革命秩序中的論斷,它賦予文藝以現(xiàn)實(shí)性、實(shí)踐性、啟蒙性。而這種論斷在20世紀(jì)60—70年代走向了極端抽象與扭曲,它本身又需要一種強(qiáng)調(diào)人的感性審美的理論來(lái)對(duì)之進(jìn)行批判。其次,1980年代之前,以理性秩序?yàn)楹诵奶卣鞯膯⒚芍髁x和以主觀(guān)創(chuàng)造為核心的浪漫主義之間經(jīng)常是共存的。盡管文藝作品被要求要“政治第一”,這使得文藝作品中最核心的價(jià)值場(chǎng)域被政治理性占據(jù),但是這種政治性又被要求通過(guò)對(duì)革命英雄的塑造來(lái)實(shí)現(xiàn)。“革命英雄”形象中包含著對(duì)“政治啟蒙”和“浪漫主義激情”的雙重發(fā)揚(yáng),“革命英雄”往往具有堅(jiān)定的革命信念和堅(jiān)忍不拔的個(gè)人精神品質(zhì)兩個(gè)特征——前者使革命英雄成了“階級(jí)英雄”,其意義必須由階級(jí)政治來(lái)詮釋?zhuān)笳邉t使革命英雄成了“精神英雄”,其意義則主要從個(gè)人性上來(lái)理解,因?yàn)楦锩叩拇鬅o(wú)畏精神一方面被視為一種天賦,另一方面又被闡釋為無(wú)產(chǎn)階級(jí)在失去土地、家庭后的階級(jí)革命性,后者雖然在表面上兼具了歷史性和物質(zhì)性,然而它并不能解釋少數(shù)“英雄人物”何以從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群體中脫穎而出。最后,無(wú)論是極端的“浪漫化”還是極端的“理性化”都走上了自己的反面,那種極度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創(chuàng)造的文藝觀(guān)無(wú)一不預(yù)設(shè)著一種抽象的人性,因而它們實(shí)際上與抽象的啟蒙理性無(wú)異;而那種極端強(qiáng)調(diào)“階級(jí)性”的文藝觀(guān)又無(wú)一不使“階級(jí)”脫離了歷史和物質(zhì)基礎(chǔ)變成了一種純主觀(guān)的構(gòu)建。正是在這種關(guān)系中,我們必須在“現(xiàn)代性”的視角下來(lái)分析“啟蒙”和“浪漫”之間的對(duì)立統(tǒng)一;也正是由于這樣的對(duì)立統(tǒng)一始終存在,我們又不能因?yàn)樵谀骋粫r(shí)期某一傾向占據(jù)了主導(dǎo)地位就將中國(guó)文論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視為斷裂的。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看,我國(guó)“新時(shí)期”對(duì)物質(zhì)欲望的肯定、對(duì)審美的強(qiáng)調(diào)并非一種斷裂,它實(shí)際上正是這種“現(xiàn)代性辯證法”運(yùn)動(dòng)的必然結(jié)果。
二、文藝的“新浪漫主義轉(zhuǎn)向”
浪漫主義首先針對(duì)的是那種啟蒙主義的理性獨(dú)裁,在啟蒙主義的理性化進(jìn)程中,為了對(duì)世界形成有效控制,人必須將世界中“非理性”的層面排除在外,而這種邏輯發(fā)展的極端便是,人為了實(shí)現(xiàn)對(duì)自身的全面理解,也會(huì)將“人”這一范疇中的“非理性”的偶然性和個(gè)性化因素排除在外。理性體系對(duì)“人”的簡(jiǎn)單化或異化使人們開(kāi)始將目光轉(zhuǎn)向情感和無(wú)限,這便是浪漫主義的開(kāi)端。對(duì)于浪漫主義者來(lái)說(shuō),那種理性劃下的價(jià)值區(qū)間過(guò)于狹小,以至于不能完整地反映主體性的訴求,于是他們便想要求助于一種居于核心地位的無(wú)限價(jià)值,正是在無(wú)限性中,浪漫主義者找到了確立現(xiàn)代性?xún)r(jià)值觀(guān)的基礎(chǔ)。
啟蒙主義的有限性或簡(jiǎn)單化傾向奠基在“理性”這一范疇之中,在啟蒙主義者那里,理性的哲學(xué)揭示了世界的真理,而審美則只是精神無(wú)法直達(dá)本質(zhì)時(shí)所繞的彎路。而浪漫主義對(duì)無(wú)限的強(qiáng)調(diào)則奠基在“審美”之中。在浪漫主義者看來(lái),理性實(shí)際上刪減了世界的豐富性,只有通過(guò)審美才能恢復(fù)。施萊格爾認(rèn)為,“詩(shī)將是我們考察的核心目標(biāo)。……對(duì)于整體所作的人和描述都不可避免地要變成詩(shī)。”在浪漫主義者那里,理性的抽象只不過(guò)是人在無(wú)法對(duì)世界進(jìn)行直接體驗(yàn)的時(shí)候所采用的替代手段,只有通過(guò)感覺(jué)和審美,人才能直接接近真理。于是,啟蒙主義的理性被顛倒過(guò)來(lái)。
浪漫主義的這種反撥從思想實(shí)質(zhì)上來(lái)說(shuō)是想通過(guò)“審美”來(lái)批判理性對(duì)世界的簡(jiǎn)化和專(zhuān)制。在諾瓦利斯那里,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聯(lián)系就發(fā)生于消弭主客對(duì)立的“感動(dòng)”之中,“人們將感動(dòng)著我們的東西之整體稱(chēng)為自然,可見(jiàn),自然始終關(guān)涉著我們身軀的肢體,即我們所稱(chēng)的感官……自然就是我們的身體將我們引入其中的那個(gè)美妙的共體,我們要學(xué)會(huì)按照我們身體的組織和能力認(rèn)識(shí)這個(gè)共體。”施米特將這種路徑劃歸為批判啟蒙的思想路徑之一,這些路徑在他看來(lái)共有四種:“哲學(xué)的反對(duì)運(yùn)動(dòng)”“神秘主義的—宗教的反對(duì)運(yùn)動(dòng)”“維柯(Vico)所代表的歷史的—傳統(tǒng)的反動(dòng)”和“情感—審美的(抒情的)反動(dòng)”。其中前三種批判形式都嘗試在理性體系之外重新構(gòu)建一種新的能夠具有普適性的范式,而以浪漫主義為代表的最后一種反動(dòng),“沒(méi)有創(chuàng)立哲學(xué)體系,而是把它所看到的對(duì)立轉(zhuǎn)化成一種具有審美平衡性的和諧。換言之,它雖然沒(méi)有用二元論制造出一個(gè)統(tǒng)一體,但是它為了消除對(duì)立而把它們歸結(jié)為審美的或情感的對(duì)比。”盡管浪漫主義的批判嘗試超越二元對(duì)立,但是它并沒(méi)有取消理性,“審美”這一浪漫的范疇,“不是非理性、反動(dòng)的,而是反思和批評(píng)啟蒙理性主義的弊端并與之競(jìng)爭(zhēng)的一種現(xiàn)代性理論”,浪漫主義者所追求的是主體的完整性,而非感性的片面性。
總的來(lái)說(shuō),西方的浪漫主義亦帶有鮮明的現(xiàn)代性,它是一種現(xiàn)代性思想體系中產(chǎn)生的內(nèi)生性自我批判,這種批判的重點(diǎn)在于以審美中包蘊(yùn)的“無(wú)限性”來(lái)反抗啟蒙理性對(duì)主體的簡(jiǎn)化。盡管由于我國(guó)的歷史語(yǔ)境與西方不同,對(duì)現(xiàn)代性啟蒙的批判因此也與西方的浪漫主義批判不盡相同,但是在大方向上二者是一致的。
我國(guó)新時(shí)期文藝?yán)碚摻绲摹靶吕寺髁x轉(zhuǎn)向”首先表現(xiàn)在對(duì)“審美”維度的恢復(fù)上,這種恢復(fù)的先聲便是“能動(dòng)反映論”“審美反映論”以及隨后的“審美意識(shí)形態(tài)”理論。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首先是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這一方面表明理論家們依然在反映論的基礎(chǔ)上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要表達(dá)某種本質(zhì)性真理,另一方面預(yù)設(shè)了這種認(rèn)識(shí)必須要對(duì)社會(huì)有能動(dòng)的反作用,以此便強(qiáng)調(diào)了意識(shí)形態(tài)建設(shè)對(duì)于“發(fā)展”和“進(jìn)步”這些現(xiàn)代性?xún)r(jià)值來(lái)說(shuō)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本質(zhì)特征之一是“審美”,又是為了區(qū)別于那種階級(jí)政治的抽象規(guī)定性,至于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權(quán)宜性和矛盾性則需要另當(dāng)別論。這種批判一方面表現(xiàn)在“審美”在這些理論家的論述中,正如在西方浪漫主義者那里一樣,既非純粹的理性,又非純粹的感官體驗(yàn),而是二者的統(tǒng)一,至于統(tǒng)一的基礎(chǔ)是什么,似乎還缺乏獨(dú)特而足夠的論證;另一方面,這種批判又表現(xiàn)為審美強(qiáng)調(diào)“個(gè)性”,而“個(gè)性”恰恰是諸如階級(jí)理論一樣的理性體系因其不能容納而極力想要將之排除在外的,當(dāng)然,個(gè)性如何與意識(shí)形態(tài)所強(qiáng)調(diào)的群體性統(tǒng)一起來(lái),似乎也不是這些理論的關(guān)注點(diǎn)。在這層意義上來(lái)說(shuō),“審美意識(shí)形態(tài)”理論已經(jīng)初步具備了浪漫主義美學(xué)的特征,但是它又不同于西方的浪漫主義,因?yàn)樵谄渲猩胁淮嬖趯ⅰ皩徝馈弊鳛橐环N獨(dú)立價(jià)值,并使之成為一種烏托邦理想的論斷,盡管其中也明顯地呈現(xiàn)出這種趨勢(shì)與指向,但在話(huà)語(yǔ)邏輯中還不充分不自洽。完整的浪漫主義必須具備兩種特性,其一是通過(guò)審美來(lái)彰顯主體創(chuàng)造自由,其二是將一種建立于這種審美自由之上的無(wú)限性?xún)r(jià)值觀(guān)放置在現(xiàn)代性?xún)r(jià)值體系的核心位置,對(duì)于“審美意識(shí)形態(tài)”理論來(lái)說(shuō),它只完成了前者。
真正使“審美”成為一種核心價(jià)值的是“純文學(xué)”的概念,正是“純文學(xué)”使得文學(xué)審美獲得了相對(duì)獨(dú)立性,而又正是由于這種獨(dú)立性的存在,使得理論家們向“審美”或“文學(xué)”之中灌注了審美烏托邦的理想。其中“純文學(xué)”能夠站穩(wěn)腳跟又正是基于對(duì)“文學(xué)是社會(huì)生活的反映”這一論斷的批判,“文學(xué)”從此擺脫了只能作為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而存在的狀態(tài)。劉再?gòu)?fù)于1986年指出,新時(shí)期文學(xué)發(fā)展的一大主潮便是“走向藝術(shù)的自覺(jué)與批評(píng)的自覺(jué)”,這種自覺(jué)表現(xiàn)為以下五個(gè)方面,“第一,文學(xué)從‘工具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lái),認(rèn)識(shí)到自己的特殊使命。第二,文學(xué)從‘反映論’的單一本質(zhì)規(guī)范中解放出來(lái),認(rèn)識(shí)到自身廣闊的道路。第三,文學(xué)從絕對(duì)化的共性觀(guān)念的規(guī)范中解放出來(lái),開(kāi)始了藝術(shù)個(gè)性自覺(jué)的時(shí)代。第四,語(yǔ)言符號(hào)正在醞釀一場(chǎng)重要的變革。第五,文學(xué)批評(píng)領(lǐng)域也表現(xiàn)出批評(píng)的自覺(jué)。”從劉再?gòu)?fù)當(dāng)年的這種判斷來(lái)看,1980年代的文學(xué)走向大體來(lái)說(shuō)有兩個(gè)方面:其一是對(duì)“工具論”和“反映論”的批判,確認(rèn)文學(xué)具有所謂獨(dú)立的價(jià)值,其中語(yǔ)言學(xué)轉(zhuǎn)向和批評(píng)的自覺(jué)實(shí)際上是文學(xué)自律化傾向的表征;其二是文學(xué)價(jià)值不再追求理性主義的普適性,開(kāi)始擺脫“絕對(duì)化的共性觀(guān)念”,追求藝術(shù)個(gè)性。其中前者使文學(xué)的本質(zhì)從“審美意識(shí)形態(tài)”進(jìn)一步轉(zhuǎn)變?yōu)椤罢Z(yǔ)言審美”、“思想探索”等形式,后者將“審美”的價(jià)值意味從理性的普適性即階級(jí)理性中解放出來(lái)。
借由“純文學(xué)”這一中介,文藝?yán)碚撔纬闪苏嬲饬x上的“新浪漫主義轉(zhuǎn)向”。“審美”開(kāi)始正式以批判政治理性并承載烏托邦價(jià)值的方式承擔(dān)起它特定的現(xiàn)代性職責(zé)。從這個(gè)意義上講,此時(shí)“審美”并不是對(duì)文學(xué)的減壓,那種被寄托于文學(xué)之上的現(xiàn)代性理想相較于那個(gè)以政治理性為中心的社會(huì)主義啟蒙時(shí)代來(lái)說(shuō)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此時(shí)出現(xiàn)的美學(xué)熱,是對(duì)處于轉(zhuǎn)型時(shí)期中國(guó)社會(huì)未來(lái)前景的一次美學(xué)想象和藝術(shù)探索。伊格爾頓在討論美學(xué)與時(shí)代生活的關(guān)系時(shí)說(shuō),“美學(xué)著作的現(xiàn)代觀(guān)念的建構(gòu)與現(xiàn)代階級(jí)社會(huì)的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各種形式的建構(gòu)、與適合于那種社會(huì)秩序的人類(lèi)主體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進(jìn)而他指出,“從某種意義上來(lái)理解,美學(xué)對(duì)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shí)形態(tài)形式提出了異常強(qiáng)有力的挑戰(zhàn),并提供了新的選擇。因此,美學(xué)又是一種極其矛盾的現(xiàn)象。”“純文學(xué)”“審美”之類(lèi)的范疇不僅承載著一種知識(shí)生產(chǎn)或?qū)徝纼A向,還肩負(fù)著對(duì)之前政治理性、秩序、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諸種形式進(jìn)行批判與消解,進(jìn)而試圖建構(gòu)起新的意識(shí)形態(tài)形式和審美烏托邦的任務(wù)。浪漫主義的批判中,“審美性”實(shí)際上取代了原來(lái)位于價(jià)值核心為之的政治理性,“借助于‘純文學(xué)’概念的這一敘事范疇,在當(dāng)時(shí)成功地講述了一個(gè)有關(guān)現(xiàn)代性的‘故事’,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自我、個(gè)人、人性、性、無(wú)意識(shí)、自由、普遍性、愛(ài)等等,都經(jīng)由‘純文學(xué)’概念的這一敘事范疇,被組織進(jìn)各類(lèi)故事當(dāng)中。”
自“審美”被放置于價(jià)值的核心位置之后,文藝界興起了兩種富有浪漫主義傾向的文學(xué)書(shū)寫(xiě):其一是以現(xiàn)代派為代表的先鋒文學(xué)寫(xiě)作,其二是“尋根”文學(xué)。對(duì)于前者來(lái)說(shuō),它們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一種以個(gè)性化的審美體驗(yàn)為依托對(duì)理性的規(guī)范性進(jìn)行突圍,如劉索拉的《你別無(wú)選擇》(《人民文學(xué)》1985年第3期)、徐星的《無(wú)主題變奏》(《人民文學(xué)》1985年第7期)、殘雪的《山上的小屋》(《人民文學(xué)》1985年第8期)等作品都以形式實(shí)驗(yàn)為依托,在“純文學(xué)”之中寄托了對(duì)“審美自由”的希冀。正如歐洲的浪漫主義者不斷回返自己的古希臘家園,在我國(guó)“尋根”文學(xué)對(duì)傳統(tǒng)的發(fā)掘中,也鮮明地體現(xiàn)著浪漫主義那種從過(guò)往中尋求“無(wú)限性”,又同時(shí)追求一種線(xiàn)性的進(jìn)步性的現(xiàn)代性張力。韓少功在《文學(xué)的“根”》一文中指出,尋根的作家“大概不是出于一種廉價(jià)的戀舊情緒和地方觀(guān)念,不是對(duì)方言歇后語(yǔ)之類(lèi)淺薄的愛(ài)好;而是一種對(duì)民族的重新認(rèn)識(shí)。”所謂對(duì)民族傳統(tǒng)進(jìn)行“重新認(rèn)識(shí)”,就是說(shuō)“尋根文學(xué)”是要通過(guò)對(duì)傳統(tǒng)的挖掘來(lái)為當(dāng)代社會(huì)尋找一種建構(gòu)新的現(xiàn)代性歷史意識(shí)的可能。“文化尋根,也是反文化回歸”,它一方面從傳統(tǒng)中獲得一種價(jià)值上的“無(wú)限”,但又并不希望“復(fù)古”,而是希望通過(guò)對(duì)這種無(wú)限性的價(jià)值的審美呈現(xiàn),能實(shí)現(xiàn)在理性體系之外,為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指明方向。
這種依靠“審美”來(lái)批判政治理性的方式之所以稱(chēng)之為一次“新浪漫主義轉(zhuǎn)向”,是因?yàn)檫@次浪漫主義思潮的興起承襲了西方經(jīng)典意義上的浪漫主義對(duì)啟蒙理性的批判,但有著兩方面的異質(zhì)性。其一,從批判的對(duì)象上看,這種“新浪漫主義的轉(zhuǎn)向”所批判的雖然也是理性主義對(duì)主體性的簡(jiǎn)化,但是這種簡(jiǎn)化來(lái)自“階級(jí)論”,“階級(jí)”本身并非一個(gè)純理性主義的概念,它在很長(zhǎng)的時(shí)段內(nèi)曾有著明確的歷史唯物主義內(nèi)涵,只不過(guò)到了20世紀(jì)60—70年代,這一范疇被做了抽象化理解,“新浪漫主義”對(duì)之進(jìn)行的批判并不是反對(duì)理性,而是通過(guò)批判與消解抽象的階級(jí)以恢復(fù)人的主體的完整性;其二,從批判的手段上看,“新浪漫主義轉(zhuǎn)向”在“審美性”的總體特征下,又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基礎(chǔ)上,用以“身體”為代表的不包含主客二元對(duì)立的概念來(lái)對(duì)“審美”進(jìn)行補(bǔ)充,反對(duì)以語(yǔ)言邏輯為基礎(chǔ)的理性邏輯,身體美學(xué)試圖以這種無(wú)限性來(lái)維持主體性話(huà)語(yǔ)的豐富性,這種擴(kuò)充是經(jīng)典浪漫主義中所沒(méi)有的。
以往被學(xué)界劃歸在“新啟蒙”之下的諸多文學(xué)特質(zhì),實(shí)際上需要被置于“新浪漫主義”下來(lái)討論才能打開(kāi)。上世紀(jì)末,有學(xué)者注意到了“新啟蒙”與“五四啟蒙”之間的異質(zhì)性,并認(rèn)為“新啟蒙”是一種“現(xiàn)代人道主義”,它“肯定人的非理性、內(nèi)在分裂與矛盾,指認(rèn)人的終極無(wú)意義局面,肯定人作為本能和欲望的存在”。這里被用來(lái)指認(rèn)“新啟蒙”的概念恰恰正好大多是“浪漫主義”的特征,以“人道主義”為依據(jù),將之放置在啟蒙理性之下,這些文學(xué)的“人學(xué)”特質(zhì)的出現(xiàn)便具有了偶然性,因?yàn)閺睦硇灾髁x出發(fā),我們并不能解釋為何“非理性”的人道主義能夠?yàn)閱⒚涩F(xiàn)代性服務(wù)。如果我們單純從理性意義出發(fā),我們便不能理解為何在1980年代興起了一股對(duì)“真實(shí)”和“虛構(gòu)”之間關(guān)系進(jìn)行討論的熱潮,因?yàn)椤爸饔^(guān)性的虛構(gòu)”無(wú)論如何并不符合啟蒙的理性化追求。當(dāng)“本質(zhì)真實(shí)”成為一種問(wèn)題的時(shí)候,實(shí)際上就說(shuō)明那種能夠直達(dá)本質(zhì)的理性本身已經(jīng)在此時(shí)變得可疑。單純以啟蒙觀(guān)之,我們便只能將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含混地解釋為“啟蒙策略”的變遷,可是,這樣會(huì)帶來(lái)理論認(rèn)識(shí)的嚴(yán)重混亂。同樣,我們也不能回答此時(shí)興起的身體美學(xué)身體敘事為何不強(qiáng)調(diào)理性,不試圖建立一套以身體為基礎(chǔ)的理性體系,而是試圖繞開(kāi)理性和感性之間的二元對(duì)立關(guān)系?我們就只能將之理解為一種對(duì)現(xiàn)代性的反撥,認(rèn)為它在反思啟蒙的同時(shí),其實(shí)帶有后現(xiàn)代性色彩。但是,“身體啟蒙”這個(gè)詞本身就是曖昧的,因?yàn)椤吧眢w意識(shí)”的覺(jué)醒和“啟蒙”只有目標(biāo)上的一致性,即確立主體性,實(shí)質(zhì)上卻并不相融合,在啟蒙主義的視角下,身體美學(xué)中總是包含著一種手段和目的上的內(nèi)在矛盾。如果在浪漫主義的視角下,我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種“非理性化”實(shí)際上是一種與理性啟蒙同樣強(qiáng)烈的現(xiàn)代性訴求,而那種手段和目的上的矛盾性恰恰是由于它雖然是現(xiàn)代性的,但卻從屬于浪漫主義的一脈。
對(duì)“新浪漫主義”的強(qiáng)調(diào)并非意在說(shuō)明整個(gè)1980年代的文學(xué)寫(xiě)作及文學(xué)理論都是“浪漫主義的”,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領(lǐng)域中,諸如“傷痕文學(xué)”“改革文學(xué)”等寫(xiě)作流派都帶有更鮮明的啟蒙理性色彩。“新浪漫主義”與“新啟蒙”往往在“新現(xiàn)代性”的大方向大目標(biāo)之下而被雜糅進(jìn)各種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理論表述之中。
三、“去政治化”與審美自由
我國(guó)新時(shí)期在政治領(lǐng)域?qū)Τ橄箅A級(jí)理性的批判開(kāi)始于一種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去政治化”。所謂“去政治化”不是不要政治,而是取消政治爭(zhēng)論。正如汪暉指出的那樣,“‘去政治化’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國(guó)家生活或國(guó)際政治中永遠(yuǎn)不會(huì)缺席的權(quán)力斗爭(zhēng),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價(jià)值及其利益關(guān)系的政治組織、政治辯論、政治斗爭(zhēng)和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亦即政治主體間的相互運(yùn)動(dòng)。”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中進(jìn)行的“去政治化”實(shí)際上就是讓政治爭(zhēng)論從經(jīng)濟(jì)問(wèn)題中退場(chǎng),“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這樣,經(jīng)濟(jì)政策便不再被從政治路線(xiàn)的意義上來(lái)闡釋?zhuān)?jīng)濟(jì)在保持其政治性的同時(shí)被“去政治化”了。
政治領(lǐng)域中的“去政治化”主要表現(xiàn)為試圖在將政權(quán)和國(guó)家機(jī)器之間做出明確區(qū)分,通過(guò)這種區(qū)分,政權(quán)的階級(jí)性和路線(xiàn)性就不再必然意味著在國(guó)家運(yùn)轉(zhuǎn)的層面上也要用階級(jí)和路線(xiàn)來(lái)與之一一對(duì)應(yīng)。汪暉在談到西方“去政治化”問(wèn)題時(shí)指出,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中,資產(chǎn)階級(jí)最初并沒(méi)有與之經(jīng)濟(jì)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權(quán)力,這促使他們力圖使經(jīng)濟(jì)成為一種自足的體系,“以政治與經(jīng)濟(jì)的分離為中心,現(xiàn)代資本主義試圖創(chuàng)造一種自我循環(huán)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及其‘去政治化’的秩序。”而從政治領(lǐng)域上看,在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完成之后,“一種去政治化的程序性的國(guó)家政治逐漸取代了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時(shí)代的多樣化的政治格局,其實(shí)質(zhì)也就是通過(guò)政治交換關(guān)系將統(tǒng)治集團(tuán)中資本主義的和非資本主義的成分連接起來(lái)。政治辯論由此轉(zhuǎn)化為權(quán)力爭(zhēng)吵,而其根本的環(huán)節(jié)即一種中性的國(guó)家概念及其現(xiàn)實(shí)機(jī)制的產(chǎn)生……在理論上,這一國(guó)家形態(tài)的出現(xiàn)導(dǎo)致了經(jīng)典作家們將作為政治性階級(jí)斗爭(zhēng)目標(biāo)的國(guó)家政權(quán)與國(guó)家機(jī)器區(qū)分開(kāi)來(lái),即一方面承認(rèn)國(guó)家是鎮(zhèn)壓性的、在一定疆域內(nèi)具有使用暴力的壟斷權(quán)的機(jī)器,但另一方面又必須對(duì)國(guó)家政權(quán)和國(guó)家機(jī)器加以區(qū)分,以此將奪取政權(quán)的政治性階級(jí)斗爭(zhēng)作為政治問(wèn)題的核心。”我國(guó)的“去政治化”與西方的“去政治化”話(huà)語(yǔ)實(shí)踐的共性在于,二者都將“國(guó)家政權(quán)”和“國(guó)家機(jī)器”區(qū)分開(kāi)來(lái),承認(rèn)二者都具有相對(duì)的獨(dú)立性,在一定限度內(nèi),其中一方的演變并不必然影響到另一方的性質(zhì)。這種以“去政治化”的方式又早在蘇聯(lián)的列寧時(shí)代就已經(jīng)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內(nèi)部衍生出來(lái),盧那察爾斯基曾在維護(hù)出版審查制度時(shí)說(shuō),“對(duì)于我們來(lái)說(shuō),大炮、刺刀、監(jiān)獄甚至國(guó)家……它們是一切資產(chǎn)階級(jí)——保守的和自由的資產(chǎn)階級(jí)的武器庫(kù)。但是我們認(rèn)為刺刀、大炮、監(jiān)獄本身和我們的國(guó)家,作為摧毀和消滅這一切的手段,是非常神圣的。”在這里“大炮、刺刀、監(jiān)獄甚至國(guó)家”都實(shí)際上被理解為不同形式的政權(quán)機(jī)器與工具,它們的性質(zhì)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而非決定政權(quán)的性質(zhì)。但與汪暉所描述的、終結(jié)了各個(gè)層次上的“政治論辯”的“去政治化”相異,國(guó)家政權(quán)與國(guó)家機(jī)器之間的區(qū)分恰恰強(qiáng)調(diào)前者按照統(tǒng)治階級(jí)來(lái)獲取其性質(zhì),而后者則可以體現(xiàn)為政治論辯與斗爭(zhēng)的場(chǎng)域。
我國(guó)新時(shí)期的“去政治化”開(kāi)始于改革開(kāi)放。1978年鄧小平提出“社會(huì)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根本表現(xiàn),就是能夠允許生產(chǎn)力以舊社會(huì)所沒(méi)有的速度迅速發(fā)展,使人民不斷增長(zhǎng)的物質(zhì)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mǎn)足。”這種對(duì)物質(zhì)需求的承認(rèn)暗含了這樣一種邏輯,“物質(zhì)需求”是中性的,“物質(zhì)需求”本身并不具有政治性。1979年,鄧小平進(jìn)一步指出“經(jīng)濟(jì)工作是當(dāng)前最大的政治,經(jīng)濟(jì)問(wèn)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wèn)題。”鄧小平是通過(guò)一種對(duì)“政治第一”原則的顛倒完成了對(duì)經(jīng)濟(jì)相對(duì)于政治而言的相對(duì)獨(dú)立性的確認(rèn)。這與階級(jí)論中對(duì)經(jīng)濟(jì)的政治性的強(qiáng)調(diào)的不同之處在于,“經(jīng)濟(jì)”的內(nèi)涵發(fā)生了變化,在階級(jí)論中,“經(jīng)濟(jì)”本身就是政治的物質(zhì)基礎(chǔ),經(jīng)濟(jì)層面的國(guó)家機(jī)器和國(guó)家政權(quán)實(shí)際上不能分開(kāi);在新時(shí)期的論斷中,“經(jīng)濟(jì)”則更主要地是被從國(guó)家機(jī)器的角度上來(lái)理解。這種策略的“去政治化”傾向在于,一旦經(jīng)濟(jì)被從國(guó)家機(jī)器層面上理解,那么國(guó)家政權(quán)的性質(zhì)問(wèn)題便和經(jīng)濟(jì)路線(xiàn)問(wèn)題不再相關(guān),這樣一來(lái)雖然國(guó)家政權(quán)領(lǐng)域中“階級(jí)性”依然被保留了下來(lái),而有關(guān)“階級(jí)性”的爭(zhēng)論則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中退場(chǎng)了。這種“去政治化”也是在改革開(kāi)放初期一以貫之的話(huà)語(yǔ)邏輯,在“南巡講話(huà)”中鄧小平明確提出“計(jì)劃多一點(diǎn)還是市場(chǎng)多一點(diǎn),不是社會(hu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zhì)區(qū)別。計(jì)劃經(jīng)濟(jì)不等于社會(huì)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jì)劃;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huì)主義也有市場(chǎng)。計(jì)劃和市場(chǎng)都是經(jīng)濟(jì)手段。”“經(jīng)濟(jì)手段”這一范疇直接對(du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和“計(jì)劃經(jīng)濟(jì)”都做了“去政治化”的理解,說(shuō)它們都和社會(huì)性質(zhì)無(wú)關(guān),實(shí)際上就表明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和政權(quán)的性質(zhì)在此時(shí)被做出了區(qū)分。
如果說(shuō)在社會(huì)領(lǐng)域中這種“去政治化”是通過(guò)對(duì)“國(guó)家政權(quán)”與“國(guó)家機(jī)器”的區(qū)分來(lái)完成的,那么在文學(xué)領(lǐng)域中這種審美的“去政治化”則是通過(guò)對(duì)為“革命機(jī)器”而寫(xiě)作與為“國(guó)家機(jī)器”而寫(xiě)作之間的區(qū)分來(lái)完成的。之前,將文藝與政權(quán)的性質(zhì)結(jié)合起來(lái),是通過(guò)將文藝納入政治機(jī)器中實(shí)現(xiàn)的,這一過(guò)程完成的標(biāo)志是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huà)》。張旭東認(rèn)為《講話(huà)》將文藝定位成了“革命機(jī)器”的一部分,“文藝是小政治,政治是大文藝,這是《講話(huà)》對(duì)文藝所做的一個(gè)政治哲學(xué)的界定,結(jié)論是文藝徹底的政治性。這并不是說(shuō)文藝應(yīng)該有多少政治含量,而是說(shuō)哪怕最純粹審美意義上的文藝也必然已經(jīng)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所以文藝必須是整個(gè)黨的革命工作整體中一個(gè)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在確立了政治本體論的總體性之后,談?wù)撐乃嚪懂牭奶厥庖?guī)律或‘自律性’才有意義,不過(guò)這種自律性并不存在于‘革命機(jī)器’內(nèi)部的‘黨的文藝工作’概念之中,因?yàn)楹笳邚母疽饬x上從屬于革命工作整體,直接服務(wù)于革命戰(zhàn)爭(zhēng)和社會(huì)動(dòng)員的要求。”“革命”是意識(shí)形態(tài)性的,它指涉一種階級(jí)斗爭(zhēng),“革命機(jī)器”意味著政權(quán)性質(zhì)和機(jī)器本身的性質(zhì)是一致的,于是被納入其中的文學(xué)便沒(méi)有理由獲得某種相對(duì)于政治的獨(dú)立性。
文藝觀(guān)上的“去政治化”必須符合兩個(gè)條件,其一是“國(guó)家政權(quán)”和“國(guó)家機(jī)器”首先要被區(qū)分開(kāi)來(lái),其二是在這種區(qū)分之上,“國(guó)家政權(quán)”必須放棄將文學(xué)作為自己的意識(shí)形態(tài)工具。1979年4月《上海文學(xué)》的評(píng)論員首先對(duì)“文藝”與“國(guó)家政權(quán)”之間的關(guān)系提出了質(zhì)疑,其核心要點(diǎn)在于,人們往往認(rèn)為文藝的問(wèn)題全部來(lái)自“四人幫”,但是“對(duì)炮制陰謀文藝的這個(gè)理論基礎(chǔ)——‘文藝是階級(jí)斗爭(zhēng)的工具’卻從未進(jìn)行過(guò)批判”,換言之,從根本上來(lái)講文藝的問(wèn)題在于它始終被迫要為“國(guó)家政權(quán)”的階級(jí)斗爭(zhēng)性質(zhì)服務(wù)。1979年鄧小平在為中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huì)做祝詞時(shí),明確地在“黨”的政治需要和“文藝”的自身規(guī)律之間做出了區(qū)分:“黨對(duì)文藝工作的領(lǐng)導(dǎo),不是發(fā)號(hào)施令,不是要求文學(xué)藝術(shù)從屬于臨時(shí)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wù),而是根據(jù)文學(xué)藝術(shù)的特征和發(fā)展規(guī)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lái)不斷繁榮文學(xué)藝術(shù)事業(yè),提高文學(xué)藝術(shù)水平,創(chuàng)作出無(wú)愧于我國(guó)偉大人民、偉大時(shí)代的優(yōu)秀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和表演藝術(shù)。”其中,“黨”即是“國(guó)家政權(quán)”性質(zhì)的代表,而黨不對(duì)文藝發(fā)號(hào)施令,只是對(duì)其做出符合其自身規(guī)律的指導(dǎo),這明確表明鄧小平讓“文藝”與“政權(quán)”之間保持了距離。在同一次會(huì)議上,周揚(yáng)也指出:“文學(xué)藝術(shù)發(fā)展的歷史表明,以某一種固定的創(chuàng)作方法來(lái)統(tǒng)一整個(gè)文藝創(chuàng)作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這樣做不利于充分發(fā)揮不同個(gè)性的作家、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才能,不利于創(chuàng)作的繁榮和發(fā)展。”所謂“某一固定的創(chuàng)作方法”,其實(shí)是對(duì)為政權(quán)而寫(xiě)作的委婉說(shuō)法,解放創(chuàng)作方法說(shuō)的就是將創(chuàng)作和政權(quán)需要區(qū)分開(kāi)來(lái)。
這種文藝觀(guān)上的轉(zhuǎn)變從社會(huì)根源上來(lái)講是社會(huì)整體“去政治化”的一部分,正如張旭東所言,“只有當(dāng)革命政黨和革命國(guó)家的政治本體論本身所涵蓋的社會(huì)和文化領(lǐng)域出現(xiàn)新的實(shí)質(zhì)性變化后,特別是當(dāng)‘革命機(jī)器’轉(zhuǎn)變?yōu)槌R?guī)意義上針對(duì)全社會(huì)和全體國(guó)民的‘國(guó)家機(jī)器’后,文藝和審美領(lǐng)域的自律范疇才作為客觀(guān)存在出現(xiàn)在新中國(guó)文藝評(píng)論和文藝?yán)碚摰囊曇爸小!边@里所說(shuō)的那種從“革命機(jī)器”到“國(guó)家機(jī)器”的轉(zhuǎn)變,就是一種“去政治化”,“革命”和“機(jī)器”之間產(chǎn)生的距離,在張旭東看來(lái)這正是那些對(duì)“文學(xué)自律”的討論之所以成為可能的根本原因。
這種“去政治化”在此意義上又不是一種徹底不講政治的“非政治化”,文藝依然是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維度之一,服務(wù)于國(guó)家的現(xiàn)代性理想。文藝的“去政治化”最初是一種對(duì)文藝社會(huì)性功能的解放,它一方面彰顯著個(gè)人的主體自由,另一方面其實(shí)依然在現(xiàn)代性的意義上具有集體性?xún)r(jià)值。程光煒認(rèn)為,“80年代一代,都把文學(xué)看作‘人的文學(xué)’,卻沒(méi)有意識(shí)到它同時(shí)也是‘社會(huì)的文學(xué)’。80年代文學(xué)的豐富性和復(fù)雜性,正是在這個(gè)節(jié)骨眼上被人誤解了。”這種“去社會(huì)化”正是當(dāng)時(shí)的文藝界極力避免的,飽受“去社會(huì)化”詬病的現(xiàn)代派實(shí)際上在最初是非常注重現(xiàn)代性進(jìn)程中的社會(huì)性的。馮驥才就曾為中國(guó)的現(xiàn)代派辯護(hù)說(shuō),“我們需要‘現(xiàn)代派’是指社會(huì)和時(shí)代的需要,即當(dāng)代社會(huì)的需要。”劉心武則直接將“現(xiàn)代派”放置在社會(huì)性視角下審視,“農(nóng)村讀者的文化水平和欣賞習(xí)慣還很難說(shuō)有了多大的改變,因此,中國(guó)的作家為他們寫(xiě)作品時(shí),盡管也無(wú)妨從高行健小冊(cè)子所介紹和歸納的現(xiàn)代小說(shuō)技巧中汲取營(yíng)養(yǎng),但畢竟還不能一律跌入‘現(xiàn)代派’范疇中。”現(xiàn)代派并非要以“審美性”來(lái)取代“社會(huì)性”,它實(shí)際上非常注重通過(guò)技巧與社會(huì)性之間建立起聯(lián)系,使文學(xué)參與到社會(huì)的現(xiàn)代性進(jìn)程中去。
社會(huì)對(duì)物質(zhì)欲望的肯定和文藝界對(duì)審美的發(fā)揚(yáng),都是在原有的政治理性維度上增加人的感性的要素。通過(guò)“去政治化”,我國(guó)在社會(huì)領(lǐng)域中肯定了物質(zhì)利益的相對(duì)獨(dú)立性,物質(zhì)利益及其背后的主體欲望不再被要求必須從階級(jí)性上來(lái)理解,在這一過(guò)程中物質(zhì)欲望被從階級(jí)性的意識(shí)形態(tài)中解放出來(lái);文藝中那種對(duì)審美的強(qiáng)調(diào),正是通過(guò)承認(rèn)人的感受、欲望等維度不必一定要從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的角度上去理解來(lái)完成的。在社會(huì)層面上來(lái)看,對(duì)物質(zhì)需求的滿(mǎn)足被理解為社會(huì)主義的本質(zhì)要求,如果說(shuō)社會(huì)主義最終是為人類(lèi)自由而奮斗的理想的話(huà),那么此時(shí)物質(zhì)滿(mǎn)足就具有了一種達(dá)到烏托邦的路徑的意義;而在文學(xué)領(lǐng)域中,“審美”這一范疇實(shí)際上突顯的是人的物質(zhì)性層面,這一范疇雖然表明一種理性和感性的和諧狀態(tài),但是在當(dāng)時(shí)的語(yǔ)境下,理性本身已經(jīng)足夠強(qiáng)大,而感性則被理解為是一種長(zhǎng)期缺失的維度,“審美”與自由之間的聯(lián)系同樣也主要是依靠對(duì)感性層面的強(qiáng)調(diào)來(lái)完成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審美”作為一個(gè)本質(zhì)上是要消除理性與感性之間對(duì)立關(guān)系的范疇,對(duì)它的強(qiáng)調(diào)在1980年代卻只呈現(xiàn)出“向內(nèi)轉(zhuǎn)”形式。
“審美”和那種以物質(zhì)的感性形式對(duì)理性的補(bǔ)充針對(duì)的都是曾經(jīng)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已經(jīng)抽象化了的階級(jí)理性,是一種通過(guò)感性形式完成的“去抽象化”。這兩種感性形式之間依然有著質(zhì)的區(qū)別。物質(zhì)實(shí)踐性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主義的本質(zhì)在于滿(mǎn)足人的物質(zhì)需求,這其中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功利性,感性需要實(shí)際上在其中被理解成了欲望的滿(mǎn)足和物質(zhì)財(cái)富的積累,而不是感性維度的全面恢復(fù)。因此社會(huì)層面的感性化指向最終形成的依然是一個(gè)理性化的政治策略,這一策略雖然強(qiáng)調(diào)感性,但是它更強(qiáng)調(diào)的是感性維度中符合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需要的那一部分,從對(duì)某一理性目標(biāo)的追求上講,社會(huì)的物質(zhì)化追求的是典型的啟蒙現(xiàn)代性,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需要的也是一種理性人的假設(shè)。而對(duì)于文藝觀(guān)上的審美轉(zhuǎn)向來(lái)說(shuō),雖然它的追求依然是現(xiàn)代性的。“復(fù)雜的審美主義最終指向的是一個(gè)非審美的問(wèn)題——人的主體性建構(gòu)的問(wèn)題”,在力求以審美自由來(lái)確立主體自由這一意義上,審美也帶有一定程度的功利性,但是這種功利性卻是一種“無(wú)目的的合目的性”,它只面向“完整人”的恢復(fù)而不面向人所確立的某一理性的目標(biāo)。如果說(shuō)感性作為物質(zhì)利益依然對(duì)人有著某種程度的簡(jiǎn)化的話(huà),那么在審美中則力圖恢復(fù)人感性的全面性。雖然社會(huì)的物質(zhì)化和文學(xué)的審美化都強(qiáng)調(diào)感性維度在現(xiàn)代性建設(shè)中的作用,都強(qiáng)調(diào)主體性的確立繞不開(kāi)感性,但是二者卻在感性的功利性問(wèn)題上分道揚(yáng)鑣,前者更強(qiáng)調(diào)作為物質(zhì)經(jīng)濟(jì)利益及欲求的感性,而后者則更強(qiáng)調(diào)感性中包含的那種人性的豐富性。
社會(huì)物質(zhì)化和文學(xué)審美化雖然同屬于社會(huì)“去政治化”的現(xiàn)代性進(jìn)程,二者之間卻從一開(kāi)始就存在著對(duì)立。在1980年代,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二者之間的統(tǒng)一,在反對(duì)抽象的階級(jí)性的大語(yǔ)境下,在強(qiáng)調(diào)感性這一共性的基礎(chǔ)上,二者形成了一種共謀關(guān)系。“80年代期間,文學(xué)對(duì)于這場(chǎng)經(jīng)濟(jì)變革報(bào)以熱烈的掌聲。作家驚奇地看到,許多人的自信、尊嚴(yán)和人格都是借助經(jīng)濟(jì)的拐杖站立起來(lái)的。”這種共謀關(guān)系一直維持到了1990年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確立之前,隨著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逐步深化,物質(zhì)利益的滿(mǎn)足從感性補(bǔ)充演進(jìn)為一種“商品理性”“消費(fèi)理性”,社會(huì)正式進(jìn)入了一種“后啟蒙”的狀態(tài)。“商品經(jīng)濟(jì)的交換原則逐漸演變?yōu)橹鲗?dǎo)甚至唯一的尺度之后,美學(xué)立場(chǎng)中的另一個(gè)傳統(tǒng)開(kāi)始復(fù)活了——從莎士比亞、莫里哀到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文學(xué)具有一個(gè)嘲弄或者鄙視金錢(qián)的傳統(tǒng)。無(wú)論是張承志的《黑駿馬》《北方的河》還是張煒的《秋天的憤怒》《古船》,無(wú)論是‘以筆為旗’的宣言還是‘融入野地’信念,人們都可以察覺(jué)到這個(gè)傳統(tǒng)的血緣。”在審美的感性形式和物質(zhì)利益之間的對(duì)立性被突顯出來(lái)的同時(shí),文學(xué)也在向著商品理性靠攏或者說(shuō)被商業(yè)邏輯整合進(jìn)市場(chǎng)領(lǐng)域,新浪漫主義也在市場(chǎng)理性的巨大引力場(chǎng)中或者消失或者轉(zhuǎn)化為文化資本的煉金術(shù)。如果說(shuō)1980年代的文藝觀(guān)最突出的特點(diǎn)是出現(xiàn)了一種“新浪漫主義”的話(huà),那么以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正式確立為標(biāo)志,文藝觀(guān)領(lǐng)域則進(jìn)入了一種圍繞“商品理性”“消費(fèi)理性”展開(kāi)討論的“后啟蒙”階段。
四、“后啟蒙”時(shí)代的現(xiàn)代性困境
“啟蒙”是一個(gè)現(xiàn)代性的范疇,但是“后啟蒙”中的“后”并不指涉一種“后現(xiàn)代”,盡管其中有“后現(xiàn)代”的因素,但這里的“后”主要指的是一種理性模式的變遷。“新啟蒙”指的是通過(guò)對(duì)物質(zhì)利益的強(qiáng)調(diào)來(lái)補(bǔ)充政治理性的狹隘與不足;而“后啟蒙”則指的是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建立之后,“新啟蒙”中的“物質(zhì)利益”“物質(zhì)需求”發(fā)展為一種“商品理性”。通過(guò)將前一時(shí)期具體的甚至說(shuō)真實(shí)的感性的物質(zhì)需求轉(zhuǎn)化為抽象的“商品價(jià)值”,啟蒙基本完成了自身的“再理性化”,其中真實(shí)感性需要逐漸消逝,逐漸興起的是象征與符號(hào)化消費(fèi)。“后啟蒙”時(shí)代指的就是這種以商品交換價(jià)值為核心,以消費(fèi)主義經(jīng)濟(jì)理性為主要原則的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混雜的時(shí)期。
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建立為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的現(xiàn)代性分期在學(xué)術(shù)界早已有之,但是學(xué)者們往往只看到了這種現(xiàn)代性的世俗性,卻并未看到這種現(xiàn)代性的理性“抽象化”實(shí)質(zhì)。有學(xué)者提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確立以來(lái),我國(guó)進(jìn)入了一種“生活的現(xiàn)代性”“物質(zhì)的現(xiàn)代性”,或稱(chēng)“中國(guó)新現(xiàn)代性”,它一方面作為現(xiàn)代性的物質(zhì)奠基,在多種現(xiàn)代化追求中處于最基礎(chǔ)的位置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指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為我國(guó)帶來(lái)的物質(zhì)化變革。從理論建設(shè)的角度來(lái)講,“稱(chēng)這種生活現(xiàn)代性或物質(zhì)現(xiàn)代性是中國(guó)新現(xiàn)代性,還在于我們一個(gè)時(shí)期以來(lái)的現(xiàn)代性研究基本上沒(méi)有將其納入考察視野,我們的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一直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二元模式中徘徊,而這個(gè)模式的唯啟蒙現(xiàn)代性的價(jià)值偏向又使其以啟蒙論的價(jià)值現(xiàn)代性為統(tǒng)領(lǐng),尤其以知識(shí)分子的啟蒙話(huà)語(yǔ)為主導(dǎo),封閉和遮蔽了更加豐富的現(xiàn)代性?xún)?nèi)容。”然而,我國(guó)的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其實(shí)從未完全拋棄“啟蒙與救亡”的邏輯,中國(guó)的現(xiàn)代化始終具有憂(yōu)患意識(shí),特別是包含著現(xiàn)代性民族國(guó)家建構(gòu)的面向。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確立以來(lái)的現(xiàn)代性變化依然延續(xù)著中國(guó)自“五四”以來(lái),甚至是自“維新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直至1980年代的現(xiàn)代性邏輯,其中真正的本質(zhì)性區(qū)別并不在于物質(zhì)性和世俗性,真正的新質(zhì)實(shí)際上是從前不曾真正有過(guò)的“商品理性”與市場(chǎng)邏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也關(guān)注物質(zhì)滿(mǎn)足,但它卻較之從前而言更具抽象性。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下的物質(zhì)滿(mǎn)足不再只是具體的物質(zhì)需求的滿(mǎn)足,它更是一種符號(hào)化的滿(mǎn)足。在交換價(jià)值中,一切物品都揚(yáng)棄了自己富有個(gè)性的特質(zhì),具體的特質(zhì)均被抽象為符號(hào)化的貨幣價(jià)值。
這種商品理性絕不僅僅是一種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內(nèi)的價(jià)值體系,它更具有整體性的特征: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邏輯實(shí)際上大幅度地改變了社會(huì)的政治、文化結(jié)構(gòu)。“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因此對(duì)于我國(guó)來(lái)說(shuō),試圖在引入資本同時(shí)不改變既有的社會(huì)關(guān)系是不可能的。新社會(huì)關(guān)系必然會(huì)以商品交換邏輯為依托,其極端情況便是商品拜物教的出現(xiàn)。這種社會(huì)關(guān)系又必然會(huì)有其文化上的影響,在價(jià)值觀(guān)領(lǐng)域中,一種符合這種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價(jià)值觀(guān)必然出現(xiàn)。并且,這種價(jià)值觀(guān)的出現(xiàn)與中國(guó)改革開(kāi)放,進(jìn)入現(xiàn)代世界體系,受到日益深化的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影響密切相關(guān),新質(zhì)的商品理性和社會(huì)價(jià)值觀(guān)并不完全是本土的內(nèi)生的。盡管我國(guó)沿海地區(qū)已經(jīng)部分地于1980年代走向了工業(yè)化,但絕大部分的內(nèi)陸地區(qū)還都處在農(nóng)業(yè)文明階段,“而90年代卻有了一個(gè)根本的改變,這就是社會(huì)機(jī)制的運(yùn)行開(kāi)始受著‘全球一體化’的影響和制約,表面上它首先是經(jīng)濟(jì)上的市場(chǎng)化帶來(lái)的種種社會(huì)現(xiàn)象的變化,但是,更深層面的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的入侵,包括從生活觀(guān)念到思想觀(guān)念,乃至小到審美觀(guān)念的迅速蛻變,卻是改變這個(gè)世界的根本動(dòng)力。”在一個(gè)已經(jīng)“去政治化”了的社會(huì)中,國(guó)家政權(quán)的性質(zhì)可以通過(guò)與國(guó)家機(jī)器保持一定得距離來(lái)維持自身,但是對(duì)于社會(huì)文化領(lǐng)域來(lái)說(shuō),此時(shí)它不可避免地會(huì)因失去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的庇護(hù)而被強(qiáng)大的商品理性滲透改造。如果說(shuō)1990年代之前,中國(guó)的改革開(kāi)放是以人性的解放之類(lèi)的價(jià)值觀(guān)來(lái)為物質(zhì)需要賦權(quán)的話(huà),那么1990年代之后,通過(guò)全球化輸入的則是一種非經(jīng)驗(yàn)、非歷史的抽象的商品理性模式。因而可以這樣說(shuō),中國(guó)社會(huì)自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建立之后已經(jīng)基本轉(zhuǎn)入了一個(gè)“后啟蒙”的時(shí)期。
“后啟蒙”時(shí)代的文藝是尷尬的,無(wú)論是浪漫的現(xiàn)代性還是啟蒙的現(xiàn)代性都在其中既受到壓抑又批判乏力。說(shuō)它們受到壓抑是因?yàn)樾聲r(shí)期以來(lái)無(wú)論是“新浪漫主義轉(zhuǎn)向”還是“新啟蒙”,知識(shí)分子們都在其中追求著一種對(duì)現(xiàn)代主體自由的確立。到了“后啟蒙”時(shí)代,一方面商品交換價(jià)值的抽象性排斥審美的具體性,于是那種審美自由便被驅(qū)逐出話(huà)語(yǔ)場(chǎng)域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商品理性只允許主體擁有消費(fèi)自由而不愿讓主體獲得溢出商品理性體系之外的自由。說(shuō)它們批判乏力是因?yàn)?990年代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實(shí)際上在1980年代改革開(kāi)放之初就已經(jīng)開(kāi)始醞釀,它是中國(guó)現(xiàn)代性建設(shè)自身邏輯發(fā)展的結(jié)果。正是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們自己以現(xiàn)代性理論為這種現(xiàn)代性路徑賦予了合法性,無(wú)論是社會(huì)開(kāi)放還是對(duì)物質(zhì)性的肯定都曾經(jīng)與知識(shí)界確立主體性的努力形成過(guò)共振關(guān)系。
對(duì)于現(xiàn)代性中更具浪漫主義傾向的一群人來(lái)說(shuō),他們?cè)?jīng)肯定過(guò)物質(zhì)性,此時(shí)物質(zhì)性在社會(huì)上被以一種極富現(xiàn)代性的形式全面確立,欲望被充分肯定,然而在其中人們并沒(méi)有找到曾經(jīng)希望的那種審美烏托邦,反而看到的是欲望橫流下的價(jià)值困境;對(duì)于更接近啟蒙的一群人來(lái)說(shuō),他們“一方面致慨于商業(yè)化社會(huì)的金錢(qián)至上、道德腐敗和社會(huì)無(wú)序,另一方面卻不能不承認(rèn)自己已經(jīng)處于曾經(jīng)作為目標(biāo)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之中。中國(guó)的現(xiàn)代化或資本主義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是以啟蒙主義作為它的意識(shí)形態(tài)基礎(chǔ)和文化先鋒的。正由于此,啟蒙主義的抽象的主體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題在批判毛的社會(huì)主義嘗試時(shí)曾經(jīng)顯示出巨大的歷史能動(dòng)性,但是面對(duì)資本主義市場(chǎng)和現(xiàn)代化過(guò)程本身的社會(huì)危機(jī)卻顯得如此蒼白無(wú)力”。任何有效的批判都必須在否定的同時(shí)做出某種形式的肯定,然而現(xiàn)代性思想意欲批判的對(duì)象正是兩種現(xiàn)代性自身在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演進(jìn)的結(jié)果,現(xiàn)代性思想對(duì)其自身結(jié)果的批判實(shí)際上都必將因同時(shí)否定了自身而失去任何肯定性因素。
這種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的批判困境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必然會(huì)在價(jià)值觀(guān)領(lǐng)域引發(fā)變革,但是價(jià)值觀(guān)變革總是帶有某種滯后性,因而這種變革不至于如此迅速以至于1992年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被正式確立,1993年就爆發(fā)了“人文精神大討論”。“商品理性”的確立以及現(xiàn)代思想對(duì)之批判乏力的狀況從根本上來(lái)講存在于1980年代本身的現(xiàn)代性危機(jī)之中。自“五四”以來(lái),我國(guó)的現(xiàn)代性批判實(shí)際上一直都是依靠“浪漫”與“啟蒙”二者之間那種對(duì)立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作為追求主體性的自我確證和自我認(rèn)同的現(xiàn)代性工程之一個(gè)重要而獨(dú)具特色的組成部分,浪漫主義一方面在審美和藝術(shù)領(lǐng)域內(nèi)推進(jìn)和確立了現(xiàn)代性的主體性原則(因而在初期的浪漫派中不乏自由主義的傾向),但另一方面,當(dāng)以理性主體為旨?xì)w的現(xiàn)代性發(fā)展到了要扼殺人的主體性時(shí),浪漫主義又反戈一擊,擎起了審美現(xiàn)代性的大旗,從而造成了現(xiàn)代性最終的分裂。”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無(wú)論是浪漫的還是啟蒙的現(xiàn)代性書(shū)寫(xiě)都開(kāi)始被質(zhì)疑。“新生代”詩(shī)人感慨朦朧詩(shī)派過(guò)于浪漫,“要從朦朧走向現(xiàn)實(shí)。”而在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新寫(xiě)實(shí)”的一派則不滿(mǎn)于啟蒙價(jià)值的抽象性和浪漫的幻想性,試圖還原現(xiàn)實(shí)作為某種“真實(shí)”,“新寫(xiě)實(shí)小說(shuō)與以往的寫(xiě)實(shí)小說(shuō)比較起來(lái)看最為突出的一個(gè)美學(xué)特點(diǎn)就是審美態(tài)度的客觀(guān)化,追求生活的原色魅力。以往的寫(xiě)實(shí)小說(shuō)當(dāng)然也注重作品的客觀(guān)性特征,但客觀(guān)的生活內(nèi)容中明顯地呈現(xiàn)出作者的思想傾向性。對(duì)于新寫(xiě)實(shí)小說(shuō)來(lái)講他們則把自己的傾向性和價(jià)值趨向盡量地隱藏于生活和人物形象之中,使創(chuàng)作主體的思想情感避免對(duì)生活原相的過(guò)多介入。”在一定意義上來(lái)講,保持與對(duì)象的距離,隱藏自己,不表達(dá)價(jià)值判斷,實(shí)則就是對(duì)啟蒙的反思;而避免流露出直接而熱烈的感情實(shí)則就是對(duì)浪漫的質(zhì)疑。
中國(guó)1980年代中后期的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困境往往被理解為價(jià)值觀(guān)的缺失,在“去政治化”之后人們不再需要反抗政治的教條,于是價(jià)值觀(guān)領(lǐng)域便由于政治的退場(chǎng)和新價(jià)值觀(guān)未能及時(shí)跟進(jìn)而形成了空白。這種論斷實(shí)際上是片面的,因?yàn)楝F(xiàn)代性?xún)r(jià)值觀(guān)的確立本身就是批判的結(jié)果,在西方,人的自由實(shí)際上根植于對(duì)教會(huì)權(quán)力的批判,而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性則一方面在20世紀(jì)80年代之前表現(xiàn)為對(duì)帝國(guó)主義和封建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在80年代之后表現(xiàn)為對(duì)政治階級(jí)論的批判。這種在批判中確立價(jià)值的方式實(shí)際上正是現(xiàn)代性以進(jìn)步為旨?xì)w的特質(zhì)。因此1980年代中后期思想界表現(xiàn)出的那種批判乏力實(shí)際上是由于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終于為自己謀到了自律,其自身此時(shí)成了待被批判的對(duì)象。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的乏力并不表明現(xiàn)代性進(jìn)程發(fā)生了倒退。它的乏力實(shí)則正好表明現(xiàn)代性已經(jīng)在中國(guó)充分展開(kāi)了自身,從辯證法上來(lái)講,也正是在這一時(shí)刻,一種話(huà)語(yǔ)模式中的固有矛盾才會(huì)將自身凸顯出來(lái)。在此意義上,“后啟蒙”時(shí)代與自“五四”以來(lái)中國(guó)歷史之間的關(guān)系并不是斷裂的,“后啟蒙”本身就是“五四”以來(lái)現(xiàn)代性訴求的充分展開(kāi)。“后啟蒙”時(shí)代的問(wèn)題在“五四”時(shí)期并非沒(méi)有,在劉吶鷗等人對(duì)上海洋場(chǎng)的書(shū)寫(xiě)中,在郁達(dá)夫的自敘傳浪漫主義中,在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中,現(xiàn)代性的困境都同樣存在,只不過(guò)它們只有到了“后啟蒙”這樣一個(gè)現(xiàn)代性的高峰時(shí)期才會(huì)現(xiàn)實(shí)地、強(qiáng)烈地集中迸發(fā)。
五、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的內(nèi)部與外部批判
我國(guó)理論界對(duì)現(xiàn)代性困境的解決大體分為兩個(gè)方向:一種是繼續(xù)尋求在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內(nèi)部尋求批判發(fā)展的可能性,它具體表現(xiàn)為理論家求助于對(duì)各種各樣的“中國(guó)性”來(lái)作為核心價(jià)值觀(guān),以補(bǔ)充的形式批判經(jīng)濟(jì)理性的抽象;另一種則是求助于現(xiàn)代性之外的話(huà)語(yǔ)體系來(lái)對(duì)現(xiàn)代性做出外部批判,它具體表現(xiàn)為理論家們?cè)噲D走出現(xiàn)代性,從對(duì)某種具有普適性的核心價(jià)值觀(guān)的追求走向價(jià)值多元。
就第一種方向而言,“中國(guó)性”實(shí)際上是一種與政權(quán)保持距離的政治性,具體來(lái)說(shuō),這個(gè)大方向?qū)嶋H上是要以“文化政治”的方式在保持與政權(quán)意識(shí)形態(tài)之間存在必要的距離的同時(shí),在文化與國(guó)家或民族而非政權(quán)之間建立起更加緊密聯(lián)系,重建一種“新的政治性”,以此來(lái)使文化話(huà)語(yǔ)重新具有現(xiàn)代性效力。這一路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對(duì)“主旋律”的重寫(xiě)。新的“主旋律”文藝與階級(jí)政治下的文藝書(shū)寫(xiě)之間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前者對(duì)“階級(jí)”和政權(quán)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性質(zhì)保持距離。在諸如《建國(guó)大業(yè)》《建軍大業(yè)》《戰(zhàn)狼》這樣的電影制作中,“民族敘事”往往取代了過(guò)去的“階級(jí)敘事”,換言之,“主旋律”實(shí)際上書(shū)寫(xiě)的是“啟蒙”而非“革命”,是“現(xiàn)代性”而非“革命史”,或者換一種說(shuō)法,是把“革命”納入“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啟蒙”話(huà)語(yǔ)之中,消解了其中的階級(jí)革命與斗爭(zhēng)的獨(dú)立價(jià)值。
這種“主旋律”敘事策略出現(xiàn)的原因是復(fù)雜的,從最根本上來(lái)講它實(shí)際上是一種對(duì)1980年代以來(lái)那種“去政治化”的文化現(xiàn)代性的延續(xù)。從一方面來(lái)看,這些“主旋律”電影的意識(shí)形態(tài)敘事是“去政治化”的,因?yàn)椤半A級(jí)”在今天的社會(huì)語(yǔ)境中實(shí)際上已經(jīng)被轉(zhuǎn)化為了“階層”,這種轉(zhuǎn)變開(kāi)始于1980年代,完成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建立,“在今天,20世紀(jì)的政治邏輯已經(jīng)退潮,知識(shí)分子大多以實(shí)證主義的方式看待中國(guó)社會(huì)的分層及其政治。不但右翼,甚至也包括一些左翼,都相信在20世紀(jì),相對(duì)于農(nóng)民和其他社會(huì)階層,工人階級(jí)成員在中國(guó)政治生活中所占據(jù)的位置非常有限,資產(chǎn)階級(jí)尚不成熟,因此,現(xiàn)代革命不可能具有社會(huì)主義的性質(zhì),工人階級(jí)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領(lǐng)導(dǎo)階級(jí)。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構(gòu)了中國(guó)革命的政治原理。這套實(shí)證主義的政治觀(guān)點(diǎn)共享的是一個(gè)結(jié)構(gòu)性的、本質(zhì)主義的‘階級(jí)’概念,而不是基于對(duì)資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分析而產(chǎn)生的能動(dòng)的‘階級(jí)’概念。”這種對(duì)“階級(jí)”概念的“去政治化”導(dǎo)致當(dāng)前的敘事不再能依靠原有那種階級(jí)斗爭(zhēng)的邏輯,革命史也因此由斗爭(zhēng)史轉(zhuǎn)化為了民族國(guó)家的“啟蒙史”或“救亡史”。這種“主旋律”書(shū)寫(xiě)其中也包含著一種對(duì)資本的肯定,它們雖然在內(nèi)容上并沒(méi)有明確的贊頌資本,但是這些作品本身在制作過(guò)程中就有賴(lài)于資本的運(yùn)作,其中既包括對(duì)大眾傳媒的使用又包括對(duì)海外投資的吸引,在這種情況下的“主旋律”便更不可能是斗爭(zhēng)性的,它所觸及的傳統(tǒng)革命敘事是話(huà)題性的而非問(wèn)題性的,它必須同時(shí)對(duì)國(guó)族敘事的要求和資本的要求做出回應(yīng)。從另一方面來(lái)看,這種“中國(guó)性”也折射出一種面對(duì)全球化的中國(guó)焦慮。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浪潮下中國(guó)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世界,加入現(xiàn)代世界體系和全球化浪潮之中,這在文化領(lǐng)域中意味著西方文化也會(huì)一夜之間隨著資本涌入一并前來(lái)。國(guó)家不斷在文化領(lǐng)域中放權(quán),而西方思想則不斷涌入,這就在中國(guó)思想界形成了一個(gè)中國(guó)和西方交匯之處的公共空間,經(jīng)濟(jì)上的中間階層的城市中產(chǎn)群體便大多處于其中。在這樣的公共空間中,他們實(shí)際上對(duì)于中國(guó)和西方都不能有效認(rèn)同,換句話(huà)說(shuō),他們既有民族性也有世界性,如有的學(xué)者所說(shuō),“如果他們是‘民族主義者’,那么規(guī)定他們這種民族主義的,既有私有產(chǎn)權(quán)的因素,也有集體歸屬感的因素;既有世界主義的渴望,也幾乎宿命般地認(rèn)識(shí)到了世界主義的局限:既是一種對(duì)于歐美早先歷史時(shí)期所實(shí)現(xiàn)的民族主義的理性化效仿,也希望在認(rèn)同已變得均等而單調(diào)的時(shí)代里維持某種‘中國(guó)性’。”
除了創(chuàng)作領(lǐng)域的“主旋律”敘事之外,我國(guó)文藝?yán)碚摻缬执蠖鄬⒁环N新的現(xiàn)代性寄希望于以“傳統(tǒng)”來(lái)建設(shè)“中國(guó)性”上。這一類(lèi)思想背后的邏輯在于:中國(guó)的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失去效力的根本原因在于照搬西方現(xiàn)代性理論,要想走出困境我們必須對(duì)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進(jìn)行中國(guó)化。從文化傳統(tǒng)出發(fā),甘陽(yáng)提出了“通三統(tǒng)”理論,所謂“通三統(tǒng)”就是要把“改革傳統(tǒng)”“毛澤東思想傳統(tǒng)”和“中國(guó)儒家傳統(tǒng)”結(jié)合在一起。繼承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化之間表面上是一種對(duì)立,然而正如汪暉指出的那樣,從“五四”時(shí)期以來(lái),現(xiàn)代性就一直試圖與傳統(tǒng)建立起某種聯(lián)系,其原因在于傳統(tǒng)雖然位于時(shí)間上的過(guò)去,然而在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中卻能夠通過(guò)建立一種線(xiàn)性時(shí)間的完整性,來(lái)“將文化放置在與未來(lái)的時(shí)間關(guān)系之中,從而在方法論上自然地顯示出文化進(jìn)化論的前提:文化上的長(zhǎng)期的、方向性的變化,表示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自簡(jiǎn)單向復(fù)雜發(fā)展的過(guò)程。把東西文化的差異與現(xiàn)代化相關(guān)聯(lián)的結(jié)果之一,就是將文化、特別是傳統(tǒng)視為社會(huì)變遷及其方向的主要?jiǎng)恿蜎Q定因素”。傳統(tǒng)提供的那種現(xiàn)代性敘事所必需的那種線(xiàn)性連續(xù)性在此意義上非常可能成為現(xiàn)代性繼續(xù)前行的動(dòng)力。此論的核心邏輯在于中國(guó)現(xiàn)代性理論之所以不完善,是由于我們切斷了與傳統(tǒng)之間的聯(lián)系,而傳統(tǒng)恰恰能夠幫助我們完善現(xiàn)代性的話(huà)語(yǔ)邏輯,它既能夠?yàn)楝F(xiàn)代性建設(shè)賦予一個(gè)開(kāi)端,也能通過(guò)歷史的邏輯為現(xiàn)代性指明一個(gè)未來(lái)。
這種現(xiàn)代性?xún)?nèi)部的批判能否具有效力依然是成問(wèn)題的,因?yàn)槿绻f(shuō)現(xiàn)代性困境本身即是現(xiàn)代性自身發(fā)展的結(jié)果的話(huà),那么這種理論的內(nèi)部批判并沒(méi)有在現(xiàn)代性自我展開(kāi)的必然性上來(lái)對(duì)之進(jìn)行理解,希望重塑某種價(jià)值核心的思想總是在其背后對(duì)過(guò)去的“彎路”進(jìn)行了預(yù)設(shè),仿佛我們?cè)?jīng)偏離了現(xiàn)代性的理想,只要重新走上正軌,現(xiàn)代性的問(wèn)題就會(huì)消失。這實(shí)則依然延續(xù)了過(guò)去“新啟蒙”理論那種要恢復(fù)某種啟蒙之正統(tǒng)性的思路。張旭東將此種思路批判為一種依靠“回歸本位”來(lái)獲得虛假穩(wěn)定的理論造神,“與八十年代的憂(yōu)患意識(shí)和開(kāi)放心態(tài)相比,九十年代的文化生活似乎帶有更多的保守性和封閉性。八十年代所特有的‘一切都四散了,再也沒(méi)有中心’(葉芝,《重返拜占庭》)那樣的現(xiàn)代主義‘震驚’體驗(yàn)在九十年代的今天變?yōu)榱朔N種關(guān)于‘本位’或回歸本位的幻想,仿佛‘欲望’、‘國(guó)學(xué)’、‘個(gè)人’、‘市場(chǎng)’、‘大眾’、‘學(xué)術(shù)史’、‘寫(xiě)作’、‘自由主義’或‘中華性’之類(lèi)的符號(hào)本身可以替代對(duì)這些出現(xiàn)于此時(shí)此地的歷史現(xiàn)象和社會(huì)神話(huà)的分析和思考,仿佛對(duì)某種意識(shí)形態(tài)的本體論膜拜不但保證了存在的穩(wěn)定性和恒常性,而且還顯示出思想的成熟。”這種批判是中肯的,因?yàn)槿绻f(shuō)對(duì)價(jià)值觀(guān)的重塑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現(xiàn)代性問(wèn)題的話(huà),那么在那些被視為啟蒙現(xiàn)代性未曾斷裂的歐美國(guó)家中,就不可能出現(xiàn)什么現(xiàn)代性問(wèn)題。正是在這些現(xiàn)代性的自我展開(kāi)更為充分的國(guó)家中,其現(xiàn)代性的弊端表現(xiàn)得尤為顯著;如果說(shuō)中國(guó)存在一種價(jià)值觀(guān)領(lǐng)域的缺失的話(huà),那么在西方高度現(xiàn)代化了的社會(huì)中當(dāng)代價(jià)值觀(guān)的解體則更為明顯。
對(duì)于現(xiàn)代性的外部批判在文藝?yán)碚摻缰饕性趯?duì)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模式進(jìn)行突圍的多種理論嘗試上,理論界最主要的突圍方式就是通過(guò)反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研究上的現(xiàn)代性自律化傾向來(lái)建立非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種,其一是對(duì)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譯介,其二是文化研究中“新歷史主義”的興起,其三是從屬于后現(xiàn)代思潮的“身體轉(zhuǎn)向”。
自1980年代以來(lái)我國(guó)理論界一直在嘗試建立起理論自覺(jué)或自律,這在當(dāng)時(shí)是出自一種對(duì)政治理性的專(zhuān)斷進(jìn)行批判的需要,學(xué)科自律意味著學(xué)科的“去政治化”。當(dāng)現(xiàn)代性開(kāi)始接受質(zhì)疑的時(shí)候,這種學(xué)科自律也就出現(xiàn)了問(wèn)題。薩義德就曾認(rèn)為知識(shí)分子應(yīng)該式“特立獨(dú)行的人,能向權(quán)勢(shì)說(shuō)真話(huà)的人”,他們“尤其必須的是處于幾乎永遠(yuǎn)反對(duì)現(xiàn)狀的狀態(tài)”。這種獨(dú)立性正是學(xué)術(shù)自律提供的,然而伊格爾頓又從另外的方向指出,知識(shí)分子要想保持某種現(xiàn)代性,他們又必須遠(yuǎn)離那種純粹的學(xué)術(shù)自律:“對(duì)知識(shí)分子最簡(jiǎn)潔的定義是:知識(shí)分子是學(xué)究的對(duì)立面。……知識(shí)分子關(guān)注的是思想對(duì)整個(gè)社會(huì)和人性的影響。因?yàn)樗麄兲接懙氖顷P(guān)于社會(huì)的、政治的和形而上學(xué)的基本問(wèn)題,他們必須熟諳諸多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內(nèi)容。”在中國(guó)同樣也是如此,一方面文學(xué)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自律確實(shí)為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開(kāi)辟出了一片不受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干擾的獨(dú)立場(chǎng)域,這使得文學(xué)研究通過(guò)某種相對(duì)獨(dú)立性而獲得了批判距離;從另一方面來(lái)看,學(xué)術(shù)自律又和“純文學(xué)”一樣,在其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時(shí)候,將由于與社會(huì)之間的距離過(guò)遠(yuǎn)而再次喪失自己的批判性。
在“后啟蒙”時(shí)代,在文藝上的自律分化成了兩條:其一是延續(xù)1980年代的“去政治化”路徑的文藝自律,試圖以文藝來(lái)迎合商品理性,文藝變成了“單維度的”,其目的只是為了讓自身被消費(fèi)掉。伊格爾頓曾有這樣的論述:“作為一種理論范疇的美學(xué)的出現(xiàn)與物質(zhì)的發(fā)展過(guò)程緊密相連。文化生產(chǎn)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早期階段通過(guò)物質(zhì)的生產(chǎn)成為‘自律的’——自律于傳統(tǒng)上所承擔(dān)的各種社會(huì)功能。一旦藝術(shù)品成為市場(chǎng)中的商品,它們就不再專(zhuān)為人或物而存在,隨后它們便能被理性化,……新的美學(xué)話(huà)語(yǔ)想要詳細(xì)論述的就是這種自律性或自指性(self-referentiality)。”如果想要在一種話(huà)語(yǔ)中將其他話(huà)語(yǔ)的統(tǒng)治終結(jié),就必須使它以自指的方式形成相對(duì)于另一種話(huà)語(yǔ)的獨(dú)立性,啟蒙理性對(duì)主體性的確認(rèn)亦是試圖以理性體系來(lái)讓主體擺脫既有的各種話(huà)語(yǔ)權(quán)力,形成一種自我確認(rèn)的獨(dú)立方式,理性本身就是一種自指性。伊格爾頓所言的情況在我國(guó)也有相似的表征,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特定時(shí)期面對(duì)政治這個(gè)龐然大物時(shí),審美與啟蒙現(xiàn)代性的暗合之處。從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角度來(lái)說(shuō),藝術(shù)商品化其實(shí)和國(guó)家從文化領(lǐng)域中大幅度退出,出版業(yè)市場(chǎng)化,作協(xié)不再為作家提供能夠維持生活水平的薪酬等變化有關(guān),文學(xué)商品化實(shí)際上是文化領(lǐng)域的職能徹底從意識(shí)形態(tài)性向社會(huì)性轉(zhuǎn)變的一個(gè)表征。
其二是試圖以“純文學(xué)”“純藝術(shù)”“純審美”來(lái)抵抗市場(chǎng)邏輯,這種通過(guò)堅(jiān)守某種“文學(xué)性”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批判同樣也是一種自律,這應(yīng)該說(shuō)是1980年代新浪漫主義的延續(xù)。只不過(guò),“到了90年代以后,文藝自主性訴求的批判對(duì)象發(fā)生了微妙卻重要的變化。自主性訴求本來(lái)就有兩個(gè)否定的對(duì)象,一是政治權(quán)力,二是市場(chǎng)/商業(yè)壓力。如果說(shuō)80年代文藝學(xué)自主性訴求要求擺脫其政治奴仆的地位;那么,由于語(yǔ)境的變化,90年代文藝自主性訴求的批判對(duì)象已轉(zhuǎn)化為市場(chǎng)/商業(yè)。”就是說(shuō),新時(shí)期以來(lái),文藝的解放與自律曾經(jīng)試圖通過(guò)商品化、市場(chǎng)化而遠(yuǎn)離政治來(lái)實(shí)現(xiàn),之后,文藝又不得不通過(guò)逐出文藝的商品性而獲得解放與自律。在 1980年代,強(qiáng)調(diào)審美的主要意圖是打破那種外部性,重新關(guān)注人的內(nèi)部方面,所謂“向內(nèi)轉(zhuǎn)”其實(shí)是一種補(bǔ)充。審美針對(duì)的是原來(lái)不講審美、不講形式、不講個(gè)性之類(lèi)的傾向。1990年代以來(lái),那種對(duì)“文學(xué)性”的強(qiáng)調(diào)其實(shí)是意在以純文學(xué)的內(nèi)部封閉性來(lái)對(duì)抗那種經(jīng)濟(jì)理性。準(zhǔn)確地說(shuō),1980年代的“新浪漫主義轉(zhuǎn)向”并沒(méi)有導(dǎo)致一種審美自律,它以審美的方式表達(dá)的卻是它所反叛的對(duì)象的主題,即現(xiàn)代化;1990年代審美話(huà)語(yǔ)的自律性,則產(chǎn)生于它同它所反叛的對(duì)象站在了絕對(duì)的對(duì)立面,審美從一種“完整性”變成了“絕對(duì)的區(qū)別性”,試圖以一種自律性絕對(duì)地與現(xiàn)實(shí)保持距離。
因此在1990年代,對(duì)現(xiàn)代性審美、藝術(shù)自律的研究同時(shí)要對(duì)上述兩種自律性做出回應(yīng):一方面它必須在面對(duì)市場(chǎng)邏輯之時(shí)重提審美,另一方面它又必須在面對(duì)美學(xué)、藝術(shù)性的自律時(shí)重提現(xiàn)實(shí)。針對(duì)這兩種訴求,“新左派”試圖通過(guò)對(duì)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譯介來(lái)構(gòu)成批判路徑,既批判商品理性和政治理性對(duì)社會(huì)理性的“單維化”,又強(qiáng)調(diào)借由先鋒藝術(shù)中依然保留審美性人們可以形成一種“新感性”,并以此來(lái)打破政治理性、工具理性的桎梏。這是一種對(duì)審美與政治經(jīng)濟(jì)批判相結(jié)合的審美政治學(xué)。在這種批判形式中依然保留了某種現(xiàn)代性,因?yàn)樗廊槐A糁鴮?duì)某一政治烏托邦的訴求,然而在話(huà)語(yǔ)形式上,它又是反現(xiàn)代性的,它或是強(qiáng)調(diào)理性與感性并重,或是試圖打破這種二元對(duì)立。但是,把打破工具理性的任務(wù)交給審美,甚至交給先鋒藝術(shù)和邊緣文化,似乎因距離社會(huì)大眾過(guò)于遙遠(yuǎn)而批判乏力,建設(shè)無(wú)效。
對(duì)于文化研究來(lái)說(shuō),以其中的“新歷史主義”為例,它雖然強(qiáng)調(diào)外部性,但是卻不強(qiáng)調(diào)政治性,因此它徹底走出了現(xiàn)代性對(duì)某種核心價(jià)值的訴求。“新歷史主義”在話(huà)語(yǔ)模式上“化簡(jiǎn)單二元對(duì)立為復(fù)雜二元對(duì)立或二元復(fù)合狀態(tài),價(jià)值判斷趨向于相對(duì)化、內(nèi)在化和隱蔽化”。它強(qiáng)調(diào)以文本的外部性來(lái)打破現(xiàn)代性自律,因而它要求研究者“不斷返回個(gè)別人的經(jīng)驗(yàn)與特殊環(huán)境中去,回到當(dāng)時(shí)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對(duì)的物質(zhì)必需與社會(huì)壓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小部分具有共鳴性的文本上”。然而同時(shí),“新歷史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不同,他們沒(méi)有那種強(qiáng)迫自己去爭(zhēng)取協(xié)調(diào)性的名義壓力。它甚至可能堅(jiān)稱(chēng),歷史的好奇心將會(huì)采取獨(dú)立于政治考慮之外的發(fā)展道路;而在它對(duì)文學(xué)實(shí)施歷史化研究的愿望背后,并不存在任何種類(lèi)的政治動(dòng)機(jī)。”換言之,“新歷史主義”只是在謀求對(duì)文本的豐富性進(jìn)行理解,而對(duì)這種理解是否具有某種進(jìn)步性的價(jià)值,是否能夠?qū)δ撤N主體性進(jìn)行確立并不關(guān)心。
最后,對(duì)于后現(xiàn)代的“身體轉(zhuǎn)向”來(lái)說(shuō),它主要反對(duì)的是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建立在理性和感性上的主體論。“身體”絕非主體,“主體”這一范疇中總是同時(shí)包含著自由等價(jià)值的預(yù)設(shè)。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對(duì)于價(jià)值的判定又總是具有排他性,肯定一種價(jià)值的同時(shí)就必然要將所有其他價(jià)值排除在外。一方面,“身體”反對(duì)任何依靠話(huà)語(yǔ)邏輯的價(jià)值建構(gòu),“身體”維度的豐富性總是溢出話(huà)語(yǔ)表述之外;另一方面“身體”又長(zhǎng)期以來(lái)深受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邏輯的桎梏,人類(lèi)歷史“是身體遭受懲罰的歷史,是身體被納入生產(chǎn)計(jì)劃和消費(fèi)目的中的歷史,是權(quán)力讓身體成為消費(fèi)對(duì)象的歷史,是身體受到贊美、欣賞和把玩的歷史。身體從它的生產(chǎn)主義牢籠中解放出來(lái),但是,今天,它不可自制地陷入了消費(fèi)主義的陷阱。一成不變地貫穿著這兩個(gè)時(shí)刻的,就是權(quán)力(它隱藏在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實(shí)踐中)對(duì)身體精心而巧妙的改造”。“身體”既包含了現(xiàn)代性的困境,又在其中保留著溢出現(xiàn)代性之外的豐富性,對(duì)于身體的強(qiáng)調(diào),一方面對(duì)現(xiàn)代性主客二分的話(huà)語(yǔ)模式進(jìn)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又對(duì)某種由話(huà)語(yǔ)邏輯規(guī)定的核心價(jià)值進(jìn)行了質(zhì)疑。但是,其難題在于面對(duì)強(qiáng)大的社會(huì)生產(chǎn)邏輯,“身體轉(zhuǎn)向”可能嗎?身體能夠逃脫社會(huì)權(quán)力的掌控,“從它的生產(chǎn)主義牢籠中解放出來(lái)”嗎?
對(duì)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進(jìn)行質(zhì)疑的理論都存在著一個(gè)相同的困境,它們雖然都以不同的方式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現(xiàn)代性話(huà)語(yǔ)的批判,但是不可否認(rèn)的是,從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上看,中國(guó)目前依然處于一個(gè)由商品理性主宰的“后啟蒙”時(shí)代,這一時(shí)期帶有強(qiáng)烈的現(xiàn)代性特征,它本身就是我國(guó)現(xiàn)代性進(jìn)程的必然結(jié)果。無(wú)論我們?nèi)绾卧诶碚撋蠈?duì)現(xiàn)代性進(jìn)行批判,我們都無(wú)可否認(rèn)一個(gè)事實(shí):如果說(shuō)我們生活中的困境源于現(xiàn)代性,那么同樣使我們當(dāng)下生活能夠成為一種可能的也是現(xiàn)代性。一種理論上的批判必須同時(shí)具備兩方面的特質(zhì)才能算得上是有效的,其一是要揭示現(xiàn)代性的困境,并對(duì)它進(jìn)行反撥,這一點(diǎn)在大多數(shù)理論中已經(jīng)有了不同程度的實(shí)現(xiàn);其二,更為重要的是,一種對(duì)現(xiàn)代性的批判必須能夠同時(shí)在其中保留現(xiàn)代性在物質(zhì)財(cái)富生產(chǎn)和維持社會(huì)平穩(wěn)發(fā)展等方面的能量,并開(kāi)啟未來(lái)的可能之門(mén),否則這種批判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從目前來(lái)看,“后啟蒙”時(shí)代,中國(guó)現(xiàn)代性批判理論任重道遠(yuǎn),未來(lái)還有著很長(zhǎng)的待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