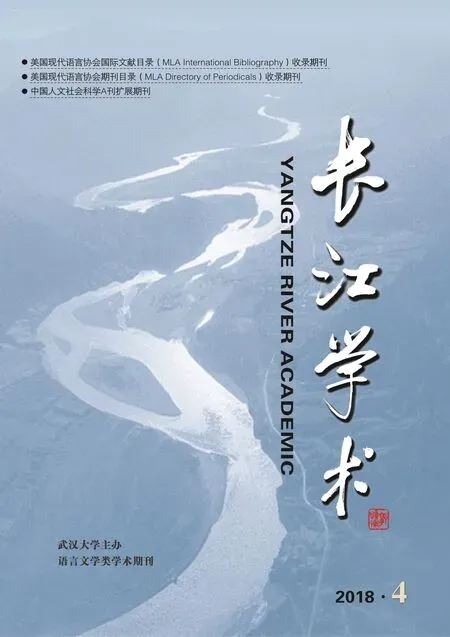論胡適新詩理論中的跨界式敘事
——從“作詩須得如作文”的詩學命題談起
姜玉琴
(上海外國語大學 文學研究院,上海 200439)
一、承上啟下的“作文如作詩”
相對于古代的抒情傳統,確切說是以抒情為主體的傳統,胡適論詩明顯是劍走偏鋒:他擱置了抒情這一因素,其實也就意味著擱置了整個中國詩歌傳統的主線,從非主流視角,即“寫實”的角度切入新詩理論的構建中,提倡“作詩須得如作文”。也就是說,主張要像作“文”一樣來作“詩”。
“文”歷來是不同于“詩”的。《說文解字》對“文”的解釋是:“文,錯畫也。象交文。”而對“錯畫”的闡釋是:“交錯而畫之,乃成文也。”“文”就是要一筆一畫地反復“描畫”,“描畫”的目的就是要盡可能“像”。無疑,“文”強調的是寫實性。假如把這樣一種思想引申到文學創作中,自然在美學上彰顯的就是描畫、刻畫之功能。事實上,胡適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描畫的層面上來理解與接受“文”的。正如他以傳統的、最為缺少“描畫”的寫景詩為例說:“就是寫景的詩,也須有解放了的詩體,方才可以有寫實的描畫。”顯然,胡適引“文”入“詩”,就是把“文”的“寫實的描畫”功能引入詩歌中。如果說傳統詩歌主要是沿著抒情這個維度發展、構建起來的,新詩的發展與構建則開始轉向了從“文”中尋找支撐。
胡適這種要求詩歌“寫實的描畫”的思維方式,與以往那種習慣從玄虛、抽象的抒情層面來言說詩歌的傳統有著本質性差異。或許正是由于挑戰了傳統詩歌的審美規范和創作條例,所以自從胡適提出這個新詩寫作的命題始,就遭受到眾多新詩從業者的反對與攻擊。如穆木天就指認胡適為“罪人”:“中國的新詩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胡適說:作詩須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錯。”直到今天,新詩研究者們對胡適的這個“作詩須得如作文”的理論主張依舊充滿偏見:“這個理論拋棄了白話詩的詩性,致使新詩先天不足。此后,大量用白話的非詩也大量產生……”“作詩須得如作文”到底是新詩發展中的一塊“絆腳石”,還是一種新的美學訴求在“五四”時代的崛起?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返回到肇始該理論的時代語境中。
1916年,還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圍繞“文學革命”之想法寫了一首長詩,送給同樣在美國留學的好友梅光迪。由于此時的胡適正被“古人作古,吾輩正須求新”的激情激蕩著,所以為了達到“求新”之目的,在該首詩歌中使用了不少外國字的譯音。胡適這一明顯為“新”而“新”的舉動,引起了他們兩人的另一位好友,也在美國讀書的任叔永的“恥笑”。他把胡適這首詩中的外國字一一挑選出來,編成了一首諸如“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的游戲詩,回贈給胡適。胡適從該詩中讀出了好朋友的嘲諷之意——諷刺他寫詩不守規矩,胡亂使用不該使用的文字。以今天的眼光看,胡適這樣做,一方面有搗亂成分,另一方面更有出于“實驗”的考慮。說其搗亂,是因為胡適有意采用這種“越位”手法對禁錮傳統舊詩詞發展的清規戒律予以沖擊;說其有出于“實驗”的考慮,是因為他當時的確有把過去那些不能入詩的文字引入詩歌的想法,即要擴大詩歌使用的詞匯量,不但雅文字可以入詩,就是俗文字也可以入詩。事實上,他的這一反叛本身就是對“詩界”發起的進攻。
他的這番苦心非但沒有得到好友們的理解,反而引來了一番訕笑。或許胡適覺得有必要再解釋一下,或許也是出于爭取“同道人”的考慮,他在接到了任叔永的諷刺詩后,又提筆寫下了另一首詩:“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啄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儒腐生。”從這首詩中不難窺探出“作詩須得如作文”出籠的前因后果:胡適認為中國舊詩詞“啄鏤粉飾喪元氣”,意思是這些詩看上去貌似詩,其實早已喪失了“元氣”,只是憑靠對語言文字的雕琢和粉飾勉強存在而已。正是基于這一估價——舊體詩詞已經淪落成了偽詩,胡適才號召伙伴們起來“革命”,不要再作“儒腐生”。
從這樣一個去舊更新的框架出發,可以說“作詩須得如作文”并非是胡適隨口一說的一句話,相反是建立在通盤考慮的基礎上,即作為“詩界革命”的一項基本策略而有意識地提出來的。這并非有意拔高“作詩須得如作文”的作用,胡適在20世紀30年代所寫下的一篇文章中曾回顧和交代過這件事。他說:“在這首短詩里,我特別提出了‘詩國革命’的問題,并且提出了一個‘要須作詩如作文’的方案,從這個方案上,惹出了后來做白話詩的嘗試。”話不多,邏輯線索卻清晰地呈現出來:“詩國革命”——“要須作詩如作文”——開啟了白話詩創作的閘門。在這個邏輯鏈條中,“詩國革命”是目標,“要須作詩如作文”是實現目標的方案和手段,由這個方案、手段引發出了中國白話詩的創作大潮。而位于這一邏輯鏈條中心的環節無疑就是“要須作詩如作文”。
這說明“要須作詩如作文”或者“作詩須得如作文”,看似沒有太多的含金量,其實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它在中國詩歌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往前,它繼承和推進了近代以來的詩歌革新精神,一舉搗毀了中國上千年的詩歌傳統;往下,它發揚光大并奠定了白話新詩的創作傳統。自此以后,中國詩歌便走向了一條像“文”一樣自由發展的道路。也就是說,在這個看似直白而簡單的命題里,其實蘊藏著一系列新的美學訴求,這個訴求里既有破舊的成分,又有立新的意義。在那個缺乏橋梁的年代,是它把舊體詩詞與新詩創作架通起來,開辟出了一段新的詩歌歷史。
二、以變法圖強為目的的詩學理論的賡續與超越
胡適的朋友們顯然并未意識到潛存于該詩學理論中的玄機。其表現是,他們一方面對“我輩不作儒腐生”的反叛精神深表贊同,另一方面又對“詩國革命”的策略——“作詩須得如作文”的倡議懷有強烈的異議。言辭最激烈的當屬梅光迪,他直截了當地與胡適展開商榷:“足下謂詩國革命始于‘作詩如作文’,迪頗不以為然。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Poetic 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于詩,即謂之革命,則不可也。……一言以蔽之,吾國求詩界革命,當于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詩,即謂之革命……以其太易易也。”梅光迪并不反對胡適要對“詩界”展開革命,但他堅決反對把“詩國革命”的起點設置在“作詩如作文”的框架上。其理由是,“詩”與“文”是兩種不同的文體,詩歌有詩歌的語言文字,散文有散文的語言文字,這兩種文字絕不可以混同。
梅光迪的這一說法看上去也有道理,“詩”就是“詩”,“文”就是“文”,如果模糊了二者間的界限,或者說“詩”完全像了“文”,“詩”也就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了。無疑,梅光迪是從兩種文體的差異性角度來反對“作詩須得如作文”的。梅光迪論詩有與胡適一致的地方,即二人都是把其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加以討論的。他們的分歧之處在于,梅光迪論詩的思路始終沒有離開詩——他試圖通過詩歌這一文體內部的改良來改革和完善詩歌,強調的是詩歌自身語言形式的革命和轉變。胡適則認為,單純從詩歌語言到詩歌語言是無法完成詩歌文體變革任務的,唯有采用“跨界”策略,也就是把“文”的一些文體優點吸收和采納到詩歌中來,才能從根本上實現“詩界革命”的任務設定。
由于兩人立論的基點不同,一個拘泥于詩歌自身,一個立志于把詩歌從封閉的體式中解放出來,所以面對梅光迪提出的“文之文字”不可入詩的說法,胡適沒有表現出應有的興致,只淡淡地應付了一句:“我不相信詩與文是完全截然兩途的”,“我的主張并不僅僅是‘文之文字’入詩”這么簡單。至于“詩”與“文”為何不是“截然兩途”,以及“文之文字”可以“入詩”這一行為自身有何更深刻內涵,胡適并無解釋,而是繼續沿著自己的思路前行:“今人之詩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耳。其中實無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勝質。”梅光迪與胡適商榷的是“詩之文字”就是“詩之文字”,意在強調要維護“詩之文字”的純潔性;胡適回答的則是“今人之詩”的文字、音韻和修辭都無比講究,一首首詩歌看上去像是貨真價實的詩歌,其實它們只是徒有空殼,揭去華麗的外表,內容都是空虛無比。胡適不但總結出了舊詩詞的弊病,還找出了造成這一弊端的原因——由“文”勝“質”,也就是形式大于內容之傳統所造成的。顯然,梅光迪是主張要捍衛“詩之文字”。在他看來,唯有如此,才能保證詩歌文體的獨立存在性;胡適則認為正是圍繞著“詩之文字”所形成的那些清規戒律,才導致了中國舊體詩的虛假繁榮——繁榮了外在的文字,空虛了內在的思想內容。因此說,胡適之所以堅決反對“詩之文字”,或者說他主張讓“文之文字”入詩,主要是出于詩歌內容的考慮。
當然,在胡適的“作詩須得如作文”理論構想中,也包含有一定的語言文字問題,如寫詩不避“文之文字”本身就是一個語言形式問題,只不過他的語言形式與梅光迪的語言形式不是同一個層面上的問題:梅光迪通過語言文字的差異性,說明“詩”不能越界到“文”中去;胡適則是要通過對“文之文字”的使用來解決“文”勝“質”的問題。無疑,“作詩須得如作文”的終極目的,是指向詩歌的內容,也就是“質”。對胡適而言,他就是要通過“文之文字”入詩的方式,實現對傳統舊詩詞內容的改換與替代。
思想內容第一,語言形式第二。辨別清楚這一點,對我們認識胡適的“作詩須得如作文”理論,乃至于整個“五四”時期的新詩理論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至少可以說明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新詩理論的出籠看似一個語言形式,即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變問題,其實不是,語言形式轉變的背后隱藏的是對西方現代社會的新思想、新觀念,甚至新科技的渴望與焦慮。換句話說,新詩理論工作者試圖借用一套西方先進的思想價值理念來瓦解已經腐朽了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舊思想體系。這樣一種強烈理念表明“五四”新詩運動首先是一場思想上的解放運動,其次才是一場有關于詩的審美運動。歸根結底,這場“詩”的運動主要是圍繞人的思想觀念的大變革展開的,其他都是為此服務的。
這種奉人的思想觀念為上,而不是人的審美觀念為本體的文學革命,其實并非“五四”新詩運動的首創,而是對以龔自珍、黃遵憲、梁啟超等所開創的以變法圖強為目的的近代詩學的一種賡續。當然,如果僅僅止步于賡續,胡適的新詩理論也就沒有走出近代詩學的認識水準。我們之所以說胡適的詩學理論具有現代性意義,就在于他在賡續中又予以了改造與推進。為了更好地說明它與近代“詩界革命”的關系,需要先回顧一下以變法圖強為目的這一詩學流脈的特質。
正如文學史所揭示的那樣,這一流脈肇始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這一特殊的歷史時空和時間節點注定了該詩學理論的特殊性:在“救亡”壓倒一切的前提下,一己的悲歡離合已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詩歌參與到民族救亡的社會思潮中來,并使之成為行之有效的宣傳武器。這樣一來,必將存在著一個詩歌文本如何與危機意識、“救亡”主題相契合的問題。抑或說,在當時的歷史境遇下,危機意識和“救亡”主題將以何樣的形式參與到詩歌文本的構建中來?
這無疑取決于當時的有識之士對社會危機的認知情形。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但其最直接的作用是,它在一舉擊毀中國封建主義價值體系的同時,也讓一直酣睡于“天朝上國”美夢中的知識分子認清了一個現實:我們這個所謂文明古國無論是在現代科技,還是人文思想方面都已遠遠地落后于西方諸國。而落后的直接后果就是要不斷遭受西方列強的欺侮與掠奪。所以奮起直追,由“弱”變“強”就成為了當時知識分子的不二選擇。為了盡快趕上西方文明的進程,他們制定了內外兩套行動方案。對內,高舉變革、革新的大旗,號召人們從封建主義思想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努力使自己變成一名“新人”,即通過“變”達到“強”的目的;對外,主張大力引入、借鑒和吸收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觀念,即試圖用西方的現代文明來改良、夯實我們的思想與精神,通過對他國的學習來達到最終能與西方列強相抗衡的目的。
以上兩大變法方針很快就從思想界傳播到了詩歌界,并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黃遵憲率先向自明代以來就在形式主義、擬古主義道路上愈行愈遠的舊詩壇開火,提出了“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后人,驚為古斑斕”的口號。黃遵憲在此為何采用“我手寫我口”和“俗語”“登簡編”的方式來顛覆傳統詩壇?道理很簡單,就是鼓勵詩人們不要被“傳統”束縛住手腳,要勇于發現和探索“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即強調創新的精神。當時思想界的另一重要人物梁啟超也是從創新性角度倡導詩歌創作的,他在《夏威夷游記》《飲冰室詩話》中多次呼吁詩人要開辟出“新意境”。黃遵憲、梁啟超都呼吁詩人們要在“古人”從未涉獵過的“物”和“境”中開辟出詩歌的新紀元。
顯然,“未有之物”也罷,“未辟之境”“新意境”也罷,最終指向的都是詩歌的內容。因為“未有之物”的“物”,“未辟之境”“新意境”中的“境”最終都與題材相關,而“題材”導向的則是內容。這說明黃、梁兩位都已經意識到,在詩歌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之間,前者才是當下最急需解決的問題——舊有的詩歌內容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新的社會歷史條件的需要,必須要有新的內容來取而代之。
然而,到底該取用何樣的新內容來取代舊內容?有關這一點,此時的他們似乎還尚未考慮清楚。這個問題一直拖宕到幾年后為配合戊戌變法而出現的“詩界革命”時,才算有了比較明確的目標。黃遵憲說,“掃詞章家一切陳陳相因之語,用今人所見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時勢,一寓之于詩。”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說:“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前者主張用“今人”的“所見之理”“所用之器”和“所遭之時勢”來取代傳統舊詩詞中的“陳陳相因之語”;后者主張今日的詩歌要從歐洲的“精神”和“思想”中尋找詩歌的新材料,以此來取代舊體詩中的落后之內容。無疑,兩位都是從社會實用、功用性層面來尋找和設定詩歌內容的,即在他們的價值視閾中,詩歌內容之“新”都是與當下的社會思潮、文化思想、時事政治,甚至與20世紀出現于歐洲的新事物、新名詞、新科技聯系在一起的。
由上可見,以變法圖強為目的的詩學理論所強調的詩歌內容之“新”是有著特定運行軌跡的:“內容”必須要有鮮明的時代性,而且這種時代性常常通過具體的“時勢”——社會時勢和政治時勢反映出來。也就是說,詩歌的“內容”一定要具有反映和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功能才行。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的時代性也就是社會、政治性的意思。廓清了這一前提,也就順理成章地明白了該詩歌流脈一直把其重心擱置在詩歌內容方面的邏輯動因了。
經過以上這番溯源,回過頭來再勘查胡適“作詩須得如作文”的詩學理論,不可理解的也就理解了。譬如,在詩歌中并不關心社會意義和政治性的胡適,為何在論述詩歌的時候卻一反常態地以詩歌內容為先,而且還格外重視詩歌內容的時代性?只有從承傳的角度加以勘測,才能解釋其矛盾性,即胡適詩論中的這一特點其實就是對近代詩歌以詩救國之傳統的賡續。
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新詩運動的確與黃遵憲等為代表的近代詩歌有著難解之緣,正如朱自清在1935年對二者間關系的梳理,他說黃遵憲“一方面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試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詩。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于民七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的影響。”朱自清從“觀念”的角度,把以黃遵憲為代表的近代詩歌與“五四”新詩運動銜接到一起,使之成為互為邏輯和互為因果的一個統一體。
朱自清在當時的這一指認還是頗有見地的。胡適所秉持的這種以內容為上的新詩“觀念”,就是對黃遵憲等人思想的繼承。當然,這種繼承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在繼承中予以重大變革:或許“五四”前后的中國社會已經渡過了最為危機的關頭;也或許胡適本人天生就對藝術自身的問題更有興致,反正到了他的詩學框架里,隱藏在變法圖強派詩歌中的那種強烈的政治功利性悄悄隱退了身影。這種“隱退”大致可總結成,胡適繼承了近代詩歌強調要有新穎而充實內容的傳統,但在繼承中他又有意識地讓詩歌與社會現實,特別是時事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換句話說,胡適在保持以內容為上的前提下,把近代詩歌從社會時勢中提取內容的精神特質擯棄掉了,從而給這個原本偏于社會政治性的詩學理論注入更多的文學審美性。
三、以“文”之長補“詩”之短
當然,胡適的這種擯棄是小心翼翼地擯棄,用“不說”代替“說”的。有關這點從他發表于1918年的《易卜生主義》一文中,不難看出來。在該文中,他以易卜生的戲劇為例,反對詩人、作家以及文學活動家動不動就給社會開“藥方”的做法,理由是:“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后或者須用瀉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于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于中國;……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卻不肯下藥。”這番話正代表了胡適對中國詩歌改良的一個基本態度:中國傳統舊詩詞的內容浮泛、虛夸、僵化,的確是亟需改良,但怎么個改良法,即要用什么樣的內容來取代和替換,他則不肯“下藥”了,只是借易卜生的話說,“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不能指定”的背后,其實意味著他并不認可黃遵憲等人所倡導的那種以詩歌來救國的思想。
既然如此,是否表明胡適的“作詩須得如作文”的理論,除了在詩歌內容需要重鑄的這一點,即要像“文”一樣有著充實而新穎的內容方面,與黃遵憲等人為代表的近代詩歌達成一致外,其他方面都是分道揚鑣的?當然不是。誠如前文所言,朱自清認為近代詩歌主要是在“觀念上”,而不是在“方法上”影響了“五四”新詩。前一個無疑是正確的,后一個則有些偏頗。或者說,朱自清由于囿于“五四”新詩的白話,即白話是“五四”新詩最為主導的特征,所以他就從作詩的“方法上”割裂了“五四”新詩與近代詩歌的邏輯關系,以此來與較為保守的近代詩歌劃清界限。事實上,“五四”新詩不但在“觀念上”與近代詩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就是在“方法上”也有著難以割舍的內在牽連。具體說,胡適所說的“作詩須得如作文”中的“如作文”的藝術手法,就是取法于以黃遵憲等人為代表的近代詩歌的。
黃遵憲們的詩歌理論雖然是以變法圖強為目的,注重的主要是內容的變革,至于形式的變革在當時還無暇顧及,但是由于他們重視的是詩歌內容的“實”,而且這種“實”還不是一般的“實”,往往是與民族存亡、國家興衰的歷史、政治大事件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如黃遵憲一生創作了一千多首詩歌,其中絕大多數的詩歌都屬于此類,以至于被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稱之為“詩史”,這就決定了嚴滄浪所標舉的那種以“虛”為上,即“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詮釋方式——其實這也正是中國傳統詩歌最為正宗的表達方式,是無法完成這一任務設定的。這一窘況決定了以黃遵憲等為代表的近代詩人們,必須要另辟出一條更適合于展示思想內容的創作手法。這種手法就是“以文為詩”的手法,即為了能在詩歌中更有效地展示出詩人的憂國情懷,使詩歌成為啟蒙救國的輿論武器,把“文”的一些語言表達方式引入“詩”中來,從而擴大詩歌內容與思想的表現力,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他們在“語言方面則表現為以文為詩的特點,揮灑淋漓,汪洋恣肆,以此適應表達壯闊的思想內容和奔放不羈的感情的需要”。“以文為詩”,就是為了滿足“壯闊的思想內容和奔放不羈的感情”的需求,而不得不使用的一個策略。
當然,“以文為詩”的手法并非近代詩人們的首創,中國古代詩歌中也有。在唐代時,韓愈就曾提出過“以文為詩”的口號,主張將古文中的一些謀篇布局的技巧以及古文中的句式和文字等引入詩歌中。他的這一主張到了宋代又被歐陽修等人發揚光大,從而對宋代的詩歌創作與發展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以文為詩”在唐代還主要表現為口號的話,在宋代則成為了詩人創作的一條不可忽視的準則。而且這一思想還一直綿延在其后的詩歌創作中,正如趙翼對其的總結:“以文論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把“以文為詩”之手法總結成“成一代之大觀”,或許有夸大的成分,畢竟中國的詩學一直還是以抒情——不是以描寫事件、描摹物狀為正宗。但不管怎么說,這種“以文為詩”的藝術手法,非常適合于近代詩歌的敘事性要求。從技術層面上看,胡適所言的“作詩須得如作文”就是繼承了近代詩歌的這種借鑒“文”的一些敘事手法來寫詩的傳統,正如他說:“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么做。”話說得雖然有些籠統,但至少可以說明胡適反對那種以“虛”寫“虛”的寫法,倡導一種更能敘事、寫實的,即能把詩歌內容更好地彰顯和詮釋出來的藝術手法。
總之,對胡適而言,所謂的“作詩須得如作文”有兩個目的:一方面想把“文”中的敘事、抽象、說理之思維引入“詩”中來,另一方面也想借“文”中的“事”來填充“詩”之內容的空疏,即借“文”之長來補“詩”之短,從而為中國新詩構建起一種新的,也就是像“文”一樣有著充實的思想內容的靈魂。
由以上論述可見,“作詩須得如作文”非但不是一個“非詩”主張,相反它是中國詩歌發展到20世紀初期必然出現的一次美學轉型:舊體詩的那種以抒情為主導的表達模式,藝術性超凡,但只能讓詩歌的思想內容沿著“虛”的方向發展。而且,唯有此,才算得上是好詩。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則是一個崇尚思想觀念,尤其是先進的思想觀念為上的特殊時代,這就宣告了舊體詩表達模式的出局。既然舊有的表達模式不能滿足彰顯“內容”的要求,胡適便大膽采用了跨界取用的策略——把更適用于表現“內容”的“文”的一些特長,如描寫、敘事等特點汲取到詩歌中來,彌補了詩歌不擅長表達和詮釋思想性的問題。以今天的眼光看,胡適把“詩”與“文”融合為一體,也就是使之既有傳統詩歌的抒情性,又有“文”的描寫、敘事性,是一件了不起的創舉,不但讓中國詩歌完成了從古代到現代的轉型,而且為其發展開辟出了一條廣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