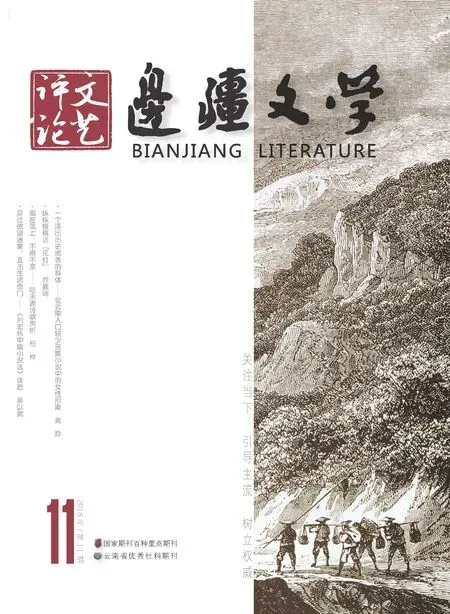聶耳音樂文化價值的當代啟示與時代超越
申 波
曾幾何時,手機微信圈盛傳一個帖子,即,討論聶耳“是不是音樂家”的話題而引發業內的討論。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在筆者看來,這樣的討論可以說幾乎是不需證偽的。如果我們把討論的視角轉入特定的歷史語境,就會發現,20世紀30年代,一個出自偏隅之地、18歲出頭的青年去到上海,在很快的時間里即進入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職業藝術表演團體,既奏樂又唱歌還演戲,這已經是難得的天才表現,更何況,在那民族危亡的艱難時期,當他不經意間拿起如椽之筆,即譜寫出了那個時代中華民族集體心理結構中的最強音并由此喚起華夏民眾必勝信心的旋律時,他的所有行為,就遠遠超越了形而上學“藝術”的一切內涵與外延,而具有了橫跨古今、超越時代的社會學意義而輻射出情感的熱、精神的光。我們知道,在災難深重的20世紀之初的華夏大地,為了民族的崛起、喚醒昏睡的民眾,用音樂達成民眾的情感認同、喚起人們的覺悟、搭建情感的社會契約,幾乎是那個時代所有文藝青年心底自覺的沖動。其中,以貼近民眾的歌曲體裁作為創作方式,尤其以旋律化共性寫作這樣的手法傳情達意的選材方式,就成為熱衷于國事天下事有識之士所喜愛的文化鼓動渠道。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開篇的討論,就成為了一個十足的“偽命題”。一個民族,只有記住過往的歷史、崇拜先賢的功德,才會有美好的明天。因此,今天由昆明市政協、昆明聶耳研究會牽頭開展對聶耳音樂“大眾性、民族性、藝術性”歷史貢獻的紀念活動,也就具有了現實的意義。
一、聶耳音樂文化價值的當代識讀
聶耳的名字之所以成為云南一方水土偉大的文化記憶、他譜寫的旋律之所以直到當下仍然是中華民族集體精神的歷史記憶,首要因素,就在于他將自己的音樂實踐體現在關注生活、貼近民族命運的價值情懷之中,輻射出情感的熱、精神的光,再現了一個時代不同階層民眾情感的豐富性,從而構成了縷縷深沉壯美的音響世界。如:《鐵蹄下的歌女》,中國數千年婦女的悲慘境遇,在聶耳琴鍵的流動中一旦變為音響,業已上升為心靈創造,便具有一種不可抗拒、令人泣然欲涕的崇高境界,流露出人文之光和人性之美。他的《梅娘曲》,以“格式塔”的手法,依托抒情性的旋律對崇高愛情的傾訴,喚起了人性的復蘇,從而將戰爭的慘烈轉化為對愛情、對生命的無比珍惜,進而將反侵略戰爭勝利的必然性轉化為審美人生的必然性,將戰爭毀滅愛情的苦難變為了對和平自由的憧憬,將悲劇化為了人生的喜劇,以“引領聽眾去享受悲劇的壯麗和快慰”,這正是尼采所倡導善良的人們必須從日神精神提升到酒神精神、以此不斷提升人生意義并不斷獲得審美快感的要旨。在這里,我們無須考證聶耳在創作心理上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但在他的音樂實踐中,卻是這樣踐行的,且踐行的風流瀟灑。眾所周知,聶耳更以其《義勇軍進行曲》為標志,以“大樂必簡必易”的審美設計,喚起了一個古老民族集體精神的“儀式”感、抒發了一個古老民族不屈不撓的堅定意志,其猶如號角般激昂的“動機”音調中勇往直前進行曲節拍運動所蘊涵的能量聚集與能量釋放,更是應和了中華集體心理結構中對于藝術精神彰顯的潛在追求,即:體貴正大、志貴高遠、氣貴雄渾、韻貴雋永。因此,聶耳音樂創作所表述的崇高情懷與藝術取向,其內涵和外延早已超越了音樂本身的意義,實乃作為藝術家與民族火熱生活同呼吸、共命運的生命物化,節奏運動中蘊含的不屈力量,是音樂家人格向音樂中的沉浸與融合,可以說,作為一種“美與善的結合”,這是中國近代音樂創作優秀傳統構建的藝術豐碑。作為一種創作方向,彰顯出作曲家貼近生活、緊扣時代脈搏、自覺從生活哲理和情感取向上關注民族未來、與現實生活永難割舍的火熱情懷和血肉聯系的心聲,因而,在聶耳繽紛的音響創造中,無不張揚了那個時代民眾的心聲。作為一種特殊時代的文化記憶,聶耳的音樂滿足了不同時代民眾的審美需求,以他的旋律,與他所生活那個時代的生活場景保持了一致的狀態,成為一個時代民族精神的“定格”。我們從聶耳許多歷久彌新的音響所呈現的審美隱喻中,直到今天,仍然能夠聆聽到時代風煙滾滾的回聲、感悟到民族鏗鏘的吶喊,由此,綿延樂音的流動,其作為一種文化象征,與后世構建了一種永恒的可對話性。這種對現實生活的關注與執著表達,既是中國近代主流音樂的傳統使然,也是中國特殊國情的根脈所系之必然。作為一種把握生活脈搏、關注民族命運的藝術取向,聶耳音樂所倡導的激揚時代精神、鼓舞民族抗爭的創作風范,永遠是當下音樂創作應該傳承的典范。
這樣的立論絕不是說,關注生活就一定是但凡音樂的創作,就一定要遵循現實主義的原則進行創作,而其他發揮藝術家主觀感受的音樂創作就沒有關注生活或缺少生活的根基,更何況,隨著時代的發展,當下是一個提倡政治文明和以人為本的多元時代,我們更不可能采用“紅頭文件”的方式把藝術家往他不情愿成為其中某個“分子”的層面上驅趕——尤其在一個提倡和諧思維構建、接受個性張揚的新時代,這似乎構成了一個悖論。但是,我們說,藝術創作無論如何超越時代、體現個性,但仍有一個遵從“大眾性”的立場問題。歷數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被時代所銘記的音樂家,他們在現實主義審美道路上,又確立了各自的創作風格,如冼星海、馬可、李煥之、呂其明、劉熾、施光南、谷建芬、趙季平、印青等,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于時代火熱的生活,即便沒有身體“‘在場’的親歷親為,但在他們充滿情感表達的音樂語言的呈現中,卻已證明他們的精神一定是‘在場’”的,在他們熠熠生輝音樂音響的回聲中,無不折射出他們音樂創作與腳下這塊土地緊密的聯系、無不以華夏民族豐厚的音樂傳統為素養。因此,唯有把生活本身作為藝術的源泉和審美的過程,才能領悟生活的意義。由此出發,審視我省當下的樂壇,可以說,我們不是沒有優秀的音樂作品,但似乎是,在面對一個多元需求的新時代,樂壇所呈現的許多作品卻缺乏表現大時代大格局的大氣度,音樂創作的體裁和題材以及創作技法的使用都顯得與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不相匹配,少有“職業化”與“大眾化”有機融合的作品在民眾中傳唱,也少有標志性的作品在全國層面產生影響,即使偶有亮相,也多出自僅有的幾位高手,與全省這樣一個龐大的音樂消費市場和豐富民族音樂素材的地位是不相稱的。
二、從聶耳音樂的價值取向看當下云南的音樂生活
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是一個人人追求文化創新、強調個性張揚的時代,也是一個全民族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而努力奮斗的新時代。特別是在改革開放40年我國各方面取得偉大成就的大背景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我們的音樂生活也伴隨社會思潮的變革出現了各種表現流派和寫作風格,特別在青年一代新興藝術家的音響世界里,云波詭譎各領風騷,人們通過創意迭出的手法,希望以各種新奇的音樂語言來表達自我價值的彰顯和個人的生活感受,以此彰顯青年一代反理性、反傳統的主張,音響中追求標新立異的個性情感流露成為當代音樂表現的主題。在這種多元審美表達的現狀下,業內學者不由生出一種茫然若失的感嘆:在我們的生活中,仿佛不知道什么是審美的尺度、似乎音樂的創作可以脫離火熱的現實社會天馬行空、無須與民生相關照,音樂創作“為誰而音樂”已成為一句無力的口號。現實中,個別音樂從業人員,為了單純追求觀念更新而“去思想化”、崇尚虛無的現代手法在作品中的使用而“去價值化”,個別音響只有形式的呈現而缺少內容的表達,更在浮躁心態的牽引下,為了單純追求經濟利益,“速成”音樂作品的創作,把音樂活動視為謀求物質利益的手段,其創作動機遠離了音樂表現生活、滌蕩心靈、促進社會移風易的學科宗旨。君不見,曾幾何時,為了商業目的,許多低俗的歌會競相登臺,主辦方把音樂活動作為“為商業塔橋”的工具、視音樂為商品的附庸而隨俗沉浮,活動內涵喪失了社會教化的職責和化人養心的思想啟迪,弱化了音樂謳歌生活新風、促進社會啟蒙發言的自覺。
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國情的需要,從省委、省政府到省委宣傳部、省文聯等部門,無不對文化建設給予充分的重視,省委宣傳部也多次牽頭舉辦了促進云南文學藝術創作的座談會,但從總體上看,作為本應該對生活抱有最敏銳和最具有鮮活激情的音樂創作,對廣大民眾、特別是對占云南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民眾的關注和作為卻不盡人意。如何在音樂創作中通過行之有效的調節與安排,既呈現精品,以適應“專業評價”學科自身發展之需,同時又創作出更多適合普通民眾傳唱的通俗化作品,以滿足“社會評價”的大眾審美之需,這對文化管理機構和從業人員都是一種考量。現實中,我們的音樂生活不得不犧牲藝術對不同社會需求的人文關照,更有許多音樂現象值得警覺,那就是只求娛樂至死、不求魅力永駐,只求向社會索取,不求向社會負責、只對主題晚會的委約創作充滿激情、不愿潛下心去雕琢精品,以“去主流化”孤芳自賞的態度為由拒絕面對火熱的現實,不愿也無法表現眼前的生活,用他們的話說,他們的音樂是“表現自我、表現時尚”的作品,在這樣的音響中,要指望再次出現象聶耳那樣“與時代同呼吸、與民族共命運”的經典之作,無疑存在較大的距離。法國結構主義學者佛里杰?哈特曼在他的藝術理論中就認為:藝術作品可分為“前景層”和“后景層”的兩個緊密關聯著的層構造。在哈特曼看來,前景層是物質的、感性的形態;后景層則是精神的內容,亦即當代音樂美學中關乎形式與內容、結構與意義問題的討論,這樣的命題,是值得業內思考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倡導講品味、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加強文藝隊伍建設,造就一大批德藝雙馨名師大家,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創作人才”,這就為包括音樂創作在內的文藝事業回歸火熱的現實生活吹響了集結號。作為一種精神源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系列重要論述的核心要旨就是要求當代的音樂創作,必須用專注的態度、敬業的精神,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這無疑對云南當代音樂創作如何走好“傳承聶耳音樂傳統、開創時代新風”的創作路徑提出了期待。
三、聶耳現實主義創作之路的當下意義
事實是,我們今天無論身臨任何一場弘揚正能量的高水平音樂會,節目單中的多數曲目仍然是聶耳、冼星海、劉熾、徐沛東、印青以及數十年積淀下來的器樂作品,“知識老化”這一說,似乎不太適用于音樂的審美領域。相反,歲月的煙塵常常還會襯托其無盡的魅力,人們熟悉的旋律猶如開壇的陳釀反而更令人陶醉。這說明,但凡記錄歷史精神、反映民族情懷、立足現實主義創作道路的旋律,其生命力是完全可以跨越古今、超越物象行跡而不受時空阻隔的。
波蘭的音樂美學家卓菲婭·麗莎就曾說過,音樂作品“當它無論是在其產生的那個時代,還是在后來的時代……都能喚起人們的感情,打動聽眾并豐富他們的內心世界,這時才稱得上持續存在著。音樂作品能不能完成這樣的功能,是它的價值和持續存在性的標準”。當然,音樂價值屬性的產生,是由各種復雜的社會與心理要素決定的,音樂作為“表達人類心靈陣陣波瀾狀態過程”的一種文化表象,其存在的最大價值就在于它對于人類至深情感的表達、刻畫了人類心靈深處最隱秘的情感與律動。無論社會科技發展到什么程度,音樂永遠是人類情感最強烈的催化劑,從這個立場來講,擁有深刻情感內涵的音樂就擁有了永恒的生命力,美國作家約翰·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趨勢》一書中就指出:“我們周圍的高技術越多,就越需要人的情感。”音樂作為音樂家對客觀存在的一種觀照,聽眾一方面以一種特殊的心理表象,即:審美過程中的感覺、體驗、想象、情緒等心理形式去感知樂音之流;另一方面,又以其文化觀念、審美趣味、生活經歷等形成對作品的態度。我們從聶耳雖然不多、但卻記錄了一個時代民族命運的音響中,無不蘊含著華夏民族對于美好未來的共同追求、體現出華夏民族集體精神的本質力量。我們在這里討論聶耳音樂的當代價值,這不單單在于聶耳音樂安慰、鼓舞、記錄了一個時代,更在于他的音樂超越了時空的四維,燭照了那個時代蕓蕓眾生的靈魂,其“儀式”性的文法表意,為我們舉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園提供了有效的支撐。一個民族只有民族精神也同時強大,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民族精神的強大,是不能拋棄自己傳統的,沒有自己傳統的民族,無異于宣布自己的滅亡。
千百年來,在人類生生不息的歷史長河中,人們逐漸形成了與客觀現實相適應的審美心理慣性,能自覺地在內容和形式上繼承,利用過去時代創造的一切有價值的文化,如那些高度提煉了的、異常精煉的音樂創作手法美的形式,而那些美的形式,正是千百年來人類精神化了的一種物化形態,他們在人類漫長的藝術創造和審美實踐中,早已脫離了具體的事物而具有了獨立普遍的審美意義,人們已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審美生理和心理機制。應該說,這正是聶耳音樂能在今天仍然煥發不朽生命力的源頭與動力所在。我們如果從詩意化的立場去解讀,聶耳音樂中所體現的偉大力量,不僅在于它對中西音樂手法的自覺運用,更在于他的音樂中,深深地承載了中華民眾集體精神的靈魂狀態,是華夏民族高貴的激情與時代精神相撞擊所發出的崇高的回響。因此,鏗鏘的律動符合華夏傳統音樂美學的價值取向:“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
我們今天紀念聶耳,其實是對我們民族之魂的祭奠,是一種自我覺醒和發現,特別是在舉國上下團結一心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大背景下,我們的民族更需要這種奮進的情和精神的光,在新時代的背景下,萬眾一心,前進、前進、前進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