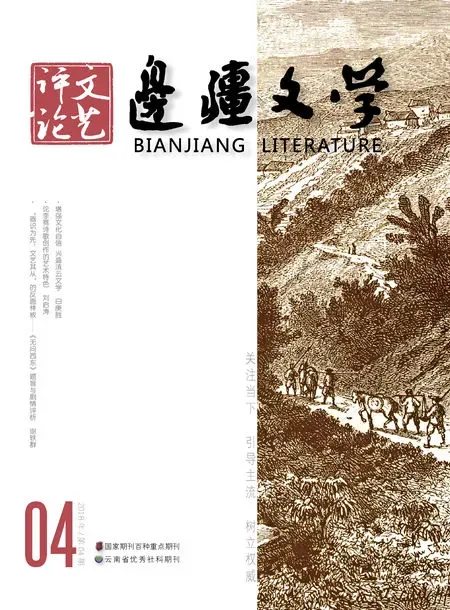文化自覺意識在原生態舞蹈田野調查中的啟示
——以云南省鎮雄縣以古鎮小米多村為個案
曾金華
2008年雪災期間及2009年盛夏,筆者曾兩次深入到云南省鎮雄縣以古鎮小米多村進行民族傳統文化田野調查,在調查中有一現象一直在我腦海中記憶猶新,即當地給我們表演彝族喪祭舞蹈《喀紅唄》的四名舞者基本上都是村委會的干部。其中有村總支委員兼村委會副主任李會員,男,彝族,43歲,黨員,初中文化;村總支委員陸金平,男,彝族,53歲,黨員,高小文化;村電管員張友明,男,彝族,40歲,高小文化;本村村民及畢摩傳人文全德,男,彝族,52歲,初小文化。在場的村領導還有村總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陸紹國,男,彝族,36歲,黨員,初中文化;村計劃生育宣傳員羅傳奇,男,彝族,32歲,預備黨員,初中文化;村總支委員、會計兼宣傳員劉世林,男,漢族,50歲,黨員;以及文全德的兒子文發財,男,彝族,22歲,鎮雄縣民族中學畢業,2009年考上昆明理工大學,是本村第二個大學生等等。觀看他們表演和訪談完畢,我們還去到村總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陸紹國家里,看望了他的父親和母親——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彝族畢摩陸金華老人與王子香老人。陸金華老人61歲,王子香老人58歲,都是當地能寫會畫、能歌善舞的民族傳統文化傳承人。我們還欣賞到了陸金華老人用彝族文字書寫的春聯和王子香老人用彝族語言表演的《酒禮歌》。我們深深感觸到這是一個彝族傳統文化非常濃厚的生態村,特別是整個村的領導班子把彝族傳統文化看作他們的生命之根而倍加珍視,他們這種熱愛民族、熱愛故土、熱愛傳統、熱愛文化的精神強烈地震撼著我們,感染著我們。他們希望我們能夠把古老的彝族傳統文化遺產介紹傳播出去,從他們一雙雙期盼的眼里我們感受到了保護和傳承民族傳統文化根性力量的重要意義。
一
云南省鎮雄縣以古鎮小米多村位于云貴兩省交界的烏蒙山區,距縣城60公里,距鎮政府30公里。與本鎮麥車村、安爾村及貴州省赫章縣財神鎮接壤。這里的彝族同胞至今還遺存著許多古老的民族傳統文化習俗。
鎮雄縣以古鎮小米多村的彝族,每逢長者亡故,首先須告知親友。臨葬前夕,母舅和姑媽家分別帶上祭品到死者家里祭奠。母舅家帶一活竹置于門前,用竹葉蘸酒蘸水灑于地上,繼而由“喀約”(歌舞班子)從左邊順時針方向圍房繞三圈,口中念念有詞,吟唱有聲,邊唱邊跳《喀紅唄》(意為跳舞除邪,安定魂靈。當地漢語也稱這種歌舞形式為《跩腳》《拐腳》《跳腳》)。爾后入屋內繞棺木于左邊繼續唱跳。姑媽家帶的“喀約”則與其相反,逆時針方向圍房繞三圈,進屋后繞棺木三轉,然后集中于棺木右邊跳《喀紅唄》。如此循環往復,兩家輪流進行,從傍晚跳至清晨。
死者葬后,用青竹削成人形,捆上羊毛,扎上紅綠線,放入約四寸長的竹管內,又在管內放入米和茶葉,然后再置于一圓桶內,此桶名曰“鬼桶”或“靈桶”(彝語稱“租哦”),隨后又將“鬼桶”供入“靈房”(彝語稱“阿皮卡”)。“靈房”一般設在長子家人跡罕至的屋后,如長子絕嗣,則要供于幺房(小兒)家。每至彝族年(農歷十二月十二日)祭祖時,均要在“靈房”前跳《喀紅唄》。
《喀紅唄》由很多舞段組成,但每一舞段只有一個特殊技巧動作,如羊角碰角、猴子爬樹、老鷹展翅、老鷹抓雞、毛狗(狐貍)鉆洞、四馬追羊、野雞鉆籬笆、猴子翻跟斗、猴子搬樁等,主要為模擬禽獸的各種技巧動作或造型。它有十幾種基本舞步,如跩腳步、甩鈴步、左右甩鈴步、行進甩鈴步、斜伸手甩鈴步、吸腿步、跳腳步等,其中跩腳步為核心舞步,貫穿整個舞蹈始終。
從表演形式上看,《喀紅唄》上身動作多變,幅度較大,用小臂帶動大臂甩鈴,沿弧線上下左右來回劃動。舞蹈時,第一人為領舞者,左手持鈴,右手持白色孝布,其余三人正好相反。馬鈴鐺為不可缺少的道具和伴奏響器,整個舞蹈始終伴隨著清脆悅耳的鈴聲,節奏鮮明,鏗鏘有力。孝布隨手舞動,翻飛飄逸,對舞姿起到了美化作用。
從表演效果上看,上年紀的人步伐穩健沉著,動作含蓄凝重,內蘊回波旋浪之力;年紀輕的人步伐剛勁灑脫,動作舒展豪放,勢如披荊斬棘,模擬禽獸動作更是惟妙惟肖,尤顯豁達、勇猛之志。彝族耿直、豪爽、粗獷、強悍的性格,溢漫于整個舞蹈之中。
二
從上述彝族喪祭舞蹈《喀紅唄》的禮儀習俗中,可以看出原始宗教信仰和古老歌舞藝術在彝族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和作用。宗教和藝術都同屬于社會意識形態,它們既有共同之點,也有不同之處。共同之點主要表現為它們都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又反作用于客觀存在;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有歷史的繼承性。不同之處則表現為它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客觀世界并為其服務。二者之間并不是孤立地發展,而是互相聯系、互相滲透和互相影響的。
烏蒙山區彝族的喪祭禮俗,是在父母靈魂不死觀念基礎上產生的,是祖先崇拜意識的產物,是較為古老的帶有濃厚原始宗教神秘色彩的早期儀式的一種特殊類型。這種儀式和歷史上的鬼巫信仰與“鬼主”制度分不開。據樊綽《蠻書》記述,唐代云南東北部阿芋、阿猛、夔山、暴蠻、盧鹿蠻、磨彌蠻等烏蠻六部落崇尚鬼巫,部落首領即稱之為“鬼主”,“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奉鬼巫,用相服制”,利用鬼巫信仰進行統治。《宋史·黎州諸蠻》中也說:“夷俗尚鬼,謂主祭曰鬼主,故其酋長號部鬼主。”古代彝族摯信鬼巫,曾有過部落酋長與鬼主同為一人的類似政教合一的制度。鬼巫信仰的一大特點是視人的靈魂為鬼魂,對人的死亡十分看重,認為靈魂未能安得其所會給活著的人帶來極大的禍害,因而人死后必須舉行隆重儀式包括歌舞活動進行祭禱。這種原始的信仰與祭祀形式,在滇東北彝族地區早就盛行了。昭通出土的東晉霍承嗣墓有一幅反映“夷漢部曲”及祭祀墓主的壁畫,在墓主人前左右有幾排頭上留有“天菩薩”(英雄髻)、身著“察爾瓦”(披氈)的彝族先民形象。這些形象明顯地在參加某種儀式,很可能是參加墓主的葬禮。因為據墓上款識所言,此墓是霍承嗣的余魂來歸墓即招魂墓,所以墓主面前這些“夷漢部曲”形象可能就是參加招魂儀式的場面寫照。其中的彝族先民形象,也可能反映了當時彝族喪祭歌舞的實際場景。由此而知,彝族喪葬禮俗及喪祭歌舞由來已久,而且一直流傳未已。
清代,這種彝族喪祭歌舞禮俗其端倪仍可窺見。清乾隆《鎮雄州志》載:人死“往吊者族姓,則用雞一只,謂同籠生長也。姻戚則邀親好,率仆屬,步騎成群,繞靈呼吁,哭聲震地,名曰‘打鬼’”。這里所說的“打鬼”,其實就是送喪驅鬼之舞。又說:“其祀先三代以上,則祧之。祧者,以金銀為片,剪作人形,藏諸木桶,按次世奉于極險峻之山洞,令人守之,曰‘鬼桶巖’。……此皆黑白倮倮舊俗也,今亦襲……”“鬼桶”即祭祀時用的一種器具,同時也是歌舞時供奉的道具。另外,從文獻記載和傳說中所反映的情況來看,這種祭祀活動中還雜有對竹、雞、馬、猴等動植物崇拜的習俗。祖先崇拜與自然崇拜交融,體現于喪葬禮俗,形成了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復合體”,使產生于靈魂不死觀念之上的祖先崇拜和產生于萬物有靈觀念基礎上的自然崇拜,成為彝族喪祭歌舞的意識中樞,更增強了喪祭歌舞濃厚的原始神秘色彩。
藝術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具有明顯的再現生活、總結經驗、傳授知識、獲取美感等作用。由于原始宗教的滲入,在彝族等一些民族中,舞蹈藝術在特定的時期內曾變成一種具有宗教性質的、功利性很強的表現形式載體,使其具有淳樸生產生活氣息的藝術被神秘的宗教氣氛所籠罩,原來贊美勞動的詩歌,變成了對神靈的禱詞和唱誦;原來表現生產生活的舞蹈動作,變成了宗教儀式的組成部分和傳承工具。因而,宗教把舞蹈藝術對生產生活的真實、積極的表現,變成虛幻、神秘的反映,變成了對彼岸世界的幻想魔法。這里必須指出的是宗教對于舞蹈的產生和發展并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藝術最終要還其本來面目,要從宗教迷霧中剝離出來。從鎮雄縣以古鎮小米多村彝族喪祭舞蹈《喀紅唄》中,我們可以看出它所反映的內容,大量的都是源于原始先民們的狩獵和游牧生活。如羊角碰角、四馬追羊、猴子爬樹、老鷹展翅、老鷹抓雞、毛狗鉆洞、野雞鉆籬笆等,形象地再現了彝族先民們早期的原始生產生活風貌,以及折射出他們的原始圖騰崇拜等情況。
三
“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多次提出的一個概念,“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堅守傳統’。自知之明是為了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
鎮雄縣小米多村彝族喪祭舞蹈《喀紅唄》對本民族生產生活中的客觀事物采用模擬、象征、會意、敘事等手法,構成相應的舞蹈動作,因而具有舞蹈形成的原初性特征。它的舞具及響器僅用舞者手中的馬鈴鐺與孝布,其伴奏聲清脆有力,舞姿靈動翻飛飄逸,具有象征性特征。它的舞蹈動作形式單一銜接緊湊,形象生動寓意深刻,具有簡約性特征。《喀紅唄》作為承載著彝族一代代人的文化記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動地反映出本民族的民俗、宗教文化內涵,具有很深的學術研究價值。整個舞蹈兼容了敘事性、抒情性、趣味性和技巧性,因而具有較高的開發利用價值。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迅速蔓延,隨著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不斷沖擊,彝族喪祭舞蹈《喀紅唄》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已發生了變革,使這種傳統民俗活動在民間日益淡化。加之新時期殯葬制度改革帶來的喪事從簡,要求在新的時代注入新的文化內涵,因此其主要活動范圍已逐漸縮小,該舞蹈越來越成為人們的一種民族傳統文化記憶。
為了使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并在傳統文化的基石上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我們必須珍視、繼承祖先遺留下來的寶貴文化遺產。增強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識”和“危機意識”,切實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工作。鑒于上述情況,鎮雄縣文化主管部門已在普查的基礎上對會跳《喀紅唄》的人員進行摸底調查,為了使這一瀕危傳統文化遺產得以傳承,調動他們熱愛民族民間歌舞的積極性,當地政府領導對他們進行了慰問,小米多村總支委及村委會對其舞蹈人員的生活上給予了幫助。當地文化主管部門還擬定了保護計劃和保護措施,投入相應資金,以帶動和促進當地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與發展。如今,為了不斷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當地欲建立小米多彝族文化生態保護村,對《喀紅唄》舞者實行重點保護,讓更多的彝族青少年參與其中,發展壯大舞蹈表演隊伍,從根本上解決傳承中遇到的難題,已于2013年舉辦了數十人的彝族傳統歌舞培訓班。筆者認為,小米多村全體村干部以身作則、立足本土、繼承傳統、挖掘特色,帶頭保護、傳承和發展彝族傳統文化的這些行為舉措,就是模范踐行文化自覺意識較好的案例,它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在原生態舞蹈田野調查中有益的啟示。
綜上所述,云南省鎮雄縣以古鎮小米多村彝族喪祭舞蹈《喀紅唄》伴隨著歷史的進程,在特殊的封閉、半封閉的自然、社會環境中得以衍生滋長,成為當地彝族藉以超度亡靈、告慰子孫、祈求壽福、企望安康的一大祭祀禮俗活動。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科學的進步,今天已失去了它以往極大的內聚力和影響力。但是,這種宗教與藝術雜糅相生的特殊觀念形態的傳統文化遺產,為我們探究這一地區彝族的歷史源流、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心理素質、文化習俗、藝術風貌等諸多人類學、民俗學、宗教學、藝術學現象,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民族傳統文化“活化石”。鎮雄縣以古鎮小米多村各位村干部率先垂范,帶領大家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的文化自覺意識和行為舉措,更值得我們大力褒揚和引起思考。我們由衷期待著在國際國內高度重視和發展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背景下,使這一深藏在烏蒙山區的彝族民間瑰寶走出大山,走向人們更加廣闊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