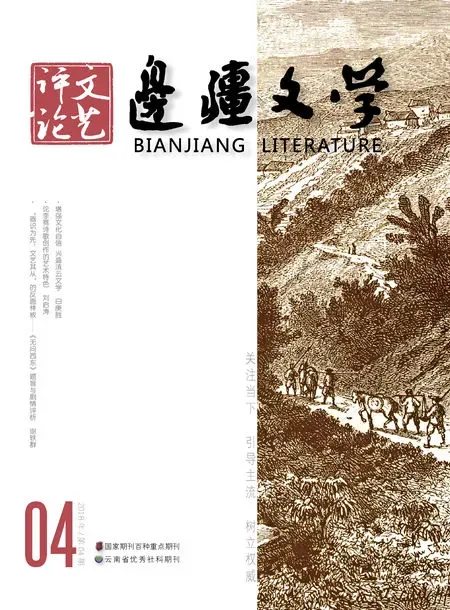新世紀云南民族文學原生態元素的繼承與發展
于昊燕
“原生態文學”不是傳統民間文學的翻版或復古,而是現代文化再創造和民族文化轉型的一條道路,是社會發展的大“場”(政治、經濟、文化)和諧寬松的環境之下,民族文學內部對于傳統民間文學的繼承與現代化運用。新世紀以來,民族文學的原生態元素繼承與現代轉型中,民族身份與生態理念成為兩個備受關注的關鍵詞。
民族文學中對民族身份認同的原生態特征不會隨著時間而流逝,在新世紀同樣是民族文學的立足之根本。“正是在民族這一層次上的社會才具有最鮮明的文化差異。我們感到自己所屬的是某個民族,我們試圖仿效我們同胞的習俗和風度。而且,我們非常方便地辨別出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以及他們各自的言談方式、風俗和服飾等等”。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描摹民族日常生活、深層挖掘民族文化底蘊、弘揚民族意識和宗教意識、認同和傳承民族文化、表達少數民族族群體驗,最終塑造并凸顯出民族的身份特征。
因此,新世紀民族文學中的原生態特征繼承文學中書寫民族宗教信仰、祖先傳說、民族情感、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特性,表現出作家本民族身份的認同與自豪。比如,哈尼詩人哥布的長詩《神圣的村莊》通過追溯民族本源的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詠嘆哈尼族深沉優美的神話傳說與圖騰崇拜,運用豐富的民間故事、原始宗教、諺語歌謠、風俗人情等元素建構詩歌敘事資源。哥布的靈感來自哈尼族生活世界的歷史和傳統中,他認為文化多樣性的流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本民族的知識分子對傳統的背棄,他堅持雙語寫作,用母語喚醒人們對本民族文化的關注,希冀“作品與哈尼族文化有一種自然的傳承關系,也希望成為哈尼族未來文學傳統的一部分。”
當然,民族身份原生態的表現不是大一統的民族特點總結,新世紀的民族文化身份具有多層次性相互融合滲透的特征。民族作家作為民族共同體中的個體成員,既是民族共同體的一部分,又不能混同于民族共同體。“個人有多重身份……包括歸屬性的,地域性的,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以及國別的”而文化性的身份則多來源于“民族,部落……語言,國籍,宗教,文明”。在現實生活中,文化存在于民族發展的具體語境中,構成元素具體而豐富,并且影響到民族性格形成。云南少數民族因地域跨境的特殊與民族雜居融合的多元,受到傳統文化、域外文化、主流文化、時代文化的多結構多層次多因素的動態影響,民族作家作為特定的民族個體,其文化身份比之漢族文學作家更為多重,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的文化身份元素也更為復雜多樣。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生態和歷史條件,各區域各民族社會經濟和政治文化發展程度呈現不平衡狀態:少數民族跨境而居、邊民互市聯姻,民族關系及中外國際關系交織在一起,由此形成多樣化、復雜化的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結構;經濟狀態發展不均衡,有些民族在新中國成立后才結束了前資本主義的幾種社會經濟形態一步跨入社會主義社會;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還有一些民族群眾信仰原始宗教,成為一種普遍而重要的社會存在,并且具有廣泛性、包容性、群眾性、民族性和國際性特點,輻射于社會和人生的各個方面;云南民族作家大多同時受漢語和母語雙重教育,語言本身所攜帶的文化基因潛移默化滲透到文化態度、審美追求之中;云南邊疆民族文學不是孤立存在的,中華文學格局影響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意識的內涵。在這種多元生活習俗與文化格局中,民族作家具有多重情感傾向和文化視角,需要實現對不同文化的多重超越,在作品中呈現出文化人格的復雜性、文本內容的多樣性與意識形態的復雜性,有追溯優秀歷史傳統的文化尋根作品,有融匯當下思潮意識與形式現代化乃至后現代文化的作品,滲透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地域中他族文化的因子,呈現出區域性民族文化融合特征,表現出豐富多層次的主題意識。
新世紀以來,一些作品把民族身份簡化為民族景觀標簽,在作品里滿目充斥著遙遠的大山、茅草的屋頂、優美的山歌、美麗的民族服飾、異彩紛呈的民俗節日等詞匯意象,認為這就是民族身份的原生態表現。但是這種風土氣息并沒有融入到民族性格與生活體驗中,缺乏對于民族心理結構與民族情感的深入描述,導致民族身份這個嚴肅主題變成了載歌載舞表演式的“最炫民族風”。云南民族文學的民族身份是一種價值觀念,原生態寫作中的民族身份表達不是放棄對時代重大話題的參與,也不是放棄對世界文學的展望與融合。民族文學的民族身份的原生態表達應該是對民族形象、民族文化的如實塑造與深刻反思,不能離開時代與地域的生活土壤,不能脫離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弘揚。
因此,新世紀民族文學對于民族身份的原生態表現不是復古到原始狀態,而是如實表現這種豐富的民族身份特征。比如,佤族作家伊蒙紅木的報告文學《最后的秘境》是作者深入佤山腹地,親自采訪境內外佤族山寨而寫成的涉及佤族遠古部落及當下的生存境遇、文化現象的作品。作者以現代性的警醒重新審視和認知自己民族的生存需求,以更開闊的文化視野,對本民族既有的文化重新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和解讀。如作者所言“這本書是我走訪了境內境外的佤族村寨整理出來的,我用紀實的形式,把我看到的認識到的佤族的民風民俗還有歷史記錄了下來。”這本書為我們在全球化、后工業化迅猛到來的時代,保留下了佤族山寨原生態的文化記憶,表明了作者自覺的文化擔當。
作為民族代言人的作家需要切入本族文化的精粹內容與變革歷程,積極汲取自己民族偉大的傳統與歷史文化,將民族精神與個體意識融為一體,將民族意識與中華精神融為一體,文化身份從單一向多重的綜合,成為民族文化身份意識的歷史性特征,進而形成對人類的終極性關懷。再者,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并不對立,“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不過我們一方面這樣重視外國文學,另一方面也不應拘守某一種特殊的文學, 奉它為模范。……對其他一切文學我們都應只用歷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還有可取之處,就把它吸收過來。”民族性與人類性(即人性)雖有區別,但從根本上說又是統一的,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學藝術原生態表達是追求一樣的人性中真正值得贊揚的美好品德。云南民族文學應該與世界文學中各個民族文學之間相互學習、相互對話交流、相互吸取、借鑒的論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和文學藝術。
繁雜多樣的云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背后深藏著對人與自然關系的一致性認同,它們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面貌講述著人與自然關系這一生態主題,是原生態文化中的重要母題。比如,創世史詩中,大自然與人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納西族的保護神“三朵”,就是玉龍雪山的化身;圣湖中居住著神靈,是孕育生命、庇佑納西族子民的地方。根據創世史詩,許多少數民族部落對于山中椿樹、紅豆杉、眼鏡蛇等自然造物,都持敬畏態度。佤族創世史詩中,人們與大自然和諧地生活在一起。阿佤人甚至贊美小小的蒼蠅、螞蟻,因為它小而善良智慧、具有實干精神。
生態文學也是新世紀以來的文學主潮之一。生態文學是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文學,而不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為理論基礎、以人類的利益為價值判斷為終極尺度的文學。生態文學以生態整體主義或生態整體觀作為指導考察自然與人的關系,它對人類所有與自然有關的思想、態度和行為的判斷標準是:是否有利于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即生態系統和諧、穩定和持續地自然存在。不把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并不意味著生態文學蔑視人類或者反人類;恰恰相反,生態災難的惡果和生態危機的現實使生態文學家認識到,只有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根本前提和最高價值,人類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態危機,而凡是有利于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的,最終也一定有利于人類的長遠利益或根本利益。
新世紀以來的云南民族文學中也充溢著生態表達意識,由于特殊的歷史、地理和經濟的諸多因素,邊疆民族地區的語言、文字、習俗、宗教、飲食、服飾、體育、教育以及各種傳統文化保留比較完好,在遼闊的邊疆背景下體驗大自然的壯美與民族文化的燦爛,書寫狩獵、種植、建筑、魚類、醫藥等生態觀念、行為模式和道德范式,書寫與動物重塑,樹立了自然倫理的尊嚴,表達了對過度技術化的反思,對樸素的民族性進一步深層體認。比如,白族詩人何永飛的《茶馬古道記》,以串珠式的結構,串起了這條西南地區千年生命線上的自然山川、人文風物、歷史民俗、人物傳奇,用生動的筆觸將之熔于一爐,再現了它作為生命之路與文化之路、通商之路與血緣紐帶之路的神奇與壯美。回族作家葉多多的散文集《我的心在高原》記述了云南這片土地上少數民族的生活故事,書寫真正的鄉村生活及鄉村人生存狀態,葉多多筆下的人物都是鮮活、富有個性的,人物的喜、怒、哀、樂都躍然紙上,她在寫這些人物的時候,自身也在與他們一起嘗受著這些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展現了中國云南底層的生活現實。林賢治在為她做的序言中說:“文學與土地的聯系,可以從先民們的關于勞動、游戲、節慶和祭神活動的文字中看出來,其中,生命直覺、生命力、生命狀態的表現生動而鮮明,后來,文學幾乎為官方和專業文人壟斷,當文學被供進廊廟和象牙之塔以后,生存意識日漸淡薄,人生中的辛勞、掙扎、抵抗、忍耐與堅持不見了,多出了瞞和騙,為生存的緊迫性所激發的喜怒哀樂也被有閑階段的嬉玩或無動于衷的技巧處理所代替,文學的根系一旦遭到破壞、枝葉枯萎、花果凋零是必然的事。”對葉多多作品中的生態性做了恰如其分的評價。2011年,昆明兒童文學研究會向全國兒童文學作家發出《生態文學倡議書》,并在昆明兒童文學研究會掛牌成立“兒童文學領域生態文學創作基地”。
新世紀以來,邊疆民族文學中對生態性的書寫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部分作品對“生態性”的文學表達有失偏頗,把生態特色簡化概括成標簽、簡化成對民族生活進行獵奇景觀式異化塑造。部分作品把生態性表達等同于“民俗”化表達,流于民俗展示、風情展演的淺表層面。還有一些作品在創作中建立起“傳統文化生態與現代社會破壞生態”的二元對立式萬能書寫模式,主體意象描寫孤獨的老人、衰敗的山寨、寂寞的鄉村、生態惡化的生存環境、精神迷失的年輕人,情節架構往往是“失樂園”模式,即某個云南民族群落寧靜質樸的生活受到現代城市文化與經濟的強勢沖擊,固有的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傳承千年的民族記憶被割裂、年輕一代的民族情感走入迷惘。這的確是云南民族面臨的普遍處境,也是現實生活遭際在文學中的真實反映,但這不是云南民族生活的唯一內容,也不是云南少數民族人民的唯一狀態。這種敘事固化在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沖突中,文學創作以邊地悲歌的形式追溯民族歷史曾經的燦爛與描摹當下的無奈,卻沒有從社會結構、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結構等方面進行開掘,忽視了對云南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為何會在現代進程中的被動弱勢地位的深入思考與叩問,于是,深厚久遠的生態文化傳統成為了抽象的、標簽化的祭幡,鮮活生動的生態意識也由此缺乏主觀能動性,缺乏對傳統思維的揚棄,缺乏在現代文化浪潮中繼續生長的自立自強的生命力。
云南生態文學的優勢在于它為作家提供了更廣闊的藝術空間,以進一步反思人類文明的弊端,但是,要寫好生態文學,作家必須克服盲目趨同的心態,盡快從一味的情感宣泄和浮躁的攻擊咒罵中擺脫出來,對伴隨人類社會發展出現的生態問題進行更為理性的反思。
新世紀以來,云南民族文學獲得新發展,屢屢斬獲駿馬獎,大量優秀作品呈現出新的創作面貌,與文學長河里流淌不息的原生態元素有密切關系。云南民族文學中的原生態元素既是寶貴的文學遺產,也是文學現代化轉型中的有活力的生長點,是文學多樣性的體現,也是文學發展的重要動力,是文學建設與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文化基礎,也是民族文學魅力和生命力的源泉。
【注釋】
[1] [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歷史的投影[M].夏克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7
[2] 哥布·我為什么用哈尼文寫詩——全球化語境下文化多樣性的意義探求與文學實踐.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發言
[3] [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M].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25
[4] (德)愛克曼輯錄,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M]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