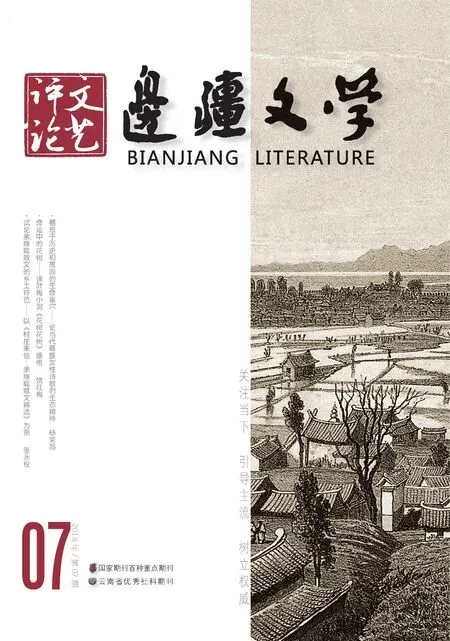日暮鄉關何處是 煙波江上使人愁
——讀鄭山明《鄉愁的滋味:那年·那事·那人》
沈德康
《鄉愁的滋味:那年·那事·那人》是鄭山明先生創作的一部散文集。此書語言簡潔、流暢,筆觸細膩、節制。作者飽含深情的追憶,讓“湘南故園”的風俗禮儀、世態人心、鳥獸蟲魚在讀者心中熠熠生輝。
每一個人都有令他魂牽夢系的故園。鄭先生筆下的故園,有難熬的春荒與秋旱,有糯米酒里氤氳出的醇香、“花喋婆”中飄出的閑適,也有舂水河畔的鄉民們直面生存困境、挑戰無常命運時表現出的勇敢、堅韌與善良。
當然,鄭先生的鄉土之思,并不全然是一種個人化的追憶。實際上,若換一種眼光來看,鄭先生的鄉愁也是近百年來國人在這曠日持久的“轉型期”里、在“城市化”(現代化)這一大背景下幾代人的鄉愁。更進一步說,鄭先生筆下的故園亦可謂是古今中外所有對人性還持有信心、對未來還抱有希望之人心中的“桃花源”,因而這里的故園既是“生我養我的故園”,也是令世人向往的“理想人性的家園”。一言以蔽之,這故園是坐落在我們每一個人心田之上的故園,這故園是對現代人浸淫其中的“技術時代”的超越與理想化。
一、“薄暮時代”的鄉愁
在鄭先生平實、質樸的文字里,飽含著對故土的眷念。這眷念,根植于鄭先生早年與土地的交道。在這“薄暮時代”,太陽西下,燈光升起,群星溺死在城市絢爛的“光污染”中。此時,恐怕只有農人才能真切地體味到那蘊含在“大地母親”這一類比中的深情厚意,恐怕也只有像鄭先生一樣從農村走出的游子才會萌發出刻骨銘心的思鄉之情。
鄉愁是寫給大地母親的詩,其間包含著一個明媚的意象:“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我們來到春天的田野,漫山遍野的晨露在朝陽中閃耀,透過圓潤、婉轉的露珠——這些大自然的眼睛——我們能感受到柔嫩而悠長的蔓草沁人心脾的綠,這是大地母親的心意。于是,在毫不起眼的野草中,我們“看”到了春天,難怪鄭先生也會如此寫道:“從來沒有人比農民更能接近春天,從來沒有什么活兒比割草更能感知春天。”
事實上,農人揮舞鐮刀割草時,是心懷感激的,這跟城市里的園丁像清除垃圾般用割草機一絲不茍地為草坪剪一個標準的“平頭”不一樣。在莫名的感激中,草兒更綠,春意更濃,大地母親也似乎更寬厚、更深情。其實,比大地還要深情的是割草的人。當把碧綠的狗尾草或開著小白花的“馬兒桿”割下、捆扎起來背回家一把把喂給家里飼養的白兔、馬駒、牛羊或雞鴨,此時此刻,你的心里會升起一種唯有當過母親的人才能體會到的溫柔與充實。
農人的生活的確艱辛,在鄭先生筆下,“雙搶”“抗旱”“打石灰”“挑煤”等營生讓每一個勞動者遍嘗生活的苦楚。如鄭先生所言,在“雙搶”時節,“割禾是很累的事。連續幾個時辰彎腰勞作,腰板又酸又脹,伸一下腰就能聽見腰椎嘎嘎的爆響聲。” 但是,那種與春水、山風以及默默奉獻的泥土打交道的過程,確實又飽含著城市人很難體會到的濃濃“詩意”。這種“詩意”根源于農人的生存境遇:在無限而神秘的長天與大地之間,在無數個寒來暑往、朝暉夕陰的輪回中,農人領會并確認了那“生于大地又歸于大地”的宿命,他們默默地接受大地母親豐厚的饋贈,也默默地承受突如其來的洪澇、饑饉與死亡,他們對人的處境以及人在天地間理應占有的位置具有遠比城市人更恰當的領會。
盡管“進步主義”的觀念已讓世人習慣了俯視甚至蔑視那個業已衰敗了的農業時代,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這“進步主義”的邏輯不過是維護著現代人尊嚴和信心的一種“獨斷論”。想一想我們的老祖宗是如何用“大同社會”“黃金時代”“桃花源”等理想以及堯、舜等前圣來錨定他們“退步主義”與“永恒復返”的歷史觀,我們或許就能洞悉作為一種“偏見”的“進步主義”的“偏見性”。
鄭先生的文字讓我想起了西方18到19世紀如盧梭、雪萊、海涅、華茲華斯、愛默生、梭羅等浪漫主義、超驗主義思想家和詩人,也讓我想起了我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如海子、顧城等詩人以及如莫言、劉亮程等小說家、散文家,這些“時代的歌者”,盡管時殊境異,但他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們對自然人性與淳樸人情的珍視,對山川湖海、大地蒼穹的熱愛,對無限宇宙的景仰與對弱小者的同情,對劇烈變動時代的種種不適應以及在遭受時代浪潮的沖刷、打擊之下對理想人性的憧憬與堅持。所以,正如一位潦倒的詩人所言:全世界的詩人都在詛咒城市而歌頌鄉村。這說法雖有些言過其實,但我們不難感受到現代社會特有的現實困境和思想危機帶給世人的那種深層次的困惑、焦慮與虛無感。
由此可見,鄭先生的鄉愁具有時代性、普遍性,絕非孤例。任何一個從農村進入城市并在時代洪流的裹挾下不得不修正或放棄傳統道德或信仰的人,他都會不由自主地懷念那個業已消逝了的、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的、閃著金光的世界。
事實上,忍不住地思念,根源于難以忍受的現實。因為不安,所以憧憬。哲學家說這是一個“懸于深淵的世界”,是漆黑的“夜半時代” ;詩人說“我們的習慣意識越來越局促于一座金字塔的頂尖上”,因而全然忘記了“我們是‘不可見者’的蜜蜂”這一實情 ;小說家則認為現代人的幸福都是“被幸福” ……因而,我們已很難體會到生命的神圣或神秘,也很難體會到“命運”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么。薄暮時分,這蔚藍的星球已淪為浩瀚星海中一艘迷惘的“航船”,旅人像晚風一樣疲憊和落寞,即使乘上銀色的翅膀追趕太陽,可在這無盡的虛空里,何處是那安頓心靈的家園?
二、何處是家園?
何處是家園?詩人荷爾德林回答道:“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 通過荷爾德林的詩句,我們或許能對幾個世紀以來飄蕩在大地之上的浩蕩“鄉愁”會有所理解。
如哲學家所言,一味地、單純地“筑居”只意味著現代人擁有了物質的、現實的“居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那“居所”便是“家園”。 “家園”是什么呢?“家園”不僅僅是用來遮陰避寒的棲身之地(生存),它還是思念的方向,是浩蕩鄉愁的策源地,是一開始就樹立在心田上引導我們不斷抵近理想人格的路標(倫理),是將天地四方的神靈與大地之上的有死之人建立起聯系的無比強烈的希望與詩意的想象(信仰)……一句話,“家園”不只是安頓人“肉身”的“家園”,它還是安頓人“良心”的“家園”,它更是安頓人“靈魂”的“家園”。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讀懂鄭先生筆下湘南農人在建房時“立門”“上梁”“封頂”等儀式中顯出的神圣性。此時,筆者也想起了湘南傳統民居庭院中常見的采光、采雨的“天井”,還有村落中不可或缺的“祠堂”,以及祠堂門口半月形的“池塘”中亭亭凈植、香遠益清的“蓮花”。從鄉村孑遺的古跡中,從天、地、神、人水乳交融的格局中,從風雨臨庭、家燕棲梁、荷香四溢的意象中,我們才能明白何為“家園”。
“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詩人荷爾德林喃喃自語。肉身是“沉重”的,生活“充滿勞績”,而苦難則是生活之舟必須負載的“壓艙石”。正因為人還能以“詩意”的眼光審視自己的有限與不幸,所以我們明白把“大地”稱為“母親”意味著什么,所以我們也能夠在想象中強烈希望,而正是這希望為人的生活鍍上了意義的金色。
“家園”是金色的,是等待收割的稻田,是“天堂的桌子” ,鳥群不時從中竄起,是農人感念的“谷魂”。望著這“金色的餐桌”,挨過了春荒的農人仿佛已嘗到新米的滋味。“家園”的確是一種滋味,在鄭先生細膩又充滿韻律的文字中,我們可發現“家園的味道”并不僅僅駐留在舌尖,而是需要我們通過“身體力行”的方式去參與、去欣賞才能獲致。對此,筆者以鄭先生的一段文字為例:
“豆腐師傅把石膏碾成粉末,和點豆漿存放在一個大缸里。看著鍋中的純豆漿煮開了,立即將其裝入兩個木桶里,兩個青壯勞力提起木桶站立在大缸兩側,豆腐師傅用手攪動缸里的石膏漿,速度越來越快,攪得石膏沾滿缸壁時突然將手抽出,大喝一聲‘倒’,兩個木桶的豆漿頃刻沖入缸中,‘啪’的一聲將大缸蓋好。幾分鐘后,在人們焦急的等待中,豆腐師傅慢慢地掀起缸蓋,將浮在表層的泡沫除去,原來液體狀的豆漿已變成晶瑩白嫩的豆腐腦。”
從上面這段引文,我們可以發現,人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美好,如此令人留戀,那是因為——人不僅活著,更關鍵的是人還能用欣賞的姿態來審視生活,用客觀、冷靜的態度來反思生活。正是在這樣的審視與反思中,我們擁有了“詩意”與“思想”。鄭先生筆下的豆腐師傅讓我想起了莊子文章中解牛的庖丁、斫堊的匠石。不論是庖丁還是匠石,甚或是湘南村中的豆腐師傅,與其夸贊他們的技藝如何精湛,還不如說他們已經學會了用一種超越性的、非功利的亦即詩意的眼光來看待生活。事實上,唯有能試著以這種方式看待生活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正是在此意義上,莊子表達了“逍遙”的人生境界;也正是在這個層面,尼采才會說:“唯有用審美的眼光打量生活,人生才是有意義的。”
“家園”何在?按鄭先生的意思,“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故我們的“家園”必然也是生長“愛”的沃土。如同大地與農人的關系,父母對兒女的呵護,這種天然的情感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滋潤著“善”的萌芽,并最終長成了挺拔的“德行之樹”。所以,家庭是人的“第一學校”,父母是孩子最初的教師,孩子在這里學到的絕不是“知識”“技術”,而是遠比“知識”“技術”更為重要的“道德”。對此,鄭先生深有同感,他在書中這樣寫道:“那時,學生們沒有被當作一個個裝知識的容器,而是作為一個個完整的有靈性的人來培養的……那時讀書最大的特點,就是學生始終沒有脫離大自然,沒有脫離日常生活,也沒有脫離簡單質樸的家庭關愛。” 古人云:“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 這是極為深刻的論斷。當我們為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而感到憂慮時,有誰可曾想到如今不堪的道德狀況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問題恰是因為我們的“第一學校”(家庭)受到了代表社會、國家的“第二學校”的嚴重“擠壓”?
現代文明是高度社會化、集約化的文明。文明的兩大支柱——“人的生產”(生育)與“物的生產”(經濟)——在我們時代都是十足計劃性的。如學者所言:“機械化(機械技術)和嚴格的社會組織管理(社會技術),這兩者本身在歷史上并非是新花樣,新的僅是這種機械化和嚴格管理現在已是有計劃地、有形地在統治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這種“整體主義”和“激進主義”傾向的“計劃”中,與過去相比,社會的細胞“家庭”的位置是極大地下降了,或者說傳統家庭葆有的“德育”的內涵被時代的浪潮侵蝕掉了。于是,“德”也在世人對“才”(工具性的知識與技術)的狂熱追求中喪失其作為“帥”的主導地位。故而我們時代的缺憾,用鄭先生的話來說即:“他們沒有學到比父輩更多的東西,卻喪失了許多祖輩傳承守望了一代又一代的東西。”
此時此刻,我想起了鄭先生筆下不時施展“楊梅爪”的父親,想起了為了兒女的安危而憂心惙惙的母親,我還想起善良、堅強的秀秀,為人師表的“高長子”以及盡職盡責的“駝子”……我們不難意識到,秉有傳統教育觀念的嚴父、慈母對于兒女健康人格的養成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正如鄭先生在書中所言:“每隔一兩個月,我就會抽空回老家看看他們,陪父親喝兩杯,和母親說說話,看到他們幸福愉悅的樣子,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 由此可見,我們的“家園”是“愛”的象征,是從倫理道德的維度指向生命意義和人生價值的坐標。
三、煙波江上的“返鄉之思”
我們處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技術時代”。在所謂“現代化”這一潮流中,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我們磕磕絆絆又匆匆忙忙地幾乎走完了西方四五百年走過的路。換句話說,“中庸”了數千年的國人對“技術”的傾情擁抱已經讓我們對“革命”這個概念所秉有的“激進主義”性質安之若素。所以,發生在這片神奇土地上的所有“偉大的革命”——無論是“社會技術”層面的還是“機械技術”層面的,甚或是“身體技術”層面的——對我們而言似乎都具有“絕對價值”。在這種“絕對價值”的背景下,那種浪漫主義的“鄉愁”往往因其保守主義的傾向而被視為不合時宜。但是,如學者所言:“浪漫主義所代表的理想的力量是現代文明的必要組成元素,我們今天需要的是把它轉換成可以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體現出來的模式。” 所以,在鄭先生的書中,所有那些對家園的美好追憶其實都散發著理想主義的光華,追憶過去則是為了更好地憧憬未來、創造未來。
在這個逐漸泯滅和混淆“人性”與“物性”之本質差異的“技術時代”,“社會技術”在各個層面都“機械技術化”了,人和由人構成的社會失去了應有的神性(不可剝奪的尊嚴),人們以對待物的方式來對待人,人們以操縱一臺機器的方式來管理社會。對于這個時代,《共產黨宣言》做出了大體準確的診斷:“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般的關系都破壞了”“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使東方從屬于西方”“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當我們讀懂了這本關于我們時代的“病歷”,我們對鄭先生書中的美好追憶才能有深切的體會。
在鄭先生的追憶中,我們的“機械技術”還沒有“高級”到把一個有尊嚴的人變成單純的“交換價值”,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書中描繪出的作為嫁妝的嗚嗚吟唱的舊式紡車上看到。在紡紗織布的同時,含辛茹苦的父母也將一曲關于鄉愁的歌謠送到了數十年后的游子耳畔。在那個“沒有使用農藥的年代”,田里種的是高梗水稻,圈里喂的是土豬,所謂的“良種”還未大行其道,人們在河里摸魚、田里抓鱔,感受到“煎魚送飯,鍋底刮爛”的生活況味。此時,人們為在草叢中偶遇一叢天鵝菌而高興,為酒壇子飄出的楓葉氣味而喜悅,聽著糯米酒發酵時在壇中清脆的嘀咕聲而滿懷希冀地進入夢鄉。在這“故園”,為了過年,人們不僅“殺豬”,還“殺豆腐”,人們尊奉“亥日不殺豬”的禁忌,也從炸豆腐中嗅到了濃濃的年味兒。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機械技術”得到長足發展的今天,我們擁有了無數的工具、商品,可是它們帶給人的“幸福”卻遠不如從前那些簡單的事物。對此,我們的學者指出:“若把現代和歷史做一比較,可從提供豐富、舒適安定的現代經濟的社會關系加以考察。在聽到人們把這些稱為人類進步的同時,這種社會關系卻犧牲了人類的精神價值,把所有的尊貴和美都犧牲了。” 的確如此,在這個崇奉“商品拜物教”并將“工具理性”視為至高價值的時代,我們把“物”的位置放得有多高同時也就決定了我們把“人”的位置放得有多低,我們把測度、加工和評價“物”的方式視為至高價值,這也就決定了我們必然以對待“物”的方式來對待“人”。對于這樣一種普遍“存在”卻尚未“自覺”的悲慘狀況,鄭先生書中對傳統手工技藝的詩意描寫就像是一劑解毒劑:
“這時補鍋匠左手拿一塊疊了好幾層的小布塊,迅速從地上掏一層草木灰在上面,大拇指在灰上面壓一小坑;右手用鐵鉗夾一個小泥勺,把爐中的鐵水舀到左手的小坑里,形成一粒圓圓的鐵水球。左手平穩迅速地移向那只鐵鍋,把那粒鐵水對準鐵鍋的裂縫,往上一抬,鐵水擠進裂縫變成了月偏食的模樣;右手放下鐵鉗,快速拿起一支用破布扎成的布柱,將布柱蘸上水對準那粒‘月偏食’壓下去,‘滋’的一下布柱被灼熱的鐵水燒出一道火苗。”
從這段引文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詩意的勞動者,還有詩意的觀賞者。勞動創造價值,但是勞動創造的價值絕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價值。勞動值得贊美,但是我們不能僅僅在功利算計的層面贊美。我們是人,我們不僅活著,我們還要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故此,我們勞動不僅僅是為了吃喝拉撒,我們還通過勞動去實現自己追求的那種人生意義——這即使是一個幻覺那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我們完全不用倫理的、審美的眼光看待勞動,那我們就跟非人的動物沒有任何區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詩人才始終強調:“棲居是以詩意為根基的。”
在鄭先生用文字搭建的“家園”中,我們確實看到了尚未被“機械技術”磨蝕殆盡的“詩意”。但是,在“社會技術”層面,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經過幾十年激進的“革命”,極少數像“木魚腦殼”那樣“腦袋空洞嗓門大、四肢發達一根筋”的激進分子的確是“昧了良心”,而大多數人則已麻木不仁了。所有這一切,我們可以在農民上交的“公糧”變成了“救濟糧”“救命糧”時他們錯愕的表情中看到,也可以從“把守在圩場的各個口子的基層民兵的吆喝聲”中聽見,還能從“停課鬧革命”“割資本主義尾巴”“‘吃肥肉的’受制于‘吃瘦肉的’”“四類分子”“現行反革命”等歷史名詞中讀出。還是聽聽我們的哲學家是怎么說的吧:“現代科學和極權國家都是‘技術’之本質的必然結果,同時,也都是技術的隨從。” 事實上,人的生存與發展都離不開“技術”,但是在我們的時代,“技術”的過度發展亦即技術對人與物的普遍強制毫無疑問是一種“病”,浩蕩的“鄉愁”則是其癥狀,就像發燒之于感冒,在本質上是“社會有機體”免疫功能的自動強化。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田里有“嗷嗷待哺的禾苗”,蒼天之下則有“嗷嗷待哺的農人”。如鄭先生所言:“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他們對得失已顯得有些麻木,他們不去抱怨蒼天,也不想去與社會抗爭,他們只是用自己的韌勁去詮釋一種生命的意義:人活著的價值就在于勞動。” 事實上,遠不止是“勞動”,人的價值不能僅僅從他者的角度被測算,它必須建立在一種主觀主義的對生活的信仰(熱愛)上,所以人的價值還在于用“詩意”的眼光審視和反思自己的“勞動”。對于這一點,筆者在前文中已多次談到。但是,筆者此時還是非常愿意用鄭先生對美好生活的暢想來印證這個看法:
“陽光從窗戶射進來,男人又在火塘上架起桌子,取一塊臘肉切成薄片,和青蒜、辣椒一起烹炒,肉和大蒜的清香夾雜著酒香裊裊飄飛在雪后初霽的湛藍天空。一壺酒,一場雪,一個咸淡的冬季。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作者系湖南科技學院講師、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