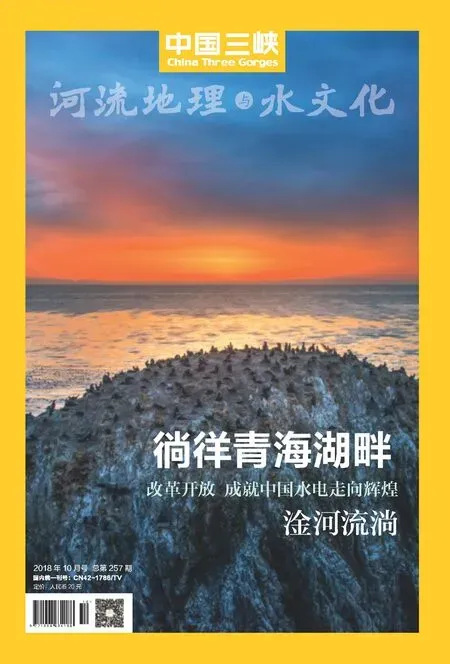宗喀巴與塔爾寺
◎ 文 | 耿占坤 編輯 | 孫鈺芳
情人喲!神佛喲!
我依戀情人,
卻犧牲了佛緣;
我入山修道,
又違背了情人的心愿。
天哪!天哪!
我愿隔世陷落豐都,
片刻也不離開情人的倩影。
——青海藏族民歌
日月山公平地將落在山頭的雨雪之水一分為二,一半向西形成倒淌河,穿過廣闊的草原流入青海湖;另一半則逐天下流水而東去,在窄峽寬谷之間匯集成黃河上游一條最大的支流——湟水,于是沿途地名就有了“湟源”、“湟中”這樣的稱謂。
湟水河的南、西、北三面山巒環繞,向東一面敞開,直奔黃河,從而營造了青藏高原東北部最大的河谷走廊。這條走廊所創造的人類文化,被史籍與黃河上游文化并稱為“河湟文化”。
湟水流域堪稱世界上最大的彩陶文化博物館。1973年出土的“舞蹈紋”彩陶盆,距今4000多年歷史,已成為中華彩陶文明的象征。
止貢巴·貢卻丹巴然杰在《安多政教史》中,曾引用乃東·曲吉尼瑪尊者如此充滿激情的描繪:“這里有‘恒河之妹’的湟水,河水滔滔向東。其南北兩岸的廣大土地,美麗富饒,人稱宗喀。南部的積石山脈逶迤磅礴,伸向遙遠的天邊,被譽為‘第二佛陀’的宗喀巴就在這逶迤壯麗的山腳下降臨人世。”《圣地頌》中贊道:“此地形似八瓣蓮花,天空宛如八個轉輪;后山雄偉而優雅,前山象谷物堆就。”
被尊為“第二藍毗尼園”的塔爾寺就座落在這朵盛開的蓮花之中。六百年來,它由一片美麗的山間牧場成為藏傳佛教的圣地,成為千千萬萬信徒們的身心歸宿。
“第二佛陀”誕生
1357年,這里的人們總是不經意地看到,已有三個孩子的藏族婦人香薩阿切幾乎每天都背水走過這片山間谷地,她在負重途中總要在一塊石頭上靠停下來休息一陣,因為那時她已懷有身孕。到了金色的十月,香薩阿切順利地生下了她的第四個孩子,就在這片草地上,她剪斷臍帶,幾滴鮮血悄然滲入草下的泥土。聽著嬰兒的呱呱啼哭,母親的臉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此時的香薩阿切同所有認識她的人一樣,絕對沒有意識到她已經成為一位至尊的圣母。直到第二年,那臍血滴落的地方生長出一株翠綠的菩提樹,十萬片葉子上每片都呈現一尊獅子吼佛(釋迦佛第七化身)像,因此取藏語名為“袞本”(十萬佛身像)。雖然大家都欣喜地相信這是一個吉祥之兆,但并沒有誰清楚它真正意味著什么。
香薩阿切這第四個孩子于七歲時出家,在距家鄉以東數十公里的夏瓊章(今化隆縣查甫夏瓊寺)授于沙彌戒,當時的寺主、藏傳佛教高僧敦珠仁欽為其取名羅桑扎巴,密號頓月多杰。這就是一代宗師宗咯巴。顯然,宗咯巴的稱謂是他后來在西藏取得很高地位之后人們對他的尊稱,意為宗咯(湟水河畔)人。
宗咯巴不僅具有聰慧無比的天資,他對佛學更具有一種敏銳的悟性。在他僧人生涯的最初十年里,師從敦珠仁欽,到17歲時,他在佛學方面已經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也就在這一年,受敦珠仁欽的鼓勵和資助,宗咯巴赴西藏游學深造。

湟水河 攝影/張國財
也許宗咯巴注定要成為一代宗師,他在西藏求學期間并不始終依附于一個門派之下,而是廣學博采,顯密并修,終于博通顯宗、密宗技法,成為一代高僧。宗咯巴于29歲時受比丘戒,此后開始接收門徒,講經弘法,他敏銳的思維、嚴密的邏輯、獨到的見解在同各派的辯經中屢戰屢勝,在藏傳佛教界以及民間逐漸獲得聲譽。到40歲前后,宗咯巴對顯密教經論已經有很深的造詣,他繼承阿底峽所付龍樹的中觀思想,吸取薩迦派的道果法、噶舉派的手印法和寧瑪派的圓滿法等各派法要,形成了自己的佛教思想體系,并進而展開了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宗教活動。從43歲到53歲的十年間,宗咯巴集中撰寫了闡述自己思想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為創立格魯派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他一生著作達一百七十部之多,因而被稱為“百部論主”。在著書立說的同時,宗咯巴還積極進行宗教改革活動,主張僧人應嚴守律戒,廣學經典,先顯后密,顯密雙修等。1409年,宗咯巴利用他的影響發起不分教派和地區、有萬人參加的拉薩祈愿大法會,這就是傳承至今的傳召大法會之創始。大法會的成功,使宗咯巴獲得了西藏佛教領袖的地位,同年甘丹寺建立,標志著藏傳佛教格魯派正式形成。格魯派形成后迅速擴展實力,在中央王朝、西藏地方政權和信徒的支持下,很快就超過原有各教派,成為在藏族社會長期占領導地位的教派,并逐漸集政教權力于一身。因格魯派僧人戴桃形尖頂黃色僧帽,世俗又稱其為黃教。
宗咯巴于1419年圓寂于甘丹寺,他的一生充滿了種種神奇。
1378年,22歲的宗咯巴在西藏收到了母親托人帶來的一綹白發,并附信說“吾已年邁體衰,望兒務必返里一晤”。宗咯巴對母親和家鄉充滿思念之情,望著母親的白發,他仿佛看到了母親那深切期盼的目光,但最終他還是決意學佛不返,讓人給慈母和姐姐帶回血繪的自身畫像一張、獅子吼佛像一軸,并在信中說:“倘若在我出生的地方,以十萬獅子吼佛像及菩提樹為胎藏建一佛塔,則如同親晤兒面。”第二年,宗咯巴的母親依照兒子的囑托,將由臍血而生的菩提樹用綢緞包裹,與印成的十萬尊獅子吼佛像共為胎藏,建成一座蓮聚寶塔。據說,最初的菩提塔只是磚石結構,塔身很小。

酥油花雕塑 攝影/董寧生

塔爾寺唐卡珍品 攝影/殷生華
蓮花中的珍寶
一百多年后的1560年,靜修僧仁欽宗哲堅贊來到這片幽靜而神圣的山間谷地,他在距蓮聚寶塔不遠處修建了一座供其誦經坐禪的參康(禪堂)。寒來暑往之間,僧人的慧眼終于觀悟了這凈地的勝妙之處。從蓮聚寶塔環望,四周由八座平緩的山峰環繞,每座山峰均呈蓮花瓣形。夏秋季節山色一片青翠,山間流水潺潺,高空云雀啼鳴,一派幽靜祥和,幾座青山襯映在蔚藍的天幕之中,呈現一個巨大的優波羅(青蓮)花狀;冬春時節山峰白雪皚皚,一片靜穆圣潔,超然世外,八座玉峰又組成了一朵勞陀利(白蓮)花狀。座座山峰之間碧空高遠,瑞氣凝霞,光芒勁射,猶如八根輻輪,恰似法輪常轉,傳播著永恒的妙諦。
于是在1577年,一座佛、法、僧三寶俱全的彌勒佛殿在菩提塔南側正式建起了,藏語合稱為“袞本賢巴林”,意為“十萬佛身彌勒洲”。以后四百多年間,佛寺不斷擴建,菩提塔也幾經修繕裝飾而被置于殿內。據說因為先有佛塔爾后有佛寺之故,便有了“塔爾寺”這個漢語俗稱。
今天的塔爾寺已經形成了一座占地40多公頃、漢藏建筑藝術相互輝映的古剎建筑群。我無法猜測,當年香薩阿切帶著對兒子的深切思念而建起那座簡樸的佛塔時,是否預知這里將會成為多少善男信女、多少圣賢和凡夫俗子身心向往的圣地呢。當年那些在這山間背水的女人、牧羊的少年一定沒有意識到,那株由宗咯巴的臍血而生長的菩提樹,會給這偏僻的山隅帶來一座佛國圣城。

塔爾寺如意八塔 攝影/殷生華
塔爾寺的中心是大金互殿,是覆蓋于蓮聚寶塔之上的塔殿。寺中主要建筑還包括:小金互殿、大經堂、文殊菩薩殿、釋迦佛殿、祈壽殿、印經院、如來八塔、依估殿、遍知殿、花院以及供僧人學習研究天文歷法、舞蹈藝術、醫學、密宗、顯宗等學識的“扎倉”。還有眾多依山而建的僧舍。
作為宗咯巴的誕生地,塔爾寺無疑是青藏高原藏傳佛教的重要寺院,但它的重要性還遠不止于此。寺院珍藏的經卷、文獻資料浩如煙海,不同時期、不同風俗的雕刻與壁畫以及各式各樣的宗教法器數不勝數,更以精美的壁畫、獨特的堆繡和奇妙的酥油彩塑“藝術三絕”而著稱,從而使它成為一座文化藝術寶庫。數百年來藏族社會政教合一的歷史,又使塔爾寺成為一個集政治、經濟、文化等世俗權力于一體的中心,是一部研究藏族社會歷史的百科全書。寺中各種金玉珠寶琳瑯滿目,僅它們的商品價值就難以估量,更不用說那賦予它們無限身價的宗教與文物價值了。塔爾寺在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根據三世達賴和四世達賴的要求進行大規模擴建,此后,第五、七、十三、十四世達賴和第六、九、十世班禪都在此駐錫。清康熙以后,歷代帝王都對它格外重視,多次向塔爾寺賜贈匾額、法器、佛像、經卷、佛塔、金銀珠寶等,從而使塔爾寺的地位不斷提高,影響更加深遠。據說在塔爾寺全盛時期曾有建筑物近萬間,僧侶3600多人。
對于所有現代的觀光游客來說,塔爾寺只是他們生活經歷中的一個驚訝。他們匆匆而來,匆匆而去,一知半解地聽完導游一成不變的解說詞,腦子里留下一片輝煌、一片神秘、一片空白,然后這一切在他們的生活中很快就淡漠了,假如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們有機會偶爾接觸到這個詞語,他們或許會說:“噢,塔爾寺?我去過。”
對于數不清的信徒,那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塔爾寺、宗咯巴、佛祖、瑪尼等等,這一切沒有根本的不同。他們來到這里,不在于追溯它的歷史,也不在于欣賞它的藝術,而來到就是目的。他們匍匐于金瓦之下、紅墻之間、佛殿之前,他們轉經、祈禱、唱頌,他們將自己的靈魂、肉體、財物和自己的來世無條件地交付到這里,從而獲得身心的解脫和撫慰,達到寧靜與幸福的境界。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除了佛祖,沒有誰注意他們、記得他們。
走進塔爾寺的兩種方式
我有機會一次次地來到塔爾寺。假如我是一個觀光客,我早已厭倦了;假如我是一個信徒,我也許多少也該獲得某種佛緣了。然而我既沒有絲毫倦怠,也沒有半點得道,我只是一次次到來、觀看、感受。我體會到,進入塔爾寺的內在之處有兩種渠道。一種是走進大金互殿或大經堂,在幽暗的光線下仰望大銀塔或在數百名僧人的誦經聲中悄然佇立,當我在無意識中屏住呼吸的那一瞬間,我進入了它的奧秘。另一種就是遠遠地觀望,在這種狀態中我能夠輕松地吸著香煙甚至哼著優美的曲調。

夏日塔爾寺 攝影/張國財
塔爾寺宏大的建筑使你相信那些殿宇中有足夠的空間任你的精神飛馳,然而當你一旦進入,那想象中的自由就立刻不存在了。在所有的殿堂中我都深切地意識到,這里的時空并不屬于我。高大莊嚴的佛像、威猛獰怖的金剛、神秘的靈塔與佛龕、壁畫和懸掛于間堂的布畫、各種吉祥物與裝飾物占據了寬闊的殿堂。殿堂內光線低暗,幾乎沒有來自外界的自然光線,一排排的酥油燈長明于佛像之前的供案上,燈光閃耀跳動,使殿內的一切都處于忽明忽暗的氛圍之中,佛像的金身、鑲嵌于各處的珠寶發出奇異的光芒。偶爾有一兩個僧人無聲地走動于殿堂之中,卻更增添了氣氛的肅穆。這時我感到,時間在這里早已凝結了,如果它存在,也只能以“劫”來計算,對于我來說,這無疑代表一種永恒。因為在這里,我們世俗中一切顯示時間存在的事物都消失了,陽光的游移、風的吹拂、水的流淌,更不要說鐘表的擺動。這時候,我就產生這樣一種感覺,我的身體雖然沒有像信徒一樣五體投地,但我的靈魂早已匍匐在地下了。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歡樂或痛苦都無法獨立而自由地存在,它們被一種超然的力量統攝著,繼而被徹底消解轉化,變成敬畏之感。這種敬畏消失之后,我便進入了一個空寂的寧靜狀態。
多數時候,我總喜歡爬上寺院北面的一座山包,靜靜地坐下來去縱覽眼前的一切。這使我再次成為游客與信徒之外的另一種人,因為游人難得這樣充裕的閑暇,而對于信徒,這種居高臨下無疑是一種罪過。
與在殿堂中的感覺完全不同,在這里我可以擁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我可以隨意開始或停止看、聽、想等一切行為。在藍天白云覆蓋下的這片山巒沒有什么奇異之處,我凡俗的目光無法分辨山峰的蓮花之形,它們平凡得如一支牧歌,但它們寧靜青翠,的確很美,也美得如一支牧歌,沒有任何令人身心厭倦的雕琢之痕。山巒之間是塔爾寺宏大的建筑群,在陽光照耀下,最醒目的是幾種交相輝映的色彩,金黃色的殿頂,班禪行宮和大殿的紅色,灰色的飛檐屋角,潔白的墻壁。

塔爾寺大殿廣場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跳欠法會 攝影/殷生華
塔爾寺的建筑群中漢式歇山頂和藏式平頂共存,建筑物依山就勢,錯落有致,不追求宮廷式的嚴謹與對稱布局,而是在變化中求和諧,顯示了藏傳佛教寺院與漢傳佛教寺院完全不同的特點。漢佛教寺院大多采用軸心對稱的宮廷式建筑格局,各大殿前后排列、相互對應貫通,層層升高,體現了與封建王權相一致的嚴謹、刻板和不容打破的規則,充分表現了對世俗權力和世俗文化的趨同。而藏傳佛教寺院在布局上則保持了更多的自由,在地形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寺院建筑努力以一個中心為基點,呈四周輻射狀態,猶如各大部洲環繞著神圣的須彌山一般,仿佛在講述一個佛教的創世故事。像塔爾寺這樣地形條件不具備的寺院,建筑風格更加豐富多樣,不要求對稱或統一,殿宇隨自然地勢而建,遙相呼應,顯示了一種變化中的和諧。
塔爾寺的外觀與殿內形成了鮮明對比,豐富多變的色彩和高低錯落的殿宇,或隱或現于山間植物的蔥郁之中,它們共同營造了一個全新的時空,這個時空不是凝固或僵化的,而是開放性的,使得人的思緒和情感與佛的精神和奧義之間能夠交流,將世俗與圣境兩個世界溝通起來。由于山、水、云、樹這些自然事物的參加,使得塔爾寺不再是一個單一的人文事物,它與自然共同組成了一個復合景觀,建筑物和各種色彩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山水與樹木又成了人文不可缺少的成分。我深信這種構成絕不是一種巧合,它體現了自然精神、宗教倫理和人類情感的交織和相融。崇尚自然的我忽然間產生這樣一種感覺,六百多年以前的多少個世紀,這些山巒、這片綠色以及這條小小的溪流,它們是多么孤單和寂寞。我覺得,塔爾寺的奧秘就在于體現了這種神、人、自然的三位一體。
由于旅游業的發展,寺院的幽靜只能在早晚的時刻才會出現了,多數時候,道路和殿宇之間運動著的色彩已不再是以暗紅色的袈裟為主,而更多的是男人們的西裝革履,女人們各色各樣的長衫短裙。從殿宇之中仍然有法鼓長號和深冗的誦經聲不斷傳來,但它們常常被汽車的轟鳴和游人的喧嚷所淹沒。在我的印象中,始終如一的依舊是那些虔誠的朝圣者,他們和她們悄然地匍匐在每一座殿堂、佛塔和每一塊磚石之前,一步一叩,五體投地,全然不去在意汽車揚起的塵土和游人匆忙的腳步,除了心中的佛祖,他們身外旁若無人。
在這個山頭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佛界與塵世之間難以隔絕的聯系。塔爾寺西面一個山包之隔,是一座最初依托塔爾寺而興起的名為魯沙爾的小鎮,目前是縣政府所在地。近些年來,隨著旅游業的興旺,小鎮的發展也格外快起來,餐飲、賓館、娛樂設施不斷增加,樓房到處生長。一條經過多次擴建的寬闊道路從縣城中心直通到塔爾寺的山門,道路兩側無例外地是一間間出售宗教用品和以藏族風格為主的各式旅游紀念品的小商店。有趣的是,在這個佛教中心從事相關商業活動的絕大多數是回族,他們毫不含糊的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物質與精神、商品與文化就這樣和諧地聯系在一起又微妙地分離著。象征釋迦牟尼一生八件大事的如來八塔所在的廣場,現在是各種旅游車的停車場。一直令我費解的是,幾年前的一次維修中,原來的八座舊塔被徹底替換了,取而代之的是八座裝飾鮮艷的新塔。它們真的比以前那些顯得破損的舊塔好看多了,我猜想,當游客以此為背景照相留影時,彩色效果一定更勝于原來那些經歷了百年風雨的舊塔。然而每當我站在這里時,我總是很強烈地懷念那幾座舊塔,因為這些新塔不對我說話。
塔爾寺同西藏的布達拉宮、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和甘肅的拉卜楞寺共稱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中心寺院,在數百年的歷史中,它們既是神權、政權和財富的象征,精神與物質的體現,更成為藏族社會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匯集之地。在六大寺院中,塔爾寺是規模較小的一座,但它的地位無可取代。
宗咯巴對藏傳佛教的貢獻遠非只是創立了諸多教派中的一種,而是對藏傳佛教的發展興盛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格魯派的地位
十四世紀后期,西藏佛教各教派處于混亂低落狀態。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一代宗師宗咯巴已經把顯密宗各派的教法全部系統地學習和掌握,他淵深的學識和敏銳的思想無人能比,享有極高的聲望。針對西藏佛教界的種種弊端,十五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宗咯巴通過講經、辯經、著書立說等一系列活動,發起了一場“宗教改革”運動。宗教改革因得到民眾的擁護、地方政權的支持和宗教界的響應而得以順利進行。宗咯巴在噶當派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因而當時又被稱為“新噶當派”,格魯派發展起來后,噶當派歸于格魯派。“格魯”意為善規,直接道出了這個教派的根本特征。

格魯派僧人服飾 攝影/殷生華
從宗咯巴兩位弟子傳出格魯派兩大活佛轉世系統:達賴喇嘛,全稱“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這是一個梵、蒙、藏語組合的名稱,意為精通顯密學識如大海一樣淵博的至圣大師。被認為是觀世音的化身。班禪,全稱“班祥額爾德尼”,梵、藏、滿語組成的名稱,意為珍寶大學者。被認為是無量光佛的化身。兩個活佛系統均在其五世時受到清朝皇帝的冊封。1751年,清政府下令由七世達賴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權,從而格魯派正式取得對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長達二百余年。
宗教擁有對信徒思想和精神上的絕對統治是不言自明的,而藏傳佛教所以同時能取得世俗權力具有特殊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藏族社會沒有世俗教育,寺院就是教育中心,進而也就成了文化中心,藏傳佛教寺院掌握著歷史、哲學、文學、天文、歷算、醫學等所有知識,從而也很自然地控制了經濟、貿易、農事、畜牧和文化生活方面的權力,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宗教的依賴還包括:醫病、占卜、擇吉、念經、念咒、祈福、 攘災、超薦亡靈、祈雨防雹等等。另一方面,佛教在藏地傳播之初便是自上而下,即從王公貴族開始的,到后來,許多封建領主本身就是法臺或寺主,寺主、活佛擁有莊園和領地,不僅擁有教徒而且擁有農奴。同時,自明清以來,中央王朝均極為重視和推崇藏傳佛教,不斷對其宗教首領進行冊封和賞賜,使他們的世俗地位和權力不斷提高與加強,最終使宗教領袖得以“大皇帝”之名行使世俗統治權。

幾位藏族人在塔爾寺磕等身長頭為家人祈福。 攝影/劉浪/視覺中國
藏傳佛教的眾多寺院中,生活著大量的僧尼。僧尼們的生活因其等級地位、職業分工以及教派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僧尼的生活充滿神秘,他們既食人間煙火,又守持種種律儀;既向往寧靜超脫,又追求成就和幻想。他們跋涉于世俗和神界之間,既可轉身成為丈夫或妻子,也能夠潛往深山獲得超凡的瑜伽神力。
僧人生活與我們生活之間的距離遠不只是相隔一道山門或一件袈裟,實際上他們與我們分屬兩個不同的文化和精神世界。而他們那個世界我無緣進入。于是,更多的時候我轉而去努力接近那些朝圣的香客。
塔爾寺的香客以安多藏區最多,還有不少來自西藏、四川和云南藏區,也有來自內蒙的。信徒以藏族為主,也有大量的蒙古族、土族和漢族等。我常找機會和這些香客聊天,同所有好事者一樣,我有時會因為語言不通或者對方不愿交流而被一陣沉默或一個微笑回絕,有時也能談得很投緣。
與香客的對話
我一直記得在塔爾寺遇到的來自云南迪慶的一家人,兩個女人和一個男孩。那時她們正圍繞著寺院磕長頭,坐在如來八塔附近休息。我走過去同她們答話,沒想到她們的漢話竟說得很不錯,當我知道她們來自云南中甸時,我高興地說,幾個月前我去過中甸,還去了松贊林寺,那是個很美的地方。我的話把我們之間的距離一下拉近了,她們用驚訝而欣喜的目光看著我,氣氛頓然融洽起來,因為她們的家就往在中甸縣城附近。于是我在她們對面席地而坐。她們問我到中甸去干什么,我回答說,同你們一樣。這使她們疑惑起來。當我簡單說了我在中甸到過的地方和經歷的事情后,我看得出來,她們相信我沒有撒謊,但她們糾正我說:你那是旅游。我們都笑起來。這是祖孫三代,老婦人大約五十至六十歲之間,她的女兒三十來歲,外孫子十歲左右,我問她們的名字,老人只告訴我她女兒叫拉姆,男孩叫扎西。在一種同鄉的感覺中我們聊得很融洽。老人十幾年前按照當地一位活佛的卜算,曾同她的丈夫一起來塔爾寺,那時她們在宗咯巴大活佛面前祈過一個愿,這次是專程帶了女兒和孫子來還愿的。我不好問是個什么愿,因為那是她們同佛祖之間的秘密,但從老人的話中我猜想那一定與女兒和外孫子有關。我問她們給了寺院什么布施,拉姆說因為路途很遠,帶不了什么東西,只有一點錢。我問有多少錢她卻笑而不答。
拉姆一家在中甸以農業為主,她說這些年生活很富裕,所以出門很方便,一路坐車,晚上可以住價格不高的旅社,而十多年前,她的父母出來時卻歷盡了艱辛,夜晚無論多冷都露宿在墻角樹下,白天要轉經磕頭,還常得忍受渴饑,現在就不用受那些罪了。老人對這話似乎有點不太滿意,她表情嚴肅地說,可佛爺在保佑我們。拉姆知錯地吐了一下舌頭。拉姆告訴我,她們這次的旅程非常遙遠,等離開塔爾寺后,她還要和阿媽與兒子一起去拉薩,這次朝圣她們計劃兩個月完成,她們剛離家十幾天時間。雖然現在交通很方便,但我能夠想象她們未來的旅程仍然會十分艱苦。

青海湖風光 攝影 / 東方 IC
祖孫三人又要起身繼續磕頭了。我問拉姆,為什么不到大金互殿那里磕頭。拉姆很風趣地笑著說,還沒排上隊呢。
我默默地望著她們一叩三拜地朝前而去。藏傳佛教信徒這種獨特的叩拜方式對我的心靈產生一種震撼的力量。我曾在青海湖畔的草原上嘗試過這種磕長頭的方式,雖非出于信徒的虔誠,也并不完全是一種游戲,它使我體會到了五體投地的那種謙卑之感,只有幾十米的距離,我已感到腰酸背疼。我從心底由衷地欽佩信徒們那源自心靈的意志和力量。有時我這樣想,一個人在一種超然寧靜又滿懷感恩的心態中,進行如此的身心旅行,豈不是一種對精神的升華、身體的鍛煉和意志的磨礪?未必這不是佛祖為眾生賜福和禳災去病的妙法。
透過信徒們寧靜的表情和他們謙卑的身影,我深深感到,不是黃金和珠寶、也不是香薩阿切和他非凡的兒子創造了塔爾寺,而是世世代代、千千萬萬的男女創造了它。宗教除了是一種信仰、一種寄托,更重要的是一種與他們的身心融為一體的生活方式。正是由于集納了無數男人和女人的希望、歡樂和愛,集納了他們的真誠與智慧,塔爾寺才成為一塊閃射著人類精神光芒的物華天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