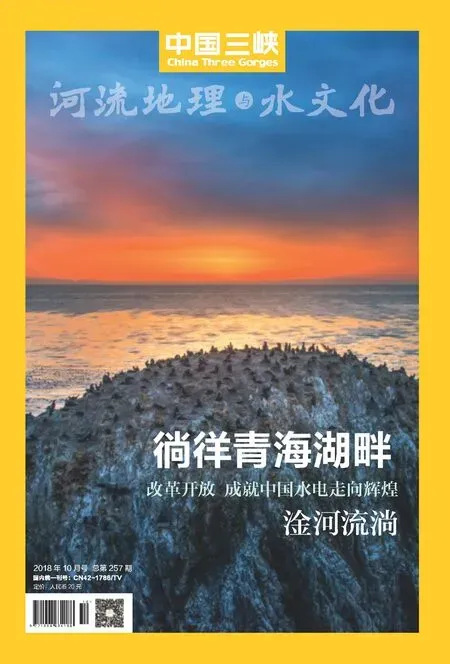故鄉滋味長
◎ 文、圖 | 伍紹東 手繪 | 帥圣生 編輯 | 王芳麗
1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剪春韭,就應該趁著夜雨。一場春雨之后的新韭菜,特別鮮嫩。與此對應的,是冬天的雪地里,白茫茫一片,母親從積雪中撈出一顆卷心菜,哎呦,那個沉甸甸的嬌嫩啊。清炒卷心菜,或者放幾片臘肉,美味極了。
城里總吃不應季的菜,從而感受不到春天的菜、夏天的菜、秋天的菜、冬天的菜各自的滋味,也就難以感受到四季的滋味,因此很難有葦岸在《二十四節氣》里的感受:一個“驚”,一個“蟄”,兩個平淡無奇的漢字,組合在一起就可以有無窮的想象。太陽升高了一些,土壤開始溫暖,冬眠的蟲子醒了,莊稼開始冒芽,春天的菜,就要開始破土而出了……
2
初中時,大概是清明前后,地里的第一茬蠶豆出來了。母親煮好嫩蠶豆,叫父親騎車送到我宿舍。我當時在上課,宿舍里有其他同學在睡覺。父親將蠶豆放我床上,就回家了。
五天后,我周末放假回家,才得知父親送過蠶豆。原來,最新最嫩的蠶豆太香了,被我同學偷吃了。
父親叫我不要追究:同學嘛,吃就吃了,想吃現在就去地里摘。地里的蠶豆,就像魯迅《社戲》里寫的,“烏油油的都是結實的羅漢豆”。我還在埋怨著同學,怎么就不能像《社戲》里的阿發,只偷自家的蠶豆呢?父親已經摘了滿滿一籃子,胖乎乎的,沉甸甸的。
3
“胸中歌千首,都為家鄉山水留。”想起故鄉的歌,印象里最深刻的,一是陽春三月的時候,母親跟村里的女人一起,用土話唱《四季歌》。那時候我還小,母親還年輕,我覺得母親真好看。
二是有一年冬天,外面飄雪,各家大門都緊鎖著。我們一家人圍著爐子烤火,外面有一家人賣唱,有拉有唱,唱完后敲門乞食。母親并不嫌棄,立即開門,送兩角錢,再遞一碗熱飯。賣唱的是外地人,我聽不懂他們的話。他們唱的歌,現在想來,像是《紅樓夢》里的《好了歌》,“荒冢一堆,草沒了,草沒了,草沒了……”然后,唱歌的人越走越遠,只留白茫茫一片……
母親說他們是安徽人,逃荒到我們縣城。
4
故鄉的山藥,跟外地的山藥一點兒都不像。
它的形狀像人手。相傳禪宗四祖司馬道信小時候體弱多病,他母親挖山藥燉湯給他喝,病就好了。后來,道信專門培育這種山藥。再后來,故鄉人就把這種山藥叫佛手山藥。
佛手山藥產于梅川北邊的山里,就是故鄉最北的屏障——橫崗山,屬于大別山的尾梢。佛手山藥比外地的鐵柱山藥好吃多了。山藥燉肉,再放一把故鄉特產豆腐果(豆泡),是故鄉的一道名菜。
初中時,有天晚上我發燒,躺在宿舍很難受。附近一位教師家屬打開水路過,看見我憔悴的樣子,就回家燉了山藥和排骨豆腐果,給我送來一大碗。我趁熱吃完,出了一身大汗,居然漸漸燒退了。當時我很靦腆,只會說“謝謝這位娘”,居然不知道問她名姓。后來也再沒見過,想來遺憾。
5
中學時,我們的語文老師很不討人喜歡。他講課照本宣科,讓人昏昏欲睡。我們私下里給他起難聽的綽號。但是,有幾節課,讓我印象深刻。
一節是講林覺民的《與妻書》,講得十分動情。一節是講歸有光的《項脊軒志》,也同樣聲情并茂,尤其是文中那句“兒寒乎?欲食乎?”非常打動人,如今讀來,仍能讓我想起母親的很多事。小時候家里沒有什么補品,母親每天早上都會給我和哥哥蒸一碗雞蛋羹,或是用開水加冰糖沖一碗雞蛋花。
還有一節課,是另一個語文老師講魯迅的《社戲》,一群少年相約去看戲,架起兩支櫓,劃白篷船,小河水聲潺潺,兩岸是碧綠的豆麥田地。長三角水網密布,到處是汊港,村莊林立,特別容易形成鄉愁。多年以后,我還記得課文中的小河流、青草香、偷自家蠶豆的阿發、劃船時的那個輕快,以及漁火里忽明忽暗的故鄉。
6
記憶中,母親幾乎從來沒有批評過我,更沒有打過我。唯一的一次責備,讓我刻骨銘心。
那年我家筑新屋,缺錢用。9月1號,我升四年級,母親帶我去學校報名,結果學費漲了,錢不夠。報名老師還沒說話呢,我一下就委屈得哭了起來。母親恨我不爭氣,說了一句特別重的話:“男伢哭什么!哭你娘死了啊!”
我立即就消停了。一來,我知道母親是讓我堅強一些;二來,我也很難過,不是因為委屈,而是驚詫于母親怎么這樣說她自己;三來,我才知道,原來母親也是可以對我不好的。一個人并不是必須要對你好,她對你好,只是因為心里有愛。
7
我小時候倔強,遠近聞名。父親年輕時脾氣也暴躁,曾經提起我的雙腿,倒著打。所以小時候,我恨了父親一段時間。和解的那次,發生在我上初一那年。有一回上課的時候,我在窗戶邊看見遠遠走來的父親。他推著單車,車后綁了一箱東西。父親等了一節課時間,我一下課就飛奔過去。原來,父親廠里發了麥飯石飲料,一下班,他就送過來了,因為我們以前從來沒喝過這種叫“麥飯石”的東西。
父親越老越溫柔。他后來對我侄女、侄子的疼愛,簡直就是溺愛,有求必應,有打必護。父親晚年對我,也是特別溫和。2010年,我過年回家探親。父親帶我到地里摘橙子、枇杷。一不留神,只見六十多歲的父親,像猴子一樣爬到枇杷樹上。仿佛只要我愛吃,父親愿意去做任何事。

金燦燦的橘子很打眼 攝影/伍紹東

我哥盤弄的菜園 攝影/伍紹東
六十多歲的父親如此健碩,誰知道幾年后他的身體就垮了呢。
8
“家兄酷似老父親,一對沉默寡言人。可曾閑來愁沽酒,偶爾相對飲幾盅。”正如這歌詞里唱的,父親和我哥都是沉默的人。兩個內向的人之間,容易憋話、生悶氣。父親不善于表達愛,我哥從小就不善于撒嬌;嚴父很少去夸獎孩子,我哥也甚少去炫耀成績;父親年輕時候脾氣不好,我哥青春期又很叛逆。所以記憶中,我哥和父親之間一度關系緊張。每逢父親責怪,我撒撒嬌,給個擁抱,就過去了;我哥則會頂牛,表達不滿。
和解的那次,是我哥從上海打工回來,坐輪船回。那時候沒有高速公路,家鄉的港口很繁華。我哥坐的輪船是半夜到的,當時沒有出租車。父親和我,各自騎著單車,早早就在碼頭邊等。輪船晚點了兩個小時,我們一直等到夜里一點多。我哥初次外出打工回家,給我們都帶了禮物,給父親買了皮鞋,給母親買了衣服,給小弟買了球鞋。父親很感動,我哥也很感動,他沒想到那么晚,家里人還來接他,畢竟家離碼頭,有近十里路。
9
父親手工很好,有天分。從來沒人教,他就自己用竹篾啊、編織帶啊,編了竹籃、魚簍等各種各樣的家用工具。他種樹,搭葡萄架,干凈利落。
仲夏的黃昏,葡萄藤順著父親架好的鐵絲網,浩浩蕩蕩爬到我家三樓頂上,藤下有足以傾聽牛郎織女竊竊私語的蔭涼;絲瓜藤似火一樣燒綠了三棵意楊樹,母親得用竹竿才能夠得著在樹上吊著晃蕩的絲瓜;黃瓜藤也不甘落后地占滿了整個茅廁屋頂;南瓜花變戲法一樣地開花了,映襯著旁邊紅紅的洗澡花,色彩斑斕,喜慶熱鬧!
有一天黃昏,葡萄藤日漸沉重,突然“啪”的一聲,把鐵絲壓斷了,驚得父親丟下正在編織的竹籃,出屋看個究竟,而我們一幫小孩,則高興壞了,因為滿地都是葡萄!
10
父親走后,我哥開始接管、盤弄菜園,很認真,很辛苦,也樂在其中,但總沒有父親那么有條有理,而是顯得有些雜亂,像個大拼盤。
白菜秧苗出來了。我哥說:“白菜太容易遭蟲子了。不打農藥,簡直就沒法長大。所以,城里那些肥大的油菜,基本上都是打過農藥的。”
像父親一樣,我哥知道我愛吃橘子,所以地里種了一排橘子樹。秋天,金黃的橘子掛滿枝頭,很打眼。因為經常吃橘子,我和我哥發明了橘子的十幾種吃法:翻瓣吃瓤花,烤著吃,做罐頭吃,橘子皮曬干泡茶喝,橘子汁,橘子茶,橘子湯,橘子醬……居然十幾年了還吃不厭。
11
村里的主要親戚,是我的大舅和小舅,以及三個表哥和一個表弟。三個表哥都是大舅家的,表弟是小舅家的。
大舅、小舅和我母親并非嫡親的兄妹姐弟,他們是我外公弟弟的兒子,但因為從小就在一起同甘共苦過,所以感情深重,情同手足。三個表哥小時候也由我母親帶過,所以他們都很敬重他們的大姑。每逢我們家有事需要幫忙,兩個舅舅和三個表哥都會過來出力。兩位舅舅都是忠厚人,所以三個表哥和表弟,也都是忠厚人。
三個表哥都做了泥瓦匠。這樣,他們就都有了吃飯的手藝。我們村里幾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他們仨蓋的,包括我們家的,從房屋設計,到材料選擇,兄弟仨齊上陣,一磚一瓦地改變著村莊的模樣。
12
小舅會做事,又會做人,有一方鄉賢的氣質。每逢過年,小舅總會把全家族的人都聚攏,大擺酒席。小舅當年是部隊有名的炊事員,會燒一手好菜。一道道家鄉特色菜擺上來,一杯杯酒開始互相敬起來,那時候就特別有年味,特別有家族的香火味。
小舅為人大氣量,凡事總會讓著別人。他承包的魚塘到了收獲的季節,總會捉一條最大的魚送到我家,讓母親熬魚湯喝。他養的蘑菇發出來了,也會剪上幾朵最鮮嫩的送來我家。
有一回,我騎單車上學,不小心把一個人蹭了一下,當時特別慌張。幸好小舅在一旁路過,趕緊過來,讓我先去上學,剩下的事他來處理。
小舅是我們家族的靈魂人物。
時光慢慢流轉,老一輩的人就漸漸地少了起來,一開始是小外婆走了,然后是小外公走了,然后是大舅走了,然后是我父親走了,然后是我母親走了。離家出去找生活的年輕人越來越多,過年的時候,全家族的人就很難湊齊了。老一輩的人,就數我小舅年紀最大了,可他也日漸蒼老下去。當兵出身的他,腰桿居然也有點駝了,大嗓門似乎沒以前洪亮了,那張英俊的臉,越來越黑,黑到暗淡。
今年清明節回家,小舅拿著一個老舊的手機打電話,抱怨著信號不好,抱怨著電池不好。
我想給他買個好一點的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