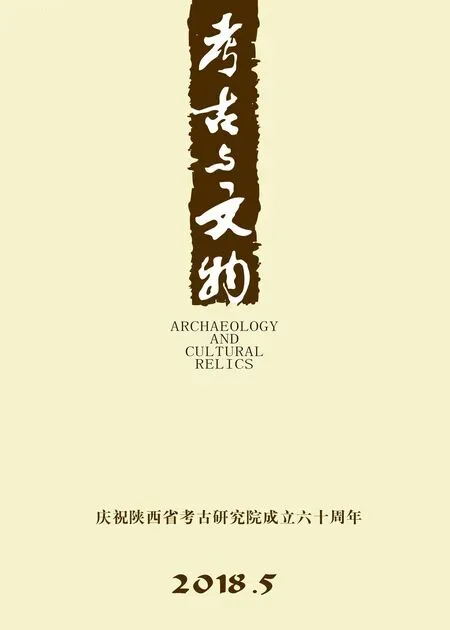2008~2017年陜西三國隋唐宋元明清考古綜述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隋唐考古研究室
在三國到明清近1700年的歷史長河中,曾經有八個朝代在陜西建國立都,其中有民族大融合時期的西晉、前趙、前秦、后秦、大夏、西魏、北周,還有繁榮輝煌的隋、唐時代,即使宋元明清時代,陜西依然是經濟文化發達、軍事地位顯赫的重鎮。此期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一直是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的主線或重要組成部分。從上世紀20年代始,唐代陵墓和隋唐長安城的調查發掘是這一時期考古研究的中心內容,取得了很多令人矚目的成果。2008年以后的近十年來,陜西地區三國至隋唐明清考古,不但隋唐時代大中型墓葬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繼續有新的收獲,以往不被關注的十六國—北朝時期,乃至宋元和明等各時段都涌現了很多重要的考古發現。在考古的理念、綜合記錄手段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
始于2006年的唐代帝陵大遺址考古項目,創建了地毯式全面深入調查、大面積普探、關鍵部位試掘以及全方位測繪、高精度數字采集的全套田野工作方法,在這種工作理念和方法的主導下,唐代帝陵考古從宏觀的陵園布局的演變到具體的陵前石刻文物保護復原、建筑構件編年,乃至唐代帝陵制度的內涵研究都取得了豐碩成果。這是十年來陜西隋唐考古工作的重大收獲。
在墓葬考古方面,比較突出的是十六國—北朝墓葬的發掘收獲。在咸陽北原一帶及西安南郊集中發現的十六國—北朝高等級墓葬,填補了這一時期考古發現的空白。十六國—北朝處于漢制向唐制的過渡期,這些考古資料將是研究歷史變革時期文化交流融合、新舊制度交替的重要資料。
隋唐墓葬的考古新發現,尤其如唐上官婉兒墓、韓休墓、李道堅墓等一批墓志和壁畫保存較好的大型唐墓,備受各界關注,在唐代毀墓習俗、歷史史實復原、美術考古、尤其是中國早期山水畫研究方面引起了廣泛討論。
北宋呂氏家族墓是陜西地區首次發現的大型高等級的宋代貴族墓葬,其隨葬品中成套的茶具、酒具和文房用具以及青銅器等藏品,反映了北宋士人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而陜北宋金畫像磚墓則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這些宋金貴族和平民墓葬的發掘,為研究區域墓葬習俗制度和唐宋墓制的轉變提供了詳實資料。
在城址考古方面,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隋唐長安城考古工作,在大明宮等宮殿遺址區、里坊區和東、西市遺址,都有了新的考古發現和認識。同樣為大遺址項目的統萬城遺址考古,確定了東西城、外郭城的分布格局和年代,通過周邊的墓葬及祭祀遺址的發掘,對統萬城的生活群體葬俗葬制及延續時期有了一定了解,同時積累了沙漠考古的工作方法和經驗。
歷史時期考古是傳統考古學與文獻史學的相互滲透、結合,二者互為印證、解讀。其內涵豐富、物質文化面貌復雜、門類繁多。既有城市考古、帝陵大遺址考古等綜合性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又有與其他自然或社科門類的交叉結合形成的專題類研究,諸如陶瓷考古、美術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10年來,陜西三國—隋唐宋元明時代考古,正是由于考古理念的更新、多學科研究的緊密結合以及資料采集和記錄手段的大幅度提升,拓展了學術視野,推進了學術研究的深入,從而取得了較大的突破和收獲,為文化遺產的保護和規劃的制定提供了科學的依據,為這一時期城市歷史風貌的復原積累了資料。
本文試對近10年來這一時期考古發現和研究做一概述,以城址、陵墓、宗教、手工業考古的發現和研究為重點,并將工作內容較多的長城調查和西藏考古單列介紹。
一、城址
近年來,城址考古的理念已經進化為城市考古。城市考古雖仍是以古代城址為對象,但研究的視野更加開闊,其目的是“為了掌握古代城址不同時期的遺跡現象,復原古代城市不同時期的形態結構,認識古代城市社會生活的空間場景,從而為研究城市發展的歷史、開展歷史城市保護奠定基礎”[1]。所以,城址本身的布局、結構,城址周邊的環境變遷,城市居民的墓葬分布及城市的興衰,都是其研究的主要內容。近十年來,陜西城市考古以統萬城遺址、隋唐長安城遺址考古新發現最受關注[2]。
(一)統萬城遺址
統萬城遺址考古近十年來主要著眼于城市布局、周邊墓葬、祭祀遺址等方面的考古勘探與發掘研究。
城市布局方面,首先是外郭城的確認。統萬城外郭城呈曲尺形,周長13865.4米,面積7.7平方公里,西北部凸出,城垣走向與東西城城垣基本一致[3]。
其次,經發掘確認統萬城東西城門外均有甕城。西城西門甕城位于西城西垣偏南處,甕城南北長38.5、東西寬22、高10米,城垣寬3.8米。甕城門面南,緊貼西城西垣。西門平面呈“亞”字形,門道內外兩側均有凸出的夯土臺,進深20.6米,單門洞,門道寬6.5、長19.5米。從地層堆積看,唐代西門甕城廢棄后,西門內側人為修筑夯土,隔斷城內與甕城的聯系[4]。
第三,對東城建筑基址的發掘,為確定東城的建筑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這組建筑基址東西寬96、南北進深48米。從其所處位置來看,應該是東城的主體建筑之一。中心夯土臺東西寬28.3、南北進深26.7、面積755平方米。夯土邊緣與城垣方向一致。東南部夯土厚度達2米。南面有兩個斜坡漫道,長6.8、寬4.4米,北面及東西兩面各有一個斜坡漫道。南面漫道兩側及夯土臺外側有磚砌散水。南北中心夯土臺外有“U”字形夯土帶,與中心夯土臺相隔2.2~2.6米。中間形成凹槽,凹槽內發現近40個柱洞。夯土臺外地面出土數十件獸面瓦當,另外有沙石雕刻的蓮花座、浮雕壸門、佛頭像的石刻殘塊等。夯土臺疊壓唐代晚期地層,其建造年代當在晚唐五代時期[5](圖一)。

圖一 統萬城東城建筑基址
第四,經過對統萬城的鉆探和發掘,基本搞清了馬面的規模及功能。統萬城西城城垣外、東城南、東、北垣外均建造有馬面或垛臺,每面8~10個。這些凸出的馬面或垛臺,將城垣外廣場分成若干區域,便于守城將士從多面居高臨下用弓箭、擂石等武器抗擊攻城之敵。另外,還在城垣外設立虎落,地面撒鐵蒺藜防范敵騎兵入侵。
在統萬城周邊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其墓葬區和祭祀遺址的發掘與統萬城有關的墓葬群分布南至華家洼、波羅地梁、周家梁墓群,東南至爾德井墓群,西至敖包墓群、北至瓦渣梁墓群。整體范圍南北約10、東西約20公里,面積約200余平方公里。共發掘北朝、唐、五代、宋代墓葬40座,基本搞清了與統萬城有關的墓葬年代、形制及各時代墓葬形制的演變序列[6]。在統萬城周圍還發現了疑似祭祀遺址的夯土臺。西梁夯土臺基址位于統萬城遺址東南,隔紅柳河與城址相望,距統萬城直線距離約2公里。主要由圍墻及圍墻內的南墩臺、中墩臺和北墩臺等部分組成。三座墩臺形制大小相近。南墩臺平面近方形,南北長37、東西寬36米,中部距底部深約8.8米。夯土基礎部分深約4.8米。地表部分夯土略呈覆斗狀,殘高約4米,頂中部較平坦,墩臺四周均有斜坡漫道。
中墩臺、北墩臺規模與南墩臺相當,只中墩臺形制如龜背,東、北兩面設漫道;北墩臺形如覆斗,東、南、西三側設漫道。
查干圪臺位于統萬城遺址西城西北、外郭城內,東南距西城距離約2.3公里。查干圪臺共發現三座夯土臺,發掘了1、2號夯土墩臺。
1號夯土墩臺主要由西、南、東三條夯土道路、中部平臺基礎和外圍覆土等組成。其構筑方法是先夯筑呈矩尺形的西、南兩條夯土道路,然后夯筑東夯土道路,三條夯土路相交呈“T”字形,之后以三條夯土路為中心夯筑方形平臺,最后于方形平臺基礎外緣再夯筑護坡。墩臺平面整體呈南北長、東西短的圓弧形,且西、南兩側坡度較緩,東、北兩側坡度較陡,墩臺主體部分南北殘長27、東西殘寬20.5、厚2米,西側夯土路超出墩臺主體部分,總長79.5、寬1.1~1.5米。三條夯土路和中心平臺部分夯層清楚。護坡為青白色夯土(圖二)。
2號夯土墩臺平面近方形,方向35°,墩臺長約6.8~6.9米,邊緣夯土厚0.18~0.3米,中部夯土厚0.4~0.5米,中部高出現地表約0.3米。同樣是在“斗”形方坑內起夯。
西梁和查干圪臺兩處夯土遺址均被隋唐時期墓葬打破,因此其時代應當早于隋唐時期,結合統萬城歷史沿革,我們認為其建造年代應與統萬城同期,為兩組禮制性建筑,可能與大夏國時期統萬城的祭祀活動有關。

圖二 統萬城查干圪臺夯土基址1號墩臺(西城西北部,東俯瞰)
(二)唐長安城
唐大明宮的持續考古發掘是這一時期隋唐長安城最重要的考古工作之一。2007~2010年,為配合大明宮遺址保護及國家遺址公園建設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大明宮宮墻和北夾城、含元殿南水渠、太液池西池北岸及玄武門南側的兩處道路過水涵洞、宮廷膳食灰坑、宮城東北角墩臺等遺存進行了全面的勘探與局部清理發掘[7]。重點發掘了興安門遺址。門址分為早、晚兩期,早期門址有三個門道,晚期門址有兩個門道,晚期門址由東、西墩臺、門道、隔墻以及東西兩側的城墻和馬道等組成。出于遺址保護原則,只發掘了晚期門址,發掘面積2939平方米。早期門址的發掘采用小型探溝、鉆探等方法進行探究。出土遺物有建筑材料和日用品陶瓷器等[8]。
在城市改造和基建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遺址。2009年9月,在西安市碑林區邊家村、黃雁村改造過程中,發現了大片唐代遺跡,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做了發掘工作。遺址位于唐代通義坊范圍內,發掘面積約500平方米,揭露出通義坊內東西向道路及其南側排水溝遺跡,出土了陶瓷器殘片、骨器、錢幣、建筑材料、善業泥、經幢等文物[9]。2012年2~7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發掘了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遺址,揭露出朱雀大街、安仁坊坊墻墻基和第七橫街等遺跡[10]。2014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了唐長安城東市遺址,發現了道路、水溝、店肆后作坊、水井、窖井、滲井、灰坑、活土坑等遺跡[11]。
此外,在隋唐長安城周圍,還發現了兩處陶窯遺址、一處糧倉遺址,這些遺址當與長安城內人們的生活有關。2011年,我院在西安市未央區大白楊村發掘唐代陶窯16座、水井3座[12]。2011年底~2012年初,西安市文物保護研究院在西安市昆明西路與團結南路十字路口西北角處發掘陶窯9座[13]。這些陶窯均成組分布,每組2~6座不等。成組陶窯在操作間之外有供出入的過洞與斜坡道相連。2012年7、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未央區梨園路北側發掘了4座糧倉遺址。根據其排列規律,推算這一帶至少存在3排21座糧倉,東西成行、南北成排分布。糧倉內發現大量炭化的谷物堆積,另外還發現有“開元通寶”錢、手印磚等。糧倉位于西安北郊龍首原的高爽地帶,并在唐都長安之北的禁苑之內,而且靠近漕渠,十分有利于糧食的運輸、保存及安全[14]。
這一時期出版了3部與隋唐長安城有關的重要考古報告。關于唐長安城醴泉坊三彩窯址[15]和醴泉坊遺址[16],報告對1999和2001年發掘的唐長安城醴泉坊遺址全部成果予以闡述。歷年來對唐長安城青龍寺和西明寺調查和發掘的全部資料也已公布。另外,還有張建林、田有前對2012年之前的隋唐長安城的考古發現進行了 梳理和介紹,對隋唐長安城的相關考古研究的綜述[17]。
(三)陜北麟州故城
麟州故城位于陜西省榆林市神木縣店塔鎮楊城村西北部的楊城山上,城址依自然山勢逶迤而筑,高差約200米。2009年7~10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與榆林市考古隊對麟州故城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與測繪。整個城址呈不規則長條形,面積約為1.12平方公里,城周長約5.4公里。分別由東城、西城和紫錦城組成,三個小城既相互聯系又相對獨立,城內皆發現建筑遺跡,以東城最密集。城防工事中甕城、城墻、馬面、角樓等均保留很好,尤其是位于城址中部的紫錦城,有一殘存20米保存非常好的夯筑墻體,墻體上部為麟州城的最高點。
麟州城始建于唐代開元十二年(724年),廢棄于明代正統八年(1443年),歷時719年。五代麟州刺史楊宏信及其長子楊重勛和其孫楊光,世代守衛麟州,抵御契丹、西夏。而楊宏信的次子楊業和其孫楊延昭均為宋代名將,在山西朔州北拒契丹,稱雄一方。由于麟州故城與楊家將的淵源關系,后代人們懷著對楊氏英雄的崇敬心情,將此城稱為楊家城,延續至今。
二、帝陵
十年來主要對隋文帝泰陵、唐帝陵、明藩王陵進行了考古勘探與試掘。
(一)隋文帝泰陵
泰陵為楊堅與文獻皇后獨孤氏的合葬墓,位于陜西省咸陽市楊陵區五泉鄉雙廟坡村。現陵前立清乾隆年間陜西巡撫畢沅書“隋文帝泰陵”石碑。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扶風縣博物館羅西章曾對泰陵做過多次勘察[18]。為配合隋文帝泰陵保護規劃的制定,2010年5、6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陵園遺址和隋文帝廟遺址進行了全面的調查與勘探,取得了重要收獲。
現已探明陵園遺址周圍有平面呈長方形的城垣,南北長約628.9、東西寬約592.7米,墻基寬約4.4米,陵園總面積372749平方米。陵園四面各辟一門,南門門址保存較完整,門外分別有一對門闕,門闕平面呈梯形。陵園外環繞有圍溝。陵園中部偏東南部筑有覆斗狀封土,現高約25.1米。封土頂部南北寬約33、東西長約42米,底部南北寬約153、東西長約155米,基礎部分呈倒“凸”字形、覆蓋墓道。封土南部發現兩條東西并列的墓道,形制和結構相同,東西間距23.8米,均為7天井、7過洞,西側墓道(包括天井、過洞)南北長約78.7、寬約3.4~5.6米,東側墓道略短,也稍窄。
“隋文帝廟”遺址周圍有長方形垣墻,南北長約384、東西寬約354米、面積135936平方米。其中南墻寬10.1、東墻寬16.4米,南北兩面的垣墻分布有馬面6處,南墻正中有門址一座。在城址內偏南部有《大宋新修隋文帝廟碑》。
此次調查和勘探進一步確認了陵園遺址和“隋文帝廟”遺址的準確位置和布局、范圍。探明了主要建筑基址及陵墓玄宮墓道部分的結構,探出兩個墓道,證實泰陵確為文獻記載的“同塋而異穴”[19]。
(二)唐代帝陵
2006年,陜西唐代帝陵被國家文物局正式確定為全國100個大遺址保護項目之一,這對唐代帝陵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義。在國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我院對關中21座唐代帝陵(“唐十八陵”加上永康陵、興寧陵、順陵)開展了系統的田野考古工作。截止2017年底,已完成21座唐陵的考古調查、勘探和測繪工作,其中對16座唐陵的部分陵園建筑和神道石刻做了考古發掘和清理,搞清了這些陵園的基本布局、陵園石刻的分布規律及數量、相關遺跡的分布及保存現狀、陪葬墓的數量和分布情況。
經過詳細地調查、勘探、發掘和測繪,對唐代帝陵的陵園結構與布局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唐代的帝陵陵園坐北朝南,地勢北高南低,以南北為中軸線,呈東西對稱布局。各陵園的規模差別較大,據宋敏求《長安志》記載,昭陵和貞陵周圍一百二十里,乾陵周圍八十里,泰陵周圍七十六里,定、橋、建、元、崇、豐、景、光、莊、章、端、簡、靖等13陵周圍四十里,獻陵周圍二十里。

圖三 唐元陵下宮正視影像圖
在陵園布局方面,各陵雖構筑方式不同,有些陵園垣墻因山勢而稍作曲折,但整體上陵園平面大體呈方形。玄宮所在之封土或陵山為整個陵園中心,四周筑垣墻,四面垣墻正中設門,門外各有門闕一對,圍墻四角各有角闕。南門為正門,南門外為神道(又稱司馬道),南門之外、神道北端,有蕃酋殿與列戟廊遺址。神道南端,有門闕一對,在其南又有門闕一對,加上陵園南門,共有3對門闕。其中第1對門闕與第2對門闕距離較遠,第2對門闕與第3對即南門門闕之間為南神道,神道兩旁列置石刻。此外,又有寢宮與為數眾多的陪葬墓。
初唐時期的高祖獻陵、太宗昭陵,布局設計“斟酌漢魏”制度,同時吸收南北朝帝陵的傳統,試圖探索建立唐代帝陵的新形制。獻陵墓上筑覆斗形封土,封土現高約18米。周環方形墻垣,四面辟四門,陪葬墓分布于陵園東側及東北,這些特點與漢陵相同,惟陵園四門及神道石刻為漢陵所無[20]。四門所立石虎取站立姿勢,造型與西魏永陵之神獸類似;神道所立石柱則明顯仿照南朝陵墓造型,石柱座上雕刻兩條盤繞的龍,石柱頂部雕刻蹲獸等,這些特征無不與南朝陵墓石柱相仿[21]。獻陵陵園北部偏東鉆探發現的建筑遺址緊鄰陵園,坐北向南,周環墻垣和圍溝,整組建筑呈軸對稱布置:中軸線上安排兩進院落,并有大型建筑基址,應該是禮制建筑。遺址出土的磚瓦、瓦當等建筑材料與獻陵南門遺址完全一致,說明建造年代相同。推測此處建筑很可能是獻陵最初的寢殿建筑群。這種將陵寢建筑緊鄰陵園的做法也與漢陵相仿。唐太宗昭陵開唐代“因山為陵”之先河,在具體的設計和布局上多有創新,與獻陵幾無相似之處。因山勢在九嵕山南面懸崖開鑿玄宮,南北山梁上分別建造南北司馬門,東西不設門,也沒有環繞的城垣。西南面的平緩開闊地帶建造寢宮。北司馬門從外向內(從北向南)依次為三出闕、列戟廊、殿堂式大門。寢宮宮城的平面布局刻意仿照長安城的宮城設計,南面為宮城正門,北面有夾城,形成兩道北門,主體建筑沿南北中軸線依次排列,布局與大明宮極為相似。陪葬墓主要分布在南面及東南面。陵園石刻完全不同于前朝,北司馬門矗立具有紀念碑意義的“昭陵六駿”石屏,前無古人。寫實性的“十四國蕃君長像”石人具有紀功宣威的功能,有學者認為此種做法可能源自突厥陵墓石人[22]。
盛唐時期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橋陵是唐代帝陵形制確立的階段。自乾陵開始,陵園環繞陵山一周修筑平面方形的城垣(唐代文獻稱之為“壖垣”或“行墻”),四面辟四門。由南向北布置三重門闕,第1對闕臺(宋代稱之為“鵲臺”)通常距第2對闕較遠,相距1000~2000米,有些超過2000米,其間中軸線的西側建造下宮,東側分布陪葬墓。第2對闕(宋代稱之為“乳臺”)距離南門闕一般不超過1000米,兩者之間的神道兩側對稱排列石刻。陵園四門由外及里依次筑三出闕、列戟廊和殿堂式大門,南門外還修建放置蕃酋像的建筑(蕃酋殿)。需注意的是蕃酋殿的位置曾發生變化,乾陵將之安排在南門與南門闕之間,橋陵及以后則將其移至南門三出闕以南。寢宮(后稱下宮)位于第1對闕(鵲臺)與第2對闕(乳臺)之間的西側,宮城規模較大,乾陵下宮面積145000平方米、橋陵下宮面積206515平方米;平面呈方形或長方形,有內外兩重城垣;較大的建筑基礎為數條平行的夯土基構成。陵園石刻從乾陵開始形成定制,四門外各立石蹲獅1對,北門闕以外再立石馬和牽馬人各3對(乾陵北門外還有石虎1對、尚不明確的石刻1對),南門闕以外神道兩側由南向北依次立石柱1對、翼馬(或麒麟)1對、鴕鳥(或鸞鳥)1對、仗馬和牽馬人各5對、石人10對以及數量不等的蕃酋像。石刻體量高大,如門外石獅高達2.7~3米,石人高達4米左右。以上可以看出,乾陵—橋陵的總體設計布局和石刻組合分別吸收獻陵、昭陵兩者的設計理念,基本呈方形的陵園墻垣、神道石刻最南端為1對石柱、四門外設置1對石獅等源自獻陵(獻陵為1對石虎);因山為陵、北門外設置6匹石馬、南門外設置蕃酋石像(昭陵蕃酋石像設在北門內)、門外設三出闕及列戟廊等均源自昭陵。還有學者認為高宗太子李弘恭陵的神道石刻組合和造型對乾陵神道石刻制度有很大影響[23]。無論如何,乾陵陵園形制標志著唐代帝陵制度的正式形成,此后的唐代帝陵陵園基本按照這一布局設計建造。

圖四 唐光陵東門及南列戟廊遺址
中唐時期的玄宗泰陵、代宗元陵(圖三)穆宗光陵(圖四)延續盛唐帝陵形制,略有變化。仍然是“因山為陵”,但陵園平面多隨山勢,平面形狀多不規則。東西兩門以及東北、西北角闕的地點選擇只能依據不同地勢。下宮規模減小,如泰陵下宮宮城面積23100平方米,崇陵26800平方米;宮城平面多為長方形,不再是內外兩重城垣,北面不設門。陪葬墓急劇減少,甚至沒有陪葬墓。從泰陵開始,石人體量變小,分為左文右武,東側為手持笏的文官,西側仍為手拄儀刀的武將。鴕鳥不再采用寫實方法,逐漸失去鴕鳥原型,頸、腿變得粗短,或許這一時期的應當稱之為“鸞鳥”更為合適。翼馬定型化,不再出現獸頭的麒麟。蕃酋像更為注重表現不同民族的服飾差異,在建陵陵園城垣附近發現的馬頭人身石像和猴頭人身石像,顯示著這一階段還曾流行在陵園周圈埋設十二生肖石像的制度。
晚唐時期的敬宗莊陵、僖宗靖陵,陵園形制與前一階段相比變化不大,但呈現出不穩定的狀態。有3座陵園即敬宗莊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采取久已不用的封土為陵的設計。陵園規模逐漸變小(貞陵是一個例外),尤其是3座“封土為陵”的陵園,邊長僅500米左右,“因山為陵”的章陵邊長也不過800余米。陵園石刻的種類未減少,但在數量上有減少、體量上有變小的趨勢。到唐末的僖宗靖陵,石人高度不足2米,與前一階段的蕃酋像大小相差無幾。或僅有1座陪葬墓,或沒有陪葬墓。這一階段中,貞陵是一個特例。陵園規模巨大,南北門之間的間距達3500米,在所有唐代帝陵中是最大的。下宮宮城規模也較崇陵要大些。陵園石刻出現一些不同于其他陵的種類,南門門址殘存4個石座,從石座的結構分析,其上原可能是4個守門武士的雕像。南門外兩側還發現一個較大的石座,座上正中殘存有榫眼,座上原來的石雕應為一形體高大的雕像。蕃酋像重新變得程式化,服飾不再多樣,稍顯雷同。
據歷年來的考古調查與發掘資料,可將唐陵陵園形制的發展演變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初唐兩座帝陵,屬于借鑒漢魏帝陵制度的探索階段。這一時期陵園布局尚未形成定制,兩座陵園采用截然不同的形制。
第二階段的乾陵、定陵、橋陵,標志著唐代帝陵陵園形制的正式形成。這一階段最初的乾陵最為重要,是唐帝陵形制變化的一個轉折點,形成的“乾陵模式”對后來諸帝陵影響深遠,為此后諸唐陵設計的楷模。
第三階段基本沿襲盛唐時期的陵園布局—“乾陵模式”,又發生一些調整和變化。從某種意義來講,泰陵也是唐代帝陵形制的一個轉折點。從泰陵開始,陵園平面不再追求方形布局,因地勢調整,往往呈不規則形狀。神道兩側的石人分為左文右武。石刻個體變小,下宮規模減小,陪葬墓數量減少。
第四階段唐代帝陵制度逐漸走向衰微。除貞陵外,陵園規模逐漸變小。門闕等闕臺不再使用三出闕形式。石刻組合基本穩定,石刻體量更趨變小,陪葬制度漸趨消失[24]。

圖五 明愍王陵前石麒麟
(三)明秦藩王陵考古調查
明代200余年間,先后有13位藩王、30余位郡王及其夫人、子孫等埋葬于今西安南郊的少陵原、鴻固原、高望原、鳳棲原等地,其中明秦藩王墓葬13座,被稱為明秦藩十三陵。2006年5月被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調查發現7座陵園,結合文獻記載,應該分別為第一代愍王朱樉陵園、第二代隱王朱尚炳陵園、第三代康王朱士契陵園、第四代惠王朱公錫陵園、第五代簡王朱誠泳陵園、第八代宣王朱懷埢陵園、第九代世子朱敬鉁陵園。
第一代愍王朱樉陵陵園位于整個秦藩陵園區中部偏北,東與西漢宣帝杜陵相距2000米。平面長方形,方向355°,南北長430、東西寬370米,占地面積15.6萬平方米。由陵墻、主墓、陪葬墓、陵園內建筑基址及神道石刻五部分組成。陵園南墻墻址東西走向,全長369米,東段保存較好。陵園東、南、西面中部各發現一座門址。南門門址位于陵園南陵墻中部,東西長23、南北寬12米。主墓朱樉陵位于緩坡地至高點,9座陪葬墓分布于東南、西南兩側,目前有封土者5座,推測M2、M3當為朱樉兩妃王氏、鄧氏的墓葬。上世紀70年代在陵區地表仍可見到朱樉妃鄧氏墓碑。
2010年考古調查時發現第三代秦僖王朱志堩墓志石,據村民介紹其墓葬為朱樉陵園帶封土墓葬之一,后來封土被夷平,M11當為其墓。
朱樉墓M1墓道南端發現一座建筑基址,整體呈方形,由四座房址及通道五部分組成,四座房址圍成一個院落,南北、東西對應。南房址位于陵園內中部神道正北端,東西長23、南北寬11.5米,夯土距地表0.7~1.5米。東房址平面長方形,南北長20.8、東西寬15.9米。建筑基址南端10米處,發現一殘石龜座,當為石碑基座。其南為陵園神道,神道為南北走向,通至南陵墻中部門址。神道兩側當有9對石刻,目前東側9件、西側8件。由南向北分別為華表東西各1、石虎各1、石羊東1、石麒麟各1、石馬各2、石文官像東西各1、石武士俑東西各1、石獅東西各1件(圖五、六)。
第二代隱王朱尚炳陵園,位于西安市長安區韋曲街道辦東伍村北,陵園呈南北方向,平面長方形,南北長336、東西寬192米,占地面積64512平方米。陵園內現存3座圓丘形封土,現存石刻12件,位置被移動(圖七)。

圖六 明愍王陵前文官像
第三代康王朱士契陵園,位于長安區大兆鄉康王井村東,南北長276、東西寬170米,占地面積46920平方米。地表封土破壞嚴重,墓前尚存神道碑龜座、石馬、石文武官俑、石獅計10件。第四代惠王朱公錫陵園,位于長安區大兆鄉龐留井村東,方向348°,南北長326.8、東西寬170.1米,占地面積約55588.7平方米,地表殘存圜丘形封土兩座,墓地尚存“大明宗室秦惠王神道碑”(殘)及“秦惠王暨妃王氏合葬墓”碑各一通,其他石刻14件。第五代簡王朱誠泳陵園,位于西安市長安區杜陵鄉韋曲街道辦,陵園平面長方形,坐北面南,南北長約334、東西寬約179米,占地面積約59786平方米。陵園內尚存封土3座,神道石刻尚存華表、石虎、石羊、石馬、文官俑12件,另有3件位置被移動等。

圖七 明隱王陵前石刻
第八代宣王朱懷埢陵園,位于長安區杜陵鄉三府井村東,南北向,尚存封土2座,高約7米。神道石刻11件,由南向北,依次為華表1對、石虎1對、石羊1對、牽馬人及馬1對、文官俑1對。另外尚可見到石龜座1件。宣王墓石刻肥胖臃腫,形體不似前幾陵高大雄偉。
第九代世子朱敬鉁墓,位于長安區杜陵鄉世子井村東北,封土被毀,地表尚存墓碑一座,立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螭首龜座,碑高3.2、寬1.15、厚0.3米,碑額刻“賜嫡子敬鉁墓”[25]。
據研究,明秦藩王王位受封者1位、襲封者8位,嗣封者2位,進封者3位,追謚者5位,除過追謚者計有14位,加追謚者計19位[26]。據明史最后一位秦王是景王朱存樞(第十一代秦王),朱誼漶子,襲封,崇禎末陷于賊,不知所終。梁志勝、王浩遠依據發現的朱存樞、大明秦世子暨妃張氏合葬壙志、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博物館院內的大明宗室秦景王壙志認為《明史》記錄有誤,朱存樞為世子時已薨,秦景王當為朱存機,最后一位秦王當是朱存極[27]。但是目前考古調查只發現了7座陵園,其原因可能是未生子而卒的秦王附葬其他陵園,比如第三代秦僖王朱志堩附葬愍王陵園;也可能有如明史記載明末戰亂秦王不知所終,未建陵園;還有一種可能是至今未發現。依據調查數據,秦藩王陵園基本是正南北方向,第一代愍王陵園面積最大,接近正方形,往后陵園面積變小,也變得狹長。陵前石刻配置當有9對,目前所見沒有完整的,在第八代宣王陵前首次發現馬及牽馬人,但是低矮臃腫。陳冰對秦藩陵園內的墓冢分布特征所反映出的喪葬禮制等規律、歷史文獻、地名學及守墓制度等相關問題展開探討,提出了六條保護建議[28]。

圖八 咸陽機場二期M54出土的陶九枝蓮燈
三、墓葬
2008年以來,墓葬考古從西晉到宋元時期,均有數量不等的發現。西晉、十六國時期墓葬發現百余座,西魏墓葬發現較少,但多為紀年墓,特點顯著。北周墓葬數量不多,但等級較高,隋唐墓葬數量較多,貴族平民均有。宋金墓葬極具時代特點,出土的瓷器、畫像磚及壁畫為以前少見,元代墓葬的壁畫是一大特色,明代墓葬以家族墓葬為多,多石室、石棺。
(一)西晉墓葬
1989年在東郊田王發掘一批西晉墓,其中M426前室有 “元康四年” 墨書題記,結合該墓出土新莽錢幣和東漢五銖錢,可確定墓葬年代為西晉惠帝元康四年(294年)[29]。以此為標準,確定了關中西晉墓的特點:墓葬形制有單室、雙室、多室幾種,西晉早期墓葬形制繼承東漢之制,其后開始變化。甬道劵頂較平,前后室之間設后甬道,一般前室放置器物,后室葬人。多室墓側室也會葬人。隨葬器物中出現了陶俑、多子格等典型器物。近十年來,西安發現的西晉墓如下: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廟坡頭村南發掘1座[30],2012年,在長安區茅坡村發掘西晉墓1座[31],2009~2011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機場二期擴建工程中,在底張、西蔣村發掘西晉墓9座。值得注意的是墓葬中出現了新的器物—空柱盤,關于其用途,有燈臺、帳座、盛放實物等說法[32]。
(二)十六國墓葬
關中地區發現的十六國墓葬約70余座,多數位于空港新城的洪瀆原、咸陽北原以及西安市近郊。1995~2001年,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咸陽市北部的頭道原一帶發掘24座十六國時期墓葬[33],其中文林小區9座墓出土刻銘磚6件,有前秦建元十四年(公元378年)紀年磚1塊,為關中地區首見。岳起、劉衛鵬根據新發現的紀年墓,對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進行了初步梳理和認定,確定了十六國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等特點[34]。
十六國墓葬多以家族墓地的形式出現,排列有序。均為帶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道平面均呈較長的長方形,以南向、東向居多。流行在墓道壁設置1~5個生土臺階,以兩級臺階最常見。少數墓葬帶1~2個長方形的天井。墓道斜坡前段平緩,后端陡深。部分在墓道北壁、過洞口上部生土上雕刻有門樓。絕大多數墓葬在墓道終端的甬道口設有封門。封門分磚質和土坯兩種,以磚質封門常見。磚質封門以小磚為主,也有一部分用空心磚或空心磚與小磚混用。封門絕大多數為一道,設于甬道口的墓道末端,墓室口基本無封門。甬道平面多呈長方形,也有一部分呈梯形。梯形甬道一般口小里大,均為土洞弧頂或平頂,以弧頂為主。
墓葬形制有單室、單室帶耳室、雙室、雙室帶耳室幾種。主室平面均為四邊形,四邊長度相等或相近,頂呈四面起坡式的攢尖頂或穹隆頂。側室平面呈長方形或梯形,弧頂或平頂。
一般情況下墓室葬具為木質單棺,仰身直肢葬,以多人合葬為主,盛行祔葬;隨葬器物一般陳放于主室的兩側、四隅和墓主的頭部附近。單室墓的隨葬品主要陳放于墓室東西兩側,前后室(或帶側室)墓隨葬器物一般陳放于前室,側室、后室一般用來葬人。

圖九 咸陽機場二期M298出土女樂俑

圖一〇 咸陽機場二期M298出土馬俑
出土器物有武士俑、樂俑、具裝馬、雞、狗、豬等;生活明器有罐、倉、灶、井、碓、磨、連枝燈等;實用器有銅釜、鐎斗、熏爐、銅尺、銅(鐵)鏡、叉、簪、鐲、指環及銅錢等。其中武士俑、樂俑、牛車和九枝蓮燈最具時代特征。
十六國墓葬主要分布在咸陽北原一帶及西安郊區,近十年來發現的主要有以下幾處:
1.洪瀆原墓葬區
2007年,我院在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專用高速公路發掘9座[35]。2008~2011年,西安咸陽國際機場二期擴建工程中在底張、北賀、西蔣村發掘17座[36](圖八),其中M298為坐南朝北的雙室土洞墓,墓葬全長75.25米。墓道帶四個臺階,寬6米。有2個天井、2個過洞。過洞口上方有在生土上雕刻的闕樓,甬道口上方也雕刻有門樓。墓室內繪壁畫。該墓是關中地區目前所見規模最大的十六國墓葬(圖九、一〇)。2012年,在空港新城空港花園小區發掘4座,2014年,咸陽市文物考古所在涇陽坡西發現1座[37],2017年,在空港新城竇家村發掘6座。在秦漢新城擺旗寨發掘1座[38]。
2.西安郊區
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鳳棲原杜陵鄉焦村發掘1座[39]。2011年,西安東郊灞橋區洪慶街道辦紡織工業新園發掘1座[40]。2017年,在西安市漢城南路發掘1座[41]。
隨著十六國墓葬資料越來越豐富,相關的研究也在展開。對墓葬形制、出土陶俑、騎馬俑、樂俑、釉陶罐等也有專門的討論[42]。
十六國墓地的分布,與十六國都城的位置有極大的關系。前趙、后前秦、后秦均在長安建都,都城使用了西漢長安城東北宮城的一部分。十六國、北朝時期,只對局部進行重建、維修,北周延續使用。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漢長安城考古隊在西漢長安城東北部勘探發現了東西并列的兩個小城,具體位置在宣平門大街與洛城門大街圍成的區域內。經對小城的城墻局部試掘,發現墻體建筑于西漢文化層之上,而墻體北側地層堆積情況為:最下為西漢文化層,出土板瓦、筒瓦、瓦當等建筑材料。在西漢文化層之上,有兩層地面遺跡,上層地面以上地層出土黑灰色磨光板瓦和筒瓦等北周特征的遺物,顯然屬北朝時期,應是該時期建筑[43]。201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聯合調查發掘了5座古橋。其中4座位于西席村北,正對漢長安城北墻中間的城門—廚城門,稱“廚城門橋”。另外一座位于高廟村北,正對漢長安城北墻洛城門,稱“洛城門橋”。此橋便是北周的“宣平門橋”,通過此橋十六國北周時期渭河南北兩岸暢通無阻,故作為十六國、北周都城周邊最近的高原,洪瀆原是十六國貴族最理想的埋葬之地[44]。
(三)北魏、西魏墓葬
1.北魏墓葬
近十年,關中地區發現的北魏墓葬,多見于西安南郊[45]和咸陽北原[46]上,墓葬均南向,斜坡墓道,帶天井,墓室為方形或長方形穹窿頂,有的帶有后室或者側室,出土器物以俑最有特點,另外還見有牛車以及少量青瓷器等。
陜西地區發現的北魏墓葬數量很少,很難概括出一個清晰的特征。陜西地區北魏墓葬很大部分仍承繼了西晉、十六國的因素,包括墓葬形制、隨葬品的類型等。隨葬品中陶俑占比很大,頗具自身風格特點。倪潤安通過對關中地區發現的北魏墓葬綜合分析,認為關中地區北魏墓葬文化正處在逐漸接受洛陽地區文化的過程中,同時也顯現出地方特色[47]。張全民則對關中地區的北魏陶俑從制作方法和演變方面做了研究,認為北魏前期,陶俑基本上延續了十六國時期的工藝和風格,到了北魏晚期,才逐漸形成了組合完整、特點較為鮮明的陶俑群,同時兼有分模制作和單模制作兩種工藝[48],前者至西魏后不再使用,后者則被西魏北周沿用,最終形成了當時關中特有的一種陶俑形制。
除了關中地區之外,2011年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陜西靖邊距統萬城約3公里處清理了5座北魏晚期至西魏時期墓葬,這批墓葬墓室均在生土上雕刻出仿木結構的柱子、斗拱等,墓葬的主人應為北朝時期統萬城居民,其中M1墓主或為粟特人,壁畫題材包含有濃厚的佛教因素。這批墓葬的發掘對研究中國北方地區特別是統萬城周邊地區北朝墓葬的葬俗及統萬城居民的構成與宗教信仰具有重要意義[49]。
2.西魏墓葬
近幾年陜西地區連續發掘了6座保存較好、并有紀年的西魏墓葬。2014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韋曲北原上發掘大統六年(540年)婁氏和大統十四年(548年)長孫俊合葬墓[50]。2015年在長安郭莊發現2座西魏墓葬[51],或為乞伏氏家族墓葬,其中M2墓志記載為大統七年(541年)茹茹族乞伏孝達和吐谷渾暉華公主的合葬墓,M3則為西魏末廢帝元欽時期茹茹族乞伏永壽妻臨洮郡君墓葬。2017年7月在咸陽擺旗寨清理大統四年(538年)陸丑墓[52],同年8月在咸陽西郭村發現大統十五年(549年)袁紇頠墓[53]。
西魏墓葬的研究囿于發現數量少,認識尚較模糊,學界多將其做為北魏和北周的中間階段,并未截然分出。張全民對關中地區北魏和西魏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做了分析和研究,并且把西魏陶俑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基本概括出了西魏陶俑的特點,北周陶俑群正是沿著西魏的傳統繼續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地域和時代特征。直到隋代統一以后的大業年間,關中地區才在北周、北齊俑群特征的基礎上,融會形成了隋代陶俑的特征[54]。趙強通過對姬買勖墓和鄧子詢墓與已發表的西魏墓葬的對比分析,認為西魏國祚短暫,尚未形成嚴格的墓葬制度,姬買勖、鄧子詢墓葬的形制,更多的受到西晉方形單室磚墓的特征的影響,其墓葬形制具有過渡性。同時文中還對姬買勖、鄧子詢墓志做了釋讀[55]。
(四)北周、隋墓
1.北周墓葬
在配合西安咸陽國際機場一期建設的考古工作中,我院等發掘了一批有明確紀年的北周墓,確定了洪瀆原為北周的貴族墓地之一。北周墓葬形制以斜坡式土洞墓為主體,豎穴次之,少見磚室墓。墓道修建規整,天井數量不等,有的墓葬天井長度不一。墓室有單室、單室帶耳室、雙室、雙室帶耳室數種。有的墓葬還開有小龕。隨葬器物以陶器為主體,騎馬出行儀仗是常見的配置。倉、灶等庖廚用具齊全,男女侍俑較多。但個體較小,制作粗糙。高等級墓葬有少量青瓷及青銅藥具。
2007年在咸陽市渭城區底張鎮龍棗村發掘北周獨孤賓墓[56]。獨孤賓原名高賓,由北齊投奔北周,依附于獨孤信門下,賜姓獨孤。其子高穎為隋代名相。在渭城區正陽鎮柏家嘴村發掘郭生墓[57],該墓使用石門、石棺。石棺四周有線刻,棺蓋為太陰、太陽,左右兩側為青龍白虎,前檔上部朱雀下為石門圖案,兩側有柱劍門吏線刻。后檔為玄武。前檔座上刻一組六人的樂舞圖。2009年,在長安區夏殿村發掘莫仁相、莫仁誕父子墓[58],是近年在西安南郊發現的規模較大的北周墓。2010年,在機場二期建設的布里村發掘拓跋迪夫婦合葬墓[59]。2010~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長安區高望堆村發掘4座北周家族墓[60]。其中3座有紀年,為天和二年(567年)張猥墓、建德元年(572年)張政墓和天和六年(571年)張盛墓。2013年在空港新城鄧村發掘2座古代墓葬[61],其中一座為北周新昌公宇文某夫人拓拔氏墓。2017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空港新城陶家寨西北發掘北周建德六年晉顗墓[62],出土玉佩2組、東羅馬金幣3枚及色彩鮮艷的陶俑70余件。
2.隋代墓葬
近十年來,隋代墓葬發掘40余座,其中紀年墓較少。根據以往的發現,多位學者對其進行研究,申秦雁的研究范圍為中原地區。劉呆運根據新出土的資料對關中地區隋墓形制和葬地進行了研究。張全民對隋代陶俑的演變進行了研究[63]。關于隋墓特點可總結如下:
墓道:平面形制多呈長方形或梯形,上口略大于下口。斜坡地面經踩踏較平整,東、西兩壁一般都經鏟平修整,表面均光滑。
過洞和天井:過洞平面呈長方形或方形,土洞式拱頂。多數過洞入口處兩壁稍有收分。地面為斜坡,坡度同墓道,壁面光滑,起券處較高,拱頂弧度大小各異。天井平面均呈南北向縱長方形,早期的天井南、北兩壁從開口至過洞頂的高度處逐漸斜收,天井東、西兩壁基本豎直。隋代后期,天井四壁均較豎直,天井開口已逐漸變短,與初唐墓葬天井趨于一致。隋墓天井四壁表面一般不作修整,壁面略顯粗糙。

圖一一 咸陽機場二期唐墓M92及圍溝全景
甬道:其水平進深大小不一。平面呈縱向或橫向長方形,均為拱頂土洞式,起券高度、拱頂高度一般與過洞相當,而低于墓室頂部高度。大多數甬道地面與墓室地面高度相平,兩壁面均作鏟平修整,平整光滑。早期甬道位于墓室南壁的中部或偏西,晚期開始向東部偏移,使墓室平面成刀把形。
封門:封門一般位于甬道入口處或墓室入口處。土坯或磚砌,土坯多為草拌泥制作。一層順平、一層頂向錯縫平砌。石門一般見于雙室土洞墓、單室土洞墓中。
墓室:墓室一般修建的不是很規整。平面形制多樣,有長方形、方形、梯形、平行四邊形、不規則方形等。墓頂多數為拱頂式,個別為四角攢尖式。
棺床:有磚棺床及石棺床,磚棺床均用條磚平輔,砌磚方法丁、順錯雜,隨意性很大。棺床早期多為東西橫向設置于墓室北部,晚期南北縱向置于西側的較多。沒有棺床的棺木也基本按照同一規則放置。高等級墓葬中出現石棺。
隨葬器物分為鎮墓類、出行儀仗類、庖廚用具類、家禽家畜類、生活用具類。鎮墓類的武士俑及鎮墓獸來自兩個系統:繼承北周風格的個體略小,繼承北齊風格的個體略大。隨葬品中的釉陶和白瓷是這一時期的特色。特別是白瓷,胎質細膩光滑,做工精細,尤其透影杯更是少見,工藝水平極高。
十年來發現的隋墓主要有下面幾處:
2009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邊方村、布里村發掘隋墓4座。其中鹿善夫婦墓[64]與元威夫婦墓[65]較為典型。墓建造規整,墓外建有兆溝。對研究墓葬制度尤為重要。元威夫婦墓內出土一組白瓷,出土的方鏡也較為少見。同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長安區韓家灣村發掘隋蘇統師墓[66],出土瓷器5件,其中透影杯器壁最薄處僅厚1毫米左右,杯體上半部分胎釉融為一體,如玻璃般呈半透影狀。
2010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長安區何家營村發掘隋開皇十八年韋協墓[67],墓葬為斜坡墓道帶三個天井的土洞墓,在三個天井下繪有列戟、儀仗圖,墓室四壁繪女侍及內侍,惜只存西壁及北壁局部下半部分。
201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棗園西路三民村發掘隋代小型墓30座[68]。這批墓葬結構特殊,墓室地面也為斜坡狀。每墓葬一人,頭向南。隨葬器物較少,多為小瓷盒、小罐和五銖錢。發掘者認為應該是隋代宮人墓地。
(五)唐代墓葬
陜西地區的唐墓,集中發現在唐都長安及其周邊區域。圍繞西安周圍的黃土臺塬分布。北至渭河以北的底張灣,南至長安縣韋曲鎮之南的神禾原、少陵原;東至浐河兩岸的龍首原、長樂原、白鹿原、銅人原、洪慶原;西至長安縣西北的高陽原、細柳原等范圍內,均有唐代墓葬被發現。尤其地處唐長安城東以及東南近郊的龍首原、白鹿原、銅人原、洪慶原,之南的鳳棲原、少陵原、畢原等地,分布更為密集[69]。
2007~2017年,陜西省內共發現唐代墓葬500余座,分布在西安西郊、南郊及西咸新區周圍,多為配合基本建設、少量為主動性發掘項目,配合基本項目主要有2007~2017年咸陽機場二期項目,共發現唐墓60余座,其中紀年墓30余座(圖一一);2008~2010長安區韋曲街道辦韓家灣村西,黃河上游水電開發有限責任公司“1000兆瓦太陽能光伏電池項目一期工程”建設項目用地共發現唐墓30余座,其中紀年墓8座;2008年,棗園三民村清理唐墓22座,4座紀年;2009年西安煙草物流項目發掘的唐紀年墓,為清河房氏成員;2010年灞橋棗園村墓,發掘唐墓7座,其中紀年墓4座;2011年長立豐惠澤苑項目發掘唐墓25座;2012年長安萬科二期項目,共發現唐墓百余座,其中紀年墓十余座;2014年,西安西郊金色悅庭項目清理唐墓7座;2014~2015年,涇陽太平堡遺址墓群清理唐墓30余座。主動性項目有2008年的西安龐留唐武惠妃墓、2014年的長安郭莊韓休墓、2014年的華陰唐宋素墓、2016年富平獻陵陪葬墓李道堅墓等。大量實物資料的出土,推動了唐墓相關研究工作的深入進行。如墓葬形制、墓內隨葬品、墓葬壁畫的研究及墓葬的文物保護工作,尤其是關于墓葬壁畫和墓志的研究,越來越深入細致。正如陳寅恪所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70]。

圖一二 唐竇希瓘墓出土壁畫
上述唐代墓葬中,壁畫墓中保存較好的有唐韓休墓[71]、唐李道堅墓[72]、唐武惠妃墓[73]、長安航天城M13(諸葛芬)和M4[74]、長安韓家灣村M29和M33[75]等。這幾座壁畫墓的時代從初唐延至晚唐,內容豐富。尤其以唐韓休墓墓室內的山水圖和樂舞圖最為完整。出土三彩器的墓葬有唐楊貴夫婦墓[76],墓內出土了三彩侍女俑和模型明器等;西安楊家圍墻唐墓[77]內出土的三彩扁壺,保存較好。此外,還發現了一批唐代名人墓葬,如唐昭容上官氏墓[78]、唐執失思力墓、唐竇孝諶墓及其子竇希瓘墓[79](圖一二)、長孫無傲夫婦墓[80]、戶部尚書李承嘉墓[81]、殿中侍御醫蔣少卿夫婦墓葬[82]、司農卿秦守一墓葬[83]、兵部尚書戴胄夫婦墓[84]、涼國夫人王氏墓[85]、涇原鎮海節度使周寶之妻博陵郡夫人崔氏墓[86]等。任職縣令的墓葬有敦煌縣令宋素墓[87]、洛州密縣令馮孝約墓[88]等。唐代家族墓地新發現有郭子儀家族墓地[89]。目前,已發現的郭氏家族成員包括郭曖和升平公主墓、郭曜和王氏墓、郭仲文墓、郭仲恭和金堂公主墓、郭锜和盧氏墓、郭釗和沈素墓、郭鍔墓、郭在巖墓等,郭子儀家族墓中出土了諸多珍貴的墓志以及豐富的隨葬器物。唐代令狐楚家族墓成員墓,包括令狐緘墓和裴氏墓[90]。兩墓均為豎穴墓道單室土洞墓。據墓志記載,令狐緘為唐代文學家令狐楚侄,葬于唐咸通六年(865年);裴氏丈夫為令狐均,葬于乾符四年(878年)。
另外,還有兩處外來人群墓葬。一處是唐代百濟國遺民禰氏家族墓地[91],共發現3座墓葬,出土了2合墓志,可推斷3座墓為禰氏祖孫三代,為探討唐代百濟國禰姓的淵源提供了重要證據。另一處是唐代突騎施王子光緒墓[92],墓中出土了各種類型的陶俑和墓志。墓志所載內容,為我們研究西域歷史、西突厥史、突騎施活動都提供了重要資料。
此外,在配合基本建設考古中,發掘出土了一批特殊人群的墓葬,如唐代女官墓[93]和宮女墓[94]。女官墓墓主為宮廷五至七品女官,官職司正等,墓志未載墓主年齡及籍貫。宮女墓形制較簡單,為木棺單人葬,均有漆盒等漆器出土。
在發現的眾多唐墓中,以韓休墓、竇孝諶墓、昭容上官氏墓最具代表性。現簡介如下:
1.唐宰相韓休墓 位于西安市長安區大兆街辦郭新莊村南100米處。該地在杜陵東南2公里的少陵原上,是唐代重要的墓葬區之一。在該墓西側有著名的韋氏家族墓、郭子儀家族墓、長孫無忌家族墓,該墓南側為武惠妃敬陵,東側為唐代宰相杜如晦家族墓葬。該墓為長斜坡墓道單室磚室墓,平面呈“刀把”形,坐北向南,方向175゜。南北水平總長40.6米,由墓道、5個過洞、5個天井、6個壁龕、磚封門、石門、甬道、墓室、棺床組成。墓內共出土隨葬品186件(組),多發現于西二龕內,其余散布于甬道和墓室內,包括陶俑、陶器、瓷器、鐵器、石門及墓志等。在墓室入口放置有兩合墓志,載其墓主為唐玄宗朝宰相韓休,開元二十八年(749年)八月葬于少陵原,夫人為河東柳氏,天寶七年(757年)十一月合葬于此。墓葬內甬道和墓室繪制有精美的壁畫,是本次考古發掘最重要的收獲。甬道兩側為侍女圖、宦官抬箱圖。墓室頂部為日月星象圖,南壁為朱雀圖,北壁西側為玄武圖、東側為山水圖。西壁為樹下高士圖,東壁為樂舞圖(封三,2)。
2.唐豳國公竇孝諶墓 位于西安咸陽國際機場二期工程新修停機坪內偏北中部,原屬咸陽市渭城區底張鎮西蔣村農耕地。2009~2010年發掘,該墓被盜嚴重,墓上分布有封土、祭祀坑、石刻。現存封土底徑約23、頂徑約4、殘高10米。封土東北約0.3米處有一長方形祭祀坑,坑內殉葬動物。封土以南從北向南,立石羊、石虎、石人各一對。封土下為斜坡墓道多天井雙室磚券墓室,平面呈刀把形,坐北向南,方向180゜。墓葬水平總長74.2米,由墓道、5個過洞、5個天井、2個壁龕、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等部分組成。壁龕開于第三過洞兩壁。后室西側以磚砌棺床,其上置石槨,人骨多已無存。墓內繪有壁畫,墓道兩壁為祥云、導引人、青龍、白虎,北壁繪門樓。過洞天井兩側壁繪有侍女、牽牛圖、寶相花等,墓室壁畫保存較差。共出土隨葬品77件(組),有武士俑、騎馬俑、侍女俑、風帽俑、三彩盒、三彩馬頭、玉珠,鎏金銅泡釘、鎏金銅馬鑣以及石人、石虎、石羊、石門殘塊和華表、墓志等。
3.唐昭容上官氏墓 位于咸陽市渭城區北杜鎮鄧村。墓主為唐中宗昭容上官氏,即唐代著名女政治家、詩人上官婉兒。該墓系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小龕的單室磚券墓,坐北向南。由墓道、5個天井、5個過洞、4個壁龕、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組成,全長36.5米。壁龕內放置彩繪陶俑,未被盜掘擾動,保存較好。甬道內放置墓志一合,蓋題“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銘”。志文為楷書,近千字,記載上官昭容的世系、生平、享年、葬地等信息,依此可確定墓主人的身份。
除大量的考古新發現外,唐墓發掘報告的整理出版也有很大收獲,如唐懿德太子墓、唐順陵、唐武惠妃墓、唐韋貴妃墓、唐嗣虢王李邕墓等[95]。同時,關于唐代墓葬的綜合性研究專著也涌現出來。包括對整個陜西地區唐墓綜述性研究,關中地區墓葬的分區分期研究,墓葬壁畫研究[96]等方面。如墓葬形制與分期、壁畫、隨葬品、喪葬制度和習俗、墓志、文物保護等。同時,對墓葬中所包含的宗教文化因素也開始了廣泛的探討[97]。而墓葬出土遺物的現場保護和提取也越來越科學有效,更多更先進的科技手段不斷被應用到考古現場信息資料的采集工作中[98]。
唐墓壁畫的研究包括壁畫的分期、題材、布局、風格、形式及意義、局部內容的考釋、制作工藝、文物保護等方面。發表的論著有《唐代墓室壁畫研究》[99]《唐墓壁畫研究綜述》[100]《唐墓壁畫中周邊民族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關系》[101]此外還有一些壁畫圖錄等。
墓志類研究近年來頗受學界的關注。墓志研究主要從志文記載的墓主生平經歷、相關歷史事件、家族譜系、宅地葬地、墓志撰文書寫、墓志紋飾研究等方面補史證史。關于家族墓地研究,重要的有郭子儀家族墓志研究[102],百濟移民禰氏家族[103];墓志中史學、文學研究,以唐上官昭容氏墓志、唐李建成墓志、唐韓休墓志、李應玄墓志和姬揔持墓志為代表[104]。
同時,各類墓志[105]匯編等綜合性研究成果也紛紛涌現,《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106]將同一墓地考古發掘出土的墓志按照古籍整理的標準結集刊布,并附出土現場信息和照片,大大拓展了碑刻文獻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是考古與歷史文獻研究緊密結合的有益嘗試。
在唐墓研究方面,一些以往不被關注的方面,如墓葬建造過程和技術、墓葬壁畫的多學科研究、陶器隨葬品的研究等,都有了一定的進展。發掘竇孝諶墓、韓休墓時,由于仔細記錄了墓葬筑造時留下的痕跡,為復原墓葬建造的過程、探討唐墓建造技術積累了珍貴的資料。墓葬壁畫研究中,檢索歷史文獻,將出土壁畫放到當時社會大環境、墓主地位和家世的小環境以及繪畫史發展大框架中進行探討,拓展了唐墓壁畫研究的空間和深度。在唐墓隨葬品研究方面,迄今對出土陶俑、唐三彩、金銀器的研究較多,《隋唐五代時期灰陶制品》則是關于唐墓出土陶器演變專題研究的有益嘗試[107]。
總之,唐墓的考古發掘工作更加科學規范,研究視角更加客觀、開闊和深入。
(六)宋金元墓
相較于漢唐,陜西宋金元時期墓葬發現數量較少,但近年呂氏家族墓、甘泉金墓、劉黑馬家族墓、橫山羅圪臺壁畫墓、蒲城洞耳壁畫墓重要發現,為宋金元時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難得的資料。
1.宋代墓葬

圖一三 韓城宋氏壁畫墓北壁下部墓主圖
陜西地區宋代墓葬按照建筑材質可以分為土洞墓和磚室墓,其中土洞墓較多。根據目前公布的材料,土洞墓主要發現于關中地區的西安市周邊[108]、蒲城[109]、藍田[110]、鳳翔[111]等地。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墓道為豎穴土坑或斜坡帶臺階,墓室基本呈長方形土洞,有的帶有小龕,既有單人葬,也有多人合葬,出土隨葬品除呂氏家族墓特例外,大多較少,一般為數件瓷器和陶器,最常見的是銅錢。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葬,該墓地共清理墓葬29座,有規劃完備的墓地。墓地周繞平面如長頸瓶形的圍溝。家廟遺址1座,位于“瓶頸”處,29座墓葬則分布于“瓶底”部位。出土文物700余件組,磚、石墓志銘24盒。墓葬排列規劃整齊,約呈橫向三排、縱向南北成軸的布局。南端為長,中軸線上自南向北縱向排列長子長孫墓;橫向則按輩分分排布置。墓地使用時間為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至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共埋葬五代呂氏族人。墓葬皆為豎井墓道土洞墓室,坐北朝南,深7.5~15.5米,形制分為單室、前后雙室、并列雙室、單前室雙后室、主室帶側室五種,頂部近平或略拱。其中有5座墓葬主室上部縱向疊置1~2個空墓穴,其作用應屬防盜設施。葬具已朽,仍可辨有木棺或棺槨,人骨基本為仰身直肢。隨葬品有豐富精美的瓷、石等遺物[112],且多為成套的餐具、茶具、文房用具、酒具等,是研究宋代士人生活和北宋歷史文化的珍貴資料。
陜西地區發現的宋代磚室墓較少,但是分布范圍較廣,見于陜西全境。按照墓室形制,大致可以分為長方形券頂墓和方形穹窿頂或攢尖頂墓葬兩種,前者見于西安市和韓城市,在西安市西南乳駕莊發現1座,墓葬為豎穴墓道長方形磚室墓,墓室內砌出仿木結構及門窗等,并施彩繪,出土陶器、瓷器及鉛器等[113]。2009年韓城宋代壁畫墓,該墓為單墓道長方形磚室夫婦合葬墓。墓室東、西、北三壁繪滿壁畫,色彩鮮艷,保存完好。墓室北壁正中為坐于書法屏風前的墓主人畫像,墓主像左右兩側為研方備藥場景的畫面。整個畫面暗示墓主生前應有從醫的經歷(圖一三)。東壁為佛祖涅槃圖,西壁壁畫為北宋雜劇演出場景[114]。
方形磚砌墓見于渭北和陜北地區,墓室內均有簡單的仿木構,墓壁有壁畫及磚雕等[115]。2010年在合陽縣王村鎮蔡村發掘2座宋墓,為長方形豎穴墓道八邊形磚室墓,攢尖頂,墓室內有仿木結構的磚雕斗拱、屋檐、柱子,墓壁鑲嵌佛教和世俗圖案的磚雕。該墓除發現1枚牡丹紋銅鏡外,未發現其他隨葬品[116]。2012年統萬城遺址東南發掘北宋墓葬3座,墓道為帶有臺階的斜坡式,墓室為磚砌,基本呈方形,內設棺床,疊澀頂或穹隆頂,四壁用磚砌出門窗,隨葬品極少,有銅錢、鐵器、瓷器等[117]。2008年8月在陜西西鄉縣發現1座宋墓,墓葬未公布詳細資料,但是從圖片大致可知墓室為長方形磚室墓,墓壁用磚砌出仿木構斗拱,墓室內設有棺床,隨葬有精美的瓷器[118]。
目前對于陜西地區宋代墓葬的研究,多集中在墓志考釋[119]和器物[120]研究上,對于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葬[121]和韓城北宋壁畫墓[122]的專題研究較多。
2.金代墓葬
陜西地區金墓較有特色集中發現于陜北和關中兩個大的區域。陜北地區金代墓葬主要發現于延安市甘泉縣[123],墓室為磚砌單室或多室,墓室內裝飾磚雕仿木構等。主要的壁面裝飾可以分為磚雕畫像和壁畫兩類,前者內容主要表現頗具地域風情社火場景(圖一四),孝行圖比較少見[124];壁畫則多見孝行故事[125]。另外在富平、甘泉、合陽等地還發現了一批佛徒火葬時使用的陶棺,灰陶,質地堅硬,在棺擋地方寫有“大師父”等題記[126]。

圖一四 陜西甘泉縣金墓出土彩繪磚雕
關中地區金代墓葬可分為磚室和土洞墓兩種,磚室墓又有券頂墓和穹窿頂墓兩種。穹隆頂墓發現4座,位于渭南市靳尚村,墓道為帶臺階斜坡形,其中M1墓室內繪有伎樂類壁畫,壁畫直接繪于磚壁上,沒有地仗層[127]。券頂墓在西安市曲江發現1座,為豎穴墓道長方形磚室,墓室后部設棺床,隨葬品較多,有耀州窯酒具、鈞窯食器、金屬器、買地券等[128]。土洞墓發現較多,多位于西安市南郊,多為豎穴墓道,隨葬有鐵豬、鐵牛等[129]。
3.蒙元墓葬
陜西地區發現的蒙元墓葬主要分布于陜北和關中地區,且兩地葬俗葬制有著明顯的區別。
關中地區發現的蒙元墓葬20余座[130],大部分位于西安南郊[131],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在曲江夏殿村發掘了12座蒙元時期劉黑馬家族墓葬,該墓地布局完整,隨葬品組合清晰,為關中地區同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132]。此外在西安市東郊十里鋪和高陵涇河工業園也有個別發現。這批墓葬均為土洞墓,墓室多為方形,少量近圓形,尸骨葬為主,隨葬品仍然以灰(黑)陶俑和陶器最富有特色,另外還隨葬有瓷器、金屬器等。
以灰(黑)陶器作為隨葬品的習俗目前只發現于陜西、甘肅、河南三省,楊潔認為,其中陜西關中地區在這種習俗中起著主要作用。
在陜北地區發現2座元代壁畫墓,分別位于榆陽區[133]和橫山縣[134],這兩座墓葬均為八邊形石室墓,墓室內通繪壁畫,內容主要有夫婦并坐圖、孝行圖、伎樂圖、出行圖等,同樣的墓葬形制之前在蒲城地區也有發現[135],但這三座墓與西安市韓森寨發現的元代壁畫墓[136]風格有著明顯的區別,前三者有著濃厚的蒙元特征,后者則為漢地風格。
雖然此期榆林地區與關中地區在墓葬形制和隨葬傳統上有著巨大差別,但雙方也存在一定的交流和融合。1987年在延安市南柳林鄉虎頭峁村發現的2座元代石砌墓葬,形制均為抹角八邊形穹窿頂單室墓,并隨葬有黑陶俑及黑陶器。其墓葬形制為陜北地區的傳統,并有一定的改變(由直角多邊形變為抹角多邊形),而隨葬品則當為關中地區因素,因此虎頭峁元墓是蒙元時期陜北和關中二區域墓葬文化勢力共同結合的產物,兩種墓葬文化在位于二者之“中”的延安地區“合二為一”。
近年陜西多座蒙元墓葬的發現,推動了蒙元時期考古的研究。除了對于關中地區蒙元墓葬的綜合研究[137]之外,主要集中于陶俑研究[138]和墓志釋讀兩個領域[139],也有學者對于早年發掘的蒲城洞耳村墓主族屬進行了考證[140]。
(七)明墓
十年來,陜西地區發掘的明墓超過80座。墓主身份上至明藩王家族,下至一般平民,時代大多為明中晚期。
小型墓發現范圍廣、形制單一,大多為豎穴墓道土洞墓,如澄城縣善化鄉明墓、咸陽西石羊廟墓群、黃陵西寨子明清墓地、漢中勉縣老道寺楊寨墓、西安新筑西坡墓地、長安南留墓葬等。
大中型墓葬主要分布在西安南郊、涇陽、三原、高陵等,尤以高陵縣最為集中。西安南郊明墓以明藩王家族墓為多,高陵縣明墓為張氏等幾大家族墓地,這一區域明中晚期流行石槨或石券墓,墓門上部多有仿木構的額枋等石雕刻,頗具地域特色。
大中型墓以萬歷十年為界,成化至萬歷十年以前為明中期,萬歷十年以后為明晚期。明中期墓葬相對較少,代表性的有以下幾處:
西安南郊明上洛縣主墓,為階梯狀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券合葬墓,墓室東、西、北壁各有一座磚券壁龕,墓門上有仿木結構磚砌門樓。葬具為一棺一槨。出土有彩繪木俑、木器、銅錢、幽堂(買地)券、墓志等。墓主為明保安王嫡長女,逝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明成化七年(1471年)葬于此地[141]。
銅川市未來新城小區明墓,為斜坡墓道帶天井、過洞的單室磚券合葬墓。出土有釉陶器、瓷器、玻璃器、木器、織物、宋金舊錢等陪葬品。買地券記載墓主為任福,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年下葬[142]。
西安南郊曲江觀邸明墓,為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券合葬墓,墓室三面各有一個壁龕。出土有陶俑、銅錢等,并有墓志兩盒,墓主為明嘉靖年間撫寧知縣郭淶世及其夫人合葬[143]。
西安市廣電中心基建工地共發現4座明墓,為秦藩王朱秉橘家族合葬墓,有3座為明正德、隆慶和萬歷初年,形制為斜坡墓道單室磚券合葬墓,單棺或多棺合葬。以磚室墓M26為例,墓門上部磚砌門樓,墓志放置于墓室頂部填土中,墓室內有磚砌祭臺,左右兩壁及后壁設有壁龕,紅底花草、翔龍的彩繪漆棺槨出土有玉器、陶器、錫器、鐵器等器物以及10件陶俑[144]。
西安南郊翠竹園二期項目,共清理明墓20座,多為弘治到萬歷以前。墓葬形制有豎穴墓道土洞墓、斜坡(有的帶階梯)墓道磚券或土洞墓,均為單墓室的單人或雙人合葬。出土遺物較少,主要為銅錢及墓志,另有錫器、銅質佛像、冥幣等[145]。
高陵徐吾村涇欣園住宅小區三期工地發掘25座明墓,均為平面甲字形的墓葬,以斜坡帶階梯墓道的單室土洞墓為主,并有少量磚券單室雙人、三人合葬墓,砌仿木結構門樓。隨葬品有瓷碗、銅錢、飾品等。根據出土墓志,為明中期隆慶、嘉靖、萬歷初年張氏家族墓地。
明代晚期墓發現較多。
西安市廣電中心基建工地M25(1621年)為斜坡墓道單室土洞墓,墓室平面為梯形。墓門處有磚砌門樓,木質棺槨表面髹有紅漆,繪有龍鳳、花卉等圖案。出土器物有瓷罐、鐵器等。
三原縣王徵家族墓,共清理3座墓葬,呈“品”字形分布,M23為帶有長斜坡墓道的單室土洞合葬墓,墓室內并排置棺,中間墓主王徵木棺高于兩側木棺。墓室出土有玉瓶、玉香爐、硯臺、黑瓷罐等物。其余2座晚到清代,均為多洞室合葬墓[146]。
高陵地區發掘的明墓有院張村明代家族墓及姬家安置區明墓、楊官寨明墓等。這三處墓葬均位于高陵縣姬家鄉附近。
院張明代家族墓,共發掘26座,從出土墓志可知,絕大部分為萬歷十年以后。墓葬可分為東、西兩區,在西區發掘出土了一座完整的有夯土圍墻的墓園,內筑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墓葬。墓葬為斜坡帶臺階或豎穴式墓道的多室合葬墓,由墓道、前庭和磚(石)砌仿木構門樓及磚砌或石砌墓室組成,其中兩座石券墓分別有4個和2個石室,另外一座為磚券3室。出土的1塊買地券和4塊墓志表明墓主為明秦藩知印張棟(1535~1585年)及其子孫的家族墓。東區發掘19座墓,墓葬形制與東區基本相同。是以斜坡墓道為主,個別為豎穴墓道的券頂(或洞室)墓,多為并列雙室或三室,磚、石門樓上雕出仿木構門脊、瓦當、滴水、斗拱及花卉裝飾圖案。出土隨葬品以瓷器、錫器、墓主隨身金銀首飾為主,數量較少。
姬家安置區發掘有兩處共7座墓葬,分屬兩個家族。根據出土的墓志記載,M5為山西省左布政使王翼明及其4位妻妾合葬墓。王翼明為晚明時期官員,去世于崇禎十四年(1641年)。M4修建于天啟二年(1622年),為明代奉政大夫工部管繕善司郎中王伊菴及其妻妾李氏田氏合葬墓。
彬縣東關村明墓,為短墓道石砌雙室夫妻合葬墓。主墓室三壁及頂部均繪有壁畫,內容以人物、花卉、瑞獸為主。墓葬出土有銘旌、朱書鎮墓磚、墓志、買地券等遺物,根據墓志記載,墓主紀泰葬于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其夫人葬于崇禎三年(1630年)。在紀泰墓附近有其家族成員的墓葬[147]。
總結明中晚期大中型墓資料,在墓葬形制演變、隨葬品、葬俗等有以下特征。
1.明代中晚期墓葬多為夫妻妾合葬墓,墓葬形制可分同穴單室合葬、同穴多室合葬兩大類,有磚券、石砌及土洞墓。明代中期,中型墓多見斜坡墓道(有的呈階梯狀)磚券的單室合葬墓,長方形墓室的中后部棺床上,置一具或多具棺木,也有單室土洞墓內置多具石棺的。規模較大的墓葬,在墓室兩壁和后部皆設壁龕,一般的僅在后壁開壁龕。明代晚期,單室合葬墓依然存在,但較少帶壁龕,墓道多成斜坡帶臺階狀,而同穴多室合葬墓逐漸流行,土壙內并列多個磚券或石砌墓室,或直接掏挖成并排的土洞墓,墓室的數量依男墓主妻妾多少而定,墓室間隔墻上,往往開挖方形通道連接;墓室前部共用一個前庭,最前部一般為豎穴墓道或斜坡臺階墓道,墓道均較短。這種形制的墓葬一直延續至清代。無論中期或晚期,規模較大的磚、石墓,在墓門上部都砌出仿木構的額枋、屋檐等雕刻,晚期因多墓室并排,上部額枋瓦檐連成一體,更寬闊華麗,其前庭兩壁也多砌出帶滴水瓦檐的院墻。
2.葬具多為木棺,規模較大的墓葬有石槨。出土陪葬品以2~3件黑釉瓷碗、缽或罐較多見,豐富者還隨葬有小件青花瓷器、錫器或鉛器及墓主隨身首飾,個別明藩王家族墓或品官命婦墓中見有彩繪陶俑、彩繪木俑、木器、玻璃器。此外,買地券、墓志也較多見,墓志有置于墓前庭、墓室內的,還有埋于墓封門上部填土中的。
四、陜西長城資源調查與研究
長城由墻體、單體建筑、關堡、營堡及相關遺存等組成,是一個由政府主持修建的軍事防御工程體系。對陜西長城的研究,早就有學者開始關注,擇其要者,有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對陜西境內的長城遺址進行了調查,對于長城的位置和保存狀況有大致的描述[148],但是語焉不詳。史念海從歷史地理的視角,依據文獻資料,結合實地調查,考證了長城延伸的方向和位置,但對一些遺跡的定性與斷代缺乏考古學依據[149]。彭曦對戰國秦昭王長城進行了全線考察與研究,詳細記錄了調查所見長城的分布,但對部分分布于河流山谷北岸或西岸的長城遺跡沒有發現,在長城分布上也有一些誤判[150]。艾沖對于陜西長城曾做過研究,指出隋長城被后來的明長城沿用疊壓,但沒有發現具體的隋長城遺跡[151]。通過前述的調查與研究,可以了解陜西長城的大部分遺跡的大體分布情況,由于缺乏全面系統的實地調查,對長城的認識,無法具體到每一個單體建筑或一段墻體的分布保存狀況,對全部的長城遺跡分布、走向也沒有宏觀的認識和把控,未形成成熟、完備的長城研究體系。
2007年以來,長城遺址的實地考古調查全面鋪開,對各時代長城遺址的具體長度、各類遺跡的數量、分布位置等方面的信息有了較詳細的了解,尤其是對明長城遺址的精確測繪,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詳實的基礎資料。
陜西境內的長城主要有戰國魏長城、戰國秦長城(秦漢沿用)、隋長城和明長城等,長城墻體遺跡總長度是1802公里。
(一)隋長城
隋長城墻體遺跡全長18公里,由墻體和單體建筑組成,墻體都是堆土筑成,保存程度差;單體建筑為夯土筑成,但也圮毀嚴重,多數坍塌呈一個圓形土包[152]。
由于隋長城堆土而筑的特殊建造方式,加之修建過程短促,其后又被明長城沿用,一直未能被辨識。2007年以來調查發現的隋長城遺跡,分布在神木縣、靖邊縣(圖一五)、定邊縣。三個縣區的隋長城由于大量被毀,現已互不相連。神木縣段隋長城分布在明長城西北側,靖邊縣隋長城與明長城相交,定邊段的隋長城東與明長城相交,西接寧夏鹽池縣隋長城,再向西連接內蒙與寧夏境內隋長城,直抵黃河東岸。崔仲方所修筑的長城,就分布在今陜西北部向西經內蒙古南部與寧夏交界附近直達黃河岸邊,可知隋長城的本來面目是同于后來的明代延綏鎮長城“橫截河套之口”。這種情況說明隋長城所選定的修建位置基本被后來的明長城所延續使用,這也正是隋長城比戰國秦長城的進步之處。
(二)明長城
陜西省明長城即明代延綏鎮邊墻的大部分,墻體遺跡總長達1170公里,有單體建筑(馬面、敵臺、烽火臺)1151座,關堡112座[153]。
墻體 全線土墻夯土土質以黃土為主,全部土墻現狀基本呈脊狀鋸齒形或駝峰形。有少量墻體是以石構筑而成,大部分是純以片石壘砌,有一段墻體是用片石壘砌兩側,內部用石塊或片石堆砌填充。
還有利用自然險要經人為加工而成的墻體。稱為山險墻。或是山險加以人工鏟削而成,或是山險加以人工增筑補缺而成,增筑部分所用材料以片石為主。
還有利用自然河流而成的防御,稱河險墻。
單體建筑 是單獨建筑為防守、傳信目的實體建筑,共調查到1286座。依據其功能可分為三大類別:馬面、敵臺、烽火臺。
營堡 指規模較大的軍事性駐軍據點,營堡遺址現共有46座,部分是由于遷建造成,在明代同時存在作為軍事駐地的約為36座,所以俗稱為“三十六營堡”[154](圖一六)。
明長城是為了防御北方的蒙古勢力而修建的[155],整個長城系統包括大邊、二邊和三十六營堡。大邊位于該防御帶的北側,主要防御外來的侵擾;二邊位于南側,是為控制內地軍民不得出境;營堡分布其中,作用為屯兵駐守之處。大邊和二邊共同構成“夾墻”,形成延綏鎮的縱深邊防工事。
延綏鎮明長城經過數次修建、不斷完善充實形成的防御系統,最初是守在天險,又發展為守在界石,再發展為守在營堡,再發展為守在墩臺、界石、營堡,再發展為守在邊墻,最后發展為守在互市與邊墻,至此長城系統臻于完備[156]。但此后再無大規模修筑長城的工程,并且長城在邊防上的重要性逐漸降低,直至后來逐漸頹棄。

圖一五 靖邊隋長城-銀灣村長城(由西向東)
考古調查資料,也為探索不同時代長城的發展演變規律打下了基礎[157]。目前長城研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尚需更全面深入的調查和研究。
五、陶瓷手工業遺址考古
陶瓷窯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是手工業考古的重要門類。近年來,隨著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理念逐漸完善,做為聚落或城市中手工業區重要組成部分的陶窯、陶瓷器制品、工藝技術的研究,逐漸被重視起來[158]。
陜西地區陶瓷手工業考古可分為陶窯和瓷窯作坊、窯爐兩大類遺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陶窯有位于城之內的,兼燒磚瓦建材和陶器的,也有純粹為陵墓建造服務的陶窯,二者的一致之處在于,制陶原料門檻較低,不像瓷窯對原料和燃料環境依賴性大,制陶技術的流向和陶窯的位置均主要因生產和消費需求而轉移。一些為大型建筑服務的陶窯,往往建前設窯燒制,完成需求后隨即毀窯平地。故陶窯大多延續時間相對較短,很少像瓷窯那樣動輒延續百年以上。這也是雖然陶窯曾普遍存在,但遺址常難發現且保存不好的原因之一。陜西近十年發現的陶窯大多比較零星,唯獨唐陵附近的陶窯,因其位置偏僻,故保存較好。
瓷窯遺址考古,主要為銅川耀州窯遺址的研究和澄城堯頭窯址的勘探發掘。

圖一六 定邊明長城-安寺村營堡
(一)陶窯
1.桑園窯址 位于渭南富平縣宮里鎮澗頭村,距唐定陵約1000米,是目前發現的最大的一處唐代磚瓦窯址,有個體窯爐545座,分16組分布,整體范圍達0.9平方千米(圖一七)。
據勘探發掘結果顯示,每組窯均生產某一類產品。該窯場可分為五個功能區,有兩個磚窯區、兩個瓦窯區和一個特種窯區(產品為獸面磚、鴟尾等特種建材)。
每組窯爐分兩排相對分布,共用一條兼做操作間的南北向通道,單組窯長度300米左右,窯爐最多達83座。各組窯平行呈北南向分布,間隔均勻,為60米左右,相鄰窯組長度相當,兩端基本平齊。
窯爐全部是平面馬蹄形的半倒焰式窯,由窯門、火膛、窯床、煙囪幾部分組成。窯門里是平面扇形的火膛,窯床近方形,窯床后壁底部有三個或五個吸煙孔通向后部煙室,由煙室頂部煙囪排出。大部分窯爐窯壁及以下部分為生土掏挖形成,窯頂磚砌,另有一部分窯爐包括窯頂全部在生土中掏挖,窯爐頂部完整,呈微弧形。
窯爐尺寸較大,如第四組Y261,是磚窯,窯床寬3.6、長3.4、火膛深1.5米。窯室兩側壁下部有引火槽,從火膛引至吸煙孔,后壁下部有五個吸煙孔通向煙室,由1個煙囪通向地面。
桑園磚瓦窯址位于唐定陵陵區附近,產品時代和種類與定陵陵園遺址出土物吻合,是專為唐中宗定陵建材生產開設的官方磚瓦窯場,隸屬唐甄官署管轄。唐十八陵中有十一座唐陵都發現有附屬的磚瓦窯,從數座到十數座乃至數十座不等,而桑園窯址是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一處,再現了唐代陶業的盛況,說明制陶業在唐代仍是比肩瓷器制造、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重要手工業門類。
2.小土門村陶窯遺址 位于西安市蓮湖區小土門村以南,時代為唐代。共清理窯爐9座,均為平面馬蹄形的半倒焰式窯爐,分為3組,第一組是6座,兩兩相對,共用一個操作窯道。出土有磚瓦殘塊等建筑材料、碗罐類生活器皿,還有鎮墓獸、陶俑類等喪葬明器殘塊。
3.西郭村陶窯遺址 位于咸陽市渭城區底張鎮西郭村,分布范圍大約1000平方米,目前探明有10多座,發掘區共清理陶窯9座。其中有6座陶窯南北兩排相對、分別共用一操作間,從出土磚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陶窯的形制來看,應屬于隋唐時期。
4.銀溝村陶窯遺址 位于富平縣銀溝村,此處曾是富平縣唐—元代縣城所在,分布著數十座陶窯,或呈“品”字形分布,或雙排兩兩相對分布。經發掘的兩座顯示,窯爐為半倒煙式窯爐,時代為唐代,產品包括生活用品陶器、磚瓦建材、喪葬明器,但未見陶俑。
5.西安西郊窯頭村陶窯遺址 位于唐長安城延平門西側,共有陶窯9座,有多個窯室共用一個操作間的對窯、兩個一組的陶窯和單體陶窯,時代為唐代中晚期。出土物以條磚、方磚、瓦當、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為主,其次為盆、缽、罐、陶爐等日用器皿,另有少量陶拍、馬頭殘塊等[159]。
以上發現的唐代陶窯遺址,或為陵墓建材和隨葬品燒制服務,如桑園窯址、小土門村陶窯、西郭村陶窯;或為城市建筑建材或日常用品生產服務,如銀溝村陶窯。說明唐代陶窯生產,磚瓦建材和日用(隨葬用)品是在同一類陶窯中生產。窯場布局模式分兩種,窯爐個體數量多的成雙排分布,窯爐個體數量少的或并排或呈“品”字形分布,均共用操作間;窯爐形制相對固定,僅個體尺寸和煙囪部分的局部結構略有不同,這一點與唐之前陶窯形制多、差異大的情況有別,說明唐代的建窯和燒成技術更穩定、成熟。唐代瓷器的生產處于起步和發展時期,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占比仍較多,銀鉤遺址陶窯中眾多的陶器類型,為研究此期陶器發展提供了資料。

圖一七 陜西富平縣唐桑園窯正射影像圖
(二)瓷窯
1.耀州窯址 2016年,為配合耀州窯遺址公園游客服務中心項目的建設,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遺址區的北部進行了局部勘探,了解了黃堡中心窯場的北邊緣區域的堆積分布情況。確認了黃堡窯場的北部邊界。
調查勘探發現,在南距耀州窯博物館2公里處、漆水河與312國道之間,地層堆積以宋金文化層為主,在中區范圍內可能有五代文化 層的存在;地層堆積西高東低,南厚北薄,尤其南部仍有較密集的瓷窯、作坊和灰坑遺址分布。崖壁斷面可見的作坊為窯洞式,與以往發現的形制相同。采集瓷片以青釉為主,尤其是金代翠青釉瓷器較多,另有少量黑釉、姜黃釉、月白釉瓷器殘片等,可辨認出土器形以碗、盞、碟為主,另有少量的壺、器蓋等器物殘片。
近十年來,耀州窯考古發掘雖然很少,關于耀州窯的研究,近10年來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關于五代耀州窯青瓷的性質,自禚振西提出耀州窯五代青瓷產品是中國古陶瓷史上的柴窯后,引起了學界高度關注,學界同仁從文獻記載的柴窯特征、地望和耀州窯及越窯、河南一些瓷窯產品特征等方面進行正反兩方面的討論和激烈爭論,中國古陶瓷學會分別在2010年和2014年兩次舉行了圍繞柴窯和耀州窯的小型研討會和考察,民間收藏界也數次召開會議討論,雖然至今并無確定的結論,但五代—宋初耀州窯天青釉瓷的工藝成就和意義也被學界所廣泛認可[160]。同時,王小蒙對五代耀州窯與越窯、邢窯等工藝的對比研究,認為五代耀州窯青瓷以北方瓷器工藝為基礎,融合南北瓷窯工藝精髓,最早創新了薄胎厚釉的天青釉瓷器,開啟了中國官窯體系天青釉瓷的發展序列[161]。王芬等對五代—宋初天青釉瓷的胎釉成分進行了測試,歸納出了天青釉的呈色機理,認為天青釉瓷的燒成是當時的刻意追求[162]。彭善國和易立等通過對內蒙、東北及中原地區墓葬出土耀瓷資料的梳理,認為《五代黃堡窯址》中部分青瓷器應該屬于宋代早期[163],張紅星、穆青研究文章也持同樣觀點。
其次,耀州窯各時期造型、裝飾工藝的特征及與同期中外其他瓷窯工藝交流的研究;耀州窯青瓷與金銀器造型裝飾的對比研究;通過研究,對耀州窯各期的風格特征、工藝來源有了更清晰深入的認識[164]。第三,窖藏、居址、墓葬出土耀州窯資料的梳理歸納,館藏耀州窯瓷介紹,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耀州窯產品的流布研究[165]。
另外,陜西富平銀溝遺址發掘出土了大量耀州窯各時代瓷片標本及其他窯場陶瓷、金屬日常用品遺物和宗教遺物,結合銀溝遺址附近曾經是唐富平縣城—義亭城這一文獻記載,這一區域很可能是分布著豐富手工業遺存的縣城遺址。因距離耀州窯僅30余公里,故出土有大量耀州窯瓷器。至于此地是否有瓷器生產,并進而是否有可能和文獻記載中的鼎州窯相關,目前考古工作還在進行中,有待于新資料的發現。
2.堯頭窯遺址 位于渭南市澄城縣堯頭鎮,是一處規模宏大的瓷器民窯遺址,因獨特的黑釉剔花工藝與粗獷大氣的器形裝飾,且窯火不熄至今,被譽為“瓷窯活化石”。據考古調查、發掘和民間藏品判斷,堯頭窯瓷器最晚元代始燒,上世紀80年代前后逐漸停燒。產品種類豐富,以黑釉瓷最多,有“黑珍珠”之美譽。
201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第一次對窯址區做了大范圍的、系統的調查,調查可見古瓷窯爐、作坊等遺跡點共有319處/組,其中窯爐遺跡130處,整個遺址范圍分布達8平方公里。
2016年發掘了1000平方米,揭露出窯爐、作坊、加工原料的耙泥池等遺跡。發掘出土的文化堆積和遺跡、遺物可分為三期,早期包含物以M形匣缽窯具為代表,產品以黑釉碗盤類器為主,時代可早到元末明初;中期以支柱、擱板窯具為代表,產品以黑釉的碗盤類為主,并有青釉器,出現盆缸類大型器。發掘揭露的有Y5、Y6兩座瓷窯,在Y5的窯壁上可見有利用廢棄的擱板砌筑的跡象,窯室內也有擱板、支柱及黑釉澀圈碗等出土。這一時期對應的歷史時代為明初至明代中期;晚期以直筒形匣缽窯具為代表,產品以黑釉、白釉、青釉器為主,器類更趨繁復。發掘的窯爐有Y1~Y4,以煤為燃料,此期對應時代相當于明代中期以后至解放后。解放前后堯頭窯的產品以盆、甕、海子等大型器為主,所以甕窯區占整個窯區面積約三分之二,堯頭窯地面可見的窯爐多屬此階段,發掘揭露的一處耙泥池,也屬此期。
堯頭窯是元代以后渭北地區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窯場之一,其元代受耀州窯青瓷影響較多,明代以后,與銅川陳爐窯、山西窯瓷器生產也有很多交流。
3.安坪村窯址 該窯址是調查所見,位于寧陜縣安坪村。遺址面積約3600平方米。地表分布有大量匣缽,有幾處較為集中的紅燒土區域,偶見瓷片。初步判斷,該遺址為宋元時代民間瓷窯遺址。
陜西古代瓷器手工業一直以來都是耀州窯生產一枝獨秀,元代以后,耀州窯黃堡中心窯場的生產逐漸沒落,周邊自金代以來開始的瓷業則不斷擴張。各窯場產品從以青瓷為主,向青瓷、黑瓷、白瓷、白釉黑花等多品種過渡。陜西瓷器生產“青”一色的格局被打破了。關中西部和秦嶺以南等地瓷窯遺址的發現,填補了這一區域瓷器生產的空白。堯頭窯遺址的系統調查和考古發掘,為了解渭北地區這一最大的窯場提供了資料。
六、佛教考古
陜西地區的古代佛教遺存主要包括佛教石窟、土窟以及寺院遺址三類。此外,還有少量出土于墓葬和其他遺址中的佛教遺存。其中,石窟遺存的數量最多,主要集中在銅川、延安、榆林三個地區,其余四類遺存的數量相對較少,陜北、關中、陜南地區均有分布。
石窟 7處。分別為2007年發現的延安市安塞縣大佛寺石窟[166],2008年發現的寶雞市岐山縣宋家堯石窟[167]、2009發現的漢中市留壩縣武關河佛教造像龕[168]及榆林市神木、府谷兩縣2015年發現的4處藏傳佛教遺存[169]。其中,大佛寺石窟保存了典型的北朝佛教雕像與樹下誕生、步步生蓮、出游四門等佛傳故事。宋家堯石窟造像均為石胎泥塑,題材以佛、菩薩、弟子為主,時代從北朝時期延續到盛唐時期。武關河佛教造像龕時代為隋唐時期,造像題材為一佛二菩薩、一佛二菩薩二弟子。神木藏傳佛教遺存共計3處,分別為喇嘛廟石窟、廟溝石窟、王樂溝石窟;府谷縣藏傳佛教遺存1處,為石窯溝石窟。遺存主要為藏傳佛教高僧造像、佛塔與六字真言、觀音菩薩心咒等藏文經咒。
土窟 1處。為2017年發現的榆林市綏德縣圪針灣佛窟遺址[170],6座洞窟均坐北面南。K1為僧房窟。K4為塑像壁畫窟,塑像為三佛、二弟子、二脅侍菩薩、文殊、普賢的組合,壁畫內容為藥師佛與十二神將及熾盛光佛與九曜。此外,還發現有畫像石、石柱、瓦等遺物。K5亦為塑像壁畫窟,塑像為地藏菩薩與閔公、道明,壁畫內容為地獄十王。此外,還發現有石貢器、瓦等遺物。K2、K3、K6均為小型龕式窟,后兩者內發現有石造像龕、圓雕石造像等。該遺址洞窟組合完整,遺物豐富,時代跨度大,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文化遺產價值。
寺院遺址 2處。分別為2009年發現的延安市富縣廣家寨寺院遺址[171]和2016年發現的商洛市鎮安縣毗盧寺遺址[172]。廣家寨寺院遺址殘存遺跡主要為兩道南北向的石砌墻基和一道南北向的走廊(過道),遺物主要為北朝至宋代的石刻造像(或殘塊)300多件,數量大,風格多樣,延續時間長,對于研究陜北地區的佛教傳播、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意義。毗盧寺遺址系一座元代密宗寺院遺址,發掘四邊形石塔1座,建筑遺跡1處。出土石刻文字記載該寺建于元末明初,石塔修建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對研究秦嶺山區寺院結構以及明清宗教興衰有重要意義。
與佛教相關的墓葬發現 5處。分別為2009年西安市南郊翠竹園二期明墓M36出土鎏金銅佛像和西安廣電中心明墓M26西棺頭擋板紅漆描金佛像[173]、2010年咸陽市機場十六國墓M54出土彩繪九盞佛像蓮花燈[174]、2011年榆林市靖邊縣八大梁墓地M1出土佛教壁畫與雕刻[175]、2014年渭南市蒲城平路廟墓群M22出土磚雕佛傳故事——涅槃圖像[176]以及2017年西安市長安區大居安唐墓M2出土兩件小型鎏金彩繪金銅佛教造像[177]。翠竹園二期明墓M36鎏金銅佛像火焰紋背光,高圓肉髻、雙手合十、結跏趺坐于蓮臺上,穿通肩袈裟。西安廣電中心明墓M26西棺頭擋板紅漆描金佛像穿通肩袈裟,結跏趺坐于須彌蓮花座上,兩側侍立童子。機場十六國墓M54彩繪九盞佛像蓮花燈由燈座及九個燈盞組成。在圓筒形燈架柄上,貼塑有兩層8個佛教造像,禪定印、結跏趺坐于雙層覆蓮臺上。八大梁墓地M1甬道入口處兩側于生土上雕刻柱式尖拱形仿石窟窟門。墓室東壁南、北兩側分別繪制一尊力士;北壁西部為主要表現胡僧禮拜舍利塔的場面。西壁南側為一跪于繩床上的僧人與一立姿僧人。南壁壁畫中可見跪姿僧人跪于繩床上的形象。
其它相關遺址 2處。分別為2016年發現的西安市雁塔區馬騰空遺址出土的1件唐代泥塑佛頭部[178]和2017年發現的空港新城遺址2號窯址內出土的65件北朝時期的彩繪泥塑佛教造像[179]。
考古發掘之外,陜西佛教考古近十年來在田野調查、資料刊布與相關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成果。
2012年至2014年,陜西省文物局組織專業團隊對陜西省銅川市[180]、延安市[181]、榆林市[182]三個地區的石窟遺存開展了專題調查,共計發現石窟遺存664處。調查結束后,及時整理公布了調查成果,用統一體例對每一處石窟進行了全面介紹。
此外還相繼出版了1987年法門寺唐代塔基與地宮遺址發掘[183]、2012年至2014年藥王山摩崖造像田野調查[184]、1973年青龍寺遺址發掘、1985年西明寺遺址發掘成果的考古報告[185]。同時,還對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收藏的百余件佛教造像精品[186]以及1985年田野調查所獲藥王山碑刻實物照片、測繪圖、碑文拓本以圖示、碑文著錄[187]以圖錄的形式進行了介紹。
研究方面,馬世長、丁明夷對陜西延安地區石泓寺等幾處石窟進行了介紹和分析[188],冉萬里用考古學方法對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進行了綜合研究[189],程旭對陜西館藏造像資料進行了收集整理和初步分析[190],介永強對唐代長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進行了綜合研究[191],常青對麟游蔡家河石窟與喇嘛帽山千佛院石窟開展了綜合研究[192]。
綜上所述,2007年以來,陜西佛教考古在田野發掘與調查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新發現很多,遺存的類型與特征進一步豐富。一批考古報告、考古簡報的出版刊布為今后的田野工作和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為下一步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專題或相關研究專著及論文的發表充分表明陜西佛教考古研究工作已逐步走向系統化和深入化。

圖一八 2013年發現的西藏阿里日土洛布措巖畫
七、青藏考古
自2007年以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繼續組隊參加文物考古援藏工作,這些工作均與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合作進行。同時,在西藏自治區之外的其他藏區,也開展了一些相關的考古調查工作。
在結束了連續三個年度的西藏薩迦北寺的考古工作之后,2007~2008年,先后派出兩批次專業人員,參加了西藏自治區7個地市的“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試點及技術指導工作[193]。
2009年,對芒康、察雅兩縣已知的5處吐蕃石刻遺存做了全面的考古調查,并新發現2處吐蕃石刻遺存,取得了重大收獲[194]。此次調查是迄今為止對藏東地區吐蕃石刻遺存所做的首次全面考古調查,成果豐碩,為研究吐蕃時期佛教史、佛教藝術史、唐蕃關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195]。同時,還對芒康瀾滄江兩岸的鹽井、鹽田等進行了調查[196]。
2012年9、10月,我院應邀與西藏山南地區文物局聯合組隊,對位于洛扎縣的吉堆墓地進行全面的考古調查和測繪。新發現墓葬20、條狀殉牲坑3、方形殉牲坑7座。與此同時,考古隊還調查了與墓地相關的兩處吐蕃摩崖刻銘[197]。
2013年7、8月,對阿里地區日土縣熱幫鄉洛布措進行了環湖考古調查。共發現巖畫618組(圖一八)、墓葬57座、祭祀坑24座、大型石片圖案1組、石構遺跡4組、石墻4道[198]。同時,還對日土縣多瑪鄉烏江村丁穹拉康石窟群及其壁畫進行了全面的測繪、拍照與記錄,對窟形、組合、壁畫內容與制作技法等進行了詳細的觀察[199]。
2014年8、9月,對阿里地區古格王國時期的遺址進行了調查。札達縣象泉河及其支流的河谷臺地和土林崖壁上密集分布著城堡建筑、窯洞居址、寺院建筑(圖一九~二一)、石窟遺址、佛塔遺址等各類古格王國時期的遺存。共調查遺址近10處。
2015年7、8月,對阿里瓊隆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和測繪。共計發現洞室742座,院落105座,房址45座,護墻29道,墻體25道,碉樓1座,瑪尼墻13道,塔20座,其它遺跡2座,發現陶、鐵、銅、石、骨角、木、玻璃、毛織物、擦擦、經書殘頁、唐卡殘片、塑像殘塊等遺物以及木、碳、谷物樣品等近400余件(組)。此外,還對曲龍村境內的3處相關遺址進行了調查[200]。

圖一九 2014年調查發現的阿里札達熱尼拉康東壁北段早期壁畫獻乳糜與藏文題記
2016年7、8月,對阿里象泉河流域進行了考古調查。主要圍繞象泉河上游曲龍段及中游托林段的干流與支流開展,共計調查遺址16處,遺跡類型十分豐富,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元明時期,表明象泉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發展具有多樣性和延續性。而三普新發現后首次做全面調查的遺址點有8處,其中對度日堅巖畫做了全面調查,發現651組畫面,確認了迄今為止西藏地區數量最多、車輛和圖案巖畫最典型的一處巖畫地點,首次確立了象泉河流域古代巖畫在西藏巖畫中的重要地位[201]。
2017年7、8月,主要參與了阿里札達縣格布賽魯墓地的考古發掘工作。共發掘墓葬9座,除M6為帶封堆的異穴合葬土坑墓外,其余8座均為墓室底部有涂紅跡象的小型土坑石室墓。出土各類遺物300余件(組),采集人骨和動物骨骼約100余個個體。根據出土物特征初步推斷,8座豎穴土坑石室墓的時代約為公元前3~7世紀,M6的時代可能晚至漢晉時期。這兩類墓葬的結構、葬俗與隨葬品特點既顯示出了濃郁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又體現了與中亞、南亞、新疆等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聯系,是西藏西部高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物遺存。
在西藏自治區之外其他藏區開展的工作:
一是2013年5月,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宮博物院等單位,聯合對西藏、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區新發現的吐蕃石刻造像進行了考古調查。新發現吐蕃石刻造像多處,填補了從青海西南部到四川西北部再到西藏東南部這段古代交通要道上的缺環,為吐蕃佛教史和唐蕃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圖二〇 2014年調查發現的阿里札達縣麥隆溝佛寺遺址主殿局部
二是2014年5、6月,與西藏等五省區文物機構聯合組隊,對唐蕃古道進行了全程考察。行程6500余公里,考察相關文物點56處。這次考察擴展了唐蕃古道所涉及的地域范圍和文化內涵,使得各省區唐蕃古道考古工作能在一個完整的時空框架和相互聯系的文化背景下展開[202]。
三是2014年4、9月,參加了青海省海西州都蘭縣熱水鄉哇沿水庫淹沒區的考古發掘及整理工作。發掘區以察汗烏蘇河為界,分為南岸區和北岸區。北岸區包括房址9,灰坑14座、灶31、墓葬3、石堆3座、寺院遺址1處;南岸區包括房址1、灶1、墓葬22、殉牲坑及殉人坑6座。其中25座古墓葬盡管遭到嚴重盜擾,但結構類型完整,營建方式多樣,出土的墨書古藏文卜骨、帶古藏文編號的槨板及棺板、“開元通寶”等表明這批古文化遺存的主人應該是唐代吐蕃統治時期活動在該地區的吐蕃人或吐谷渾人。出土的鑲嵌玻璃珠則是漢晉以來通過絲綢之路自西向東傳播的重要物品。
三國隋唐宋元明時代考古,時間跨度近2000年,歷史進程起伏跌宕,文化面貌復雜多變,重要考古發現層出不窮,研究內涵豐富、門類繁多,遠超過其他時期。上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綜述,僅僅是擇其要對一些基礎性的工作進行歸納,城址、陵墓、手工業、宗教考古中的任何一個門類都有若干個獨立的專題性研究課題。總之,10年來陜西三國隋唐宋元明時代考古無論是理念方法,還是田野工作實踐,都取得了卓著的成果,同時,也有多方面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
第一,加快考古發掘資料的整理出版迫在眉睫。近年來,考古發掘尤其是基建考古任務繁重,資料整理時間被嚴重壓縮,成果發表出版滯后,不利于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應在這方面加大經費和人員支持力度,擴大合作,推進考古發掘成果的迅速轉化。
第二,基本建設考古工作仍需重視。西安及周邊基建勘探中發現最多的是漢唐時代墓葬、居址等遺跡,并且很多是高等級墓,尤其是唐代貴族墓高度集中于兩京地區。近10年甚至20年,城市建設還在高速行進,漢唐墓葬發掘仍處于高峰期,以后,隨著基本建設工程的減緩和地下墓葬資源的減少,這種情景和機遇也不會再有。所以,一如既往地重視基建考古中的墓葬發掘,嚴格按照田野操作規程發掘每一座墓葬,詳細采集和提取墓葬信息,建立墓葬考古的數據庫。
第三,著力推進本時期城市考古工作開展和研究進度。西安地區城址考古中,東漢之后、隋大興城之前長安城考古發掘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歷史考古研究相對薄弱;隋唐長安城除宮殿遺址之外,里坊格局、東西市和城門遺址考古,由于現代城市的疊壓,很難展開,唯有抓住城市基本建設的機會,艱難推進;此外,唐宋縣城遺址考古,陜北宋金古城考古等都是今后城址考古方面的課題。

圖二一 2014年調查發現的阿里札達縣熱尼拉康南壁西段下部早期菩薩塑像
第四,加強十六國—北朝和宋金元明時代墓葬考古的研究。隋唐時代墓葬分期、制度和葬俗等的研究做為隋唐考古的重大課題,一直備受關注,研究成果豐富,目前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序列;十六國—北朝時期以及宋金元明時代墓葬考古研究則較為薄弱。十六國至北朝曾有7個政權在陜西建都,近年在西安周邊發現了大量的這一時期的貴族墓,對其分期及喪葬制度文化研究尚需深入。近年的陜西宋金元明墓葬的考古發掘,顯示了這一時期墓葬的區域化特征較為突出,分區、分期及與周邊同期墓葬的比較研究應進一步展開。
第五,以城市考古的理念,整合數十年來漢、唐長安城及周邊發掘的城址、墓葬、手工業遺址等資料,從宏觀的角度審視以漢、唐長安城為中心的都城圈的文化生態模式,設立基于考古資料基礎上的關于城址、墓葬、生產、生活的系統化綜合研究和各項專題研究課題。
第六,廣泛開展多學科結合的專題研究。本時期因遺存類型豐富而在此方面大有可為,如歷史、美術和科技測考古相結合的壁畫研究,考古和歷史地理及科技測試等相結合的古陶瓷生產工藝和貿易流通綜合研究;美術、宗教、考古相結合的石窟寺考古研究;分類細化深入的墓志碑刻研究以及以絲綢之路沿線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等。可以肯定的是,新的研究方式和多維的研究角度必然帶來新的研究成果。
占據考古學研究“半壁江山”的三國隋唐宋元明時代考古,以其文獻和實物雙重豐富的特征,在考古學人的努力下,未來必將展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
執 筆:劉呆運 邢福來 田有前于春雷 王小蒙 趙占銳苗軼飛 李 坤 席 琳肖健一
統 稿:王小蒙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現長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成立六十周年紀念[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2]同[1].
[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統萬城遺址近幾年考古工作的收獲[J].考古與文物,2011(5).
[4]同[1].
[5]邢福來.關于統萬城東城的幾個問題[J].考古與文物,2014(5).
[6]邢福來.關于統萬城周邊墓葬的幾個問題[J].考古與文物,2013(3).
[7]a.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第一工作隊.西安市唐大明宮遺址考古新收獲[J].考古,2012(11).b.龔國強,李春林,何歲利.唐長安城遺址[C]//留住文明—陜西“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及課題考古概覽(2006-2010).西安:陜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2012.
[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西安市唐長安城大明宮興安門遺址[J].考古,2014(11).
[9]a.田有前.西安市唐長安城通義坊遺址[C]//中國考古學年鑒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446-447.b.田有前,張建林.西安唐長安城通義坊遺址[C]//留住文明—陜西“十一五”期間基本建設考古重要發現(2006-2010).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10]張全民,辛龍.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遺址[C]//中國考古學年鑒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56.
[11]張佳.大唐東市或有商鋪七萬多間與西市并列唐長安城CBD[N].西安晚報,2015-11-19(4).
[12]王志友.西安市未央區大白楊漢墓與唐代陶窯遺址[C]//中國考古學年鑒2012.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416.
[13]張翔宇,高博.西安市昆明路唐代陶窯[C]//中國考古學年鑒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57-458.
[14]徐龍國,劉振東,張建鋒.西安市未央區梨園路唐代糧倉遺址[C]//中國考古學年鑒201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449.
[15]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長安醴泉坊三彩窯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醴泉坊遺址2001年發掘報告[M].西安: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
[17]張建林,田有前.隋唐長安城的考古發現與研究[C]//中國考古學會第十六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18]羅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記[J].考古與文物,1985(6).
[19]張建林.隋文帝泰陵[C]//中國考古學年鑒2011.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481.
[20]雖然《封氏聞見記》載:“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象儀衛耳。”一些學者如宮大中也推測在洛陽等地發現的石刻可能屬于東漢陵園,畢竟未得到證實,見宮大中.東漢帝陵及神道石刻[C]//中國古都研究(第四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1]朱偰.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2]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與“突厥化”問題[C]//歐亞學刊(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
[23]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間與秩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12-224.
[24]張建林.唐代帝陵陵園形制的發展與演變[J].考古與文物,2013(5).
[25]a.徐衛民等.陜西帝王陵墓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b.陜西省文物局.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卷[M].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9.
[26]肖健一.明秦藩家世譜系與墓葬分布初探[J].考古與文物,2007(2).
[27]梁志勝,王浩遠.明末秦藩世系考[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5).
[28]陳冰.西安明秦王墓的考察與研究[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3.
[29]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東郊田王晉墓清理簡報[J].考古與文物,1990(5).
[30]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雁南二路西晉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0(9).
[31]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茅坡新城西晉墓清理簡報[J].文博,2014(6).
[32]王輝.西晉墓葬的美術文化考古思索—以偃師杏園墓出土的陶空柱盤為例[J].中華文化論壇,2014(10).
[33]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陽十六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4]岳起,劉衛鵬.關中地區十六國墓的初步認定—兼談咸陽平陵十六國墓出土的鼓吹俑[J].文物,2004(8).
[35]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專用高速公路十六國墓發掘簡報[J].文博,2009(4).
[3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掘,待刊.
[37]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涇陽坡西十六國墓發掘簡報[C]//文物考古論集(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38]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掘,待刊。
[39]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鳳棲原十六國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4(1).
[40]李維,楊軍凱等.西安灞橋發現十六國墓首次驚現彩繪鎧甲俑群[J].收藏界,2012(1).
[4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掘,待刊.
[42]a.岳起,劉衛鵬.關中地區十六國墓的初步認定—兼談咸陽平陵十六國墓出土的鼓吹俑[J].文物,2004(8).b.韋正.關中十六國考古的新收獲—讀咸陽十六國墓葬簡報札記[J].考古與文物,2006(2).c.韋正.關中十六國墓葬研究的幾個問題[J].考古,2007(10).d.董雪瑩.十六國北朝墓葬出土鼓吹俑的類型與分期[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12).e.易立.魏晉十六國墓葬中“降釉小罐”初探[J].中原文物,2008(1).f.周揚.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出土坐樂俑的時代與來源—十六國時期墓葬制度重建之管窺[C]// 西部考古(十四).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g.劉衛鵬,張淑娟.十六國北朝時期的女樂[C]//碑林集刊(十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4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十六國至北朝時期長安城宮城遺址的鉆探與試掘[J].考古,2008(9).
[44]劉呆運.鹿善墓葬地研究[J].考古與文物,2013(4).
[45]a.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韋曲北塬北朝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5(5).b.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韋曲高望堆北朝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0(9).c.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魏墓發掘簡報[J].文物,2009(5).
[4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獲[J].考古與文物,2010(2).
[47]倪潤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與社會演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54.
[48]張全民.關中地區北魏西魏陶俑的變化[J].文物,2010(11).
[49]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陜西靖邊縣統萬城周邊北朝仿木結構壁畫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3(3).
[50]同[48].
[51]劉呆運.長安新發現兩座西魏墓葬[C]//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年報(2014年).西安: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5.
[5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內部資料。
[5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內部資料。
[54]同[48].
[55]趙強.西魏兩座紀年墓葬及相關問題探討[J].考古與文物,2015(4).
[5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獨孤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1(5).
[5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郭生墓發掘簡報[J].文博,2009(4).
[58]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莫仁相、莫仁誕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2(3).
[59]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掘,待刊.
[60]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張氏家族墓清理發掘收獲[N].中國文物報,2013-8-2(8).
[6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7(3).
[6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掘,資料待刊。
[63]a.申秦雁.論中原地區隋墓的形制[J].文博,1993(2).b.劉呆運.關中地區隋代墓葬形制研究[J].考古與文物,2012(4).c.劉呆運.關中地區隋代墓地分布研究[J].考古與文物,2015(5).d.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J].文物,2018(1).
[64]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陜西咸陽隋鹿善夫婦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3(4).
[65]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隋元威夫婦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2(1).
[6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蘇統師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0(3).
[67]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隋韋協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5(3).
[68]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西郊三民村隋代墓葬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5(5).
[69]程義.唐代長安城周圍墓葬區的分布[J].唐史論叢,2011(13).
[70]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J].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冊,1930.后收入陳寅恪著.金明館叢稿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6.
[7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掘,待刊.
[7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掘,待刊.
[73]2008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與陜西歷史博物館合作發掘了龐留唐墓,即唐武惠妃墓。目前,較為詳細的資料介紹可見程旭.皇后的天堂—唐敬陵貞順皇后石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74]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航天城兩座唐代壁畫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5(2).
[75]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韋曲韓家灣村兩座唐代壁畫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7(5).
[7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唐代楊貴夫婦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6(11).
[77]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市西郊楊家圍墻唐墓M1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3(2).
[78]李明.論唐代的“毀墓”—以唐昭容上官氏墓為例[J].考古與文物,2015(3).
[79]2009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陽機場二期建設項目中,發掘了執失思力墓,編號M117;唐竇孝諶墓,編號M151;東為其第三子竇希瓘墓,編號M152。資料未刊布。
[80]寧琰,辛龍.唐長孫無傲及夫人竇胡娘墓志的發現與考釋[J].文博,2017(5).
[8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掘,資料未刊布.
[82]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唐殿中侍御醫蔣少卿及夫人寶手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2(10).
[83]張小麗.郭永淇.西安東長安街唐代石槨墓[C]// 2009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84]張小麗.朱連華.唐太宗民部尚書戴胄夫婦墓的新發現[J].文物天地,2015(12).
[85]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唐涼國夫人王氏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6(6).
[86]鄭旭東.西安曲江唐故博陵郡夫人崔氏墓相關問題略論[J].文博,2017(3).
[8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華陰唐宋素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8(3).
[88]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戶縣兆倫遺址隋唐墓葬發掘簡報[J].文博,2015(5).
[89]a.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鳳棲原唐郭仲文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2(10).b.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唐郭仲恭及夫人金堂長公主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3(2).c.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唐太府少卿郭锜夫婦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4(2).d.郭永淇.新出土郭子儀孫郭在巖墓志考[J].文博,2014(6).其他資料均未公布,保存在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
[90]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長安區晚唐時期令狐家族墓葬發掘簡報[J].文博,2011(5).
[91]張全民.新出唐百濟移民禰氏家族墓志考略[J].唐史論叢,2012(14).
[92]a.柴怡.西安西郊唐代突騎施王子墓[J].收藏界,2012(2).b.葛承雍.新出土《唐故突騎施王子志銘》考釋[J].文物,2013(8).
[93]2008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為配合“長安萬科”項目基本建設,在西安棗園三民村發掘22座唐代小型墓葬,其中4座紀年墓墓主均為女官。
[94]201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為配合“長樂盛世”項目基本建設,在西安西郊棗園西路與棗園北路交匯處發掘了16座唐墓,其中7座紀年墓墓主皆為宮女,時代為唐中宗景隆三年(709年)至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之間。
[95]a.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編著.唐嗣虢王李邕墓考古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b.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順陵文物管理所編著.唐順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c.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編著.唐懿德太子墓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d.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昭陵博物館編著.唐韋貴妃墓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e.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周原博物館編.周原漢唐墓[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f.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博學院編著.陜西鳳翔隋唐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96]a.冉萬里編著.隋唐考古[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9.b.程義著.關中地區唐代墓葬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c.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陜西出土壁畫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d.陜西歷史博物館編.唐墓壁畫珍品[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e.程旭.絲路畫語—唐墓壁畫中的絲路文化[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6.f.程義.20世紀關中唐代墓葬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唐史論叢,2008(10).
[97]唐墓中道教文化因素研究的文章主要有:a.程義.關中唐代墓葬里的道教因素鉤沉[J].唐史論叢,2011(12).b.尹夏清.從守門與鎮墓之制看漢唐喪葬文化中的道教因素[J].宗教學研究,2007(3).唐墓中佛教文化因素研究的文章主要有:c.霍巍.唐宋墓葬出土陀羅尼經咒及其民間信仰[J].2011(5).d.郭曉濤.陜西鳳翔唐墓出土陀羅尼經咒的圖像解讀[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8).e.冉萬里.略論佛教地域觀念對隋唐時期喪葬習俗的影響—以各類追冥福行為為中心[J].西部考古,2009(四).f.楊潔.唐代鎮墓天王俑的世俗文化因素考略—兼談兩京地區的差異[J].四川文物,2009(5).
[98]唐墓中有關文物保護研究的文章主要有:a.楊忙忙.唐墓壁畫環境監測與分析研究[J].考古與文物,2010(3).b.楊文宗.陜西歷博壁畫保護工作的回顧與展望[C]//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c.2016.楊文宗.我國墓葬壁畫的保護方法[J].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7(4).d.梁龍.基于樣本的圖像修復算法在唐墓壁畫上的應用[D].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3.
[99]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畫研究[M].西安:陜西美術出版社,2005.
[100]鄭以墨.唐墓壁畫研究綜述[J].藝術設計研究,2009(3).
[101]程旭.唐墓壁畫中周邊民族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關系[D].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12.
[102]a.榮新江,李丹婕.郭子儀家族及其京城宅第—以新出墓志為中心[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b.楊軍凱.楊潔.唐郭仲文墓志及其家族葬地考[J].文物,2012(10).
[103]張全民.新出唐代百濟移民禰氏家族墓志研究[J].唐史論叢,2012(13).
[104]a.李明,耿慶剛.《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箋釋—兼談唐昭容上官氏墓相關問題[J].考古與文物,2013(6).b.李明.論唐代的“毀墓”—以唐昭容上官氏墓為例[J].考古與文物,2015(3).c.賈二強.釋唐李建成及妃鄭觀音墓志[J].唐史論叢,2014(18).d.趙占銳,呼嘯.唐宰相韓休及夫人柳氏墓志考釋[J].唐史論叢,2016(23).e.王其祎.周曉薇.應予關注的中晚唐文學研究新史料—新見張籍撰《唐陽城縣主李應玄墓志銘》[C]//唐研究(十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f.仇鹿鳴.新見《姬揔持墓志》考釋—兼論貞觀元年李孝常謀反的政治背景[C]//唐研究(十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05]a.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志[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b.趙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續編[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c.西安市長安博物館.長安新出墓志[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d.西安市文物稽查隊.西安新獲墓志集萃[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e.故宮博物院,陜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三)[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f.胡戟編著.珍稀墓誌百品[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6.g.陜西歷史博物館.風引薤歌: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墓志萃編[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106]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編著.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志[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107]王小蒙,陳力.隋唐五代時期的灰陶制品[J].文博,2015(1).
[108]a.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孟村宋金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0(5).b.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宋范天祐墓發掘簡報[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6).
[109]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獲[J].考古與文物,2015(2).
[110]a.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藍田縣五里頭北宋呂氏家族墓地[J].考古,2010(8).b.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獲[J].考古與文物,2011(2).
[111]a.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鳳翔孟家堡唐、宋、明墓發掘簡報[J].文博,2012(6).b.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鳳翔孫家南頭墓地宋元明墓葬發掘簡報[J].文博,2014(3).
[112]a.張蘊等.九泉之下的名門望族—陜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地[N].中國文物報,2009-9-11(4).b.張蘊,衛鋒.藍田五里頭北宋“考古學家”的家族墓地[J].中國文化遺產,2010(2).c.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藍田縣五里頭北宋呂氏家族墓地[J].考古,2010(8).d.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獲[J].考古與文物,2011(2).e.張蘊.北宋名門的悲與喜—陜西藍田呂氏家族墓園發掘記.中國文物報[N].2013-9-5(3).f.張蘊.陜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園考古北宋金石學家的長眠之地[J].大眾考古,2015(2).
[113]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乳駕莊宋代磚雕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3(8).
[114]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獲[J].考古與文物,2010(2).
[115]王沛,王蕾.延安宋金畫像磚[M].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11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獲[J].考古與文物,2011(2).
[11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獲[J].考古與文物,2013(2).
[118]秦育春.陜西西鄉縣宋墓新出土瓷器[J].收藏,2013(21).
[119]a.魏軍.北宋呂倩容墓志考釋[J].考古與文物,2016(3).b.郭永淇.北宋范天佑墓志考釋[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6).
[120]a.程義,程惠軍.漢中宋代鎮墓神物釋證[J].四川文物,2009(5).b.秦育春.陜西西鄉縣宋墓新出土瓷器[J].收藏,2013(21).c.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等.陜西華縣南宋銅錢窖藏[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10).
[121]a.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異世同調.陜西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M].北京:中華書局,2013.b.張蘊.古硯遺芳—記藍田北宋呂氏墓出土文物[J].收藏家,2014(9).c.藍田墓地與北宋藏家呂大臨的《考古圖》[J].美成在久,2016(1).d.劉濤.呂氏家族墓出土的北宋耀州瓷[J].收藏,2016(5).
[122]a.姚小鷗.韓城宋墓壁畫雜劇圖與宋金雜劇“外色”考[J].文藝研究,2009(11).b.周華斌.乞兒驅儺與宋雜劇—韓城“北宋雜劇圖”壁畫讀解[J].中央戲劇學院學報(戲劇),2015(5).c.康保成,孫秉君.陜西韓城宋墓壁畫考釋[J].文藝研究,2009(11).d.延保全.宋雜劇演出的文物新證—陜西韓城北宋墓雜劇壁畫考論[J].文藝研究,2009(11).e.楊效俊.陜西韓城盤樂村宋墓壁畫的象征意義[J].文博,2015(5).
[12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發掘調查新收獲[J].考古與文物,2014(2).
[124]王沛,王蕾.延安宋金畫像磚[M].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125]a.王勇剛.陜西甘泉金代壁畫墓[J].文物,2009(7).b.袁繼明.陜西甘泉城關鎮袁莊村金代紀年畫像磚墓群調查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4(3).c.王勇剛.陜西甘泉柳河渠灣金代壁畫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6(11).
[126]王保東.富平發現金代陶罐[J].考古與文物,2015(5).
[12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渭南靳尚村金末元初壁畫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4(3).
[128]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金代李居柔墓[J].考古與文物,2017(2).
[129]a.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孟村宋金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0(5).b.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等.西安南郊黃渠頭村金墓發掘簡報[J].文物春秋,2014(5).c.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銅川阿來金、明墓葬發掘簡報[J].文博,2015(2).
[130]李舉剛,楊潔.陜西地區蒙元墓葬的發現與研究[C]//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十八).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131]a.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皇子坡村元代墓葬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4(3).b.張小麗,袁長江.西安雁塔南路發掘一元代墓葬[N].中國文物報,2009-10-9(4).c.張全民,郭永淇.西安長安鳳棲原墓葬發掘[C]//2009中國考古重要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d.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大朝劉黑馬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5(4).e.成立.一夫三妻元代合葬墓驚現罕見瓷器:看,這是珍貴的元青花[N].西安晚報,2011-6-21(3).f.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張達夫及其夫人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3(8).g.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繆家寨元代袁貴安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6(7).
[13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大朝劉黑馬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5(4).
[133]榆林榆陽區的元代壁畫雖然為征集品,但是根據與相關材料的對比,可以肯定其墓葬應該為八邊形穹窿頂單室石墓,與橫山縣羅圪臺村元代墓葬形制相同。姬翔月.陜西榆林發現的元代壁畫[J].文博,2011(6).
[134]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橫山縣羅圪臺村元代壁畫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6(5).
[135]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畫墓[J].考古與文物,2000(1).
[136]a.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東郊元代壁畫墓[J].文物,2004(1).b.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編.西安韓森寨元代壁畫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37]袁泉.洛渭地區蒙元墓隨葬明器之政治與文化考[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10).
[138]a.楊潔.陜西地區出土蒙元陶俑類型分析[J].文博,2013(5).b.楊潔.陜西關中蒙元墓葬出土陶俑的組合關系及相關問題[J].考古與文物,2015(4).
[139]a.李舉綱.西安南郊新出土《劉黑馬墓志》考述[J].考古與文物,2015(4).b.李舉綱.元劉天與墓志及相關問題探析[J].文博,2015(2).c.段毅.元代醫學教授武敬墓志考略[C]// 碑林集刊(二十).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140]侯新佳,李根枝,張芳.陜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畫墓墓主族屬淺析[J].華夏文明,2016(3).
[14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明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142]銅川市考古研究所. 陜西銅川新區未來城明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6(2).
[14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明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144]同[143].
[145]同[143].
[14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留住文明[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147]劉衛鵬.陜西彬縣東關村明代石室壁畫墓的發掘[J].蘇州文博論叢,2010.
[148] 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M].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8:5、9、70.
[149] 史念海. 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時諸長城遺跡的探索[J]、鄂爾多斯高原東部戰國時期秦長城遺跡探索記[J]、洛河右岸戰國時期秦長城遺跡的探索[J]、再論關中東部戰國時期秦魏諸長城[J]、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佈及其歷史軍事地理[J],見史念海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50] 彭曦.戰國秦長城考察與研究[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
[151] a.艾沖.明代陜西四鎮長城[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b. 艾沖.中國古長城新探[M].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
[15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省早期長城資源調查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5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省明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墻體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54]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省早期長城資源調查報告(營堡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155]于春雷.“新修龍泉寺碑記”與延綏鎮長城[J].文博.2012(6).
[156]于春雷.從點到面:明代延綏鎮長城的形成與演變—兼談延綏鎮的邊防理念[C]//長城資源調查工作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157]于春雷.長城的進化—以陜西長城為例[J]. 文博.2016(4).
[158]白云翔.手工業考古論要[C]//東方考古輯刊,2012.一文中認為,手工業考古研究不能等同于手工業制品的研究,其主要內容有:原材料的研究,生產工具和生產設施研究,工藝技術和生產流程研究,產品研究,產品流通和應用研究,生產者研究,生產經營方式研究,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研究,社會經濟研究,社會文化研究十個大的方面;將其作為一種“社會存在”一個“產業系統”和“一個文化因子”進行研究。
[159]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西郊窯頭村唐代陶窯發掘簡報[J].洛陽考古,2009(2).
[160]a.陸明華.陜西出土耀州窯青瓷考察記[N].中國文物報,2010-8-4;b.錢冶.探尋柴窯之旅—五代耀州窯天青釉瓷考察散記[N].中國文物報,2014-6-4.c.高功,張繼開.探索千年之謎—柴窯—聚焦中國柴窯文化論壇[J].收藏界,2010(10),C.岳巖,王學武.第二屆中國柴窯文化高層論壇在京舉辦[J],收藏,2013(1).這兩次以收藏界為主的論壇,展開了柴窯產地的討論,其中,《收藏界》2010年11期,集中刊登了會議論文。
[161]a.王小蒙.模仿與創新—唐至宋初耀州窯與越窯青瓷的影響和互動[C]// 中國古陶瓷學會.中國古陶瓷研究輯叢編(越窯青瓷與邢窯白瓷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10).b.黃堡窯裝燒工藝的發展演變—兼談黃堡窯與越窯、汝窯及高麗青瓷的關系[C]//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耀州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10).
[162]王芬,施佩,朱建峰,林營,王學武.耀州窯五代天青瓷的研究[C]// 2016中國硅酸鹽學會陶瓷分會年會會刊.
[163]a.易立.試論五代宋初耀州窯青瓷的類型與分期—以墓葬塔基出土文物為中心[J].考古與文物,2009(3);b.彭善國,劉輝.東北、內蒙古出土的耀州窯青瓷—以墓葬材料為中心[J].考古與文物,2015(2);c.同[a];d.張紅星.內蒙古地區出土耀州窯瓷器[J].內蒙古文物考古,2009(12);e.穆青.河北出土的耀州窯青瓷—兼談五代至北宋早期青瓷與白瓷上的深剔刻裝飾[C]//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耀州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10).
[164]a.禚振西.黑釉耀瓷的裝飾藝術[J].收藏,201(13);b.王小蒙.唐耀州窯素胎黑彩瓷的工藝特點及其淵源、影響[J].考古與文物,2013(6);c.楊俊艷.析唐代金銀器對十世紀耀州窯青瓷的影響[C]//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耀州窯[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10).d.徐仙女(韓國)[C]//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耀州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10).
[165]a.杜文.窖藏及墓葬出土耀州窯瓷器問題探討[C]//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耀州窯(圖錄).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10);b.馮小琦.故宮博物院藏耀州窯瓷器[C]//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耀州窯(圖錄).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10);c.耿東升.析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宋金時期耀州窯青瓷[C]//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耀州窯(圖錄).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10);d.張蘊.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出土耀州窯瓷器[C]//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耀州窯(圖錄).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10).
[166]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考古所,安塞縣文物旅游局.陜西安塞縣大佛寺石窟調查簡報[J].文博,2013(12).
[16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隊,岐山縣博物館.陜西岐山蔡家坡石窟考古調查報告[J].考古與文物,2009(5).
[168]楊一苗,耿凌楠.陜西留壩縣發現隋唐佛教造像龕[N].新華每日電訊,2008-10-09(8).
[169]李俊,喬建軍.陜西榆林市藏傳佛教石窟及摩崖石刻調查[J].考古與文物,2016(3)
[170]席琳.綏德圪針灣佛窟[C]//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年報(2017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8.
[171]張建林,田有前.陜北富縣發現一批北朝至宋代佛教造像[N].中國文物報,2010-02-26(4).
[172]a.韓宏,陳永輝.陜西鎮安發現元代寺院遺址[N].文匯報,2017-03-28(5).b.劉呆運.鎮安毗盧寺遺址[C]//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年報(2016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7.
[17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明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41,88.
[174]趙爭耀.西咸機場二期考古重大發現[N].西安晚報/三秦都市報,2010-12-10.
[175]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榆林市考古勘探工作隊,靖邊縣文物管理辦公室,靖邊縣統萬城文物管理所.陜西靖邊縣統萬城周邊北朝仿木結構壁畫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3(3).
[176]肖健一.空港新城楊家村遺址[C]//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年報(2014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5.
[177]邢福來,苗軼飛.長安大居安村唐代墓地[C]//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年報(2017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8.
[178]王志友.馬騰空遺址[C]//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年報(2016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7.
[179]肖健一.空港新城楊家村遺址[C]//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年報(2017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8.
[180]《陜西石窟內容總錄》編纂委員會.陜西石窟內容總錄·銅川卷[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陜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2017.
[181]《陜西石窟內容總錄》編纂委員會.陜西石窟內容總錄·延安卷[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陜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2017.
[182]《陜西石窟內容總錄》編纂委員會.陜西石窟內容總錄·榆林卷[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陜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2017.
[18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門寺博物館,寶雞市文物局,扶風縣博物館.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84]銅川市考古研究所,西安美術學院中國藝術與考古研究所.藥王山摩崖造像考古報告[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18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龍寺與西明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186]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文物精華·佛教造像[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
[18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省銅川市藥王山管理局.陜西藥王山碑刻藝術總集[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188]馬世長,丁明夷.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概要[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89]冉萬里.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的考古學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190]程旭.陜西館藏造像概述[J].敦煌學輯刊,2014(3).
[191]介永強.唐都長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J].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4(2).
[192]常青.蔡家河與喇嘛帽山千佛院—陜西麟游的兩處佛教窟龕造像調查[J].考古與文物,2016(3).
[193]席琳.高原上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西藏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2008年試點工作散記[J].中國西藏,2008(6).
[194]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西藏芒康縣扎進瑪尼石刻造像與達瓊摩崖造像調查報告[J].西藏研究,2017(1).
[195]席琳等.西藏昌都地區芒康、察雅兩縣考古調查新發現兩處吐蕃石刻遺存[N].中國文物報,2009-11-13(4).
[196]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等.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芒康縣鹽井鹽田調查報告[J].南方文物,2010(1).
[197]席琳.洛扎縣吉堆吐蕃墓地調查[C]// 中國考古學年鑒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23.
[198]席琳,何偉,張建林.西藏日土洛布措環湖考古調查取得重要收獲[N].中國文物報,2013-10-18(1).
[199]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西藏日土縣丁穹拉康石窟群考古調查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4(6).
[200]于春等.西藏阿里瓊隆銀城遺址考古手記[J].大眾考古,2015(12).
[201]席琳等.西藏札達度日堅巖畫考古調查取得重要收獲[N].中國文物報,2016-11-18(8).
[20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從長安到拉薩:2014唐蕃古道考察紀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