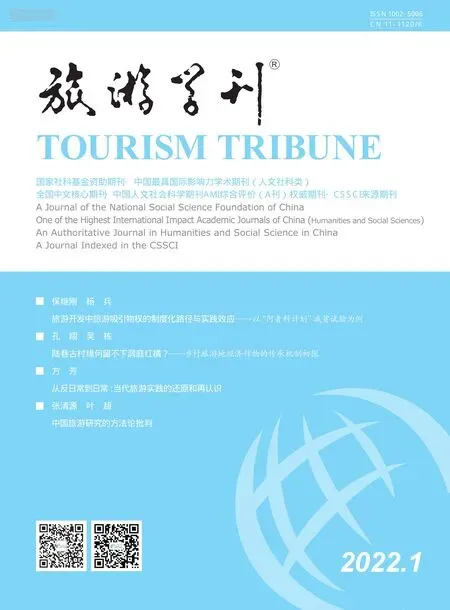以“藏銀”之名:民族旅游語境下的物質、消費與認同
李菲
[摘要]在今天中國的民族工藝品和旅游紀念品市場中,“藏銀”已成為一個頗為流行的物質標簽。以“藏銀”之名制造、消費的商品占有顯著的市場份額。在旅游人類學視域下,“藏銀”同時作為“物”與“物的觀念表達”,折射了中國多民族國家想象與認同實踐中物質性與族群性的復雜關聯,其社會性建構過程也因而關涉到:(1)藏族古老的合金制造技藝如何表達了特定的族群文化傳統;(2)“藏銀”之物與名如何在漢藏互動的歷史進程中生成與變遷;(3)借助旅游消費時代的“社會煉金術”,“藏銀”之名如何經由重構、挪用與泛化而成為牟利的商業策略;(4)圍繞“藏銀”展開的記憶、敘事、制造和消費,如何隱喻了當代民族旅游的深層社會政治結構及其實踐邏輯。
[關鍵詞]民族旅游;物;消費;族群認同;藏銀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8)01-0074-12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1.012
引言:物的故事
在對“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dd)族群工藝品與旅游紀念品的開創性研究中,美國人類學家Graburn教授注意到,文化外部人士較少關注作為制作原料的物質與質材,而在其制造者看來,這卻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事實上,在一件族群工藝品或旅游紀念品中,盡管所用物料與質材不像設計主題、范型、色彩乃至尺寸等要素,往往在第一眼就能傳達出明顯的象征性意義,但同樣也負載著不亞于前者的復雜文化內涵。
過去數十年來,在國際學術界關于族群工藝品和旅游紀念品的民族志研究與理論探討中,物(material)與物質性(materiality)的相關議題已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維度。其主要研究取向包括:(1)在文化展示和消費語境中探討文化內部與外部立場關于物的觀念與態度差異;(2)探討在原始的/族群的/土著的藝術與現代的/旅游的/大眾的藝術之間的轉換法則與限度;(3)在族群文化商品化、商業化的進程中反思和重建對于“真實性”(authenticity)的理解;(4)在旅游互動的“主-客”框架下考察族群工藝品、紀念品制造者的傳統、文化和社會變遷;(5)在自殖民時期至當代的歷史進程中討論不同社會之間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或“旅游邊界地帶”(touristic borderzone)所發生的文化適應、文化涵化和文化雜交現象(hybridity);(6)考察旅游實踐中地方社會認同與游客自身認同的調整與重塑等。這些研究由物、物的社會歷史到物的觀念與實踐,展現出西方人類學旅游研究的開闊理論視域和前景,但遺憾的是,其中較少涉及來自中國的相關個案和討論。與此同時,在實踐層面,旅游紀念品早已成為國外旅游業收入的重要來源,在中國卻仍然是旅游產業鏈條中的薄弱環節。這一滯后現狀的扭轉,關鍵不僅在于加強消費行為分析與產品開發設計等技術環節,還在于如何借鑒國外研究經驗,圍繞族群工藝品和旅游紀念品所承載的族群文化、歷史記憶、認同、意義與情感等重要維度來拓展視野,深化認識。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藏銀”個案,力圖在人類學旅游研究的動態框架下,從歷時追溯與共時分析的雙向維度來考察當代中國民族旅游語境下物質、族群與民族國家的錯綜圖景,進而沿著以下四個問題層次展開討論:其一,藏族傳統的銀合金制造技藝如何表達了他們獨有的宗教、文化、審美觀念;其二,“藏銀”的名與實,如何根植于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王朝的互動歷史之中,并在近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最終形成;其三,借助消費時代的“社會煉金術”(social alchemy),“藏銀”之名如何經由重構、挪用、泛化而成為牟利的商業策略,并成為消費時尚;最后,在當代多民族中國,通過制造和消費不同的族群物質——如“藏銀”“苗銀”“羌銀”“傣銀”等,關于“內部他者”“漢與非漢”以及“多元一體”的族群想象與認同,如何被持續地具象化并反復確認,最終在游客個體的身體經驗層面得到落實。
透過“藏銀”卷入中國多民族歷史與當代旅游實踐的復雜過程,本文試圖指出,物質并非是透明的、靜止的反映出特定的社會一文化意義;或者,被視為某種次級的、次要的東西——當被制成民族工藝品和旅游紀念品時,就因消融為整體的一部分而喪失了豐富多元的聲音。在歷史與人類學的雙重視域下,一方面經由“物”與“詞”的知識考古,揭示出了“藏銀”所負載的獨特族群傳統和復雜歷史意涵;另一方面,“藏銀”更超越了名詞態的“詞”與“物”,表征了一個物質性與非物質性交融、族群性與商品性生成轉換的動態實踐過程,折射了當代民族旅游語境中消費、文化與認同政治的重要議題。
1名實之間:物的跨族群歷史與歷史敘事
在當今中國,各式各樣號稱以“藏銀”制作的民族工藝品、裝飾品與紀念品,已日益成為廣受大眾游客和民族文化愛好者歡迎的流行時尚。與此同時,關于“藏銀”,還出現了一些非常典型的社會話語表述。這些表述通過網絡廣為傳播,在相當程度上代表并塑造了旅游消費時代大眾對“藏銀”的基本認知:
“……藏銀是一種名稱,其實是一種合金,在藏族人那里說來,藏銀其實就是白銅。可以把藏銀理解成銀的合金,一般來說真正藏銀的含銀量都在10%~30%之間,因為藏銀的提煉都是在沒有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基礎上的,所以無法高度提純。所以當藏人拿著藏飾品對你真誠地說是真正的銀子時,請別懷疑他們的誠信!藏銀制品的民族工藝才是主要買點。……”(互動百科“藏銀”詞條)
不過,問題也由此而生:“藏銀”究竟是種什么物質?“藏銀”之名由何而來?為何那些廉價的合金可以、且應當被當作“真正的銀子”?在旅游語境中,這種看似“不真實”的族群質材如何反映出不同人群之間的互動關系?看來,“藏銀”并不能理所當然地憑其名稱就被理解為“藏族的銀飾”或“藏族的銀器”。這一問題的討論還必須返回到藏族古老的制銀歷史之中加以深入展開。
1.1“藏銀”的歷史與歷史敘事
從物質生產層面來看,根據考古學研究,西藏古代銀器制作最早的高峰可追溯到公元7至8世紀的吐蕃帝國。在當時,通過連接中國與地中海地區利潤豐厚、文化交融的絲綢之路,地處中亞樞紐位置的吐蕃與外部世界有著頻繁的交流和貿易往來。該時期吐蕃銀器制作的卓越技藝、式樣、紋飾和風格等,通常被認為是來自中國、波斯、薩珊王朝等跨文化影響的結果。
由于兼具美與功用的價值,銀和金一樣,在世界各地的古代文化中也是一種廣受珍視的金屬物質。銀是混合性礦物,在古代不易開采。迄今為止,僅有一些零星的記載散見于藏族古典文獻之中,如《紅史》《青史》及《賢者喜宴》等均提及,古代藏族的銀礦開采和銀器制造,始于大約公元1世紀的吐蕃第9代贊普布德貢結時期,但尚缺乏展開進一步討論的細節資料和證據。盡管上述文獻均指出藏族有悠久的制銀歷史,而事實上在西藏的整個歷史中銀都并非主要是其本地出產物,東面那些強大的中原王朝則在漢藏互動交往的漫長歷史中擔當了其最重要的銀供應者。尤其自元代至清末,銀一直是中原王朝賜給西藏地方政府的豐厚賞賜和貴重禮物之一。大量銀元不斷流入藏地,越來越成為中原王朝加強對西藏掌控的重要物質一經濟手段,西藏的銀器制作傳統因而亦深植于漢藏文化政治關系的深遠歷史脈絡之中。
在藏語中,Dngul這個詞同時表示“銀”和“錢”。在舊時代,銀也被藏人視為財富和地位的象征。在高度階層化的傳統西藏社會中,銀主要為僧侶和上層貴族所擁有和消費,對于普通民眾和農奴等低下階層來說,銀極為稀有。因此,一些含銀量較低的銀合金被制造出來以滿足民眾日常生活的宗教、功用和審美需求。一般來說,常見的傳統藏式銀合金含有約70%的銅和不到30%的銀成分。對下層民眾來說,它更廉價,也更耐用,因而常被用于制造雕像、神龕、首飾、瓶和碗等儀式用具、裝飾物與日常生活用品等。與此同時,“白銅”,一種銅鎳合金,由于擁有與銀相似的外觀和色澤,也常常被藏族人在各種場合用作銀的替代品。
從跨族群互動的歷史維度來看,“藏銀”則顯然是一個由文化外部群體——漢族所給定的命名。事實上,“藏銀”這一說法出現的時間相當晚近,大約在20世紀后半葉才逐漸成為一個相對固定的概念。并且在此百余年中,它始終與中國近現代貨幣史上的另一個關鍵概念——“番銀”,有著錯綜復雜的關聯。
自18世紀以來,隨著清帝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越來越多的外國銀幣通過殖民與貿易活動從大不列顛、法蘭西、荷蘭、日本等國流人中國境內。這些外國銀幣往往有較高的鑄造工藝、更均勻的尺寸和更足、更穩定的成色,因而受到國人歡迎,也很快對中國歷史悠久的既有貨幣體系造成了巨大沖擊。相關資料顯示,至晚清,各種外國銀幣在中國的市場流通量已經高達約43%,幾近整個貨幣流通量的半壁江山。正是在此背景下,“番銀”在清代歷史文獻中體現了其原初的意指:來自外國的銀幣。
1792年(乾隆五十六年),清中央王朝下令西藏地方政府組建“西藏寶藏局”,并在拉薩開設“雪造幣廠”,開始鑄造“寶藏銀幣”。1793年,乾隆皇帝正式頒布著名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旨在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領域的全面掌控。“西藏寶藏局”的開辦以及“寶藏銀幣”的鑄造正是《欽定二十九條》中政治經濟領域的關鍵條款和重要舉措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近現代貨幣史上,西藏寶藏局所鑄造的“寶藏銀幣”乃是清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政府鑄造、發行自有銀幣的首次嘗試。中央王朝此舉目的首先在于抵御18世紀以來由廓爾喀大量流入西藏的劣質銀幣對藏區經濟所造成的侵蝕,阻止廓爾喀以劣質銀幣換走大量中國銀錠;此舉也力圖抵御英、法等西方殖民勢力,尤其是覬覦西藏已久的英殖民者對西藏的不斷滲透,從而鞏固中央王朝對西藏的政治經濟主權;與此同時,“寶藏銀幣”的鑄造也是清王朝為在內地創建銀幣幣制而累積經驗的一項重要嘗試。換言之,在鑄制之初“寶藏銀幣”便肩負著抵御外國銀幣——“番銀”大量涌入、抵御列強入侵,維護帝國經濟主權的重要使命。“寶藏銀幣”的問世也因而成為近現代史上西藏與中央王朝貨幣一體化、邁向經濟統一的重要里程碑。
由于清帝國沿襲了歷代中原王朝的“天下觀”和“漢/番”族群治理框架,在遙處西南邊陲一隅的藏地所展開的這一重要幣制改革舉措,也在“漢/番”族群互動的歷史脈絡中被加以表述。因而,“寶藏銀幣”在其后的漢文歷史文獻中常常又被稱為“番銀”,意指在非漢族地區所鑄造的銀幣。這便是“番銀”一詞所具有的另一重要歷史意涵。
作為一種整合西藏與內地幣制、鞏固帝國政治經濟統治的重要手段,清中央王朝一直力圖使西藏“番銀”與內地貨幣體系保持一致的成色和標準,但在帝國內外多重壓力之下,隨著近代西藏社會經濟的嚴重崩塌,西藏“番銀”的含銀量也隨之迅速降低。據相關史料記載,僅數十年間其含銀量便跌至不到內地銀幣成色的50%~60%。由此,在西藏及其周邊地區鑄造流通的“番銀”成為近現代中國貨幣史上劣質銀幣的典型代表。而中央王朝、西藏地方政府以及藏邊割據軍閥等多方勢力圍繞這一地方幣種的純度、成色、鑄造權、控制權所展開的漫長爭斗,也折射了晚清至民國復雜糾結的漢藏關系。
20世紀以來,在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番”這個源遠流長、意涵多重的重要漢語關鍵詞,由泛指華夏內外的“非我族類”,逐漸退縮至民族國家邊界之內,弱化了諸如“國外的”“外國人”等意指,退而僅指民族國家內部的“非漢”族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民族政策下,“番”最終被一個全新的術語——“少數民族”所取代。在新的歷史語境中,西藏人被識別為56個民族之一的“藏族”,相應地,西藏“番銀”這一歷史概念也逐漸轉換為一個新的指稱,“藏銀”。一方面,在民間,漢藏交融地帶的民眾自晚清以來對藏地所鑄銀幣即有“藏銀”“藏元”的說法,另一方面,“藏銀”一詞的正式形成及在全社會的流傳則晚見于20世紀末期。新時期以來,中國古錢幣研究領域的一些學者開始在著述中使用“藏銀”概念。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旅游和民族旅游的快速興起,“藏銀”開始成為社會消費領域一個廣為人知的語匯。在語匯傳播過程中,“藏銀”這一指稱首先與其學術意涵“晚清時期西藏所鑄造銀幣”發生了分離,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借助學術話語的權威性,“藏銀”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并獲得了新的社會意涵:通過將特定民族稱謂加諸于金屬物質銀之前,“藏銀”被視為某種特殊的“民族質材”,用以制造藏族工藝品或具有西藏文化格調的旅游紀念品。不過,某種“質材不純”的強烈暗示卻始終縈繞于“藏銀”這一命名之上。
1.2純/不純:民族質材與文化差異
在現實消費領域,“藏銀”這一“民族質材”的命名具有強烈的二重意味:既試圖掩飾又同時暗示了其質材的不純。這二重意味之間模棱兩可的模糊地帶恰是商人借以牟利的巨大操作空間。不過,從物質的文化意義維度來加以分析,對于銀制品的質材純度問題,藏族人卻有著相當不同的傳統、態度和觀念。在傳統西藏社會生活中,由于銀金屬資源的匱乏,低純度銀合金的使用遠較純銀更為普遍。事實上,大量的純銀制品在最近數十年間才在西藏廣泛制造、貿易和使用。不過,在金屬銀匱乏這一物質事實之外,還有一些更深層次的文化觀念有助于我們在“藏銀”質材不純的問題上能超越簡單的物質決定論。
首先,比較而言,中原漢族社會在漫長的經濟文化進程中發展出了一套根深蒂固的銀本位貨幣體系。金屬銀在其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統治者改朝換代,但純銀始終為中原地區的市場經濟活動和商品交易價格提供了基礎和標準。正如法國藏學家Boulnois指出,在過去,漢人非常依賴純銀,也喜歡使用純銀錠作為支付手段,他們難以接受任何以銀合金來替代純銀的想法。而對藏族人來說,他們在歷史上從未建立起任何一種金屬本位的貨幣體系,因而也不像漢人那樣對銀的純度懷有根深蒂固的執念。正因為如此,17世紀廓爾喀劣質銀幣在西藏的流通事實上并未對藏人產生很大的困擾,也因為如此,清末西藏“番銀”成色的一降再降,使中央政府深刻體會到了藏人對銀幣純度無關痛癢的麻木態度。這種觀念上的差異有助于解釋清王朝在試圖統一西藏和中原貨幣體系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巨大困難。
其次,在西藏,當工匠們將其他質材摻入貴重金屬時,并不一定意味著貴金屬質材變得低劣或次等了。以西藏著名的傳統質材“白利瑪”為例,白利瑪具有美麗的銀白色外觀和色澤,而它實際上是一種銅合金。白利瑪可能含有少量銀或不含銀,但卻由于其古老繁復的鑄造工藝和神圣的宗教意涵,反而是一種受到藏族高度珍視的傳統金屬質材。正如其他各種利瑪——花利瑪、黃利瑪、紫利瑪、紅利瑪等,白利瑪被廣泛用于制造佛像和宗教儀式用具,體現出了西藏能工巧匠們高超的鑄造技藝,也表達了藏族獨特的宗教觀念以及他們對佛之崇高、神秘與美的禮贊。
簡而言之,“純”與“不純”的物質觀念,在此或許不應當簡單地被置于現代冶金學知識體系之中,用純粹的科學標準和精確度量去加以評判。“藏銀”的不純,應該被理解為西藏傳統社會一套獨特的地方性知識,其中包含著藏族人特殊的生活方式、宗教情懷和審美情感。
2以“藏銀”之名:物的大眾消費與社會煉金術
由上文分析可見,“藏銀”同時作為一種物質,以及一種物質的觀念,在一個多層次的復雜社會進程中被歷史性地制造出來。在此過程中,迫于外部殖民主義壓力與內部統治危機,清帝國被動卷入了一個正在建構的、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體系;西藏更緊密地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框架之中;雖然速度和程度不同,但內地漢區社會和邊陲藏區社會均無法避免地邁入了不可逆轉的近現代進程。
需要強調的是,在“藏銀”個案中出現的關于物質“純/不純”的這對概念,本文并非是在人類學家Douglas有關“純潔”(purity)的意義上加以使用。Douglas在《潔凈與危險》一書中對物的“純/不純”“潔凈/不潔”的分析有著強烈的圣俗/世俗的二元意義指涉,而這里漢語的“不純”則是對物質雜糅性的一種描述,尤其指將某些價值較低的物質摻入價值較高的物質,也同時指人們認為其貶值、折損等的價值評判。在旅游消費語境中,“藏銀”一詞所顯現的“社會煉金術”效應背后,正是這種“不純”的物質印記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2.1族群符碼的商品轉換
今天,在中國的民族工藝品和旅游紀念品市場上,“藏銀”已然成為了一個非常流行的物質標簽。以“藏銀”之名制造、交易、消費的各色物品占據了頗為可觀的市場份額。游客當然可以從那些“對”的地方買到各種“藏銀”制品、飾品,比如拉薩老城的八廓街、后藏日喀則古老的金銀作坊扎西吉彩,或者位于四川省會成都的著名“藏民街”;同時,在北京、麗江、大理乃至遙遠的海南三亞等旅游勝地買到“藏銀”,也并不令人感到詫異。只要有旅游紀念品攤點和商販之處,“藏銀”可謂無處不在。然而,究竟“藏銀”指的是一種怎樣的物質,卻幾乎沒人能準確無誤地說出。在消費主義邏輯之下,“藏銀”成了一個語焉不詳、包羅萬象的游動能指:
對于漢族來說,“藏銀”這個名稱,聽上去就像是某種由藏族所創造的、具有藏族特色的銀或銀器,而且價格通常要比“真”的銀器來得便宜。對于藏族來說,在傳統上它指的是一些銀合金,由于西藏歷史上金屬銀的匱乏以及藏區特有的金屬鑄造技藝,這些銀合金中銅與其他物質的含量常常要遠大于銀的含量。而在今天,由于純銀不再難以獲得,傳統意義上的老“藏銀”已經難得一見,其鑄造技藝也將瀕臨失傳。此外,由于藏區和尼泊爾歷史以來在宗教、文化、貿易等多方面的密切聯系,過去和現在的許多“藏銀”佛教用品、工藝品等,其實是由尼泊爾工匠所打造的。而在今天拉薩北部的太陽島商業區,還有眾多來自云南大理的白族銀匠所開設的銀器作坊。他們或他們的祖輩沿著茶馬古道來到西藏,憑借高超的技藝和逐漸建立的良好聲譽,在“藏銀”的制造和銷售中也占據了可觀的市場份額。對于眾多從事民族工藝品和旅游紀念品交易的商販來說,“藏銀”則是他們獲利的重要來源。“藏銀”因而可以是任何一種具有與銀相似外觀、色澤的廉價金屬、合金與其他質材,如錫、鎳、錫鉛合金、白銅、白鐵等,或者甚至是鍍上銀色外觀的樹脂——只要它們能以“藏銀”之名帶來豐厚的經濟收益。
同理,游客和普通消費者也可能在“藏銀”之名下買到各式各樣的物品,只不過,這些物品往往被期待能顯現出“藏銀”所應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比如,它們應該具有銀白色的外觀但不應過于閃亮,最好還要有些黑色印跡,顯得更加古老神秘;它們的表面摸起來不能過分光滑,反映出少數民族古樸的金屬加工技藝;無論器物大小,它們的輪廓線條都應在第一眼就能直觀地體現出藏族獨有的式樣、格調和美感;通常來說,它們可能鑲嵌綠松石、珊瑚、琥珀或水晶等作為裝飾,但不大可能鑲鉆石;并且,其常見的裝飾圖紋符號,如蓮花、金剛杵、六字真言、萬字符等,大多都源自藏傳佛教的基本教義。游客為購買這些“真的”(authentic)或“假的”(fake)“藏銀”器物飾品所付出的價錢,可能有很大差異。這取決于一系列相關因素,包括制造者、購買地點、物品展示場所、購買者自身的知識背景與審美趣味,以及某些受時代語境制約的、與少數民族工藝品及其價值相關的更為深廣的社會文化觀等。不過無論如何,“藏銀”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旅游市場中最為成功的藏族文化商品和文化象征符號之一。
正如前文指出,物質的不純性是深嵌在有關“藏銀”的社會記憶和表述系統中的一個重要標簽。從藏文化的立場來看,“藏銀”不純這一歷史事實和歷史記憶的形成是多重因素交織影響的結果,其中包括歷史上西藏銀金屬物資源的匱乏、西藏制銀傳統的地方性知識和技藝體系、藏族獨特的日常生活經驗、宗教態度和審美需求以及漢藏間政治經濟文化的長時期互動。然而,在當今旅游工業時代,“藏銀”不純所包含的上述多元歷史記憶和文化意涵都逐漸消散了,“不純”被重新加以建構——成為某種促進物的商品化轉換的符碼,成為一種追逐商業利益的觀念工具。
2.2民族質材的“物類”生成
來自康定的澤旺大哥在成都武侯祠橫街開了一家專門從事藏族特色飾品零售批發的小店,類似這樣由藏族人經營的民族、宗教特色工藝品和紀念品商店占到了周邊業態的一半以上。通過分享武侯祠這張國際旅游名片所聚集的龐大游客資源,這條遠近聞名的“藏民街”也在近年來逐步擴展為一個從武侯祠延伸至整個西南民族大學周邊的更具規模的“藏民街區”。在澤旺的店中,各類“藏銀”飾品,包括戒指、項鏈、手鐲、嘎烏盒、護身符、發箍,以及一些小型佛像、油燈盞、茶杯碗筷等,占其產品種類的近70%。除去批發和零售的價格差異、顧客來源的地區差異之外,發生在“藏銀”消費行為過程中的文化互動則更具意義。首先,對于一般漢族和其他非藏族游客來說,他們多選擇如戒指、項鏈、手鐲之類具有藏族特色而又兼顧自身佩戴習慣的日常飾品,較少選擇更為“藏族化”的嘎烏盒、護身符、發箍、佛像等,反映了文化身份邊界意識的潛在尺度。其次,不同于長期來此進貨的藏族或漢族批發商,一般游客在進店挑選商品的過程中幾乎都會詢問質材是否是“銀”,店主澤旺則會解釋說是“藏銀”或者“是我們藏族特色的銀飾”。顧客要么心有疑慮卻不便究根問底,要么欣然接受這個解釋,但都不影響彼此接下來討價還價,進一步完成或放棄交易。“藏民街”所創設的“異文化”情境和民族旅游街區的“前臺”語境,使身為“少數民族”的藏族文化優勢在此得到建立和穩固,也在相當程度上主導了游客的消費預期。澤旺由于其藏族身份擁有了“藏銀”的合法話語解釋權,也在日常生活的微觀情境中通過對游客心理和買賣技巧的靈活把握,設置了一個調控潛在民族文化沖突的安全閥。在此,“藏銀”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已經溢出了“純與不純”或“真與假”的設問,而指向了民族質材的“物類”生成邏輯。
通過將特定族群性與物質性加以拼合,當代“藏銀”制造和消費的社會過程建構出了一種新的物質形態,并同時顯現出了某種“族群”(ethnic)與“非族群”(non-ethnic)、“真實”(authentic)與“非真實”(inauthentic)的內在悖論:作為一種專名,“藏銀”的表述使一般性的金屬物質銀“族群化”(ethnicalization)了,它揭示了西藏銀器制造傳統的某些重要歷史文化特征。在此意義上,按照族群文化的“內部眼光”,“藏銀”體現了物的“真實”價值;而作為旅游消費品市場中的一種泛稱,“藏銀”則在很大程度上被挪用為劣質或偽制品的遮羞布。作為一種商業策略,“藏銀”的說法有助于將其歷史上“不純”的物質特征轉化為追逐利潤的工具。這些劣質偽制品的盛行其道往往容易導致對藏文化的扭曲和誤解,因而既是“非族群”的,也是“非真實”的。
借用Bourdieu所提出的“社會煉金術/社會象征煉金術”(social/sociosymbolic alchemy)這一啟發性概念,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藏銀”的物質神話之所以大獲成功,無疑是商業資本、大眾傳媒乃至學術界等多方力量對圍繞其所展開的歷史敘事和文化想象進行博弈和操弄的結果。“藏銀”的社會煉金術一方面對其作為物的“他者”文化表征進行了強化,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回避了對其物質性構成的追問與對其物質不純性的質疑。因此,人們有必要深入反思“藏銀”概念如何被制造、挪用,進而泛化為當代民族工藝品和旅游紀念品市場上一個點石成金的“魔法語詞”。更重要的,還應該認識到“藏銀”的社會觀念建構過程如何反過來促生了現實中大量“以藏銀之名”的物質實存的出現,也促生了“民族質材”這一全新的物類(material genre)。與此同時,中國多民族國家內部一種新的文化認知模式也隨之被建構起來。
綜上所述,在“藏銀”個案中,“社會煉金術”效用的發揮有賴于兩個基本前提:其一,在“藏銀”之名與其靈活多變的所指之實之間所發生的歷史變遷、脫位、挪移與再建構過程,為今天旅游市場中民族文化價值與商品價值的操弄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其二,它還與多民族國家的“內部他者”想象,以及消費者的自我身份建構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正如旅游人類學家Salazar和Graburn所指出,民族工藝品與旅游紀念品的消費,即意味著通過物來想象不同的人群和地方。這些想象根植于復雜的社會權力關系之中,因而從來都不是純粹中立的實踐行為。
3想象多民族中國:超越“藏銀”的個案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大眾旅游在中國逐漸興起,民族旅游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被認為同時肩負著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體現國家民族團結政策的重要責任。尤其對占中國人口總數逾90%的漢族來說,民族旅游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去到邊遠民族地區,了解不同的少數民族群體以及他們的文化。與此同時,按照澳大利亞學者Moms的理論,各民族工藝品和旅游紀念品的制造和消費,則意味著在國家行政版圖之上建構起了一個“民族形象空間”(national image space),民族國家內部物與族群性的關聯由此得以空間化、直觀化地想象和表達。民族工藝品和旅游紀念品也因而成為承載中國多民族國家想象以及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質載體和媒介。在“藏銀”個案中,濃郁的民族風情與大眾時尚的合流帶給人們新奇的文化體驗,也使無形的“他者性”(otherness)經由物質化/實體化轉換而變得可消費。接下來的問題是,在今天中國的“多民族形象空間”中,有相當多樣化的“他者性”可為消費者提供超越日常生活、充滿異族情調的文化想象,但民族旅游工業卻無法允諾提供均等的機會將各民族文化轉化為利潤豐厚的文化商品。在民族國家內部,想象“他者”與消費“他者”之間的轉換法制和限度,植根于某些歷史的和當下的深層社會文化結構之中。
3.1他者的逆襲:從“帝國想象”到“民族風”
前引互動百科“藏銀”詞條中說:“所以當藏人拿著藏飾品對你真誠地說是真正的銀子時,請別懷疑他們的誠信!”在此,“誠信”的道德評判和以“文化專家”口吻對“藏銀”純度的辯解暗示了,“藏銀”可能是白銅或者其他廉價合金,而不同于漢族所認為的什么是銀,這種現象非常正常,因為藏族是與漢族“不同”的另一群人。漢族也因而應該對少數民族及其工藝品持有一種更為寬容和理解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是對民族間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呼吁,揭示出一種更為隱秘的觀念——與漢族相比,少數民族的文化、技術和經濟都在現代化進程中處于較為落后的發展階段。按照Harrell的觀點,這幾乎就是“中國古老帝國想象”(the old imperial imagination of China)的又一個當代更新版本:在帝國時代,沒有其他任何一種文化能與中原人群的文字文明相媲美,地處邊緣地帶的人群因為不同于中原人群而處于劣勢地位,他們的文化因而也是更低級的。自20世紀早期以降,新版的“高文化”(high culture)則被認為是漢族近現代以來快速發展和現代化的結果,邊緣地帶的人群轉而由于他們處于發展劣勢而被認為擁有不同的文化。“帝國想象”的這種歷史轉型伴隨著中國近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而發生,卻在本質上遵循了幾乎相同的“內部想象”邏輯。
作為物與“他者性”的耦合與再表述過程,“藏銀”的制造與消費在民族國家內部的多元歷史、差異性想象與事實上的非均衡關系中烙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也通過“自我”與“他者”之間文化界限的表達和強化折射出了特定的身份認同。“民族質材”的流行因而不僅在于強調其文化特質的“不同于”(other to)漢族文化,還在于其必然與漢族自身的身份認同形成某種互動交涉的建構性關系。在此意義上,“藏銀”的流行實為當代社會文化領域“民族風”現象的一個縮影。
在過去30年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非均衡發展中,漢族作為“主體”民族始終處在國家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前沿優勢位置。相比于身處“落后”地區的少數民族,漢族的文化身份認同與地方和傳統的根基性聯系恰恰也因此經受了更為劇烈的沖擊,變得更加脆弱。伴隨著民族旅游的發展,“民族風”的興起通過將各種各樣的邊緣族群文化引入大眾消費時尚而大獲成功,成為近年來一股經久不衰的社會風潮。這是一場“他者”的逆襲——古老“帝國想象”中地處邊緣劣勢的“內部他者”成功突入社會文化的主流與旅游消費的前臺。一方面,“民族風”所表征的異質文化和多元文化可成為抵御文化全球化與均質化危機的有效手段,“他者想象”在此發生倒置;另一方面,“民族風”對于漢族消費者和游客來說,亦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參照物,以確證自身作為多民族國家內部唯一“非一少數民族”(non-minority)的身份認同。更準確地說,在“民族風”旅游消費的特定語境中,漢族的身份認同不僅是“被建構的”(constructed),更是“被反射的”(reflected)——與“被識別”的55個“少數民族”相比,“漢族”這一指稱背后所隱含的“不證自明”性,恰恰在物的微觀層面有賴于“藏銀”的“不同于”(other to)。
3.2轉換與限度:在族群性與商品性之間
“藏銀”的商業成功并非僅僅是對燦爛杰出的藏文化的成功表達,它同時揭示出,不同少數民族群體間存在的歷史/文化差異,不僅催生出了“內部他者”想象的不同類型和階序,也在旅游工業語境中被轉換為社會/經濟處境的現實差異。
例如,對大多數漢族游客來說,苗族和傣族比較符合典型的浪漫類型;北方的蒙古族、哈薩克族和南方的佤族,則因其游牧或狩獵的傳統常被視作強壯、勇敢乃至剽悍的典型代表;納西族算是相對神秘古老的類型;而滿族、回族、壯族、土家族等,則由于在生活文化的許多方面大量吸收了漢族的文化和習俗而常常被認為不夠“他者”。相較之下,藏族文化不僅同時在異域情調、浪漫色彩和神秘感等多方面擁有高辨識度,也要比其周邊人口較少的鄰近民族門巴族、珞巴族等顯得更具吸引力——在大部分時候,這些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對普通游客來說似乎是面目模糊、難以區分的,也顯現出某種“無關緊要的他者性”(does-not-matter otherness)。在這樣的文化想象類別和階序結構之中,“藏銀”的流行就并非單純是市場法則的自然結果。
與“藏銀”相關,彝族銀器也是一個可供比較的個案。從技藝、審美和文化內涵來看,彝族的銀器制作傳統完全可以與藏族媲美。銀不僅是彝族人傳統中財富、權勢和美的象征,也是德古調節民間糾紛、畢摩施行宗教儀式的必用之物。技藝高超的彝族銀匠可以手工打制出精美的銀器銀飾,并飾以蕨草、雞冠、羊角、云紋、日月星辰等民族傳統紋樣圖案。在大涼山腹地的布拖、昭覺等地區,彝族女性在火把節慶典上佩戴的整套傳統銀飾可重達20多千克,其尺寸和精美程度都令人嘆為觀止。然而與藏族不同的是,彝族人似乎只喜歡純銀,傳統上也很少接受銀合金作為純銀的替代品。在聞名涼山的“銀飾之鄉”吉拉布拖的傳統銀器作坊中,銀匠們至今仍采用將銀飾投入碳火中燒后再用明礬水刷洗以達到拋光效果的土辦法。“真銀不怕火煉”,是彝族工匠和老百姓驗證銀飾純度的手段,也帶有超越實用維度的儀式意味。這種崇尚純銀的觀念部分源自彝族古老的泛靈論信仰以及彝族對稱作“瑟瑟”的銀精靈的敬畏。
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彝族銀器制造在近現代的發展與自晚清以來漢地和彝族土司轄地之間的鴉片和銀錠銀幣交易有著深厚淵源。事實上在整個民國時期,涼山彝族地區一直是全中國最大的鴉片種植基地,通過彝族地區鴉片的輸出,銀錠源源不斷地流入彝區。因而與“藏銀”相似,彝族銀器制作傳統也根植于“漢/番”之間的文化、政治、經濟互動地帶(interaction zone)。但不同的是,今天并沒有出現一種與“藏銀”類似的民族質材概念,“彝銀”。如果說“藏銀”以族群之名成功地繞開了對其究竟為何種物質的追問,那么彝族傳統以來對銀物質純度的強調,則阻礙了當代旅游工業對族群性與物質性之間的含混關系進行操控的可能。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彝族銀器為何難以在旅游紀念品市場上取得“藏銀”那樣的商業成功。
在今天中國的民族旅游市場上,西藏已成為最炙手可熱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而彝族地區的旅游開發,尤其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聚集區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則相對較為落后。因此,盡管彝族工匠制作的銀器和銀飾同樣體現了鮮明的“他者”文化特征、高超的技藝,也有著高純度的好口碑,但其制造和消費仍然主要局限于彝族地區,并且常常被游客和外來者認為是土氣的、不夠時髦的。在“民族風情”與“土氣”的微妙分野之間,“藏銀”和彝族銀器折射出了兩個民族在當代旅游工業中的結構性位置差異。
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族群想象和消費也可能突破多民族國家內部固有的關系結構,受到內外部復雜因素的影響。
盡管西藏社會和彝族社會都長期背負著“農奴/奴隸制社會”的歷史負擔,但今天圍繞藏地和彝區所展開的旅游想象卻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當彝族文化的“他者性”在很大程度上仍與某種社會、文化、經濟的落后狀況相聯系時,“想象西藏”不僅擺脫了“落后”的沉重歷史負擔,更建構起一種超越庸常社會生活之上的“旅游烏托邦”。在改革開放以來更為寬松的宗教政策環境下,過去30年間藏傳佛教在全國各地的影響不斷擴大,這似乎給“想象西藏”又增加了一層道德凈化的面紗。通過“雪域藏地”“圣潔高原”“藏地密碼”“最后一片凈土”等家喻戶曉的社會修辭術,“想象西藏”從民族國家內部“少數民族自治區域”的現實位置上實現了某種超越,締造了一個大眾流行的人文地理學神話。相應地,“藏銀”工藝品和紀念品上最為常見和流行的式樣圖案,如蓮花、雍仲萬字、金剛杵、六字真言等,似乎提供了一種精神力量,使消費者能從現代社會的物欲和道德失落中得到拯救;也同時提供了一種物質觸發機制,使平庸的日常生活升華至超越性的神圣信仰之域。這種充滿道德凈化意味的文化想象反過來也使那些“以藏銀之名”的器物變得更受歡迎。
與此同時,西藏不僅是中國的,也是當代國際社會最重要的人文地理學神話之一,它同時被認為是文化的、宗教的和生態的“最后一片凈土”。基于近現代西方社會對“香格里拉”的神秘想象和眾多現實的復雜國際政治因素影響,藏族或許算得上是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對西方社會最具吸引力、知譽度最高的一個民族。藏式風格廣受西方人士歡迎,西藏的難以企及甚至大大強化了其神秘感和吸引力。對他們而言,“藏銀”器物和飾品的消費,即是對難以企及的雪域藏地進行的一種“間接旅行”(indirect tourism)。以加州大學所在的伯克利小鎮為例,在當地的藏飾商店和周末街頭集市上,常可見各種稱為“Tibetan Silver”的物品。它們不單是西方社會想象西藏、消費西藏的物質象征,也成為伯克利這個美國西海岸民運重鎮崇尚文化政治多元主義和世界主義的一個微觀標識。受益于較高的國際知名度和普遍正面化的道德形象(generalized positive moral image),藏文化在國際社會占據了一種較具文化優勢的位置。通過消費“藏銀”工藝品和紀念品,漢族游客也由此產生一種緊跟世界潮流的感覺。這也是推動“藏銀”成為大眾消費風尚的另一個影響因素。
綜上所述,在民族旅游語境下,“族群性”向“商品性”轉換的可能和限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主體民族的自我認知與不同類型的少數民族他者想象之間,是否存在足夠的文化闡釋和商業操控空間。“藏銀”的商業成功揭示了中國多民族國家“內部他者”想象的非均衡結構,也是內外部多重權力關系博弈協商的結果。
3.3多元一體:民族旅游的消費體驗與實踐反思
在西南中國,除藏族與彝族以外,還有苗族、傣族、侗族、羌族、景頗族等眾多少數民族在跨族群互動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制銀傳統,因而社會上也流傳著“苗銀”“傣銀”“羌銀”等相關說法。當“藏銀”由于其宗教象征價值而廣受歡迎時;“苗銀”則被認為極具浪漫、繁復和夸飾的美感;“傣銀”,由于傣族工匠從前有以草藥水對銀器進行特殊處理的傳統而據稱具有某種療治功效;至于“羌銀”,則在最近幾年才開始作為羌族的旅游紀念品受到外界關注,對“羌銀”的扶持和發展,則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羌族聚居區域地方文化經濟重建工程的組成部分。無論“藏銀”,還是“苗銀”“傣銀”“羌銀”,都遵循了相同的命名策略,通過將某一民族之名——藏、苗、傣、羌,置于金屬“銀”之前,從而賦予物質以特定族群性,或者說使特定族群性得以物質化、具象化,以此來謀取商業利益。而至于這些被冠以特定民族指稱的物質是否是純銀、銀合金或者其他質材的問題,也往往或被懸置,或被回避,或被默許。
不可否認,在民族旅游語境中,這些“民族質材”的商品化過程仍然有助于表達多元的文化傳統和身份認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強化這一表達。因而,無論是“藏銀”,還是“苗銀”“傣銀”“羌銀”,作為大眾消費領域的“亞文化符號”(subculture sign),對引導大眾理解和體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國家主導意識形態話語,都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不過,也正是在這些“亞文化符號”被吸納入主流的文化整編(cultural incorporation)過程中,商業化過程與族群文化想象的內在矛盾,將可能導致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解出現某些偏誤。
1989年,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論述,希望“多元一體”的觀念能打破“漢/非漢”以及“漢族/少數民族”的二元話語桎梏,增進各民族間的理解和認同。在多元民族構成的基礎上強調文化統一的“中華民族”觀念有利于國家認同的凝聚,因此這一重要論述迅速在學術界、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發揮了巨大的影響。緊隨“多元一體”的國家意識形態頂層設計,在社會實踐的中觀層面,眾多便利而通俗的大眾話語被制造出來——比如,瑯瑯上口的“多彩民族大花園”“民族大家庭”“56個星座,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等等,以幫助全體社會成員知曉并理解多民族國家的“結構性修辭形式”(structural rhetoric form)。與此相應,在個體實踐的微觀層面,通過民族旅游的大眾參與以及民族旅游紀念品的大眾消費,一種典型的文化類比模式被廣泛地建立起來。這一文化類比模式有效地將國家政治話語和社會集體敘事加以整合,并融入游客的個體消費經驗之中,從而使“多元一體”的抽象觀念最終落實到切實的身體維度。
“藏銀”的命名,揭示了旅游工業語境中物質性與族群性相耦合的文化邏輯;“藏銀”“苗銀”“傣銀”“羌銀”等新生“物類”及其對應社會實存的制造與消費,則揭示出民族國家的基本族群觀念對旅游工業的滲透和形塑。在遺產時代,無獨有偶,漢族游客不僅可以購買“物質性”的“藏銀”“苗銀”“傣銀”“羌銀”;以及“彝繡”“苗繡”“侗繡”“羌繡”;也可以欣賞到“非物質”的“藏族鍋莊”“羌族鍋莊”“彝族鍋莊”“傈僳鍋莊”“普米鍋莊”等。這種便捷而高效的文化類比模式隱含了消費“他者”的3個基本步驟:(1)對不同民族文化的消費、比較和想象;(2)按照漢文化傳統在不同民族文化間尋找相似性,建構類比想象并加以歸類;(3)在漢語表述系統中建構起新的物類并進行再命名。上述3步模式揭示了民族旅游推動族群文化想象的基本法則——既將其想象為“他者”,也想象為游客“自我”的某種鏡像版本。
通過消費這些共享一套文化表述邏輯的“民族質材”,如“藏銀”“苗銀”“傣銀”“羌銀”,各個民族獨特深厚的“物的傳統”可能被收編人一個整飭的“物的系統”之中,成為想象“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實存對應物。民族旅游的社會實踐也在強化少數民族“他者性”的同時,成為了某種創造中華民族“文化同一性”——即“超越并包容地方性和漢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同一性”的過程。盡管這反映了特定區域內多民族互動交往、文化交融的歷史事實,但在此過程中,文化多樣性也可能遭遇喪失獨立價值的風險,從而被降格為編綴民族國家共同體想象宏偉圖景的“文化馬賽克”(cultural mosaics)。如此一來,在本文的個案中,“藏銀”將理所當然地被視作“中華民族”制銀傳統中那些技術、水平、品質較低的分支之一;其“不純”的物質屬性也將難以被理解為藏族制銀傳統的獨特性,傳達出藏族關于銀的故事、記憶與生命體驗。
結束語
透過歷史與人類學的雙重視域,“藏銀”個案所指涉的多民族國家認同議題同時在“物”與“物的觀念建構”,以及“物的社會實踐”等多個層次上得以揭示。作為大眾旅游時代一個充滿悖論的象征之物,“藏銀”既是制造族群想象的機制,亦是這一機制的產物,在多元話語操弄之下,它更成為一種靈活的工具來滿足不同社會角色的多元訴求。以“藏銀”之名,所有圍繞其展開的敘事、建構、制造和消費,都融入一個跨族群互動的社會歷史進程之中——最終,無論是少數民族學習如何成為“少數民族”,還是漢族如何被建構為“非少數”的主體民族,都在物的族群化和商品化過程中熔鑄為切身經驗的社會事實。
透過民族旅游這一實踐和分析界面,物可以映射出一個共同體關于文化、價值、美與傳統的某些核心觀念與特質,也映射出“物質性”“族群性”與“商品性”之間不斷地發生的重疊、交錯與轉換。這些映射與轉換總是內嵌于近現代民族國家的多族群關系脈絡之中,因而既非直接,亦非透明,應當成為旅游人類學“物”的研究領域中一個值得進一步關注的焦點問題。
[責任編輯:吳巧紅;責任校對:王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