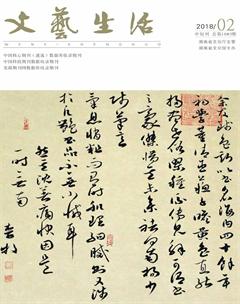影像敘事中的男性身份認同解析
周靜媛
摘要:身份認同是一個古老的哲學課題,在眾多影視作品中也對人物身份認同展開探討。《烈日灼心》是一部于2015年上映的文藝警匪片,片中對男性角色背后復雜的身份體驗塑造得淋漓盡致。本文通過這部影片中各男性角色進行角色研究和身份詮釋,試圖分析影像敘事中的身份認同所建構的意義。
關鍵詞:烈日灼心;身份認同;角色研究
一、前言
身份認同包括性別、種族、階層、群體等諸多方面。隨著現代哲學的發展,尤其是各種后現代哲學思潮的不斷推進,身份認同由確立主體、中心、本質的哲學研究走向了去中心、反本質、消解整體性的文化研究。在當代影視作品中也同樣強調主體的多元性和異質性,在影視作品中主體身份是被建構的,而非刻板而單一的。這與在充滿不確定性和極度碎片化的現代社會中,人們對身份認同所呈現出的失落與焦慮有著密切的關系。以曹保平導演的《烈日灼心》為例,該片模糊了一貫的價值導向和身份認同,充滿善與惡的對壘、情與法的沖突。正如卡斯特所言:“認同所建立的是意義,而角色所建立的是功能。”本文通過對三個男主角進行角色研究,試圖分析其身份認同所建構的意義。
二、三位男主的個體身份認同
(一)殺人犯和警察的雙重身份:辛小豐
在傳統敘事中,女性通常作為被凝視的對象,被男性所控制和操縱;男性則通常占據著權力中心,是欲望的象征。這一性別身份認同在本案件的開端中充分體現:辛小豐在面對年輕女畫家的裸體時,抑制不住內心的潛意識沖動,從而作出強暴的行徑,導致女畫家心臟病突發猝死。作為整個故事的始作俑者,他充分暴露了男性欲望的膨脹以及凌駕于女性之上的權力。然而在女畫家猝死后,她的家人正好上樓撞見此景,一陣慌亂之中,辛小豐一行人將其全家殘忍殺害。從逃亡的那一刻起,他便成了一個失去自我、沒有權力的“去主體化”的人。辛小豐作為逃犯的精神不自由以及自身身份的缺失,最明顯表現在他為了掩蓋自己強奸殺人的嫌疑,不得不隱瞞自己真實的性取向,并強迫自己與同性發生性行為。這樣抑制天性的強迫性行為給本來就己水深火熱的逃亡生活增添了更多壓抑的情緒,刻畫出角色的飽滿性和復雜性。
七年后,他為自己穿上了一個正義的馬甲,搖身一變成了一名協警。這一正義的形象和他罪惡的本身融于一體,這種雙重身份的對立又極具諷刺的意味。這也可以說是辛小豐自我麻痹的盔甲。他在執行任務時充當正義的化身,企圖通過做好事來掩蓋自己曾經卑劣的行徑,善與惡的邊界逐漸模糊。就現實認同而言,協警的設定體現出創作者試圖借助身份符號,對現實存在的一種隱喻性的表達。在現實社會中,協警身份的社會認同也是模糊不清、難以定位的。
最后,在接近尾聲的天臺戲中,追擊犯人時伊谷春不小心失足踩空險些跌下高樓,在千鈞一發之時辛小豐及時拉住他的手。這一危急時刻從設計上是給時辛小豐重新選擇善與惡的機會。如果他此時放手,來自殺人犯的威脅就會隨著伊谷春的墜樓永遠成為一個謎。然后辛小豐最后還是選擇將伊谷春救回。觀眾本來已在動搖的側隱之心在此徹底傾泄,轉而更多地認同他作為好人的一面。可最終伊谷春在被他救回后將他緝拿歸案并執行死刑。他的身份再次回到故事一開始的殺人犯身份。經過故事的輾轉,雖同樣是殺人犯的身份,觀眾前后對他的態度和認同卻已截然不同。
(二)理性狀態的典型代表:楊自道
同樣是逃犯,相比于辛小豐的怯懦和感性,楊自道則是始終處于理性狀態的典型代表。片子巧妙的安排了兩場阿道與劫匪對峙的戲,第一場是在夜里開出租的時被劫匪要挾的同時撞上正在執勤的伊谷春。這是一場純粹的內心抗爭,當殺人犯遇到劫匪,在生命和錢財遇到威脅時,他理智地抑制住潛意識里的自我反抗沖動,低調地偽裝成一個老實人,展現了他作為殺人犯的小心翼翼。第二場劫匪戲發生在喧囂的白日里,這一場他充當了見義勇為的英雄。在目睹當街搶劫后,善良的本能沖動和贖罪的心理作祟下,他毫不猶豫地開車追向持刀歹徒。那一刻他作為正義的形象,開始洗白觀眾對他逃犯身份的認同。直到與歹徒赤膊相拼,最終身負數刀、鮮血流淌,他才從自我營造的好人夢中恍然醒悟,跌到逃犯的現實中,開始正視自己逃犯的身份,于是開車決然離去,深受重傷卻不敢去醫院,只能回到自己的小黑屋,強忍著極度疼痛,用白酒消毒、棉線縫針,乃至暈厥在床上。他寧可受骨肉之苦,也不肯去醫院拋頭露面,這行為正是常人所不能及的理性境界。
在兩性意識上,他和伊谷春的妹妹小夏之間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關系。這個不平等一方面來自陣營上的對立,小夏是警長的親妹妹,所以他內心對小夏是懼怕的;另一方面則來自他在這段關系中的自我身份缺失,殺人犯的身份讓他不敢在愛情面前做自己,想要靠近卻又止步不前。當小夏赤裸上身站在阿道面前時,瞬間喚醒了阿道最真我的雄性荷爾蒙意識。在喜歡的女人面前,他拋開了一貫的理性作風,輕率地將自己小心翼翼保護了七年的命交給小夏賭一把。當釋放了真我狀態后的他反而回到了最輕松的狀態。
(三)情與法的交融:伊谷春
伊谷春作為一個偵查能力極強,并具有豐富辦案經驗的警長,他在本片中起到了法律的化身這一功能性作用。在與辛小豐的接觸中,伊谷春憑著警覺的專業嗅覺,發現了辛小豐三兄弟與滅門命案之間的貓膩,于是他開始暗自偵查。可隨著在執行公務的過程中,他與辛小豐并肩作戰滋生兄弟情,并動惻隱之心,于是他開始游走在情與法的邊界。當小豐為了給尾巴籌看病的巨額藥費而私吞兩千多收繳的賭資時,論法本應嚴懲,可伊警官卻沒有追究。后來他懷疑辛小豐為了籌藥費賭球的時候,競主動拿出自己的存款。這時他心中自我認同開始從一個嚴謹公正的警察轉化成一個排憂解難的朋友。雖然他內心不想承認,但在證據完全暴露之后,他不得不接受小豐就是殺人兇手的事實,鐵證再次讓他明確自己警察的身份。
他與辛小豐問的博弈關系,是不斷伴隨著彼此間的身份認同而展開和推進的。并且其身份認同的構建,是建立對立認同基礎之上的角色關系。警察與罪犯這種彼此身份的存在關系,已先在地決定了兩人之間必然呈現為一種內在博弈的關系。然而,作為警察系統中的同事,在面對相同的外在矛盾時,他們彼此間卻形成了利益關系的一致性。事實上,辛小豐每次協同伊警官出警,彼此間都在不斷推進和加深著這種認同關系的同時,卻又在各自內心深處更加防范與質疑。基于這樣一種認同機制所構建起的人物關系,毋庸置疑具有極大的戲劇性張力,將沖突內化為一種心理博弈,既表現為各自內心與自我的博弈,又表現為彼此間的博弈與認同關系。
二、兄弟三人的群體認同
辛小豐兄弟三人在群體認同上有兩個身份,一是殺人犯,二是尾巴的爸爸。一方面,作為犯下滔天罪行的殺人犯,長期的逃亡生涯使辛小豐三人逐漸迷失了自我,喪失了主體性。他們不得不將真實的社會身份隱藏起來,他們失去了與人正常交際的機會,缺乏家庭的關懷和社會的溫暖,在逃避和自責中惶惶度日。
另一方面,三人為了贖罪收養了受害者家的女嬰,取名叫尾巴。之后三人與尾巴建立了親密的關系,尾巴的健康成長也成為支撐三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們將所有的愛都傾注在她身上,這時父愛在他們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觀眾在影片最后得知阿道和辛小豐他們其實并不是殺人犯,殺人的是案發當天同行的大哥。他們寧愿選擇死亡也不愿意說出真相,為的是換取尾巴沒有心理負擔地快樂成長。這個行為徹底扭轉了三人的道德形象,從殺人逃犯到父愛無邊的爸爸,三人被放置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成為觀眾敬佩的對象。
那到底辛小豐三人是善還是惡?善與惡的評定標準是什么?界限又在哪里?影片中伊谷春的一段臺詞似乎可以看作是對這一問題的答案。當他知道辛小豐私藏了收繳的賭資時說“人是神性和動物性的總合。”這段話在某種程度上正契合了本片的主題,即善與惡并非單純的二元對立,或者是能夠以清晰明了的界定一言概之的東西,這種黑白之間的模糊地帶正是人區別與動物的特性。而影像敘事中的身份認同也是同理,在復雜的社會環境和人物背景下,并沒有絕對單一和固定的身份,觀眾對人物身份的認同是在敘事的發展中不斷推進和演化,直至界限模糊、異質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