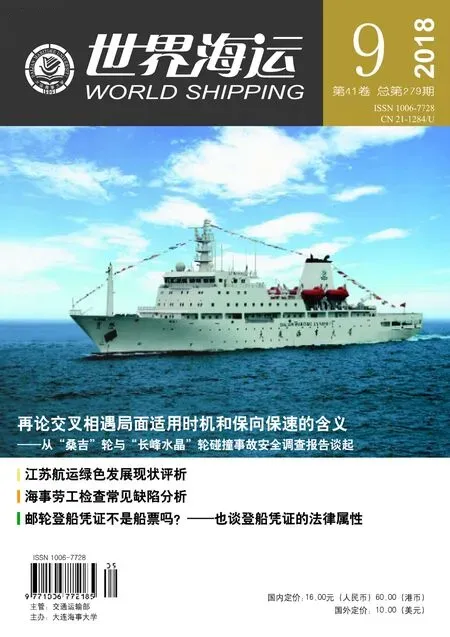郵輪登船憑證不是船票嗎?
——也談登船憑證的法律屬性
孫思琪 金怡雯
上海自2017年12月開始試點郵輪船票制度,其中明確規定統一使用上海港郵輪登船憑證。①參見上海市交通委員會、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關于上海試點郵輪船票制度的通知》(滬交航〔2017〕1464號)。登船憑證作為郵輪船票的法律屬性本應無可置疑,但近來漸有不同觀點興起,主張登船憑證不是船票。2018年3月,筆者拙文《中國郵輪船票制度:缺失、進展與方向》投稿旅游領域某權威刊物,②該文后在文化和旅游部直屬研究機構中國旅游研究院主辦的2018年中國旅游科學年會獲得三等獎。匿名外審專家給出的審稿意見認為登船憑證在旅行社包船模式下不是船票;上海國際郵輪旅游服務中心有限公司的微信公眾號“上海郵輪中心”于2018年5月11日推送的《郵輪登船憑證的法律屬性》一文,也在開篇便明確提出:“登船憑證不是船票,雖然兩者看起來非常相似。”[1]
此種觀點原本并不值得過多關注,相關論述不僅未能給出登船憑證不是船票的可靠依據,而且否定登船憑證的船票屬性似乎也并無多少理論抑或實踐意義。但是,考慮到官方媒體同樣輸出此種觀點,③上海國際郵輪旅游服務中心是在政府指導下以服務郵輪游客、服務郵輪企業、服務郵輪經濟發展為宗旨的企業,也是郵輪行業官方信息的發布平臺。加之登船憑證是否構成船票,直接關乎上海試點船票制度克服船票隱形化的努力是否行之有效,進而影響郵輪旅游法律關系能否得以厘清,使得對于登船憑證的法律屬性又有澄清的必要。
一、什么是登船憑證?
登船憑證是上海試點郵輪船票制度確立的證明文件,旅客進港、登船均須持有登船憑證。主張登船憑證不是船票的觀點認為:登船憑證是上海首創,[2]作為實踐創新的產物尚無法律定義。[1]然而,“上海港郵輪登船憑證”的英文名稱是“Shanghai Cruise Setsail Pass”,而Setsail Pass顯然不是上海的首創。皇家加勒比國際游輪作為上海郵輪船票制度最早的試點單位,不僅在本次試點以前就在我國市場針對快速登船的情形使用Setsail Pass,而且長期以來在國外各個地區的市場也均有使用。“上海港郵輪登船憑證”的記載事項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船票類型,主要分為個人、團隊兩類。
第二,船票認證碼。
第三,航線信息,包括承運人/船名、航班號、起航日期、始發港、航線。
第四,旅客信息,包括姓名、國籍、旅行證件號、身份證號、聯系方式。
第五,艙位信息,包括預定編號、船艙樓層、房間編號、逃生集合區。
第六,明示信息,包括:(1)登船憑證是您進港的必要憑證。前往碼頭時,請務必攜帶登船憑證、通關便捷條形碼、旅行證件及登船所需其他必要文件。(2)持有本憑證進入碼頭,表明您已經仔細閱讀××××郵輪公司乘客條款與細則,并同意其規定的所有條款及其約定的雙方的所有權利和義務。(××××郵輪有限公司乘客條款與細則可以通過https://www.××××.com查閱)(3)請確認登船憑證個人信息與您旅行證件信息保持一致,否則可能會導致延誤或被拒絕登船。(4)口岸截關后所有旅客將不允許登船,請在截關前30分鐘抵達碼頭并辦理完登船手續。
考察否定登船憑證是船票的理由,大致可以總結為四項:一是登船憑證不符合船票的定義;二是登船憑證不具備船票的全部功能;三是登船憑證與船票的簽發主體不同;四是包船模式下登船憑證不宜認定為船票。以下逐一進行分析。
二、登船憑證不符合船票的定義嗎?
主張登船憑證不是船票的觀點認為:船票有法律定義,登船憑證并不完全符合該定義。[1]據此必須考察何謂船票的法律定義。至少在狹義的法律層面,船票在我國并無明確定義。《海商法》第110條規定:“旅客客票是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成立的憑證。”《合同法》第293條規定:“客運合同自承運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者另有交易習慣的除外。”上述法律規定的對象都是客票,也即旅客乘坐火車、飛機、船舶等的票證。[3]船票則是其中一種具體類型,專指水路運輸情形下的客票。而且,《海商法》第110條、《合同法》第293條實質上都是關于客票功能的規定,而不是針對客票本身的定義性規定,也即并未揭示客票是什么,只是規定了客票有什么用。個中原因恐怕正是因為客票本身并非需要專門定義的復雜文件。至于廣義法律的層面,《水路旅客運輸規則》第6條亦有類似規定:“旅客運輸合同成立的憑證為船票,合同雙方當事人——旅客和承運人買、賣船票后合同即成立。”《水路旅客運輸實名制管理規定》第2條第2款則規定:“本規定所稱船票,是指水路旅客運輸中旅客乘船的憑證,包括紙質船票、水路電子船票以及其他符合規定的乘船憑證。”
上述規定共同指向一點:船票是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憑證。除此以外并無關于船票內涵的其他規定。據此考察登船憑證,登船憑證具有證明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功能應無爭議,即使主張登船憑證不是船票的觀點對此也并不否認。例如,上海郵輪中心認為:“登船憑證可證明在旅(游)客與郵輪公司之間存在合同法律關系。”[2]如果認為上述規定就是船票的法律定義,登船憑證也完全符合船票的定義。上海郵輪中心主張船票在實務中的定義①筆者并不贊成船票的定義存在理論與實務之分。同一概念在不同學科之下可能存在不同定義,但互相之間應當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例如,《合同法》第237條是融資租賃合同在法律上的定義,《企業會計準則第21號——租賃》第5條則是會計準則關于融資租賃的定義。而且,所謂的實務只是對應學科的實踐而已,郵輪旅游涉及的旅游學、法學各有其實踐。除非理論定義存在明顯錯誤,否則對應的實踐不應另有定義。是:“郵輪船票是海上、水路旅客運輸合同的紙質或電子證明,由承運人簽發并交付旅客,旅客需憑票上船、乘船,票上應載有承運人名稱、船舶名稱、航次信息、上下船時間地點、艙室等級、船上服務、票價以及旅客身份信息等內容。”[4]“上海港郵輪登船憑證”的記載事項除票價外完全符合該定義。由于包船模式下船票是包價郵輪旅游產品的組成部分,旅行社在向旅客銷售產品時不會針對船票專門定價,因而要求船票載明票價既無必要,也不可行。因此,登船憑證不符合船票法律定義的說法不能成立。
三、登船憑證不具備船票的全部功能嗎?
否定登船憑證是船票的觀點認為:登船憑證不具有船票的全部法律屬性,僅履行船票的兩項功能,一是合同證明功能,二是上船權憑證功能。[2]由此必須澄清船票在法律意義上究竟具有何種功能。
上文提及的法律規定已經明確:船票的法律功能僅有一項,即作為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憑證,此外再無其他功能。至于所謂的“上船權功能”,上海郵輪中心認為是指:“登船憑證可顯示旅(游)客有上船、并享受船上服務的權力。”①其中“權力”應為“權利”。[2]但是,旅客享有登船的權利應是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應有之義,提供符合合同約定的船上服務也是承運人理所當然的合同義務。船票既然可以證明海上旅客運輸合同,能夠證明旅客基于合同享有的權利自不待言。無論是“上船權功能”或者其他類似功能,實非船票的獨立功能,而是合同憑證功能的具體體現。因此,既然船票和登船憑證具備的唯一功能完全一致,登船憑證不具備船票全部功能的說法不能成立。
四、船票和登船憑證的簽發主體不同嗎?
主張登船憑證不是船票的觀點認為:郵輪船票的簽發人是承運人,而登船憑證的簽發人是郵輪公司。[5]《關于上海試點郵輪船票制度的通知》確實規定:“各郵輪公司嚴格按照‘上海港郵輪登船憑證’樣張(附件1)規定的版式和內容向郵輪旅客出具紙質或電子登船憑證。”但是,郵輪公司并非法律概念,因而必須找到郵輪公司在郵輪旅游中對應的法律地位。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至少從我國當前的郵輪旅游市場來看,郵輪所有人出租郵輪的情況并不多見。郵輪運輸畢竟有別于貨物運輸,經營者購置郵輪的主要目的仍是為了直接經營郵輪旅游。上海試點郵輪船票制度也是基于上海郵輪旅游市場的現實情況進行制度設計。認為郵輪出租導致郵輪公司不再是承運人,更多只是基于理論可能性作出的假設。租船情況下運輸合同的承運人識別紛繁復雜,不可一概而論。不能刻板地認為“郵輪公司”就是指郵輪所有人,從而認為郵輪公司在租船情況下降格為實際承運人。[5]如果實際經營郵輪的已是承租人,負有簽發登船憑證義務的郵輪公司難道還是指出租人嗎?人們通常所稱的郵輪公司,顯然是指整體經營郵輪船上服務的公司,即與旅客訂立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當事人,也即承運人。至少從“上海港郵輪登船憑證”的記載事項來看,登船憑證載明的經營者也是“承運人”而非“郵輪公司”。因此,船票和登船憑證的簽發主體總體而言均是承運人,主張二者簽發人不同的說法不能成立。
五、包船模式影響登船憑證的法律屬性嗎?
否定登船憑證是船票的觀點大多認為登船憑證在包船模式和直銷模式下的法律屬性存在區別。上海郵輪中心認為:“如旅(游)客直接與郵輪公司訂立郵輪旅游合同,郵輪公司將向旅(游)客簽發船票并出具登船憑證,此時兩者功能重合。但若旅(游)客與旅行社訂立郵輪旅游合同,則郵輪公司向旅(游)客出具的登船憑證將充分發揮其功能。”[1]前文提及的旅游領域某權威刊物提供的匿名外審意見也認為:“此時不再是郵輪公司與旅游者之間的單純的海上旅客運輸合同關系,不能適用海商法,而應適用專門調整包價旅游關系的旅游法……郵輪公司既是海商法下的承運人,又是旅游法下的履行輔助人,這兩種身份只能是二選一,不得兼具。直接說,要么有船票,適用海商法;要么有不具船票性質的登船證,適用旅游法。”上述觀點實難駁斥,因為在現行法律之下無法找到任何可供支持的依據,更多只是論者的主觀臆斷。同時也表明目前我國郵輪法律的研究尚不深入,甚至未能掌握基本的法律思維與分析方法,尤其對于包船模式下郵輪旅游的法律關系及其合同基礎存在明顯誤解。
所謂包船模式,也即旅行社包銷郵輪船票,是指旅行社在郵輪船票開始銷售之前即與郵輪公司議定艙位訂購價格,通過預付一定款項訂購郵輪公司提供的全部或部分郵輪艙位。旅行社在訂購艙位后將會根據市場需求以及自身資源設計郵輪旅游產品并進行定價,郵輪船票通常與旅行社提供的岸上觀光等旅行項目以及簽證、領隊等服務打包銷售,旅行社的利潤來源主要是采購郵輪船票與銷售郵輪包價旅游產品之間的差價,[6]以及岸上觀光環節的返傭,而非委托代理關系下的傭金。包船模式下郵輪旅游主要涉及旅客、郵輪公司、旅行社三方之間的法律關系,相應的基礎合同分別是旅客與郵輪公司之間通過船票證明的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旅客與旅行社之間直接簽訂的郵輪旅游服務合同,以及旅行社與郵輪公司之間的郵輪船票銷售合同。①關于郵輪旅游的三方法律關系,詳見孫思琪、戎逸:《郵輪旅游法律關系的立法范式與理論辨正》,《中國海商法研究》2017年第3期,第85-96頁。此種模式已經基本得到郵輪旅游實踐以及相應司法實踐的認可,②旅客與旅行社之間存在郵輪服務合同關系,實踐中并爭議;上海試點郵輪船票制度規定船票作為旅客與郵輪公司之間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證明,旅客與郵輪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也得以確定。至于司法實踐的態度,上海海事法院(2017)滬72民初136號民事判決書認定郵輪公司在郵輪旅游服務合同下是履行輔助人;上海海事法院(2016)滬72民初2336號民事判決書也認可旅客與郵輪公司之間存在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關系。上述兩起糾紛涉及的郵輪旅游均為旅行社包船。理論研究對此不宜再有爭議。
郵輪旅游服務合同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是兩個有所關聯但又相對獨立的合同,郵輪公司為何不能在兩種法律關系下分別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③關于郵輪公司的法律地位,詳見孫思琪、金怡雯:《郵輪旅游郵輪公司法律地位之認定》,《世界海運》2018年第4期,第49-54頁。基于不同合同產生不同的法律關系,郵輪公司在郵輪旅游合同下作為履行輔助人的同時,仍然可以并行不悖地依據郵輪船票與旅游者形成相應的法律關系。[7]郵輪公司的海運承運人身份和旅游履行輔助人身份究竟有何沖突,論者未能釋明,實際也并不存在。而且,是否旅行社包船并不必然影響郵輪旅游的包價旅游性質。假設未來允許外商投資郵輪公司經營我國內地居民的出境旅游業務,郵輪公司據此可以直銷船票,但由于郵輪公司同時提供交通以及船上住宿、餐飲等兩項以上的旅游服務,還有可能涉及岸上觀光環節的旅游服務,仍然符合《旅游法》第111條第3項關于包價旅游的定義。④《旅游法》第111條第3項規定:“包價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預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過履行輔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飲、游覽、導游或者領隊等兩項以上旅游服務,旅游者以總價支付旅游費用的合同。”此時郵輪公司提供的海上旅客運輸服務難道也不能適用海事法律?因此,包船模式并不影響旅客與郵輪公司之間存在海上旅客運輸關系,郵輪船票的銷售模式對于登船憑證的法律屬性未有明顯影響。主張包船模式下登船憑證不是船票的說法不能成立。
六、郵輪登船憑證與航空運輸類似憑證的比較
論及郵輪登船憑證的屬性認定,時常關聯的另一問題便是航空運輸中類似憑證的法律屬性,對此加以比較確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目前我國國內航空運輸中旅客持有的紙質憑證主要包括兩項,一是登機牌,二是航空運輸電子客票行程單;而于國際航空運輸的場合,后者則被“國際航空旅客運輸專用發票”取代。
基于航空運輸客票電子化的基本趨勢,1999年《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也即《蒙特利爾公約》第3條“旅客和行李”第2款規定:“任何保存第一款內容的其他方法都可以用來代替出具該款中所指的運輸憑證。采用此種其他方法的,承運人應當提出向旅客出具一份以此種方法保存的內容的書面陳述。”反映在運輸實踐中,旅客在訂票后承運人的電子訂座系統中將會生成相應的訂座記錄,該電子訂座記錄便是上述規定所指的“其他方法”。旅客據此可以直接在機場乘機,而不必持有紙質機票。[8]國內電子客票在成功出票的同時,將會生成“航空運輸電子客票行程單”,國際運輸則是“國際航空旅客運輸專用發票”,可以作為法定的機票報銷憑證,但不作為通過機場安檢以及登機的憑證,這一部分功能則由“登機牌”承擔。[9]質言之,傳統紙質機票的登機憑證、報銷憑證兩項功能在電子化趨勢下被拆分為“登機牌”和“航空運輸電子客票行程單”或“國際航空旅客運輸專用發票”兩個部分,其中任何一種單獨而言都不等同于航空客票。
郵輪旅游運輸畢竟有別于航空運輸。航空運輸主要是公共運輸,而郵輪旅游運輸不然。而且,旅客與航空公司之間存在航空運輸合同鮮有爭議,因而機票的具體形式并不非常重要,但旅客與郵輪公司之間的運輸關系卻由于船票的隱形化而陷入模糊狀態。因此,上海試點的相應制度明確定名為“船票制度”,目的正在于促使船票能夠“顯形”。
K、結語
基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結論:登船憑證符合郵輪船票的法律定義,具備船票作為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憑證的全部功能。登船憑證和船票的簽發人均為承運人,即使在包船模式下登船憑證也具有船票的屬性。因此,登船憑證的法律屬性就是郵輪船票。
認定法律文件的性質不應拘泥于文件的名稱,文件實際體現的權利義務關系更為重要。上海試點郵輪船票制度采用登船憑證,規定旅客必須憑票進港、憑票登船。如果登船憑證不是船票,又何來“憑票”一說?如果登船憑證不是船票,那么船票何在?通過何種形式體現?而且,此前理論和實踐之中總體上并不否認船票的存在,只是由于船票在包船模式下被隱形化,[10]導致旅客與承運人之間的海上旅客運輸合同關系未被充分認知。上海試點郵輪船票制度的核心目的之一正是確定船票的形式和簽發、使用等規則。如果登船憑證仍然不是船票,意味著船票的“顯形”仍未實現,將會導致船票制度的意義大為減損。質言之,政策與制度并非必然正確——凡事皆不可能絕對正確。但是,如果在缺乏充分依據的情況下貿然否定登船憑證的船票屬性,強行將原本單一的合同憑證拆分為船票和登船憑證,恐怕仍是弊多利少,實非理性而妥當的做法。
例如,《合同法》第293條規定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原則上自承運人向旅客交付船票時成立。如果船票的形式及其交付過程不能得以明確,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成立時間也將無從判斷。一旦郵輪開航前發生航程變更,旅客也就難以依據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向郵輪公司尋求救濟。此時上海試點郵輪船票制度維護各方合法權益的目的也將落空,導致郵輪旅游的法律關系重新陷入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