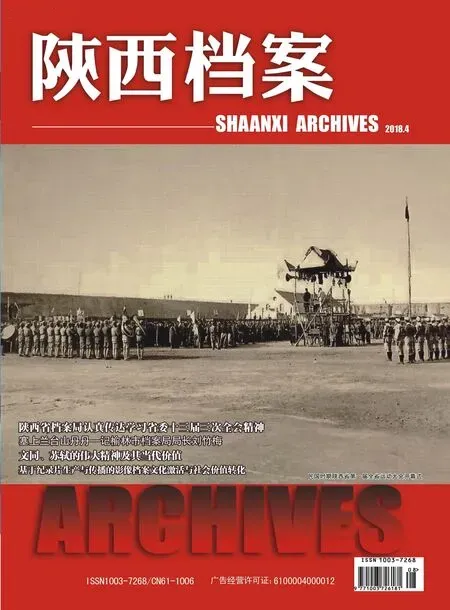“只因先主丁寧后,星落秋風五丈原”(終)
文/董燕翔

再看北戰。從建興六年至十二年,諸葛亮先后五次主動出擊魏軍,一次防守反擊。《三國演義》將其并稱為“六出祁山”。其中,最后一次出征,打到五丈原,距離長安最近。但天不假年,諸葛病死軍中,北戰旋即戛然而止。前后七年的戰爭,蜀軍左來右去,東征西討,歷盡艱辛卻寸土未得,“興復漢室”大業當然也就最終化為了泡影。
對于諸葛的北戰,千百年來,人們更多的都是為諸葛早喪、致使北伐中斷而嘆惋,也都為諸葛眾多的奇思妙計未竟全功而遺憾。杜甫就曾用一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高度概括了這種心態。只是,假如諸葛身體康健,北戰就真的能夠獲得成功么?未必然!
一為客觀條件不給力。三國之中,蜀國轄區最小,蜀地百姓數量也最少。據史載,劉禪投降時,蜀民共計二十八萬戶,九十四萬人。以這樣的基數考慮北戰,軍人數量必然有所牽制。我們粗略做個計算。將總人口簡單除二,除去婦女;再簡單將男性人口占五分之一的、已經喪失勞動能力和尚未具備勞動能力的垂垂老者與束發小生除去,則蜀國最多只有三十八萬壯丁。以當時生產力水平計,一位軍人至少要五個農民供養。如此,則蜀軍總數最多為八萬人。但事實是,蜀軍共有十萬人,外加官吏四萬人。可見,整個蜀國供養非生產人員總數幾乎超出可承受能力峰值的兩倍。這樣的社會比例構成,我們就不難理解,蜀地官府為何總要橫征暴斂、魚肉百姓;百姓為何又總要打破男耕女織的社會平衡,不分男女,也無論老幼,一起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了。當然,這其中,自然就會有人嘯聚山林,反抗苛捐雜稅。南中地區以及羌族所在地區常年民變蜂起,狼煙不絕,就是這種社會比例構成的直接后果。那么,以這樣的后方為基礎,諸葛又當如何使用兵力呢?基本對半而分。即維護地方治安占去一半兵力,真正的野戰部隊也僅僅只有五萬左右。反觀曹氏集團,占據整個北方,統轄人數包括在冊的與隱匿的,總計在千萬人以上,常備兵力也不低于七十萬。諸葛用五萬人與七十萬人對決,其難度當然不言自明。
二為戰略思路不連貫。從諸葛最初的戰略設想和后來的戰爭實踐來看,諸葛用兵,思路上不類相似,始終相悖,具有很大的矛盾性。這當然與形勢變化有關,或許也與諸葛本人戰略方向飄忽不定不無關系。
北戰的戰略思路最初源自《隆中對》。在該篇問對中,諸葛明確提出,劉備占據荊州、益州兩地后,如若北戰,可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劉備)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隆中問對時,劉備尚無一寸自有土地。這時,諸葛就能鋪陳后來的戰略構想,確屬不易。但這種構想只有啟蒙、鼓動成分,本身并不具有實際上的可操作性。其一,這種戰略構想附加的“天下有變”條件不成立。以弱敵強,期待敵國內亂、敵將無能當然最好。但終諸葛之世,兩種情況并未發生。從諸葛的角度看,這當然很遺憾。然而,實際上,即便這一附加條件在諸葛在世時就已真實出現,情況也不會好到哪去。因為,這一戰略構想以荊州、益州為戰略支撐點,去設想蜀魏兩國的前景,卻忽略了第三國——東吳自身的利益訴求。荊州之地,自古以來為兵家所必爭。諸葛占據,自然可以謀天下。但殊不知,位居荊州東面的東吳君臣同樣也知道它的戰略意義。東吳謀士魯肅就曾說:“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在東吳君臣看來,要想謀求霸業,首先也必須占據荊州。此時,無論是蜀還是魏,誰占據荊州,誰就是孫權成就帝王的羈絆,當然也就是東吳的敵人。諸葛的籌劃,僅以吳蜀交好為前提,以為“外結好孫權”就萬事大吉了,并未料到吳國君臣自己固有的戰略籌謀,更不知此時螳螂捕蟬,黃雀早已在其身后了。之后的蜀將關羽北出,與魏軍征戰。東吳則趁機偷襲荊州,并最終占有這片地區,就充分印證了這一點。其二,分兵擊敵、且不分主次,犯了兵家大忌。《孫子兵法》作為一種戰略兵書,一直強調集中優勢兵力與敵交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向來被看做基本的用兵之法。即使敵我力量相當,也要“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應當說,孫子所述,均為戰爭中一般意義上的戰略戰術原則,早已被古今戰爭所采信。而諸葛用兵,恰與其相反。本身兵少(加上荊州之兵也不過杯水車薪),使用起來原本就捉襟見肘,卻偏要兩路出兵,分散出擊。而兩路之間,又崇山阻隔,信息不暢。既無法調度兵員,也缺少戰略呼應。這與各自出征、各自為戰又有何異?況且,既是兩路出兵,當然要區分主攻、助攻。從地理上看,荊州距離魏國都城許昌較近,從兵貴神速的意義上講,荊州作為主攻方向更為合適。但諸葛卻讓一上將由此率隊出征,主帥劉備同時負責攻擊偏遠的秦川。如此平行用兵,又焉有勝算?
諸葛秉政后,荊州已經丟失。《隆中對》所述的戰略構想當然也就無疾而終。接下來,諸葛要想北戰,繼續恢復漢室,就必須拿出新的作戰方案。從當時形勢看,沿長江東下作戰,需經過東吳轄區,顯然已不可取。剩下的唯一路線,就是北征。由漢中出發,奪取長安后東向,劍指許昌。由此,則奪取長安城就必然成為建立戰略支撐點的首選。但奇怪的是,諸葛五次出征,其進攻方向或祁山、或陳倉、或武都、或斜口,非常凌亂,毫無章法,似乎根本就未考慮過占有長安城。我們看《三國演義》中諸葛是怎樣解釋這個問題的:諸葛部下對反復用兵祁山非常不解,曾問道,奪取長安,有很多道路,為什么非要選擇走祁山這條路線呢。諸葛答道,“祁山乃長安之首也。……先取此,得地利也”。因為便于作戰,所以選擇攻取此地。言下之意就是長安城池堅固,不易攻取,沒有地理優勢,所以不予考慮。這分明已成搪塞之詞,眾將如何能服?魏延就常常“謂(諸葛)亮為怯”,害怕攻堅克難。認為如此用兵,何時才能打到許昌。殊不知,此時的諸葛,戰略構想已經游移:能順利實施隆中策略最好;即使無法實現,攻取祁山也“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即趁機擴大一點地盤,同樣可以不枉此行。但由此一來,與恢復漢室、還于舊都的根本大業設想也就漸行漸遠了。
三為用兵方式不科學。按照孫子所說,戰爭計略分為奇正兩術。正兵可以理解為規范式作戰,而奇兵則“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諸葛用兵,因其性格所致,所以處處以正為先。唐代軍事家李靖就說,“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諸葛南征使用正兵,當然毫無問題。畢竟南中叛亂,蟊賊大都龜縮在山洞之中。大軍壓境如泰山壓頂,又何須用奇?北戰則不同。以少敵多,以弱敵強,如果繼續循規蹈矩,步步為營,則無異于以卵擊石。很不幸,諸葛仍舊“無他道”,還是使用正兵作戰。那么,諸葛使用正兵的方法是什么呢,兩點:一為制軍,二為制陣。先說制軍。制軍就是強化紀律,上下一體。在諸葛看來,“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就是說,軍隊將領有無能力并不重要。只要整個軍隊軍紀嚴明,令行禁止,就會無往而不利。但真實情況是這樣么?我們先看一例“有制之兵”的結果。諸葛手下有一位將軍名叫向寵。此人“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又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屬于治軍有方的典范,《出師表》中還專門表彰過他。有一年,漢嘉蠻夷叛亂。向寵親自率軍前往鎮壓。結果在混戰之中被殺,圍剿叛軍之事旋即告敗。這樣一個品性善良的人,帶著“有制之兵”前去平叛,最終卻身首異處,客死他鄉。由此,還能說“有制之兵”“不可敗”么。我們再看“無制之兵”的效果。漢代有一位將軍名叫李廣,鎮守邊關二十余年。他的治軍風格非常別致:部隊行軍走路松松垮垮,走到有水草的地方便隨意安歇。一旦休息,就“人人自便”,各行其是。甚至連崗哨都不設置。這樣的將軍如果放在諸葛手下,怕是早已斬首示眾了。但李廣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威震漠北,被匈奴稱作“飛將軍”。各支匈奴部隊只要聽到李廣的名聲,都唯恐避之不及。如此,你又能說,這種“無制之兵”“不可勝”么。事實上,“有制之兵”只是戰爭獲勝的一種因素,不可能涵蓋整個戰爭所有的致勝條件,更無法取代戰爭中將軍應起的作用。過分強調制兵的作用,只能是缺少用奇的一種無奈而已。
再看制陣。戰前排兵布陣,這是使用正兵與敵交戰的基本方法。對此,諸葛深諳其道。他在借鑒古人布陣的基礎上,推演出著名的八陣圖。他的對手司馬懿在看到八陣圖后,曾脫口說出“(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也”。由此,八陣圖便蜚聲天下,一舉走紅。后世更將其神話,作為與敵交戰的制勝法寶。《三國演義》有一段專門描寫八陣圖的作戰效果:夷陵之戰,孫權大將陸遜獲勝后,乘勝追擊,準備徹底消滅劉備武裝。在離夔關不遠處,看到一股殺氣,沖天而起。原本以為遇到了蜀軍。但等上前看去,卻是橫七豎八的一堆亂石。有人告知說,這是諸葛入川時就排列好的,是一種陣勢。陸遜當然不信。但當他準備離開時,“忽然狂風大作,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涌,有如劍鼓之聲”。“(陸)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應該說,真要遇到這個陣勢,換做誰,都會嚇得七竅生煙了。杜甫也因此專門賦詩一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但可惜,這里的八陣圖功效只不過是一種文學渲染而已,如何當的真?那么,八陣圖究竟是什么呢。唐代李靖對其中的奧妙進行了解密。他說,所謂八陣圖,不過是利用八種不同形制的旗子,區分“隊伍之別”。就是說,只是區分隊伍的符號,用于整軍齊伍而已,并無作戰功效。“后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這才是從諸葛開始直到后世,一直被人們認為的神奇之法從無勝績記錄的真實原因。那么,面對強敵,諸葛為何不出奇兵,卻只以正兵迎戰?由于謹慎!當時就真的沒有出奇制勝之策么。當然不是。魏延就曾獻計,“欲請兵萬人,與(諸葛)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這就是著名的“子午谷奇謀”。但諸葛不同意。這一奇謀是否可行,至今還有爭論。但以小博大,以弱搏強,不出奇招、不用狠式是不足以戰勝敵方的。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而諸葛則恰恰缺少了這一素養。由此,即使諸葛身體康健,你還相信北戰會成功么?有趣的是,《三國演義》從火燒博望,到六出祁山,表現的都是諸葛大量的奇招、陰招、怪招、險招,用以說明諸葛計謀的出神入化,以彌補諸葛實際的不足。但,與實際對比,這不更感可笑么。史學家陳壽曾說:“然(諸葛)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這才真正是一語中的。
寫到這里,原本可以收筆了。只是還有一個小問題怕也應該有所評說。這就是,魏蜀爭鋒,雙方的前沿陣地就是漢中。謹慎一生的諸葛何以會將自己的塋冢置于險地呢?對此,大體有兩種說法。一為“門額大書昭烈廟,世人都道武侯祠”。因蜀中百姓都懷念諸葛,每當祭祀之日,大家都去祭奠諸葛,而忘掉了劉備。這讓劉禪情何以堪。有念及此,所以諸葛自請歸葬外埠。二為“生為興劉尊漢室;死猶護蜀葬軍山”。未定中原,心有不甘。寧愿死后利用余威震懾魏國,力保蜀國長盛不衰。應該說,兩種說法都表達了人們對諸葛忠貞的認定,也同時道出了人們對諸葛“龍驤虎視,包括四海”志向的崇敬。只是在我看來,或可還有另外一解。諸葛死后,劉禪明令不許官員前去吊喪。直到蜀國將要滅亡時,劉禪才同意為諸葛立廟。僅憑這些就可以看出,劉禪對“事無巨細,咸決于亮”早已心存不滿。諸葛焉得不知?葉落歸根固然符合封建禮數,如劉備病死永安,即歸葬成都。但聊補君臣嫌隙當更為時局需要。諸葛身后不回成都,寧愿身處漢中險地。內心苦衷,又有幾人知曉?(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