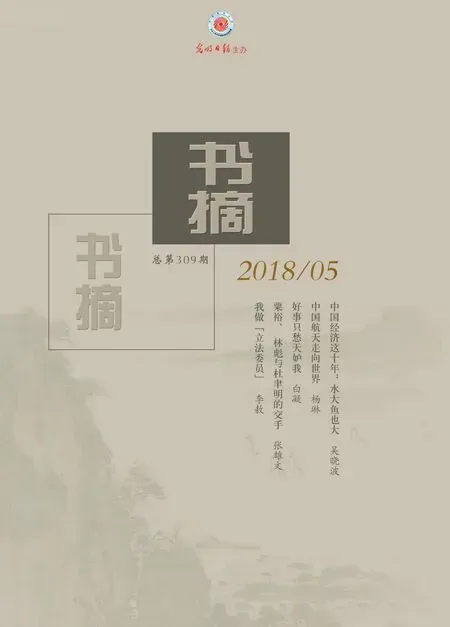書與讀書人
☉胡洪俠
燭光里的文化夢
姜德明《余時書話》中的代跋文中提到,“文化大革命”初起時,線裝書一夜之間由柜中珍藏的神品變成了心念“四舊”的罪證。可是,“當時在北京圖書館門前常有不留姓名、地址的公、私藏書家,趁著夜深人靜把線裝書成車地堆在那里”,讓書有個好去處,而“這在當時要冒一定風險”。冒著風險給書找個好去處,自己已經沒有了尊嚴而偏偏還想著讓書能體面地“活”下去,這是亂世中經常可以看到的文化風景。
動亂的火焰愈燒愈烈的時候,往往是文化燭光漸弱漸熄的時候。多虧了有那些盡全力維護書的尊嚴的人,文化才能夠薪火相傳。金耀基記述劍橋一個名叫臺維的書商,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學術之燈如風中殘燭,在劍橋,臺維先生決心使小小的火光保持不滅。那時,劍城幾乎沒有穿學袍的人在街上了,但他的書攤還是敞著,他的兩個店鋪還是開著。他使書顯出了尊嚴。”金耀基感嘆道:我們如要想建立文化的金殿,也需要像臺維先生這樣愛書、敬書,又喜歡把書的尊嚴、書的快樂帶給別人的書賈。
書籍本身擁有尊嚴。有書之尊嚴,才有文化之尊嚴,才有人之尊嚴。不把書視為有尊嚴的書,也就不會把人當成有尊嚴的人。所以秦始皇不僅焚書,還要坑儒;乾隆皇帝不僅要纂修“焚毀書目”,還要大興“文字獄”,該殺頭的殺頭,該流放的流放。文化人有時會夢想著“一言興邦”,但他們看到的,卻常常是“一言喪命”。
乾隆皇帝自然聰明得很,他似乎不欣賞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簡單了當,而愿意玩一種更為復雜的游戲:書既然禁不絕,燒不盡,那就修書;儒士們既然“玩”不完,殺不全,那就把他們組織起來,為自己“編”書。黃裳先生認為,“這就是《四庫全書》產生的背景”。這部大書的功過是非,學界似早有定論。我感興趣的是乾隆皇帝召集學者,令他們“聚集群書,暗暗改削,寫成‘定本’,頒示天下”(黃裳語),是對書的尊嚴的維護還是褻瀆?是文化的關懷,還是政治上的霸道與思想上的專制?
眼下《四庫全書》已開始續(xù)修了。據(jù)說,續(xù)修范圍中,包括恢復一部分因乾隆朝廷無視書的尊嚴而“致殘”的珍貴典籍的本來面目。這真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文化燭光風吹不熄,歷史總會存其真,去其偽,揚其名,閃其光,這大概是乾隆皇帝想不到的。
但是,一本書什么時候成為禁書,什么時候又被人奉若至寶,也實在說不大清楚,所以,“雪夜閉門讀禁書”也仍會是讀書人的一種樂趣。雪夜,閉門,肯定要燃起一點燭光的吧;書,能寫出來,印出來,又被禁,但又到了你手中,這便是書緣了;你在燭光里讀它,不啻圓了一個小小的夢想:向好書表示尊敬,以燭光傳遞薪火。
當然這個時候你也不會忘記,獻上一杯茶,向寫作、編輯、出版這些書的人表示敬意。
夢中的橋下并非總有銀子
李慶西先生的《禪外禪》,很是欣喜,自視為“忙中一樂”,可列入金圣嘆“豈不快哉”之列。此書是從前人筆記中選出些“自有窮理之妙處”的短小篇目,略加譯述,輔之點評,配以圖畫,讀起來頗能放松身心。但消遣之余,尤其碰到別有會心處,輕松也會得之即失,再求不得,仿佛進酒店吃飯,原本是為休閑而去,卻往往會因飯菜、茶酒、服務或席間的話題而生起氣來。
比如書中有三則涉及讀書人的故事,單賞或可哈哈一樂,合觀則覺意味深長。第一則故事講宋朝詩人“漢書下酒”的事:說蘇舜欽豪放好飲,讀書必以酒為伴,每夜須飲酒一斗。某夜讀《漢書·張良傳》,每讀至可驚可嘆可惜可贊處,必痛飲一杯。他的做大官的岳父看見后笑曰:“有這等下酒之物,一斗酒但怕不夠。”
第二則故事名為“書生販書”:謂明朝時,某書生甲忽動了“下海”之念,于是變賣家中薄業(yè)做本錢,馱運書籍往京城販售。途中遇書生乙。乙取書翻閱,愛不釋手,恨無錢購買,說自己家中有一堆舊銅器,可賣錢買書。甲因有古董雅癖,大喜,說,不必去賣錢,折價與我換書就是了。結果乙得書籍,甲得銅器,皆大歡喜,唯甲妻大怒:“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能作飯吃?”
第三則故事說清朝事:有一書生,有心趕考,無錢上路,夜做一夢。夢里遇仙人告知,“市街橋下有白銀二十兩,五更時分可前往覓取”。書生竊喜,依言行事,卻一無所獲。后又屢做此夢,無一應驗。一銀匠得知此事,想捉弄書生。某夜書生又起五更趕到橋下,果然找見二十兩銀子。銀匠一見,連連頓足:“我真是昏頭了!本想把鉛錫銅熔成銀錠模樣,耍弄你一下,不料陰錯陽差,把自己篋中的真銀子拿去化了。”悔嘆不已。

聯(lián)系起來看這三件事,頓時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嘆。“宋朝書生”以書下酒,雅興豪興俱佳,虧得老丈人有錢,一斗不夠,可再添一斗,書還能讀得下去。“明朝書生”的書就讀不下去了,轉為經商,可惜本性難移,賺了一堆舊銅器回來,惹得老婆斥罵。“清朝書生”更差了,既無岳丈供酒,也無薄業(yè)變賣,所剩只有美夢。那時的商人不及現(xiàn)在的精明,才有“捉雞不成”的事,否則,夢中仙子說的話也算不得數(shù)的。
聯(lián)想起近來時常聽到“讀書人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之類的話。如果這是讀書人的自我選擇,那很值得敬佩;如果是讀書人之間的相互鼓勵,那多半是以無奈為安慰,意思接近于“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如果是不讀書而富起來的人這樣要求讀書人,那就應了“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老話;如果這種清濁渾然一體的觀點竟是“風氣”在推波助瀾,那就只能證明多數(shù)人的目光投錯了方向:可能把落日當成朝陽了!
貧困、孤獨、逆境,確實造就過一些思想家,但它們扼殺了多少思想家又有誰說得清呢?讀書人致富自然很不容易,但脫貧總應該大加鼓勵。
“宋朝書生”的路雖然誘人,但不是一般人能碰得上的;“明朝書生”的路當然可以走,但不能走得太笨拙,先賺到錢填飽肚子再來照顧古董雅癖不遲;“清朝書生”的路也不是走不得,但不一定非要趕考,白天飽讀萬卷,自成世界,晚上悄入夢鄉(xiāng),與仙子同游仙境,也符合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精神世界的自我獨立生存”的目標。不過要小心,仙子送銀子的話經常信不得,老是起個大早趕到橋下終究不是個辦法:夢中的橋下哪里總會有銀子?